巴利经典中的佛陀生平
南传上座部佛法, 精选 ·Index
A Sketch of the Buddha’s Life - Readings from the Pali Canon
巴利经典中的佛陀生平 - 约翰·布列特 编 / 良稹 译 - 摘要
无论过去、现在,我讲的只是,苦与苦的止息——追随悉达多王子的足迹,从奢华的宫殿到艰苦的修行,直至证得无上觉醒,亲历佛陀不凡一生的关键时刻。
菩萨
先知阿西陀拜访新生王子
[佛历 -80]
先知阿西陀于日中禅境,看见了三十位喜庆的天神; 身著礼敬因陀罗的纯白,高举旗幡、纵声欢呼。
见天神如此喜气洋洋,行礼之后,他请问其因: “众天神何以如此欢喜?为何故旗幡挥舞摇曳?
即便与阿修罗那一战告捷,其时也未有过此番喧哗。 众天神何以如此欣喜,究竟是见到了何等奇迹?
他们欢呼、他们歌唱,奏演器乐、起舞击掌。 我请问住在须弥山顶的各位,快为我解惑吧,亲爱的天神!”
“至尊之宝、无上菩萨,为著人间的福利、人间的安乐, 已降生于释迦的兰毗尼城:这就是我们全体欢庆之因。
他是有情之最,人中之圣,是人中之公牛、人中之至尊, 在以先知为名的林中他将转起法轮,如征服众兽的强壮吼狮。”
阿西陀闻此速离天界,迳自前往净饭王宫。 落座后他问释迦族人:“王子何在?我也求一见。”
于是释迦人为先知展示王子,他如纯金一般熠熠生辉, 如巧匠于炉口锤炼成就,光华夺目、色泽完美。
见王子如火焰般闪射光华,皎洁如夜空平移的星群, 明亮如拨开秋云的太阳,先知阿西陀喜不自禁。
众天神在空中张起华盖,环饰千层、支辐无数, 金柄拂尘在上下飘动,持华盖拂尘者却隐而不现。
见男婴头悬白色华盖,如金饰展陈于红色羊毡, 这位名号暗光的虬发先知,满心喜悦、迎接王子。
大师他精通相术密语,热切接过释迦的公牛, 满怀自信大声宣说:“这是两足类之尊,至高无上。”
接著想起自己不久于人世,他黯然神伤、低首垂泪。 见先知哭泣,释迦人便问:“王子必定无不祥之兆?”
见释迦人多忧先知便答:“我预见王子不受伤害; 我预见王子安然无患;请放心,他绝非低微之辈。
这位王子将自触终极觉醒,他将自证无上清净, 慈悯众生,他将转起法轮,他的梵行之道将传遍四方。
然而我此生寿命无多,死亡将先于转法轮时, 无缘闻法于这位旷世尊者,正是我为何伤感痛惜。”
——Snp 3.11《经集》
年轻王子对优裕生活升起厌离
“我曾经过著优裕的生活,极度优裕、彻底优裕。我的父亲甚至在宫内造起莲池:一座盛开著红莲、一座盛开著白莲、一座盛开著蓝莲,皆为我而造。非来自波罗那斯的檀香我不用。我的头巾来自波罗那斯,我的外衣、下衣与斗蓬也来自波罗那斯。白天黑夜,有人在我的上方举著白色华盖,保护我不著寒暑与尘露。
“我曾经拥有三座宫殿:一座用于冷季、一座用于热季、一座用于雨季。雨季的四个月里,我住在雨宫,有歌舞伎人伴我娱乐,其中无一男子,我一次也不曾出宫。别家仆人、役工与家臣们吃豆汤与碎米,我父亲的仆人、役工与家臣们吃小麦、大米与肉。
“尽管我拥有如此福佑、如此优裕,我想到:‘未受教的凡夫,自己不免衰老、不能超越衰老,看见另一位老者,他惊骇、耻辱、厌恶,忘记自己也不免衰老、不能超越衰老。如果我——自己不免衰老、不能超越衰老——看见另一位老者,却惊骇、耻辱、厌恶,这对我是不合适的。’我注意到这一点时,年轻人对于青春特有的的沉醉感[青壮骄],便彻底消失了。
“尽管我拥有如此福佑、如此优裕,我想到:‘未受教的凡夫,自己不免患病,不能超越疾病,看见另一位病者,他惊骇、耻辱、厌恶,忘记自己也不免患病、不能超越疾病。如果我——自己不免患病、不能超越疾病——看见另一位病者,却惊骇、耻辱、厌恶,这对我是不合适的。’我注意到这一点时,无病者对于健康特有的沉醉感[无病骄],便彻底消失了。”
“尽管我拥有如此福佑、如此优裕,我想到:‘未受教的凡夫,自己不免死亡,不能超越死亡,看见另一位死者,他惊骇、耻辱、厌恶,忘记自己也不免死亡、不能超越死亡。如果我——自己不免死亡、不能超越死亡——看见另一位死者,却惊骇、耻辱、厌恶,这对我是不合适的。’我注意到这一点时,生者对于生命特有的沉醉感[生命骄],便彻底消失了。”
——AN 3.38《增支部》
二十九岁的年轻王子出家
[佛历 -51]
“在我觉悟之前,在我还是未觉悟的菩萨时,我想到:‘居家生活拥挤、是条多尘之道。出家生活开阔。在家梵行,不容易具足成就、具足清净、如磨光的珠贝。我何不剃除须发、身着袈裟,从在家到出家、成为沙门?’”
——MN 36《中部》
他的静谧光辉与念住为路人瞩目
他出家之后,戒以身作恶,离以言作恶,净化生活。 此后佛陀他前往王舍城,托钵于摩羯陀国的山堡,妙相具足。
立于宫楼上的频毗沙罗国王看见了他,见他妙相具足便说:“你们看! 此人何等俊美、端庄、纯净!前视一犁之距,举止何等完美!
垂目、念住,他不像出身低微者,这位比丘行往何处,快遣人探查。” 出遣的使者跟随其后:“这位比丘前往何处?他居于何处?”
善修自制、意守根门,念住、警觉,他沿户行走,不久钵满。 于是他,这位圣人,乞食后离城,往槃多婆山,“那是他的住地。”
御使们见他走向住地,于是三位坐待,一位回禀国王。 “陛下,那位比丘在槃多婆山坳里,如虎、如公牛、如狮子般安坐。”
——Snp 3.1《经集》
一位国王问你为何出家
尊贵的刹帝利国王,闻使者之言,立即乘御辇,前往槃多婆山。 在车道尽头他下车步行,到达后坐下。坐下后交换友好的问候,接著说:
“你年轻、少壮,正值青春初期,拥有刹帝利的体魄与肤色。 大军前锋之中、象骑阵营之内,你必定辉煌夺目。
我为你提供财富:享受它吧。 我欲知你的出身:请告诉我。”
“在前方的喜马拉雅山麓,陛下,有一个繁荣富庶的国家。 居民称拘萨罗人,部落称太阳,我出身的氏族名为释迦。
我出家离开该氏族,非为追求感官欲乐。 以五欲为危险,以出离为安稳,精进修行:那才是我心乐住之境。”
——Snp 3.1《经集》
佛陀很快超过了导师的成就
“为著探索善巧之道、为著追求无上宁静,出家后,我去见阿罗罗-迦罗摩,到达后对他说:‘迦罗摩贤友,我愿于此法此律中修行。’
“言毕,他对我答:‘贤友,你可以留下。于此法,智者藉由亲身实证自知,不久即能进入、安住[等同]于导师的智识。’
“我不久便学得此法之教义。仅于唇诵与复述层次,我可以讲知识之言、长老之言,我可以宣称我知我见——有他人也同样如此。
“我想:‘阿罗罗-迦罗摩非仅以信念宣称:“我藉由亲身实证自知,进入、安住此法。”他确实住于知见此法。’于是我去见他说:‘你宣称已进入、安住之此法,是何等程度?’言毕,他宣布说,是无所有处。
“我想:‘不仅阿罗罗-迦罗摩有信念、精进、正念、定力、智慧。我,也有信念、精进、正念、定力、智慧。阿罗罗-迦罗摩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我何不也努力自证。’于是不久,我很快进入、安住该法。我去见他说,‘阿罗罗贤友,你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这等程度么?’
“‘是的,贤友……’
“‘贤友,我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这等程度。’
“‘贤友,我们在梵行中有这样一位同伴,是我们的增益、是我们的大增益。那么说,我宣称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你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而你宣称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我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我了解的法正是你了解的法。你了解的法正是我了解的法。我达到的,你达到了;你达到的,我达到了。来吧,让我们一起领导这个团体。’
“如此,我的导师阿罗罗-迦罗摩,把我——他的学生——置于与他同等的地位,给予我崇高的敬意。但我想到:‘此法不趋向厌离、无欲、止息、寂静、智识、觉醒,也不趋向解脱(涅槃),只会重生于无所有处。’于是,对该法不满意,我离开了。
“为著探索善巧之道、为著追求无上宁静,我去找郁陀伽-罗摩弗,到达后对他说:‘郁陀伽贤友,我想于此法此律中修行。’
“言毕,他对我答道:‘贤友,你可以留下。于此法,智者藉由亲身实证自知之后,不久即能进入、安住于导师的智识。
“我不久便学得此法之教义。仅于唇诵与复述层次,我可以讲知识之言、长老之言,我可以宣称我知我见——有他人也同样如此。
“我想:‘罗摩非仅以信念宣称:“我藉由亲身实证自知,进入、安住此法。”他确实住于知见此法。’于是我去见他说:‘你宣称已进入、安住之此法,是何等程度?’言毕,他宣布说,是非想非非想处。
“我想:‘不仅罗摩有信念、精进、正念、定力、智慧。我,也有信念、精进、正念、定力、智慧。罗摩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我何不也努力自证。’于是不久,我很快进入、安住该法。我去见他说,‘郁陀伽贤友,你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这等程度么?’
“‘是的,贤友……’
“‘贤友,我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这等程度。’
“‘贤友,我们在梵行中有这样一位同伴,是我们的增益、是我们的大增益。那么说,罗摩宣称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你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而你宣称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罗摩亲身实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他了解的法正是你了解的法。你了解的法正是他了解的法。他达到的,你达到了;你达到的,他达到了。来吧,贤友,来领导这个团体。’
“如此,我的导师郁陀伽-罗摩弗,把我——他的学生——置于导师的地位,给予我崇高的敬意。但我想到:‘此法不趋向厌离、无欲、止息、寂静、智识、觉醒,也不趋向解脱[涅槃],只会重生于非想非非想处。’于是,对该法不满意,我离开了。”
——MN 36《中部》
他在森林里修极端苦行
“我想:‘我试修咬紧牙关、舌抵上颚,以觉知打压、强迫、征服心。’于是,咬紧牙关、舌抵上颚,我以觉知打压、强迫、征服心。如壮汉紧抓弱夫的头部、咽喉或肩部,打压、强迫、征服他,同样地,我以觉知打压、强迫、征服心。如此修时,汗水自腋下涌出。尽管在我内心,不倦的精进激起了、不乱的正念确立了,我的身体却因痛苦奋力而激荡、不得轻安。然而由此升起的痛感,并不侵住于心。
“我想:‘我试修止息禅定。’于是,我停止口、鼻的出入息。如此修时,呼啸之风自耳涌出,如呼啸之风自铁匠风炉涌出……于是,我停止口、鼻、耳的出入息。如此修时,有强力当头劈下,如壮汉以利剑劈开我的头部……剧痛在头部升起,如壮汉勒紧硬皮头箍……有强力剖解我的腹部,如屠夫或其学徒剖解牛腹……身体灼痛剧烈,如两个壮汉抓著一个弱夫的手臂在炭堆上炙烤。尽管在我内心,不倦的精进激起了、不乱的正念确立了,我的身体却因痛苦奋力而激荡、不得轻安。然而由此升起的痛感,并不侵住于心。
“有天神见到我时便说:‘沙门乔达摩死了。’又有天神说:‘他还未死,正在死去。’又有天神说:‘他既死了、又不曾死,他是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正是这般活着。’
“我想:‘我试修绝一切食。’却有天神来对我说:‘亲爱的尊者,请勿修绝一切食。你若绝食,我们会把天食注入你的毛孔,你会靠它们活下来。’我想:‘我若宣称完全绝食,其时天神们却在把天食注入我的毛孔,我是在妄语。’于是我说:‘停止,’要他们退下。
“我想:‘我试修一次只食少量,一餐只食一掬——大豆汤、小豆汤、野豆汤、或豌豆汤。’于是我一次只食少量,一餐只食一掬——大豆汤、小豆汤、野豆汤、或豌豆汤。我的身体极度憔悴。四肢如藤茎竹节,只因进食过少。背如驼蹄……椎骨突起如珠串……肋骨毕现,如朽仓毕现之椽木……眼神暗淡、眼窝深陷,如深井之水,微有其光……头皮皱缩,如青苦瓜受热风之皱缩……前腹紧贴后背,手摩腹部,触及脊背;手摩脊背,则触及腹皮……排尿排便时,我前扑倒地……我手摩肢体时,体毛因根部腐蚀,随之脱落,只因进食过少。
“有人见到我时便说:‘沙门乔达摩是黑人。’又有人说:‘沙门乔达摩不是黑人,是褐色人。’又有人说:‘沙门乔达摩非黑非褐,是金黄色人。’我过去肤色清净皎洁,如今衰褪至此,只因进食过少。
“我想:‘凡过往僧侣沙门苦修之剧痛、窒痛、锥痛,这已是极点,无有过之。凡未来僧侣沙门苦修之剧痛、窒痛、锥痛,这已是极点,将无过之。然而,以如此紧窒苦行,我仍不曾超越凡夫、修得圣者知见。可有另一条觉悟之路?’”
——MN 36《中部》
正视怖畏惊骇
“我曾居住于园中祠堂、林间神龛、树下灵祠等令人怖畏发指之地。居住期间,或有野兽近前,或有鸟折弃树枝,或有风吹落叶瑟瑟作声,其时我想:‘可是那怖畏惊骇迫来了?’接著又想:‘我何以一迳等候怖畏?我何不制服那怖畏惊骇,无论来者为何?’于是,在我经行时,怖畏惊骇迫来,我不站不坐不卧,继续经行,直到制服那怖畏惊骇。在我站立时,怖畏惊骇迫来,我不行不坐不卧,继续站立,直到制服那怖畏惊骇。在我端坐时,怖畏惊骇迫来,我不卧不站不行,继续端坐,直到制服那怖畏惊骇。在我横卧时,怖畏惊骇迫来,我不坐不站不行,继续横卧,直到制服那怖畏惊骇。”
——MN 4《中部》
摩罗来访
“比丘们,摩罗不休不止地在你们身边盘旋,[想着]‘或许我可以藉眼获得机会……或许我可以藉耳……鼻……舌……身获得机会。也许我可以藉识获得机会。’因此,比丘们,你们当善守根门。”
——SN 35.199《相应部》
我在尼连禅河边,决意精勤,为成就解脱之安稳,勤修禅那。
纳摩支前来,道以同情:“你灰败枯藁,死期将近; 死亡已取走千分,你命悬一分。活下去吧,活著你可以善修福德。 梵行、火供将有多少福德,你何须如此一意精进? 精进之道难行、难为又难持。”口说此偈,摩罗立于佛陀身前。
对摩罗此言,世尊作答:“无慎之辈,邪恶者,无论你来此何意: 我不需要哪怕丝毫福德,摩罗只配与求福德者交谈。 我有的是信念、刻苦、持恒、智慧,决意至此,你为何劝我活著? 此风能把河流烤干,我决意时,血焉能不干? 胆汁、粘液随血干涸,肌肉消损,心愈清明,念、慧、定愈坚强。 住此证得终极之受,于感官之乐心无欲求。看吧:他清净如此! 感官之欲是你的先头军,第二支军为不满,第三军为饥渴,第四军称作贪爱, 第五军名为昏睡,第六军为畏惧,第七军称作迟疑,你的第八军是虚伪与顽固。 以不当手段获取利益、供养、名声、地位,褒扬自我,贬低他人。 那就是你的军队,纳摩支,是你这黑暗者的强兵。懦夫抵挡不了你,胜者将得到至乐。 我是携孟加草之辈么?我唾弃性命,宁可战死,决不败中苟活。 有僧侣沙门覆没于此处,他们不了解善修者之道。 旌旗浩荡,摩罗率兵乘骑而来,我挺身迎战,愿他们不能动撼我的阵地。 天神征服不了你的军队,我会以智慧摧毁它,如以石击毁未焙的泥罐。
我决心已定,念住已立,我将游方各国,教诲弟子, 听从我的教导,他们审慎、坚定,无视你的希冀,将到达无忧之境。”
摩罗满怀悲哀,琵琶自胁下跌落,这个垂头丧气的生灵,就地消失不见。
——Snp 3.2《经集》
他放弃苦行
“我想到:‘记得有一次,我父亲释迦正行公事,我坐于凉爽的阎浮树荫下,接著——远离感官之欲、远离不善巧心态——我进入、安住于初禅:由远离而生起了喜与乐、伴随著寻想与评量。那可是觉悟之道?’随著该忆念,我意识到:‘那是觉悟之道。’我想:‘我为何畏惧无关乎感官之欲、无关乎非善巧素质的那种喜乐?’我想:‘我不再畏惧无关乎感官之欲、无关乎非善巧素质的那种喜乐,不过身体如此极度憔悴,是不易达到那种喜乐的。我何不进摄些实食——米饭与粥汤。’于是我进摄实食——米饭与粥汤。有五比丘一向事奉我,想着:‘我们的沙门乔达摩若证得某个高等境界,会传与我们。’然而,当他们见我进摄实食——米饭与粥汤时,便厌恶地离我而去,心想:‘沙门乔达摩生活奢侈。他舍弃精进,退堕于奢溢。’
“于是,在进摄实食、恢复体力之后——远离感官之欲、远离不善巧心态——我进入、安住于初禅:由远离而生起喜与乐、伴随著寻想与评量。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随著寻想与评估的平息,我进入、安住于第二禅;由定而生起喜与乐,内心笃定,心念专一。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随著喜的消退,我安住于舍,具念、觉知,身体感到安乐。我进入、安住于第三禅,对此圣者们宣告:‘舍、念、乐住。’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随著乐与苦的舍离——如先前喜与忧的消退一般——我进入、安住于第四禅:舍念清净,不苦不乐。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
——MN 36《中部》
觉醒
[佛历 -45]
他找到中道
“比丘们,有此两极端,出家者不可耽于其中——哪两极?于感官对象,追求感官之乐:是低级、粗鄙、庸俗、非圣、无益的;追求自虐:是痛苦、非圣、无益的。比丘们,避此两极端,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
八正道
“比丘们,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者——是什么?正是此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比丘们,此为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
——SN 56.11《相应部》
他洞悉三智
“当心这般入定、纯净、明亮、无瑕、无染、柔韧、可塑、稳定、不动摇时,我将它朝向宿命通。我回顾过去无量生命:一生、二生……五生、十生……五十、一百、一千、十万、多少宇宙成劫、多少宇宙坏劫、多少宇宙成坏劫:‘在彼处我名为何、族姓为何、容貌为何。我的食物为何、我的苦乐经验为何、我的寿终为何。从该境界死去后,我重生于此处。在此处,我又名为何、族姓为何、容貌为何。我的食物为何、我的苦乐经验为何、我的寿终为何。从该境界死去后,我重生于此。’如此,我回忆著宿世的形式与细节。
“这是那一夜初更里我证得的第一明。对一位审慎、精勤、决意者,无明摧毁、明生起;黑暗摧毁、光明生起。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
“当心这般入定、纯净、明亮、无瑕、无染、柔韧、可塑、稳定、不动摇时,我将它朝向天眼通。我以清净、超人的天眼,察看有情的死亡与重生,了知他们如何各随其业,有尊卑、美丑、福祸:‘这些有情——具足身、语、意的恶行,辱骂圣者,持邪见、依邪见之影响而行动——身坏命终时,生于恶趣、恶道、堕处、地狱。然而,这些有情——具足身、语、意的善行,不曾辱骂圣者,持正见,依正见之影响而行动——身坏命终时,生于善趣、天界。’如此,我以清净、超人的天眼,察看有情的死亡与重生,了知他们如何各随其业,有尊卑、美丑、福祸。
“这是那一夜中更里我证得的第二明。对一位审慎、精勤、决意者,无明摧毁、明生起;黑暗摧毁、光明生起。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
“当心这般入定、纯净、明亮、无瑕、无染、柔韧、可塑、稳定、不动摇时,我将它朝向漏尽通。我如实了知:‘此为苦……此为苦之集……此为苦之灭……此为趣向苦灭之道……此为漏……此为漏之集……此为漏之灭……此为趣向漏灭之道。’如此知、如此见,我的心即从欲漏中解脱、从有漏中解脱、从无明漏中解脱。解脱之时,生起‘已解脱’之智。我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这是那一夜后更里我证得的第三明。对一位审慎、精勤、决意者,无明摧毁、明生起;黑暗摧毁、光明生起。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
——MN 36《中部》
无上觉醒
为追求造屋者, 我游荡于多少轮重生, 无所得,苦无尽, 再生之苦,一次次。
造屋者,你已被看穿! 你再也不能造屋。 你的椽条已断,栋梁已摧, 心已证无为,渴爱已尽。
——Dhp 153-154《法句经》
他成为如来
“如来对世间已彻底觉悟。如来已脱离世间。如来对世间之起源已彻底觉悟。如来对世间之止息已彻底觉悟。如来已实现了世间的止息。如来对趣向世间止息之道已彻底觉悟。如来已培育了趣向世间止息之道。”
“凡此世间一切——与其天神、摩罗、梵天、世代的沙门、婆罗门、王子、平民——如来已见、已闻、已感受、已认知、已达到、已证得、已用心思索、对之彻底觉悟。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从如来(Tathagata)彻底觉醒、达到正自觉醒之夜起,直到他彻底涅槃、达到无余涅槃那夜为止,凡如来所言、所论、所释,皆如是(tatha)无他[真实无偏]。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如来是行如(tathā)其所言教者,是言教如其所行者。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在此世间——有其天神、摩罗、梵天、世代的沙门、婆罗门、王子、平民——如来乃是不可征服的征服者、见一切者、大神通力者。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Iti 112《如是语》
觉醒之后
佛陀探索因果缘起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新近自证觉醒,住于优楼毗罗村尼连禅河边的菩提树荫下;他在菩提树荫下连坐七日,感受著解脱的喜乐。七日末出该定境,在后夜里,密切专注正序与倒序的缘起过程,即:
有此,则有彼, 此生,则彼生。 无此,则无彼, 此灭,则彼灭。
换言之:
缘无明,有行。缘行,有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处。缘六处,有触。缘触,有受。缘受,有爱。缘爱,有取。缘取,有有。缘有,有生。缘生,则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生。如此,这整大堆苦聚集起。
接下来,从无明无余褪去、止息,则行止息。缘行止息,则识止息。缘识止息,则名色止息。缘名色止息,则六处止息。缘六处止息,则触止息。缘触止息,则受止息。缘受止息,则爱止息。缘爱止息,则取止息。缘取止息,则有止息。缘有止息,则生止息。缘生止息,则老、死、愁、悲、苦、忧、恼全部止息。如此,这整大堆苦止息。
接著,意识到那件事的重要性,世尊当时大声道:
“当诸法对精勤禅修的 婆罗门显现时, 他的一切疑惑皆消逝, 因他了知诸法及其因。”
——Ud 1.1《自说经》
他想我应敬谁为师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新近自证觉醒,住于优楼毗罗村尼连禅河边羊倌的榕树脚下。在他独自独处时,觉知中升起此念:“人若无所崇敬、依止,则会有苦。那么有哪位沙门、婆罗门,我可以依止、崇敬、尊敬他?”
接著,他想到:“我若依止另一位沙门、婆罗门,崇敬、尊敬他,将是为著完善一个尚未完善的戒蕴。然而,在这个有天神、摩罗、梵天、世代的沙门、婆罗门、王族、平民的世间,我见不到另一位沙门、婆罗门,比我更有具足的戒德,使我得以依止、崇敬、尊敬他。
“我若依止另一位沙门、婆罗门,崇敬、尊敬他,将是为著完善一个尚未完善的定蕴……
“我若依止另一位沙门、婆罗门,崇敬、尊敬他,将是为著完善一个尚未完善的慧蕴……
“我若依止另一位沙门、婆罗门,崇敬、尊敬他,将是为著完善一个尚未完善的解脱蕴……
“我若依止另一位沙门、婆罗门,崇敬、尊敬他,将是为著完善一个尚未完善的解脱知见蕴。然而,在这个有天神、摩罗、梵天、世代的沙门、婆罗门、王族、平民的世间,我见不到另一位沙门、婆罗门,比我更有具足的解脱知见,使我得以依止、崇敬、尊敬他。
“我何不依止我完全觉悟的此法,崇敬、尊敬它?”
此时,梵天娑婆主以自己的觉知,识得世尊觉知中的此念——如壮汉伸臂、曲臂一般——消失于梵天界,出现在世尊面前。他整理上衣袒露一肩、合掌于心前向世尊施礼,对他说:“正是如此,世尊!正是如此,善逝者!过去那些阿罗汉、正自觉醒者——他们也正是依止此法本身,崇敬、尊敬它。未来那些阿罗汉、正自觉醒者——他们也将依止此法本身,崇敬、尊敬它。请世尊,当世的阿罗汉、正自觉醒者,也依止此法本身,崇敬、尊敬它吧。”
——SN 6.2《相应部》
他想我是否传法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新近自证觉醒,住于优楼毗罗村尼连禅河边羊倌的榕树脚下。在他独自独处时,觉知中升起此念:“我所证此法,深刻、难见、难解、寂静、崇高、超越寻思、微妙、唯智者能知。然而,这一代[有情]乐于执取、耽于执取、喜于执取。对乐于执取、耽于执取、喜于执取的一代来说,见此缘起之理,则难矣。见此境界——即:一切行之止息、一切依之舍离、爱之灭尽、离欲、灭、涅槃——亦难矣。我若传授此法,若他人不能领悟,将于我徒劳、于我困扰。”
其时,世尊想到这段以往未言、未闻的偈句:
“我艰辛作证,何须今宣说? 为贪嗔所困者,此法不易悟。
“此法逆流而行,微妙、甚深、难见, 耽于欲乐、为无明暗所覆者,不能得见。”
随著世尊如此思惟,其心倾向于安住,无意传法。
此时,梵天娑婆主以自己的觉知,识得世尊觉知中的此念,想道:“世界即将毁灭!世界即将消亡!如来、阿罗汉、正自觉醒者的心倾向于安住,无意传法!”于是——如壮汉伸臂、曲臂一般——梵天娑婆主从梵天界消失,出现在世尊面前。他整理上衣袒露一肩、右膝着地,合掌于心前,向世尊施礼,对他说:“世尊,请世尊传法!请善逝者传法!有情之中,有眼内仅存些许尘垢者,因未闻法,正在衰退。将有能解法义者。”
……理解了梵天的恳请,出于对有情的慈悲,世尊于是以佛眼观世间。如此观时,他看见了有情之中那些眼内少尘者与多尘者、利根者与钝根者、善相者与恶相者、易教者与难教者,他们当中有的视来世之罪与险为畏途。犹如在青莲、红莲、白莲池中,有些莲花——生于水中,长于水中——未出水面,沉于水中生长;有些莲花则立于水面;有些则伸出水面,不为水所沾染——同样地,世尊以佛眼观世间。如此观时,他看见了有情之中那些眼内少尘者与多尘者、利根者与钝根者、善相者与恶相者、易教者与难教者,他们当中有的视来世之罪与险为畏途。
……梵天娑婆主心想:“世尊已允传法,”于是对世尊顶礼、右绕后,就地消失。
——SN 6.1《相应部》
他想我先传法予谁
“我想:‘我应先向谁传法?谁将迅速领悟此法?’接著我想到:‘这阿罗罗-迦罗摩有智慧、卓越、聪颖。长久以来他的眼内仅有些许尘垢。我何不先向他传法?他将迅速领悟此法。’其时,有天神来对我说:‘世尊,阿罗罗-迦罗摩七日前已逝。’我内心升起知见:‘阿罗罗-迦摩罗七日前已逝。’我想:‘阿罗罗-迦罗摩损失甚巨。他若听闻此法,本可迅速领悟。’
“我想:‘我应先向谁传法?谁将迅速领悟此法?’接著我想到:‘这郁陀伽-罗摩弗有智慧、卓越、聪颖。长久以来他的眼内仅有些许尘垢。我何不先向他传法?他将迅速领悟此法。’其时,有天神来对我说:‘世尊,郁陀伽-罗摩弗昨夜已逝。’我内心升起知见:‘郁陀伽-罗摩弗昨夜已逝。’我想:‘郁陀伽-罗摩弗损失甚巨。他若听闻此法,本可迅速领悟。’
“我想:‘我应先向谁传法?谁将迅速领悟此法?’接著我想到:‘在我精进苦修之时,那五比丘曾事奉于我、饶益于我。我何不先向他们传法?’接著我想:‘那五比丘今居何处?’我以清净、超人的天眼,看见他们住于波罗那斯仙人堕处的鹿野苑。
“于是,在优楼毗罗住够后,我出发游方,渐次往波罗那斯行去。邪命外道郁婆迦在伽耶与觉醒地之间的路上看见我,看见时,他对我说:‘贤友,你诸根清澈、肤色纯净光洁。你从谁出家?谁是你的导师?你信奉谁的法?’
“言毕,我对邪命外道郁婆迦答以此偈:
“‘我已征服一切,了知一切, 于一切法皆不染,舍弃一切, 爱尽而解脱: 自证圆满,应称谁为师?
我无师尊,亦无与我同等者; 于人天世界,无有能匹敌。
我是世间阿罗汉,是无上导师, 我独自圆满觉醒,清凉、寂灭。
我将往迦尸城,转动法轮, 在盲目的世间,击响不死之鼓。’
“‘贤友,据你所言,你必定是位无上胜者。’
“‘胜者如我,已证诸漏灭尽。 我已降伏恶法,故郁婆迦,我是胜者。’”
“言毕,郁婆迦说:‘贤友,愿你如此。’——他摇摇头,走上旁道,离去了。
“接著,我渐次游方,到达波罗那斯仙人堕处的鹿野苑,来到五比丘居住地。他们看见我从远处走来,看见后,相互约定说:‘贤友们,沙门乔达摩来了:他生活奢侈、舍弃精进、退堕于奢溢。他不值得顶礼、站立迎接、或接其衣钵。不过仍可敷座,他若愿意,可以坐下。’然而,我走近时,他们不能够自守其约。一位起立恭迎、接过我的衣钵;一位敷座;另一位备洗足水。然而他们直呼我名,并称我为‘贤友’。
“于是我对他们说:‘比丘们,勿对如来直呼其名,或称其为“贤友”。比丘们,如来是阿罗汉、正自觉醒者。比丘们,注意听:不死之法已证得。我将教导你们,我将为你们说法。依法修行,你们不久即会证得、安住于梵行生活的无上目标——善男子为此离俗而出家——于现法中自知、亲证、成就。’
“言毕,五比丘答:‘贤友乔达摩,以那等行持、那等作为、那等苦行,你都未曾证得任何超人境界、任何堪称圣者的殊胜知见。那么你如今——生活奢侈、舍弃精进、退堕于奢溢——又如何能证得任何超人境界、任何堪称圣者的殊胜知见?’
“言毕,我对他们答道:‘比丘们,如来并未生活奢侈、并未舍弃精进、并未退堕于奢溢。比丘们,注意听:不死之法已证得。我将教导你们,我将为你们说法。依法修行,你们不久即会证得、安住于梵行生活的无上目标——善男子为此离俗而出家——于现法中自知、亲证、成就。’
“第二次……第三次,五比丘对我说:‘贤友乔达摩,以那等行持、那等作为、那等苦行,你都未曾证得任何超人境界、任何堪称圣者的殊胜知见。那么你如今——生活奢侈、舍弃精进、退堕于奢溢——又如何能证得任何超人境界、任何堪称圣者的殊胜知见?’
“言毕,我对五比丘答道:‘比丘们,你们可曾记得我过去曾以此种方式说话?’
“‘尊者,未曾。’
“‘比丘们,如来并未生活奢侈、并未舍弃精进、并未退堕于奢溢。比丘们,注意听:不死之法已证得。我将教导你们,我将为你们说法。依法修行,你们不久即会证得、安住于梵行生活的无上目标——善男子为此离俗而出家——于现法中自知、亲证、成就。’
“如此我说服了他们。”
——MN 26《中部》
转法轮
佛陀对五名苦行沙门的初次说法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波罗那斯仙人堕处的鹿野苑。在那里,世尊对五比丘说:
“比丘们,有此两极端,出家者不可耽于其中——哪两极?于感官对象,追求感官之乐:是低级、粗鄙、庸俗、非圣、无益的;追求自虐:是痛苦、非圣、无益的。比丘们,避此两极端,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
八正道
“比丘们,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者——是什么?正是此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比丘们,此为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
四圣谛
“比丘们,此为苦圣谛: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愁、悲、苦、忧、恼是苦;与不爱者共处是苦、与爱者别离是苦、所求不得是苦:简言之,五取蕴是苦。
“比丘们,此为苦集圣谛:[苦因是:]导致再生的渴爱——伴随着喜与贪、于处处耽享——即是:欲爱、有爱、无有爱。
“比丘们,此为苦灭圣谛:对该渴爱的无余离贪、息灭、舍离、弃绝、解脱、无染。
“比丘们,这是趣向苦灭之道圣谛:正是这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对于四圣谛的责任
“‘此为苦圣谛’:比丘们,对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生。‘此苦圣谛应遍知’……‘此苦圣谛已遍知’。
“‘此为苦集圣谛’:比丘们,对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生。‘此苦集圣谛应断除’……‘此苦集圣谛已断除’。
“‘此为苦灭圣谛’:比丘们,对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生。‘此苦灭圣谛应作证’……‘此苦灭圣谛已作证’。
“‘此为趣向苦灭之道圣谛’:比丘们,对于这前所未聞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生。‘此趣向苦灭之道圣谛应修习’……‘此趣向苦灭之道圣谛已修习’。
十二行相法轮
“比丘们,只要我对此四圣谛之三转十二行相的如实知见尚不纯净,比丘们,我未在有天神、摩罗、梵天、沙门、婆罗门、王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我已证得无上正自觉醒。然而,一旦我对此四圣谛之三转十二行相的如实知见真正纯净,比丘们,我即在有天神、摩罗、梵天、沙门、婆罗门、王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我已证得无上正自觉醒。我内心生起此知见:‘我的解脱不可动摇。此为最后一生。今不再有生。’”
圣僧团的诞生
此为世尊所说。五比丘对世尊之说心悦、随喜。在此解说期间,尊者乔陈如生起了无尘、无垢的法眼:“凡是集法,皆是灭法。”
法轮转起
世尊转法轮之际,地居天人大呼:“在波罗那斯仙人堕处的鹿野苑,世尊转起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或世间任何者,皆不能阻止。”闻地居天人之呼声,四大王天人大呼……三十三天的天神……夜摩天的天神……兜率天的天神……化乐天的天神……他化自在天的天神……梵众天人大呼:“在波罗那斯仙人堕处的鹿野苑,世尊转起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或世间任何者,皆不能阻止。”
于是,那时刻、那瞬间,呼声直达梵天界。此十千世界在震动、颤动、抖动,一道无量大光明出现在宇宙间,胜于诸天神之威力。
其时,世尊大声道:“乔陈如真了悟了!乔陈如真了悟了!”故此,尊者乔陈如得名:阿若-乔陈如[了悟的乔陈如]。
——SN 56.11《相应部》
第二次说法有关无我此后世间有了六位阿罗汉
“因此,比丘们,一切色,无论属于过去、未来、当下;内在、外在;粗糙、细微;低劣、殊胜;远、近:必须以正慧如实看待:‘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
“一切受……
“一切想……
“一切行……
“一切识,无论属于过去、未来、当下;内在、外在;粗糙、细微;低劣、殊胜;远、近:必须以正慧如实看待:‘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
“如此看待时,圣者的多闻弟子便厌离于色、厌离于受、厌离于想、厌离于行、厌离于识。因厌离而离欲。因离欲而解脱。于解脱中,生起‘已解脱’之智。他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那就是世尊所说。比丘们对他的话心悦、随喜。并且在这段讲解进行期间,五位比丘的心,由无所执取,从诸漏中解脱。
——SN 22.59《相应部》
佛陀与阿罗汉的区别
[佛陀:]“那么,一位正自觉醒者与一位慧解脱的比丘之间,有何等不同、何等差异、何等区别?”
[一群比丘:]“世尊,对我们来说,教法以世尊为根本、为导师、为依归。善哉世尊若能亲自解说其义。听闻世尊之言,比丘们将会受持。”
“既如此,比丘们,注意听,我来解说。”
比丘们答:“世尊,是的。”
世尊说:“如来——阿罗汉、正自觉醒者——是未生起之道的生起者、未生出之道的产生者、未宣说之道的宣说者。他知晓道、洞见道、善于道。他的弟子们,如今是道的追随者,随他之后而成就。”
“一位正自觉醒者与一位慧解脱的比丘之间,正是有这等不同、这等差异、这等区别。”
——SN 22.58《相应部》
四十五年的教化
他的教导一贯实用包括了基本的礼仪
“一位比丘如何才算通晓聚会?在此,一位比丘了解聚会:‘这是刹帝利聚会;这是婆罗门聚会;这是居士聚会;这是沙门聚会;在这里,我应该这样接近他们、这样站、这样做、这样坐、这样说、这样沉默。’他若是不了解这些聚会,就不能说他通晓聚会。正因为他的确了解这些聚会,才能说他通晓聚会。这才是一位通晓法、通晓义、通晓自己、通晓节制、通晓时间、通晓聚会的人。”
——AN 7.64《增支部》
如何对待父母
奉养父母、 照顾妻儿、 行事周全: 这是至上的吉祥。
——Snp 2.4《经集》
母亲与父亲,慈悯其家人, 被称为梵天、古时之师, 值得子女供养。
因此智者应当礼敬他们, 以饮食、衣物、卧具供养, 为他们涂油、沐浴、洗足。
智者如此奉养父母, 于今生受赞誉, 死后在天界享乐。
——Iti 106《如是语》
布施的价值
“何为布施的宝藏?在此,一位圣弟子,心离悭吝之垢,住于家中、慷慨、乐于布施、有求必应、乐于分享。此谓布施的宝藏。”
——AN 7.6《增支部》
戒德的价值
“何为戒德的宝藏?在此,一位圣弟子,戒杀生、戒不与取、戒邪淫、戒妄语、戒导致放逸的酒与麻醉品。比丘们,此谓戒德的宝藏。”
——AN 7.6《增支部》
操行端正的果报
具足正直的身、语、意, 此世间有智慧、行福德者, 生命虽短, 身坏命终时,了知者往生天界。
——Iti 63《如是语》
一切感官欲乐甚至天界之乐的过患
“在此,某人自己不免于老,了知不免于老的过患后,去寻求那无上安稳、不老的涅槃。他自己不免于病,了知不免于病的过患后,去寻求那无上安稳、无病的涅槃。他自己不免于死,了知不免于死的过患后,去寻求那无上安稳、不死的涅槃。他自己不免于染污,了知不免于染污的过患后,去寻求那无上安稳、无染的涅槃。”
——AN 4.252《增支部》
出离的价值
“在看见了感官之乐的过患后,我探索该主题;在理解了出离的利益后,我亲证实修。我的心向于出离,视出离为安稳,充满信心、稳固、坚定。于是,远离感官之欲、远离不善巧的心态,我进入、安住于初禅:从远离中生起了喜与乐,伴随著寻与伺。”
——AN 9.41《增支部》
四圣谛
“比丘们,正是因为未能觉悟、未能洞见四圣谛,我与你们,才长久地流转于此生死轮回。哪四谛?是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趣向苦灭之道圣谛。但是比丘们,如今这些圣谛已经觉悟、洞见,有爱已被斩断,导向再生者已被摧毁,不再有后有。”
——DN 16《长部》
简言之佛陀教导了通往涅槃真正而持久之乐的道路
“有那么一个境界,其中无地、无水、无火、无风;无空无边处、无识无边处、无无所有处、无非想非非想处;无此世、无他世、无日、无月。于此,我说,无来、无去、无住;无死、无生;无基础、无所缘、无依止。这,正是苦的终结。”
——Ud 8.1《自说经》
“无论过去、现在,我所教导的,只是苦与苦的止息。”
——SN 22.86《相应部》
佛陀举世无双他的声名传播开来
他坐下后,[卫兵目犍连]对尊者阿难说:“阿难大师,是否有一位比丘,在所有方面都与世尊乔达摩,阿罗汉、正自觉醒者完全相同?”
“不,婆罗门,没有任何一位比丘,在所有方面都与世尊,阿罗汉、正自觉醒者完全相同。因为世尊乃是未生起之道的生起者、未生出之道的产生者、未宣说之道的宣说者,是知晓道者、洞见道者、善于道者。他的弟子们,如今是道的追随者,随他之后而成就。”
——MN 108《中部》
“关于乔达摩尊者,流传著这样的美名:‘彼世尊是阿罗汉、正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他亲证此有天神、摩罗、梵天的世界,此有沙门、婆罗门、国王、人民的世代后,为众宣说;他教导的法,初善、中善、后善,义理圆满,文辞善巧;他阐明的梵行,完全圆满、清净。得见这样的阿罗汉是件善事。”
——MN 41《中部》
他四处游方向来自各种姓阶级各社会阶层的人们说法包括居士
“我记得曾前往几百次刹帝利聚会……几百次婆罗门聚会……几百次居士聚会……几百次沙门聚会……”
——MN 41《中部》
一时世尊住在舍卫城附近的祇树给孤独园。其时,如法优婆塞率五百优婆塞往诣世尊。近前后顶礼,坐于一边。坐下后,如法优婆塞对世尊说道……
——Snp 2.14《经集》
拘利族人长胫往诣世尊,到达时顶礼,坐于一边。坐下后对世尊说:“我们身为居士,享受感官之乐、生活于妻儿之间、享用迦尸国布料与檀香、配戴花环、香水、油膏、受用金银。愿世尊对我们这些人传法,使我们今生得安乐,来世也得安乐。”
[世尊说:]“虎爪,这四种法,能使居士今生得安乐。哪四种?具足精勤、具足守护、善友、生活平衡。
“何谓具足精勤?在此,一位居士,凡所营生计——务农、经商、牧牛、射箭、王家仆役、或其它手艺——灵巧、不倦,具足智慧,善于成办。此谓具足精勤。
“何谓具足守护?在此,一位居士拥有正当所得之财产——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以臂力积攒、以汗水挣得——他善加守护,[想着:]‘如何不让国王、盗贼夺走我的财产,不让火烧尽、不让水冲走、不让无爱的子孙拿走?’此谓具足守护。
“何谓善友?在此,一位居士,无论住哪个村镇,去亲近具足戒德的居士或居士之子,不论长幼。与他们谈话,参与讨论。他效仿具足信者而具足信,效仿具足戒者而具足戒,效仿具足舍者而具足舍,效仿具足慧者而具足慧。此谓善友。
“何谓生活平衡?在此,一位居士,了知其财产的收入与支出,维持平衡的生活,既不奢侈、也不吝啬,[心想:]‘如此,我的收入将超过支出,我的支出将不超过收入。’正如一位秤量者或其学徒,执秤时,了知:‘它下沉了这么多,或上翘了这么多,’同样地,一位居士,了知其财产的收入与支出,维持平衡的生活。假若一位居士收入少,却生活奢侈,人们会说:‘这位族人吞噬他的财产,如食无花果者。’假若一位居士收入多,却生活困苦,人们会说:‘这位族人将饿死。’然而,当一位居士了知其财产的收入与支出,维持平衡的生活,此谓生活平衡。
“耗尽财富有这四条途径:沉溺女色、沉溺饮酒、沉溺赌博、与恶人为友、为伴、为伍。正如一座有四个入水口、四个出水口的大水库,有人关闭入水口、打开出水口、又无天降阵雨,水库之水只会耗尽,不会增加。同样,此为耗尽财富的四条途径。
“积累财富有这四条途径:不沉溺女色、不沉溺饮酒、不沉溺赌博、与善友为友、为伴、为伍。正如一座有四个入水口、四个出水口的大水库,有人打开入水口、关闭出水口、又有天降阵雨,水库之水只会增加,不会耗尽。同样,此为积累财富的四条途径。
“虎爪,这四种法,能使居士今生得安乐。
“这四种法,能使居士来世得安乐。哪四种?具足信、具足戒、具足舍、具足慧。
“何谓具足信?在此,一位圣弟子有信,坚信如来的觉醒:‘彼世尊是阿罗汉、正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此谓具足信。
“何谓具足戒?在此,一位圣弟子离杀生、离不与取、离邪淫、离妄语、离导致放逸的酒与麻醉品。此谓具足戒。
“何谓具足舍?在此,一位圣弟子,心离悭吝之垢、住于家中、慷慨、乐于布施、有求必应、乐于分享。此谓具足舍。
“何谓具足慧?在此,一位圣弟子有智慧,具足导向生灭的智慧——圣、决择、趋向苦的正尽。此谓具足慧。
“虎爪,这四种法,能使居士来世得安乐。”
——AN 8.54《增支部》
比丘
我听说有一次,世尊住在迦毗罗卫大森林里的释迦人之中,同住的还有一大群比丘僧团,约五百名比丘,全是阿罗汉……
——DN 20《长部》
麻风病者
接著,世尊以他的觉知遍览全体在场者的心后,自问:“现在,这里有谁能理解法?”他看见麻风病者善觉坐在人群之中,看见他时,他想:“此人能理解法。”于是,针对麻风病者善觉,他作了一场次第说法,即,布施说、戒德说、天界说;他宣讲了感官之欲的过患、堕落、染污,以及出离的利益。接著,他见麻风病者善觉的心已预备、柔软、无盖、高昂、明净,便作了一场诸佛特有的法义开示,即:苦、集、灭、道。犹如无垢、洁净之布能善吸染料,同样地,麻风病者善觉正端坐原地,即生起无尘、无垢的法眼:“凡是集法,皆是灭法。”
——Ud 5.3《自说经》
国王
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于日中往诣世尊,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世尊对他说:“大王日中从何处前来?”
“世尊,我方才正忙碌于那些沉溺于王权、迷恋于感官欲乐、已得国土安稳、征服广大领土的油顶刹帝利王所惯常忙碌的事务。”
“大王你以为如何?假定有一位可信可靠之人从东面来见你,到达后说:‘禀告大王,我从东面来。我在那里看见一座如天高的大山,正朝这边移动,碾碎所有生灵。请您即刻决策。’接著第二个人从西面来……接著第三个人从北面来……接著第四个人从南面来,到达后说:‘禀告大王,我从南面来。我在那里看见一座如天高的大山,正朝这边移动,碾碎所有生灵。请您即刻决策。’陛下,假定此等巨大的灾难将临,此等可怕的人命毁灭将至——人身已如此难得——你该当如何?”
“假若此等巨大的灾难将临,此等可怕的人命毁灭将至——人身已如此难得——除了行法、行善,修习善巧、福德之业,又能如何?”
“大王,我告诉你,大王,我知会你:老与死正朝你碾压过来。当老与死朝你碾压过来时,大王,你该当如何?”
“世尊,当老与死朝我碾压过来时,除了行法、行善,修习善巧、福德之业,又能如何?” ……
“正是如此,大王!正是如此,大王!当老与死朝你碾压过来时,除了行法、行善,修习善巧、福德之业,又能如何?”
——SN 3.25《相应部》
贱民
我的种姓低贱,贫穷无食; 我的职业卑下:我收拾谢萎的花。 为人所厌恶、鄙视、轻贱, 我心谦卑,对众人恭敬。
后来我见到正自觉醒者,为比丘僧团围绕, 那位伟大的英雄进入摩羯陀城。 我放下担子,上前礼敬, 他,这位至高之人,出于慈悲,为我停步。
我礼敬导师之足后,立于一边, 请求这位一切有情之至尊,准我出家。 慈悲的导师,悲悯全世界,他说: “来,比丘。”那便是我的具足戒。
我独居林中、精勤不懈,奉行导师之言,如胜者所教。 在初夜,我忆起宿命; 在中夜,我清净天眼; 在后夜,我粉碎无明之暗。
黑夜终结,旭日东升, 因陀罗与梵天前来礼敬我: “礼敬您,人中贵人,礼敬您,人中至尊, 您的诸漏已尽,尊者,您值得供养。”
——Thag 12.2《长老偈》
其它精神传统的求道者
拘利族人之子牛行者富楼那与裸身的狗行者塞尼耶,往诣世尊。牛行者富楼那对世尊行礼后,坐于一边;裸身的狗行者塞尼耶与世尊互致问候,交换礼貌友好的言辞后,如狗一般蜷缩身体,也坐于一边。
牛行者富楼那坐下后,问世尊:“尊者,这位裸身狗行者塞尼耶行难行之事:他只食用弃置于地之物。长久以来他行持、修习狗行。他的归宿为何?他的未来命运为何?”
“够了,富楼那,别问了。”
第二次……第三次,牛行者问世尊:“尊者,这位裸身狗行者塞尼耶行难行之事:他只食用弃置于地之物。长久以来他行持、修习狗行。他的归宿为何?他的未来命运为何?”
“好吧,富楼那,既然我以‘够了,富楼那,别问了’仍不能劝止你,那么我为你解答。”
“富楼那,在此有一人完全、无保留地修习狗的习惯、他完全、无保留地修习狗的心态、他完全、无保留地修习狗的行为。修成后,身坏命终时,他投生于狗群中。不过,他若有此见:‘凭此戒德、苦行、梵行,我将成为天神’,那是邪见。我说,持邪见者有两个归宿:地狱或畜生道。因此,富楼那,假若他的狗行圆满,这将引导他投生狗群;否则,他将堕入地狱。”
——MN 57《中部》
还有天人
“……几百次四大王天的天神聚会……几百次三十三天的天神聚会……几百次摩罗的聚会……几百次梵天聚会。我曾在那里与他们同坐、对话、讨论……”
——MN 41《中部》
佛陀教导他的亲属包括儿子罗睺罗
“舍弃五欲乐,它们悦意而迷人, 具信而出家,为了终结苦。
亲近善友,择偏远安静处独居, 饮食知量;衣袍、食物、药品、住所—— 勿对这些生起渴爱, 勿再返回世间。
持戒防护,约束五根。
修习身念住,常对身体生厌离。 避开美丽、与贪欲相连的相; 藉修不净观,培育专一、安止的心。
修习无相,断除我慢。 因断除我慢,你将寂静而行。”
世尊如此反复教诫罗睺罗。
——Snp 2.11《经集》
继母大爱道-乔达摩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毗舍离大森林里的尖顶堂。其时大爱道-乔达摩往诣世尊,近前顶礼后,立于一边。站立时,对他说:“善哉尊者若能为我简要说法,使我从世尊处闻法后,得以独自安住、独处、警觉、精勤、决意。”
“乔达摩,对于那些法,你若了知:‘这些法导向贪欲,不导向无欲;导向束缚,不导向解缚;导向累积,不导向消减;导向自大,不导向谦虚;导向不满,不导向满足;导向纠缠,不导向独处;导向懒惰,不导向精勤;导向负累,不导向轻松’:你可断定:‘这不是法,这不是律,这不是导师的教导。’
“至于那些法,你若了知:‘这些法导向无欲,不导向贪欲;导向解缚,不导向束缚;导向消减,不导向累积;导向谦虚,不导向自大;导向满足,不导向不满;导向独处,不导向纠缠;导向精勤,不导向懒惰;导向轻松,不导向负累’:你可断定:‘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导。’”
那就是世尊所言。大爱道-乔达摩对世尊之言心悦、随喜。
——AN 8.53《增支部》
他辅导表兄弟难陀成就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舍卫城附近的祇树给孤独园。其时尊者难陀——世尊的兄弟、他姨母之子——对一大群比丘说:“贤友们,我不乐于梵行生活,我不能忍受梵行生活。我将放弃修行,还俗。”
有位比丘往诣世尊,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对世尊说:“世尊,尊者难陀——世尊的兄弟、他姨母之子——已告诉一大群比丘:‘贤友们,我不乐于梵行生活,我不能忍受梵行生活。我将放弃修行,还俗。’”
于是世尊嘱咐某位比丘:“来,比丘。以我的名义去找难陀,说:‘难陀贤友,导师唤你。’”
该比丘答:“遵命,世尊。”于是去见难陀,到达后说:“难陀贤友,导师唤你。”
尊者难陀答:“遵命,贤友。”于是他往诣世尊,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世尊对他说:“难陀,你已告诉一大群比丘:‘贤友们,我不乐于梵行生活,我不能忍受梵行生活。我将放弃修行,还俗。’这可是真的?”
“是的,世尊。”
“不过,难陀,你为何不乐于梵行生活?”
“世尊,我离家时,有一位全国最美的释迦族少女,头发半梳,瞥我一眼道:‘大师,请速回。’忆及此事,我便不乐于梵行生活,不能忍受梵行生活。我将放弃修行,还俗。”
这时,世尊抓著尊者难陀的手臂——如壮汉曲臂、伸臂一般——从祇树给孤独园消失、重现于三十三天。当时约有五百名鸽足天女,前来服侍天帝释。世尊对尊者难陀说:“难陀,你可见那五百鸽足天女?”
“是,世尊。”
“你以为如何,难陀:哪位更美丽、更可爱、更有魅力——是那位释迦族少女,还是这五百鸽足天女?”
“世尊,与这五百鸽足天女相比,那位全国最美的释迦族少女,就像一只被火烧伤、割去耳鼻的母猴。她根本无法相比,不及她们的千万分之一。这五百鸽足天女远比她更美丽、更可爱、更有魅力。”
“那么欢喜吧!难陀,欢喜吧!我担保你得到五百鸽足天女。”
“世尊若能担保我得到五百鸽足天女,我将在世尊座下乐于梵行。”
接著,世尊抓著尊者难陀的手臂——如壮汉曲臂、伸臂一般——从三十三天消失、重现于祇树给孤独园。比丘们听闻:“据说尊者难陀——世尊的兄弟、他姨母之子——为著天女而修梵行。据说世尊担保他得到五百鸽足天女。”
于是,尊者难陀的旧友比丘们,对待他如同对待雇工和商贩:“据说我们的难陀贤友是雇工,据说我们的难陀贤友是商贩。他为著天女而修梵行。据说世尊担保他得到五百鸽足天女。”
尊者难陀对旧友比丘们待他如雇工和商贩,感到羞耻、惭愧、厌恶——独自安住、独处、警觉、精勤、决意。不久他便进入、安住于梵行生活的无上目标——善男子为此离俗而出家——于现法中自知、亲证、成就。他自知:“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于是尊者难陀成为世上又一位阿罗汉。
——Ud 3.2《自说经》
佛陀的最后日子
阿难注意到佛陀渐老
那一次,世尊于傍晚时分走出独处,坐于日光下温暖背部。尊者阿难往诣世尊,近前顶礼后,以手按摩世尊的四肢道:“多么惊人,世尊,多么稀有,世尊的肤色不再纯净光洁;他的四肢松弛起皱;他的身体前倾;他的根门——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有可见之衰变。”
“阿难,正是如此。青春终将衰老;健康终将患病;生命终将死亡。肤色不再纯净光洁;四肢松弛起皱;身体前倾;根门——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有可见之衰变。”
——SN 48.41《相应部》
佛陀死后弟子当以何为依止
“阿难,我如今已衰老、年迈、高寿。我已八十岁,寿缘将尽。阿难,犹如一辆旧车,仅靠捆绑勉强维持,如来之身亦复如是,仅靠支撑勉强维持。唯有当如来不作意一切相,灭除某些受,进入、安住于无相心定时,身体才感到安稳。
“因此,阿难,当以自己为洲,以自己为依止,不以其它为依止;以法为洲,以法为依止,不以其它为依止。
“阿难,一位比丘,如何以自己为洲,以自己为依止,不以其它为依止;以法为洲,以法为依止,不以其它为依止?
“在此,比丘于身观身,精勤、觉知、具念,调伏对世间的贪与忧;
“于受观受……于心观心……于法观法,精勤、觉知、具念,调伏对世间的贪与忧。那时,他就真正做到了以自己为洲,以自己为依止,不以其它为依止;以法为洲,以法为依止,不以其它为依止。”
——DN 16《长部》
他放弃续寿的意志
“阿难,今日于遮婆罗塔,邪恶者摩罗来见我说:‘世尊,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皆已成为世尊的真正弟子——智慧、自律、博学、持法、法随法行、具足正行;学得导师的教法后,能够解说、宣讲、开示、建立、揭示、详述、阐明;有异论生起时,能够以法彻底驳斥,并宣说此具说服力、能引解脱之法。’
“‘世尊,如今世尊所传的梵行已成功、兴盛、广为人知、普及、流传,在天界与人间善为开示。因此,世尊,请世尊入般涅槃吧!请善逝者入般涅槃吧!现在正是世尊般涅槃之时。’
“阿难,其时我答邪恶者摩罗:‘邪恶者,你勿自扰。如来的般涅槃已近。三月后如来将圆寂。’
“阿难,如此,今日于遮婆罗塔,如来已舍弃寿行。”
听闻此言,尊者阿难对世尊道:“世尊啊!请世尊住世一劫!世尊啊,请善逝者住世一劫!为著众生的利益与安乐,为著慈悯世间,为著天神与人类的利益、福祉与安乐。”
世尊答:“阿难,够了。莫再恳请如来,因为阿难,这等恳请的时机已过。”
——DN 16《长部》
他对比丘们的最后教诫
“比丘们,我告诉你们,我所亲证并为你们宣说的这些法——你们应当善学、善习、善修、广布,使此梵行得以确立、久住,为著众生的利益与安乐,为著慈悯世间,为著天神与人类的利益、福祉与安乐。
“那么,比丘们,这些法是什么?它们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比丘们,这些正是我所亲证并为你们宣说的法——你们应当善学、善习、善修、广布,使此梵行得以确立、久住,为著众生的利益与安乐,为著慈悯世间,为著天神与人类的利益、福祉与安乐。”
接著,世尊对众比丘说:“比丘们,因此我告诫你们:一切因缘和合之法皆趋于坏灭。当以不放逸努力成就。如来入般涅槃之时已近。三月后,如来将圆寂。”
——DN 16《长部》
他的最后一餐
世尊用过铁匠之子纯陀供养的食物,遂染重病乃至血痢,经历剧烈、濒死之痛。然世尊具念、觉知,忍受剧痛,不为所扰。
接著,世尊对尊者阿难说:“来,阿难,我们去拘尸那罗。”尊者阿难答:“是,世尊。”
——DN 16《长部》
他临终卧床
于是,世尊与大群比丘走向熙连禅河对岸,拘尸那罗末罗人的优波跋单娑罗林。到达后,他对尊者阿难说:“阿难,请为我在娑罗双树之间准备卧具,头朝北。我疲倦,欲卧。”
尊者阿难答:“遵命,世尊。”便在娑罗双树之间准备卧具,头朝北。于是世尊以狮子卧姿,右侧偃卧,一足叠于另一足之上,保持正念、觉知。
其时,那娑罗双树非时而花开满枝,花朵飘撒、散落于如来之身,以示崇敬。天界的曼陀罗花自空中飘落,纷撒、散落于如来之身,以示崇敬。天界的檀香粉自空中洒落,纷撒、散落于如来之身,以示崇敬。天界的音乐自空中奏起,以示崇敬。天界的歌声自空中颂起,以示崇敬。
——DN 16《长部》
佛陀所荐的四个朝礼圣地
“阿难,有此四处,能令具信的善男子、善女人见后心生紧迫感。哪四处?‘此处如来诞生’,是能令具信者心生紧迫感之处。‘此处如来证得无上正自觉醒’……‘此处如来转动无上法轮’……‘此处如来入无余涅槃界’,是能令具信者心生紧迫感之处。阿难,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将前往朝礼这些圣地。若有以明净、信仰之心朝礼此诸圣地时命终者,身坏命终之际,将重生于善趣、天界。”
——DN 16《长部》
数千人痛哭世尊将逝
其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正聚于会议厅商议公事,尊者阿难走向会议厅,到达后对他们宣布:“婆西塔人,今晚的后夜,如来将般涅槃。出来吧,婆西塔人!出来吧,婆西塔人!莫要日后追悔:‘如来就在我们镇内般涅槃,我们却未得见他最后一面!’”听闻尊者阿难之语,末罗人与其子、其媳、其妻皆震惊、哀痛、忧伤。他们有的扯发痛哭、有的举臂大泣。有的如双足被斩般倒地,翻滚哭叫:“世尊般涅槃如此之速!善逝者般涅槃如此之速!世间眼灭没如此之速!”
接著末罗人与其子、其媳、其妻——震惊、哀痛、忧伤——走向拘尸那罗附近的优波跋单,末罗人的娑罗林中尊者阿难处。
——DN 16《长部》
只要有人修八正道世上就有阿罗汉
“任何法与律中,若无八正道,则无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沙门。然而任何法与律中,有八正道,则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沙门。此教此律有八正道,故此处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沙门。其他教派则无觉悟之沙门。比丘们若能正住,世间将不缺阿罗汉。”
——DN 16《长部》
佛陀的临终之语
[佛历 1]
于是世尊对众比丘说:“听着,比丘们,我告诫你们:一切因缘和合之法皆趋于坏灭。当以不放逸努力成就。”那就是如来的最后遗言。
于是世尊即入初禅。自初禅出而入第二禅。自第二禅出而入第三禅……第四禅……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自非想非非想处出,而入想受灭尽定。 ……
于是世尊出想受灭尽定而入非想非非想处。自非想非非想处出而入无所有处……识无边处……空无边处……第四禅……第三禅……第二禅……初禅。自初禅出而入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自第四禅出后,他即刻般涅槃。
——DN 16《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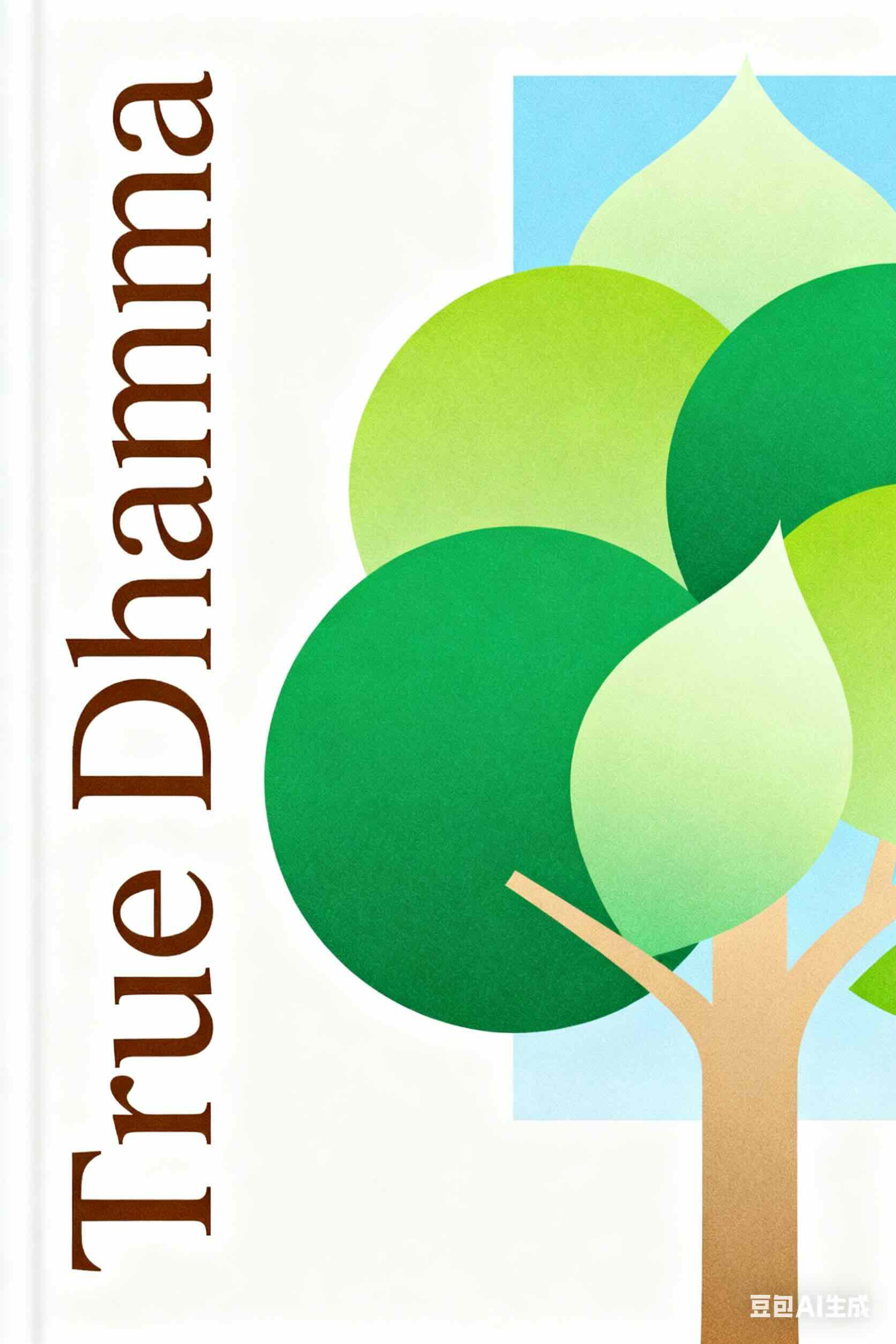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浏览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