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教了什么
巴利圣典, 西方世界的佛法 ·Index
What the Buddha Taught - Walpola Rahula
佛陀教了什么 - 罗睺罗·化普乐
西方世界的佛法:拨开宗教的迷雾,直探佛陀教义的理性核心,一部为现代人撰写的佛学入门经典。
佛陀简介
佛陀,俗名悉达多,姓乔达摩,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北印度。他的父亲是释迦国的国王,母亲是摩耶王后。年轻的王子在宫中享尽奢华,但在目睹了人生的现实与痛苦后,他决心寻找解脱之道。二十九岁那年,在他的独子罗睺罗出生后不久,他毅然离开了王宫,成为一名苦行者,以探寻宇宙人生的真理。
经过六年的寻访、学习和极端的苦行,悉达多发现这些传统方法都无法让他满意。于是,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三十五岁那年,在一个夜晚,他坐在一棵菩提树下,于菩提伽耶的尼连禅河畔获得了彻悟,从此被称为“佛陀”,意为“觉悟者”。
觉悟之后,佛陀在鹿野苑向他过去的五位苦行同伴进行了第一次说法。自那天起,他在四十五年的时间里,不分阶级、种姓,向国王、农夫、婆罗门、贱民、富商、乞丐等各类人士传授他所发现的真理。他所倡导的道路向所有愿意理解和追随的人开放。
八十岁时,佛陀在拘尸那迦城安然离世。如今,佛教流传于斯里兰카、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西藏、中国、日本等地,全球信众超过五亿。
第一章 佛教的心态
在所有宗教的创始人中,佛陀是唯一一位声称自己纯粹是人类的导师。他未曾宣称自己是神、神的化身或受神启示。他将自己的一切证悟与成就,都归功于人类自身的努力与智慧。他教导说,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佛。
人是至高无上的。佛陀认为,人是自己的主宰,没有任何更高的存在能审判他的命运。他告诫弟子:“人是自己的皈依处”,并鼓励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获得解脱。佛陀的角色是发现并指示解脱之路的导师,但路必须由我们自己走。
基于这种个人责任的原则,佛陀给予弟子们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他从不强迫任何人接受他的教诲。在一个著名的故事中,他告诉迦摩罗人,不要因为传说、传统、经文权威、逻辑推断或老师的身份就轻易相信,而要亲自验证。当你自己知道某些事是不善的、错误的,就应舍弃;当你自己知道某些事是善良的、正确的,就应接受并奉行。
佛陀的教诲中,怀疑(vicikicchā)被视为一种障碍,但并非“罪恶”。因为佛教中没有信条,罪恶的根源是无明(avijjā)和邪见(micchādiṭṭhi)。要破除怀疑,唯有清晰地“看见”和“理解”。强迫自己去相信,是政治而非灵性。
佛教的宽容精神也极为突出。当一位耆那教的弟子优波离在与佛陀辩论后,心悦诚服地希望成为佛陀的弟子时,佛陀反而劝他慎重考虑,并继续尊敬和供养他原来的老师。这种宽容精神贯穿了佛教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从未有过暴力传教的记录。
那么,佛教是宗教还是哲学?这标签并不重要。真理没有标签,它不是佛教的、基督教的或任何宗教的专利。执着于标签只会产生偏见,阻碍对真理的独立理解。佛陀强调的是“看见”和“理解”,而非“信仰”或“相信”。当一个人亲眼看见时,相信的问题便不复存在。佛陀的教诲被称为“Ehi-passika”,意为“来,亲自看一看”,而非“来,相信吧”。
佛陀从不执着于他自己的教诲,甚至告诫弟子不要执着于法。他著名的“筏喻”说明了这一点:佛法就像一只渡人过河的木筏,一旦到达彼岸,就应舍弃,而不是背着它继续前行。教义是工具,而非执着的终点。
佛陀的态度是极其务实的。他拒绝回答那些纯属形而上学的思辨问题,如宇宙是否永恒、人死后是否存在等。他用一个“毒箭之喻”来阐明:一个人身中毒箭,最紧要的是拔箭疗伤,而不是去研究箭是谁射的、用什么材料做的。同样地,人生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苦”的问题,即认识苦、苦的起因、苦的止息以及通往灭苦的道路——这便是四圣谛。佛陀只教导那些有助于解脱、能带来和平与幸福的实用法门。
第二章 第一圣谛:苦谛(Dukkha)
佛陀教诲的核心是四圣谛,这是他在成道后初次说法的全部内容。四圣谛分别是:
- 苦谛(Dukkha):苦的真理。
- 集谛(Samudaya):苦生起或其根源的真理。
- 灭谛(Nirodha):苦止息的真理。
- 道谛(Magga):通往苦止息之道的真理。
第一圣谛:苦(Dukkha)
将“Dukkha”简单翻译为“痛苦”或“苦难”是片面且容易引起误解的。这使得许多人认为佛教是悲观的。事实上,佛教既非悲观也非乐观,而是写实的。它客观地看待生命,不提供虚假的安慰,也不制造无谓的恐惧。佛陀就像一位高明的医生,准确诊断病症(苦),找出病因(集),宣告可以治愈(灭),并开出药方(道)。
巴利文“Dukkha”一词的哲学含义远比“痛苦”要深刻。它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痛苦,还包含更深层次的意义,如“不圆满”、“无常”、“空”、“无实体”。
佛陀承认生命中有快乐,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快乐。但即使是最高深的禅定状态,虽然毫无痛苦,仍被归于“Dukkha”之列,因为“凡是无常的,就是苦”。
苦的概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 苦苦(Dukkha-dukkha):即日常生活中普遍公认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 坏苦(Vipariṇāma-dukkha):由变化所产生的苦。快乐的感觉和状态是短暂的,当它们改变或消失时,就会产生痛苦。
- 行苦(Saṃkhāra-dukkha):作为“有为状态”的苦。这是最深刻的哲学层面,它关系到我们对“生命”或“我”的构成理解。
根据佛教哲学,我们所谓的“生命”、“个体”或“我”,只是五种不断变化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组合,称为五蕴(Pañcakkhandha)。这五蕴本身就是“苦”。
五蕴
- 色蕴(Rūpakkhandha):物质的集合。包括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及其衍生物,如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和它们对应的外部对象(色、声、香、味、触),甚至包括某些意念对象。
- 受蕴(Vedanākkhandha):感受的集合。包括所有愉快、不愉快或中性的感受,这些感受由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接触而产生。
- 想蕴(Saññākkhandha):感知的集合。即对事物的识别和概念化,也是由六根与六尘接触而产生。
- 行蕴(Saṃkhārakkhandha):心理构造或意志活动的集合。所有善、恶的意志活动都属于此类,我们通常所说的“业”(Karma)就在其中。佛陀定义业为“思”(cetanā),即意志。
- 识蕴(Viññaṇakkhandha):意识的集合。意识是基于六根之一,并以六尘之一为对象的反应。例如,视觉意识以眼为基础,以可见的形态为对象。它只是一种“觉知”,而非“识别”(识别属于想蕴)。
佛教哲学中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与物质对立的“灵魂”或“自我”。我们所谓的“我”,只是给这五蕴组合体贴上的一个方便标签。五蕴皆是无常的、不断变化的,它们处于刹那生灭的流转之中。背后并没有一个永恒的“我”在体验这一切。如佛家偈语所说:“唯有苦存在,却找不到受苦者;事迹存在,但找不到作者。”
生命的开端是不可思议的。佛陀说,众生在无明和渴爱的束缚下,于生死轮回中流转,其最初的起点是不可见的。
理解第一圣谛至关重要,因为佛陀说:“见苦者,亦见苦之生起,亦见苦之止息,亦见通往苦止息之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佛教徒的生活是忧郁的。相反,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是快乐的,因为他看清了事物的真相,内心平静安详,不受外境变迁的困扰。
第三章 第二圣谛:集谛(Samudaya),苦之生起
第二圣谛是关于苦的生起或根源。最普遍的定义是:
“此即‘渴爱’(Taṇhā),它导致再生与轮回,与强烈的贪欲相连,在在处处寻求新的喜乐。”
这种“渴爱”具体分为三种:
- 欲爱(Kāma-taṇhā):对感官享乐的渴求。
- 有爱(Bhava-taṇhā):对生存和形成的渴求。
- 无有爱(Vibhava-taṇhā):对不存在(自我毁灭)的渴求。
这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渴爱”、欲望、贪婪,是所有形式痛苦和生命延续的根源。但它并非“第一因”,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相对和相互依存的。这种“渴爱”本身也依赖于其他条件,如感受(vedanā)的生起,而感受又依赖于接触(phassa),如此循环,构成了“缘起”(Paṭicca-samuppāda)的法则。
“渴爱”不仅指对感官享乐、财富、权力的欲望,也包括对思想、理想、见解、理论和信仰的执着。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上所有的纷争,从家庭纠纷到国际战争,都根植于这种自私的“渴爱”。
这种“渴爱”如何导致再生和轮回?这就涉及到业和轮回的理论。
佛陀教导,有四种“食”(āhāra),即维持众生存在和延续的四种必要条件:
- 段食:普通的物质食物。
- 触食:感官(包括心)与外界的接触。
- 识食:意识。
- 思食:心的意志或意愿。
其中,“思食”是生存、延续、不断形成的意愿。它创造了存在的根源,通过善恶行为(业)不断向前推进。它与“思”(cetanā)是同义的,而“思”即是业。佛陀说:“当一个人理解了思食,他就理解了三种渴爱。”因此,“渴爱”、“思”、“意愿”和“业”都指向同一事物:一种存在的欲望和意志。
苦生起的根源,就在苦的本身(五蕴)之内,而非之外。同样,苦止息的根源,也在苦的本身之内。这便是“凡有生起之法,皆有止息之法”的道理。
我们所谓的死亡,是身体机能的完全停止。但这股强大的生存意志力量并不会随之消亡,它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显现,产生新的存在,即再生(轮回)。
如果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或“灵魂”,那死后是什么在再生呢?佛陀的回答是,生命本身就是一连串不断变化的物质和精神能量的组合,没有一个固定的实体。就像火焰彻夜燃烧,既非同一簇火焰,也非另一簇火焰。一个人的死亡和再生,就像一个相续不断的系列。前一生的最后一个念头,制约了下一生的第一个念头。只要“渴爱”这股驱动力存在,轮回就会继续。只有通过智慧看清实相、真理、涅槃,才能切断它。
第四章 第三圣谛:灭谛(Nirodha),苦之止息
第三圣谛是存在从痛苦、从轮回中解脱的真理。这被称为苦灭圣谛,也就是涅槃(Nirvāṇa)。
要彻底消除苦,就必须根除其主要根源——“渴爱”。因此,涅槃也被称为“渴爱之熄灭”(Taṇhakkhaya)。
那么,什么是涅槃?用人类的语言无法完全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语言是我们表达感官和心智经验的工具,而像涅槃这样的超世俗体验,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就像鱼无法用它的词汇来描述陆地的坚实。
因此,涅槃通常用否定性的词语来表达,以避免人们产生错误的执着。例如:“渴爱的熄灭”、“无为”、“无欲”、“止息”。
佛陀也用肯定性的词语描述过。他说:“有一种不生、不长、无为的状态存在。如果没有这种状态,那么从出生、成长、有为的状态中解脱就是不可能的。”
将涅槃描述为否定,是错误的。涅槃绝非自我的毁灭,因为根本没有一个“自我”可以被毁灭。它毁灭的是对“自我”的幻觉和错误观念。涅槃超越了肯定与否定、善与恶、存在与不存在等所有二元对立的概念。
涅槃即是绝对真理。根据佛教,绝对真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有条件、无常的;内外都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绝对的实体,如“自我”或“灵魂”。 认识到这个真理,即如实地看待事物,就是“渴爱”的熄灭,就是苦的止息,就是涅槃。
有趣的是,大乘佛教认为“生死即涅槃”。你如何看待同一事物,决定了它是生死轮回还是涅槃。这个观点源于原始的巴利文经典。
认为涅槃是熄灭渴爱的“结果”是错误的。涅槃不是任何事物的结果。如果它是结果,那么它就是由因所生的“有为法”。涅槃超越了因果。真理不是被制造出来的,真理就是它本来的样子。我们能做的只是去看见它、证悟它。
人们常问:涅槃之后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不成立,因为涅槃是最终的真理,其后便无他物。
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如果没有“自我”,是谁证悟涅槃?佛陀的教诲是,是智慧在证悟。并没有一个在智慧之外的“我”去证悟。苦的生起之因(渴爱)和灭苦之因(智慧)都在五蕴之内。佛陀说:“我于此一寻长的身躯中,宣说世界、世界的生起、世界的止息,以及通往世界止息之道。”
与许多宗教不同,涅槃可以在今生此世证悟,不必等到死后。证悟了真理、涅槃的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摆脱了所有烦恼、忧虑和困扰,内心达到完美的健康、平衡与宁静。他活在当下,以最纯净的方式欣赏和享受事物。他充满慈悲、善良、理解和宽容,对众生的服务是纯粹的,因为他没有自我的观念。
第五章 第四圣谛:道谛(Magga),灭苦之道
第四圣谛是通往苦灭之道,即中道(Majjhimā Paṭipadā)。它避免了两个极端:一是沉溺于感官享乐,二是进行各种形式的苦行。佛陀亲身尝试过这两个极端后,发现它们都无益,于是发现了中道,它能“产生知见,导向寂静、内观、觉悟和涅槃”。
这条中道通常被称为八正道(Ariya Aṭṭhaṅgika Magga),因为它由八个部分组成:
- 正见(Sammā diṭṭhi)
- 正思(Sammā saṅkappa)
- 正语(Sammā vācā)
- 正业(Sammā kammanta)
- 正命(Sammā ājīva)
- 正精进(Sammā vāyāma)
- 正念(Sammā sati)
- 正定(Sammā samādhi)
这八个部分并非按顺序逐一修习,而是尽可能同时发展,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促进。这八个要素旨在促进和完善佛教训练的三个核心:戒(Sīla)、定(Samādhi)、慧(Paññā)。
(一) 戒(Sīla):道德行为
戒建立在对一切众生普遍的爱与慈悲之上。慈悲(karuṇā)与智慧(paññā)是佛教徒需要同等发展的两种品质。只发展情感而忽略理智,会成为善良的傻瓜;只发展理智而忽略情感,会成为冷酷的智者。八正道中的三项属于戒:
- 正语:不妄语、不两舌(不搬弄是非)、不恶口(不说粗鲁伤人的话)、不绮语(不讲无聊的闲话)。
- 正业:不做杀生、偷盗、邪淫等行为。
- 正命:以正当的职业谋生,不从事对他人有害的行业,如贩卖武器、毒品、从事屠宰等。
(二) 定(Samādhi):心智锻炼
这部分旨在训练和发展心智,包括八正道中的另外三项:
- 正精进:努力防止不善念的生起,断除已生的不善念;努力使未生的善念生起,并发展已生的善念。
- 正念:精勤地觉知和专注:(1) 身体的活动(身念住),(2) 感受(受念住),(3) 心的活动(心念住),(4) 思想、观念等法(法念住)。
- 正定:通过正确的专注,达到四种禅定(Dhyāna)的境界。心在禅定中变得宁静、纯净、强大。
(三) 慧(Paññā):智慧
这部分包括八正道中剩下的两项:
- 正思:指无私、舍离、慈爱和非暴力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扩展到所有众生。自私、憎恨和暴力的思想都源于智慧的缺乏。
- 正见:如实地理解事物,也就是透彻地理解四圣谛。这种理解是见到最终实相的最高智慧。佛教区分两种理解:一种是知识性的“相应知”(anubodha),另一种是深刻的、无分别的“洞见”(paṭivedha),后者只有在心通过禅修得到净化和发展后才可能实现。
总之,八正道是一条通过道德、精神和智力的完善,导向最终实相、完全自由、快乐与和平的生活之道。它与信仰、祈祷或仪式无关,而是一条自我修养、自我发展和自我净化的道路。
第六章 无我之教义:无我(Anatta)
“灵魂”、“自我”、“我”或梵文中的“我”(Ātman),通常指人内在有一个永恒、不变、绝对的实体。佛教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否认存在这样一个灵魂或自我。
根据佛陀的教诲,“自我”的观念是一种虚构的、错误的信念,它产生了“我”和“我的”等有害思想,引发了自私的欲望、执着、仇恨、傲慢等烦恼。世界上从个人冲突到国家战争的所有纷争,都可以追溯到这种错误的“我见”。
佛陀的“无我”教义,是五蕴分析和缘起法则的必然结论。当我们分析所谓的“人”时,发现它只是五蕴的组合,背后并没有一个永恒的主宰。同样,根据缘起法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相互依存的。
佛教接受两种真理:世俗谛(sammuti-sacca)和胜义谛(paramattha-sacca)。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我”、“你”等词语,这是符合世俗惯例的方便说法,即世俗谛。但从最高真理(胜义谛)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
有些学者试图在佛教中找到“自我”的观念,这是对佛陀教诲的误解。佛陀在很多场合都明确、断然地否认了“我”的存在。在《法句经》中说:“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诸法无我。”这里用“诸法(dhamma)”一词,其范围比“诸行(saṃkhāra)”更广,包含了有为法和无为法(如涅槃)。这表明,无论在五蕴之内还是之外,都没有一个“我”的存在。
有人会问:既然无我,那又是谁在承受业报呢?佛陀的回答是,我们应该在一切事物中看到“缘起性”。并没有一个不变的实体在承受业报,只有因果相续的过程。
对于旅行者瓦奢(Vacchagotta)提出的“有我还是无我”的问题,佛陀保持了沉默。他后来向阿难解释,如果回答“有我”,就等同于“常见”(永恒论);如果回答“无我”,就等同于“断见”(虚无论),会让本来就困惑的瓦奢更加困惑。佛陀的沉默是一种高超的教导方式,旨在破除提问者对“有”和“无”的执着。
“无我”的教义并非消极或虚无的。它破除了对一个虚幻自我的错误信仰,带来了智慧的光明。它揭示了事物的实相:所谓的“我”,只是身心聚合体在因果法则下刹那生灭、相互依存的流动过程,整个存在中没有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
第七章 “禅修”或心智的培育:修行(Bhāvanā)
佛陀说,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免于精神上的疾病,哪怕是片刻。佛陀的教诲,特别是“禅修”,旨在达到一种完美的心理健康、平衡与宁静。
“禅修”一词远不能表达巴利文“Bhāvanā”的含义,其意为“培育”或“发展”,即心智的培育。它旨在净化内心的杂染,如贪欲、嗔恨、懒惰、忧虑、怀疑,并培养专注、觉知、智慧、意志、精进、喜悦、宁静等品质,最终达到洞见事物本质、证悟涅槃的最高智慧。
禅修主要有两种形式:
- 止(Samatha):发展心智的专注力,达到“心一境性”。这种禅修可以带来极高的神秘体验,但它们是心所创造的,与实相、涅槃无关。这是佛陀之前就存在的修行方法。
- 观(Vipassanā):内观事物的本质,导向心智的完全解脱和涅槃的证悟。这是佛教特有的禅修方法,是一种基于正念、觉知、观察的分析方法。
佛陀关于心智培育最重要的开示是《念住经》(Satipaṭṭhāna-sutta)。该经将禅修分为四个主要部分:身、受、心、法。无论何种形式,核心都是正念(sati)或觉知(anupassanā)。
- 身念住:最著名的是出入息念(ānāpānasati)。练习者坐直,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呼吸上,觉知呼吸的长短、粗细,不加控制。这个练习能培养专注力,对身心健康、情绪平静都极有益处。此外,还包括对身体姿势(行、住、坐、卧)和日常一切行为的全然觉知。活在当下,活在此刻的行动中,是其精髓。
- 受念住:对所有感受(乐、苦、不苦不乐)的觉知。客观地观察感受的生起和消失,而不带主观评判,从而不对其产生执着。
- 心念住:觉知心的状态。无论内心是贪婪、嗔恨、愚痴,还是充满慈爱、专注,都如实地观察,像照镜子一样看清自己的心。当你觉知到愤怒时,愤怒本身就会开始消退。
- 法念住:对各种思想、观念和精神对象的观察与思索。包括对五盖(贪、嗔、昏沉、掉举、疑)的观察,了解它们如何生起和消失;对七觉支(念、择法、精进、喜、轻安、定、舍)的培育;以及对五蕴、四圣谛等教义的深入研究和思索。
除此以外,还有对“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的修习,即将无限的慈爱、悲悯、随喜和宁静心扩展到一切众生。
第八章 佛陀的教诲与今日世界
有人误认为,佛教是出世的,只有出家为僧才能实践。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佛陀的教诲是为所有人设立的,包括在家的普通男女。真正的舍离,不是身体上逃离世界,而是内心的净化。佛陀曾明确表示,有无数在家的男女,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却成功地修行并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
僧团的建立,是为了让那些愿意奉献一生的人,不仅能致力于自身的灵性发展,还能服务大众。
佛陀非常尊重在家人的生活。《教诫罗 G 罗经》(Sigālovāda-sutta)中,佛陀将父母、师长、妻儿、亲友、仆役、宗教人士分别比作东、南、西、北、下、上六个方位,教导在家人要通过履行对他们的责任来“礼敬”他们,这体现了佛教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重视。
如果想成为佛教徒,无需繁复的仪式。只要理解并相信佛陀的教诲是正确的道路,并努力遵循,他就是一名佛教徒。传统上,以佛、法、僧“三宝”为皈依,并受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即是成为一名在家佛教徒。
佛教同样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经济福祉。佛陀认为,没有基于道德和精神原则的清净生活,就不可能有幸福。但他深知,在不利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下,过这样的生活很困难。因此,佛教承认一定的物质条件是精神成功不可或缺的手段。
佛陀指出,贫穷是导致不道德和犯罪的根源。他建议,要根除犯罪,应改善人民的经济状况。他教导在家人如何理财,如何通过正当手段获得财富,并享受四种幸福:拥有财富的幸福、使用财富的幸福、无负债的幸福,以及过着无过失、清净生活的幸福。但他强调,物质幸福远不及精神幸福。
在政治、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佛教倡导非暴力。没有任何所谓的“正义战争”。佛陀不仅教导和平,还曾亲身介入战场,阻止了释迦族与拘利族之间的战争。他提出了“国王十法”(dasa-rājadhammd),作为对统治者的行为准则,包括布施、持戒、正直、仁慈、不害、忍耐等。
历史上最伟大的榜样是印度的阿育王。他在武力征服了迦林伽国后,因目睹战争的残酷而深感悔悟,转而信奉佛教,并宣布放弃武力,以“法胜”(dhamma-vijaya)即道德的感化来治理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胜利的征服者在权力顶峰时放弃战争的唯一典范。
今日世界充满了恐惧和紧张。佛陀的和平、非暴力、慈悲、宽容和智慧的讯息,提供了一条根本的解决之道。如佛陀所说:
“恨不止恨,唯爱能止。” “征服了自己,才是最伟大的征服者。”
佛教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摒弃权力斗争、充满慈悲与和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追求最高尚的目标——证悟最终的真理,涅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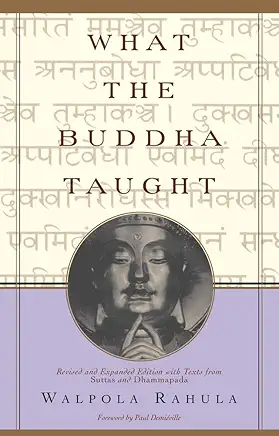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