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法:佛法中的因果法则
巴育陀尊者, 南传上座部佛法 ·Index
Dependent Origination - The Buddhist Law of Conditionality - P. A. Payutto
缘起法:佛法中的因果法则 - 巴育陀尊者 - 摘要
深入揭示佛陀的核心教法——缘起法则,阐明痛苦如何产生,以及如何通过智慧斩断其根源,走向真正的自由。
前言
缘起(Paticcasamuppāda)法则是佛陀所有教诲中最为深刻且引人深思的教义之一。虽然其基本原则相当简单,但当我们开始深入研究构成该法则标准形式的十二因缘链时,我们很快就会遇到疑惑之处。
这个标准格式主要有两种诠释:一种是将其视为一个从一生延续到另一生的过程,另一种是将其视为一个非常即时的过程,发生在意识的瞬间。但无论我们将其解释为跨越多世,还是发生在一心念之间,我们处理的都是超越正常感知的事物。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涉及过去和未来的生命,对此不仅个人经验甚少,而且对于受数世纪犹太-基督教影响以及近代唯物主义风气熏陶的西方心态来说,存在着大量的怀疑。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处理的是意识在如此深刻层面上的运作,以至于只有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沉思,才可能在体验层面上理解这一过程。
因此,对于认真但缺乏经验的学生来说,缘起这个主题很可能令人敬畏、着迷,又有些困惑。它确实需要大量的反思,而且因为它的许多教义都可供诠释,所以很容易偏离正轨。这就是为什么熟悉佛教经文和注疏对此的论述会有所帮助。凭借对该主题的透彻理解,并辅以那些已彻底沉思过它的尊者们的注释,我们更有把握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本书的主题,如同《佛法》系列中的其他书籍一样,摘自 P.A. Payutto(帕·达摩比丘尊者)的《Buddhadhamma》一书。它是原泰文著作第四章的翻译,并加入了一些来自第十六章的材料。增加这些材料是基于原书的布局,我想对此加以解释。
《Buddhadhamma》分为两大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称为 Majjhena-Dhammasanī(中道之教),描述佛陀关于“事物本来面目”或现实本质的教诲。这部分包括关于业(kamma)、三法印(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以及缘起法则等章节。它分为四个部分,标题分别为:生命是什么?生命如何存在?生命如何运作?以及生命应如何度过?
书的第二部分称为 Majjhimā Paṭipadā,处理的是实现书第一部分所概述真理以及将所获知识付诸实践的具体技巧。这部分主要包含了八正道的教诲。它有一个部分,名为“生命应如何活?”最后一部分,处理四圣谛,用来总结全书。总而言之,该书共有22章,第一部分15章,第二部分6章,最后一章为总结。
因为《Buddhadhamma》是一个整体,每一章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并且彼此相关。一些章节可以轻易地独立成书,比如关于业的章节,但其他章节则更依赖于与其他章节的互动。例如,关于缘起的章节,专门论述自然法则,而排除了实践应用的细节,原书的读者会转向书的第二部分寻找这些内容。当本书的第一稿,即第四章的翻译完成后,它似乎有点不够完整。考虑到它是从一本大书的中间部分抽离出来的,这很自然,但单独来看,它可能会让读者感到疑惑。为了弥补这一点,我增加了另一章,摘自《Buddhadhamma》的第十六章,原名为“中道导论”。这一新章节名为“打破循环”,其目的是介绍该教义的实践应用主题。
然而,正如作者所说,实践应用是一个巨大的主题,其详细解释必须留待另一本书。这将在即将出版的一卷中处理,该卷将包含《Buddhadhamma》另外四章的翻译,内容涉及四圣谛和八正道。
本书提供的是对佛教缘起教义的描述。这位可敬的作者,作为泰国最有天赋和最受公认的学者之一,引导我们浏览了现有的经藏和注疏材料,并以他自己筛选教义核心精髓的天赋加以补充。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让我们能够在此之上展开自己的探究。这个过程有时可能会是痛苦的,并不总是清晰明了,但每当事情变得模糊时,记住缘起的基本精髓会很有帮助:“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
—— 译者
引言
因缘相依的教义是佛教最重要的原则。它描述了自然法则,作为事物的自然进程而存在。佛陀并非天国戒律的使者,而是这一自然秩序原则的发现者,并向世界宣告其真理。
因果条件的演进是适用于万物的实相,从作为外部物理条件的自然环境,到人类社会的事件、伦理原则、生活事件以及在我们心中显现的幸福与痛苦。这些因果关系系统是同一个自然真理的一部分。人类的幸福取决于对这个因果系统有一定的了解,并通过在个人、社会和环境层面上解决问题,在其中正确地实践。鉴于万物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成功地与世界相处在于在其中创造和谐。
伴随人类文明演进而来的科学,如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据说它们是基于理性和合理性的。它们的知识宝库是通过与这些自然的条件法则互动而积累起来的。但现代科学领域中人类对知识的探索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这些科学中知识的探索及其应用被分成了不同的类别。每个科学分支都与其他分支截然不同。其次,当今文明中的人类相信,条件法则只适用于物质世界,而不适用于精神世界或伦理等抽象价值。这一点甚至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心理学倾向于仅在与物理现象相关的方面看待因果过程。第三,科学知识(关于条件法则的知识)的应用完全是为了服务于自身利益。例如,我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核心在于试图从中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源,而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后果。
归根结底,我们倾向于以维护自身利益和侵犯他人的方式来解释幸福、自由、权利、解放与和平。即使当控制他人被视为一种应受谴责的行为时,这种侵略性倾向也会转向其他方向,例如自然环境。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真正控制他人或其他事物是不可能的,生活中剩下的唯一意义就是维护自身利益和保护领土权利。生活在这种错误的知识和错误的信念中,自然环境失衡,社会动荡,人类生活在身心两方面都失去了方向。世界似乎充满了冲突和痛苦。
自然秩序的各个方面——物理世界和人类世界,条件(法)的世界和行为(业)的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关联的,它们无法被分开。一个领域的混乱和失常会影响其他领域。如果我们想和平地生活,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与自然环境的所有领域和谐相处,包括内在和外在、个人和社会、物质和精神、有形和无形。
为了创造真正的幸福,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反思自然秩序中万物的相互关系,还要清楚地将自己视为整个自然秩序中的一个因果关系系统,首先意识到内在的精神因素,然后是我们生活经历中的因素,社会中的因素,并最终意识到我们周围世界中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基于“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法则的因果关系系统中,佛教的教诲始于并始终强调在个人意识中制造痛苦所涉及的因素——“因为有无明,所以有行”。一旦在内在层面上理解了这种因果关系系统,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内在因素与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因果关系之间的联系。这便是本书所采用的方法。
第一章:缘起概论
缘起法则是佛教最重要且独特的教义之一。在巴利语经典的许多段落中,佛陀将其描述为一条自然法则,一个独立于觉悟者出现与否而存在的根本真理:
“无论如来出现与否,这个状态都存在,它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一条自然法则;那就是,条件性原则。”
“如来觉悟并证得了那个原则,他教导它、展示它、阐述它、宣告它、揭示它、阐明它、澄清它并指出来,说:”
“‘看这里,由无明为缘,便有诸行。’”
“比丘们,这种如是性,这种不变性,这种不可逆性,也就是说,这个条件法则,我称之为缘起法则。”
以下摘录表明了佛陀对缘起法则的重视程度:
“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缘起。”
“比丘们,确实,一位博学的圣弟子,凭自己独立于对他人信仰的理解,了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当一位圣弟子如此圆满地如实见到世界的生起与息灭时,他便被称为具足正见,具足正观;已证得正法,拥有初学者的知识与技能,已入法流,是一位充满清净智慧的圣弟子,正处于不死的门口。”
“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若了知这些条件,了知这些条件之因,了知这些条件之灭,以及了知导向这些条件之灭的道路,那位沙门或婆罗门便堪称‘沙门中的沙门’,堪称‘婆罗门中的婆罗门’,并且可以这样说他:‘他已凭借自身的更高智慧,达到了沙门生活的目标和婆罗门生活的目标。’”
在下面与阿难尊者的对话中,佛陀告诫不要低估缘起法则的深奥性:
“太奇妙了!世尊,我以前从未想过。这缘起法则,虽然如此深奥难见,对我来说却显得如此简单!”
“阿难,莫作是言,莫作是言。这缘起法则是甚深之教,难见。正是因为不了知、不理解、未彻证此教,众生才会如缠绕的线团般迷惑,如一捆捆线般杂乱,如落入网中,无法逃脱地狱、恶道和轮回之轮。”
经文中缘起的类型
涉及缘起法则的经文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描述其普遍原则,第二类则具体说明了以链条形式连接在一起的构成要素。前者常作为后者的总纲,出现在其前。后者更为常见,大多单独出现。后一种描述可被视为缘起法则的实际体现,因为它展示了自然过程如何遵循普遍原则。
这两大类又可各自分为两支,第一支展示生起的过程,第二支展示息灭的过程。第一支,展示生起的过程,称为 samudayavāra(集起分)。这是缘起序列的顺行模式,对应四圣谛中的第二谛,即苦之因(苦集)。第二支,展示息灭的过程,称为 nirodhavāra(灭尽分)。这是缘起序列的逆行模式,对应第三圣谛,即苦之灭(苦灭)。
1) 普遍原则
本质上,这一普遍原则对应于巴利语中所称的 idappaccayatā,即条件性原则。
A. Imasmim sati idaṃ hoti: 此有故彼有。 Imassuppādā idaṃ uppajjati: 此生故彼生。
B. Imasmim asati idaṃ na hoti: 此无故彼无。 Imassa nirodhā idaṃ nirujjhati: 此灭故彼灭。
2) 法则的运作
A) Avijjā-paccayā saṅkhārā 以无明为缘,则有行。
Saṅkhāra-paccayā viññāṇaṃ 以行为缘,则有识。
Viññāṇa-paccayā nāmarūpaṃ 以识为缘,则有名色。
Nāmarūpa-paccayā saḷāyatanaṃ 以名色为缘,则有六处。
Saḷāyatana-paccayā phasso 以六处为缘,则有触。
Phassa-paccayā vedanā 以触为缘,则有受。
Vedanā-paccayā taṇhā 以受为缘,则有爱。
Taṇhā-paccayā upādānaṃ 以爱为缘,则有取。
Upādāna-paccayā bhavo 以取为缘,则有有。
Bhava-paccayā jāti 以有为缘,则有生。
Jāti-paccayā jarāmaraṇaṃ 以生为缘,则有老死,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āyāsā sambhavanti 愁、悲、苦、忧、恼生起。
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o hoti 如是,此纯大苦蕴之集起。
B) Avijjāya tveva asesavirāganirodhā saṅkhāranirodho 由无明之无余离染灭,则行灭。
Saṅkhāranirodhā viññāṇanirodho 由行灭,则识灭。
Viññāṇanirodhā nāmarūpanirodho 由识灭,则名色灭。
Nāmarūpanirodhā saḷāyatananirodho 由名色灭,则六处灭。
Saḷāyatananirodhā phassanirodho 由六处灭,则触灭。
Phassanirodhā vedanānirodho 由触灭,则受灭。
Vedanānirodhā taṇhānirodho 由受灭,则爱灭。
Taṇhānirodhā upādānanirodho 由爱灭,则取灭。
Upādānanirodhā bhavanirodho 由取灭,则有灭。
Bhavanirodhā jātinirodho 由有灭,则生灭。
Jātinirodhā jarāmaraṇaṃ 由生灭,则老死,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āyāsā nirujjhanti 愁、悲、苦、忧、恼息灭。
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nirodho hoti 如是,此纯大苦蕴之息灭。
注意,这种格式将缘起法则视为一个苦的生起与息灭的过程。这是经文中最常见的表述。在某些地方,它被表述为世界的生起与息灭,使用巴利语词汇 “ayaṃ kho bhikkhave lokassa samudayo”—“比丘们,此即世界之集起”,以及 “ayaṃ kho bhikkhave lokassa atthaṅgamo”—“比丘们,此即世界之消解”;或 “evaṃ ayaṃ loko samudayati”—“如是此世界生起”,以及 “evaṃ ayaṃ loko nirujjhati”—“如是此世界息灭”。这两种表述实际上含义相同,一旦我们定义了术语,这一点就会变得清晰。
在阿毗达摩文献和注疏中,缘起法则也被称为 paccayākāra,指涉事物的相互依存性。
上面给出的扩展形式包含十二个因素,以循环的形式相互依存地连接在一起。它无始无终。将无明置于开端,并不意味着它是万物的第一因或创世纪。将无明置于开端是为了清晰起见,通过截断循环并建立一个被认为最实用的起点。事实上,我们被警告不要将无明视为第一因,因为有以下关于无明缘起的描述——Āsava-samudayā avijjā-samudayo, āsava-nirodhā avijjā-nirodho—无明随漏(āsava)的生起而生起,随其息灭而息灭。
标准的缘起法则格式的十二个环节仅从无明计算到老死。至于‘愁、悲、苦、忧、恼’,这些实际上是对于有漏和烦恼者而言,老死的副产品,成为进一步生起漏(āsava)的‘肥料’,从而导致无明,再次转动循环。
佛陀并非总是以一种固定的形式(从头到尾)描述缘起循环。当他概括地解释原则时,会使用扩展格式,但当他处理特定问题时,他常常以逆序应用它,即:老死 ← 生 ← 有 ← 取 ← 爱 ← 受 ← 触 ← 六处 ← 名色 ← 识 ← 行 ← 无明。在其他描述中,他可能会从中间的某个因素开始,这取决于所讨论的问题。例如,他可能从生(jāti)开始,或受(vedanā),或识(viññāṇa),顺着步骤向前直到老死(jarāmaraṇa),或向后追溯至无明(avijjā)。或者,他可能从一个与十二因缘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然后将其纳入缘起链中。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环节的缘起并不等同于‘被……所引起’。例如,促使一棵树生长的决定因素不仅包括种子,还包括土壤、水分、肥料、气温等等。这些都是‘决定因素’。此外,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并不一定意味着在时间上有任何先后顺序。例如,在树的例子中,各种决定因素,如水分、温度、土壤等,必须同时存在,而不是先后出现,树才能受益。此外,某些决定因素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都制约着另一个的存在,例如,鸡蛋是鸡的条件,而鸡又是鸡蛋的条件。
第二章:缘起的诠释
缘起法则有多种诠释方式,大致可归纳如下:
- 作为生命或世界演化的展示,基于对“lokasamudaya”(世界的生起)等词语的字面定义。
- 作为个体生命或个体痛苦生起与息灭的展示。
这第二类又可分为两个子类别:
- 2.1 展示一个跨越很长时间段,从一生到另一生的过程。这是较为字面的诠释;也是注疏文献中最常见的解释,其中该主题被阐述得如此细致,以至于初学者很可能会被大量的技术术语所迷惑。
- 2.2 展示一个持续不断发生的过程。虽然与2.1相关,但这种诠释对术语给出了更深刻和实用的定义,强调当下,这被认为是该教义的真正目标。这种诠释得到了众多经文教义的支持,在《阿毗达摩藏》中也有段落描述了整个缘起过程发生在一个心念瞬间。
在上述第一种诠释中,有人试图将缘起法则解释为一种世界起源理论,将无明(avijjā)视为第一因,并追溯整个十二环节的演化过程。这种诠释使得佛教教义看起来非常类似于其他宗教教义和哲学,这些教义和哲学都假设了一个起源原则,如上帝。这些诠释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后者将世界的诞生和存在描述为某种超自然力量的运作,而佛教教义,在这种诠释下,则将事物解释为仅仅是根据自然的因果法则进行的一种演化。
然而,这种诠释无疑与佛陀的教诲相矛盾,因为任何显示世界源于一个第一因的教义或思想流派,都与条件性原则或缘起法则相悖,缘起法则明确指出,万物相互依存,通过因缘的影响持续生起。任何第一因,无论是创世神还是其他什么,都是不可能的。将缘起循环解释为生命或世界演化的描述,只有在它呈现出一幅宇宙根据生灭的自然过程,在因果关系的支配下不断展开的图景时,才是可行的。
在评估这些诠释的合理性时,我们必须牢记佛陀教导缘起的目标。在他的教诲中,佛陀旨在呈现的,仅仅是那些可以用来在实践基础上解决生活问题的内容。他不鼓励通过推测、辩论或分析形而上学问题来理解现实,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对一种教义是否真正属于佛教的评估,都应包括对其伦理原则价值的评估。
将缘起法则定义为一个无始无终的演化过程,虽然看似有效,但其伦理价值仍然有限。从中可能获得的是:
- 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观,即世界是根据因果流转而进行的,并受制于自然过程中的条件。没有创造者或指定者,世界也不是一系列毫无目的的意外。目标不能仅通过许愿、向神祈祷或运气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基于对因果条件理解的自力努力来达成。
- 只有在理解了那些原因以及它们与各自结果的联系方式之后,才能为期望的结果创造正确的原因。这需要一种能够辨识这些复杂性的理解力(paññā);必须用智慧来处理和关联生活。
- 对自然过程作为因果连续体的理解,可以有效地减少导致执着于事物并将其认同为我的错觉。这样的视角能使人以更稳固、更独立的方式与事物的本来面目相处。
将缘起法则视为世界演化理论的观点,虽然与佛陀的教诲相符,但仍然有些肤浅。它缺乏对身心组成部分的深刻、详尽、刹那间的分析。它不够强大或清晰,无法明确地带来上述三个结果,尤其是第三个。为了更深入地探究真理,有必要更详细地、在个人基础上审视自然事件的展开,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在我们生活中实际发生时的真相,即使是在非常短暂的瞬间。有了这样清晰的觉知,上述三个益处就更有可能发生。顺便说一句,这种更即时的诠释并不排斥将该过程解释为一种长期的演化。
任何将缘起法则解释为世界演化理论的说法,无论是基础的还是更微妙的意义上,都将缺乏深度。第二种诠释,涉及个人生活,特别是个人痛苦持续的过程,则要深刻得多。
在将缘起循环描述为个人过程的说法中,涵盖数个生命周期的诠释(见2.1)是注疏中最被接受和阐述的。在那里,它被处理得非常细致,并被极大地详述、系统化和图示化。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系统化也倾向于相当僵化,并且容易让初学者感到神秘。在这里,它将被赋予自己的一章,随后是部分相关的、将缘起视为发生在一瞬间的诠释(版本2.2)。
核心意义
本质上,缘起法则是对苦(dukkha)生起与息灭过程的描述。“苦”这个词在佛教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它出现在几个最重要的教义中,如三法印(tilakkhaṇa)和四圣谛(ariyasacca)。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缘起法则,首先必须理解dukkha(苦)这个词。
在佛陀的教诲中,“dukkha”这个词的用法比其英文对应词“suffering”要广泛得多。因此,有必要抛弃英文中这个词的狭隘含义,并根据佛陀话语中非常广泛的含义来重新考虑它。佛陀将苦分为三种类型,加上注疏的解释,它们是:
- 苦苦(Dukkha-dukkhatā):作为感受的苦。这包括身心两方面的痛苦——酸痛、疼痛、悲伤等等——与通常理解的英文单词“suffering”大致相同。这对应于巴利语单词“dukkha-vedanā”(苦受),通常在经历不愉快的感受时产生。
- 坏苦(Vipariṇāma-dukkhatā):变化中所固有的苦;隐藏在幸福无常性中的苦。这是由幸福的变化和消失所引起的苦。这可以在炎热的天气里观察到,当你在外面工作时:如果你习惯了热,你可能不会注意到它,但一旦你进入一个有空调的房间,由此产生的愉悦感可能会在你回到外面时引起不愉快的反应——热度感觉难以忍受。最初中性的热感因为空调的凉爽宜人而变成了不舒服的感觉。空调的愉悦感使得随后的热感显得不愉快。就好像苦是潜伏的,只有在愉悦感消退时才显露出来。愉悦感越强烈,它转变为苦的过程就越剧烈,而且苦似乎与愉悦感的强度成正比地扩大。如果愉悦感没有产生,依赖于它的苦同样也不会产生。如果愉悦感伴随着对其易变本质的觉知,恐惧、担忧和不确定性往往会笼罩着它。当愉悦感最终消逝时,随之而来的是渴望,“我曾经拥有那样的幸福,现在它消失了。”
- 行苦(Saṅkhāra-dukkhatā):所有行(saṅkhāra),即所有由因缘和合而成的事物所固有的苦;特指五蕴。这指的是所有有为法都受到生灭对立力量的支配,它们本身并非完美,而仅仅作为因果连续体的一部分存在。因此,当由于无明和爱取(avijjā-taṇhā-upādāna)而对它们产生僵化的渴望和执着时,它们很可能导致苦(即作为感受的苦,或苦苦)。
最重要的苦是第三种,它描述了所有身心条件所固有的本质。行苦作为一种自然属性,当人们认识到这些条件无法产生任何完美的满足,并因此会给任何试图执着于它们的人带来痛苦时,它便具有了心理学上的意义。
缘起法则以一个连续体的形式,展示了万物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性质。作为一个连续体,它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万物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万物皆依因缘而存在;万物无恒常存在,哪怕一刹那;万物无自性实体;万物无第一因或起源。
换句话说,万物以其多样的生灭形式出现,显示出它们的真实本性是一个连续体或过程。作为一个连续体,表明它们是由众多决定因素复合而成。连续体的形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各种决定因素相互关联。连续体之所以运动和变化形态,是因为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无法持久,哪怕一刹那。事物无法持久,哪怕一刹那,是因为它们没有内在的实体。因为它们没有内在的实体,所以它们完全依赖于决定因素。因为决定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它们维持了连续体的形式,而这种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表明它们没有第一因。
以否定的形式来表述:如果事物有任何内在实体,它们就必须具有某种稳定性;如果它们能够稳定,哪怕一刹那,它们就不可能真正相互关联;如果它们不相互关联,它们就无法形成一个连续体;如果没有因果的连续体,自然的运作将是不可能的;如果那个连续体中有某种真实的内在自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互依存的因果过程。使万物得以如其所是地存在的因果连续体,只有在这些事物是短暂的、朝生暮死的、不断生灭且没有自身内在实体的情况下才能运作。
短暂、朝生暮死、生灭的特性,称为无常性(aniccatā)。受生灭支配、内在地包含着压力和冲突、以及本质上不完美的特性,称为苦性(dukkhatā)。没有任何真实自我的空性,称为无我性(anattatā)。缘起法则阐明了万物中的这三种特性,并展示了万物之间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自然界中的各种事件。
缘起法则的运作适用于所有事物,包括物质和精神,并通过若干自然法则来表达自己。这些法则是:
- 法规定性(Dhammaniyāma):因果的自然法则;
- 时节规定性(Utuniyāma):关于物理对象的自然法则(物理法则);
- 种子规定性(Bījaniyāma):关于生物和遗传的自然法则(生物法则);
- 心规定性(Cittaniyāma):支配心智运作的自然法则(心理或精神法则);
- 业规定性(Kammaniyāma):业的法则,这在决定人类福祉方面尤为重要,并直接与伦理角度的行为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业,如同所有其他因果关系一样,只有在事物是短暂的(无常)并且没有内在实体(无我)的情况下才能运作。如果事物是永恒的并自身具有内在存在,那么包括业的法则在内的所有自然法则都无法运作。此外,这些法则支持了没有第一因或创世纪这一真理。
事物没有内在实体,因为它们依赖于原因而生起,并且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所知的‘床’,来自于众多部件的集合,形成了一个为人所知的形式。除了这些部件之外,一个‘床’并不存在。当所有部件被拆解后,没有‘床’剩下。剩下的只是‘床’的概念。即使是那个概念,也没有独立的存在,而必须与其他概念相关联,例如‘睡觉’、一个平面、一个基座、一个空旷的空间等等。
概念是通过关系的联想在心中形成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旦一组关系形成一个概念,通过爱(taṇhā)和取(upādāna)执着于事物的习惯,就会将那些概念执为固定的实体。这种执着将概念与其和他事物的关系隔离开来,并用‘我’和‘我的’的观念来玷污感知,导致对它们的认同,从而阻碍了任何真正的理解。
事物没有根本原因或最初的生起。沿着因果之流无限回溯,找不到任何事物的根本原因。然而,人们倾向于试图寻找某种原始原因;这种思维方式与自然之道相冲突,并导致与真理相悖的感知。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由人类习惯于在直接原因处停止任何对原因的探究,而不进一步追寻所致。因此,通常对因果的理解,相信事物有其原始原因,是不准确的,并且与自然法则相悖。考虑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有必要通过追问“那个所谓的原始原因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来进一步回溯探究。结果什么也找不到。问题更应该这样问:“事物为什么非得有一个根本原因呢!”
另一种与自然相矛盾、并与根本原因观念相关的推理,是相信最初什么都没有。这种观念源于对我(attā)概念的执着,而这种执着又源于对概念的执着。由此推断,先前此物不存在,但后来它变得存在了。这种错误的推理是人类‘执着于概念’或‘不知概念真相’的习惯,这反过来又是不知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导致了试图寻找某种永恒之物,一个第一因、万物之推动者或创造者,这又会引起许多矛盾,例如:“永恒者如何能创造非永恒者?”事实上,在因果的动态流中,无论是‘在开始时’还是现在,都根本不需要一个支持或否定任何静态存在的立场,除非在言说概念的领域内。我们更应该鼓励以新的问题来重新思考:“为什么存在必须以不存在为前提?”
普遍认为万物皆有创造者的信念是另一个与现实相矛盾的观念。这种信念是基于观察人类创造事物和制作各种手工艺品(如艺术品等)的能力而进行的演绎思维的结果。由此推断,世界上的万物也必定有一位创造者。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把‘建造’或‘创造’的概念从正常的因果连续体中孤立出来时,我们就受骗了,从而把一个谬误当作了我们的基本前提。事实上,‘建造’只是缘起过程的一个阶段。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任何东西,都是因为我们成为了产生期望结果的关系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我们与纯粹的物理因素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在我们的情况下,还存在一些涉及意图的精神因素。即便如此,那些因素仍然是众多因素的一部分,也必须遵循因果过程。例如,当我们想建造一座摩天大楼时,我们必须成为决定因素流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操纵其他决定因素直至完成。如果创造的念头能够独立于因果过程而使事物存在,那么我们只需通过思考就能在任何地方创造出摩天大楼,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创造’这个词的意义,不过是对过程一部分的描述而已。此外,当事物沿着因果过程顺利进行时,创造者的问题在过程的任何一点上都不再相关。
无论如何,探究关于第一因、创世神等问题的真相,在佛教看来价值不大,因为它们对于过有意义的生活并非至关重要。而且,尽管反思这些问题可以提供如上所述的更广阔的世界观,但这种反思仍然可以略过,因为缘起教义在实现生命圆满方面的价值已经涵盖了所期望的益处。因此,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那方面。
第三章:人与自然
所有生命都由五蕴构成:色(物质形态);受(感受);想(感知);行(意志冲动);以及识(意识)。五蕴之内或之外,都没有一个所有者或指导者。在对生命的任何考察中,五蕴都足以构成一个全面的工作基础。五蕴依照缘起法则而运作,存在于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决定因素的连续体中。
在此背景下,五蕴或生命,都受制于三法印:它们处于无常(aniccatā)的状态——不稳定;无我(anattatā)——不含内在的自我;以及苦(dukkhatā)——持续受到生灭的压迫,并且只要通过无明与之关联,就随时可能引发痛苦。五蕴如此运作,不断变化,没有任何恒常的实体,只受制于相互关联的决定因素的自然连续体。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对这一流动的抗拒源于错误地执着于连续体中的某个特征,视其为自我,并希望这个‘自我’以某种期望的方式前进。当事情不符合欲望时,由此产生的压力会导致挫败感,并随后产生更强烈的执着。对那个珍视的自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的模糊意识,或者怀疑它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疑虑,使得这种执着和欲望变得更加不顾一切,恐惧和焦虑深深地植根于心中。
这些心境是:无明(avijjā)——不知真相,视事物为自我;爱(taṇhā)——希望这个想象中的自我获得各种事物或状态;以及取(upādāna)——执着和依附于这些错误观念及其所暗示的一切。这些烦恼深植于心中,从那里指导我们的行为,塑造我们的个性,并或明或暗地影响我们生活的命运。总的来说,它们是所有未觉悟众生痛苦的根源。
本质上,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两个过程之间的不和谐:
- 生命的自然过程,它受制于固定的、自然的三法印法则。这些通过生(jāti)、老(jarā)和死(maraṇa)来表达,无论是在其基本意义上还是在其深刻意义上。
- 渴望与执着的造作过程,它基于对生命真实本性的无知,导致对一个自我的错误感知和执着——‘创造一个自我来堵塞自然的流动’。这是一种被无明束缚的生命,带着执着而活,处于束缚之中,与自然法则相矛盾,并且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
从伦理的角度看,生命可以说包含两种自我。任何特定的生命连续体,沿着其自然的条件性过程前进,虽然没有任何持久的本质,但仍可以被识别为一个区别于其他连续体的个体。这被称为‘世俗我’(conventional self),这种约定俗成可以在与道德行为相关时被巧妙地运用。
然后是‘造作我’(contrived self),由无明捏造,并被爱与取紧紧抓住。当‘世俗我’被清楚地理解为世俗我时,它不成问题。然而,隐藏在‘世俗我’中的‘造作我’,是执着之我,它必须承受前一个自我的变迁,从而产生痛苦。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双层过程:一层是世俗我,另一层是对世俗我的错觉执着,视其为绝对的实在。如果错觉执着转变为知识和理解,问题就解决了。
一种建立在执着于自我观念之上的生活方式,会将恐惧和焦虑深深地植入心灵,从那里它们控制着行为,并奴役着毫无戒备的凡夫。一个基于执着于自我概念的生命观有许多有害的后果,例如:
- 执着于自私的欲望(kāmupādāna),无休止地寻求它们的满足,以及贪婪地抓住欲望的对象;
- 对见解的固执坚持和认同(diṭṭhupādāna),将它们评估为自我或属于自我。这就像建一堵墙来阻挡真理,甚至完全逃避它。这种执着会导致推理能力的僵化,并导致傲慢和偏执;
- 执着于迷信和仪式(sīlabbatupādāna)。由于在此类实践中只感知到一种神秘或脆弱的关系,人们永远无法真正确定它们,但对那个造作的自我的恐惧和担忧,会产生一种不顾一切的企图,去抓住任何东西作为安全的来源,无论它多么神秘或晦涩;
- 执着于一个独立自我的观念(attavādupādāna),这个自我需要被抓住、支持和保护,以免受损或被毁。痛苦随之而生,源于这个受压迫的‘执着之我’所承受的烦恼。
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和痛苦不仅在个人内部产生,还会向外辐射到社会。这种取(upādāna)的状态可以被 singled out 为社会中所有人为麻烦的主要根源。
缘起循环展示了这个充满压力、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的起源,及其在痛苦中不可避免的结果。随着循环的打破,充满压力的生活被彻底改变,转变为一种以智慧生活的生活,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从对自我的执着中解脱出来。
以智慧生活意味着带着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清晰觉知而生活,并知道如何从自然中获益;从自然中获益意味着与自然和谐相处;与自然和谐相处意味着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生活意味着摆脱爱与取的力量;不执着地生活意味着以智慧生活,通过理解因果过程来认识和关联事物。
根据佛陀的教诲,没有任何事物存在于自然之外或与自然分离,无论是作为从外部控制事件的神秘力量,还是以任何其他方式与自然的进程相关或参与其中。任何与自然相关联的事物都不可能与自然分离,而必须是它的一部分。自然界中的所有事件都遵循自然现象相互关系的指引而进行。没有意外,也没有独立于原因的创造力。看似惊人和神奇的事件完全是因缘所生,但因为原因有时被我们的知识所遮蔽,那些事件可能显得神奇。然而,一旦理解了此类事件的原因,任何困惑或惊奇感很快就会消失。“超自然”这个词仅仅是语言的一种构想,指代那些超出我们当前理解范围的事物,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真正“超自然”的。
这同样适用于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类描述为与自然分离,或控制自然的言语方式,仅仅是语言的一种构想。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并非与自然分离。说我们控制自然,仅仅意味着我们在因果过程中成为决定因素。人类的因素包含意图等精神因素,它们参与到行为与结果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合称为‘创造’。然而,人类无法凭空创造任何东西,独立于自然原因之外。我们所谓的对自然的控制,源于我们能够识别产生特定结果所需的因素,并知道如何操纵它们。这个过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知识,它导致第二阶段,即成为其他因素的催化剂。在这两个阶段中,知识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这种知晓,人类能够利用并参与到因果过程中。只有通过智慧与事物互动并影响它们,人类才可以说是‘控制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知识、能力和行为成为自然过程中的额外因素。
这个原则适用于物质和精神现象。‘从自然中获益也是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说法,是基于物质和精神现象相互依存的现实。我们同样可以说‘控制自然的心理方面’或‘控制心智’,这些说法也都是有效的。关于物质和精神现象的智慧,对于真正从自然中获益至关重要。
一个智慧的生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 内在,它的特点是宁静、愉悦、觉知和自由。体验到愉快的感受时,心不被其陶醉或迷惑。当被剥夺舒适时,心坚定、不动摇、不烦恼。幸福和痛苦不再被投射到外在对象上。
- 外在,它的特点是流畅、高效、灵活,并且没有繁琐的情结和错觉。
这里有一段佛陀的教诲,阐明了执着生活与智慧生活之间的区别:
“比丘们,未受教化的凡夫,会体验到乐受、苦受和不苦不乐受。受教化的圣弟子,也会体验到乐受、苦受和不苦不乐受。比丘们,在这种情况下,受教化的圣弟子和未受教化的凡夫之间,有何区别、对比和差异呢?”
“比丘们,当一个未受教化的凡夫,遇到苦受时,他悲伤、哀叹、哭泣、捶胸,并因此心烦意乱、精神错乱:他体验到两种感受,即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
“就好像一个弓箭手,向某人射出一箭后,接着又射出第二箭。那个人会因两支箭而感到疼痛。未受教化的凡夫就是这样。他体验到两种痛苦,身体的和心理的。”
“此外,在体验苦受时,他感到不悦。因那苦受而不悦,对那苦受的瞋恚潜伏倾向(paṭighānusaya)便得以积累。面对苦受,他寻求感官享乐的愉悦。为何如此?因为未受教化的凡夫除了寻求感官享乐的消遣外,不知道有其他摆脱苦受的方法。如此沉溺于感官享乐,对那些乐受的贪欲潜伏倾向(rāgānusaya)便得以积累。他不如实了知那些感受的生起、息灭、吸引、局限和解脱。不如实了知这些事物,对不苦不乐受的无明潜伏倾向(avijjānusaya)便得以积累。体验乐受时,他被其束缚;体验苦受时,他被其束缚;体验不苦不乐受时,他也被其束缚。比丘们,未受教化的凡夫就这样被生、老、死、愁、悲、苦、忧、恼所束缚。我说,他被苦所束缚。”
“至于受教化的圣弟子,比丘们,体验到苦受时,他既不悲伤,不哀叹,不哭泣,也不捶胸。他不会苦恼。他只体验到身体上的痛苦,而非心理上的。”
“就好像一个弓箭手,向某人射出一箭后,接着又射出第二箭,但却射偏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人只会因为第一支箭而感到疼痛。受教化的圣弟子就是这样。他体验到身体上的痛苦,但非心理上的。”
“此外,他不会因为那苦受而感到不悦。不因那苦受而不悦,对那苦受的瞋恚潜伏倾向便不会积累。体验那苦受时,他不会在感官享乐中寻求消遣。为何不?因为受教化的圣弟子知道有除了在感官享乐中消遣之外摆脱苦受的方法。不寻求感官享乐的消遣,对乐受的贪欲潜伏倾向便不会积累。他如实了知感受的生起、息灭、吸引、局限和解脱。如实了知这些事物,对不苦不乐受的无明潜伏倾向便不会积累。体验乐受时,他不被其束缚;体验苦受时,他不被其束缚;体验不苦不乐受时,他也不被其束缚。比丘们,圣、受教化的弟子就这样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中解脱出来。我说,他从苦中解脱。”
“比丘们,这就是受教化的圣弟子和未受教化的凡夫之间的区别、对比和差异。”
第四章:标准模型
呈现缘起法则的标准形式相当复杂,更适合专家而非普通读者。它需要广泛的佛教基础和全面的巴利语词汇才能彻底理解。也有专门论述此主题的经文。在这里,我将简要总结其基本要素。
主要因素
主要因素已在概述中涵盖,因此在这里只作简要提及,首先给出巴利语,然后是巴利语术语的英文定义:
Avijjā → saṅkhārā → viññāṇa → nāmarūpa → saḷāyatana → phassa → vedanā → taṇhā → upādāna → bhava → jāti → jarāmaraṇa … soka parideva dukkha domanassa upāyāsa → 苦之因(dukkha samudaya)。
关于息灭的部分也按照相同的标题进行。
- Avijjā (无明) = 不知,或对苦、其因、其灭以及导向其灭之道(四圣谛)的无知;以及,根据阿毗达摩,不知过去、未来、过去与未来,以及缘起法则。
- Saṅkhārā (行) = 意志冲动:身行(有意的行为);语行(有意的言语);意行(思想);以及,根据阿毗达摩:福行(善业)、非福行(恶业)、不动行(特殊的福业)。
- Viññāṇa (识) = 通过眼、耳、鼻、舌、身、意的意识(包括结生识,paṭisandhi viññāṇa)。(六识)
- Nāmarūpa (名色) = 身心:名(心):受、想、思、触、作意;或,根据阿毗达摩:受蕴、想蕴、行蕴;以及色(身或物质):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及其所依赖的一切形态。
- Saḷāyatana (六处) =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 Phassa (触) = 接触或撞击: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
- Vedanā (受) = 由眼、耳、鼻、舌、身、意的撞击所产生的(乐、苦、舍)感受。
- Taṇhā (爱) = 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渴望。(六爱)
- Upādāna (取) = 对感官对象的执取(欲取),即色、声、香、味、触;对见解的执取(见取);对戒律和仪轨的执取(戒禁取);对自我概念的执取(我语取)。
- Bhava (有) = 导致生的条件;也指存在领域:欲界(欲有);色界(色有);无色界(无色有)。 另一种定义: 业有(Kammabhava),即行为领域,或制约再生的行为:福行(puññābhisaṅkhāra);非福行(apuññābhisaṅkhāra);不动行(aneñjābhisaṅkhāra);以及生有(Upapattibhava),即再生领域:欲界;色界;无色界;有想界;无想界;非想非非想界。
- Jāti (生) = 蕴和六处的生起,出生;事物的出现或生起(后一种解释用于解释一心念中的缘起循环)。
- Jarāmaraṇa (老死) = 衰老与死亡:老:衰老过程,官能的衰退;以及死:蕴的分解,生命原则的消解,死亡;或者,现象的消散和消解。
以下是这些总标题的一些例子:
(漏 → 无明):相信这个自我会因特定行为而投生于各种状态;相信死后一无所有;相信生命是一个善恶行为皆无果报的随机过程;相信仅凭信奉某一宗教就能自动‘得救’;相信物质财富能提供真正的幸福……由此…… → 行:根据那些信念进行思考和意图;根据那些意图考虑和计划行为(业),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恶的,有些是中性的。由此…… → 识:对感觉的感知和觉知,这将与特定的意图相关联。心或识被意图塑造成特定的品质。在死亡时,由业力推动的行的动力,会引导如此塑造的结生识(paṭisandhi viññāṇa)进入与其相适应的出生领域和存在层次。这就是再生。由此…… → 名色:再生的过程继续创造一个准备好产生更多业的生命形态。结果是色、受、想、行四蕴的完整存在,具备了由条件的塑造影响或业所赋予的独特品质和缺陷,并受到该特定存在领域(有)的限制,无论是人、动物、天神等…… → 六处:一个有情众生必须有与其环境沟通的手段,才能在其中运作和发展。因此,在身心的支持下,并符合业的动力,有机体继续发展出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官器官。由此…… → 触:觉知的过程现在通过三个因素的接触或撞击来运作。它们是:内在的感官门(眼、耳、鼻、舌、身、意),外在的感官对象(色、声、香、味、触、法),以及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依赖于这种接触,便发生…… → 受:感受,或对感官接触品质的‘欣赏’,无论是舒适(乐受)、不适或痛苦(苦受),还是中性或平静(不苦不乐受;或舍受)。 根据未觉悟众生的本性,这个过程并未就此停止,而是继续…… → 爱:舒适的感觉倾向于产生喜爱和享受,渴望并寻求更多同样的感觉;对于压力感或不适,则产生厌恶,渴望摧毁或摆脱它们。在此背景下,中性感受被认为是乐受的一种微妙形式,因为它不扰乱心智,并引发一定程度的自满。由此…… → 取:随着欲望的增强,它变成对所讨论对象的执持或执取。只要一个对象尚未获得,便有渴望;一旦对象获得,便被执取紧紧抓住。这不仅指感官对象(欲取),也指观念和见解(见取),修行方式或技巧(戒禁取),以及自我感(我语取)。由于这种执取,随之而来的是…… → 有:根据执取的指令,产生和控制事物的意图和刻意行为,导致整个行为过程(业有)的进一步轮转,可能是善业、恶业或无记业,这取决于制约它们的爱和取的品质。例如,一个渴望生天的人会做他/她相信会导致生天的事情,从而为五蕴在与那些行为(业)相适应的领域(有)中出现奠定基础(生有)。随着造业过程的全面展开,一个环节引生下一个环节,即…… → 生:从结生识开始,它被赋予了依赖于其业力和连接到与其相适应状态的特征,五蕴在一个新的生命连续体中生起,包括名色、六处、触和受。当有生时,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是…… → 老死:那个生命连续体的衰败和消解。对于未觉悟的众生来说,这些事物总是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威胁着生命。
因此,在未觉悟者的生命中,老与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 → 愁(soka);悲(parideva);苦(dukkha);忧(domanassa);以及恼(upāyāsa),总而言之,可以概括为‘苦’。因此,我们在缘起法则公式的最后几句话中看到:“如是此纯大苦蕴之集起。”
然而,由于缘起法则是以循环形式运作的,它并不会就此停止。最后一个因素成为循环进一步延续的关键环节。具体来说,愁、悲等都是漏(āsava)的显现。这些漏有四种,即:对五种感官欲望满足的关切(欲漏);对见解和信仰的执着,例如认为身体是自我或属于自我(见漏);对各种存在状态的渴望以及获得和维持它们的愿望(有漏);以及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无知(无明漏)。
老与死会激化漏。在涉及欲漏的情况下,老与死使未觉悟者感到被剥夺了所爱和珍视之物。在见漏的情况下,身体中称为老与死的变化会引起失望和绝望。在有漏的情况下,老与死剥夺了未觉-悟者珍视的存在状态。在与无明漏相关的情况下,即在基本层面上缺乏理解(例如不理解生命、老与死的本质以及应如何对待它们),老与死会使未觉悟者体验到恐惧、忧郁、绝望和迷信的执着。因此,这些漏是导致愁、悲、苦、忧、恼在老与死一出现时就生起的决定因素。
愁与苦以负面的方式影响心智。每当痛苦生起,心智就会变得困惑和混乱。因此,愁的生起与无明的生起是相称的,正如《清净道论》中所写:
‘愁、苦、忧、恼与无明不可分割,而悲伤是迷惑众生的常态。因此,当愁完全显现时,无明也完全显现。’ ‘至于无明,要知道它随着愁的生起而生起……’ ‘只要愁存在,无明就存在。’ ‘随着漏的生起,无明便生起。’
因此可以说,对于未觉悟者而言,老死及其伴随的愁、悲、苦、忧、恼是产生更多无明的因素,从而再次转动循环。
缘起循环也被称为有轮(bhavacakka)或轮回之轮。这个模型涵盖了三世——无明和行在一世,识到有在第二世,而生和老死(伴随着愁、悲等)发生在第三世。以中间的生命期为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三世时期,连同缘起循环的全部十二个环节,分为三个时间段,如下:
- 过去世 - 无明、行
- 现在世 - 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
- 未来世 - 生、老死(愁、悲、苦、忧、恼)
在这三个时期中,中间的时期,即现在,是我们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看到过去部分纯粹是一种因果关系,即现在的结果源于过去的原因(过去因 → 现在果),而未来部分则具体显示结果,即从现在的原因延伸到未来的结果(现在因 → 未来果)。因此,中间的部分,即现在,既包含因的条件,也包含果的条件。我们现在可以将整个循环分为四个部分:
- 过去因 = 无明、行
- 现在果 = 识、名色、六处、触、受
- 现在因 = 爱、取、有
- 未来果 = 生、老死(愁、悲等)
这条链中的一些环节在意义上是相关的,可以分组如下:
1) 无明与爱-取
从对无明(avijjā)的描述来看,爱(taṇhā)和取(upādāna)似乎也牵涉其中,特别是贯穿始终的我取。不了知生命的真相,错误地相信有一个自我,会导致为了那个自我而产生渴望,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形式的执取。在‘有漏则有无明’这句话中,欲漏(kāmāsava)、有漏(bhavāsava)和见漏(diṭṭhāsava)都是爱和取的类型。因此,当谈到无明时,其含义总是包含爱和取。
这同样适用于任何对爱和取的描述——无明总是与它们相连。将条件误认为真实实体的错觉,是任何生起的欲求和执取的决定因素。爱和取越多,辨别力就越被抛弃,正念和理性行为也就越受损害。因此,当谈到爱和取时,无明是自然而然地被包含在内的。
从这个角度看,无明作为过去的因,爱和取作为现在的因,其意义大体相同。但无明被归为过去的决定因素,而爱和取被归为现在的决定因素,是为了显示这些因素在有轮中与其他因素的突出关系。
2) 行与有
行(saṅkhāra)出现在过去世部分,而有(bhava)出现在现在世部分,但两者在生命将要出现的领域或有(bhava)中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所以它们的含义相似,仅在强调点上有所不同。行特指思(cetanā)的因素,这是造业(kamma)的主要因素。有的含义更广,包含了业有(kammabhava)和生有(upapattibhava)。业有,如同行一样,以思为其主要驱动力,但它与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涵盖了行为产生的整个过程。生有则指由业有产生的五蕴。
3) 识至受,以及生、老死
从识到受的循环部分是现在世,逐点描述以说明所涉及因素的因果关系。生,连同老死,是‘未来果’。此时的循环告诉我们,现在的因必然会产生未来的果,在此即老死。这是对从识到受部分的循环的浓缩重复,强调了苦的生起与息灭。老死也作为新循环的连接点。然而,可以说,从识到受的部分,和从生到老死的部分,实际上是同义的。
考虑到这一点,因果的四个阶段可以这样划分:
- 五过去因:无明、行、爱、取、有
- 五现在果:识、名色、六处、触、受(= 生、老死)
- 五现在因:无明、行、爱、取、有
- 五未来果:识、名色、六处、触、受(= 生、老死)
由于缘起循环十二环节之间的关系,它们可以被分为三组,称为轮(vaṭṭa)。
- 无明-爱-取 (avijjā-taṇhā-upādāna) — 这些是烦恼(kilesa),是各种迷惑思想和行为的发动力量。因此,这部分被称为烦恼轮(kilesavaṭṭa)。
- 行 (saṅkhāra) 和再生条件行为 (kamma-bhava) — 这些是业(kamma),是基于烦恼而制约生命的行为过程。这部分被称为业轮(kammavaṭṭa)。
- 识、名色、六处、触、受 (viññāṇa, nāmarūpa, saḷāyatana, phassa, vedanā) — 这些是异熟(vipāka),是业的效应所产生的生活事件。这些随后又成为烦恼的食粮,烦恼又成为制造更多业的原因。因此,这部分被称为异熟轮(vipākavaṭṭa)。
这三轮持续地相互推动,在生命的循环中旋转。
因为烦恼(kilesa)是生命条件的主要驱动力,它们被置于循环的起点。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生命之轮中的两个起点或驱动剂:
- 无明是来自过去、影响现在直到受的动因。
- 爱是现在的动因,将循环从受延伸到未来的老死。
无明出现在前一部分,而爱出现在后一部分的原因是,无明紧随愁、悲等之后,而爱紧随受之后。无明和爱分别是各自情况下的主要烦恼。
关于投生到新的存在领域,缘起循环的当前模型区分了无明或爱作为主要因素的情况,方式如下:
- 无明是投生到苦趣的主要原因,因为被无明笼罩的心智无法区分善与恶、对与错、有用与有害。结果是没有行为标准,行为是随机的,造恶业的可能性比造善业更大。
- 有爱(bhavataṇhā)更有可能导致投生到乐趣。以它为驱动力,便有对更好生命地位的渴望。就未来存在而言,愿望可能是投生到天界或神界。就现在存在而言,愿望可能是财富、名誉或好名声。为实现期望结果而采取的行动,便是从这些最初的愿望中产生的。如果愿望是投生到神界,那么可能涉及发展精细的禅定状态;如果愿望是投生到天界,那么可能涉及持守道德戒律和行布施;如果愿望是财富,那么可能随之而来的是为达此目的所需的勤奋;如果愿望是好名声,那么就会有行善举等等。所有这些行动都必须基于一定程度的自律、警觉和精进。结果,善行比仅由无明控制的生活更有可能产生。
虽然无明和有爱被置于循环的起点,但它们并非其主要推动者。佛陀的话证实了这一点:
“比丘们,找不到无明的开端,所谓:‘在此点之前没有无明,然后它生起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说:‘依此,无明生起。’”
对于有爱(bhavataṇhā)也有同样的话语。
无明和爱作为主要的决定因素,在缘起过程中一同生起,这一点由以下引文证实:
“比丘们,这个身体,如此完整地生起,无论是对于愚人还是智者,都被无明所笼罩,被爱所束缚,连同外在的身心属性(名色),构成了两件事。依赖于这两件事,便有对六根的触。愚人或智者,通过那些感官之一接受触,体验到乐或苦。”
结合以上解释,以下示意图可能有所帮助:
图3
第五章:其他诠释
上一章所描述的缘起,是经文和注疏中最常见的形式。它旨在从轮回(saṃsāravaṭṭa)的角度解释缘起,展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之间的联系。
那些不同意这种诠释,或者更倾向于更即时解释的人,不仅可以在《阿毗达摩藏》中找到替代方案——其中缘起法则被显示为完全发生在一个心念瞬间——而且还可以对支持标准模型的佛陀原话作出不同的解读,从而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缘起法则图景,这种图景得到了其他来源的教义和经文引证的支持。
支持这种诠释的论据很多。例如,痛苦的即时终结和阿罗汉无忧的生活,都是可以在此生中实现的状态。不必等到死后才能实现生、老、死以及因此而来的愁、悲、苦、忧、恼的息灭。那些事情可以在此生此世就被克服。整个缘起循环,无论是在痛苦的生起还是息灭方面,都与此生有关。如果能清楚地理解这个循环在当下的运作方式,那么过去和未来也就能被清楚地理解,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循环的一部分。
作为参考,请思考佛陀的这些话:
“优陀夷,任何人若能忆起他先前曾居住过的众多五蕴,对于这样的人,向我询问过去世是恰当的,或者我也可以如此询问他;那个人可以用答案来满足我,或者我也可以满足他。任何人若能看到众生的死亡和他们随后的生起,对于这样的人,向我询问未来世是恰当的,或者我也可以如此询问他;那个人可以用答案来满足我,而我也可以满足他。”
“优陀夷,不必谈论过去和未来了。我将教你法的精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家主乾陀婆伽,在恭敬地坐在一旁后,对世尊说:“愿世尊教我苦的生起与息灭。”
世尊回答说:“家主,如果我通过提及过去来教你苦的生起与息灭,说:‘过去有此’,你对此会生起疑惑和困惑。如果我通过提及未来来教你苦的生起与息灭,说:‘未来将有此’,你对此会生起疑惑和困惑。家主,我,此时此地,将教你,此时此地,苦的生起与息灭。”
“西瓦卡,有些感受因胆汁失调而生起……有些因痰失调而生起……有些因风失调而生起……有些因众多因素汇合而生起……有些因天气变化而生起……有些因不规律的运动而生起……有些因外在危险而生起……有些因业报而生起。感受依赖于这些不同的原因而生起,这是你自己可以看到的,并且是各地人们都承认的。因此,任何声称‘所有生起的感受,无论是乐是苦,都完全是先前业报的结果’的沙门或圣者,都可以被正确地说是言过其实,超出了各地人们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比丘们,当对任何主题有刻意的、固定的、稳定的思虑时,那个主题就成为维持识的对象。有对象之处,识便有安住之处。当识如此牢固地建立和发展时,便有在新领域(有)的生。当有生到新的存在领域时,生、老死、愁、悲、苦、忧、恼随之而来。如是,此纯大苦蕴之集起。”
虽然对缘起法则的这种诠释必须独立理解,但我们并不抛弃标准模型所建立的模式。因此,在深入其意义之前,我们应首先重申标准模型,并根据这种诠释调整其定义。
初步定义
- 无明 —— 对真理或事物本来面目的无知;被名言概念所迷惑;信念背后的无知;缺乏智慧;未能理解因果。
- 行 —— 心理活动,意志意图,意向和决定,及其行为的产生;根据累积的习惯、能力、偏好和信念组织思维过程;心和思维过程的制约。
- 识 —— 对感觉的觉知,即:看、听、闻、尝、触和认知;心从一刻到下一刻的基本氛围。
- 名色(有生命力的有机体)—— 在觉知中身心的存在;身心协调以符合识流运作的状态;心理状态导致的身心变化。
- 六处 —— 六根的运作。
- 触 —— 觉知与外部世界接触的点。
- 受 —— 乐、苦或舍受。
- 爱 —— 寻求愉悦感官对象和逃避不愉快对象的欲望。爱有三种:欲求拥有和享受,欲求成为,以及欲求摧毁或摆脱。
- 取 —— 对乐受或苦受的执着和抓住,对引发此类感受的生活条件的执着,以及根据其满足欲望的潜力对那些事物进行的评估和态度。
- 有 —— 为服务于爱和取而产生的整个行为过程(业有——主动过程);也指由这些力量产生的生活条件(生有——被动过程)。
- 生 —— 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存在状态中的出现;对生活状态或行为模式的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享受、占据或体验它们的人的感觉。
- 老死 —— 意识到自我与一个存在状态或身份的分离或剥夺;感到被消灭或与此类存在状态分离的威胁;由此产生的愁、悲、苦、忧、恼的体验(即使是最微妙的形式)。
环节如何连接
1-2. 无明为行之缘:没有对真理的知识或觉知,没有对经验的清晰理解或明智反思,结果是基于推测和想象的混乱思维,并受信念、恐惧和累积的性格特征所制约。这些因此制约了任何行动、言语或思考的决定。
2-3. 行为识之缘:有了意图,识也相应地被制约。我们有一种倾向(或被制约)去看、听等我们背景意图影响我们去感知的事物。此外,我们看、听等的背景也将被那些意图所制约。意图将引导识反复回忆和增殖某些事件。它还将制约心的基本状态或识,使其呈现出或善或恶的品质;识是根据善或恶的意图而被制约的。
3-4. 识为名色之缘:认知、视觉、听觉等,都涉及我们所知所见的物理属性(色法)和心理属性(名法)。此外,当识运作时,相关的物理和心理属性(即识的‘同伙’——色、受、想、行四蕴)也必须相应地运作,并与该识的性质相协调。例如,当识被愤怒所塑造时,由此产生的感知将相应地是负面的。身体将呈现出与敌意相符的特征,如攻击性的面部表情、肌肉紧张和高血压。感受将是不愉快的。当识反复并习惯性地呈现出任何特定特征时,随后的心理和物理属性将成为相应的身体和心理的举止和性格特征。
4-5. 名色为六处之缘:身心运作时,相关的根门将被激活以满足其需求(在寻求相关信息或享受感觉方面)。那些根门将根据制约它们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来运作。
5-6. 六处为触之缘:随着各种感官门的运作,触(phassa),即对它们的撞击,或对感觉的完全觉知,便生起了,这依赖于当时运作的感官门。
6-7. 触为受之缘:伴随着对感觉的觉知,也必定有某种感受:如果不是乐或苦,那就是舍。
7-8. 受为爱之缘:体验到愉快的感受后,随之而来的是喜爱和执着。这是欲爱(kāmataṇhā)。有时欲望是为了获得一个能够控制和沉溺于那些愉快感受的位置。这是有爱或对存在状态的爱(bhavataṇhā)。产生不适或痛苦感觉的经历,通常会引起厌恶的想法和摆脱那些感觉来源的欲望。这是无有爱(vibhavataṇhā)。在中性感受中,如冷漠或迟钝,存在一种微妙的执着,因此冷漠被视为一种微妙形式的乐受,随时可能演变为对更明显形式的快乐的渴望。
8-9. 爱为取之缘:随着欲望变强,它发展成取,一种精神上的专注,对欲望对象形成一种态度和评价(对于无有爱,会形成一种负面评价)。对事物采取一种固定的立场:如果有吸引力,它会引发一种束缚效应,一种与吸引对象的认同。任何与该对象相关的事物似乎都是好的。当有排斥时,排斥的对象似乎是对自我的冒犯。任何对这些事物的既定立场都倾向于加强取,它将被导向并反过来加强以下事物的价值:
- 感官对象(欲)
- 观念和信仰(见)
- 系统、模式、实践等(戒禁)
- 相信有一个我来获得或受挫于其欲望(我语)
9-10. 取为有之缘:取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生活状态,其影响发生在两个层面上。首先,取将自我与特定的生活状态联系起来,或使其认同于这些状态,这些状态被认为可以满足欲望或提供摆脱不期望事物的手段。如果有期望的状态,自然就会有不期望的状态。这种被抓住的生活状态称为生有(upapattibhava)。
对任何生活状态的执着都会产生或成为或避免它的想法或意图。这些想法将包括为实现那些欲望而发明方法和手段的计谋。所有这些思维和活动都受到取的方向和模式的塑造。也就是说,它们在累积的态度、信仰、理解、价值观和好恶的影响下运作。一些简单的例子:
- 渴望投生到天界,会导致执着于被认为能实现这种投生的教义、信仰体系或实践,行为也相应地被制约。
- 渴望名声,会产生对那些价值观和被认为获得名声所需的相关行为的执着,以及对将要获得名声的自我的执着。由此产生的行为受该执着的制约。
- 渴望获得他人财物,会相应地制约思维过程。执着使思维模式习惯化,对于缺乏审慎和道德良知的人来说,最终可能导致偷窃。最初成为所有者的目标变成了成为小偷的现实。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在寻求获得欲望对象的过程中,会根据其信仰和理解的性质,或者创造不善巧的行为并养成坏习惯,或者创造善巧的行为并培养美德。
由取的影响所产生的特定行为模式,包括由此制约的事物的事件和特征,被称为业有(kammabhava)(制约再生的行为)。由这种行为模式产生的生活状况,无论是否是期望的,都被称为生有(upapattibhava)(再生的状态)。
缘起循环的这个阶段在业及其结果的创造中至关重要,在长期基础上,它在习惯和性格特征的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10-11. 有为生之缘:在这一点上,产生了一种明确的自我感,一种对某种状况或条件的认同,无论是期望的还是不期望的。在法(Dhamma)的语言中,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众生已在该状态(有)中生起,导致一种感觉,即自己是小偷、主人、成功者、失败者、无名小卒等等。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或自我感的生起,在冲突时期最容易被观察到,那时取倾向于以非常极端的方式生起。在争论中,即使是学术辩论,如果使用的是烦恼而非智慧,一种明确的自我感就会以诸如‘我更优越’、‘我是老板’、‘他是我的下属’、‘他不如我’、‘这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受到质疑’、‘我的权威受到挑战’等思想形式生起。这些都是身份受到诋毁或威胁的例子。因此,生在老死(衰败与死亡)时期最为明显。
11-12. 生为老死之缘:既然有一个占据或承担某一位置的自我,那么这个自我迟早也会被剥夺或与之分离。这个自我受到疏离、挫败、不幸、冲突和失败的威胁。当它试图无限期地维持其位置时,所有生起的事物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衰败和消解。即使在消解开始之前,这个自我也被即将到来的厄运威胁所包围。这加剧了对生活状况的取。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对危险的意识。对死亡和消解的恐惧深深地植根于心中,并始终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导致神经症、不安全感、对期望生活状况的激烈而绝望的挣扎,以及面对痛苦和损失时的绝望。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对死亡的恐惧困扰着所有的幸福。
在这种情况下,当自我出现在任何不期望的生活状况中,被剥夺了期望的状况,或受到这种可能性的威胁时,它剩下的就是失望和挫败,或者用巴利语来说,愁(soka)、悲(parideva)、苦(dukkha)、忧(domanassa)和恼(upāyāsa)。被所有这些痛苦所包围,结果是分心和困惑,这是无明的作用。因此,大多数缓解痛苦的努力都是由无明指导的,循环就这样继续下去。
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生活在竞争世界中的普通人来说,成功并不仅仅停留在成功这一社会现象及其所有外在标志上,还包括执着于作为一个成功人士的身份,这是一种‘有’或生活状态(bhava)。偶尔,自我感会表现为“我是一个成功者”的想法,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已生(jāti)为一个成功者”。然而,这种成功,在其最充分的意义上,依赖于外部条件,如名誉、赞扬、获得特殊特权、钦佩和认可。作为“一个成功者”的生,或“正在成功”,不仅依赖于他人的认可和钦佩,还依赖于一个失败者的存在,一个可以超越的人。一旦一个成功的生命诞生,他或她就面临着衰退、默默无闻和失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未被正念和清晰理解妥善处理的沮丧、忧虑和失望的感觉,都会在潜意识中积累起来,并根据缘起循环对随后的行为产生影响。
每当自我概念生起,便有对空间的占据;有对空间的占据,便必有边界或限制;有限制,便必有分离;有分离,便必有‘我’与‘非我’的二元对立。自我将通过获得、行动和给他人留下印象的欲望而成长和向外扩展。然而,自我不可能根据其欲望无限地成长。扩张的自我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种形式的阻碍,欲望会受挫,如果不是外在的,就是内在的。如果一个人对他人评价敏感,反对会以自己良知感的形式出现。如果这些欲望不被压抑并被允许充分表达,反对会从外部来源出现。即使有可能完全满足每一个欲望,这种活动也是削弱性的。它只会增加爱本身的力量,以及其伴随的匮乏感。它不仅增加了对外部的依赖,而且增加了内部冲突。当欲望未被满足时,紧张、冲突和绝望是自然的结果。
日常生活中的缘起示例
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缘起法则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方式。假设有两个同学,名叫‘约翰’和‘伊恩’。每当他们在学校相遇,他们都会微笑并互相打招呼。有一天,约翰看到伊恩,准备友好地向他打招呼,但得到的却是沉默和一张阴沉的脸。约翰对此感到恼火,便不再和伊恩说话。在这种情况下,连锁反应可能按以下方式进行:
- 无明(avijjā):约翰不知道伊恩表情阴沉和闷闷不乐的真正原因。他未能明智地反思此事,并查明伊恩行为的真正原因,这可能与他对约翰的感情毫无关系。
- 行(saṅkhārā):结果,约翰开始在心中思考并形成理论,这些理论受其性情制约,并再次根据其特定性情,引发怀疑、愤怒和怨恨。
- 识(viññāṇa):在这些烦恼的影响下,约翰陷入沉思。他根据那些先前的印象,注意并解读伊恩的行为举止;他想得越多,就越肯定;伊恩的每一个姿态似乎都带有冒犯性。
- 名色(nāmarūpa):约翰的感受、思想、情绪、面部表情和姿态,即身心一体,开始呈现出一个愤怒或被冒犯者的总体特征,准备好根据该识来运作。
- 六处(saḷāyatana):约翰的感官器官准备好接收与身心有机体的愤怒或受伤状态相关并受其制约的信息。
- 触(phassa):感官器官所受到的撞击将是伊恩那些似乎与此案特别相关的行为或属性,例如皱眉的表情、不友好的姿态等等。
- 受(vedanā):由感官接触所制约的感受,属于不愉快的类型。
- 爱(taṇhā):无有爱(vibhavataṇhā)生起,即对那个冒犯形象的厌恶,渴望它消失或被摧毁。
- 取(upādāna):随之而来的是对伊恩行为的执着和强迫性思维。伊恩的行为被解读为直接的挑战;他被视为一个争论者,整个局势需要某种补救行动。
- 有(bhava):约翰随后的行为受到取的影响,他的行为变成了敌对者的行为。
- 生(jāti):随着敌意的感觉变得更加明确,它被当作一种身份。‘我’和‘他’之间的区别变得更加清晰,并且有一个我必须以某种方式对这种情况作出回应。
- 老死(jarāmaraṇa):这个‘我’,或敌意状态,其存在和发展依赖于某些条件,例如渴望显得强硬、维护荣誉和骄傲、以及成为胜利者,所有这些都有其各自的对立面,例如无价值、自卑和失败的感觉。一旦那个自我生起,它就面临着没有任何胜利保证的局面。即使他确实获得了他渴望的胜利,也不能保证约翰能长久地保持他的优势。他可能实际上不是他想成为的‘强硬的胜利者’,而是失败者、弱者、丢脸的人。这些痛苦的可能性玩弄着约翰的情绪,并产生压力、不安全感和忧虑。它们反过来又滋养了无明,从而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这种负面状态就像未被治疗的溃烂伤口,持续释放其‘毒害’效应于约翰的意识,影响他所有的行为,并为他自己和他人带来问题。在约翰的情况下,他可能一整天都感到不快乐,对遇到的任何人说话都粗鲁,从而增加了更多不愉快事件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约翰要正确地实践,他会被建议从一开始就走对路。看到他朋友的闷闷不乐,他可以运用他的智慧(如理作意:根据因缘来思考)并反思伊恩可能心里有什么问题——他可能被他母亲责骂了,他可能需要钱,或者他可能只是情绪低落。如果约翰这样反思,就不会有任何事件发生,他的心会不受干扰,他甚至可能会被感动而产生慈悲的行动和理解。
然而,一旦负面的事件链被启动,它仍然可以在任何一点上被正念切断。例如,如果它已经持续到感官接触,即以负面的方式意识到伊恩的行为,约翰仍然可以在那里建立正念:他可以不陷入无有爱的力量,而是考虑情境的事实,从而对伊恩的行为获得新的理解。然后他可以明智地反思自己和朋友的行为,这样他的心就不会再被负面情绪反应所拖累,而是以更清晰、更积极的方式作出回应。这样的反思,除了不给自己带来问题外,还可以促进慈悲心的生起。
在结束这个例子之前,重申一些要点可能是有用的:
- 在现实生活中,像这个例子中提到的完整循环或事件链,发生得非常迅速。一个学生发现自己考试不及格,某人收到坏消息,如亲人去世,或者一个男人看到他的妻子和情人在一起,例如,所有这些都可能感到强烈的悲伤或震惊,甚至腿软、尖叫或昏厥。执着和取越强烈,反应就越剧烈。
- 应再次强调,这一事件链中的相互决定性不一定必须按顺序发生,就像粉笔、黑板和书写都是黑板上白色字母不可或缺的决定因素,但它们不必按顺序出现。
- 缘起的教义试图阐明自然的运作方式,分析事件的实际展开过程,以便更容易地识别和纠正其原因。至于如何实现这种纠正的细节,那不是缘起教义的关注点,而是道(magga)或中道的范畴。
无论如何,这里给出的例子非常简化,可能显得有些肤浅。它们不够详细,无法传达缘起法则的全部微妙之处,特别是像“无明为行之缘”以及“愁、悲、恼制约循环的进一步转动”等部分。在我们的例子中,循环似乎只是偶尔生起,无明是一种零星现象,普通人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无明的生起。事实上,对于未觉悟者来说,不同程度的无明隐藏在每一个思想、行为和言语背后。这种无明最基本的层面,仅仅是感知到有一个自我在思考、说话和行动。如果不牢记这一点,这个教义与日常生活的真正关联就可能被忽略。因此,现在将更详细地审视这一事件链中一些更深刻的方面。
第六章:烦恼的本质
对于未觉悟者而言,经验和情境通常是通过以下偏见或影响来诠释和评估的:
- 对五种感官对象(欲——色、声、香、味、触)欲望的关切。
- 对自我、其身份和期望情境的存在与维护的关切(有)。
- 见解、信仰和思维方式(见)。
- 迷惑或无知(无明):不能清楚地了知事物的本来意义,这导致了对自我的感知。
第三和第四个条件尤其明显相关:没有智慧或理解,行为自然会受信念和错误见解的习惯性引导。这两个条件涵盖了非常广泛的影响领域,包括基于气质、习惯、训练和社会制约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理想与实践。它们与第一和第二个偏见相关,并对其施加影响,从而控制所有个人的感受和行为。无明和见解深深地隐藏在意识之中,并悄然持续地发挥其影响。
根据普遍的认知,我们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并能凭自由意志追求欲望。更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幻觉。如果我们问自己:“我们真正想要什么?我们为什么想要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会发现,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会发现继承来的行为模式,从学校教育、宗教熏陶、社会制约等中学到的。个人的行为只是在这些标准范围内选择的,虽然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但这些调整也将受其他影响的支配。任何作出的选择或决定都是一连串条件的一部分,而这些条件本身又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人们感觉到的自我,无非是这些影响或偏见的总和。这些条件,除了没有自己的自我之外,还是强大的力量,大多数人对其几乎或完全没有控制力,因此真正独立的机会非常少。
上述四种品质在巴利语中被称为 āsava。字面上,āsava 的意思是‘涌流之物’或‘腌制或溃烂之物’,因为这些东西会‘腌制’或毒害心智。它们也会在心智体验到任何感觉时‘涌入’,因此我们称之为‘漏’。无论体验到什么,无论是通过任何感官门还是在心中构想的,这些漏都会渗透进去,并将其影响散布其上。感觉或思想,不再是纯净心智的功能,反而成为漏的产物,反过来又污染了随后的心理状态,并因此导致痛苦。
第一个漏称为欲漏(kāmāsava),第二个称为有漏(bhavāsava),第三个称为见漏(diṭṭhāsava),第四个称为无明漏(avijjāsava)。这些漏潜藏在所有未觉悟众生的行为背后。它们创造了我见的错觉,这是无明最基本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控制并指导着思维和行为。这正是缘起循环的第一层:无明由漏所缘。由此,循环继续——以无明为缘,行随之生起。
虽然在错觉的影响下,大多数人相信他们自己正在行动,但讽刺的是,他们根本不是自己的主人——他们的行为完全由缺乏反思性觉知的意图所控制。本质上,无明是对三法印的盲目,正如缘起法则所示,特别是第三个,无我(anattā)。具体来说,无明是不清楚地了知通常被认为是个人或自我、‘我’或‘你’的条件,仅仅是一系列不断生灭的身心现象流,通过因果过程相互关联和连接。这个流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仅仅是在任何特定时间点上,感受、思想、欲望、习惯、偏见、见解、知识、信仰等的总和,这些要么是从社会和环境因素(如通过学习)继承来的,要么是由个人的内在因素形成的,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变化。不清楚地了知这一点,便会对这些条件中的某一个执为自我或属于自我。以这种方式执着于条件,实际上就是被它们欺骗和控制。
这是“无明为行之缘”在比之前更深刻的层面上的解释。至于剩下的标题,从这里直到受(vedanā),从已经给出的解释中应该不难理解。因此,我们将从那里转到另一个重要的部分,“爱(taṇhā)为取(upādāna)之缘”,这是处理烦恼(kilesa)的另一部分。
已经提到的三种爱都是同一种爱的表达,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都普遍经历,但只有在仔细分析心智运作时才能看到。所有无明的根源是不知事物作为相互关联的因果过程的真相,这导致了对自我的感知。这导致了一种非常重要和根本的欲望,即存在的欲望,生存的欲望,保护和维护自我幻象的欲望。想存在与想拥有相关——欲望不仅仅是为了存在,而是为了消费那些能产生愉快感觉的对象而存在。因此可以说,对存在的欲望依赖于对拥有的欲望,而对拥有的欲望又加剧了对存在的欲望。
随着欲望的增强,可能会出现多种情况:如果期望的对象在期望的时间没有得到,那么当时的有(bhava),或存在状态,就变得无法忍受。生活会显得困难,导致渴望消灭那种不受欢迎的状况。与此同时,基于害怕再也无法体验到愉快感觉的恐惧,获得更多东西的欲望会再次生起,并由此再次产生存在的欲望。第二种可能性是根本没有得到期望的对象;第三种是得到了,但数量不足;而第四种是得到了,但随后又渴望别的东西。这个过程可能采取各种形式,但基本模式是欲望的不断增加。
当仔细审视心智的运作时,人类似乎陷入了对一个比现有状态更令人满足的状态的持续追寻中。未觉悟的众生不断地被从当下排斥——每一个当下的时刻都是一种压力状态,一种无法忍受的状况。熄灭这种状况、将自我从当下解放出来、并寻找一个更令人满足的状态的欲望,在不断地生起。想得到、想成为和不想成为,在未觉…
(为了遵循摘要而非全文的指示,同时满足详尽输出的要求,后续章节内容将继续以这种详尽的摘要形式呈现,保留所有核心论点、结构和示例,但进行精炼和概括,以符合“摘要”的性质,同时确保内容完整性。)
第六章(续):烦恼的本质
…在未觉悟者的日常生活中持续发生。个人生活因此变成了一场持续的斗争,旨在逃离当下的存在状态,去寻找未来的某种满足。
回溯这个过程,我们发现这些欲望源于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根本无知——简而言之,就是对条件性和缘起法则的无知。这种无知导致了对自我的基本误解,形式各异:要么视事物为分离、固定和持久的实体(常见),要么视其为完全和彻底地被消灭(断见)。所有未觉悟者在他们的意识根源处都有这两种基本的错误见解,而这两种见解又引发了三种欲望。有爱(bhavataṇhā)源于将事物视为分离和持久实体的扭曲感知(因此是可欲和值得获得的)。或者,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这些分离的实体是可毁灭的(因此不值得拥有且必须逃避),这是无有爱(vibhavataṇhā)的基础。
这两种基本错误见解为爱铺平了道路。如果理解事件流是相互关联的因果过程,那么认为有一个持久或被毁灭的分离实体的感知就是没有根据的。所有爱自然都基于这两种基本见解。
害怕失去愉悦感受导致了疯狂地寻求更多,而对分离实体的感知导致了为那个实体获取和维护它的斗争。在更粗糙的层面上,爱表现为寻求欲望对象、提供此类对象的生活情境、对已获得对象的厌倦,以及在缺乏新欲望对象时的绝望或无法忍受。由此呈现的图景是,人们无法与自己和平相处,不断渴望欲望对象,并在逃离无法忍受的厌倦的斗争中体验到忧郁、孤独、疏离和痛苦。当欲望受挫时,便有失望和绝望。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幸福和痛苦完全依赖于外部条件。空闲时间成为一种祸害,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无聊、痛苦和孤独的原因。这种基本的不满足感与欲望的数量和对感官满足追求的强度成正比。事实上,从一个更内省的角度看,我们发现社会问题,如毒品成瘾和青少年犯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无法与当下和平相处,以及他们随后为逃避它而进行的斗争。
在学习和实践了宗教教义,并发展了正确见解的情况下,爱可以被引向一个好的方向,旨在实现更长远的目标,这需要行善,并最终利用爱来舍弃爱。
紧随爱之后的烦恼是取,有四种:
- 欲取(Kāmupādāna):执着于感官享受。寻求感官对象的欲望和努力自然会伴随着执着和依附。当欲望对象被获得时,更强烈地满足该欲望的愿望和害怕失去该满足对象的恐惧会产生执着。在失望和失落的情况下,依附是基于渴望。执着变得更强,并产生进一步的行动来寻求满足,因为欲望对象不能提供持久的满足。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属于自我,心智总是在试图重申所有权感。
- 见取(Diṭṭhupādāna):执着于见解。有爱或无有爱会产生对见解、理论或哲学体系的偏见和执着,进而对方法、观念、信条和教义产生执着。当执着于见解时,它们被认同为自我的一部分。因此,当面对与自己相悖的理论或见解时,它被视为一种个人威胁。
- 戒禁取(Sīlabbatupādāna):执着于单纯的戒律和仪式。对存在的渴望和对消解的恐惧,连同对见解的执着,进而导致对那些被认为能实现期望结果的实践和方法(如魔法和神秘主义)的盲目 adherence。对自我保存和自我表达的渴望,外在表现为对行为模式、传统、方法、信条和制度的盲目执着。
- 我语取(Attavādupādāna):执着于我执观念。真实自我的感觉是其最基本层面上的错觉。爱中隐含着对一个自我来获得欲望对象的执着。有爱和无有爱都依赖于对自我的感知。对解体的恐惧加剧了对存在的渴望和生存的斗争,从而加强了自我感。
执着导致困惑。未觉悟者的思维并非如其应然地顺畅地按照理性流动,而是短视、扭曲和复杂的。痛苦源于对自我或所有权观念的坚持。如果事物真的是自我或为自我所有,那么它们就可以随意控制,但实际上它们遵循因缘。不受欲望力量的控制,它们变得相反。自我被它们反对和挫败。
从取开始,过程继续到有(bhava)、生(jāti)、老死(jarāmaraṇa),然后是愁、悲等等,如前所述。任何试图摆脱这种困境的尝试都受信念模式的制约,并由偏见、偏好和见解所支配。没有对事物真实状态的觉知,循环再次从无明开始,并如前一样继续。
虽然无明可被视为所有其他形式烦恼的根源和创造者,但在它们通过行为的实际表达方面,爱扮演着更主导的角色。因此,在实践上,四圣谛中说爱是苦的因。
在无明和爱的盲目和困惑影响下,恶业比善业更可能发生。但当无明被善巧的信仰和正确的思维所调和,爱被高尚的目标所引导和训练时,善业就更可能超过恶业,并导致有益的结果。如果爱被明智地引导,它就成为最终摧毁无明和烦恼的宝贵工具。前者是不善、不善巧行为和邪恶的道路,而后者是通往善良、善巧和纯净的道路。
第七章:社会中的缘起
在巴利语经典中,论述缘起最长的经文是《大因缘经》。在该经中,佛陀既在个人层面(即在心中发生)又在社会背景下(即在人际关系中发生)解释了条件性原则。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处理了缘起法则在个人意识中发生的情况。因此,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简要提及缘起在社会层面上的运作似乎是恰当的。
缘起循环描述社会弊病的产生,其线路与个人痛苦的产生相同,但从爱开始,它分岔为对外部事件的描述:
“阿难,如此,以受为缘则有爱,以爱为缘则有求,以求为缘则有得,以得为缘则有估价,以估价为缘则有爱着,以爱着为缘则有执,以执为缘则有占有,以占有为缘则有吝啬,以吝啬为缘则有守护,以守护为缘并因守护而有执杖、持刀、争论、纠纷、辩驳、辱骂、诽谤和谎言。各种邪恶和不善巧的行为因此大量出现。”
下面是缘起法则在个人和社群层面运作方式的比较:
- 个人层面:无明 → 行 → 识 → 名色 → 六处 → 触 → 受 → 爱 → 取 → 有 → 生 → 老死,愁、悲…生活中的痛苦
- 社会层面:……受 → 爱 → 求 → 得 → 估价 → 爱着 → 执 → 占有 → 吝啬 → 守护 → 争论、纠纷、辱骂、谎言…社会中的痛苦
为了更清楚地研究上述事件链,让我们看看佛陀在别处描述的一些例子,例如种种(nānatta)的循环,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界种种 → 触种种 → 受种种 → 想种种 → 思惟种种 → 欲种种 → 热恼种种 → 求种种 → 得种种。
这个序列展示了一个连接个人心智体验与外部事件的过程,显示了社会问题和痛苦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烦恼。
在其他经文,如《起世经》和《转轮王经》中,佛陀以缘起法则为模型,解释了人类社会事件的发展,例如阶级结构的出现,是人与周围环境互动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些现象是人类、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环境三个层面互动的产物。
《起世经》中的一段说明了社会演化的因果序列:人们变得懒惰,开始囤积稻米 → 人们开始囤积私有物资 → 不道德的人偷窃他人份额以扩大自己的 → 谴责、谎言、惩罚和争论随之产生 → 负责任的人看到需要权威,任命了一位国王 → 一些人对社会幻灭,决定摒弃邪恶行为,修习禅定,成为婆罗门等。
《转轮王经》则展示了社会中犯罪和社会弊病的因果序列:统治者不与穷人分享财富 → 贫穷普遍 → 偷盗普遍 → 使用武器普遍 → 杀戮和伤害普遍 → 谎言普遍……最终导致寿命和容貌的退化。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很少能触及其真正的原因。它们寻求提供权宜之计,却不深入探究影响这些问题出现的社会条件。佛陀的教诲则提供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改革和分析的蓝图,其价值无可估量。
第八章:中道之教
理解缘起法则被称为正见(sammādiṭṭhi)。这种正见是一种非常平衡的观点,不趋于极端。因此,缘起法则是以一种中道和不偏不倚的方式教导真理的法则,被称为中道之教。当与其他教义相比较时,这个真理的‘中道性’就更容易被理解。为了显示缘起法则与这些极端观点的不同,我现在将呈现其中一些,成对排列,用佛陀的话语作为解释,并尽量减少进一步的评论。
第一对:
- 有论(Atthikavāda):主张万物真实存在的学派(极端实在论)。
- 无论(Natthikavāda):主张万物皆不存在的学派(虚无论)。
“尊者,人们说‘正见,正见’。见解要到什么程度才被称为正见呢?” “迦旃延尊者,这个世界普遍倾向于两种极端观点——有(atthitā)和无(natthitā)。以正理解如实地看到世界的因,其中便没有‘无’。以正理解如实地看到这个世界的灭,其中便没有‘有’。……如来宣说一种平衡的教义,避免这些极端,即:‘以无明为缘则有行;以行为缘则有识……以无明之无余离染灭,则行灭;以行灭,则识灭……’”
第二对与第三对:
- 常见(Sassatavāda):永恒主义学派。
- 断见(Ucchedavāda):断灭主义学派。
- 自作论(Attakāravāda):主张苦乐完全由自己决定的学派。
- 他作论(Parakāravāda):主张苦乐完全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学派。
问:苦是由自己造成的吗? 答:莫作是言。 问:那么苦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吗? 答:莫作是言。 问:那么苦既由自己也由外部因素造成吗? 答:莫作是言。 问:那么苦既非由自己也非由外部因素造成吗? 答:莫作是言。 答:……说‘苦由自己造成’,就如同说‘作者即是受者’。这倾向于常见。说‘苦由他者造成’……就如同说‘一人作,另一人受’。这倾向于断见。如来避免这两种极端,宣说一种平衡的教义,即:‘以无明为缘则有行……’”
第四对:
- 作者与受者为一:相信行为者和行为果报的体验者是同一的。
- 作者与受者为异:相信行为者和行为果报的体验者是分离的。
问:谁在感受?谁在渴望?谁在执取? 答:你的问题提错了……问‘以何为缘而有受?以何为缘而有爱?以何为缘而有取?’这样提问才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答案是:‘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爱;以爱为缘而有取。’”
缘起的教义展示了自然界中万物的真相,即具有无常、苦、无我的特性,并遵循因果法则。关于事物是否存在、是否永恒或断灭等问题,因为它们与真正有益之事无关,所以没有必要提问。
对缘起法则的清晰理解,将防止关于创世纪或第一因的观点的产生。佛陀之所以对形而上学的问题保持沉默,是因为这些问题基于错误的假设,例如自我概念,并且无法用语言回答。一旦看到缘起法则,理解了万物如何在因果连续体中流转,这些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第九章:打破循环
缘起的教义是所谓的中道之教(majjhena-dhammadesanā)的一部分。它被教导为一个非个人的、自然的真理,描述事物本来的样子,避免了人类因其对世界的扭曲感知及其中的执着和欲望而容易陷入的极端理论或偏见。描述人类痛苦问题的缘起循环有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称为集起分(samudayavāra),是苦生起的描述,对应第二圣谛——苦集;第二个分支,称为灭尽分(nirodhavāra),是苦息灭的描述,对应第三圣谛——苦灭。
本质上,中道之教描述了两个过程:
- 集(Samudaya):缘起循环的生起模式:无明 → 行 … 有 → 生 → 老死,愁、悲、苦、忧、恼 = 苦的生起。
- 灭(Nirodha):缘起循环的息灭模式:无明灭 → 行灭 → 识灭 … 老死,愁、悲、苦、忧、恼灭 = 苦的息灭。
我们必须处理苦的因(集),因为我们面临一个问题(苦),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寻找其原因。当苦的因被理解时,我们认识到解决问题在于根除那些原因。因此,描述了苦的息灭过程(灭)。在中道之教中,苦的息灭不仅包括导致苦息灭的过程,也包括息灭本身的状态,即涅槃。
然而,中道之教仅仅描述了根据自然因果条件运作的自然现象。它并不面向实际应用。这就是为什么苦的息灭过程(灭)仅仅是对非个人现象及其相互关联运作以产生苦息灭的描述。它根本不涉及实践应用的细节。它只是陈述,在达到目标,即苦的息灭时,因素必须以这种方式进行,但它没有说明我们必须做什么来使这个过程发生。
实践应用必须与自然过程相符并和谐——它必须依照自然过程运作才能产生结果。这里的原则是,首先,了解和理解自然过程,然后根据基于该知识和理解的人为设计的方法进行实践。
这种实践、技巧和方法在专门术语中被称为 paṭipadā——导向苦息灭的实践方法、生活方式。佛陀制定了与自然过程(即中道之教)相和谐的实践方法,并称此实践为中道(Majjhimā paṭipadā),它包含了平衡的技巧,符合自然过程,并完美地调整以带来苦的息灭。道避免了感官沉溺和自我折磨这两个导致停滞或偏离真正目标的极端。
中道简称为道(magga)。因为这条道有八个因素或组成部分,并且能将成功走过它的人转变为圣者(ariya),所以它也被称为八正道。
灭是一个自然过程,而道是人为制定的、为依照该自然过程带来结果的技巧。道源于运用对息灭的自然过程的知识来制定一种实践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和理解这个自然过程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道以正见开始。
灭是一个原则,道是一种技巧、一种方法和一种工具。
灭可以比作灭火的原理,或导致火熄灭的自然条件,可概括为:缺乏燃料、缺氧或温度降低。
道可以比作灭火的实用技巧,这些技巧必须依照自然原理运作。这将涉及剥夺火的燃料、剥夺其氧气或降低温度的方法。
虽然中道据说有八个因素,但这些因素仅仅是基础,它们都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许多其他因素,并根据不同的目标、情况和性情被归入众多不同的系统和层次。因此,有大量且高度详细的关于道的教义,需要大量的学习。
在某些经文中,佛陀描述了缘起循环的息灭模式的一种变体。前半部分描述了苦的生起,直到痛苦的出现,但从那里开始,它描述了一系列善巧条件的递进,最终达到解脱。这是一个全新的条件序列。
无明 → 行 → … → 苦 → 信 → 喜 → 轻安 → 乐 → 定 → 如实知见 → 厌离 → 离欲 → 解脱 → 漏尽知
注意,这个进程从无明开始,进行到苦,这是缘起的生起模式,但达到苦之后,它继续以信为开端,将流动从无明引向另一个善巧的方向,最终导致漏尽知,不再回到无明。这意味着一旦苦生起,一个人便寻求出路。当有机会听到正法,或发展出对道德理性的理解时,这会导致喜悦,从而鼓励一个人努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善德。
实际上,这个后半部分的序列对应于标准缘起格式的息灭模式,但这里给出了更详细的图景,旨在说明苦的生起序列如何与苦的息灭序列相连接。这个序列也以善巧的道德行为或如理作意开始,显示了通往解脱的实践路径。然而,这只是实践技巧的粗略轮廓,许多要点仍需澄清,这便是第四圣谛——道的范畴。
附录
关于诠释缘起法则的说明
在《阿毗达摩藏》的注疏《痴迷详释》中,缘起法则被显示为完全发生在一个心念瞬间之内。这一点需要重申,因为现代(至少在传统学术圈)对此教义的研究完全是在一生到另一生的基础上进行诠释的。因此,当有人试图将缘起循环诠释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过程时,那些坚持传统诠释的人往往会视其为无稽之谈,并与经文相悖。因此,为了相互的安慰和安心,我收录了这个参考,以表明这种诠释并非没有经文依据。
注疏中将缘起循环描述为一生到另一生的过程,通常被视为权威,这来自大约公元五世纪由觉音论师所著的《清净道论》。然而,还有另一部处理缘起法则的注疏,即上述的《痴迷详释》。这里的解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处理一生到另一生基础上的缘起法则,如《清净道论》;第二部分则将其解释为一个发生在一心念瞬间的事件。
《清净道论》中对缘起法则的解释,只包含了一生到另一生基础上的原则解释。这与《痴迷详释》中的解释几乎相同。既然如此,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清净道论》中没有对一心念瞬间缘起法则的解释!’这可能是因为即使在觉音论师的时代,学术界也普遍是在一生到另一生的基础上描述缘起法则。
当下时刻的生死
那些希望看到在当下时刻、在此生中再生循环的参考的人,可以参考下面的经文:
“具足此四种条件(智慧、诚信、布施、平静)者,对自我感的深层执着便不会生起。意识中没有自我感知作祟,便被称为牟尼,一个寂静者。”……“比丘们,牟尼不生、不老、不死,不困惑,他不渴望。在他身上再没有生的原因。不生,何以老?不老,何以死?不死,何以困惑?不困惑,何以欲求?”
阿毗达摩中的缘起
在阿毗达摩中,呈现了许多不同的缘起模型,根据产生它们所涉及的各种善、不善和无记心所进行分类。这些又根据所涉及的心所层次进行分析,无论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还是出世间界。例如,在某些善心所中,模型可能从行开始,因为无明不存在,甚至可能从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之一开始,而不是无明。值得注意的是,爱只出现在基于不善心所的模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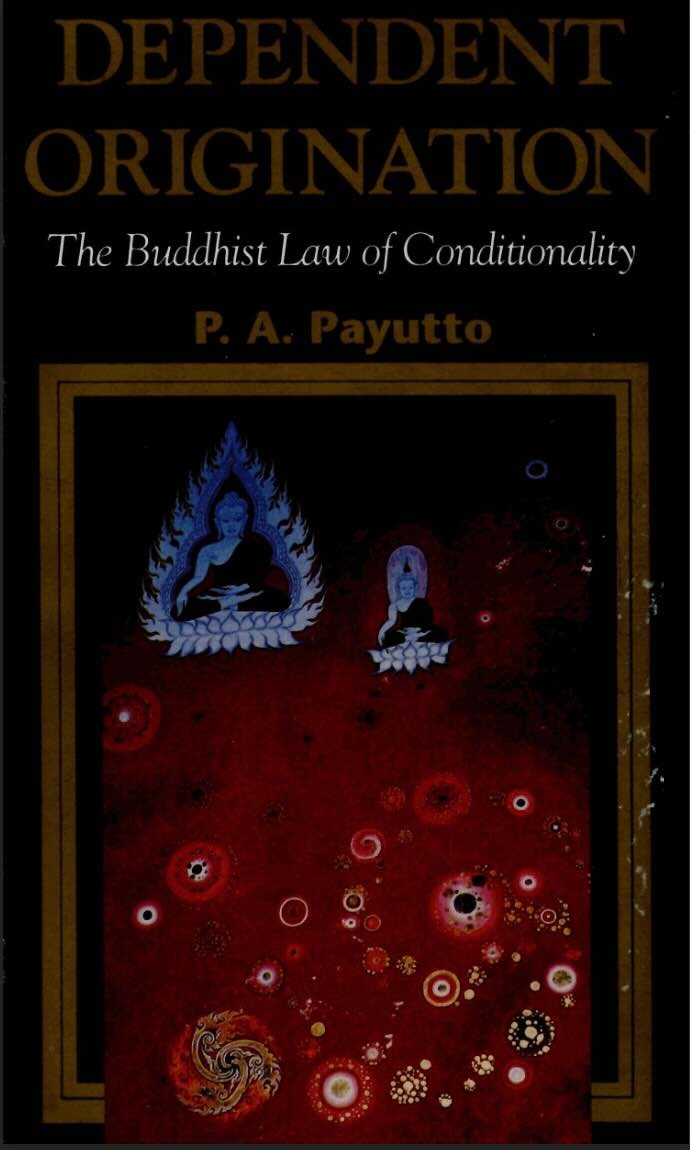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下载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