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亦安乐,死亦坦然
巴育陀尊者, 生老病死, 南传上座部佛法 ·Index
อยู่ก็สบาย ตายก็เป็นสุข - 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พุทธโฆษาจารย์ (ป. อ. ปยุตฺโต)
生亦安乐,死亦坦然 - 巴育陀尊者 - 摘要
智者洞见目标,身处悲戚,亦无忧愁。
第一章:生亦安乐,死亦坦然
生与死,还是生与死?哪一对才正确
人,活着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有生命”;当生命终结时,我们称之为“死亡”。因此,生命与死亡似乎是相对的,简称为“生与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生命终点的死亡,仅仅是生命历程的一端。生命在抵达终点之前,是从一个起点开始的,这个起点就是“出生”。开始与结束是相对的。从这个角度看,死亡并非与“生命”本身相对,而只是与生命的“开始”相对。因此,死亡应该与出生配对,简称为“生与死”。
大多数人习惯于第一种视角,即将死亡与生命视为对立。当他们想到死亡时,会立刻关联到自己的生命,并停留在那里,只想着“活着”与“死亡”的对决。
当思想停留在“活着”与“死亡”的对立上,内心会执着于“自我”的存在感。人们会从与自我相关的角度去思考死亡,认为死亡是对自我的冲击或将失去自我,这让他们感到恐惧和战栗:“我就要死了,我的生命将不复存在。”
因此,大多数人在想到死亡、看到死者或面临死亡时,会感到恐惧、惊慌,或是悲伤、沮咒。反之,如果想到的是自己憎恨的敌人之死,他们又会觉得自我得到了满足,从而心生欢喜。
人们普遍习惯并深陷于这种思维模式,以至于在某些文化和语言中,人们只谈论“生命与死亡”,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其真正对等的概念是“出生与死亡”。“出生”和“死亡”被分开讨论,仿佛两者毫无关联。
这种视角为错误的生活方式打开了大门。我们可以看到,当有婴儿出生时,人们尽情地欢乐庆祝;当有人去世时,人们则悲痛欲绝,仿佛自己也要随之而去。在这之间,人们浑浑噩噩、沉湎放纵地生活,为了争夺而互相伤害,缺乏正念的引导和智慧的指引,无法为生命和社会带来真正的利益与安乐。
相反,如果我们将死亡与出生配对来看,思想就不会停滞于“自我”之上。因为我们是从生命的一端越过它,看到了另一端。
当以这种正确的方式看待时,生命就变成了一种自然的现象,就像我们观察身外的其他事物一样。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按照其因缘条件,从起点(出生)迈向终点(死亡)的进程,而不再执着于自我的感觉。
这种视角更符合生命的实相,为正念与智慧开启了更广阔的空间。它引导我们去理解和洞悉生命本来的样子,或许能让我们减轻,乃至超越在念及、目睹甚至直面死亡时的恐惧、沮丧和悲伤。
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真相。既然无法回避,我们就应该学会如何正确地对待它,以求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伤害降至最低。
善于忆念死亡,将获得利益
佛陀教导我们要学会忆念死亡。关于这个主题的法教,既有针对第一种视角(认为死亡是自己生命的终结)的人的教导,教他们如何将负面的沮丧和恐惧转变为有益的美好心境;也有引导人们进入第二种视角(将生与死视为自然过程)的教导,从而生起智慧,让心灵获得彻底的自在与究竟的安乐。
学会忆念和审视死亡以获得益处,这被称为“念死”(Maranasati),其修习方法和效果可概括如下:
-
在第一种观察层面
- 认清生命的短暂与无常:人的生命不仅短暂,而且充满不确定性,正如俗话所说“不知今日死,还是明日亡”。这让我们认识到时间的宝贵,从而生起不放逸之心,激励自己抓紧时间履行职责、积累善行、在各方面发展自我,让生命活得有价值,并趋向崇高的目标。
-
洞悉身外之物的本质:要明白财产、财富以及我们所爱的人,并非真正属于我们。它们无法阻止死亡,死后也无法带走,只是今生暂时的使用和联系而已。
- 对于财物:我们会因此不过分贪婪和囤积,或吝啬不用于正途,让其形同废物。我们会懂得合理分配和使用它们,为自己、亲友和他人创造价值,实现其真正的意义。
- 对于亲人:我们会不过分执着和牵挂,以免在分离时产生过度的痛苦,导致内心不安、辗转反侧。同时,我们会意识到自己无法永远陪伴他们,从而用心教育和培养他们,让他们学会自立。
- 对于邻居和他人:我们会更富同情心,乐于助人。即使发生矛盾或心生怨恨,也能很快平息,因为想到“何必互相怨恨呢?不久我们都将离世,不如彼此相爱,善待对方。”
-
深切体认业力法则: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业”(Kamma),唯有业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是真正能伴随自己的财产,我们也将随业而去。明白这一点后,我们便会断除并远离恶业,只造作善业,并将财富用于行善和利益他人的事业。 当真正面临或目睹死亡时,对业力法则的深刻认识还会带来特别的益处:
- 当面对自己的死亡时:如果能忆起自己所做的善业,且未见己身有恶业,内心便会充满喜悦,能以平静、有念的状态面对死亡。即使死亡尚未到来,也能充满信心地生活,不畏惧危险,不害怕死亡。
- 当亲友离世时:我们能迅速或及时地调整心态,明白“人人皆有其业,他已随业而去”。我们的哭泣和悲伤对他毫无帮助。这样一来,就不会产生悲伤,即使产生了也能很快平息,迅速消散。同时,当放下对逝者的眷恋后,我们会将注意力转向那些被留下的、还活着的人。我们会思考:“这些人是我能帮助的,他们有什么痛苦是我能消除的吗?”然后我们会去帮助他们,至少以慈悲的眼光和心意看待彼此。我们深知,逝者已逝,我们无能为力;而生者不久后也终将离别。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应以慈悲相待,互相帮助,以免日后再添遗憾:“唉,我本想为他做些什么,还没来得及,他就又离开了。”
- 忆念众生平等的法则:应忆念“一切众生都害怕伤害,一切众生都畏惧死亡;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宝贵的。我如此,他们也如此。”推己及人,我们便不应互相残杀伤害。这样的忆念会让我们生起同情心,不互相侵害,转而互相帮助、和谐共处、善待彼此,甚至做到“待人如待己”,或“己所欲,施于人”,共同建设一个和平安乐的世界。
-
在第二种观察层面
- 洞悉自然的法则:生命受自然法则支配,其过程是自然的:以“生”为始,必以“死”为终。有生,必有死。死亡是已出生生命的终结。 总之,有生必有死。(老、病)死是生命的常态,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现象。这就是无常(Anicca)的特性。逝去的人只是遵循这个自然法则,每个人都将如此,我们自己也不例外。“无常”只是在如实地履行它的职责。因此,为此感到悲伤是既不恰当也无必要的。如此思惟,便不会恐惧,也不会产生痛苦;即使痛苦生起,也能在短时间内减轻或消除。
生亦安乐,死亦坦然
- 彻知诸行(Sankhara)的实相(从“念死”深入到“观禅”/Vipassana):彻底洞悉此真理:生命是“行”(有为法),是众多元素的组合,由各种因缘条件和合而成。它是无常的,生起之后,终将灭去。生与死,是其自然规律。 不仅是我们所见的这个有形有情的生命如此,构成生命的每个部分,以及宇宙万物,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受制于这无常的法则。它们都经历“生、住、异、灭”的过程。它们呈现何种样貌,完全取决于因缘条件,而不随任何人的意愿或执着而改变。若想改变结果,必须从因缘条件着手。
当透彻了悟这个实相后,心便能从对万物的执取中解脱出来。心灵会变得自在、清明、轻安、透亮,充满智慧。我们以智慧生活,以智慧行事,时刻都能安乐喜悦,超越痛苦,证得真正的自由与和平。
完成了第一种生命视角修习的人,对死亡的态度如佛经所言:
“我于何处都未曾作恶,是故我不畏惧死亡的到来。”
“安住于正法,便无惧于来世。”
而圆满彻证第二种生命视角的人,其对生命与死亡的态度,则如法语所诠释:
“生存,不为之烦扰;死亡,亦不为之悲伤。若为智者,洞见目标,纵然身处悲戚之中,亦无忧愁。”
“我既不喜爱死亡,也不执着于生命。我将有觉知、有正念地放下此身;我既不喜爱死亡,也不执着于生命。我等待那一刻的到来,如同雇工完成工作后,等待领取工资。”
第二章:病中如何安顿我心
我们身为佛教徒,以三宝为至高无上的皈依处。三宝即佛、法、僧。以佛陀为核心,佛陀是觉悟并发现“法”(Dhamma)的人。当他发现并了知真理后,便将此“法”教导给他人。那些遵循教法并获得实证的人,合称为“僧”(Sangha)。
佛陀所发现的“法”,就是关于世界和生命实相的真理。佛陀关注人类的苦与乐,并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此课题,以求清晰地了解人类的苦乐是如何生起的。如果问题——也就是“苦”——出现了,该如何解决。可以说,佛陀是生命领域的专家,因此他能善巧地解决我们的人生问题,这也是我们皈依他的主要原因。
人的生命由“身”和“心”两部分构成。身与心结合,成为我们的生命。无论是身还是心,都必须保持在良好状态,必须维护健康,我们才能拥有快乐,生命才能顺利前行。
但是,人不可能事事如愿。我们的身体有时会生病,原因可能是外部疾病的侵袭、季节变化,或被坚硬物体碰撞,甚至只是被刺扎到,都会引起疼痛。又或者,身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老,这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的病苦。这被称为“行”(Sankhara)的特性,即由因缘和合而成的事物,它们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依赖众多因素的聚合。
我们的身体由多种因缘和合而成,古人称之为“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的聚合。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是变动不居、无常的。当每个部分都在变化时,作为整体的身体自然会发生紊乱,从而导致疾病。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身体并非独立存在,它必须与心协同,才能构成生命。心同样如此,它也经历着各种变化。心念变动,时而生起贪、嗔、痴等烦恼。心随烦恼而变:贪时,想要这个那个;嗔时,愤怒怨恨,内心烦躁;痴时,则有种种沉迷和颠倒。
相反,当心中生起善法,生起美德,心便会清净美好,喜悦舒畅,这便是快乐。此时,心中会有慈悲等美德,会善待他人;或有“信”,如对三宝、对善业的信心。心可以如此千变万化。
身与心的关联在于:当身体生病时,往往会干扰心,让心也随之不悦。因为身体的疼痛会让心感到痛苦;或者身体虚弱,不受控制,心便会因不能如意而烦躁。这就是身心互相依存的关系。当身体不适,心也容易随之不适。
反过来,当心不适时,如有痛苦、忧虑、恐惧、担心、不如意、失望、气馁等情绪,也会通过身体表现出来,例如面容憔悴、肤色暗淡、笑容消失,甚至食欲不振、浑身无力。因为心没有力量,心力不足,身体也会随之疲软。这也是身心相互依存的表现。
有时,身体的病痛是重大的事件,身体的剧痛可能会让心也随之不安。佛法中说,如果身体不适,心也随之不适,这叫做“身病,心亦病”。
那么,当身体生病时,如何让心不随之动摇呢?佛陀对生命有深入的研究,并找到了帮助人们获得快乐的方法。
佛陀曾遇到身体抱恙、生病的人。他教导说,应在心中作意,告诉自己:“纵然我身患病,我的心决不随之生病。” 如此立志,即是保持“正念”(Sati),让心不受身体变化的控制和影响。有正念在,就能守护好自己的心。
守护好心是至关重要的。 生病时,身体是医生的事,医生去治疗;但心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必须自己守护。所以,我们可以分工合作,放下心来说:“好了,我的身体病了,这是医生的事,就让医生去治吧。我配合治疗,不必焦虑担忧。我只管守护好我的心。”
依照佛陀的教导来守护心,正如刚才引述的佛语,立定决心:“纵然我身患病,但我的心决不随之生病。”
简单地说,就是告诉自己:“身病,心不病。”
若能坚守此念,正念便在,心就不会随身体的症状而烦躁、衰弱或波动。
当然,身体的苦受、疼痛、虚弱等,自然会对心产生影响。但如果能善护己心,痛苦就会减轻许多。因此,佛陀总是强调要守护好自己的心。
如何守护心?用“正念”来守护。正念就像一根绳索。要让心安住,就要用这根绳索把心拴住。我们的心躁动不安,喜欢攀缘外境,胡思乱想,就像一只顽皮的猴子,在树枝间跳来跳去,永不停歇。所以佛陀教导说,要抓住这只“心猴”,用绳子将它绑在柱子上。
柱子是什么?柱子就是良善、不造作的所缘境,或者是导向良善的思维,如佛陀的教诲、善业功德等。当心被系于其上,心就能安住,不散乱、不飘浮、不迷惘。当心停止了无谓的造作和散乱,问题就消失了。
心无造作,便无束缚;心无压迫,便无痛苦。心会变得清明、敞亮,不被生起的苦受所笼罩。
除了将心系于佛陀的教诲等善法上,也可以用一句简单的佛号来作为正念的所缘,例如“Buddho”(佛陀)。
“Buddho”这个词非常美好,是佛陀的圣号。当我们将它作为心的依靠时,心就不会散乱飘浮,而会变得良善、清明。因为佛陀的圣号代表着纯净、智慧、觉醒和喜悦。忆念此圣号,有助于心保持清明、宁静,不陷入散乱的思绪。
“Buddho”意为“觉悟者、觉醒者、喜悦者”。佛陀了知万物实相,了知“行”的本质,如实了知世界与生命,拥有帮助众生解脱痛苦的智慧。觉悟后,他便从种种沉睡中“觉醒”,不再有任何沉迷和执着。觉醒后,无有沉迷,便只有“喜悦”。喜悦时,便有快乐,心灵自由而敞亮。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应如实了知“行”,应觉醒,不沉迷于万物,不执着于一切,从而获得内心的喜悦与自在。我们可以将“Buddho”作为座右铭,用正念忆持,在心中默念“Bud-”,然后“dho-”。
如果能配合呼吸,效果更佳:吸气时念“Bud”,呼气时念“dho”。或者不配合呼吸,只是在心中有节奏地持续默念“Bud-dho”。这是培养正念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能引领心趋向禅定。
当正念将心安住于“Buddho”一词时,心便不散乱,不胡思乱想。心不散乱,便能安稳地住于善法中,不再是忧郁之心,而是充满光明、喜悦与快乐。这即是实践“守护心,不令生病”的要旨。
以上所说,是关于如何用正念守护心的一个例子,即用正念作绳,将心系于“Buddho”等所缘上,使心有依靠,不散乱飘浮,获得宁静、喜悦与光明。
我愿以此增强你的心力,愿你的心能安住于“身虽病,心不病”的决心中,或以正念忆持佛陀的功德,念诵“Buddho”,让心恒常保持喜悦与光明。
愿你正念分明,心常安住于喜悦光明之中,时时刻刻,恒常如此。
第三章:给病患家属的佛法开示
首先,随喜各位邀请我们两位僧人前来接受僧团供养。这是各位与亲友们一同为正在病中的父亲所做的功德,表达了对他的忆念、爱与关怀,希望能助他早日康复。
作为佛教徒,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行善积德。亲近三宝,仰仗功德福报以及佛、法、僧三宝的威德力来护持,是极为重要的。
在病苦这个关键时刻,心的状态至关重要——不仅是病人的心,也包括所有关心他的亲友的心。治疗必须双管齐下:既要治身,也要治心。
真正生病的是身体,但在身体患病时,心也往往会随之“生病”,即心可能会因身体的苦受或虚弱而变得脆弱或紊乱。
因此,佛陀教导我们要如此立志:“纵然我身患病,但我的心决不随之生病。” 佛陀如此教导,是为了让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依然能保持坚强,然后让这颗坚强的心反过来帮助身体。
如果心随身体一同生病,只会让病情雪上加霜。但如果身病而心不病,这颗心反而能成为一股力量,支撑、扶持身体。若心力足够强大,甚至能帮助身体恢复健康。
我们都看到,病人在病中非常需要心力支持。如果自己无法生起心力,就需要他人的帮助。而最能给予心力支持的,就是亲人。因此,佛法教导亲近的人要给予病患精神上的鼓励。
但关键问题在于,作为亲人,因为爱与牵挂,有时自己的心也会随之“生病”,变得不安。这样一来,就无法给病人带去力量。所以,必须有方法让自己的心也变得坚强、安适。
当我们这些怀着善意的亲友之心变得坚强安适时,就能帮助病人也变得更加坚强。因此,在这种时刻,如何安顿自己的心,是极为重要的。
身体的治疗,是医生的责任,他们会依据专业知识进行处理。但对于病患家属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关照“心”。除了提供日常的便利和照顾外,更应做的是守护好自己和病人的心,让彼此的心都充满力量。
对于家属自己,首先应让内心保持清明、安适。至少可以这样想,让自己安心:“我所爱的人病了,我没有抛弃他,而是尽全力地照顾他。”当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时,首先就能获得一份心安,告诉自己:“我已经尽力做到了最好。”
尽责之后,心中便会生起一份安适。由这份安适而来的力量,会默默地支持和鼓舞病人,无论病人是否有意识。
人的心,我们无法完全揣度。有时,感官上似乎没有知觉,但内心深处仍有感知。即使是失去意识的人,在某些层面也可能会做梦,或有微细的感受。这种精神层面的感知是极为敏锐的,他或许能感受到周围安详快乐的氛围,从而获得心力,至少能减少牵挂,让心更坚强。清明、安适、光明、喜悦的心,本身就是美好的。
心的力量至关重要。子女们放下工作,前来陪伴照顾,正是源于爱与关怀之心。但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份爱与关怀,可能让我们的心变得焦虑不安。美好的事物,有时反而会成为痛苦的因缘,正如佛法所说“爱别离苦”。因为爱,所以有执着,就容易受到伤害。
那么,如何才能既有爱,又没有苦呢?这需要以智慧来引导这份爱。 当我们能正确地安顿自心,就能保留爱的美好部分,让它只剩下善与乐。这份爱会成为我们关心照顾彼此的动力,而经过智慧守护的爱,会使我们的心清明、敞亮,成为互相帮助的力量。
因此,应如前所述,审视自心:我们是否已尽到责任?审视过后,若已尽责,便可获得第一步的安心。
接着,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忧虑和悲伤,对躺在病床上的他毫无帮助。 真正能帮助他的,是良好的精神状态、内心的清明、喜悦与光明。
即使从我们自身的角度看,要想思路清晰、行事妥当,也需要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如果内心焦躁不安,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都会导致思绪混乱,行事错乱。
要想获得好的结果,必须有一颗宁静、坚强、清明、喜悦的心。
因此,核心原则是:让美好的部分,引生出更美好的部分。 对父亲的爱是美好的,应让这份爱在心中生起喜悦与光明。然后,用这颗美好的心来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安排照顾和治疗,并让自己的心境成为一种助力,帮助病人的心也获得安适。
试想,当病人感受到子女们围绕在身边,用心关怀着他,他会感受到爱,并因此生起一份心力和快乐。
同时,如果所有子女的心都是安详的,他便不必为你们担忧,这也能帮助他的心获得安宁。当他内心安宁、充满力量时,亦是对他身体康复的一种助益。
此时此刻,除了努力调整自心、以智慧思惟来增强心力外,我们还能借助功德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并非孤军奋战,还有善业功德在滋养着我们的心。
各位因为爱护父亲,为他修福,这份功德的力量将成为增强他心力的助缘。请大家将心念集中到父亲身上,祈愿这份功德的力量能够滋养、守护他。
行善时,我们会礼敬三宝,这是内心最深沉的依靠。当我们皈依三宝时,心便会变得坚强、有力、宁静、清凉。愿这份清凉成为环绕所有亲友及病人的氛围,扶持、滋养他,让他身心都得以恢复和强健。
借此机会,我随喜各位为令尊所做的供僧功德。此善举能让心灵美好,滋养内心,带来清新、光明、快乐、安详与宁静。愿这份喜悦、清凉、宁静的心,带来吉祥的善果,即身心健康、安乐与圆满的康复。
接下来,请各位接受祝福,并用心为父亲祈祷,愿他能随喜领纳这份功德。也愿各位共同营造一个宁静、喜悦、光明的氛围,日日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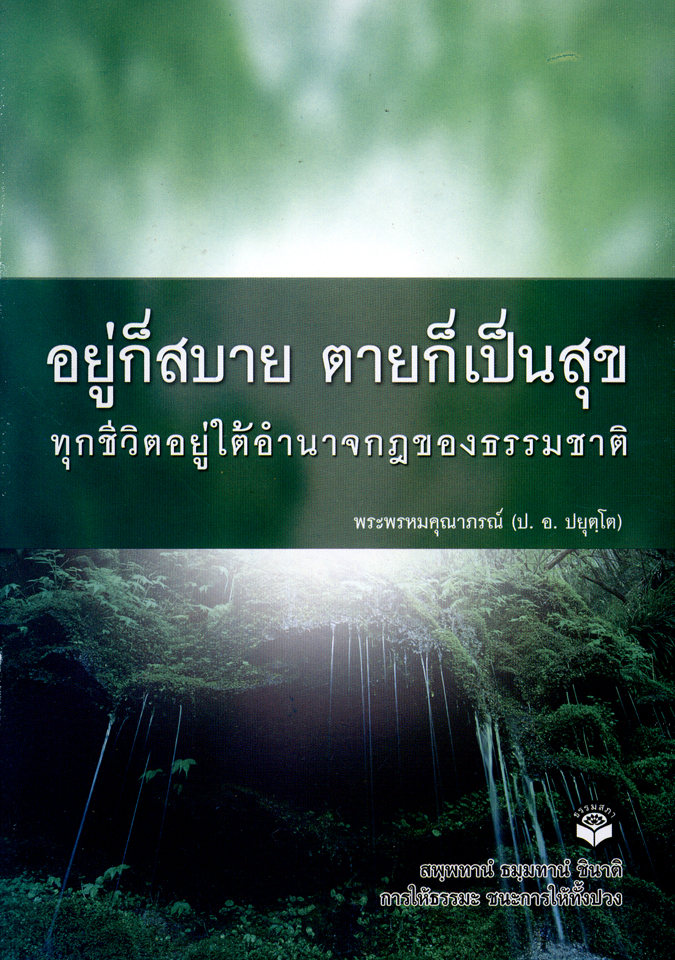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下载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