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
心理学 ·Index
Irresistible: The Rise of Addictive Technology and the Business of Keeping Us Hooked - Adam Alter
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 - 亚当·奥尔特 - 摘要
这本书剖析了技术如何精心设计,利用心理弱点让我们行为上瘾,并提供了实用的策略,帮助我们在刷屏时代重获生活掌控权。
楔子 令人上瘾的时代
2010年,史蒂夫·乔布斯推出了iPad,他认为人人都应该拥有一台。但他却从来不让自己的孩子用这台设备。一位记者发现,其他科技巨头也都对自己的孩子设定了类似的限制。生产高科技产品的人,仿佛遵守着毒品交易的头号规则:自己绝不能上瘾。
这真叫人不安。为什么全世界最大的公共技术专家,私下里也最害怕技术?
他们发现了两件事情。首先,我们对上瘾的理解过于狭隘。实际上,上瘾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和氛围促成的。瘾君子和我们其他人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只要出现合适的产品或体验,谁都有可能上瘾。其次,数字时代的环境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容易叫人上瘾。20世纪60年代,危险的东西不多,可到21世纪,到处都是诱饵:Facebook、Instagram、色情、电子邮件、网购……
现代化高科技效率高,上瘾性强。设计并提炼此类技术、游戏和互动体验的人,对数百万的用户运行了上千次的检测,了解哪些手法管用、哪些不管用。随着技术体验的演进,它武装到了牙齿,变得无法抵挡。2004年的Facebook很有趣;2016年的Facebook让人上瘾。
新一代上瘾跟摄入某种物质无关,但它们产生的效果相同——因为它们吸引力强,设计得当。行为上瘾由6种要素构成:
- 可望而不可即的诱人目标
- 无法抵挡、无法预知的积极反馈
- 渐进式进步和改善的感觉
-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困难的任务
- 需要解决却又暂未解决的紧张感
- 强大的社会联系
本书追溯了上瘾行为的兴起,考察了它们始于何处,出自何人的设计,让它们吸引力如此之强的心理设计技巧,怎样最大限度地减少危险的行为成瘾,并借助相同的科学原理驾驭它们的益处。关键是要理解为什么行为上瘾如此猖獗,它们怎样利用了人类的心理,我们怎样打败害人不浅的上瘾,同时驾驭那些能帮助我们的上瘾。
第一部分 行为上瘾是什么
第1章 行为上瘾的兴起
应用开发人员凯文·霍尔什设计了一款名为“时刻”(Moment)的应用程序,用于跟踪每天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长。大多数用户都低估了自己的使用时间。数据显示,用户平均每天使用手机近3个小时,拿起手机39次。如果按我们每天清醒16个小时计算,这相当于清醒时间的近四分之一。平均而言,人们每个月有近100个小时迷失在手机屏幕前,这相当于人一生中的整整11年。
智能手机并非唯一的罪魁祸首。游戏设计师贝内特·福迪玩过数千款电子游戏,但始终拒玩“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因为他担心自己一旦玩起来,就会投入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魔兽世界”是全球最容易让人行为上瘾的体验之一,全体玩家里有一半都认为自己“上瘾了”。
行为上瘾是什么
现代定义认为,只有当一种行为此刻带来的奖励最终因为其破坏性后果而抵消,才叫行为上瘾。它指的是对难于戒除的有害体验的深度依恋。行为上瘾与摄入特定物质无关,但如果人无法抵挡一种短期内可解决深刻心理需求,长期而言却会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这才是行为上瘾。
近一半人都有行为上瘾
行为上瘾到底有多常见?根据一项对83项研究、覆盖150万受访者的综述性论文,在过去12个月里,总人口的41%都至少存在一种行为上瘾。这些瘾头减损了我们生活的意义,让我们在工作和玩耍里丧失效力,削弱了我们与他人的互动。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总人口中高达40%的人存在某种形式的互联网上瘾。微软公司报告称,普通人的注意力幅度已从2000年的12秒下降到了2013年的8秒,比金鱼的9秒还短。
社交媒体对孩子的伤害
许多孩子跟数字世界的第一次相遇,始于注意到家长“在战斗中失了踪”。分心的家长会培养出分心的孩子。等他们进入中学,社交生活就从现实世界转移到了数字世界。在线互动跟现实世界的互动不同,由于缺乏直接的非语言反馈,共情得不到发展。许多青少年拒绝当面沟通,而是通过短信展开战斗,这显然是学习沟通的一种可怕方法。一个13岁的女孩说:“我感觉自己不再像个小孩了……课间做游戏,玩玩具,这一切,全没了。”
游戏的超强上瘾性
游戏开发商阮东因(Dong Nguyen)曾发布一款名为“笨鸟”(Flappy Bird)的简单游戏,该游戏一夜爆红,但也因其极强的上瘾性而备受争议。许多玩家抱怨它“毁了生活”,阮东因最终因良心不安而将游戏下架。
人们如今对上瘾的认识超过了19世纪,但上瘾本身也在随着时间演变。化学家们危险地炮制出了上瘾物质,设计体验的创业家们也在炮制令人同等上瘾的行为。
第2章 我们所有人的心瘾
越南战争期间,大量驻越美军士兵因无聊和易得性而染上了高纯度的海洛因。战争结束时,近20%的人报告自己上了瘾。这一情况让美国政府极为恐慌,他们预计将有10万名海洛因瘾君子回国。
只有5%的士兵毒瘾复发
通常情况下,海洛因的复发率高达95%。然而,精神病学家李·罗宾斯(Lee Robins)的研究发现,回国的越战老兵中,只有5%的人复发。这个惊人的结果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悖。为什么95%的退伍军人能轻易戒除毒瘾?答案在于环境的改变。
任何人都能成为瘾君子
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詹姆斯·奥尔兹(James Olds)和彼得·米尔纳(Peter Milner)的实验偶然发现,电击大鼠大脑的特定区域(后被称为“快感中枢”)能产生强烈的愉悦感。实验中的大鼠会不吃不喝,一次又一次地按压杠杆以获得电击,直至力竭而死。
这个实验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这只大鼠并非天生就是瘾君子,它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地点的受害者。只要碰到合适的情况,任何人恐怕都能成为瘾君子。
诱使人们上瘾的是环境
越战老兵们能够摆脱毒瘾,正是因为他们脱离了那个诱使自己上瘾的环境。他们在越南时,身边充满了战争的压力、无聊以及随处可见的毒品。而当他们回到美国,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那些与吸毒行为相关的线索(triggers)都消失了。他们的经历证明:瘾头嵌在记忆里,而环境是触发这些记忆的关键。
重回犯罪现场的危险性
前游戏瘾君子艾萨克·韦斯伯格(Isaac Vaisberg)的故事就是一个反例。他曾因沉迷“魔兽世界”而退学、健康恶化。在接受治疗后,他不顾劝告回到了原来的大学环境,结果很快复发,连续5个星期将自己锁在公寓里玩游戏。他的经历表明,即便在治疗后,重回旧的上瘾环境也是极其危险的。导致上瘾的原因很多,但并不存在什么天生的“爱上瘾的性格”。环境扮演着比我们想象中更重要的角色。
第3章 行为上瘾的生物学机制
游戏上瘾的大脑模式与吸毒相同
神经科学家发现,吸毒和行为上瘾激活的是相同的大脑奖励中心。无论是注射海洛因还是完成一轮“魔兽世界”任务,大脑深处的区域都会释放化学物质多巴胺,产生强烈的快感。虽然毒品产生的响应更直接、更强烈,但大脑神经元点火启动的模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随着大脑对多巴胺的喷涌产生耐受性,要达到最初的高峰就需要更大的剂量,无论是更多的毒品,还是更投入的游戏。
上瘾的根源是心理痛苦
上瘾并非单纯的大脑功能障碍。如果不是因为心理上的痛苦(如焦虑、抑郁、孤独),我们不会成为药物或行为的奴隶。上瘾行为成了一种应对机制,用以缓解这些痛苦。作家马娅·萨拉维茨(Maia Szalavitz)甚至认为,上瘾是一种受了误导的爱。它是一种学习过程:大脑得知某种药物或体验对于情绪稳定至关重要。
任何体验都可能导致上瘾
心理学家斯坦顿·皮尔(Stanton Peele)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我们对所爱之人产生的健康依恋,同样可能具有破坏性。他认为,任何能缓解心理困扰的体验都可能导致上瘾,无论是爱情、赌博、购物还是锻炼。上瘾是“对一种极度有害于人的体验产生极端的、不正常的依恋,但这种体验又是人生态的根本部分,人无法放弃它”。
上瘾不是喜欢,而是渴望
神经学家肯特·贝里奇(Kent Berridge)的研究挑战了“上瘾等于快感”的传统观念。他通过实验发现,多巴胺系统驱动的其实是“渴望”(wanting),而不是“喜欢”(liking)。瘾君子之所以难以戒断,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渴望”毒品或某种行为,哪怕他们早已不再“喜欢”这种体验,甚至痛恨它对自己生活的毁灭性影响。
渴望远比喜欢更难打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瘾君子复发,即使他们已经痛恨毒品毁了他们的生活。行为上瘾也是一样:就算讨厌Facebook耗费了太多时间,可你仍然想频繁地访问它。
第二部分 上瘾体验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第4章 诱人的目标
目标能激发行动,但它们也可能是挫折的来源。你要么忍受成功之后的失落,要么忍受失败带来的沮丧。
- 并不兴奋的世界冠军:1968年,鲍勃·比蒙(Bob Beamon)在奥运会跳远比赛中创造了惊人的世界纪录。但在这场巨大成功之后,他感到的却是空虚和失落。“我以后要做什么呀?”他问自己,“我这一辈子下一次的巅峰体验会是什么?”
- 成功是通往失败的路标:追求目标的主要缺陷在于,你在追求目标上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享受成功的果实。就算你成功了,成功也很短暂。一旦到达了那里,你会发现,你弄丢了那件赋予了你目的感的事情——于是你只好制订新的目标,重新开始。这助长了上瘾般的追求,孵化出一个强似一个的新目标。
第5章 不可抗拒的积极反馈
“点赞”是我们时代的可卡因
心理学家迈克尔·泽勒(Michael Zeiler)的实验发现,鸽子在奖励不确定(50%-70%的概率)时啄按钮最为狂热,频率几乎是确定奖励时的两倍。原因是,当奖励出乎意料时,大脑释放的多巴胺比可以预料时更多。
Facebook的“赞”按钮正是利用了这一原理。用户每次分享照片或状态,都是在进行一次小小的赌博。一篇帖子可能获得很多赞,也可能无人问津。这种不可预测的反馈,让人们有更强烈的动力去追求它,使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数字可卡因”。
输可以伪装成赢
现代老虎机通过精巧的设计,让赌徒感觉自己一直在赢,即使他们实际上在输钱。当玩家同时玩多条线路时,即使总的投入大于回报(净亏损),只要有一条线路中奖,机器就会播放胜利的音乐和闪烁的灯光。心理学家称之为“伪装成赢的输”(losses disguised as wins)。大脑对这种伪装的胜利和真正的胜利做出了同样的情绪反应,这使得赌徒很难停下来。
“差一点儿就赢了”好过“总是赢”
“差一点儿就赢了”的体验比真正的胜利更能激发人的动机。当人们感觉自己离成功仅一步之遥时,会产生强烈的动力去再次尝试,以消除功亏一篑的失望感。这种心理被广泛应用于彩票和游戏中,让玩家相信“胜利即将来临”,从而持续投入。
第6章 毫不费力的进步
最让人上瘾的游戏,其诀窍在于让新手和高手都能获得满足感。
- 完全无门槛的游戏:宫本茂设计的“超级马里奥”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毫无上手门槛。玩家无需阅读说明书,在游戏开始的几秒钟内就能通过实践学会基本操作,享受到通过经验获得知识的感觉。这种设计让新手能够毫不费力地取得进步。
- “新手运”是个大坑:新手运让人上瘾,因为它先向你展现成功的喜悦,接着又猛地把它夺走。许多游戏会在前期提供即时满足和快速奖励,让玩家迅速上手并获得成就感。但随着游戏的深入,获得奖励的难度会迅速增加,玩家为了重获最初的荣耀感而被迫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
- 吸血游戏的机制:许多免费游戏(如“金·卡戴珊:好जीलlywood”)利用“能量系统”或“应用内购买”来盈利。它们让玩家免费开始,但在关键节点设置障碍,迫使玩家付费才能继续或加速进程。这种模式利用了玩家的损失厌恶心理——已经投入了时间和精力,便不愿轻易放弃。
第7.章 逐渐升级的挑战
激励人心的掌控感
“俄罗斯方块”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掌控感。玩家努力将随机落下的砖块拼搭成有序的结构,完成一排后它便会消失,带来短暂的快乐,而屏幕上留下的都是未完成的错误,这驱使玩家不断尝试去纠正它们。这种“劳动带来喜爱”的“宜家效应”是许多上瘾行为背后的主要力量。
最近发展区与玩乐回路
“俄罗斯方块”的难度会随着玩家的进步而逐渐提升,使其始终处于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所说的“最近发展区”——即任务难度刚好比玩家当前能力高出一点点。这种状态下,人会体验到心理学家契克森米哈伊所说的“心流”(Flow),即完全沉浸在任务中,忘记时间流逝。在游戏中,这被称为“玩乐回路”(ludic loop),是保持玩家持续投入的关键。
第8章 未完成的紧张感
蔡格尼克效应
心理学家布尔玛·蔡格尼克(Bluma Zeigarnik)发现,未完成的体验比已完成的体验更多地占据我们的脑海,这被称为蔡格尼克效应。当一项任务开始后,内心会产生一种完成它的需求,形成一种紧张系统。如果任务未完成,这种紧张感会持续存在,使得我们对它记忆犹新。
吊胃口的播客与被掐断的故事
热门播客《连环》(Serial)和电视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大结局都巧妙地利用了蔡格尼克效应。它们在结尾留下了悬而未决的“袢子”(cliffhanger),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种开放式结局引发了观众持续数年的热烈讨论,因为大脑天生要求故事的“闭合”,而未解之谜会持续占据我们的注意力。
一看到底的剧集
Netflix的“后播”(post-play)功能(一集结束后自动播放下一集)极大地助长了“一看到底”(binge-watching)的行为。它移除了“是否要看下一集”的决策障碍,将默认选项设置为了“继续观看”。观众必须主动做出停止的决定,而大多数人会选择阻力最小的方式——什么也不做,让下一集自动开始,从而陷入一个接一个的“袢子”中无法自拔。
第9.章 令人痴迷的社会互动
评估自我价值的需求
Instagram之所以能击败功能相似的Hipstamatic,关键在于它内置了一个强大的社交网络。我们发布照片,不仅是为了记录,更是为了与他人分享并获得反馈。点赞、评论和转发成为评估自我价值的标尺。由于这种社会反馈是不确定的,我们会被驱使着不断发布内容,以寻求肯定。这种对社会认可的追求,是社交媒体上瘾的核心。
平衡社会肯定与个性化
“火辣不火辣”(Hot or Not)网站的成功,在于它同时满足了人类两种基本动机:社会肯定的需求(当自己的评分与大众一致时)和个性化的需求(当自己的评分与大众不同时)。这种反馈机制让人既能感受到归属感,又能体会到独特性,从而持续地参与其中。
再也无法适应现实互动的孩子
过度沉迷于网络社交,尤其是对于青少年,会带来“情绪弱视”的风险。就像在关键发育期只看垂直条纹的小猫无法识别水平线一样,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足够的面对面互动,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掌握解读非语言情绪线索、建立现实亲密关系等关键社交技能。他们的大脑会像“腌黄瓜”一样,永久地被改变,难以适应现实世界的复杂社交。
第三部分 如何远离行为上瘾
第10章 让孩子远离行为上瘾
儿童特别容易上瘾,因为他们缺乏成年人的自控能力。
- 自然交流提升孩子社交能力:一项夏令营研究发现,让孩子们离开屏幕五天,完全沉浸在自然和面对面的互动中,能显著提高他们解读非语言情绪线索的能力。这表明,直接的人际交往对于培养社交技能至关重要。
-
设定健康的屏幕使用时间:
- 幼儿(2岁以下):专家建议应完全避免接触屏幕。在这些关键的发育期,幼儿通过与真实的人和物体互动学得最快。
- 学龄前儿童:应鼓励家长共同参与的屏幕时间,将屏幕内容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学习迁移),选择互动性强、节奏慢的内容,而非被动观看。
- 青少年:“重启”(reSTART)等治疗中心提倡“可持续地”使用数字技术,而非完全禁绝。这意味着要设定明确的界限,确保技术不会挤占睡眠、体育活动、家庭时间和线下社交。
- 家长应该如何做:心理学家建议家长应保持“平易近人、镇定、知情而现实”。避免因恐慌而制定苛刻的规则,而是要了解孩子使用的平台,与他们进行开放的对话,并设定清晰、一致的家庭规则(例如,规定用餐时间为无屏幕时间)。
第11章 改变习惯和行为构建
使用意志力的人会最先失败
试图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来压抑或戒除上瘾行为,往往会适得其反。心理学家丹·韦格纳(Dan Wegner)的“白熊实验”表明,你越是努力不去想某件事,就越是会想到它。禁绝和意志力这套组合拳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它让你时刻关注着你想要避免的东西。
用好习惯代替坏习惯
改变习惯的黄金法则是:保留旧的线索和奖励,但用一个新的惯例来替代坏的惯例。例如,对于因压力而咬指甲的人,线索是“压力”,奖励是“缓解感”。可以用“捏减压球”这个新惯例来代替“咬指甲”,同样能获得缓解感。关键在于找到满足同样潜在需求的新行为。
构建远离诱惑的环境
最有效的策略是行为构建(behavioral architecture),即重新设计你的环境,让诱惑远离你。 * 物理距离:将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充电,而不是床头柜上。这利用了“邻近原则”——身边有什么,你就会被什么吸引。 * 增加障碍:使用像WasteNoTime这样的应用来限制访问特定网站的时间。为看下一集Netflix设置障碍,比如在“袢子”出现前就关掉电视。 * 借助负面反馈:像Pavlok腕带这样的设备,在你做出坏习惯时给予轻微电击,利用厌恶疗法来打破习惯。或者像SnuzNLuz闹钟,每当你赖床,它就会自动向你讨厌的组织捐款。 * 削弱心理迫切性:使用像Facebook Demetricator这样的工具,隐藏点赞和评论的数量。这不会阻止你使用社交媒体,但会消除那些驱动强迫性查看的数字指标。
第四部分 用行为上瘾做好事
第12章 游戏化
驱动行为上瘾的心理机制,同样可以被用来做好事。这个过程被称为“游戏化”(Gamification)——将非游戏的体验(如学习、健身、工作)转变为游戏。
- 让正确的事情更有趣:瑞典一项名为“乐趣理论”的活动,将地铁站的楼梯变成了钢琴键,结果走楼梯的人数增加了66%。这表明,乐趣是改变行为的强大动力。
- 游戏化的核心元素:成功的游戏化通常包含三个要素:分数(Points)、徽章(Badges)和排行榜(Leaderboards)。例如,健身应用Fitocracy通过奖励分数和徽章来激励用户锻炼;语言学习网站FreeRice每答对一道题就捐赠大米,将学习与慈善结合,并提供分数和等级。
-
游戏化的应用:
- 健康:游戏化的牙刷鼓励孩子刷满两分钟;虚拟现实游戏“冰雪世界”通过分散注意力来帮助烧伤患者减轻疼痛。
- 教育:“学之远征”(Quest to Learn)学校将整个课程设计成游戏任务,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参与度。
- 工作:LiveOps呼叫中心使用游戏化仪表盘,通过积分和排行榜提高了员工的效率和满意度。
然而,游戏化也有其潜在危险。它可能会排挤掉内在动机,让人们仅仅为了“好玩”或外部奖励而行动,一旦趣味消失,行为也难以持续。
尾声 不上瘾,我们能做到
我们常常陷入“历史终结”的错觉,认为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将永远持续下去。但行为上瘾仍在起步阶段,未来十年将涌现出比现在更具沉浸感和吸引力的新技术与平台。
出路并非放弃技术,而是要有意识地设计我们与技术的关系。我们可以创造保留一些不工作、不玩游戏、不使用屏幕的“关机时间”。在这些屏蔽了技术的空间里,我们直接与彼此沟通,不再依靠设备。这些实体社交纽带的粘合力,比屏幕的粘合力更能让我们感到丰富和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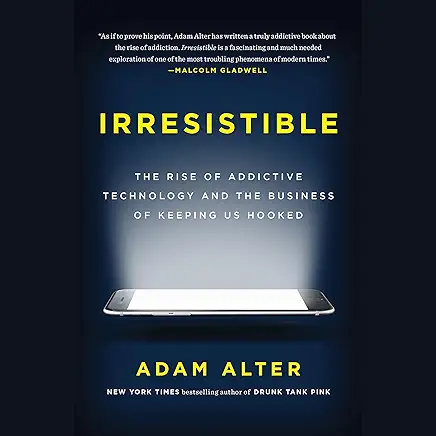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