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敏感的正念:安全与转化性疗愈的实践
心理学, 正念, 慈悲喜舍 ·Index
Trauma-Sensitive Mindfulness: Practices for Safe and Transformative Healing - David A. Treleaven
创伤敏感的正念:安全与转化性疗愈的实践 - 戴维·特雷利文 - 摘要
对于创伤幸存者来说,正念练习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本书将教你如何安全地运用其力量,避免再次受到伤害,实现真正的疗愈。
前言
作者:威利比·布里顿
我研究冥想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并在多年的工作中发现,创伤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无论是短期静修中出现闪回的学生,还是多年来一直经历与创伤相关的解离状态的资深冥想老师,他们都面临着独特的挑战。这些经历往往让他们感到羞愧,认为是自己“搞砸了”冥想,或者自己有无法弥补的缺陷。
戴维·特雷利文的这本书,为这些困境提供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清晰框架。他严谨、富有同情心且深刻地解释了为何正念练习有时会对创伤幸存者构成危险,并介绍了能确保练习安全且具有转化力量的实用方法。
本书不仅关注个体神经系统的创伤,更将其扩展到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探讨了那些创造并延续创伤的系统性问题。这挑战了我们对“相互依存”的传统理解,敦促我们批判性地审视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自身在其中的角色。
在正念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需要一场更细致、更深入的对话。《创伤敏感的正念》恰逢其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严谨、易懂且有实证依据的资源,帮助我们以一种对创伤更敏感的方式来教导和实践正念。这本书不仅不是为了劝退人们冥想,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让这些练习变得更强大,更适用于当代受众。
引言:为何需要创伤敏感的正念?
我曾收到一封求助邮件,来自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老师。他为了缓解焦虑而开始练习正念冥想,初期效果显著。但不久后,他开始在冥想结束时经历一种身体被恐惧麻痹、无法动弹的恐怖体验。旧日的车祸创伤——他曾被困在车内一小时——似乎被练习唤醒了。他感到困惑:一个如此有益的练习,为何会让他陷入恐慌和崩溃?
这个问题,正是我多年来作为心理治疗师和研究者一直在探索的核心。创伤是一种压倒我们应对能力的极端压力。理论上,旨在减轻压力的正念似乎是创伤的完美解药。但现实是,对于创伤幸存者,正念冥想有时会加剧创伤应激的症状, 如闪回、情绪过度唤醒和解离(思想、情感与身体感觉的分离)。不加引导的练习,可能让幸存者直接触碰内心最深的伤口,使情况变得更糟。
然而,正念同时也是创伤疗愈的宝贵资源。研究表明,它可以增强身体觉察、注意力和情绪调节能力——这些都是创伤恢复的关键技能。
考虑到创伤的普遍性(约90%的人经历过创伤事件),任何教授正念的场合,都极有可能有创伤幸存者在场。因此,我们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正念对创伤幸存者的潜在风险,同时充分利用其潜在益处?
本书旨在回答这个问题。我将提出一个由五项核心原则组成的创伤敏感的正念框架,为正念教师、创伤专业人士及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提供实用建议。这个框架的目标是: 1. 实现(Realize) 创伤的广泛影响。 2. 识别(Recognize) 客户、家人和员工中的创伤迹象。 3. 响应(Respond) 将创伤知识完全整合到政策、程序和实践中。 4. 抵制(Resist) 再次创伤。
这并非一套刻板的治疗方案,而是提供一系列建议,让你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用。我们应当调整正念练习来适应幸存者的需求,而不是期望他们来适应我们。
本书的目标是: 1. 将练习者的痛苦降至最低: 确保他们在练习中感到尽可能安全和稳定,避免再次创伤。 2. 推动对创伤的系统性理解: 认识到创伤不仅是个人心理体验,也与我们周围的压迫性社会系统息息相关。 3. 倡导正念从业者与创伤专业人士的持续合作: 双方的经验对彼此都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明确,是未经调整的正念冥想练习,而非正念本身,可能加剧创伤症状。通过一些简单的调整,我们可以帮助幸存者安全地练习,确保他们不会在寻求疗愈的过程中再次伤害自己。将创伤知情的框架融入其中,是当代正念运动发展的必然一步。
第一部分:创伤敏感的正念基础
第一章:无处不在的创伤:可见与无形的形式
创伤经历会彻底颠覆我们对安全、秩序和可预测性的感知,让我们感到被完全压垮。本章通过讲述斯坦福大学性侵案受害者的经历,以及弗雷迪·格雷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等事件,揭示了创伤的普遍性和系统性。
无论是个人暴力,还是由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社会不公造成的系统性伤害,创伤都以各种形式存在。当这些经历与正念练习相遇时,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一位朋友在听完性侵案陈述后参加冥想小组,结果在静坐中被过去的创伤记忆淹没,心跳加速,濒临恐慌。
什么是创伤敏感的正念?
这意味着,在教授或运用正念时,我们需要具备对创伤的基本理解。鉴于正念的普及和创伤的高发率,任何正念练习的场合都可能有创伤幸存者。我们的责任是识别创伤症状,并以熟练、安全的方式作出回应,避免再次创伤。
案例:RJ的故事
高中生RJ在姐姐因车祸去世后,开始经历创伤应激症状:孤僻、焦虑、噩梦和恐慌。学校开设的正念冥想课对他而言是种折磨。当他闭上眼睛,安静的环境反而让姐姐的影像和事故的画面不断涌现,心跳声盖过了一切,让他感到窒息和极度痛苦。
应激与创伤
- 应激(Stress):身体对任何变化需求的非特异性反应,有好有坏。
- 创伤性应激(Traumatic Stress):由经历或目睹死亡威胁、重伤或性暴力等创伤事件引起的最强烈应激。它不仅限于单一事件,也可能源于持续的压迫,如家庭暴力或种族歧视。
- 创伤后应激(Posttraumatic Stress):当创伤经历无法被正常“整合”或消化时,其印记会延续到当下,导致闪回、噩梦等症状反复出现。时间并不能治愈所有创伤。
-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一系列特定创伤症状持续一个月以上,严重影响生活。
创伤的核心:整合失败
创伤的关键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个体是否能整合(Integrate) 这段经历。整合意味着将经历的各个部分(思想、情绪、身体感觉)和谐地融为一体。创伤则导致解离(Dis-integration),使这些部分变得支离破碎,身体持续发出警报,即使危险已经过去。
这个框架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那些不符合PTSD诊断标准但同样具有创伤性影响的经历,例如由种族主义或贫困等系统性压迫造成的“微侵犯”的累积效应。
创伤的普遍性与政治性
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约90%的人在一生中会经历创伤事件。然而,创伤的分布并非随机。社会背景是决定我们是否更容易暴露于创伤的关键因素。 因贫困、残疾、肤色、性别或性取向而遭受系统性压迫的人群,面临着更高的人际暴力风险。
例如,美国的黑人被执法部门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四倍。女性、跨性别者和残疾人遭受性暴力的风险也远高于顺性别男性。这些数据提醒我们,创伤是普遍的,也是政治性的。社会结构为某些群体创造了安全,却系统性地将另一些群体置于危险之中。作为创伤敏感的实践者,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不平等。
整合的障碍:恐惧与羞耻
- 恐惧:创伤让幸存者害怕自己的内在体验。身体成为“布雷区”,充满了可怕的感觉。要求他们用正念关注内在,无异于让他们直面未愈合的创伤,这可能导致压倒性的恐惧。
- 羞耻:幸存者常常会自责,认为创伤是自己的错,或者觉得自己已经“坏掉了”。这种羞耻感是整合的巨大障碍。
对于像RJ这样的幸存者,仅仅指导他们“用正念观察恐惧”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一种能重建安全感和信任的关系,以及专业人士的指导来处理深层的恐惧和羞耻。我们必须尊重这些障碍,理解创伤是一种与生存本能相关的深刻心理生物学反应,而非简单的负面情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真正创伤敏感的方式提供正念。
第二章:直面当下:正念与创伤性应激
正念是一种让我们能够不加评判地觉察当下发生的一切的心智能力。对于创伤幸存者而言,它既可以是宝贵的资源,也可能带来问题。本章通过尼克的故事,探讨了正念如何帮助人们增强自我调节能力,同时也指出了其潜在的风险。
案例:尼克的故事
尼克因童年时期遭受父亲的暴力虐待而留下创伤。当他的儿子康纳长到他当年受虐的年纪时,创伤被重新激活。一次,在与儿子发生冲突时,尼克情绪失控,砸碎了一个杯子,这让他深感恐惧和羞耻。
在治疗中,尼克开始学习正念。他学会了观察和容忍内在的愤怒与恐惧,而不是评判或逃避它们。通过练习,他发现这些感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时刻在流动的。他开始对自己产生好奇和同情,意识到愤怒之下隐藏着一个受伤、害怕的自己。
正念的定义与作用
正念的定义是“有意识地、不加评判地、专注于当下此刻的觉察”。
- 有意识的专注:帮助我们将涣散的注意力稳定下来,像手电筒一样照亮特定体验,从而增强对注意力的控制感。
- 专注于当下:创伤使人活在过去,而正念练习能帮助我们将注意力锚定在此时此地,这是创伤恢复的一项关键技能。
- 不加评判的觉察:创伤常伴随着羞耻和自责。正念鼓励我们用好奇和接纳的态度面对内在体验,从而打破自我批判的循环。
正念与自我调节
正念的核心机制之一是增强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 的能力,即根据情境需求监控和调整自身行为、情绪和思想的能力。创伤是一种失调的体验,而正念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帮助幸存者重获掌控感:
- 注意力调节:幸存者学会了有意识地引导注意力,不再被动地被创伤性线索牵着走,从而支持内在的稳定。
- 身体觉察:创伤使身体成为“敌人”。通过正念,幸存者可以重新与身体建立连接,了解身体发出的信号,并体验到身体感觉是瞬息万变的,这打破了“被困住”的感觉。
- 情绪调节:正念帮助人们在情绪激动时保持临在,识别自己的情绪状态,并以更有选择性的方式做出回应,而不是陷入自动化的反应模式。
对创伤幸存者的两个额外益处
- 双重觉察(Dual Awareness):能够同时持有多个视角。例如,在闪回时,既能体验到过去的恐惧,又能意识到自己正安全地身处当下。正念通过强化“观察的自我”,帮助幸存者与创伤体验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避免被完全吞噬。
- 暴露(Exposure):在安全的范围内,正念鼓励我们温和地面对困难的体验,而不是逃避。这类似于暴露疗法,可以逐渐提高对创伤相关刺激的耐受度,帮助整合创伤。
一把双刃剑:正念的风险
尽管有诸多益处,但对于创伤幸存者,正念练习也暗藏风险。当尼克尝试独自冥想时,他发现自己被闪回和危险感淹没,练习反而加剧了他的焦虑和羞耻。
这是因为幸存者在练习中会过度关注创伤性刺激。当注意力被强烈的创伤记忆或身体感觉所吸引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引导和工具来保持稳定,他们很容易被卷入创伤的旋涡中。这就像潜水员被海草缠住,越是挣扎,缠得越紧。
仅仅给出“保持正念”的指令是不够的。幸存者需要具体的、经过调整的练习方法,以及来自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的支持,来帮助他们在遇到困难时稳定下来。
因此,我们的任务是了解创伤,并提供一个包容性的框架和量身定制的调整方法,让正念练习对幸存者而言既安全又具有转化力量。
第三章:被过去塑造:正念与创伤简史
我们对创伤和正念的理解并非凭空产生,而是被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所塑造。本章探讨了这两个概念在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演变,并强调了理解这些历史对于成为一名创伤敏感的实践者的重要性。
案例:玛格丽特与伊冯
社会工作者玛格丽特(白人)接待了客户伊冯(黑人)。伊冯因邻居的种族骚扰而出现恐慌发作等创伤症状。玛格丽特虽然表示同情,但无法真正理解伊冯的经历为何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创伤性影响。她认为创伤仅限于严重的身体暴力事件,而忽略了种族骚扰的累积效应和系统性根源。
当她建议伊冯进行一次引导式冥想,并告诉她“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安全的”时,伊冯感到了更深的隔阂和不被理解,最终中断了咨询。玛格丽特没能意识到,她对“安全”的理解是基于她自己的特权社会背景,而这种背景并未赋予伊冯同样的保护。
创伤的政治性历史
我们对创伤的现代理解,源于几个关键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将原本被忽视的痛苦带入了公众视野。
- 歇斯底里症与女性运动:19世纪,法国医生(如沙可、雅内和弗洛伊德)开始倾听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症”的女性患者。他们发现,这些症状往往源于真实的创伤经历,尤其是性虐待。然而,由于这一发现在当时社会无法被接受,这项研究很快被压制,女性的痛苦再次被噤声。
- 战争与反战运动:两次世界大战后,士兵们带着“炮弹休克症”等创伤症状回家,最初被视为懦弱。直到越南战争后,反战老兵组织起来,通过“谈话小组”分享他们的经历,成功推动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1980年被正式确立为一种诊断。这使得心理创伤获得了社会合法性。
- 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运动通过“意识提升小组”,揭示了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并将其与战争创伤联系起来。她们的口号“个人即政治”挑战了将这些伤害私人化的社会惯例,最终推动了性暴力被纳入PTSD的核心诊断标准。
今日的创伤与社会运动
正如历史所示,对特定创伤形式的研究只有在挑战其根源的压迫性系统的政治背景下才能蓬勃发展。今天,“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运动正在为研究种族主义的创伤性影响创造条件,揭示系统性歧视和代际创伤如何深刻地影响着有色人种社区。
作为创伤敏感的实践者,我们必须反思:
- 我们的创伤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 我们的知识体系是否包含了对系统性压迫的分析?
- 我们的社会身份(种族、阶级、性别等)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又忽视了什么?
当我们面对源于压迫的创伤时,中立是不存在的。正如德斯蒙德·图图所说:“在不公正的情况下保持中立,你便选择了压迫者的一方。” 创伤敏感的实践要求我们承担起责任,选择与受害者站在一起。
正念的历史与商品化
正念的西方历史交织着两条线:一条是2500年的佛教传统,另一条是近几十年的现代科学。
- 佛教传统:正念(Sati)是佛教冥想的核心,嵌入在一个完整的伦理框架(戒律)和智慧体系(四念处)中。
- 世俗化与商品化:从赫伯特·本森的《放松反应》到乔恩·卡巴金的“正念减压疗法”(MBSR),正念被剥离其宗教根源,作为一种世俗的健康干预手段而大获成功。然而,这种普及也带来了问题。正念被过度简化,被包装成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万能药问题),其潜在的风险和挑战被媒体和市场所忽视。
痛苦悖论的陷阱
正念教导我们,逃避痛苦只会加剧痛苦(痛苦悖论)。这一理念在处理慢性疼痛等方面非常有效。然而,当应用于创伤时,必须格外小心。创伤幸存者逃避内在痛苦是一种明智的、基于生存的策略。简单地要求他们“面对痛苦”,可能会将他们推入一个无法逃脱的旋涡。
玛格丽特正是掉入了这些陷阱。她将正念视为一种简单的放松技巧,并认为只要伊冯能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不适,问题就能解决。她未能认识到,未经调整的正念练习,加上她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忽视,最终对伊冯造成了二次伤害。
第四章:创伤与正念中的大脑和身体
本章通过神经生理学的视角,解释了创伤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为何正念练习有时会使情况恶化,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来支持安全的疗愈。
案例:蒂姆的故事
摄影师蒂姆在一次工作中遭遇持枪抢劫。在极度恐惧中,他本能地想逃跑,但最终僵在了原地。事后,他感到羞耻、麻木,并开始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紧张、失眠、闪回。他希望通过每周的正念冥想课来缓解,但练习反而让抢劫的画面更加清晰,心跳加速,汗流浃背。他感到困惑,为什么放松的练习会加剧他的痛苦?
生存的防线:战斗、逃跑与僵固
当面临威胁时,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ANS) 会自动激活一系列生存反应。神经科学家斯蒂芬·波格斯(Stephen Porges)的多重迷走神经理论解释了这一过程,他将其分为三个层级的防御系统:
- 社会参与系统(Ventral Vagal Complex):最高级的系统,在我们感到安全时激活。它让我们能够与人沟通、连接和协作。抢劫前,蒂姆正处于这个状态。
- 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System):当社会交往无法解决威胁时,该系统被激活,即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 反应。肾上腺素飙升,心跳加速,身体为剧烈运动做好了准备。蒂姆在看到劫匪时,本能地想逃跑,就是这个系统在起作用。
- 背侧迷走神经系统(Dorsal Vagal System):最原始的防御系统。当战斗和逃跑都不可行时,身体会进入僵固(Freeze) 状态,也称为“强直性不动”。心率骤降,身体麻木,甚至昏厥。这是一种“装死”的生存策略,可以减轻痛苦,并可能在捕食者放松警惕时提供逃生机会。蒂姆在巷子里被抢时,就进入了这种状态。
整合失败:创伤为何挥之不去?
在理想情况下,威胁解除后,身体会通过颤抖、哭泣等方式释放掉“战斗或逃跑”反应中积聚的巨大能量,从而恢复平衡。然而,如果这个过程受阻(例如,蒂姆无法逃跑,也无法在事后充分释放情绪),这些未完成的生存能量就会被“卡”在身体里。创伤就这样从一个外部事件,变成了内在的折磨。蒂姆持续的紧张和焦虑,正是这种未被整合的能量在他体内肆虐的表现。
大脑的警报系统
我们可以将大脑分为三个部分:
- 理性脑(新皮层):负责语言、抽象思维和决策。
- 情绪脑(边缘系统):负责情绪和生存反应,是我们的“警报中心”。
- 爬行脑:负责基本的生理功能。
在正常情况下,理性和情绪脑协同工作。但在创伤后,情绪脑会持续发出“危险”的信号,即使理性脑知道危险已经过去。这是因为创伤扰乱了大脑中三个关键区域的协作:
- 杏仁核(Amygdala):身体的“烟雾探测器”,负责快速识别威胁并触发警报。
- 海马体(Hippocampus):负责记忆的时间排序,告诉我们一件事的“开始、经过、结束”。
- 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理性脑的指挥中心,负责评估情况,抑制杏仁核的过度反应。
在创伤期间,强烈的应激激素会暂时抑制海马体的功能。这意味着创伤事件没有被正确地“存档”,它缺少一个明确的“结束”标签。因此,前额叶皮层收不到“危险已解除”的信号,无法关闭杏仁核持续响起的警报。
这就是为什么蒂姆在冥想时,即使知道自己身处安全的环境,身体却依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要求他关注内在,实际上是让他反复面对这个失灵的警报系统,从而加剧了症状。
正念如何帮助大脑?
- 研究发现,正念练习可以增强前额叶皮层的功能,让我们能更好地观察和调节情绪。
- 同时,它能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性,使我们不容易被触发。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蒂姆学会了在安全的环境中,逐步接触和释放被困在身体里的创伤能量。他开始能够在体验恐惧的同时,保持对当下安全的觉察(双重觉察)。通过哭泣、颤抖,他的身体完成了那次被中断的生存反应。最终,虽然记忆依然存在,但它不再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创伤开始被整合。
这个过程凸显了创伤知情的重要性。如果蒂姆的老师不了解创伤,可能会鼓励他“坚持练习”,结果可能会造成更深的伤害。幸运的是,他的老师识别出了问题,并将他转介给了专业人士。
第二部分:创伤敏感的正念五项原则
第五章:保持在耐受窗之内:唤醒水平的作用
佛陀通过调弦师的故事领悟了“中道”——琴弦太紧易断,太松则无声。这个比喻对创伤敏感的正念至关重要。创伤会使人陷入极端的生理和情绪状态:要么是“战斗或逃跑”的高度唤醒,要么是“僵固”的麻木。创伤后,人们可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剧烈摇摆。
创伤敏感的正念旨在帮助幸存者找到一条“中道”,避免这些极端状态。这引出了第一个核心原则:在练习中,始终保持在“耐受窗”(Window of Tolerance)之内。
耐受窗是由丹·西格尔(Dan Siegel)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我们能够有效处理信息和情绪的最佳唤醒区域。在这个“窗”内,我们感到稳定、临在和能够自我调节。
- 窗外上方:过度唤醒(Hyperarousal):表现为焦虑、恐慌、情绪反应过度、思维混乱。这是西格尔所说的“混乱”之岸。
- 窗外下方:低度唤醒(Hypoarousal):表现为麻木、解离、感觉迟钝、行动力下降。这是“僵固”之岸。
创伤幸存者的耐受窗往往会变窄,使他们很容易被“推出”窗外,陷入失调状态。
案例:布鲁克的故事
布鲁克在七个月大的女儿因婴儿猝死综合症夭折后,经历了巨大的创伤。为了寻求疗愈,她参加了一次周末冥想静修。起初,静默让她感到一丝平静。但很快,女儿去世那天的恐怖记忆开始涌现。闭上眼,她看到女儿苍白的脸;睁开眼,她仿佛听到救护车的警报声。
在静修中,布鲁克在极度的焦虑和解离之间摇摆。悲伤是如此巨大,而独自一人的静默让这份痛苦变得难以承受。她感到被孤立,极度渴望丈夫的拥抱。老师只是鼓励她继续“用正念观察”,但这让她感觉更糟。静修不仅没有帮助她,反而加剧了她的创伤症状,使她在回家后变得更加警觉和失眠。
失调的唤醒
布鲁克的经历是典型的失调的唤醒(Dysregulated Arousal)。她的神经系统在过度唤醒(恐慌)和低度唤醒(麻木)之间失控地切换。在这种状态下,认知功能会受到严重影响,使人难以思考和集中注意力。
对于像布鲁克这样唤醒水平失调的人来说,基础的正念冥想练习可能是一个“陷阱”。当她遵从指示,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在体验上时,她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创伤性的记忆和感觉,这只会进一步将她推出耐受窗。
创伤敏感的调整方法:
- 观察失调唤醒的迹象:作为实践者,我们需要学会识别他人可能超出耐受窗的非语言信号,如肌肉过度僵硬或松弛、呼吸急促、过度惊跳、脸色苍白、情绪剧烈波动或明显的解离。
- 采用分阶段的疗愈方法:创伤疗愈应遵循三个阶段:I. 稳定与安全;II. 记忆处理;III. 整合。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第一阶段,即帮助幸存者建立稳定感,而不是急于处理创伤记忆。确保练习不导致再次创伤是底线。
- 向练习者介绍耐受窗的概念:让幸存者了解这个模型,可以赋予他们力量。他们可以学会识别自己的唤醒状态,并理解这些反应是创伤后的正常现象,从而减少自责。
- 使用“正念仪表盘”(Mindful Gauges):鼓励幸存者找到一个可靠的内在“仪表盘”来衡量自己的状态,比如呼吸的深浅、胸口的开合感等。通过这个仪表盘,他们可以做出支持自我调节的决定。
- 学会“踩刹车”:幸存者需要知道,当练习变得过于强烈时,他们完全有权“踩刹车”。方法包括:睁开眼睛、短暂休息、深呼吸、自我安抚的触摸(如手放于心口)、将注意力转移到外部安全的物体上,或缩短练习时间。
- 善用呼吸:缓慢深长的呼吸有助于降低过度唤醒;轻快有力的呼吸则有助于提升低度唤醒。但需谨慎使用,避免过度。
- 使用唤醒量表(0-10):让练习者用数字来评估自己的唤彼水平,可以帮助他们更清晰地追踪自己的状态,并与老师或治疗师沟通。
- 保持在自己的耐受窗内:作为引导者,我们自身的唤醒状态会影响他人。只有当我们自己保持稳定时,才能为他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容器。自我关怀和同伴支持至关重要。
第六章:转移注意力以支持稳定:避免恐惧/僵固循环
古希腊神话中,英雄珀尔修斯被告知不能直视蛇发女妖美杜莎,否则会变成石头。他借助盾牌的反光才成功将其击败。这个故事恰当地比喻了创伤与注意力的关系。创伤的核心体验之一是“僵固”——像被石化一样动弹不得。如果幸存者在正念练习中,像直视美杜莎一样,持续、直接地关注那些与创伤相关的、令人恐惧的内在感觉,很可能会重新触发僵固反应,使情况恶化。
这引出了第二个原则:转移注意力以支持稳定。 为了保持在耐受窗内,创伤幸存者需要学会,当内在的创伤性刺激变得过于强烈时,他们有权并且有必要将注意力从其上移开。他们可以睁开眼睛,关注周围环境中的某个安全物体,或者选择一个更稳定的注意力锚点,如脚踏实地的感觉。
案例:迪伦的故事
迪伦是一名跨性别男性,在高中时期因其性别认同而遭受了严重的欺凌和骚扰。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尽管他现在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但他的身体仍然持续发出危险信号。他经常感到胃部翻江倒海,后颈有刺痛感,仿佛随时会受到攻击。
冥想练习对他来说变得异常困难。当他试图将注意力放在身体上时,这些不适感会变得更加强烈,并引发强烈的恐惧和僵固感。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它会自动地被这些创伤性线索所吸引。他感到愤怒和无助,因为那些欺凌者似乎“住进了他的脑子里”。
注意力的“定向反应”
定向反应(Orienting Response) 是我们对新奇刺激的本能反应,我们会不自觉地将注意力转向它。对于创伤幸存者,他们的定向反应系统会变得高度敏感,自动地、强迫性地朝向与创伤相关的线索——无论是外部的(如迪伦对某种蓝色的警惕)还是内部的(如他后颈的刺痛感)。
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身体试图通过时刻保持警惕来确保安全。但问题在于,这种过度的关注会让他们被困在过去的威胁中,无法准确评估当下的安全。
恐惧/僵固循环
彼得·莱文(Peter Levine)指出,在创伤中,恐惧和僵固这两种体验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幸存者感到恐惧时,可能会触发僵固反应(如呼吸变浅、身体麻木);而僵固的感觉反过来又会加剧恐惧。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恐惧/僵固循环。
这就是美杜莎问题:当幸存者遵循基础的正念指令,去关注那些压倒性的内在感觉时,他们可能会无意中启动这个循环,导致被困在创伤状态中,变得更加无助和恐惧。
创伤敏感的调整方法:
- 向练习者解释“美杜莎问题”:让他们了解,过度关注创伤性刺激可能是有害的。这有助于减少他们的自责,并为采取不同的练习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
建立稳定的注意力锚点:传统的注意力锚点(如呼吸)对很多幸存者来说并非中性,甚至可能引发创伤反应。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寻找对自己而言稳定、安全的锚点,例如:
- 身体感觉:脚踩在地上的感觉、手放在大腿上的感觉、背靠椅子的感觉。
- 其他感官:聆听周围的声音、观察一个令人平静的物体(如植物)、感受空气的温度。
- 重新定向注意力:当练习者感到被创伤性感觉淹没时,教导他们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重新定向到一个更稳定的锚点上。这并非逃避,而是在第一阶段(建立安全与稳定)疗愈工作中的必要策略。
- 关注环境:睁开眼睛,观察并命名周围环境中的物体(“这是一扇窗户”,“那是一棵树”),是一种强大的、将人带回当下的方法。这提醒神经系统,过去的威胁此刻并不存在。
- 从专注到开放:练习可以从专注式注意(集中于一个稳定的锚点)开始,如果感觉稳定,再逐渐扩展到开放式监控(觉察所有出现的体验)。如果感到失调,随时可以回到专注的锚点。
-
关注复原力(Resilience):复原力是我们即使在经历可怕事件后,仍能看到美好、建立连接和创造的能力。我们可以引导幸存者将注意力转向能带给自己力量和喜悦的资源,比如:
- 想象一个安全的地方。
- 回忆一个积极的记忆。
- 与心爱的宠物互动。
当迪伦感到不知所措时,他会看着他的狗米洛,或者想象和米洛在公园奔跑。这会给他带来温暖和活力的感觉。关注复原力,可以增强我们面对痛苦的能力。
第七章:将身体牢记于心:处理解离问题
佛教导师雷金纳德·雷(Reginald Ray)指出,许多人练习冥想时处于一种“离身”状态,只用头脑去“思考”身体,而不是真正地“活在”身体里。这种状态对于创伤幸存者来说尤为普遍,也使得疗愈变得异常困难。
创伤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更是一种深刻的身体体验。《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等著作的标题已经揭示了这一点:创伤的印记存留在我们的细胞、组织和神经系统中。
对于幸存者,身体常常变成一个“雷区”,充满了与恐怖事件相关的、令人痛苦的感觉。为了应对这种内在的折磨,他们常常会采取一种生存策略——解离(Dissociation),即切断与身体感觉和情绪的连接。这虽然能暂时减轻痛苦,但代价是失去了与自己、与生命力的深刻连接。
因此,疗愈创伤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帮助幸存者安全地“重返”身体。正念练习通过增强对内在感觉的觉察,可以成为这一过程的有力工具。但这绝非易事,因为重新连接身体感觉可能会非常强烈和可怕。
这引出了第三个原则:将身体牢记于心。 我们需要理解幸存者在关注身体时可能面临的风险和益处,并提供具体的调整方法,确保他们在练习中感到安全、有尊严和掌控感。
案例:吉娜的故事
吉娜在一次亲密关系中遭受了性侵犯。事后,尽管她已经脱离了危险,但她的身体仍然持续发出危险信号。在与新的伴侣亲近时,她会不自觉地解离——感觉自己“飘走了”。
她尝试通过正念冥想打坐来疗愈。但练习中,当她关注内在时,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会从胃部升起,让她感到既困惑又羞耻。在一次为期一天的静修中,她进入了一种看似深度专注的状态,连续静坐了三个小时。老师称赞了她的定力,但她事后感觉自己其实是解离了——身体麻木、思维混乱。她困惑地问:“我是在进步,还是只是‘掉线’了?”
创伤与身体感觉
我们的情绪状态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身体感觉来感知的。创伤扰乱了这一系统。幸存者的身体会持续对想象中的或记忆中的威胁做出反应,就好像威胁真实存在一样。这使得他们很难信任自己的内在感觉。
- 外感受(Exteroception):通过五官感知外部世界。
- 内感受(Interoception):感知身体内部的状态(如心跳、胃部感觉)。
创伤会导致内感受和外感受的失联。即使外部环境是安全的(外感受),身体内部却警铃大作(内感受)。这让幸存者感到极度混乱。他们往往会过度关注内感受,并将其误判为外部现实的反映。
正念练习,尤其是闭眼关注内在的练习,恰恰会放大对内感受的关注。如果没有适当引导,这会让幸存者陷入更大的困境。
解离:一种生存策略
解离是创伤的反面——整合的失败。它是一种聪明的保护机制,帮助人们在无法逃脱时“离开”自己的身体,以应对难以承受的痛苦。然而,从长远来看,它阻碍了创伤的整合。
吉娜的困境在于,解离既是她的应对方式,也是她被困住的原因。我们需要尊重解离,将其视为一种生存智慧,而不是强迫幸存者“保持临在”。我们的工作是好奇地探索解离如何影响他们的练习,并提供支持。
创伤敏感的调整方法:
- 让练习者拥有选择权:创伤剥夺了人的掌控感,因此在练习中赋予选择权至关重要。使用邀请式而非命令式的语言(例如,“我邀请你闭上眼睛”而非“闭上眼睛”)。提供多种姿势选择(坐、站、躺),并明确表示他们可以随时休息或离开。
- 在练习中加入动态元素:对于许多幸存者来说,在运动中(如行走冥想、伸展)保持对身体的觉察比静坐更容易。动态练习有助于感觉的流动,避免“卡住”。
- 注意解离的迹象:学会识别解离的信号(如眼神空洞、反应迟缓、对外界刺激无反应、感觉自己“离得很远”)。这能帮助我们及时介入,提供支持。
-
利用外感受进行“落地”:当幸存者出现解离时,可以引导他们关注五官的感觉来重新与当下建立连接。例如:
- 触觉:感受手中物体的质地,或双脚踩在地上的感觉。
- 味觉/嗅觉:一颗薄荷糖或一瓶精油。
- 听觉/视觉:聆听周围的声音,或观察并命名房间里的物体。
- 谨慎使用身体扫描:对于幸存者,长时间躺下并逐一扫描身体部位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提供多种姿势选择(如坐姿),允许睁开眼睛,并正常化“感觉不到”某些部位的体验,都是必要的调整。
- 灵活调整姿势:鼓励练习者找到对自己而言既警觉又放松的姿势,不必拘泥于传统形式。
- 尊重身体边界:始终征求同意后再进行任何身体接触。注意保持适当的物理距离,避免站在幸存者身后,这些都有助于建立安全感。
- 创造更安全的环境:确保练习空间光线充足、出口清晰、有私密性,并提供可预测的流程。
- 提供无香环境:气味是强烈的创伤触发器。避免使用香水、熏香等,可以为化学物质过敏者和创伤幸存者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空间。
- 提供中性卫生间:这是对跨性别和性别非规范人群的基本尊重和安全保障,体现了对系统性压迫的觉察和回应。
第八章:在关系中练习:支持幸存者的安全与稳定
在一次寺院静修中,一位名叫瑞秋的女士分享了她在海啸中幸存的经历。静修的孤独和静默非但没有疗愈她,反而让创伤记忆不断涌现,让她感到孤立无援。住持僧人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有时候,人——而不是静默和独处——才是这类创伤最好的良药。”
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创伤无法在孤立中疗愈,它需要在关系中被看见、被承载。 无论是亲人温暖的微笑,还是专业人士的悉心引导,人际关系是自我调节的重要源泉。它帮助我们感到安全,调节我们的唤醒水平,并稳定地保持在耐受窗内。
因此,第四个原则是:在关系中练习。 这意味着我们要充分利用人际连接的疗愈力量,来支持创伤幸存者的安全与稳定。这可能包括为静修中的学生提供更频繁的个别访谈,将他们与创伤专业人士连接起来,或者建立支持性的社群规范。
案例:山姆的故事
山姆是一位虔诚的冥想者,但最近一次静修让他濒临崩溃。练习中,他被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恐慌所吞噬,感觉自己随时会失控尖叫。静修的孤独感让他想起了童年被父亲长期忽视和遗弃的经历。那时,他常常独自待在房间里,假装父亲就在身边。在静修的单人房间里,那种“不会有人来救我”的绝望感再次将他淹没。
静修结束后,山姆的症状持续恶化,他感到失调、羞耻,并且不被理解。他意识到,尽管正念曾是他的避难所,但仅仅依靠独自练习,已无法处理浮出水面的深层创伤。他需要的,是他在童年时期未能得到的那种安全、关怀的连接。
安全感与神经觉(Neuroception)
神经觉是斯蒂芬·波格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在无意识层面下评估环境和人是安全、危险还是致命威胁的能力。当我们“神经觉到安全”时,我们的防御系统(战斗、逃跑、僵固)会得到抑制,社会参与系统被激活,我们便能保持在耐受窗内。
许多创伤幸存者会发展出“错误的”神经觉,即即使在安全的环境中,他们的神经系统仍然会持续发出危险信号。这使得建立安全感变得异常困难。
关系是修复神经觉的强大场域。在一个安全、协调的关系中(尤其是与创伤专业人士的关系),幸存者可以重新体验到安全。引导者可以通过自己的临在、共情和稳定的状态,帮助幸存者调节唤醒水平。
关系与共同调节(Co-regulation)
我们天生就需要通过他人来调节自身的状态。婴儿依赖看护者的抚慰来平复情绪,成年人也同样会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获得平静或激励。这种人际间的生理心理调节,对于唤醒水平失调的幸存者至关重要。
在与山姆的合作中,我不仅仅听他说话,也密切关注他的生理信号。当我看到他开始变得痛苦和思维混乱时,我会及时介入,引导他进行深呼吸或将注意力转移到安全的锚点上,帮助他回到耐受窗内。我们甚至通过调整视频通话中的距离和朝向,来探索关系如何影响他的唤醒水平。这帮助他意识到,他可以主动地通过调整人际互动来支持自己的稳定。
社群的力量
创伤恢复发生在社群中。家庭、朋友、支持小组、宗教团体等,都能提供必要的安全感和勇气,帮助幸存者面对和处理创伤。
我向山姆介绍了“猎豹之家”(Cheetah House),一个为在冥想中经历困境的人提供支持的非营利组织。通过这个社群的线上平台,山姆找到了能够理解他经历的人。这种被看见和被理解的感觉,极大地减轻了他的孤独感和羞耻感,成为他疗愈旅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创伤敏感的调整方法:
- 进行创伤筛查:在课程或静修开始前,通过问卷等方式了解参与者是否有创伤史或正在经历创伤症状。这有助于提前识别可能需要额外支持的人。
- 与创伤专业人士合作:与受过训练的创伤治疗师建立合作关系。可以为参与者提供转介,聘请治疗师在静修期间现场提供支持,或定期向专业人士寻求督导。
- 在课程开始前建立关系:对于有创伤史的参与者,提前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这有助于建立信任,了解他们的特殊需求(如座位偏好),并提前赋予他们练习中的选择权。
- 建立社群协议:明确设定关于保密性、相互尊重、发言方式等社群规范,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安全的容器。
-
善用人际接触:
- 增加教师与学生的个别访谈频率和时长。
- 在团体练习中加入简短的分享和交流环节。
- 鼓励参与者建立“伙伴系统”,相互支持。
- 学习“闪回中断流程”:当有人经历闪回时,可以使用巴贝特·罗斯柴尔德开发的流程,通过一系列语言提示(如,“此刻我感到……因为我想起了……同时,我看到……所以我知道……现在并没有发生”),引导他们重新与当下建立连接,恢复双重觉察。
- 持续学习,成为资源:创伤敏感是一条持续学习的道路。不断更新关于创伤的知识,了解相关的社会正义运动,将使我们能为他人提供更好的支持。
第九章:理解社会背景:跨越差异有效工作
在一次社会论坛上,活动家帕特里斯·卡勒斯(“黑人的命也是命”联合创始人)说:“我的父亲在去年十二月死于种族主义。”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创伤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经历,它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系统之中。贫困、歧视、暴力等社会不公,都在持续地创造和延续着创伤。
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被教导以一种个人主义的视角看待世界,忽略了这些系统性的力量。我们倾向于将创伤视为孤立的个人悲剧,而未能看到其与外部世界的连接。
这引出了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则:理解社会背景。 这意味着我们要承认并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理解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由其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身份所塑造的。它要求我们能够熟练地在这些差异中工作,为他人创造安全感。如果我们忽视了社会背景,我们的善意可能会无意中造成伤害,加剧压迫,并破坏信任。
案例:娜蕊的故事
韩裔美国人娜蕊参加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冥想静修。她很快发现自己是现场唯一的有色人种。在与一位白人男老师的首次访谈中,老师在得知她的父母来自韩国后,便理所当然地问道:“那你从小就和家人一起冥想吗?”
这个基于种族刻板印象的问题,让娜蕊感到了深深的疏离和不被看见。尽管老师可能并无恶意,但这次互动让她失去了对老师的信任,并让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时刻处于戒备状态,最终她决定提前离开静修。
社会背景与权力动态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多重的社会身份(年龄、残疾状况、宗教、种族、阶级、性取向、国籍、性别等),这些身份构成了我们的社会背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某些身份群体拥有比其他群体更多的权力、资源和特权。
创伤的分布与这些权力动态密切相关。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群体,面临着更高的创伤暴露风险。
理解社会背景对于建立安全感至关重要。安全感是创伤敏感实践的基石。当我们能够认识到并尊重他人的社会身份,并思考这些身份如何与我们自己的身份互动时,我们才能更准确、更熟练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从而建立起信任。
在回应娜蕊的邮件时,我首先做的不是解释或辩护,而是验证她的经历,并询问她希望从我们的对话中得到什么。我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作为一名白人男性治疗师),我的首要任务是赋权于她,而不是主导对话。
压迫与难以看见的“鸟笼”
压迫是指权力的不公正使用,它限制了个人的选择。女权主义学者玛丽莲·弗莱用鸟笼作比喻:只看一根铁丝,你无法理解鸟为什么不飞走;只有退后一步,看到所有铁丝共同构成的那个结构时,你才能明白它被困住了。
同样,如果我们只看到一个孤立的歧视性言论(如老师对娜蕊的提问),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它为何会造成如此大的伤害。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个言论是根植于一个庞大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鸟笼”时,我们才能理解其背后的暴力。
社会身份的“真理”与“现实”
社会身份类别(如“种族”)本身是社会建构的,并非生物学上的“真理”。然而,这些类别在“现实”中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真实而深刻的影响。
持有这种矛盾的观点是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只强调“真理”(例如,声称自己“色盲”,不看肤色),我们就会否认和抹杀他人被压迫的活生生的现实。如果我们只看到“现实”,我们又可能陷入刻板印象。
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倾听他人的经历,并诚实地审视自己头脑中的内隐偏见——那些我们自己可能都未曾意识到的、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无意识态度和刻板印象。
创伤敏感的调整方法:
-
熟练地处理社会背景:在任何互动中,都要有意识地思考:
- 社会背景是如何影响当下的?
- 我自己的特权或被压迫身份是如何起作用的?
- 我在哪些方面需要提升自己对社会背景的理解?
- 对于拥有更多特权的人来说,这项工作尤为重要,因为特权会使我们倾向于忽视权力动态。
-
愿意讨论传承与文化挪用:文化挪用是指优势群体的成员,从被系统性压迫的群体中拿走文化元素(如仪式、物品),并为己所用,而往往忽略或歪曲其原始意义。
- 在教授正念时,我们需要对自己所传授的练习的传承保持透明。这些练习从何而来?它们在原始文化中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与这个传承的关系是怎样的?
- 诚实地面对这些问题,承认其中的复杂性(例如,西方正念是否构成文化挪用?),可以将选择权交还给练习者,并建立信任。
-
采取行动:理解社会背景最终必须导向行动。
- 在自己的社群或组织中,检视并挑战不公正的现象。
- 公开反对不公。
- 加入或支持致力于改变压迫性系统的草根组织。
- 为社会与环境正义运动提供资源:个人层面的疗愈与集体层面的解放密不可分。作为创伤敏感的实践者,我们可以通过捐款、提供服务或参与其中等方式,支持那些致力于挑战创伤根源的社会运动。这不仅是对疗愈工作的延伸,也是对一个更公正、更慈悲的世界的承诺。
结论:转化创伤
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历史学家布莱恩·史蒂文森和他的“平等正义倡议”组织,努力在城市中竖立起纪念奴隶贸易历史的标志。他们认为,只有直面这段被否认和压抑的创伤历史,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地疗愈并前进。
创伤,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都有一种拒绝被埋葬的倾向。它会以各种方式浮出水面,要求我们去看见和处理。疗愈的第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就是直面创伤。
正念,作为一种培养清晰觉察能力的练习,可以成为我们直面痛苦的强大工具。它帮助我们增强内在的勇气和稳定性,扩大我们的耐受窗,让我们有能力承载那些曾经看似无法承受的经历。当我们有能力与痛苦共处时,我们也就为喜悦与平和创造了更多的空间。
然而,正念并非万能解药。本书的核心论点是:正念本身不造成创伤,但它可能揭露创伤,有时甚至会放大创伤症状。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经过调整的、创伤敏感的方法。这不仅仅是学习几个技巧,而是一种持续的承诺——承诺不断学习,承诺将个人疗愈与对社会系统的觉察相结合。
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是将“创伤知情”简化为一张清单,一种政治正确的姿态;另一条路则是走向更深层的正义,审视我们自身在更大图景中的位置,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对于致力于疗愈的人们来说,我们必须选择后一条路。
转化性的创伤工作,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心个体的内在世界,也要关心我们身处的更大的社会生态系统。个人改变与社会改变密不可分。作为正念实践者,我们有责任去理解社会系统如何运作,以及我们自身在其中的位置。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内在的神经系统与我们所处的社区、经济和社会,都在持续不断地对话。当我们承认那些尚未愈合的集体创伤——如奴隶制的遗毒、大规模监禁、对特定群体的仇恨——我们就明白,疗愈必须同时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展开。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与这份工作的连接点,并为创造一个更公正、更慈悲的未来,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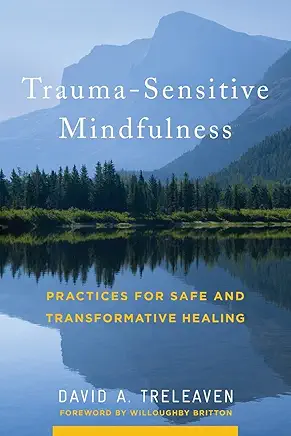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