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2.0:正在改变世界吸毒方式的网络革命
心理学 ·Index
Drugs 2.0: The Web Revolution That’s Changing How the World Gets High - Mike Power
毒品2.0:正在改变世界吸毒方式的网络革命 - 迈克·鲍尔 - 摘要
这是一场化学、技术与法律之间永无休止的猫鼠游戏,网络正在彻底颠覆全球毒品的制造、交易和消费方式。
##
前言
互联网毒品场景唯一不变的特征就是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难以理解,更无法控制。
本书自2013年5月在英国出版以来,化学、技术和法律这三者之间共生演化的压力仍在持续。书中提到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药物如今在英国已被列为非法,或受到临时药物管制令的约束。与此同时,从美国到欧盟的各国政府,仍在与化学家、使用者和黑客进行一场永无休止的追逐战。
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版所记录和预测的那样,每当一种药物被添加到那份长得荒谬的政府禁药名单上,几天后,一种新的合法替代品就会上市。政府的应对措施远未能说服人们停止吸毒,反而成功地将市场推向了更深层次的适应与实验之路。
联合国在其最新的《世界毒品报告》中承认了这种惊人的扩张:“新的有害物质在毒品市场上层出不穷,而国际药物管制体系正首次在这种现象的速度和创造力面前陷入困境。”
如今市场上销售的合法药物数量,远超当初制定全球第一部毒品法时所能想象的。1961年和1971年的联合国公约仅禁止了234种物质,而在过去的短短四年里,就已发现了总共243种新的合法化合物。其中56种是在2013年1月至10月期间出现的。
另一个重大进展涉及“丝绸之路”(Silk Road),这是一个暗网集市。世界各地的毒贩和使用者在这里通过加密通信和匿名数字货币比特币,利用各国邮政系统买卖毒品。本书第一版中的第十章《你的快克在邮寄途中》,是世界上首次对丝绸之路进行书籍长度的深入探讨。然而在2013年10月,该网站被关闭,其所谓的所有者也被逮捕。果然,仅仅几周后,一个更坚不可摧的新网站重新开放,同时还出现了大约十几个新的匿名毒品市场。本版对该章节进行了更新,包括对新丝绸之路所有者的独家采访。
我们现在都承认,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和精神面貌。我们同样需要认识到,数字时代也同样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吸毒习惯,旧有的法律管制模式如今既行不通,也适得其反。
与其进一步扩大禁令,一个更理性的应对方式是减少吸毒者面临的危害。我们现在需要利用网络及其协作与沟通的创始原则,来创造新的思想和策略,从而结束这场不可能打赢的禁毒战争。
序言:当代化学文化
2011年,共有四十九种全新的精神活性药物被发明出来,并在互联网上公开销售,好奇的消费者可以完全合法地购买它们。到了2012年,又有五十七种新药出现在网上。它们的剂量并非总是明确标注,有时甚至比人们习惯服用的娱乐性药物小得多;它们的效果也毫无记录可查——然而,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阻止其销售。仅仅在十多年前,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的。
这些药物并非人们使用了多年的海洛因、可卡因或摇头丸。它们的名字是一串令人费解的数字和字母,如6-APB、5-MeO-DMT、3-MeO-PCP,听起来更像是实验室用品而非娱乐性毒品。但普通人正在服用它们,而关于其效果的全球性讨论也和它们的销售一样明目张胆。
与几乎所有其他行业一样,毒品市场也已被网络彻底改变。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网络是他们寻找娱乐性药物或相关信息的首选之地——尤其是在面对这些新化合物快速而令人困惑的激增时。化学家、消费者和犯罪分子都利用互联网共享大量信息,并利用全球化的制造能力。这些完全未经测试的化合物构成了一个国际在线市场,其发展速度和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任何政府的有效控制。欢迎来到毒品2.0时代——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市场世界,在这里,毒品立法正被化学、技术和人类的创造力远远甩在身后。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2009年,我率先在英国媒体上报道了甲氧麻黄酮(mephedrone)的出现和流行,这种摇头丸和可卡因的替代品从一个地下的在线毒品圈子中泄露出来,成为了自摇头丸以来第一种登上全球报纸头条的新药。
甲氧麻黄酮是完全合法的。据毒理学家称,它与摇头丸只有“两个化学微调”的距离,而这些微调正是为了规避毒品法而故意为之的。它颠覆了以往所有的毒品等级,并在许多使用者中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他们错误地认为合法即无害。
这种药物被广泛获取且极受欢迎,是第一种大众市场的“可下载”毒品,因为它最初只能通过网络购买。它就像一个麻醉性的病毒视频,只需点击鼠标即可分享。甲氧麻黄酮是一个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转折点,它将一个秘密的互联网毒品场景,直接带到了英国的商业街,并进而推向了全世界。英国政府迅速而打破常规地禁止了这种新药,但这并未消除它,只是将市场交给了心存感激的黑帮,并促使化学地下世界进行更大胆的创新。
甲氧麻黄酮所引发的媒体狂热和道德恐慌,使得所谓的“合法快感”(legal highs)这一新化学风潮在几周内占据了所有媒体的头条。报纸和立法者感到震惊,但这种情况其实是可预见的。
这个故事的根源在于线上的“研究性化学品”(research chemical)场景,甲氧麻黄酮正是从中诞生的。与摇头丸、可卡因等被使用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药物不同,研究性化学品几乎没有人类使用史。它们通常在极小的剂量(几毫克)下就能起效。在2007年之前,使用者主要是数千名自称为“精神航天员”(psychonauts)的内部空间探索者,他们通过浏览科学文献或分子结构图来研究这些化合物的效果,并在在线论坛上分享经验。如今,研究性化学品的使用者可能已有数十万。
当社会、文化和技术条件成熟时,像甲氧麻黄酮这样未经测试的新药可以从地下涌入主流,赢得数百万热情但不知情的使用者。
在2012年6月17日,一个名叫“克拉珀姆男孩”的用户在一个论坛上写道,他可以完全合法地在网上订购像 6-APB(一种类似摇头丸的药物)和 MXE(一种类似氯胺酮的药物)这样的东西,并第二天就收到货。他感叹道:“整个情况看起来完全疯了,无疑在毒品法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我猜6-APB很快也会被禁,所以我得在它被禁之前囤点货,然后坐等新的合法快感来替代那些被禁的。”
克拉珀姆男孩对服用新型强效药物的随意态度如今已很普遍,但政策制定者和警方却很少接触到这种视角。MXE(美沙西胺)是一种与被禁的麻醉剂氯胺酮(K粉)结构相似的药物,分子结构的微小改变使其在大多数国家合法化。它能让使用者进入奇异的内心世界。直到2012年被禁之前,每克MXE成本仅为12英镑,可提供多达100次剂量,每次成本约12便士。而6-APB的效果也与摇头丸类似,一克约35英镑,包含10剂。截至本书写作时,它仍然是合法的。
这两者只是自2010年甲氧麻黄酮被禁以来出现的数百种新型、强效、合法药物中的两种。购买它们只需要网络连接和信用卡。化学家的创造力正在超越立法者的反应能力。
这些新药从何而来?它们是如何被构思和制造的?为什么人们愿意服用它们?当人类对改变意识状态的渴望转移到网络虚拟购物空间时,又会发生什么?我开始着手回答这些问题。
我深入研究了数十个专门讨论毒品的网络论坛,了解了新物质的来源、化学结构和地理分布。我找到了这些药物的来源并进行了核实。通过与使用者和贩卖者的深入交谈,我了解了它们的效果。我潜伏在加密的匿名网络论坛上,伪装成国际买家。我还采访了数十名科学家、毒理学家、医生、警察,倾听这一现象对他们生活和行业的影响。
在记录这一新兴社会趋势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正在见证并记录着许多国际毒品使用者习惯的重大转变的初期阶段。简而言至,新药的销售和使用正在增长,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会停止。
本书追溯了人类最早使用药物的历史,概述了其法律禁令的演变,审视了迷幻药的戏剧性出现,并解释了在现代,互联网如何深刻地改变了这一切。我探究了我们是如何走到这种强效新药在网上合法销售的奇特境地,并揭示了互联网技术的新用途如何使得购买像海洛因、可卡因、冰毒、LSD和摇头丸等被禁药物成为可能,而且几乎没有被发现的风险。简而言之,我将回答一个问题:毒品是否已经赢得了禁毒战争?
自2009年甲氧麻黄酮流行以来,毒品市场的许多部分已经原子化,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危险,以及采取行动的迫切需求。前路并无坦途——但我们已无法回到过去。精灵已经从试管里跑出来了。
第一章:从植物到化学品
人类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历史源远流长。已知最早的证据可追溯到公元前约9000年,在泰国西北部的“灵魂洞穴”中发现了一名早期人类咀嚼槟榔、荖叶和熟石灰后吐出的残渣。而在公元前约2700年,中国皇帝神农氏描述了他服用大麻后的体验:“食之不止,见鬼走……久服,通神明。”这不仅是首次有记载的迷幻体验,也是最早关于药物效果的书面分享。
从茶、咖啡、可卡因到烟草、大麻和各种蘑菇,人类使用能改变意识的植物和天然物质的历史遍布全球。在工业化前的社会,掌握这些植物知识的专家备受尊崇。然而,在不到150年的时间里,我们从一个不受法律控制的时代,走到了一个全球大多数国家都禁止使用这类物质的时代。
最早的毒品法是为了应对鸦片和可卡因等药物滥用带来的成瘾和死亡风险。1908年,英国通过立法,要求含鸦片制剂必须标注为毒药。1875年,美国出台了第一部禁毒法,禁止吸食鸦片,其目标直指旧金山的华人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保障军用物资,将鸦片和可卡因列为管制药品。这些早期的法律主要针对植物源性药物,立法和执法相对简单。
然而,实验室的介入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随着有机化学的发展,科学家们发现可以人工合成自然界中的任何化合物。1828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在实验室中合成了尿素,标志着有机化学的诞生。从此,化学家们能够像建筑师盖房子一样,用基本的化学元素构建出复杂的分子结构。他们通过改变现有药物的分子结构,例如添加“官能团”,来创造出效果更强、副作用更小,或者能够规避专利的新药。1874年,查尔斯·罗姆利·奥尔德·赖特通过在吗啡分子上添加乙酰基,合成了二乙酰吗啡——即海洛因。这种新药比吗啡更容易通过血脑屏障,因此起效更快,快感更强,当然也更容易上瘾。
这种通过改变分子结构来创造新药的过程被称为“环取代”。这些新药被称为“类似物”,它们本质上是被禁药物的合法版本。早在1912年《国际鸦片公约》签署后不久,就出现了吗啡和海洛因的合法替代品,这可以被视为世界上第一批“设计师毒品”。
但在迷幻时代之前,毒品使用仍局限于少数亚文化群体。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新的致幻剂和兴奋剂的出现,才将毒品推向了大众文化,并对立法构成了更大的挑战。
迷幻药的出现是突然且戏剧性的。1943年4月16日,瑞士科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在无意中通过指尖吸收了微量的LSD(麦角酸二乙胺),体验到了一种“并非不愉快”的醉酒感和“万花筒般的色彩游戏”。几天后,他故意服用了0.25毫克,正式开启了迷幻时代。LSD的效力极强,一克就能提供一万次剂量,这种高效力及其带来的潜在利润,极大地推动了后来的毒品文化。
最初,LSD被精神病学家用于研究精神疾病,甚至被美国军方和中情局用作“吐真剂”。但很快,它就从实验室和诊所流向了社会。20世纪50年代,“垮掉派”作家威廉·巴勒斯和艾伦·金斯堡等人通过LSD和其他迷幻物质来“解放思想”。他们的探索充满了冒险和未知,与今天只需在网上搜索就能获得药物形成了鲜明对比。
1955年,美国投资银行家戈登·沃森在墨西哥的经历,通过《生活》杂志的文章将迷幻蘑菇(有效成分为赛洛西宾)推向了公众视野。他描述了自己看到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和“神话般的野兽”,让数百万人对这种天然迷幻体验产生了兴趣。
另一类重要的迷幻药是苯乙胺类,其代表是麦司卡林(仙人掌素)。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服用了麦司卡林后写下了迷幻经典《知觉之门》。早在1898年,英国医生哈维洛克·埃利斯就在《当代评论》上发表文章,描述了自己服用仙人掌提取物的体验,他看到了“镶嵌着宝石的幻象”和“精美的花瓣”。
1955年,英国议员克里斯托弗·梅休在BBC的镜头前服用麦司卡林,他的体验被记录下来,标志着迷幻药正式进入主流文化。尽管这段影片最终未被播出,但它成为了最早的“迷幻体验报告”之一,揭示了这类药物对时间和空间感知的深刻影响。
LSD在出现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保持合法,直到它在20世纪60年代从精英圈子扩散到大众,成为大规模毒品使用的催化剂。甲壳虫乐队等文化偶像的迷幻体验,推动了青年文化、性、音乐和艺术的革命。作为回应,英国于1966年、美国于1968年相继禁止了LSD。
与此同时,另一种合成药物安非他命(“速度”)在工薪阶层青年中流行开来。最初作为抗疲劳药物,它在60年代成为英国“摩登派”文化的核心,他们拒绝酒精,通宵跳舞。政府于1964年禁止安非他命,但这反而导致其使用量增加和价格上涨。
毒品法的制定在20世纪不断收紧,形成了今天由联合国三大公约主导的国际管制体系。英国的《1971年药物滥用法》和美国的《1970年综合药物滥用预防和控制法》是各自国内的主要法律框架。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宣布“向毒品开战”。
然而,法律总是在追赶化学的脚步。英国在1977年就试图通过“通用描述”来预先禁止苯乙胺和色胺的各种可能衍生物,从而一举将MDMA等尚未出现的药物列为非法。但这并未堵住所有漏洞。这些法律诞生于一个没有大众通信、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它们制定于一种全新的药物出现前近五十年,这种药物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全球,而一个关键人物将站在新一轮竞赛的中心:亚历山大·舒尔金,摇头丸的教父。
第二章:工具制造者舒尔金的巨大狂喜
在加州拉斐特市舒尔金路1483号,有一座被松鼠环绕的小屋,这里是全球毒品文化的震中之一。亚历山大·舒尔金,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也最富争议的科学家之一,在这里工作了数十年。他自称只是一个“工具制造者”,而他最著名的工具就是MDMA,即摇头丸。
MDMA的诞生纯属偶然。1912年,德国默克公司的化学家们首次合成了它,目的是作为一种止血药的合成中间体,以规避现有专利。这份合成说明在档案中沉睡了数十年。
舒尔金的化学之旅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麦司卡林体验。他被这种白色粉末能唤醒深层记忆的能力所震惊,并得出结论:“我们的整个宇宙都包含在思想和精神之中……而有些化学物质可以催化我们接触到它。” 这次经历坚定了他探索精神活性物质的决心。
在陶氏化学公司工作期间,他发明了一种利润丰厚的杀虫剂,作为回报,公司给予他研究任何他感兴趣的化合物的自由。他选择了迷幻药。他通过“环取代”的方法,在麦司卡林的基本分子骨架——苯乙胺上进行各种修饰。苯乙胺结构与我们大脑中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如多巴胺)非常相似。舒尔金通过在苯环上添加或替换不同的原子或分子团,系统地探索着化学结构与精神活性之间的关系。他创造了数百种宇宙中前所未有的新化合物。
随着社会对迷幻药的恐慌加剧,舒尔金于1965年离开了陶氏,在自家后院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他不仅研究苯乙胺类,还探索了另一大类迷幻药——色胺,其结构与神经递质血清素相似,能产生类似迷幻蘑菇的效果。
舒尔金和他的研究小组亲自测试他合成的每一种新药。他会从微量开始,逐步增加剂量,直到感受到效果,然后详细记录下药物对感官、情绪、音乐欣赏能力乃至性欲的影响。他甚至开创了“博物馆剂量”的概念——一种适合在参观展览时服用的剂量。
最终,为了防止他的知识成果失传,舒尔金将他毕生的研究发表在两本巨著中:1990年的《PIHKAL》(我所了解和喜爱的苯乙胺)和1997年的《TIHKAL》(我所了解和喜爱的色胺)。这两本书不仅仅是化学合成指南,还夹杂着个人经历、爱情故事和对药物探索的哲学思考。书中,舒尔gin认为迷幻药是探索内心世界、开启遗传物质中“直觉知识宝库”的钥匙。他激情地为个人探索精神世界的权利辩护,质问为何我们的社会将这种自我发现的行为定为犯罪。
这两本书成为了地下化学家和毒品爱好者的“圣经”,详细列出了数百种精神活性物质的合成方法和剂量信息。
在《PIHKAL》中,第109个条目正是MDMA。舒尔金本人对MDMA的评价不高,称其为“低卡路里的马提尼”,但他的研究小组成员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描述:“我感到内心无比纯净,只有纯粹的欣快……我被这种体验的深刻性所折服。”
MDMA能同时引发大脑中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这种独特的化学组合带来了强烈的共情、欣快和超越感,这是其他任何药物都无法比拟的。
在20世纪70年代,MDMA首先被美国的心理治疗师用作治疗工具。一位名叫利奥·泽夫的治疗师在舒尔金的介绍下尝试了MDMA后,被其打破人际界限、促进坦诚交流的强大功效所震撼,取消了退休计划,转而用它为数千名患者进行治疗。
然而,MDMA很快就从治疗室走向了街头。一个绰号“德州团体”的贩毒团伙在1984年每月能售出50万粒药丸。它在达拉斯等地的夜店中迅速流行,成为享乐主义的象征。
80年代末,一群英国锐舞客在西班牙伊维萨岛的夜店里发现了这种“神奇药物”,并将其带回了英国。在那个撒切尔主义盛行、社会氛围压抑的时代,MDMA和随之而来的酸性浩室(Acid House)音乐,为英国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现实、寻求集体狂欢的方式。MDMA的使用呈爆炸式增长,它不像海洛因或可卡因那样与针头和粉末联系在一起,而是以印有友好标识的药丸形式出现,降低了人们的心理戒备。它不会引起像LSD那样的强烈幻觉,使用者只想跳舞和拥抱,这使其受众远超传统的迷幻药使用者。
摇头丸的出现,将一个原本属于小众的亚文化,变成了席卷全球的主流青年文化。从心理治疗师的沙发,到伊维萨、曼彻斯特、伦敦乃至全世界的舞池,MDMA成为了数百万人的首选药物。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另一个文化现象也从边缘走向了主流——互联网。毒品文化和网络技术不仅在舞池上相互点头致意,它们还握手、拥抱,共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三章:在线毒品文化的诞生
互联网上买卖的第一件商品是大麻。这笔交易发生在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利用ARPANET(互联网的前身)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同行们悄悄安排了这次交易。这标志着电子商务的开端,也预示着互联网与反主流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互联网的诞生根植于一种协作、利他和去中心化的理想。它的许多早期先驱,如道格·恩格尔巴特(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的发明者)和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概览》的创办者),都深受60年代加州反主流文化和迷幻药体验的影响。布兰德提出了“信息渴望自由”的口号,而恩格尔巴特则梦想着一个人们通过个人电脑进行协作的未来。这种精神与迷幻药所倡导的平等、互联的乌托邦不谋而合。
在万维网出现之前,Usenet是全球性的在线讨论系统,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媒体。它由成千上万个名为“新闻组”的讨论区组成。1987年,为了言论自由,计算机科学家约翰·吉尔摩等人创建了一个名为 .alt 的顶级分类,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自由创建新闻组,无需任何人的批准。这里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怪人和反叛者的聚集地,也催生了最早的在线毒品文化。
在 alt.drugs、alt.drugs.psychedelic 和 alt.drugs.chemistry 等新闻组里,一个由数万名读者组成的社区开始形成。在这里,人们可以公开讨论毒品的使用、效果,甚至是如何制造非法化合物。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当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加紧打击设计师毒品时,成千上万的收件箱里每天都会收到关于如何制造它们的详细教程。
互联网民主化了曾经秘而不宣的知识。alt.drugs 的常见问题解答(FAQ)用科学和逻辑粉碎了流传已久的毒品谣言(如抽香蕉皮能致幻),并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来源。在这个虚拟空间里,身份被分解为二进制代码,人们可以匿名地分享经验和知识,而不必担心现实世界中的法律后果。正如一句著名的漫画所说:“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同样,也没人知道你在合成设计师毒品。
1996年,alt.drugs.chemistry 上演了一场著名的“论战”。一位名叫 Eleusis 的发帖人,逐章逐节地批驳了地下化学经典《甲基苯丙胺制造的秘密》中的技术错误,并与该书作者“费斯特叔叔”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吸引了全球观众,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个掌握了新技术的年轻化学家,公开挑战并颠覆了旧的权威。信息的分发和复制变得即时、无限且免费。
后来人们发现,Eleusis 和他的辩论对手 Zwitterion 其实是同一个人——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名叫杰弗里·詹金斯的英语专业毕业生,他为了完善MDMA的制造工艺而自学化学。他用两个身份发帖,是为了确保能进行高质量的技术讨论,并避免被发现。他将自己学到的知识无私地分享出来,尽管他知道这可能会被不法之徒利用,但他更希望那些和他一样追求知识的人能从中受益。
随着万维网的兴起,这些讨论从文本界面的Usenet转移到了图形化的网站。The Hive 就是这样一个早期论坛,它成为了MDMA制造者和爱好者的聚集地,拥有超过6000名成员。尽管该网站于2004年被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曝光后关闭,其创始人也被捕入狱,但其内容——数千篇关于数百种药物制造方法的帖子——被一位版主 Rhodium 精心保存下来,并以档案的形式在网上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其他网站也开始提供有关毒品的可靠信息。1996年,《E代表摇头丸》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斯·桑德斯建立了 ecstasy.org 网站,免费提供关于MDMA的客观信息,并发布药丸测试数据,揭示了市面上许多所谓的摇头丸其实是假货或有毒物质。这开创了在线减少危害(harm reduction)的先河。
另一个里程碑式的网站是 Erowid.org。自1995年成立以来,它已成为全球关于精神活性物质最重要的信息库。其“体验库”收集了数万份由用户提交的第一手“迷幻体验报告”,详细记录了数百种植物和合成药物的效果、剂量、风险和相互作用。它就像一个拥有调制解调器的萨满小屋,成为了任何想要了解、分享或理解迷幻体验的人的首选之地。Erowid 在传播关于天然迷幻植物(如死藤水、鼠尾草)和舒尔金的合成化学品知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舒尔金的著作《PIHKAL》和《TIHKAL》的全文在网上发布后,一场革命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信息不再被锁在书本里,而是可以通过几次点击就发送给任何人。一个全新的化学领域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
到21世纪初,网络不仅是谈论毒品的地方,它即将成为一个可以购买毒品的地方。
第四章:“研究性化学品”场景的兴衰
大约在1999年,就在舒尔金的著作《PIHKAL》出现在Erowid网站后不久,他所创造的那些环取代苯乙胺和色胺类似物开始在美国的一些简陋网站上出售。在线用户将这些新药称为“研究性化学品”(RC)。这些物质本质上就是设计师毒品,但在当时,除了舒尔金和他的小圈子,几乎没有人服用过。
这个场景的早期参与者是数千名自称为“精神航天员”的内在空间探索者。他们通过浏览科学文献和在线讨论来研究这些化合物的效果。互联网不仅促进了这些新药的供应和分销,更关键的是,它帮助人们分辨出哪些药物有趣、哪些可怕、哪些能带来超凡的视觉体验,哪些纯粹是浪费钱,或者甚至是致命的。这既是一场信息革命,也是一场化学起义。
对于一个面对未知化学品的使用者来说,最安全理性的做法就是询问前人的经验。网络让这种交流变得简单。Erowid成为了RC使用者的核心社区,他们提交了数千份关于新药的报告,详细记录了剂量、使用情境和体验。这些来自地下、最初只影响少数无畏探索者的活动,开启了国际毒品市场部分虚拟化的进程。
在2000年,这些RCs主要在美国、东欧以及日益重要的中国的秘密实验室里小规模生产。当时,这些药物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是合法的,因为它们是全新的,并未被列入任何国际或国内的毒品管制名单。
然而,英国的法律在当时相对先进。与美国模糊的《类似物法案》(该法案试图根据化学结构和效果的“相似性”来禁止新药)不同,英国在1977年就通过了非常精确的法律,明确指出了哪些分子结构和环取代方式是非法的。
1998年,英国发生了一系列因服用一种名为4-MTA的强效安非他命衍生物而导致的急性中毒和死亡事件。这种药物是由另一位美国化学家大卫·E·尼科尔斯教授发明的,他本意是寻找无毒的血清素释放剂,用于治疗和抗抑郁。但这种药物被不法商贩当作超强摇头丸出售,造成了悲剧。
这一事件促使英国当局重新审视其毒品法。他们发现,1977年的法律修正案虽然预见性地禁止了许多舒尔金的化合物,但仍有几十种药物逃脱了管制。于是,在1999年,英国政府通过一项法定文书,几乎将《PIHKAL》和《TIHKAL》中剩余的所有化合物都列为A类毒品,与海洛因和可卡因同级。
然而,这项新法律无意中为任何不符合这些精确描述的新药敞开了大门。就像水一样,药物设计师总能找到绕过障碍的方法。从某种角度看,法律甚至为他们精确地勾勒出了什么是合法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法律漏洞更大。1992年,一个关于A-ET(一种色胺类药物)是否为DMT类似物的案件中,法官裁定《类似物法案》的定义“模糊得违宪”,因为它既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也无法有效防止任意执法。这使得许多RCs在美国处于一种法律灰色地带。卖家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在产品上贴上“非供人类食用”的标签,他们就能免于DEA(美国缉毒局)的打击。
到了2000年,随着网络使用的普及和《PIHKAL》的在线传播,RC业务开始起飞。像2C-I、2C-E、2C-T-7等迷幻药和共情剂,任何有信用卡的人都可以买到,并在几天内邮寄到世界任何地方。
然而,这个场景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些使用者因不当使用而过量死亡。例如,几起死亡事件是由于鼻吸2C-T-7造成的,这种方式会大大增强其效果。2001年,DEA关闭了JLF等几个主要的RC网站。
2004年7月21日,DEA发起了名为“网络旅程行动”(Operation Web Tryp)的大规模打击,逮捕了10名供应商,关闭了5家RC网站。DEA宣称,这些网站将“高度危险的设计师毒品类似物伪装成‘研究性化学品’进行分销”,并导致了至少两起死亡和十四起非致命性过量事件。
几个月后,英国也发起了对应的“伊斯梅涅行动”(Operation Ismene),逮捕了22名从美国网站购买2C-I的个人用户。警方声称摧毁了一条“美英之间的毒品供应路线”,但实际上这只是22个购买极少量个人用药的个体。这次行动并没有起到威慑作用,反而起了反效果。
一位被捕者回忆说:“我认为正是伊斯梅涅行动让更多人注意到了这件事。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报道。那些从未想过在网上买药的人心想:‘哦,太好了,看——你可以在网上买到毒品!’”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些打击行动的意外后果开始显现。警方本想遏制这股潮流,却无意中助长了它的蔓延。随着网络用户的增长和网速的提升,这场猫鼠游戏中的追赶者,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第五章:暴风雨前的宁静与一场奇特的干旱
在“网络旅程行动”和“伊斯梅涅行动”之后,全球的研究性化学品(RC)场景转入更深的地下。许多用户开始保持沉默,但这个圈子仍在悄然发展。像化名为“本尼”的办公室职员一样,许多对精神活性药物着迷但现实中无处可寻的人,开始通过网络探索这个新世界。
本尼在2004年左右,通过在Usenet上结识的朋友,发现许多舒尔金书中提到的物质可以从精细化工公司订购。他伪造了一份研究计划书,成功地从一家信誉良好的公司订购了2C-I。他回忆道:“当我收到包裹时,觉得这太荒谬了……怎么会有人允许我从网上订购强效药物,然后通过普通邮件收到?这简直不可思议——而且极其容易。”
本尼和像他一样的先驱者,利用谷歌搜索在线化学品目录,系统地寻找《PIHKAL》和《TIHKAL》中的药物来源。在当时,这些行为还相对孤立,但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普及,这种研究和购买新药的过程也日益商业化和商品化。
大约在2004年,欧洲的宽带连接开始普及,网速的大幅提升改变了人们的上网体验。用户开始支付包月费用以获得持续的网络接入,而不是按分钟计费。网络从一种偶尔使用的工具,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催生了大量基于新型、简单易用的论坛软件(如vBulletin)的在线社区。其中一些论坛专门讨论精神活性药物。与早期的Usenet相比,这些论坛对非技术用户更加友好,也更加活跃。在线毒品文化变得更加成熟和主流。
Bluelight 论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它于1997年作为一个小型的MDMA用户社区起步,在“网络旅程行动”后规模和影响力迅速扩大。如今,它已成为网上最繁忙的毒品用户社区之一,拥有数百万帖子和每月超过一百万的访客。它提供的信息比大多数官方渠道更详细、更准确,成为了用户、学者乃至执法部门了解新毒品趋势的前沿阵地。
Bluelight 奉行减少危害的原则,即承认人们会使用毒品,并致力于提供信息以降低使用风险。论坛最严格的规定是禁止提供毒品来源,但用户们自由地分享关于药物效果、安全剂量、危险组合的知识。这里的讨论水平很高,有时甚至需要博士级别的生物药理学和有机化学知识才能看懂。
与此同时,Web 2.0时代来临。维基百科、MySpace、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平台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们创造、分享和消费信息的方式。网络从被动消费模式转向了主动参与模式。到2011年,全球网民数量已达22.7亿。
电子商务也已成熟。亚马逊、iTunes和PayPal等服务让在线支付变得简单而值得信赖。这种信任和便利性,为在线毒品市场的扩张铺平了道路。
2004年,英国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在线毒品购买热潮。当时,关于迷幻蘑菇的法律存在一个漏洞:新鲜的蘑菇是合法的,只有经过加工(如干燥或烹饪)才算违法。荷兰的“聪明商店”利用这一点,开始通过邮购向英国销售新鲜的迷幻蘑菇和种植套件。很快,英国的实体店和网站也加入了进来,从伦敦的牛津街到时尚市集的摊位,新鲜蘑菇随处可见。网络促进了专业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跨海连接起来。2005年,英国政府匆忙修补了这个法律漏洞,禁止了新鲜蘑菇的销售。
这个“蘑菇热”证明了,一旦有新的、尤其是合法的药物出现,英国人就会去尝试,并且他们很乐意像在亚马逊上买书一样在网上购买毒品。
然而,就在这个新市场崭露头角之际,一场奇特的“干旱”正在酝酿。大约从2008年开始,英国乃至全球的可卡因和摇头丸(MDMA)的质量急剧下降。法医科学服务局的数据显示,街头可卡因的纯度从十年前的40-50%降至10%甚至更低,有时甚至不含任何可卡因。这部分是由于英镑贬值,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贩毒团伙大量使用苯佐卡因等麻醉剂作为填充物。
更神秘的是MDMA的全球性短缺。从2007年到2008年,高质量的MDMA突然从市场上消失了。Pillreports.com这个用户众包的药丸测试网站,页面上充满了粉红色的报告——代表药丸不含MDMA。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名为哌嗪的合法化合物,它会引起头痛、恶心和奇怪的幻觉,使用者普遍排斥它。
为什么犯罪集团要用这种劣质替代品来疏远他们的客户?没有人知道原因。英国和欧洲的用户们迫切需要一种可靠的MDMA替代品。一个巨大的市场真空形成了。
这个真空的背后,是2007年至2008年间在柬埔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将把本书的所有线索都串联起来,并成为未来几年毒品市场剧变的支点。
第六章:甲氧麻黄酮的疯狂:地下文化冲击商业街
2008年,在柬埔寨西南部偏远的豆蔻山脉,环保组织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营地。现场散落着被砍伐的姆烈白树的残骸,这种树的树皮和树根富含黄樟素——制造MDMA(摇头丸)最简单的化学前体。在这里,偷猎者们用简陋的设备每天能蒸馏出约60升黄樟素油。
2008年底,联合国禁毒官员在柬埔寨销毁了33吨被缴获的黄樟素油。这批原料足以制造2.6亿粒摇头丸,相当于英国用户五年的总消耗量。这次行动,加上2007年澳大利亚破获的史上最大摇头丸走私案,共同导致了2008-2009年全球MDMA的严重短缺。
当一种毒品消失时,另一种毒品总会取而代之。面对市场上充斥着劣质的哌嗪类替代品,一个巨大的市场真空亟待填补。
早在2003年,一位化名为“Kinetic”的地下化学家在The Hive论坛上发布了一篇帖子。他记录了自己如何在两天内合成了一种新药——4-甲基甲卡西酮,即后来的甲氧麻黄酮(Mephedrone)。这是一种全新的甲卡西酮类似物,其效果介于可卡因和摇头丸之间:欣快、兴奋、共情,但作用时间短,这使得它很容易让人上瘾。Kinetic在帖子结尾挑衅地写道:“我必须对英国政府和他们愚蠢的毒品法说声‘去你的’,因为我现在high得像风筝一样,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
Kinetic是对的。与已被英国法律严密控制的苯乙胺和色胺类不同,卡西酮类药物的类似物从未被管制过。他安全地绕过了法律,为四年后填补MDMA市场空白的合法药物铺平了道路。
最初,甲氧麻黄酮被隐藏在品牌产品中。2007年,一家名为Biorepublik的以色列公司开始销售名为NeoDoves和SubCoca的“合法快感”胶囊。在MDMA严重短缺的澳大利亚,这些产品大受欢迎。没人知道里面是什么,但它们效果显著,而且比被污染的摇头丸便宜。
后来,通过Bluelight论坛上化学家们的努力,这些胶囊的主要活性成分被鉴定为4-甲基甲卡西酮。地下化学界的观察家们认出,这正是Kinetic在2003年发布在The Hive上的配方。
甲氧麻黄酮与阿拉伯茶(Khat)有化学关联,后者在也门和索马里等国被咀嚼作为社交兴奋剂。2004年,以色列禁止了阿拉伯茶的主要成分卡西酮,于是Biorepublik的化学家们创造了甲氧麻黄酮这个合法的类似物来规避禁令。
当这个配方在网上被公开后,英国的毒贩们开始直接从中国工厂订购甲氧麻黄酮,并建立网站进行销售。谷歌的广告系统无意中成为了他们的帮凶,在讨论该药物的严肃新闻文章旁边,自动生成了购买链接。
毒贩们巧妙地将甲氧麻黄酮标记为“植物肥料”,以规避药品和食品安全法。它像病毒一样在英国蔓延开来,尤其是在非法毒品质量差、价格高的小城镇。这种药物的流行速度前所未有,几周内就获得了大众市场的认可,而MDMA则花了数年时间。
成吨的甲氧麻黄酮从中国运往英国和欧洲。英国的经销商们聪明地将生产外包给了劳动力成本低、监管宽松的中国。成千上万的邮递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运送这种白色粉末的毒品快递员。
甲氧麻黄酮的流行,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毒品的态度。那些从未听说过舒尔金,从不考虑在网上买药的人,开始服用这种他们认为“合法即安全”的研究性化学品。
然而,这场狂欢很快就走到了尽头。令人不安的报告开始出现:使用者出现手指和膝盖变紫(可能是血管严重收缩的迹象)、心悸等症状。医院接诊的因该药而出现精神问题的人数急剧增加。
2009年11月,英国媒体开始报道与甲氧麻黄酮相关的死亡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道德恐慌,尽管后来许多案例被证实与该药无关。在媒体的巨大压力下,英国政府于2010年4月匆忙将甲氧麻黄酮及所有取代卡西酮类药物列为非法。这一决定是在未经充分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做出的,导致多名顾问委员会成员辞职以示抗议。
这项禁令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但完全可以预见的后果。它非但没有减少危害,反而刺激了更多新替代品的出现,也没有减少需求。禁令反而推高了价格,增加了使用者的健康风险,并将市场完全交给了犯罪组织。当英国和中国都禁止了甲氧麻黄酮后,生产地很快转移到了印度。
毒品2.0的下一阶段已经准备就绪。寻找甲氧麻黄酮替代品的竞赛开始了,其驱动力是使用者的猎奇心和贩卖者的贪婪。
第七章:“汪汪”是新的“喵喵”
2010年甲氧麻黄酮被禁后,供应商们纷纷关门,但用户和经销商们立即开始寻找替代品。新一波的“合法快感”迅速涌入市场,但它们大多是危险、无效且制作粗劣的。
市场又回到了“研究性化学品”的模式,但这一次的参与者不再是追求精神探索的“精神航天员”,而是纯粹为了赚钱。一位欧洲RC供应商说:“甲氧麻黄酮的热潮过后,这个场景不再是地下的了。所有人都想从中快速赚钱,连孩子们都在以可笑的价格到处卖这种化学品。”
Ivory Wave 是一款早期的替代品。最初,它含有MDPV,一种在微量剂量下就起效的强效兴奋剂,过量服用会导致精神病。制造商为了模仿可卡因的效果,还加入了麻醉剂,这极具误导性,导致用户严重过量。当MDPV也被禁后,他们又换成了另一种更强效、作用时间更长的合法药物desoxypipradol。这导致了多起使用者出现急性偏执性精神病甚至跳崖自杀的悲剧。
在禁令后的混乱时期,欧洲毒品监测中心(EMCDDA)的数据显示,新药的出现速度惊人:2010年有41种,2011年有49种。在短短三年内,共确认了150种新化合物,而且市场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
经销商们开始销售名为NRG-1的粉末,声称其效果与甲氧麻黄酮类似,但拒绝透露成分。后来的分析发现,大多数NRG-1要么含有已被禁止的卡西酮,要么只是咖啡因,甚至是无效成分。市场一片混乱,用户在寻找一种新的、可靠的刺激物。
与此同时,合成大麻素也开始流行。在此之前,所谓的合法大麻替代品大多是无效的草药混合物。但一种名为Spice的新产品效果显著,其效力来源成谜。后来,德国的实验室分析发现,其活性成分是一种名为JWH-018的合成大麻素。
JWH-018是由美国化学家约翰·威廉·赫夫曼教授在研究人体大麻素受体时创造的数百种化合物之一。他的研究纯粹是出于科学好奇,却无意中为全球的“合法大麻”市场提供了弹药。中国实验室开始大量生产JWH-018及其他类似化合物,将其喷洒在草药上,制成各种品牌的合成大麻产品,如K2、Black Mamba等,销往欧美。
这些合成大麻素远比天然大麻危险。赫夫曼教授解释说,它们与大麻素受体的作用方式不同,可能导致严重的精神问题和血压急剧升高。然而,在美国等国,由于持有大麻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如失去工作、学业甚至福利),许多人转向了这些更危险但合法的替代品。
当JWH-018等第一代合成大麻素被禁后,市场上迅速出现了更强效、更未经测试的替代品,如AM-2201。这就像一场化学版的“抢椅子”游戏。
在英国,人们真正寻找的是一种新的、像甲氧麻黄酮一样的欣快型兴奋剂。2010年夏天,一种名为6-APB的药物出现在网上。它是一种MDA(摇头丸的一种类似物)的合法类似物。化学家们通过对MDA分子进行微小的结构调整,创造出了一种属于全新化学类别(苯并呋喃类)的化合物,从而巧妙地绕过了大多数国家的法律。
一位早期用户在Bluelight论坛上分享了他的体验:“这是一种绝对美妙的药物……就像MDMA,但没有那么多汗流浃背的渴望感。” 这种新药被供应商命名为Benzo Fury,并进行了专业的品牌包装和网络营销。通过巧妙的搜索引擎优化,它在几周内就变得广为人知。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数百种新化合物涌入市场。除了兴奋剂和合成大麻素,还有新的迷幻药(如4-AcO-DMT,效果类似迷幻蘑菇)、镇静剂(如phenazepam,一种俄罗斯的抗癫痫药,其活性剂量仅为1毫克,极易过量),以及分离性药物。
其中,美沙西胺(methoxetamine),一种氯胺酮(K粉)的合法类似物,迅速流行起来。它是由一位化名为“卡尔”的地下理论化学家设计的,目的是创造一种比氯胺酮体验更少“离奇”、身体伤害更小的替代品。它在网上以每克约70英镑的价格出售,但其活性剂量远低于氯胺酮,一克可供多达100人使用。
这个曾经由少数专家和爱好者组成的、自我约束的RC场景,在甲氧麻黄酮之后,彻底变成了一个 unregulated、利润驱动的疯狂市场。任何人都可以从中国实验室订购强效的白色粉末,而政府的禁令似乎总是在追赶,却永远也赶不上。
第八章:盐味僵尸与化学恐慌
任何严重的药物滥用,其结局无非是成瘾、过量或监禁——过去十年中出现的新药也不例外。然而,与传统毒品不同的是,这些新药还伴随着一个额外的风险:由于缺乏信息和监管,使用者往往成为无知的实验品。
在线药物安全倡导网站SOS的管理员认为,当前市场的危险性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类似物法案》的措辞。该法案禁止销售“供人类食用”的类似物,这意味着卖家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剂量、效果或安全使用的信息,否则就等于承认了其药物用途。这种法律上的悖论导致了研究性化学品(RCs)在销售时没有任何标签或使用指南。“据我所知,每一起与RC相关的死亡事件都是由这一个因素造成的,”他说。
一个最致命的危险是标签错误。2009年10月,发生了一起震惊整个RC圈子的悲剧。一名丹麦的RC供应商和他在世界各地的几名客户,都以为自己购买的是2C-B-FLY,一种强效的迷幻药。然而,中国的实验室错误地寄来了另一种效力强得多的药物——溴-蜻蜓(bromo-dragonFLY)。后者的活性剂量仅为200微克(0.2毫克),而前者是18毫克。这意味着他们服用了近90倍的致死剂量。这起事件导致丹麦和美国至少两人死亡,多人中毒。
这些悲剧凸显了在缺乏监管的市场中,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用户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瑞典是RCs过量致死事件的高发区,这与其拥有欧洲最严厉的禁毒法不无关系。当传统毒品难以获得且惩罚严厉时,人们自然会转向看似“安全”的合法替代品。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美国。2011年,明尼苏达州布莱恩市的一群高中生在一个派对上分享了2C-E,一种舒尔金发明的迷幻药。他们没有使用精确的秤来称量,而是凭感觉“目测”剂量,导致一名19岁的青年过量死亡,多人中毒。这再次证明,对于这些在微克或毫克级别就起效的强效化学品,无知是致命的。
在美国,“浴盐”(bath salts)成为了RCs的代名词。这些产品通常含有MDPV等强效兴奋剂,被伪装成沐浴产品在便利店和加油站出售。2012年,媒体对“浴盐”的报道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所谓的“迈阿密僵尸食脸案”。一名男子在攻击并啃咬另一名流浪汉的面部后被警方击毙。警方和媒体立即将此归咎于“浴盐”,尽管后来的毒理学报告并未在他体内发现这类物质。
这一事件,连同其他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引发了全国性的道德恐慌。然而,这些报道往往忽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比如佛罗里达州在精神健康服务方面的资金严重不足。将复杂的社会悲剧简单归咎于一种新药,是一种省事但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与此同时,合成大麻素在美国也造成了严重问题。2011年,美国毒物控制中心接到了近6000个与“浴盐”相关的求助电话,以及7000个与假大麻相关的电话。而在2009年,这两个数字都是零。在阿拉巴马州,30名年轻人因吸食了被农药污染的合成大麻而导致肾衰竭。
这些事件背后,是一个利润惊人的产业。一克在中国以3美元购得的MDPV,可以制成40包在美国售价25美元的“浴盐”,利润高达近1000美元。
美国的禁毒战争,尤其是对大麻的严厉打击,无意中将许多年轻人推向了这些更危险、更未知的化学品的怀抱。对于那些面临严格药物测试的学生、雇员甚至福利领取者来说,这些无法被常规检测出的新药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就连好莱坞明星也未能幸免。女演员黛米·摩尔因吸食一种合成大麻化合物而出现惊厥,被紧急送医。这表明,RCs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这个不受监管的市场充满了危险。但正如一位节日医疗帐篷的负责人所说:“目前合法的物质,远比非法的要危险得多。”
第九章:你的快克在邮寄途中
当你第一次访问“丝绸之路”(Silk Road)网站时,会有一种强烈的认知失调感。它的界面看起来就像早期的亚马逊或eBay,有商品分类、购物车、卖家评级和用户反馈。但这里出售的不是书籍或电子产品,而是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毒品:从海洛因、可卡因、LSD,到各种研究性化学品。
这是一个赛博朋克式的梦想——或者说噩梦——在现实中上演。它由一个化名为“恐惧海盗罗伯茨”(Dread Pirate Roberts, DPR)的神秘人物运营,他宣称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网站的规则很简单:禁止任何旨在伤害或欺诈的商品,如被盗物品、假币、暗杀服务和武器,也禁止任何与儿童色情有关的内容。除此之外,一切皆可交易。
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存在,得益于两大核心技术:
- Tor网络:这是一个由美国海军最初开发、后由志愿者维护的匿名网络。它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多个服务器之间层层加密和随机路由你的网络流量,从而隐藏你的真实IP地址。网站本身也托管在Tor的“隐藏服务”上,其服务器的物理位置无法被追踪。这片区域被称为“暗网”。
- 比特币(Bitcoin):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加密数字货币,由一个匿名的程序员“中本聪”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发布。它不依赖于任何中央银行或政府,交易记录被保存在一个名为“区块链”的公共分布式账本上。虽然交易是公开的,但用户的身份由一串匿名的字母和数字地址代表,这为交易提供了高度的伪匿名性。
结合这两者,丝绸之路的用户可以在几乎完全匿名的情况下,浏览商品、与卖家沟通、完成支付,然后通过普通邮政系统接收他们的“货物”。卖家们会用极其巧妙的方式包装毒品,如真空密封、多层包裹,使其能够通过海关的检查。由于包裹数量巨大,且大多是从国内卖家寄出,被查获的风险极低。
在运营的第一年里,丝绸之路的年交易额就达到了2200万美元。网站通过收取约6%的佣金获利。它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还是一个拥有活跃论坛的社区,用户们在这里讨论毒品、走私技巧和加密技术。
2011年,美国参议员查克·舒默公开呼吁关闭丝绸之路,但这反而为它做了一次巨大的免费广告,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地方。人们从新闻中听到的信息是:“丝绸之路不仅卖罕见的毒品,而且质量还很高!”
与丝绸之路相比,另一个早期的暗网市场“农贸市场”(The Farmer’s Market, TFM)就显得非常不专业。它接受PayPal和西联汇款等可追踪的支付方式,并使用了一个会与警方合作的加密邮件服务。2012年,TFM被执法部门轻松端掉。这次行动反而凸显了丝绸之路在技术上的优越性,并向所有人展示了安全运营暗网市场的关键:无可挑剔的通信和支付安全。
丝绸之路的出现,是信息时代对禁毒战争的一次终极挑战。它不仅仅是一个黑市,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实验。DPR深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通过创建这样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经济体,可以削弱政府的权力,最终实现一个没有强制和暴力的社会。
在这里,早期网络先驱们关于信息自由流动、去中心化、网络战胜权威的梦想,以一种最极端、也最具争议的方式实现了。无论你支持还是谴责,一个事实是,一个持续了数十年的化学和技术创新过程,已经使毒品使用者和生产者能够有效地规避一个被许多人认为是失败的、适得其反的刑事定罪策略。
我们正处在一个法律史的转折点。
第十章:数字时代的禁令
1920年,美国政府在教会的推动下实施了禁酒令。起初,酒精消费量有所下降,但随后急剧反弹。非法酒吧(“地下酒吧”)遍地开花,仅纽约市就有三万家。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了利润丰厚的私酒贸易。为了打击这种行为,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在工业酒精中添加剧毒物质,如煤油、苯、汞盐和甲醇,以阻止人们饮用。1926年圣诞节期间,有26人因饮用这种“毒酒”在几天内死亡。政府对此不负法律责任,但纽约市的法医查尔斯·诺里斯指出:“美国政府必须为毒酒造成的死亡承担道德责任。”
这个历史先例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惊人地相似。当政府禁止大麻等相对安全的毒品时,许多年轻人转向了那些更危险但合法的研究性化学品(RCs)。那么,当悲剧发生时,道德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
最新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正在寻找合法的方式来获得快感,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些新药的风险知之甚少。在音乐节等场所,提供紧急援助的非营利组织发现,他们处理的案例已经从LSD或MDMA引起的心理问题,变成了由RCs引起的癫痫、精神错乱、暴力甚至死亡。一位负责人说:“可悲的是,目前合法的东西,远比非法的要危险得多。”
各国政府的法律对策似乎总是慢半拍,而且往往适得其反。美国的《类似物法案》未能阻止“浴盐”和合成大麻的泛滥。当一项法案最终禁止了几十种RCs后,几周内,市场上就出现了更多、更强效、更未知的替代品,比如活性剂量仅为200微克的NBOME系列。英国推出的临时类别药物令(TCDOs)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禁止一种药物,只会催生另一种更危险的药物出现,陷入一场永无休止的“打地鼠”游戏。
警方也承认,他们无法有效监控这个市场。一位英国高级警官坦言:“我们有小队警员坐在电脑前监控这个吗?没有。公众想要的是街上的警察……这不现实。”
国际合作也举步维艰。尽管SOCA(英国严重有组织犯罪调查局)曾成功说服中国将甲氧麻黄酮列为管制物质,但印度的实验室很快就接管了生产。
舒尔金的新书《舒尔金索引》第一卷已经出版,涵盖了超过1300种化合物,其内容可在网上免费获取。这是一个永不枯竭的“弹药库”。
与此同时,国际上对禁毒战争的反思声音越来越大。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等深受毒品贸易之害的国家的总统,都公开呼吁探讨新的方法,包括合法化。在欧洲,葡萄牙自2001年将所有毒品的个人使用非罪化后,取得了显著成效:问题吸毒者人数减半,与注射毒品相关的艾滋病新增病例也大幅下降。
新西兰则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方案:建立一个受监管的合法合成药物市场。制造商可以提交新的“合法快感”产品进行审批,但必须自费进行严格的临床试验,以证明其风险较低。通过审批的产品将被允许合法销售。此举旨在将市场从不受监管的混乱状态,转变为一个由政府控制、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体系。
大卫·尼科尔斯教授,这位无意中为RCs市场提供了多种“产品”的化学家,也认为现行法律已不合时宜。他说:“解决方案很简单,将安全的药物合法化。蘑菇、麦司卡林、仙人掌和最常用的大麻。如果他们当初就将大麻像酒精一样监管,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些危险得多的合成物。”
我们必须允许吸毒者做出更安全的选择。这意味着要逐步、审慎地回退现有的毒品法,尤其是那些针对MDMA、大麻和天然迷幻药的法律,因为大多数RCs正是为了模仿它们而被创造出来的。同时,必须在学校推行强制性的、诚实的药物教育。
这并非主张任何毒品是完全安全的,它们显然不是。但是,在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数字时代,面对所有证据都表明禁令会增加危害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地坚持这种过时且武断的策略,是极其不负责任和危险的。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禁令,而是一种全新的、基于证据和理性的方法。
第十一章:路的尽头?
2013年10月2日,一个名叫罗斯·乌布利希的29岁德州男子,在旧金山一家公共图书馆的科幻区被FBI逮捕。他被指控为“丝绸之路”的创始人兼运营者——“恐惧海盗罗伯茨”(DPR)。FBI声称,在他被捕时,他的笔记本电脑正以DPR的身份登录着网站后台。
FBI是如何找到这个隐藏在技术和匿名性背后的人物的?如果指控属实,那么DPR的垮台源于一系列经典的操作安全(OPSEC)失误。
调查人员从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找到了最早宣传丝绸之路的帖子。2011年,一个名为“Altoid”的用户在多个论坛上推广这个新生的暗网市场。几个月后,这个“Altoid”又在另一个论坛上发布招聘信息,寻找IT专家,并留下了他的个人邮箱:rossulbricht@gmail.com。
这个线索将虚拟身份与现实世界中的罗斯·乌布利希联系了起来。FBI还发现,乌布利希曾在技术问答网站上用自己的真实邮箱注册,并询问了一个与丝绸之路服务器代码高度相关的技术问题,尽管他一分钟后就将邮箱改成了假名。他未能将自己的多个网络身份进行有效分割,一旦一个身份被识破,其他的也随之暴露。
FBI随后渗透了丝绸之路,进行了超过100次的“测试性购买”,并策反了网站的一名员工柯蒂斯·格林。根据起诉书,DPR在怀疑格林偷窃了用户资金并可能与警方合作后,支付了8万美元,雇佣了一名卧底探员去“折磨并杀死”格林。FBI伪造了格林被“谋杀”的照片,并将其发送给了DPR。
此外,乌布利希还被指控另外五起雇凶杀人案,涉案金额高达65万美元,目标是敲诈者和不诚信的卖家。这些交易都通过比特币完成,并在(虽然匿名但公开的)区块链上留下了痕迹。
最终,加拿大边境警察截获了一个寄往乌布利希住址的包裹,里面含有九张伪造的身份证件,照片全是他本人。2013年10月,FBI正式收网。
丝绸之路的倒台,似乎是执法部门对暗网犯罪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网站仅仅关闭了四周。2013年11月,一个全新的丝绸之路2.0上线了,由一个新的DPR运营。它嘲弄地在首页展示了FBI的查封公告,并在上面P上了一行字:“此地已复活”。
这次查封行动的真正后果是,它不仅没有终结暗网市场,反而催生了几十个新的市场。就像砍掉九头蛇的一个头,会长出两个新的来。Agora, Evolution, Nucleus 等市场迅速崛起,瓜分了丝绸之路留下的市场份额。许多新市场的运营者更加狡猾,技术上也更先进。例如,一些市场引入了“多重签名”交易,资金不再由网站统一保管,而是需要买卖双方共同签名才能释放,大大降低了网站携款跑路(一种常见的暗网骗局)的风险。
与此同时,2013年夏天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揭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正在对全球互联网进行无差别的“拖网式”监控。这让人们怀疑,FBI抓捕乌布利希可能也利用了这些秘密的、可能非法的监控手段,并通过“平行构建”(parallel construction)的方式,即用合法的手段重新“发现”已经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来掩盖其真实的侦查来源。
丝绸之路的故事,将毒品、技术和个人自由这三个主题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禁毒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享乐主义或犯罪的战争,它更是一场关于个人自由和隐私的战争。政府以打击毒品、恐怖主义和儿童色情为名,为自己对所有公民进行全面监控的行为辩护。
暗网市场的现象才刚刚开始。随着技术的演进,新的去中心化市场正在被开发,它们将更难被攻击和关闭。除非政府开始对全世界的每一封邮件进行X光扫描,否则这场猫鼠游戏将永远持续下去。
尾声
就在全球MDMA市场因黄樟素短缺而陷入低谷时,2011年,高质量的MDMA神秘地重返欧洲市场。荷兰的药丸测试中心发现,许多摇头丸的MDMA含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甚至高达220毫克,这导致了一些没有防备的用户过量服用。
起初,媒体猜测是中国出现了新的“超强”摇头丸。但真相是,荷兰的犯罪化学家们再一次展现了他们的创造力。为了绕过对前体PMK液体的国际管制,他们从中国进口了一种名为PMK-缩水甘油酯的合法化学品。这是一种被“掩蔽”的前体,只需简单的一步化学反应,就能轻松转化为被禁的PMK。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专家承认:“贩毒者可以通过对化学品进行微调来改变其外观,以规避管制,然后在非法制造前轻松恢复其母体化合物。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
PMK-缩水甘油酯至今在许多地方仍然合法。只要它存在,高质量的MDMA供应就将保持充足。如果国际社会再次匆忙修订前体管制公约,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供应将再次减少,而新的替代品——无论是新的前体类似物,还是另一种像甲氧麻黄酮一样的新药——也必将出现。
这个故事以一个与开头相似的环形结构结束:每一次法律的围堵,都只会催生出更巧妙的化学创新,形成一个自我延续的、不断升级的循环。 这场关于毒品的战争,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化学和数字的前沿阵地上愈演愈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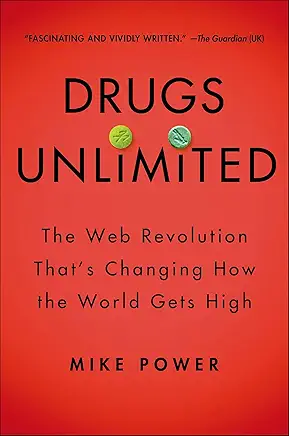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