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乘、大乘、金刚乘与大道
慈悲喜舍, 南传上座部佛法, 西方世界的佛法 ·Index
The Lesser, the Greater, the Diamond & the Way - Ajahn Amaro
小乘、大乘、金刚乘与大道 - 阿姜阿马罗尊者
佛陀曾说,所有快乐中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从“我慢”(我是)的感觉中解脱出来。一旦你仔细审视它,那个幻相便会分崩离析,你再也不会被它所迷惑。深入探索佛教三大传承的内在联系,揭示一条从“自我关怀”走向“无我智慧”的完整解脱之道。
前言:传统的融合与统一
从历史上看,关于南传佛教(Theravada)和大乘佛教(Mahayana)孰优孰劣的争论由来已久。如果你阅读过大量相关文献,你可能会觉得它们在佛教修行的路径上似乎大相径庭——然而,它们之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极为深刻的内在联系。
我初到泰国国际森林寺院时,从未读过任何佛教书籍,也并非刻意要去成为一名佛教僧侣。我当时只是一个四处流浪、自由自在的灵性探索者,偶然间来到了这个由阿姜苏美多(Ajahn Sumedho)在几年前建立的森林道场。坦白说,最初的目的不过是想找个地方吃几顿免费的饭,有个屋顶遮风避雨过几夜。我完全没有料到,在十二三年之后,我会从事着今天我正在做的事情。
但当我到达那里,向僧侣们请教佛教的教义,希望他们能为我稍作解释,好让我对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时,其中一位僧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了我一本禅宗大师的开示录。他对我说:“别费劲去读南传的文献了,那些东西非常枯燥乏味。读这本吧,它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大同小异,能让你对我们的修行有个直观的感受。” 当时我想:“好吧,看来这些人对自己的传统并不那么执着。” 那本书就是《禅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s Mind)。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尽管在任何一个佛教国家,其特定的传统形式都有其强大的影响力,但修行者并不必然会因此受到束缚或限制。
我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才第一次听说“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这两个名词,更不用说了解它们之间的分歧了。似乎当你真正地投入生活去实践时,并不会感到有什么巨大的差异;但如果你过度地思考,或者你属于那种喜欢撰写历史、著书立说,并卷入宗教生活政治层面的人,那么分歧也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
这些年来,我听阿姜苏美多讲过好几次,在他出家生活的第一年里,他所遵循的修行指导,其实来自于虚云老和尚(Master Hsü Yün)在中国举办的一次禅修开示。他把那次禅修的佛法开示当作自己最基础的禅修指南。当他去到巴蓬寺(Wat Pah Pong)时,阿姜查(Ajahn Chah)问他在修什么样的禅法。起初,他心里还咯噔一下,想:“哦,糟了,他肯定要让我放弃现在的方法,改修他的法门。” 但是,当阿姜苏美多描述了他一直在做的修行,并提到效果非常好时,阿姜查说:“哦,那很好,继续修下去就行了。”
由此可见,尽管两种传统在历史上可能存在差异,但它们的目标却有着非常强大的统一性,彼此之间是高度和谐的。
慢慢地,我们开始理解不同的佛教传统究竟在谈论什么。它们被划分为小乘(Hinayana)、大乘(Mahayana)或金刚乘(Vajrayana),看似是不同类型的佛教修行,但它们基本上只是不同的标签,用以描述我们内心的不同态度。当这些传统被善巧地运用时,它们能够触及我们心灵的方方面面——从最自私、最世俗的层面,到最高尚、最神圣的层面。它们关照我们生命中所有不同的层次。只有当人们误解了它们,将它们视为固定不变的立场时,彼此之间才会产生冲突。
小乘:自我关怀的起点
例如,南传佛教常常被视为代表着小乘的立场,其核心是一种自我关怀:“快,让我离开这里,我受够这摊烂摊子了;我希望这一切能尽快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这确实代表了一个人在灵性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明确的阶段。
比如,我们最初都持有一种世俗的态度,基本上对灵性成长毫无兴趣。我们只想获得快乐,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在何处寻得。我们的世界观是物质的,完全没有真正的灵性方向。然后,我们对灵性生活的第一次觉醒,发生在我们开始认识到“苦”(suffering)的存在之时。我们意识到需要拯救自己,帮助自己。
因此,“小乘”指的就是最初踏上灵性道路的那一步,看到有些事情必须得做,才能整理好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自然的自我关怀;如果你自己都快要淹死了,你是不可能去着手帮助别人,或是过度关心他人福祉的。你必须先让自己到达某个坚实的岸边。
然而,如果仅仅将灵性修行建立在自我关怀之上,只试图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平静和快乐,其价值显然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卡在这个层次上,某种枯燥和贫瘠感便会悄然而至。
沙漠体验:自我囚笼的困境
最近,关于这一点我有一段有趣的经历。通常,我的性格是友善、慷慨、外向的,并且一直对大乘佛教的教义抱有相当的好感。然而,去年年底,我发现一种虚无主义的情绪正悄悄地渗入我的内心。一种挥之不去的念头是:“我受够了这一切;我想解脱出去。”
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不寻常,而且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想到要活到老年,不得不应付人世间的存在、生活的琐碎以及单调乏味的寺院常规,这一切都变得“毫无乐趣”。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显得令人难以置信地毫无吸引力。那感觉就像被困在一片广阔的盐碱地的中央,看不到任何地平线。这是一种强烈而磨人的负面情绪。我对任何人都感觉不到友善;我对僧侣生活也感受不到任何启发。整件事变成了一场乏味的繁文缛节。
每两周,我们都会举行一次戒律诵念仪式,大概需要念诵45分钟。这本应是僧团精神的定期更新——重温我们的愿心,再次投入于我们的戒律和生活方式。但我坐在那里诵念着这些戒律,心里却在说:“这完全是一场闹剧,纯粹是浪费时间”——同时还要努力记起我本该念诵的词句。而且,这恰好发生在我本应协助教导的冬季安居禅修的开端。我想:“这下真的难办了。” 我本应去激励那些年轻的僧侣和尼师,而我自己的内心却正经历着这种极度负面的状态。
我观察着这一切,但似乎有很多理由可以为这种消极的思维方式辩护。我想:“嗯,也许这么多年来我都搞错了,也许我只是一个头脑空空、过度乐观的傻瓜,而做一个厌倦的愤世嫉俗者,或许才是一直以来的正确道路。”
然后,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全彩色的梦。在梦里,我把自己的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吃掉了。我先拔下我的拇指,然后是每一根手指,把它们吃了下去。那个梦是如此逼真,我甚至能尝到它们的味道,一种平淡无奇的味道。我吃掉了整个左手,然后开始吃右手,吃了前三根手指,直到只剩下食指和拇指。这时,我内在的某个东西对我说:“醒来!”
我醒了过来,对这个梦的记忆异常清晰。瞬间,我明白了自己一直在做什么。出于放逸和不觉知,我一直在摧毁那些对我最有帮助的朋友和助手——我的那些能力。那些消极和自我毁灭的态度,正在掩盖和烧毁我所有美好的品质。那些本已存在的灵性品质正在被摧毁。这真的给我的整个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意识到我走错了路。
大乘:利他主义的喜悦
接着,另一件事自发地发生了。我当时并没有刻意去想大乘佛教或菩萨道的理想,但发生的是,我开始对自己说:“好吧,我不在乎自己这辈子能否感受到哪怕一刻的快乐;我不在乎是否要为此重生一千万亿次。如果在一千万亿次的生命中,我能为另一个众生做哪怕一件善事,那么所有那些时间就没有白费。”
类似这样的念头开始自发地在我心中涌现,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喜悦和幸福,以及一种解脱感。如果你理性地思考一下,这其实很奇怪:一千万亿次生命里,尽是无效的行动、彻底的痛苦和厌倦。但其结果却是充满活力的喜悦和快乐。这正是挣脱“自我关怀”这座监狱的体验。
当心灵陷入那种“求死”的心态,只是等待一切结束时,你所关心的就只有你自己。你对他人变得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即使你本不想如此,你也会发现自己正在周围筑起各种各样的墙壁。我能看到,这正是大乘传统和教义精神的源起:唤醒那种无私,那种意愿,即使任务看起来毫无意义地庞大,也要毅然承担。它会释放我们与其他生命之间天然存在的利他主义和亲近感。我们认识到自己与所有其他生命、所有其他存在的相互联系,出于对这种联系的尊重,一个人会在能够给予、帮助和服务中感受到一种喜悦。
有趣的是,大约在同一时间,有人给了我一本书,让我看到这个原则并不仅仅存在于佛教传统中。作者在书中探讨了这个原则,并引用了印度教和犹太教传统的例子。
他讲述了室利·罗摩克里希那(Sri Ramakrishna)的故事。在他和他的主要弟子辨喜(Swami Vivekananda)诞生之前,他在某个高层的梵天(Brahma heavens)找到了辨喜的转世——他当时正沉浸在禅定之中,对世界全然不感兴趣,“靠近绝对的真理之山”。多么棒的描述!总之,辨喜坐在那里,完全沉醉于极乐之中。这时,罗摩克里希那化身为一个小孩子的形象;他用这个高层天界的氛围编织出一个金色的孩童身体,开始在这位圣者面前唱歌玩耍。最终,过了一段时间,圣者的注意力被吸引了,他睁开眼睛,看到了这个无比迷人的小孩在他面前嬉戏玩闹。最后,当他的眼睛完全睁开,注视着这个孩子时,孩子对他说:“我要下去了;你跟我一起来吧。” 于是,辨喜便下凡与他会合了。
另一个例子来自一位名叫雷布(Rabbi Leib)的拉比。他告诉他的一些弟子:“在这一世之前,我本不想出生;我不想来这里。这个人世间充满了愚蠢、疯狂和白痴。我对这一切已经受够了,根本懒得理会。然后有一天,来了一个家伙,他看起来像个农民,肩上扛着一把铲子。他对我说:‘难道你就没有比整天躺在这里享受永恒的极乐更好的事可做吗?我为了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一点点快乐、一点点喜悦而马不停蹄地工作,而你呢?你却在这里闲逛!’” 他说,他被这个人深深地打动了,于是同意跟他一起走。这个扛着铲子的人就是巴尔·谢姆·托夫(Baal Shem Tov),哈西德派(Hassidim)的创始人之一。据说,他时常漫游于宇宙的高层境界,寻找合适的角色,然后派遣他们到地球来照顾像我们这样的人。所以,看到同样的人类经验原则存在于不同的传统中,是很有趣的。
自我关怀会将我们带入一种“沙漠体验”——即使当我们注意到那些较为粗重的内心烦恼已经平息或自行消退,当我们不再被过多的焦虑、欲望、贪婪、厌恶、嫉妒等情绪所占据,内心相当平静时。正如你们可能已经意识到的,在这次禅修营进行了一周之后,你可能正坐在那里,心相当专注、相当宁静,但感觉到的并非狂喜或一种完整与圆满感,而是一种“那又怎样?”的感觉。“难道佛陀的教法就是围绕着这种空洞的心理状态建立的吗?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当思想和情感方面没有太多波澜,没有巨大的激情需要去搏斗时,这就像待在一个灰色的小房间里。它没有任何令人不安之处,但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似乎显得相当平淡无奇。
你会想:“这简直是骗人的!我跟恐惧和欲望等等斗争了五六年,现在我终于来到了这个自由的空间——我们来到了开阔地——结果却是一片沙漠。这不对劲!”
但随后,你意识到,这并非佛陀所指的圣洁生活的终极目标。因为,尽管一个人看不见任何显著的障碍或烦恼,但那个“你”依然存在,或者在这个情境中,是“我”。那里存在着一种“我”的感觉——某个在这里体验的人——有一个“人”的存在。这种身份感,尽管它并不突出,不会跳出来彰显自己,但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存在。这个“自我”(ego)是一个心理结构,它就像我们周围的一堵墙,一座监狱。因为我们如此深陷于监狱中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没有注意到自己实际上被束缚住了。只有当一切都冷却下来,当一个人有机会环顾四周,审视周遭环境时,才会有机会感受到那种局限感、贫瘠感;那是一种厌倦,一种难以言喻的乏味感!
即使在大乘佛教中——它强调外向、利他、慷慨、慈悲,为了一切众生的福祉而发展灵性生活——如果我们的修行停留在“我将我的生命奉献给帮助所有其他众生”的层面,即使这种精神被高度发扬,最终仍然存在着“我”和“你”——那个正在帮助所有有情众生的“我”。即使在这方面,虽然可以有很多喜悦,你仍然会发现这道障碍,一种孤立感或无意义感。那里存在着一种分离。
因此,运用禅修的实践,不仅仅是沉浸于利他的思想和情感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注意到,佛陀的很多教义都围绕着无我(selflessness)、围绕着空性(emptiness),比如关于“无我”(anatta)的教导。如果没有“我”,那么那个将仁慈散播到整个世界的人又是谁呢?如果没有“我”,那么是谁在发送慈心(metta),又有谁在那里接受它呢?
金刚乘:通往无我智慧的金刚钻
于是,我们看到,存在着一个超越了与“自我”和“他人”相关的理解层次、存在层次。无论我们的愿心可能有多么崇高、精致和纯粹,除非我们超越那种自我认同感和由此产生的分别心,否则那种不完整的感觉将永远存在;那种“沙漠体验”便会悄然袭来。
所以,如果我们穿越了那种宏大的心胸态度,我们便会证悟那属于究竟理解、究竟实相的智慧;这也就是所谓的金刚乘(Vajra)教法。Vajra意为金刚石或霹雳,代表着坚不可摧、力量至上、如金刚般坚固的真理。这便是对“无我”的理解。
当注意力被放在“我”的感觉上时,一个人运用修行来照亮我们对自己身份所做的种种假设。我们必须将心从外部对象上转回来,反照我们对“主体”所做的假设。当内心平静安稳时,开始探究以下问题会非常有帮助:“这一切中心的‘人’是谁?”“那个正在禅修的是谁?”“那个正在了知这一切的是谁?”“知者是谁?”“是什么在了知思想和情感?”
正是当我们审视并挑战“这里存在一个独立实体”这一假设时,监狱的围墙才会轰然倒塌。
大约六七年前,我对此有过一次体验。当时我第一次在一个长期禅修中使用这种禅法,不断地问“我是谁?”或“我为何物?”,并以此在心中制造一种迟疑,将自我感置于正确的视角下。那种感觉就像从一个灰色的牢房里走出来,步入阳光和一片花海之中。那是一种巨大的清新感和解脱感,就像在沙漠中遇到一片绿洲。
佛陀曾说,所有快乐中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从“我慢”(the sense of ‘I am’)中解脱出来。现在,这在某些人听来可能有点荒谬或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的“自我”似乎是整个宇宙中最真实的东西——“如果有什么是真实的,那就是‘我’。” 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审视过,或探究过“我”的、“我的”那种感觉。仅仅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研究过它,并清晰地看到它,所以那个幻相才得以维持。
一旦你仔细审视它,那个幻相便会分崩离析。你再也不会被它所迷惑。
所以,我们运用探究来挑战我们所做的假设以及我们在内心筑起的围墙。对那些假设的挑战,正是消解幻相的关键。然而,自我的本能是立即开始制造其他事情来引发活动,以便我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从而停止这样做。自我就像任何害怕死亡的生物一样,一旦我们开始挑战它的至高无上和中心地位,恐慌反应就会启动。你会发现,头脑会抛出各种有趣且引人注目的想法,来说服你赶快去做点别的事情。所以,这需要极大的决心,仅仅说一声“不!”,然后把心带回到探究:“这是谁?”“是什么在了知这份恐慌?”“是什么在了知这种感觉?”
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Vajra Prajñā Pāramitā Sūtra)中,你会发现这样的句子: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或者: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或者:
万法唯心造。
在《心经》(Heart Sūtra)中也是如此,万佛城这里每天都会诵念。其中有些段落是这样说的: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无明……无老死……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这所做的,正是让我们跨出整个有为法的领域,将整个有为法的世界置于正确的视角下——不要在那些本质上不安全、本质上受限于时间、自我、生与死的事物中寻求解脱、确定性或安全感。只要我们还在有为的感官世界中寻找快乐,我们就注定会失望。我们不可能在那里找到它。而诸如生、死、我、人、苦等事物——这些都是相对的真理,在究竟的层面上,没有苦,没有人曾出生,也没有人曾死亡。存在的只有“真如”(Suchness)、“奇妙”(The Wonderful)、“宇宙心”(Universal Mind)或任何其他被用来描述它的名词。
有趣的是,你不仅仅在大乘或金刚乘的文献中找到这些思想。在南传佛教的经典中,佛陀也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和阐述,尽管它可能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你甚至会遇到一些导师说,“无我”(anatta)的教法不应该被传授,那是一种危险的教法。
有一次阿姜苏美多做完开示后,在场的一位知名的佛教导师感到极其不安和困扰,因为阿姜苏美多在向在家人教授“无我”法门。他认为这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位在家人!)。我也听说泰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认为“无我”这个教法太强大了,不适合传授给你们所有人。但我可不这么认为(众笑)。这才是至高无上的解脱教法,你会在南传佛教中发现很多被忽略的内容,它们持续不断地将心推向这个究竟智慧的顶点。
例如,有一段关于一位名叫阿那律(Anuradha)的比丘的问答。他被一些婆罗门学者质问:“一位觉者死后的本质是什么?”“一位如来(Tathāgata),一位觉悟者,在身体死亡后会发生什么?”“他们还存在吗?”
这位比丘回答:“觉者没有这样说过。”
他们又问:“那么,他们不存在了吗?”
“觉者也没有这样说过。”
“那么,他们是既存在又不存在吗?”
“觉者同样没有这样说过。”他回答。
“那么,他们是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吗?”
“这个,”他说,“觉者也没有这样说过。”
于是他们对他说:“你肯定是个傻瓜,或者是个刚出家不久的新手。你显然不理解佛陀的教法,否则你就能给我们一个像样的答案了。”
然后,他去见佛陀,把与这些人的对话告诉了佛陀,并问道:“我回答得对吗?” 佛陀说:“是的,阿那律,你回答得很好。”
佛陀接着问: “你认为如来就是五蕴(khandhas)吗?” “不是,世尊。” “你认为如来拥有五蕴吗?” 他回答:“不是,世尊。” “你认为如来不拥有五蕴吗?” 他说:“不是,那也不对。” “你认为如来在五蕴之中吗?” “不是,世尊。” “那么,你认为如来与五蕴分离,在五蕴之外吗?” 他说:“不是,也不是那样的。” “正确!”佛陀说,“正是如此——我所教导的,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只是‘苦’以及‘苦的止息’。”
佛陀建议我们不要试图用概念性的术语来定义觉悟者,因为任何概念性的定义都必然是不全面的,只能是相对真实的。佛陀在南传教法中,就像在北传经典中一样,非常清楚地表明,对事物的终极视角是无固定立场的视角,是真正证悟真理,安住于觉知(Awareness)的位置,而不是采取任何一种概念性或理想主义的立场。那才是我们的皈依处。皈依佛,就是成为那个觉知。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与我们的身体、感觉、个性、年龄、国籍、问题、才能相关的一切,都仅仅是有为世界的属性,它们生起又灭去,而对它们的觉知始终存在。修行的全部要点,就是持续不断地安住于那种觉知的品质中。
空性的误区与实践的真谛
如果我们试图在作为一个“人”、身处某个“地方”——一个时间中的“存在”——的层面上寻找确定性和定义,那么生命注定是充满挫折和痛苦的。只有当我们放下“我”、“我的”的感觉,放下这里有一个“人”有地方可去或无处可去的观念时,才会有那种清晰地安住于觉知中的状态。
然而,心的倾向往往是将其概念化。你说:“好吧,我就只是去觉知。” 你把这当作一个理想,并试图用这个念头来充满你的心。接下来会发生的是,那个念头变成了一个对象。因此,我们不是仅仅安住于“是那个知”,而是试图去看“那个正在知的”是什么。正如阿姜查有时会说的——你正骑着一匹马,却在寻找那匹马。我们想知道:“那个了知‘知者’的是谁?”“那个了知‘正在了知那个知’的东西又是谁?”
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里发生着某种无限的回归,就像向后跌下悬崖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我们放下我们的认同感时,剩下的就只是纯粹的了知。心安住于那个明亮、无我、了知、超越时间的状态。然后,念头升起了:“哦,有了知。” 于是,我们不再仅仅安住于那纯粹的了知,而是执着于“有某个东西正在了知”这个念头。我们只是固着于那个念头,然后就踏入了有为世界。当我们执着于任何念头时,我们就在远离那种纯粹了知的感觉。如果只有纯粹的了知,那就像背靠着墙。一旦我们抓住任何念头,我们就从墙边走开了。我们正在走向体验,走向对某种条件的执着。
如果我们只是让心放松,安住于那种了知的感觉中,安住于那种存在的纯粹性中,那么就在那一刻,便有解脱,便有自由。在那一刻,心觉知到合一感、真如感,有一种统一的视野,在基督教的术语中,他们称之为“至福”(beatitude)。至福的景象是看见整体、看见圆满,任何分离感的消失。在这种证悟中,没有“我”——不是“你”与究竟真理同在——只有“这个”(THIS),心处于其纯粹的觉醒状态,法(Dhamma)觉知到其自身的本性。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佛教在美国早期传播时,人们大量地运用了这种理解;人们说:“人人是佛”,“我们都是佛”,“每个人都是完美的”。然而,这并没有使人们展现出佛陀的行为——谦逊、温和、克制——反而有时被当作放纵的借口。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完美的——清醒是完美的,喝醉也是完美的,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任何你受到启发去做的事——一切皆空,一切皆是真如。
对于那些将最高原则当作一个固定立场或身份来执着的人……你可以看到,仅仅拥有这个想法是不够的,它导致了一些“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中最杰出的佛教之光最终以酒鬼的身份死去。当时确实有一种伟大的精神自由在激励着他们,但“我们都是佛”和“一切都是完美的”这个想法,与对此的直接证悟并不完全相同。当心真正安住于那种证悟时,从中流淌出来的,是一种行为的纯净、言语和行动的纯净,一种温和、一种无害和一种简约。
佛陀对他证悟的反应——完全自由,超越任何痛苦——并不是去追求肉体的享乐或寻求麻醉。他的反应是生活得极其谨慎和谦逊,节俭地使用大地上的物品。他本可以变出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但他选择作为一名赤脚的弃世者,一个和平、无害的存在而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世纪以来,一些佛教传统陷入了这个问题,即执着于某个原则,然后将其当作一种身份——“我是一个大乘佛教徒”,或“我是一个南传佛教徒”,或“我是一个金刚乘佛教徒”。这就像戴上一个徽章,赋予自己某种资历,而不是看到这些术语所指的是存在的不同态度。例如,在英国,每年佛教协会的夏令营上,有一个小组会去酒吧开他们的晚间会议,表面上的理由是他们“已经超越了形式”。所以,他们会在酒吧里进行晚间的佛法讨论,这本身没问题;他们有权做他们想做的事。而南传佛教徒们只是坐在一起,聊天喝茶。但你可以看到那种态度是:“嗯,我们属于至上乘。我们不需要为戒律(sīla)这种琐碎的事情烦恼;我们尊重所有众生究竟的佛性。” 你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灵感和高尚的能量,都被转移到为一种简单的偏好辩护上去了:他们觉得喝一两杯酒,胡闹一下,过一段无拘无束的时光很享受。再说一遍,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行为,但将此贴上修习佛法的标签,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
这样做的结果——试图在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中证悟空性——意味着我们接下来将面临挑战,去证悟因追随那些欲望而来的绝望和沮丧的空性。人们当然有自由去接受这个挑战!但这是相关联的;我们不可能只沉浸在快乐中,而不得到它的另一面。这就像我们抓着轮子,当它在快乐的一侧上升时,我们紧抓不放,但当它转到另一侧下降时,我们仍然抓着它。我不是在贬低这些事情,但是,我自己也做过不少这类事,我意识到我们就是没有足够的觉知力在顶点放手!我们希望事情是那样的,但它并不会那样运作。
究竟智慧与世俗善巧的圆融
在禅修营开始时,每个人都受了三皈五戒。这个象征性的行为是为了刷新我们成为佛教徒、成为佛陀的愿心。它不像洗礼那样,是一个你经历过之后……就成为佛教徒的仪式。它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来刷新我们内在的愿心。在外部,我们可以遵循一种形式、一个传统、一种模式,但如果我们最终没有将其内化,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带入我们内心,并将“成为佛陀”、“成为那个了知者”作为目标,那么从长远来看,任何数量的对特定形式或传统的外部奉献,对我们的帮助都不会太大。
我们往往不理解的最后一点是——如果没有“我”,如果一个人旨在从这个究竟智慧的立场出发,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去做像散播慈心(metta)这样的事情呢?如果这里没有人,那里也没有人,那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把慈心传遍宇宙呢?或者功德回向:你知道这里没有人,那里也没有人,那意义何在?我们是不是省点力气去做点别的事会更好?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生命中不同层次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因为,即使在某个时刻,我们可能正从纯粹智慧的层面看待生命,从那个超越时间、空间、自我的觉知之地看待,但世界的其他部分并不必然是从那个视角看待事物。在佛教修行中,你所拥有的是一种将我们存在的所有不同层面联系在一起的方法。
佛陀使用了世俗的表达方式,他使用了人称代词。当人们问他诸如“如果没有‘我’,你为什么称自己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为什么跟别人说话,为什么称呼别人的名字?”这样的问题时,佛陀说:“尽管从根本上来说没有‘我’,但我使用通俗的语言,是为了能在人们能够理解的层面上与他们交流。”
所以,当我们思考像散播慈心、创造善业、分享我们生命中的福报这类事情时,一个人要付出努力去做。你全心全意地去散播慈爱。你去做这件事。
我们建立寺院,我们努力为人们创造学习的环境和机会。我们教导、提供指导、支持和教诲。但是,在将这些形式带入存在之后,一个人就要消解对它们的任何执着。我们将有益的原则和能量带入人们的生活中,但我们不赋予它们一种究竟的实体性。我们视它们仅仅是形状、形式、意识的模式。
我说的这些声音,它们是耳识,是你们所有人都能觉知到的声音。有一种说法是,佛陀是至高无上的织梦者,其目的是为了唤醒梦中人。他的教导、他的言语和行为,是一个梦的系统,是梦的素材。但佛陀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创造的梦能让做梦的人觉醒;引领我们走出梦的世界,进入真实的生活,进入真正的世界。
举个例子,很多年来,我对虔诚的修行实践毫无感觉。“无我,那才是核心!”每天早晚,当我们做传统的唱诵时,我也会跟着做,尽量保持音调一致等等,但基本上我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错过了整件事的精神实质——如果我们有正见,那么我们可以将那些能量注入言语,将仁慈和善意带出来,将有用和有帮助的事物带入这个世界——但随后不去占有它们,让它们如其所是,这才是伟大的艺术,也是最大的福报。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佛陀要以他那样的方式教导。那不是为了他自己。那是为了给我们这些后来者提供一些东西:形式、模式、传统、生活方式,以激励我们前进;用各种方式鼓励我们、启发我们去觉醒,去突破束缚我们的幻相,从而使所有众生都能体验到解脱的真正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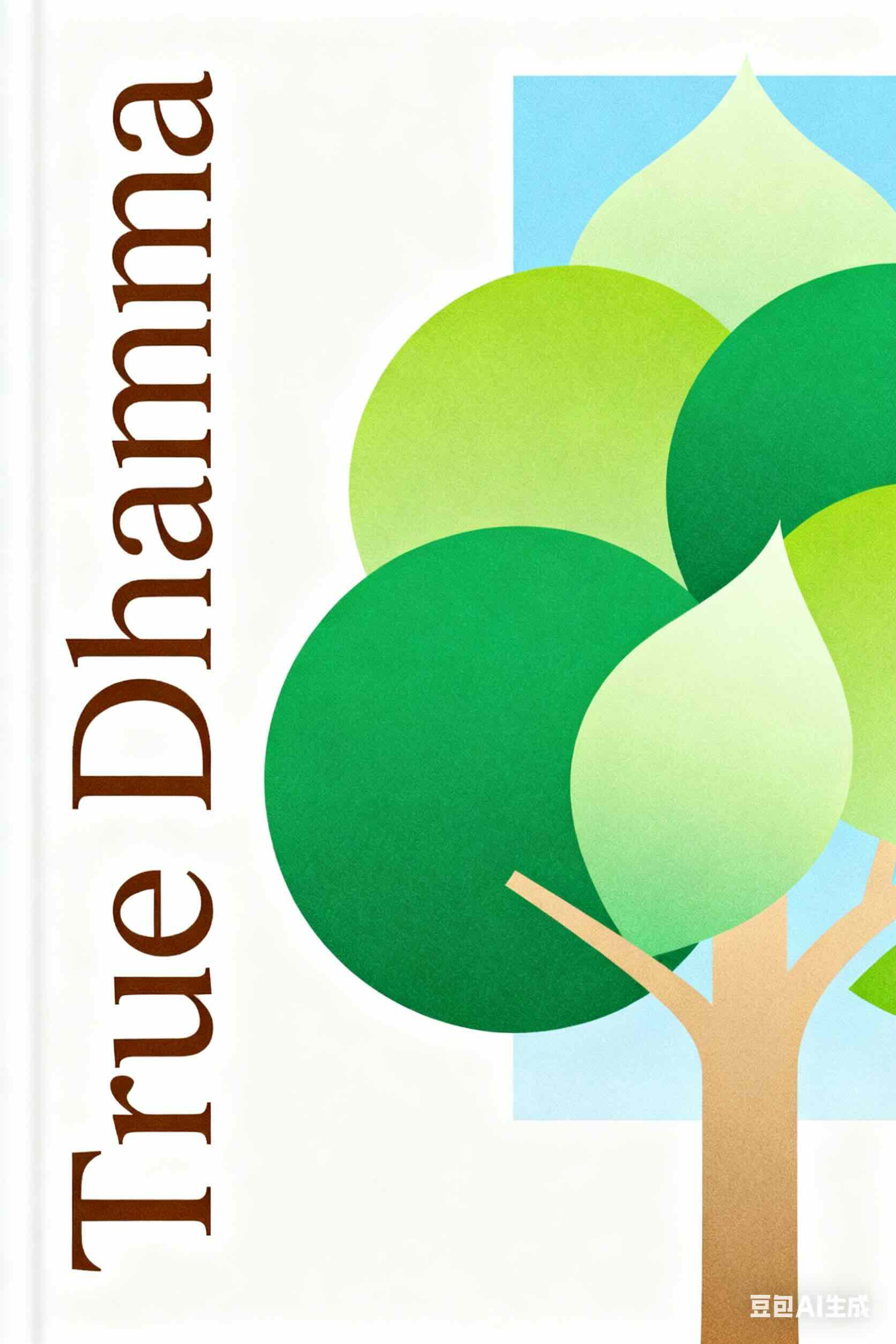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下载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