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佛教禅修中的慈悲与空性
慈悲喜舍, 西方世界的佛法 ·Index
Compassion and Emptiness in Early Buddhist Meditation - Anālayo
早期佛教禅修中的慈悲与空性 - 无着比丘(Anālayo)
早期佛法中,慈悲与空性是解脱道上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慈悲滋养智慧,空性净化慈悲。
第一章 修习慈悲
本章探讨了慈悲的修习,从慈悲的积极表现形式,逐步深入到其禅修实践。
I.1 慈悲的本质
早期经典并未对“慈悲”一词给出简明定义,其含义常需通过譬喻来解读。一个重要的譬喻来自《增支部》及其《中阿含》对应经文,描述了一个能激发悲心的情景,用以说明应如何对待沉溺于不善法之人。
譬喻中,一人在漫长的旅途中病倒,孤立无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另一人路过看到此景,心中生起这样的念头:“如果此人能得到照顾,获得良药美食,妥善护理,他的病一定会痊愈。” 生起这种希望他人离苦得乐的善念,即是慈悲。
这个譬喻的关键在于,慈悲并非仅仅是看到他人的痛苦,而是真切地希望他们从痛苦中解脱。禅修者应将心安住于“他人脱离痛苦”的愿景上,而非沉浸于他人的苦难本身。后者属于对“苦”(dukkha)的思惟,虽是修习慈悲的基础,但慈悲本身的培育,则是以“希望他人离苦”作为所缘。这样的所缘能生起积极甚至是喜悦的心境,从而导向更深的禅定。
因此,修习慈悲要避免陷入悲伤。这要求修行者在敞开心扉、真诚感受他人痛苦之后,将心转向一种积极的状态——即充满希望他人离苦的善愿。慈悲不是陪着他人一起受苦,后者被后期论典称为慈悲的“近敌”(世俗的悲伤),而残忍则是其“远敌”。
早期经典明确指出,慈悲与害心(残忍)是直接对立的。如《中部·教诫罗睺罗大经》及其《增一阿含》对应经文所示,真正培育了慈悲的人,其内心不可能再被残忍所占据。修习慈悲能深刻地改变人的品行,具有重要的戒行意义,为解脱之路奠定坚实基础。
I.2 慈悲与戒行
戒行本身就是慈悲的一种表达。如《中阿含》的《意行经》所说,杀生者即是缺乏慈悲之人。反之,不杀生即是慈悲之行。同样,不偷盗、不邪淫等戒行,都是希望他人免于伤害的表现,本质上都是慈悲。
在言语方面,《无畏王子经》阐述了佛陀说话的准则:真实、有益、是否悦耳。佛陀绝不说不真实、无益的话。对于真实且有益的话,即便不悦耳,佛陀也会出于慈悲而说。这意味着,慈悲的言语并非一味迎合,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利益,有勇气说出逆耳的忠言,帮助他人从造成痛苦的因缘中解脱。
I.3 慈悲与四圣谛
早期经典中,佛陀与阿罗汉弟子们的慈悲行为主要表现为教导佛法,而非从事慈善活动。佛陀的慈悲体现于他发现了离苦之道后,首先想到的是与他过去的老师和同修分享。他向五比丘初转法轮,宣说四圣谛,这一行为本身即是慈悲的极致体现。
佛陀的教法常被譬喻为医疗诊断,四圣谛的架构如下:
- 病症:苦(dukkha)
- 病因:爱(渴爱)
- 痊愈:涅槃(Nirvāṇa)
- 疗法:八正道
这种医疗模式凸显了佛陀作为“无上医王”的角色,以慈悲心开出离苦的药方。四圣谛是所有善法的核心,如同大象的脚印能容纳所有动物的脚印一样。
《中阿含》的一部经文将智慧分为“彻见慧”与“广大慧”。彻见慧源于洞察四圣谛,而广大慧则表现为出于慈悲而利益自他的意愿。这表明,慈悲与四圣谛是智慧的两个互补面向。真正的慈悲,应以四圣谛的框架为指导:不仅看到他人的痛苦(苦谛),也了知其成因(集谛),并知晓离苦的可能(灭谛)与实现路径(道谛)。
I.4 慈悲与教导
佛陀以慈悲心教导四圣谛,树立了典范。因此,在早期经典中,“出于慈悲”常作为请求教导的固定用语。佛陀本人也常在教导后强调,他已出于慈悲之心,尽到了为师之责。
教导佛法应出于纯粹的悲心,而非为了个人名利。佛陀的弟子们,如舍利弗,也被期望以慈悲心教导他人。当舍利弗和阿难在某些情境下未能展现出足够的责任感和慈悲心时,甚至会受到佛陀严厉的公开批评。这突显了在早期僧团中,对他人的责任感和慈悲的实践被置于极高的位置。
对于出家修行的行为,佛陀开示道,出家修行看似只利益自己,但当修行者证得解脱后,便能教导无数众生走向解脱,从而利益更多人。因此,修行与慈悲并非对立。
I.5 慈悲与独处
佛陀常在僻静处独住,他解释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为哀愍后人”,为后世的修行者树立榜样。这种通过自身行为来教导的方式,也是慈悲的一种体现。摩诃迦叶尊者的苦行同样被视为出于对后人的慈悲。
因此,退隐独处专修与慈悲利他并不矛盾。只要动机中包含了利益他人的愿望,专心修行便是在为慈悲行动打下坚实基础。如《中部·削减经》中的譬喻所言,一个自己尚未调伏的人,无法调伏他人;一个自己正在溺水的人,无法拯救他人。必须先稳固自身的修行,才能有效地帮助他人。
早期佛教的慈悲,要求在关心他人与净化自我之间保持精妙的平衡,如同两位杂技演员,必须先站稳自己,才能互相扶持。
I.6 禅修中的慈悲
对慈悲的禅修,即培育“慈悲心解脱”,能深刻地转化一个人的身、语、意行为。一个从小就能安住于慈悲心解脱的孩子,长大后不会造作不善业。这里的“心解脱”指的是暂时的体验,虽非究竟解脱,但对修行道途有巨大助益。
《中阿含》的《意行经》描述了慈悲禅修的实践过程: 1. 以戒行为基础:修行者舍离身、语、意的不善行,培育善行。 2. 净除五盖:清净的戒行有助于克服禅修的障碍(五盖),如掉举、昏沉等。 3. 遍满禅:在正念正知的基础上,修行者让充满慈悲的心遍满一个方向,然后是第二、三、四个方向,乃至上下、四维,遍满整个世界。此时的心是广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
这种遍满的修法,使得原本狭隘的心变得无限宽广。这种体验被称为“梵住”(brahmavihāra),意指安住于如梵天般广阔无垠的心境中。一个譬喻将其比作法螺号手,其声音能无分别地传遍四方。
I.7 禅修慈悲的所缘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经典中对慈悲遍满禅的标准描述,并未提及任何具体的个人作为所缘。修行并非针对朋友、中立者或敌人,而是一种无差别的、遍满一切方向的心的放射。
后期的论典,如《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发展出了以特定人物(如亲、怨、中)为所缘的修法。这种方法可作为初学者的善巧方便,或在内心烦恼较重时使用。但最终的修习,应朝向早期经典所描述的无特定对象、无限遍满的放射。
I.8 总结
早期佛教思想中的慈悲,其主要实践表现为教导佛法,帮助他人离苦。这种慈悲行也包括通过自身的戒行与禅修生活为他人树立榜样。面对苦难,慈悲的回应是希望他人离苦,并最好以四圣谛的智慧为指导。作为禅修,慈悲是一种无限的、不依赖特定对象的心的放射,最终导向一种暂时的心解脱体验。
第二章 语境中的慈悲
本章将慈悲置于四梵住(brahmavihāras)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考察。慈悲(karuṇā)在四梵住中位列第二,其前后分别是慈(mettā)、喜(muditā)和舍(upekkhā)。理解慈悲与其他三者的关系,对全面修习至关重要。
II.1 慈(Mettā)
四梵住之首是“慈”(mettā),常译为“慈爱”或“仁爱”。其词根意为“朋友”,传达出一种友善、互助的态度。
早期经典中的“慈”,并非指母亲对孩子那样的挚爱或情感依恋。如《慈经》中的著名偈颂:“如母以生命,护自己独子,亦应于一切,修习无量心。” 此处的重点是母亲愿意付出生命来“保护”孩子,强调的是“护卫”而非“爱恋”。“慈”的修习应是无量的、不带执着的,如同它能护佑修行者免受蛇咬或非人侵扰一样。
“慈”是其余三梵住的基础。《大乘庄严经论》中有一个譬喻,将慈悲比作一棵大树,而“慈”则是滋养这棵树根部的水。
“慈”可以通过身、语、意三方面来表达,这种全面的实践是检验禅修成果的试金石。一个真正修习了“慈”的人,即使面对困境和恶人,也能保持友善之心。通过在日常行为、言语和心态中贯彻“慈”,便为慈悲、喜、舍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II.2 日常行持中的慈心
《中部·小牛角经》及其对应经典生动地描述了三位比丘如何和谐共住,展现了日常生活中“慈”的实践。他们轮流打扫、准备饮水和坐具,照顾彼此的需要,而这一切都默默进行,无需言语。他们每五天集会一次,或讨论佛法,或保持圣默然。
这种和谐共住的心态基础是:
- 相互感恩:他们视彼此为修行的助缘,心怀感激。
- 三业慈心:无论他人是否看见,都以身、语、意展现慈心。
- 舍弃自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随顺他人。
这种实践表明,真正的安乐来自于舍弃“凡事都要按我的方式来”的执着。
II.3 面对敌意
“慈”的力量在面对他人的敌意时尤为重要。《中部·锯喻经》及其《中阿含》对应经典中,佛陀教导,即使被他人拳打脚踢,刀剑相向,乃至被盗匪用锯子一节节肢解,也应保持内心不为所动,不发恶言,反而对施害者生起慈悲之心。
这个极端的譬喻旨在说明“慈”的潜能和范畴,鼓励我们在远没有那么严酷的日常冲突中,保持忍耐和宽容。
II.4 心的庄严
“慈”是嗔怒和敌意的直接对治法。如《长阿含·十上经》所述,真正修成“慈心解脱”者,内心不会再生起嗔恚。嗔怒使人面目丑陋,而修习“慈”则能带来内心的庄严,这种美能超越任何外貌。如《相应部》所说,“善修慈心,为最上美”。
II.5 慈悲与喜(Muditā)
喜(muditā),即随喜,是看到他人快乐、成功时由衷生起的喜悦。它与慈悲互为补充。慈悲关注受苦者,而随喜则关注幸福者。
在僧团中,和谐共住、互相欣赏本身就是一种随喜的实践。当大家和合无诤,如水乳交融,便是安住于“喜心解脱”中。这种喜悦能带来身心轻安,有助于禅定的深入。
随喜也是嫉妒的对治法。佛陀在度化了耆那教的重要居士优婆离后,反而劝他继续供养原来的师长。佛陀这种不嫉妒他人利养的胸怀,正是随喜的体现。此外,随喜还能对治“不乐”(arati),即对修行生活或独处感到的不满和厌烦。
II.6 慈悲与舍(Upekkhā)
舍(upekkhā),即舍心或平等心,意为“旁观”,指在觉知一切发生的同时,保持内心的平衡,无有偏袒或对立。
慈悲与舍的关系看似矛盾,尤其对于发愿度众生的菩萨道行者而言。然而,“舍”并非冷漠,而是慈悲成熟后的圆满状态。当慈悲的努力遭遇冷遇或无效时,适时地转向舍心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放弃控制局势的企图,允许他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佛陀本人也曾示现过这种转变。当他调解争吵的比丘们无效时,便默默离开,安住于舍。这种能够适时转为舍的慈悲,才是不执着于结果的、解脱的慈悲。
“舍”也是对治贪欲和嗔恚的有力工具。面对辱骂,佛陀曾以一个譬喻教导舍心:若客人不接受主人的食物,食物仍归主人所有。同样,若我们不“接受”他人的辱骂,那辱骂就仍属于对方,无法扰乱我们的内心。如偈颂所言:“犹如坚固岩,不为风所动,智者于毁誉,内心不为动。”
II.7 慈悲与其他梵住的关系
慈悲主要关注处境不如自己的人,若不加以平衡,可能无意中滋生优越感或我慢。因此,必须将慈悲置于四梵住的整体框架中修习。
- 慈(Mettā)作为基础,教导我们平等地对待一切众生,如同朋友。
- 悲(Karuṇā)关注受苦者,是向下的关怀。
- 喜(Muditā)关注幸福者,是向上的随喜,平衡了悲心可能带来的局限。
- 舍(Upekkhā)作为顶峰,使前三者得以圆满,让慈悲喜乐之心在任何境况下都能保持平衡与智慧,不被外境所转。
四梵住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心态工具,使修行者能在任何情境下都作出最恰当、最有智慧的回应。
II.8 总结
早期佛教将慈悲置于四梵住的脉络中。以“慈”为基础,通过身语意在日常中实践友善;以“悲”和“喜”为互补,平等地关怀受苦者与幸福者;最后以“舍”来圆满,使慈悲之心在一切境况下都能保持智慧与平衡。如此,才能避免慈悲修习中可能出现的偏失。
第三章 成熟慈悲
本章探讨修习慈悲及其他梵住所能带来的各种利益,从世间的福德到最终的解脱智慧。
III.1 慈心的利益
修习慈心(mettā)的利益在诸多经典中都有强调。一部《相应部》经文指出,哪怕片刻修习慈心,其功德也远胜于每日三次向数百人布施。这表明,在早期佛教中,心的培育被视为积累福德的更高效方式。另一部《如是语》经文中的譬喻更将其功德比作满月之光,远超繁星之辉,说明慈心解脱的功德在所有善行中最为殊胜。
此外,修习慈心还能带来十一种具体利益,如: 1. 安稳入睡 2. 安稳醒来 3. 不见恶梦 4. 为天人所护 5. 为人所爱 6. 为非人所敬 7. 不受毒、兵、水火之害 8. 内心快速得定 9. 面色祥和 10. 临终不昏乱 11. 命终后得生梵天
更重要的是,经文最后指出,修习慈心能“速得一切善法,以智慧趣向诸漏尽”。这表明,慈心不仅带来世间利益,更是通向究竟解脱的重要助缘,但要达到最终目标,还需与智慧相结合。
III.2 放射慈悲与禅定
四梵住的无限放射修法,指向一种高度专注的心境,但这是否必然等同于证入禅那(absorption)?《中部·檀尼迦经》提供了一个反例。婆罗门檀尼迦在临终前病重,痛苦不堪。舍利弗前去探望,教导他修习四梵住的无限放射法。檀尼迦依此修习,命终后得以生往梵天。
考虑到檀尼迦病重的身体状况,以及他此前并非禅修精进者,甚至有不善业,他在临终前是不可能学会并证入禅那的。这表明,四梵住的放射体验并不局限于禅那的深度,在较低的定力层次(如近行定)上也可以成功修习。当然,若能证入禅那,其力量会更强大稳定。
心的“广大”(mahāggata)与“无量”(appamāṇa)是四梵住的特征,但这两种品质也出现在非禅那的语境中,如舍利弗在面对诬告时,或佛陀赞叹阿难对他无量的慈心侍奉时,都非指处于禅那状态。因此,四梵住的放射修法,其核心是心的无限扩展体验,而非必须达到特定的禅那阶位。
III.3 作为心解脱的慈悲
在描述修行道次第的经典中,四梵住有时与四禅并列出现,这暗示了它们具有独特的价值。与依赖其他所缘(如地遍)的禅修相比,四梵住有一个显著优势:由于其无限放射的本质,修行者在尚未证入禅那时,就可能体验到一种暂时的“心解脱”。
这对于实际禅修意义重大。它避免了修行者因执着于“必须证入禅那”而产生的过度努力和紧张,这种紧张反而会成为入定的障碍。四梵住的修习本身就是一种柔和、宽容的态度,即使面对外界干扰(如声音),也可以将其纳入修习的所缘——对制造干扰者生起慈悲心。这样,问题本身就变成了修行的一部分,修行得以不间断地进行。
III.4 慈悲与业
修习四梵住对过去所造之业的果报有着深远影响。《中阿含·意行经》指出,当修行者的心通过修习四梵住而变得无限广大后,“若因恶友,昔所放逸,造不善业,彼不能将,亦不染污,不复还会”。这意味着,过去所造的有限的业,其影响力会被这颗无限广大的慈悲心所稀释和转化。
这与佛陀教导的业力动态观相符。如“盐块喻”所示,同一块盐投入小杯水中,水会变得极咸;投入恒河中,则几乎不起作用。同样,过去恶业的果报,取决于当前心的状态。一颗充满慈悲的、无限广大的心,如同恒河之水,能极大地削弱恶业的冲击。杀人如麻的鸯掘摩罗在证得阿罗汉后,虽然仍会遭受过去业力的余报(被人投石攻击),但相比他所造的重业,这已是微不足道。
在禅修中,当不善念头生起时,只需回到心的无限状态,这些狭隘的念头便会像投入大海的盐块一样,自然消融。
III.5 慈悲与观智
《意行经》及其对应经典明确指出,有智慧地善修四梵住,若未证得究竟解脱,则能证得不还果(三果阿那含)。这揭示了慈悲修习与解脱智慧的直接关联。
早期佛教强调“止观双运”。“止”(奢摩他)能调伏内心,尤其是贪欲;“观”(毗婆舍那)能开发智慧,根除无明。四梵住的修习,不仅能培育定力(止),其本身也具有深刻的转化作用。它直接对治了修行道上的两大主要烦恼:嗔恚与贪欲。
- 慈悲直接对治嗔恚、害心。
- 修习中生起的禅悦,能使人对感官欲乐的依赖减弱,从而对治贪欲。
从初果到三果的修行,核心就是断除欲界贪和嗔。因此,四梵住的修习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可以说,四梵住的修习,如同饮用既解渴又有疗效的茶,不仅带来安乐,也直接疗愈了内心的烦恼。
当慈悲的修习与观照结合,例如观照慈悲心解脱的体验本身也是因缘和合、无常的,就能成为通往最终解脱的有力工具。
III.6 慈悲与七觉支
一部《相应部》经文展示了如何将慈心(及其他梵住)的修习与七觉支的培育相结合。在慈心的状态中,修行者可以依次培育:
- 念觉支(以慈心为所缘保持正念)
- 择法觉支(探究慈心的善法特质)
- 精进觉支(持续不断地保持慈心)
- 喜觉支(由慈心带来的喜悦)
- 轻安觉支(身心因此而放松)
- 定觉支(心安住于慈心)
- 舍觉支(对慈心的体验保持平衡)
将此修习导向“远离、离欲、灭、放舍”,便能将慈悲的禅修直接转化为解脱的智慧。
III.7 慈悲与空无边处
经典指出,慈、悲、喜、舍四梵住的修习,其在定学层面的顶点分别对应着心的庄严、空无边处、识无边处和无所有处这几个境界。
悲心的顶点是“空无边处”。后世论典解释,这是因为悲心希望众生脱离色身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如被殴打),而“空无边处”的体验超越了所有物质形态(色法)的障碍和对立。这种超越物质之苦的体验,与悲心的愿望高度契合。
将悲心与空无边处相联系,为从慈悲禅修过渡到空性禅修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下一章将探讨的《小空经》中,空无边处正是进入空性禅修的一个重要阶梯。
VIII.8 总结
成熟的慈悲修习能带来诸多利益,从世间的安乐、和谐,到修行道上的坚实进展。它不仅是培育定力的有效方法,更能直接转化导致痛苦的烦恼。通过将慈悲修习与七觉支和观智结合,它便成为一条通往不还果乃至究竟解脱的有力道路。慈悲修习在定学上的顶点——空无边处,也为进一步深入空性的禅修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 空的色法
本章从慈悲转向空性,探讨早期经典中“空”的含义,并依据《小空经》及其对应经典,阐释了进入空性禅修的初阶部分,即关于物质(色法)的空性。
IV.1 空的本质
早期经典中多用形容词“空的”(empty),而非名词“空性”(emptiness),这有助于避免将空性实体化。
“空”的一个直接含义是“空旷处”,指没有人群干扰,适合禅修的地方。另一譬喻将六内根(眼、耳、鼻、舌、身、意)比作“空村”,意指六根本身是空的、不坚实的,无法提供真正的、持久的满足,试图通过六根来平息欲望,就如同在空无一人的村庄里寻求庇护以躲避敌人一样,终将徒劳无功。
更进一步的解释是,整个“世间”是空的,因为六根、六尘乃至六识,都“空无我,亦无我所”。这意味着,早期佛教的空性教法,其适用范围是全面的,一切法(所有现象),无一例外,其本质都是无我。如偈颂所言:“诸法无我”。
《相应部》中的一系列譬喻,从五蕴的角度生动地阐释了这种空性:
- 色蕴(物质身体)如聚沫:看似坚实,实则脆弱、无有实质。
- 受蕴(感受)如水泡:瞬间生灭,短暂易逝。
- 想蕴(识别、概念)如阳焰(海市蜃楼):看似真实,实为心智的投射和幻象。
- 行蕴(意志、造作)如芭蕉树干:层层剥开,终无实心。
- 识蕴(了知作用)如幻术:变幻不定,虚幻不实。
这组譬喻是观修空性的有力工具。当执着生起时,可以观察自己执着于五蕴中的哪一蕴,然后用对应的譬喻来思惟其空性,从而消解执着。
IV.2 渐次入空
《中部·小空经》及其《中阿含》和藏译的对应经典,详细描绘了一条从粗到细、渐次进入空性的禅修路径。这条路径通过一系列感知的转变,最终导向对究竟空性的亲证。
禅修的起点是“当下”——佛陀与阿难所在的林中精舍。这暗示着空性的修习可以在任何环境中展开。
- 第一步:觉知当下的环境。精舍“空”于村庄的喧嚣、牛马等,但“不空”于比丘僧团的存在。这是空性禅修的基本原则:觉知什么是空的,同时觉知什么是不空的(即当下存在之物)。
- 第二步:从“人的感知”转向“林的感知”。修行者不再关注人的形象,而将心安住于对“林”的单一感知上。这是一种从多变、分散的所缘,转向更稳定、更统一的所缘的训练。在象征意义上,“林”代表了远离世俗的“独处”,这是深入禅修的基础。
如偈颂所教导的,应安住于当下,观照诸法的不稳定性,不追忆过去,不期盼未来。
IV.3 大地
- 第三步:从“林的感知”转向“地的感知”。修行者不再关注林中的树木、山丘、河流等千差万别的景象,而是将心安住于对“大地”的单一感知上,如同看待一张被拉平、毫无褶皱的牛皮,或平坦的手掌。
这里的“大地”并非指具体的泥土,而是代表物质世界的基本属性——坚实性(地大)。这标志着禅修进入了更高层次的抽象。通过将所有物质现象归结为“坚实”这一基本特质,为下一步超越物质奠定了基础。在洞见层面,观照身体仅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构成,能破除对身体的执着,了知其“非我,非我所”。
IV.4 空无边处
- 第四步:从“地的感知”转向“空无边处的感知”。修行者放下对“坚实性”的专注,转而关注被这坚实性所占据的“空间”。当物质的感知消融后,心便安住于无限、无边、无障碍的“空”的体验中。
这一步对应于无色界定的“空无边处”。它并非否定物质的存在,而是通过禅修训练,揭示物质的空性本质。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看,物质原子绝大部分是空的,所谓的“坚实”是由能量场相互作用产生的现象。这种禅修能深刻地瓦解对物质现象(如美丑、贵贱)的执着。正如画家无法在虚空中作画,当了知万物本质为空时,贪爱与嗔恚便失去了附着的根基。
IV.5 空无边处与慈悲
如前所述,悲心的顶点是“空无边处”。这种关联在于,悲心希望众生脱离色身之苦,而空无边处的体验正是对造成这类痛苦的物质世界的超越。
后期的一些论典认为慈悲与空性存在张力:既然众生本空,慈悲的对象何在?然而,从早期经典的视角看,这个问题并不成立。
* 首先,慈悲禅修是无限的放射,不依赖于对“个体众生”的执取。
* 其次,空性或无我,并非指众生不存在,而是指众生没有一个永恒、独立的“我”。众生作为因缘和合、无常变化的现象是存在的。因此,对这些无常、苦、无我的众生生起悲心,与空性智慧不仅不矛盾,反而是智慧的自然流露。
IV.6 总结
早期经典中的空性,核心是“空无我,无我所”。《小空经》提供了一条实修路径,从观照当下环境开始,通过将感知从多样转向统一(林),再到抽象(地/坚实性),最终通过“空无边处”的体验来解构对物质世界的执着。慈悲与空性在此交汇:对众生之苦的悲悯,最终导向了对一切现象(包括痛苦本身)空性的彻见。
第五章 空的心
本章继续探讨《小空经》所描述的渐次入空法,重点是从“空无边处”进入“识无边处”的阶段,并深入研究早期佛教中关于“识”的本质及其在缘起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将空性智慧融入日常生活。
V.1 识无边处
- 第五步:从“空无边处的感知”转向“识无边处的感知”。在经历了无限空间的体验后,修行者将注意力从所觉知的“空间”转向能觉知的“心”本身。此时,先前作为客体的无限空间之体验,被能体验这一切的“识”所取代。
整个世界,在此刻,似乎都收摄于自心之内。这并非主张“唯心主义”或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而是在禅修体验的层面,深刻地认识到“我”的世界完全是依赖于“识”而建立的。没有“识”,就没有“我”的经验世界。这一步揭示了心在构建个人经验世界中的根本作用。
V.2 识的本质
在五蕴的分析中,“识”仅指了知作用,区别于受、想、行等其他心理功能。但在某些语境下,“识”也泛指整个心。修习“识无边处”时,受、想、行等心理功能退居幕后,唯有能知的“识”凸显出来,成为体验的全部。
由于“识”的了知作用似乎恒常存在,很容易被误解为一个永恒的实体或灵魂。佛陀曾严厉斥责一位持有“是此识往后世,非有他也”观点的比丘,称他为“痴人”。佛陀教导,“识”如同在林间穿梭的猿猴,不断抓取新的树枝(所缘),其本质是刹那生灭、依缘而起的。它并非一个不变的实体在流转,而是一股相续不断的、条件性的“了知之流”。
V.3 缘起
《小空经》的禅修过程,每一步都伴随着对“疲劳”(weariness)的观照——即了知旧的感知(如地的感知)是一种应被舍弃的“疲劳”,而新的感知(如空无边处的感知)虽更微细,却仍是因缘造作,本质上也是一种“疲劳”。这种观照,是在实践中体会缘起和苦的本质,为最终超越一切经验奠定基础。
《大缘经》及其对应经典深入阐述了“识”的缘起性。其中一个核心观点是:“识”与“名色”(名指受、想、行等心理功能,色指物质身体)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 “缘识有名色”:识是生命(名色)在母胎中形成和成长的必要条件。
- “缘名色有识”:识的生起也必须依赖于名色作为其所缘和载体。
这二者如同两捆相互倚靠的芦苇,抽掉任何一捆,另一捆也会倒下。它们之间没有谁是第一因,共同构成了经验世界的生起基质。了知这一点,就能从根本上瓦解执着。
V.4 巴希亚的教导
佛陀给予苦行者巴希亚的著名教导,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缘起和空性提供了精炼的指导。当巴希亚在路上恳请佛陀说法时,佛陀教导他:
“于见唯见,于闻唯闻,于觉唯觉,于知唯知。”
这意味着,在感官接触外境的当下,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感知层面,不添加任何概念、评判、贪爱或嗔恨的“第二支箭”。当修行者能做到这一点时,他就“不在此,不在此岸,不往彼岸,亦非中间住”,即不执着于根、尘、识任何一方,也不执着于过去、现在、未来。
这个教导的核心是,在“识”与“名色”接触的瞬间,切断通往烦恼的缘起链条。通过安住于能知的“识”,而不让“名色”发展成贪嗔的反应,心便能从束缚中解脱。
V.5 日常生活中的空性
《大空经》及其对应经典,补充了如何将空性禅修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教导。
- 行禅与坐禅:无论行走还是静坐,核心都是保持内心不生起贪、忧等不善法。这种对烦恼的“空”,是修行连续性的关键。
- 乞食与工作:在与外界接触时,应时刻反观自心:“我于眼所识色,为生欲、为生爱、为生念、为生染着不?” 若烦恼生起,应如头巾着火般,迅速精进地将其熄灭。若烦恼未生,则应为此善法基础而感到欢喜,并持续努力。
- 思惟与言谈:修行者应舍离欲、嗔、害等不善思惟,培育出离、无嗔、无害的善思惟。言谈应避免世俗闲聊,而应围绕戒、定、慧、解脱等有益于修行的话题。
- 面对五欲:经典明确指出,沉溺五欲与修习空性是不相容的。当心被五欲所吸引时,应观照五欲的无常、变坏、离散、灭尽之相,从而舍离贪染。
- 观五蕴:修行者应观照色、受、想、行、识五蕴的生灭,了知“此是色,此是色集,此是色灭……”。通过如此观照,对于五蕴的“我慢”便会息灭。
《大空经》的教导表明,空性修习并非仅限于禅堂,而是要将“空于烦恼”的品质,贯彻到行、住、坐、卧、言、默、动、静的一切活动中,最终实现对所有“我”和“我所”执着的彻底放下。
VI.6 总结
从“空无边处”到“识无边处”的禅修,是将注意力从外在客体转向内在能知的心,从而深刻体悟经验世界由心所造的本质。了知“识”本身也是无常、缘起的,并通过“于见唯见”的修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切断烦恼的缘起链。最终,空性修习的目标是将心彻底地“空”于一切烦恼、执着和我慢,实现究竟的解脱。
第六章 无我之空
本章继续探讨《小空经》中渐次入空的后续步骤,并深入分析整个禅修过程的内在动力。
VI.1 无所有处
- 第六步:从“识无边处的感知”转向“无所有处的感知”。在前一步中,心以“无限的识”为所缘。现在,修行者观照这个“无限的识”本身也是虚幻不实的,从而放下对它的执着。当连能知的主体也被舍弃后,心便安住于“无所有”的感知中。
“无所有”意指“无一物”,连“识”这个所缘也已不存在。这一步将禅修的抽象程度推向了新的高度。虽然证入“无所有处定”本身不等于解脱(如佛陀的老师阿罗罗·迦罗摩虽达此境,仍未解脱),但在渐次入空的框架下,这一步的修习直指无我的甚深智慧。
如《不动相应经》所示,进入“无所有处”的一个有效方法是思惟:“此世间空,空于我,空于我所,空于常,空于恒……” 通过观照无限的识中“无”有我、“无”有我所,修行者得以进入“无所有”的体验。
这一步也揭示了“止”与“观”的紧密关系。在此,一个深刻的“观”法(观无我)被用来成就一个高阶的“止”境(无所有处定)。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即使是体验到深刻的“空”,也未必是解脱性的智慧,关键在于是否断除了烦恼和我执。
最终的解脱,是超越一切感知,包括对无所有处的感知,放下一切对经验的认同(萨迦耶见,sakkāya)。
VI.2 无我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步,我们需要回顾“无我”教法的核心。佛陀在向五比丘宣说《无我相经》时指出:
- 五蕴(色、受、想、行、识)是无我的。
- 理由是:如果五蕴是我,那么“我”就应该能完全掌控它,让它不生病、不痛苦,随心所欲。但事实并非如此。
- 因为五蕴是无常的,所以是苦的;因为是苦的,所以不应被视为“我”或“我所”。
因此,了知五蕴非我、非我所,便能对世间一切无所执着,从而证入涅槃。
然而,断除“我见”(萨迦耶见)与根除“我慢”是有区别的。初果圣者(须陀洹)已断我见,但深层的“我是……”的习气(我慢)依然存在。如《相应部·翅摩迦经》中的譬喻,一块洗净的脏布,虽然污垢已除,但气味犹存。需要用香料熏习,才能彻底去除气味。同样,修行者需要不断地深入观照,才能彻底根除“我慢”这股残余的“气味”。
“无所有处”的修习,并非导向虚无主义,认为“什么都不存在”。它只是为了破除最根本的执着——“我”和“我所”的存在感。
VI.3 非想非非想处
《小空经》的巴利版本在“无所有处”之后,提到了对应于第四无色界定的“非想非非想处”。然而,其中阿含和藏译的对应版本均未提及此步。
多部早期经典及论典指出,由于“非想非非想处”的感知极为微细,几乎难以辨识其存在与否,因此不适合作为培育观智的所缘。观智的生起需要一定清晰度的感知作为对象。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巴利版本为了凑齐四无色界定的完整序列而后来加入了这一步,而中、藏版本的传承保留了更原始的、更符合实修逻辑的次第。基于此,接下来的探讨将遵循中、藏版本的路径,从“无所有处”直接进入“无相心定”。
VI.4 无相
- 第七步:从“无所有处的感知”转向“无相心定”(signless concentration of the mind)。“相”(nimitta)指事物的外在特征,是心用来识别、记忆和形成概念的依据。例如,我们通过声音的“相”来辨认说话的人。
心的识别过程依赖于捕捉相对稳定的“相”,这无形中强化了我们对事物“常”的错觉。同时,执取“净相”(悦意的特征)会引生贪欲,执取“不净相”(不悦意的特征)会引生嗔恚。
“无相心定”的修习,即是不于一切相作意,放下所有用来识别、定义、评判的概念和标签。此时,心不再关注任何事物的特征,而是安住于“无相”这一所缘上。这比“无所有处”更为彻底,因为连“此世间空无我”这个概念本身也被舍弃。
这体现了著名的“筏喻”精神:佛法如渡河之筏,过河之后,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在此阶段,连“空性”这个概念本身,也成为需要被超越的对象。
无相的体验非常接近涅槃,但仍非究竟解脱。因为即便是最深刻的无相定境,本身依然是因缘造作的。如经典中的譬喻,国王大军的到来能暂时压制森林中蟋蟀的鸣叫,但军队离开后,蟋蟀会再度鸣叫。同样,定力可以暂时压伏烦恼,但若无智慧的根除,烦恼仍会再生。
VI.5 证悟空性
- 第八步:最终的解脱。修行者在安住于“无相心定”后,生起最后的观智:观照此“无相心定”的体验本身,亦是因缘造作(有为法),是意念所成,因此是无常的,不应于此生起任何欣喜或执着。
当修行者能彻底放下对包括最微细的“空”或“无相”体验在内的一切执着时,便实现了向“无为法”的最终突破。此时,心从贪、有、无明等诸漏中彻底解脱,证得涅槃。
这才是最上、无上的空性——心“空”于一切烦恼染污。此刻,唯一“不空”的,是这个由六根和生命机能构成的身体,它将延续到生命终结。
佛陀总结道,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如来所安住的“最上空”,就是这种烦恼灭尽、无为的心解脱。
VI.6 空性的动力学
总结整个渐次入空的八个步骤,其内在动力学可概括为逐层地解构与超越:
- 超越杂多,趋向统一 (从村庄到僧团,再到林)。
- 超越具体,趋向抽象 (从林到地,即坚实性)。
- 超越物质(色),趋向空间(空) (从地到空无边处)。
- 超越客体,趋向主体 (从空无边处到识无边处)。
- 超越主体,趋向无我 (从识无边处到无所有处)。
- 超越概念,趋向无相 (从无所有处到无相心定)。
- 超越经验,趋向无为 (从观照无相定之无常,到证入涅槃)。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掏空”过程,每一步都放下前一步的所缘,并视之为一种“疲劳”,直到最终放下一切,实现彻底的解脱。
VI.7 总结
渐次入空的禅修路径,从“识无边处”经由“无所有处”(观无我)和“无相心定”(舍概念),最终导向对涅命的亲证。关键在于,修行者不仅要放下粗重的执着,更要放下对微细禅修体验本身的执着,观照其因缘和合、无常的本质。当心彻底“空”于一切烦恼和执取,便证得了最上、无上的空性。
第七章 实修指导
本章提供一个可行的实修方案,旨在将前述的慈悲与空性禅修结合起来。此方案从四梵住的培育入手,然后无缝衔接到渐次入空的禅修,始于空无边处的体验。这仅为一种可能的路径,修行者可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调整。
VII.1 奠定基础
- 戒行基础:如《意行经》所示,清净的戒行是禅修不可或缺的基础。慈悲首先体现在不伤害他人的行为中,这是 formal practice 之外的根本。
-
克服五盖:每次静坐开始时,应先简要地审视内心是否存在五盖(贪欲、嗔恚、昏沉睡眠、掉举恶作、疑)。
- 贪欲:可修不净观,或修习“舍心”,拉开与欲望的距离。
- 嗔恚:修习慈心是对治嗔恚的标准方法。悲心和舍心亦有助益。
- 昏沉睡眠:修习喜心,或思惟修习慈悲的利他意义,能提振精神。
- 掉举恶作:修习慈心能软化过度精进带来的紧张;修习舍心能平衡内心的忧虑。
- 疑:对修行意义的怀疑,可通过思惟慈悲的广大愿力来克服。
VII.2 慈悲与其他梵住的修习
当内心清净无盖时,可以有意识地为此感到喜悦。经典中的譬喻可资利用:心无五盖,如同还清债务、病得痊愈、出离监牢、重获自由、安抵坦途。带着这份喜悦,开始培育四梵住。
可采用简短的祝愿语来激发相应的心态,例如:
- 慈(Mettā):“愿一切众生无有敌意。” (体验温暖、友善、无分别的护卫之心)
- 悲(Karuṇā):“愿一切众生无有恼害。” (体验希望他人离苦的迫切善愿)
- 喜(Muditā):“愿一切众生安乐。” (体验随喜他人善行与快乐的清净之心)
- 舍(Upekkhā):“愿一切众生自得其乐。” (体验允许他人为自己负责、同时又祝愿其幸福的平衡之心)
这些祝愿语或任何能激发相应心境的意象(如微笑的婴儿)都只是工具,一旦心境生起,就应放下工具,安住于该心境本身。
一个基于太阳的譬喻可以帮助体验四梵住的不同特质:
- 慈:如正午的太阳,平等地普照万物,给予温暖,不求回报。
- 悲:如日落的太阳,在黑暗即将降临时,更显其光辉,愿意俯就苦难众生。
- 喜:如日出的太阳,充满生机与希望,随喜万物的苏醒,积极向上。
- 舍:如夜晚的满月,本身不发光,但能宁静地映照太阳的光辉,广阔而清凉,保持平衡。
VII.3 放射修习
- 激发:用祝愿语或意象激发相应的梵住。
- 源起:感受它从胸口中心处温暖地涌起。
- 放射:柔和地让这股能量遍满前方、右方、后方、左方、上方、下方。这并非用力的“推”,而是像轻轻拉开帷幕,让光自然地照耀出去。
- 安住:放下对方向的分别,安住于无限、无边的遍满状态中。
若希望在此基础上加入观智的成分,可以结合七觉支进行修习。在遍满的状态中,保持念,以择法观察此心境,以精进维持它,从而生起喜,带来轻安,进入定,最终达到舍。修习结束时,可观照此殊胜体验的无常、缘起性,从而“导向舍离”。
VII.4 空性禅修
从四梵住,特别是从第四梵住“舍”的无限遍满状态,可以自然地过渡到渐次入空的第四步——空无边处的感知。
过渡:从安住于“舍心”的无限遍满,转向关注这遍满所处的“无限空间”。这个过渡非常平顺,因为二者的体验都具有“无限”和“平衡”的特质。焦点从“舍的态度”转向了“体验舍的空间”。
修习: 1. 建立:如同修习梵住,先觉知前、右、后、左、上、下方的空间,然后让自己身体的坚实感也融入这片空间中,最终安住于无限、无障碍的纯粹空间感中。 2. 观照:在体验中,了知自己已“空”于先前对物质坚实性的感知,也“空”于各种杂念。 3. 日常: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去留意事物之间的空间、呼吸之间的停顿、声音之间的静默。观照物质身体的空性本质,能帮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平衡。
进阶:
- 识无边处:从觉知无限空间,转向觉知能知此空间的“识”。在日常中,这表现为对自心起心动念的高度觉察,并实践“巴希亚的教导”——于见唯见。
- 无所有处:观照能知的“识”本身亦无我、无我所,从而进入“无所有”的体验。日常中,这体现为“我”和“我所”感的减弱,以及更深的放下。
- 无相:放下一切概念,包括“无我”的概念,安住于无分别的寂静中。
- 证悟:观照“无相”的体验本身也是无常、缘起的,彻底放下对一切经验的执着,证入涅槃。
这条从慈悲到空性的道路,始于温暖的人际关怀,经由心的无限扩展,最终导向对一切现象最深刻的洞见和彻底的解脱。
第八章 经文翻译摘要
本章提供了书中核心讨论所依据的三部关键经文的摘要,这些经文分别是《中阿含》中与巴利经典《行动所生经》、《小空经》和《大空经》相对应的平行文本。
VIII.1 《中阿含·意行经》摘要(对应《行动所生经》)
此经的核心在于阐明“意行”(即意图)是造业的关键。佛陀开示,有意识、有目的地造作业,其果报是必然要承受的;而无意之行,则不一定。经文详细列举了三种不善身业(杀、盗、淫)、四种不善语业(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和三种不善意业(贪、嗔、邪见)。
接着,经文的重点转向了如何通过修习四梵住(慈、悲、喜、舍)来转化和净化内心,从而影响业的果报。修行者通过持戒清净,远离五盖,然后让慈、悲、喜、舍之心无限地遍满整个世界。当心变得如此“广大”和“无量”时,过去所造的有限的、不善的业力,就如同将一把盐投入恒河,其影响力被极大地削弱,甚至不再能束缚修行者。
此经明确指出,一个从小就安住于慈悲心解脱的人,长大后不会造作恶业。更重要的是,通过有智慧地修习四梵住,修行者若未证得究竟解脱,则能证得不还果(三果阿那含)。这直接将慈悲的修习与解脱道上的果证联系起来,凸显了其在早期佛教修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VIII.2 《中阿含·小空经》摘要(对应《小空经》)
此经是全书关于空性禅修的核心依据。缘起于阿难询问佛陀是否常“多行空”。佛陀肯定后,详细开示了一条“渐次入空”的实修路径。这条路径的核心原则是:持续地觉知当下的经验“空”于什么,同时又“不空”于什么,然后放下后者,转向更微细的所缘。
次第如下: 1. 从“村落/人”到“林”:放下对人的感知,安住于对森林的单一感知。 2. 从“林”到“地”:放下对林木的感知,安住于对大地(坚实性)的单一感知。 3. 从“地”到“空无边处”:放下对坚实性的感知,安住于无限空间的感知。 4. 从“空无边处”到“识无边处”:放下对空间的感知,安住于能知这一切的无限之识的感知。 5. 从“识无边处”到“无所有处”:放下对识的感知,安住于无一物可得的感知。 6. 从“无所有处”到“无相心定”:放下一切概念,安住于无分别的定境。 7. 最终解脱:观照“无相心定”本身也是因缘造作法,从而彻底放下一切,灭尽诸漏,证得涅槃。这才是最上、无上的空性。
此经为如何系统地、有次第地通过禅修亲证空性提供了清晰的蓝图。
VIII.3 《中阿含·大空经》摘要(对应《大空经》)
此经补充了《小空经》的教导,着重阐述了如何将空性智慧稳固地安立于内心,并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佛陀首先强调了独处和建立稳固禅定(奢摩他)对于修习空性的重要性。修行者应先在内心中建立定力,然后才能有效地观照内、外、内外的空性。如果观空时心生扰动,应回到能带来安乐的定境中,使心柔软、调顺,再继续观修。
接着,经文将空性的修习扩展到一切威仪和活动中:
- 行、住、坐、卧:在一切姿态中,保持内心不生贪、忧等烦恼。
- 思惟:舍离不善思惟,培育善思惟。
- 言谈:避免无益的闲聊,只谈论有助于修行和解脱的话题。
- 五欲:当面对五欲的诱惑时,应观其无常、变坏之相,从而舍离贪染。
- 五蕴:观照五蕴的生灭,以根除“我慢”。
此经的核心教导是,空性并非一种抽离现实的哲学概念,而是一种遍及生活所有层面的、持续的净化过程。真正的空性修行者,是将“空于烦恼”这一品质,贯彻于身心的一切活动中,最终实现对所有“我”和“我所”执着的彻底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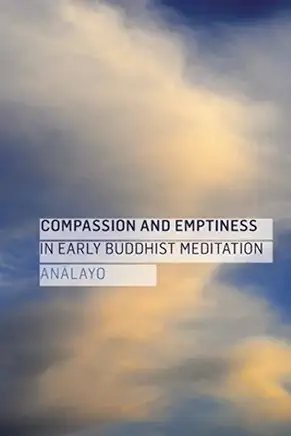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