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理想的起源
慈悲喜舍, 西方世界的佛法 ·Index
The Genesis of the Bodhisattva Ideal - Anālayo
菩萨理想的起源 - 无着比丘(Anālayo)
本书通过对巴利尼柯耶与汉译阿含经等早期佛法经典的比较研究,揭示了“菩萨”这一重要概念是如何从一个为自我解脱而修行的个体,逐步演变为一个承载着誓愿、授记与救世情怀的伟大理想。
第一章 乔达摩作为菩萨
本章旨在探讨“菩萨”一词在早期经典中,是如何用来指代尚未成佛的乔达摩的,并追溯其用法与意义的演变。我希望通过此番探寻,勾勒出这一概念从最初代表寻求觉悟的未觉悟者乔达摩,逐渐演变为注定成佛的乔达摩菩萨的脉络。
我的考察涵盖四个主题:菩萨乔达摩的觉悟之路(1),他的动机(2),他的希有特质(3),以及过去诸佛的传承(4)。
1.1 乔达摩的觉悟之路
在上座部佛教的巴利尼柯耶经典中,“菩萨”(巴利语为 bodhisatta)一词主要由佛陀乔达摩在回顾自己觉悟前的经历时使用,那时的他可谓是“菩萨”的典范。该词通常出现在一个固定的句式中,即某个事件或念头发生在“(我)觉悟之前,当还是一个未觉悟的菩萨时”,即 pubbe va (me) sambodhā anabhisambuddhassa bodhisattass’ eva sato(下文简称“觉悟前”句式)。
然而,在说一切有部传承的相应文献中,并未采用“菩萨”一词。有学者认为,这或许是出于对佛陀的崇敬,而刻意避免使用此词,转而以“世尊”等尊称来指代他觉悟前的生命阶段。这种倾向在数部巴利经典中亦有体现。在非佛陀本人叙述的段落里,即便所涉时期明确为佛陀觉悟之前,巴利语词 bodhisatta 也常被“世尊”或“佛陀”等称谓所取代。
在巴利经典中,大多数出现“觉悟前”句式的语境,都与菩萨乔达摩在禅修上的进展有关。这些实例主要涵盖三大主题:
- 菩萨克服不善的心所
- 他培育心的寂止
- 他智慧的增长
关于菩萨与不善心所的斗争,一部巴利经典及其《增一阿含经》对应版本记载了他在独处修行时如何面对生起的恐惧。另一部巴利经典及其《中阿含经》对应版本则记录了菩萨如何清晰地分辨善与不善的念头。在各种不善念中,数部经典特别强调了菩萨与感官欲望的斗争。
菩萨培育心的寂止,似乎与四神足(ṛddhipāda)的修习密切相关,有三部巴利经典提及此为其觉悟前修行的核心内容。根据《相应部》中的一部经,他主要的禅修方法是安般念(出入息念)。其他经典则记载,随着禅定加深,他体验到心之光明与禅相,通过稳定这些境界,他最终证得了四禅(dhyāna)。
菩萨智慧的增长,似乎基于他在觉悟前对苦的缘起的探究。其他经典则描述了他对诸受、四大、五蕴、六根六尘以及世间真实本性的审察。这些段落揭示了乔达摩培育智慧的各个面向,而这些面向最终汇聚成他在觉悟之夜所证得的圆满智慧。
总而言之,上述出现“觉悟前”句式的经典,描绘了菩萨乔达摩与恐惧、感官欲望等不善念的斗争,以及他培育寂止与智慧的过程。这些构成了他觉悟之路的核心。这些经典中的描述,完全符合早期佛法经典中关于一位阿罗汉迈向觉悟之路的标准记述。因此,从这些段落中浮现出的“菩萨”一词的核心意涵,可概括为将乔达摩个体呈现为一位“寻求觉悟者”。接下来,我将探讨菩萨的求道之旅。
1.2 乔达摩的动机
在一些经典中,“觉悟前”句式与菩萨乔达摩的出家有关。这些记载表明,他思惟到居家生活的束缚不利于全身心投入解脱之道。也就是说,从菩萨的角度看,出家是他觉悟的必要基础。
关于激励乔达摩菩萨踏上求道之旅的更深层思惟,我们可以在《圣求经》(Ariyapariyesanā-sutta)及其《中阿含》对应版本中找到线索。这两部经都将凡夫对终将衰败死亡的世俗事物的追求,与寻求不衰不死之道的圣者之求作了对比。两者皆揭示,正是这种神圣的追求,激励了菩萨出家寻求觉悟。他当时的思惟,两部经的记述几乎完全相同:
“我自己身为会衰老……与死亡之法,现在,我何不去寻求那无老……无死、无上安稳离缚的涅槃呢?”
“我自己确实身为会衰老与死亡之法……我何不去寻求……那无老无死……无上安稳离缚的涅槃呢?”
这似乎是巴利尼柯耶中唯一明确阐述乔达摩菩萨求道动机的段落。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丝毫没有反映出对他人福祉的关怀。相反,根据这份自述,乔达摩菩萨的动机是为“自己”(attanā)所面临的生老病死等问题寻找出路。
同样的特点也体现在《圣求经》及其对应版本对菩萨成功完成求索的描述中。根据两个版本,当乔达摩证得那无老无死、无上安稳的涅槃时,他认识到自己已从未来的生死轮回中彻底解脱。这里同样完全没有提及能够拯救他人。相反,根据早期经典的记载,佛陀对他自身觉悟的认知,完全是以“解脱了自己”来表述的。
这种对他人福祉的显著缺失,在《圣求经》接下来的情节中变得更为突出。经中记载,新觉悟的佛陀倾向于不向他人说法,而决定满足于自己所证得的解脱。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这段情节在《中阿含》的对应版本中并未出现。因此,《圣求经》中关于梵天(Brahmā)出面劝请佛陀传播解脱讯息的部分,可能是后人增补的。无论如何,鉴于梵天的劝请在其他多种文献中均有记载,这一情节的内涵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巴利义注解释说,佛陀之所以犹豫是否要说法,是因为他观察到世人被烦恼深重地影响。义注还补充道,佛陀也希望由梵天来劝请,因为这样可以使世人对佛法生起敬意。
第一种解释似乎混淆了《圣求经》中的事件顺序,经中佛陀不愿说法发生在他观察众生烦恼深浅之前。根据《圣求经》的记载,佛陀在观察了众生的状况后,认识到有些人能够理解他的教法,这促使他接受了梵天的劝请。
第二种解释则暗示佛陀怀有通过梵天劝请来提升自己声望的隐秘动机,这与经典中通常描述的圆满觉悟者完全超脱名利的状态难以相符。此外,根据《圣求经》前文,佛陀曾明确告知听他自述的比丘们他最初不愿说法的心情:“比丘们,我这样思惟时,心倾向于不劳碌,而不倾向于说法。”这并不像是他在期待梵天的邀请,更自然的理解是:佛陀确实曾不愿说法。
新觉悟的佛陀有此不愿说法的倾向,这与所有佛教传统共有的观念——即他历经无数劫的修行,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引领众生走向解脱——难以调和。《圣求经》记载,佛陀不愿说法的原因是,如果他人无法理解他所证悟的甚深真理,对他而言将是疲劳(klamatha)和恼人(viheṭhā)之事。类似的理由也出现在《增一阿含经》、Catuṣpariṣat-sūtra 以及法藏部、大众部-说出世部、化地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等传承的律藏中。
也就是说,根据众多文献的记载,当佛陀思量是否要与他人分享他的发现时,他完全是从此事将如何影响他自己的角度来考量的。这与我们之前观察到的他的动机及最终目标的达成是一致的。自始至终,根据这些文献,佛陀最主要的关切点在于他自身——无论是在他最初立志求道之时,在他成功圆满道业之际,甚至在他思索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之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早期经典的视角来看,佛陀没有悲心。《圣求经》记载,当梵天出面劝请时,佛陀是出于悲心观察世间的。另一部经则阐明,悲心是佛陀圆满觉悟后自然具备的品质。然而,早期经典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他人福祉的关怀是乔达摩菩萨踏上求道之旅的动机之一,他目标的成功达成也未显示出与教化活动有任何直接关联。这一点,即便是在没有梵天劝请情节的《中阿含》版《圣求经》中也是如此,该版本同样将未来佛的动机及目标的达成完全描绘为为自己寻求和实现解脱。
上述段落揭示,在早期佛教对菩萨动机的构想中,为救度他人而展开的慈悲教化活动并未扮演显要角色,这一品质是在菩萨证得觉悟并决定说法后才变得明显的。鉴于某些早期经典对阿罗汉的描绘,这一点尤其引人深思。
与前文提到的菩萨与一般阿罗汉在觉悟之路上的相似性相一致,在早期经典中,对众生的悲心似乎是觉悟的成果,无论是菩萨的觉悟还是阿罗汉的觉悟。
例如,众多文献记载,最早的一批阿罗汉一经觉悟,便被佛陀派遣至各地游行,以教化他人。另一个例子是,佛陀曾因一群新受戒比丘过于吵闹而将他们逐出。舍利弗未能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照看并引导这群比丘,结果遭到了佛陀的严厉斥责。另一部经记载,舍利弗因另一位比丘一再反驳他的教导而感到烦恼。阿难陀认为最好保持沉默,未出面支持舍利弗,结果因缺乏悲心而受到佛陀的公开批评。鉴于这两位上首弟子在经中常受赞叹,这两次因缺乏悲悯之心而受斥责的事例,突显了早期经典是何等看重对他人福祉的关怀。
在他人受恼时予以支持,以及教化他人,不仅是对阿罗汉的期望,也是对走在阿罗汉道上者的期望。数部经典指出,教化他人对僧侣而言至关重要,若疏于此事,将阻碍道业的进步。实际上,根据早期经典的说法,证得解脱的其中一个时机,正是在教化他人之时。由此可见,只要先前的修行已使心成熟到足以实现最终的解脱突破,一个人是可能在从事慈悲教化他人的活动中成为阿罗汉的。
总而言之,在早期佛教思想中,为他人福祉而行动的悲心,既与佛陀相关,也与阿罗汉及期望成为阿罗汉者相关,但它并非激励菩萨踏上觉悟之旅的品质。
在激励成佛的构想中,悲心并未扮演显要角色,这一特点并不仅限于早期经典。有学者指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大事》(Mahāvastu)。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在早期的某些大乘经典中,悲心在菩萨的构想中仍然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方面。
1.3 乔达摩的希有特质
早期经典并未强调悲心,而是侧重于菩萨的一系列其他特质。关于传统上认为菩萨最鼓舞人心的特质,我们可以在《未曾有法经》(Acchariyabbhutadhamma-sutta)及其《中阿含》的对应版本《未曾有法经》中找到详尽的阐述。这两部经对我探究菩萨概念至关重要。下文中,我将简要概述巴利版本,并与其中文对应版本进行比较,然后探讨此经的功能,最后转向其对菩萨概念发展的贡献。
《未曾有法经》的宣讲者是阿难陀,他列举了佛陀一系列稀有且不可思议的特质。在巴利版本中,他首先描述了菩萨乔达摩在兜率天(Tuṣita)出生、驻留(其寿尽)及辞世时,皆具足正念正知。《中阿含》的对应版本没有提及他在兜率天出生时的正念正知,而是说他在寿、色、荣光等方面超越了其他天人(deva)。不过,两个版本都同意,菩萨是带着正知入母胎的,此事件伴随着地震与大光明的显现。
《未曾有法经》接着描述了菩萨在母胎中的状况,记载了四位天人守护他;他的母亲具足德行,远离淫欲之念,同时又享受五欲之乐;并且她能看见腹中的菩萨,如同看见穿过彩色丝线的琉璃宝珠。这些希有特质在《中阿含》版本中均未出现。虽然《中阿含》也描述了菩萨在母胎中的状况,但它提到的是他在胎中右胁而卧,身体完全伸展。
接着,《未曾有法经》记载,母亲在分娩七日后去世,怀孕期为十个月,且母亲是站着分娩的。这些特质在中文对应版本中均未提及。
两个版本都同意,菩萨出生时未被任何身体杂染所污,并由四位天神接引。它们也都同意,空中有两股水流出现为他沐浴,且菩萨一出生便走了七步。巴利版本记载了新生菩萨此时所作的宣告,他宣称自己在世间至上,并将超越未来生死,而这一宣告在《中阿含》的对应版本中并未出现。
两个版本再次一致地记载,出生伴随着另一次地震与大光明的显现。巴利版本中阿难陀列举的希有特质到此结束,而在《中阿含》的记述中,他继续提及了佛陀青年时期及觉悟后发生的几件非凡之事。两个版本都以佛陀强调自己另一项希有特质作结,即他能够觉知感受、想与念头的生、住、灭。
通过这份简要的概述可见,两个版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菩萨从兜率天降入母胎,及其非凡的出生形式与环境,似乎是它们的共同起点,之后两个版本似乎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发展了菩萨希有特质这一主题。由于这些独立的发展,它们现存的希有特质列表差异多于相似之处。这两部经的差异程度,远大于通常在《中部》及其《中阿含》对应版本之间所见的差异。这一情况表明,这两个版本各自最终成型的年代相对较晚。
关于仅在某一版本中出现的特质,鉴于两部经对佛陀希有本性的态度一致,我们可以排除某一版本刻意删减了另一版本中特质的可能性。既然两部经在其他方面没有文本缺失的迹象,一个版本遗失了整整一系列仅存于另一版本中的特质,似乎也不太可能。因此,对于仅在单一版本中出现的特质,最直接的解释是,它们是后人增补的。
巴利版本中一个后人增补的迹象,与菩萨母亲在分娩七日后去世有关。在《未曾有法经》中,这一事件的安插打乱了时间顺序,因为它出现在描绘菩萨在兜率天的出生、驻留与辞世,以及他从兜率天降生并随后在母胎中驻留的一系列希有事件之后。按照这个模式,菩萨的出生应该是下一个希有事件,但在《未曾有法经》中,他的出生是在描述其母去世之后才被提及的。
由于《中阿含》的对应版本完全没有提及他母亲的去世,我们可以稳妥地推断,关于母亲去世的记载是后人增补的。实际上,人们通常不会将菩萨母亲的早逝归为她儿子的希有特质。《优陀那》(Udāna)中的一部经将她的早逝视为一件普遍意义上的希有之事,这或许是对此事件更直接的定性。也许是由于对佛陀希有特质的兴趣日益增长,在某个口传阶段,这段《优陀那》的经文被增补进了《未曾有法经》的希有事件记述中。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次增补是在未意识到该经其他地方所遵循的时间顺序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两部经的一个独特之处,反映了它们列举这些希有特质的功能。在每一项特质之后,阿难陀都会说他将此希有之事铭记于心。这样,每一项希有特质都被描述了两次,一次是实际的描述,一次是阿难陀铭记于心的事。
在早期经典的思想世界里,阿难陀以记忆第一而著称。根据不同律藏中关于所谓“第一次结集”的记载,他记住了佛陀所说的所有经典。因此,他将佛陀的每一项希有特质都铭记于心,本无需特别强调。况且,这本是自明之理,否则他根本无法列举出来。
除了陈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外,这些重复性的陈述还会向听众暗示,每一项特质都值得被记诵。通过这种方式,两个版本中“听到菩萨有如此这般的特质,然后记住菩萨有如此这般的特质”的模式,会鼓励他人也将这些特质铭记于心。
《未曾有法经》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其反复使用视觉刺激。第一个是描述伴随着大光明的地震,其光芒之强甚至超越日月,照亮了那些众生首次得以看见彼此的极暗之处。第二个意象用一颗穿过彩色丝线的纯净切割琉璃宝珠,来说明母亲能看见自己腹中菩萨的情景。第三个意象将新生的菩萨比作放在迦尸(Kāśī)布上的宝石。第四个意象再次描绘了大光明与地震的出现。
这些视觉刺激,及其对佛陀(传统上被认为是三宝中的第一宝)的教化活动驱散黑暗的象征性暗示,被置于一个与禅修相关的框架中:第一个希有事件突显了菩萨在兜率天出生、驻留与辞世时具足正念正知。最后一个希有事件,是佛陀在回答阿难陀的阐述时提及的,描述了佛陀对感受、想与念头的生、住、灭的觉知——这在其他经典中被归于正知的范畴。
因此,在《未曾有法经》列举的特质背后,我们可以辨识出一个循环模式,从菩萨的正知,经由大光明的显现,到对珠宝的描述,然后再从另一件珠宝,经由另一次大光明的显现,回到佛陀的正知。也就是说,《未曾有法经》中对佛陀希有特质的回忆,以一种近乎韵律的模式展开,始于并终于禅修的品质,其轨迹则贯穿了一系列具有强烈视觉和象征成分的意象。通过这种方式,该经展现出相当大的感染力,揭示了其目的很可能是邀请人们以一种相当生动的方式来忆念,甚至观想佛陀的希有特质。
这种忆念与感染性的讯息,对于佛陀涅槃后的早期佛教僧团,尤其是那些从未见过佛陀的弟子来说,尤为重要。由于缺乏与在世佛陀亲身接触的体验,且在早期佛陀并未被以雕塑或绘画的形式表现,像《未曾有法经》这样的经典,能让新皈依者通过记诵甚至观想他希有的特质,与他们的导师建立某种情感上的连结。
成为佛教徒的行为包含了皈依三宝。然而,一旦佛陀涅槃,新皈依者便失去了与第一皈依处——佛陀——建立直接关系的机会。与宗教传统的一般特性相符,创始人的逝世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一个不易填补的真空。对早期佛教而言,这个真空对于那些无法仅从教法中获得所需全部灵感、需要更具个人化、触动心灵之物的人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
《未曾有法经》对怀孕与出生等寻常事件的探讨,可以被理解为通过生动描述未来佛陀如何以非凡的方式经历这些全人类共有的体验,来提升和激励听众,从而满足这类需求。通过处理任何在古印度家庭中生活过的人都熟悉的事情,《未曾有法经》找到了共同点,同时又通过伴随这些事件的希有奇迹,创造了距离感并唤起了敬畏。因此,《未曾有法经》的教化功能,在于激发和增强基于佛陀超凡本性的虔敬心,这一点在他从天界如天神般降临人间的过程中伴随的希有奇迹中显而易见。
希有奇迹在这一方面所扮演的重要功能,或许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未曾有法”会成为传统经典分类(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一部分。从上述希有奇迹的功能来看,关于希有奇迹的经典被认为重要到足以被纳入佛教文献的分类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希有奇迹的功能为《未曾有法经》中一个关于菩萨概念的相当重要的发展提供了背景。这一发展体现在经中对菩萨刚出生时,走七步然后宣告的描述中:
“我是世间至尊,我是世间至上,我是世间第一;此是我最后生,此后不再有轮回。”
这一特质的希有之处,在巴利版本中似乎特别在于菩萨所说的话,因为根据《阿摩昼经》(Ambaṭṭha-sutta),另一名男婴也能在出生后立刻说话。然而,他并没有做出庄严的宣告,而是请求母亲为他洗澡,因为他皮肤黝黑。《阿摩昼经》记载,目睹他出生即能言的人,得出的结论是他必定是个恶鬼(piśāca)。
因此,婴儿出生即能言的能力本身,并不一定被视为正面之事。此外,根据巴利《本生经》集,菩萨在之前的两次生命中也曾在出生后立刻说话。既然这些例子并未被明确算作希有奇迹,那么在当前情况下,希有的应是他宣告的内容。
《中阿含》的版本与《未曾有法经》不同,它只记载了七步,完全没有提及任何宣告。有学者可能正确地总结道:“声称是佛陀在出生时所宣告的偈颂,是很晚才创作的。”
除了《未曾有法经》,一系列文献也记载了新生菩萨乔达摩所作的宣告,尽管其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关于过去佛毗婆尸(Vipaśyī)出生后所作宣告的内容,也存在差异。虽然该偈颂的巴利版本与《未曾有法经》中乔达摩菩萨的宣告相同,但《长阿含经》中关于新生毗婆尸菩萨所言的记载,则提及了救度众生。这便引入了在迄今所讨论的段落中显著缺失的“关怀他人”的观念。
从《未曾有法经》的教化功能来看,乔达摩菩萨所作的宣告,最初可能只是作为尊崇佛陀的整体框架中的又一个面向而出现的。然而,这一特定的希有事件,却带来了最初或许既未被意图也未被预见的后果。
这一宣告的重要性,在与本章第一部分所考察的段落进行比较时便显现出来。那些段落无一例外地指出,菩萨尚未觉悟(anabhisambuddho),即使在那些不使用“菩萨”一词的版本中也是如此。因此,从早期佛教经典这一普遍共识的视角来看,菩萨只有在成佛后,才能宣称“此是我最后生,此后不再有轮回”。
在巴利经典中,“此是我最后生”等宣称,无一例外都是在某人证得圆满觉悟后所作的陈述。这些段落中的大多数描述了佛陀自身的觉悟,在引出“此是我最后生,此后不再有轮回”的宣告时,都指出在那个时刻,“智生起”,了知自己已达此境地。一部经明确指出,佛陀所证得的此智是“由觉悟而生”。
综合这些表述,我们可以稳妥地断定,当这些关于佛陀觉悟的描述形成时,认为他出生时便已知此生将是最后生的观念尚未出现。换言之,《未曾有法经》中婴儿菩萨所作的宣告,清晰地体现了将原本在觉悟后才作出的宣称,前移到了乔达摩菩萨刚出生的时刻。
随着这一视角的转变,本章第一部分所描述的菩萨觉悟之路——那些段落中描绘的历程——的重要性便会减弱。一旦乔达摩在出生时便已圆满,他迈向圆满的各个阶段必然发生在更早的时期,即在某个或某些前世。这一视角转变在《未曾有法经》中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它用“菩萨”一词来指代佛陀在兜率天的前世,而在早前的经典中,该词仅用于他作为人的最后一生。
除了“菩萨”一词在时间上的扩展使用外,关于优越与最终成就的宣告还有一个相当重大的影响,因为它确立了菩萨在出生时便注定成佛的观念。《增支部》中一个列举了菩萨五个大梦的段落也反映了这一点,该段落也使用了“觉悟前”的句式。这五个梦预示了他未来将成功证得圆满觉悟、教导觉悟之道、拥有广大的在家弟子、拥有来自四种种姓的出家弟子,以及在不受执着的情况下获得丰足的供养。从这类段落的视角来看,《圣求经》及其他地方所描述的菩萨求道之旅,无论如何都注定会成功结束。
总而言之,《未曾有法经》反映了菩萨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菩萨在出生时便已具备了最高程度的圆满,而其他经典则认为这是他长期求道之旅的最终成果。由于这一视角的转变,与佛陀地位相关的优越性,现在成了菩萨与生俱来的权利。
《未曾有法经》在这方面并非孤例,其他文献也显示出一种倾向,即赋予菩萨那些在早期经典中被认为是佛陀在觉悟之夜才圆满发展的品质。例如,《僧伽施设》(Saṅghabhedavastu)暗示菩萨出生时便具足天眼。根据《譬喻经》(Divyāvadāna),菩萨甚至在前世便拥有此能力。《大事》(Mahāvastu)则宣称,菩萨在燃灯佛(Dīpaṃkara)时便已达离欲,并于无数俱胝劫前便已证得智慧圆满。
《大本经》(Mahāpadāna-sutta)对过去佛毗婆尸的立场,与《僧伽施设》相近,指出毗婆尸同样在出生时便已具足天眼。这引出了我探究的下一步——《大本经》中所描述的过去诸佛的传承。
1.4 过去诸佛的传承
《未曾有法经》中对菩萨希有特质的全部描述,在《大本经》中对过去六佛觉悟前时期的描绘中重现。有学者认为,《大本经》中对六位前佛的记述,是“仿照乔达摩本人一生的故事”而成的。通过对《大本经》中关于过去佛毗婆尸的描述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可以为这一观点提供支持。在这段描述中,与《未曾有法经》平行的段落称毗婆尸为“菩萨”,而描绘其青年时期事件的其他段落则称他为“王子”。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梵文及部分汉文的对应版本中。一旦婴儿毗婆尸被定性为菩萨,在描述其童年与青年时期时,便难以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来中断使用该称谓。因此,这种模式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较早的关于“毗婆尸王子”经历的记述,后来被增补了来自像《未曾有法经》这样经典中的希有事迹描述。
无论对此观点的最终定论如何,《大本经》所做的,无疑是将未来佛的希有特质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框架之中,指出这类希有事迹是所有即将成佛者都会经历的。也就是说,虽然迄今所考察的经典只谈及一个个体——菩萨乔达摩,但《大本经》却以一种普遍性的方式使用“菩萨”一词,向其听众介绍了过去成佛的菩萨们的特质。无论这部经是否是这些发展的历史首例,它确实是这些发展的见证,并极有可能体现了所发生之事的基本模式。
佛教文献反映出对过去诸佛传承的兴趣日益增长,这很可能与其“为佛陀的教法提供正当性”的功能有关。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显示佛陀拥有一条可与耆那教的祖师(tīrthaṃkara)或婆罗门传统的吠陀仙人相媲美的前辈传承。
从这个目的来看,将菩萨的希有事迹应用于《大本经》的过去诸佛体系中,或许一个无意的副作用,便是将这些希有特质的获得,归于任何一位即将成佛者。也就是说,随着《大本经》中关于过去诸佛记述中希有事迹的出现,《未曾有法经》中对个案的呈现,便成了任何走在成佛道上者的常态。
这是菩萨概念朝向成为一个可被效仿的理想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菩萨与过去佛之间直接关系的概念尚未出现。《大本经》对过去诸佛的描绘,并未提及过去佛与菩萨乔达摩之间的任何会面,因此也未提供他们之间有直接关系的任何迹象。它所做的,仅仅是显示所有这些个别的例子,都符合主导佛陀一生的普遍模式。
然而,一旦“我是世间至尊,我是世间至上,我是世间第一”的宣告在《大本经》中由所有菩萨作出,那么任何一位即将成佛者自然也可以作出同样的宣告。这样一来,遍及世间的优越性便成了菩萨在最后一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由于在出生时便已是菩萨——前提是这将是他的最后一生——他便是整个世间最前、最高、最好的存在。
由此产生的优越感,可以看作贯穿了后期文献中菩萨概念的发展。有学者观察到,在《大事》中,“未来的菩萨们”似乎更多地是受到佛陀的人格与光辉的影响,而非对苦难大众悲惨境况的深切思惟。在生起菩提心的那一刻,他们心中主导的,是成为与当世佛陀同等的热切渴望……获得个人色身之美与超凡光辉,在他们的决意(praṇidhāna)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优越感也是早期大乘经典的一个显著特征,有学者强调,“追求成为宇宙中最高存在”是“追求菩萨道的一个动力”。在某些大乘文献中,菩萨理想甚至包含了一种“权力幻想,佛教修行者渴望……达到圆满佛果所代表的宇宙主权与力量——不是消灭自我,而是自我的神化。”
总结
本章所考察的发展起点,是那些描述佛陀乔达摩从出家到觉悟期间的早期经典,其中将他描绘成一位寻求觉悟者。反映他动机的段落显示,乔达摩的主要关切在于为自己寻求解脱。他对他人福祉的悲心,似乎是在他觉悟后才产生的,而非激励他追求解脱的动机。
乔达摩的涅槃必然留下了一个需要填补的真空。对于那些需要与第一皈依处建立某种情感连结的弟子来说,在失去了与在世佛陀亲身接触的可能性后,忆念他希有的特质便显得尤为重要。
《未曾有法经》反映了这类关切,并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发展:佛陀在成功证得觉悟后所获得的优越性与不再有未来轮回的境界,已成为他在出生时所作宣告的一部分。伴随这一希有事迹,菩萨成了注定觉悟的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已是一位觉悟者。
导师涅槃所造成的真空,不仅在内部——在弟子僧团中——产生影响,也在外部——即与其他同时代的宗教团体与修行者关系上——产生影响。在这里,为佛陀作为一位卓越的精神导师提供正当性的需求,会促使人们对他精神传承的细节——即过去诸佛——产生日益增长的兴趣。这种兴趣构成了《大本经》及其对应版本的基础。随着这些经典的出现,菩萨乔达摩的希有事迹成了普遍意义上菩萨的常态。这为菩萨概念成为一个通用术语铺平了道路,从而为菩萨概念最终演变为一个可被效仿的理想奠定了基础。
迄今所考察的发展,尚未涉及菩萨理想的萌芽阶段,这一理想本身在早期佛法经典的文本库中并未出现。尽管在行为方面,佛陀有时以自己为榜样供人模仿,但在精神追求方面,应遵循的楷模是其他通过成为阿罗汉而证得最终目标的弟子。然而,随着上述菩萨概念的转变,必要的基础已经奠定,基于此基础,下一步的发展得以发生。这些发展包括:在过去某个时刻决定走上菩萨道时所立下的成佛誓愿,以及随后从另一位佛陀那里获得的关于此追求将圆满成功的授记。这两个观念——誓愿与授记——是接下来两章的核心主题。
第二章 遇见过去佛
本章的核心主题是菩萨在决定追求佛果时所立下的誓愿。对我探究此主题至关重要的,是关于菩萨乔达摩与过去佛迦叶佛(Kāśyapa)相遇的故事。
为了给我对此次相遇的研究提供背景,我首先将概览本生故事(jātaka)这一体裁(1),然后转向记载此次相遇的经典(2),接着考察此故事作为本生故事的性质(3)。在这些准备工作就绪后,我将转向菩萨誓愿的主题(4)。
2.1 本生故事体裁
在我探究菩萨理想起源的上一章中,我提出《未曾有法经》中将佛陀的特质应用于新生菩萨的现象,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旦菩萨被视为出生时便已圆满,他迈向圆满的历程必然发生在更早的时期,即在他出生之前。
这样一来,《未曾有法经》中关于希有事迹的阐述所体现的菩萨概念的发展,反过来会使佛陀的前世变得日益重要。换言之,希有事迹中体现的菩萨概念的转变,会激发早期佛教徒对传统经典分类(aṅga)中另一成员——本生故事(jātaka)——的兴趣。这一体裁的重要性,从其在古代雕塑与铭文中大量的表现,以及本生故事诵读者被视为独立的持经师(bhāṇaka)类别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本生故事,被传统视为记录了菩萨在逐步获得使他能够成佛的品质过程中的经历与奋斗,对于那些对菩萨概念感兴趣并为之吸引的人来说,扮演了核心角色。实际上,《大事》(Mahāvastu)这部本身便是众多本生故事宝库的著作,将讲述这类故事与揭示菩萨的修行历程联系在一起。
本生故事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是,它们融合了各种古印度的寓言、轶事与譬喻,通过将其中一位主角——通常但不总是最英勇、最典范的那位——认定为佛陀的某个前世,而使之成为本生故事。
仅举一例,巴利《本生经》集中的一个《罗摩衍那》(Rāmāyaṇa)版本,便将其英雄罗摩(Rāma)的功绩,呈现为菩萨的过去生经历。同样的情况也见于该故事的一个汉译版本,而另一个汉译版本则未采取本生故事的形式。类似的变化也见于该故事进入各种亚洲文化后的其他表现形式中,它们仅在某些时候以本生故事的面貌出现。
为了恰当地理解本生故事的形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已存在于早期经典与律藏(Vinaya)中的故事,它们将我们带到本生故事文献的初始阶段。下文中,我将考察几个例子,以说明其中一些故事是如何起源的。
有学者在其对本生故事体裁的研究中,提到了一则出自《相应部》的故事。与《相应阿含》的对应版本一致,该经记载佛陀讲述了一只鹌鹑如何因误入非其领域而被猎鹰捕获的故事。故事的寓意是,正如鹌鹑应坚守其固有领域,比丘们也应坚守正念的修行作为他们的固有领域,以抵御魔罗(Māra)。
虽然在《相应部》与《相应阿含》的经典版本中,整个故事是以譬喻的形式出现的,但在巴利《本生经》集中,同一个故事却是一则本生故事,将那只聪明的鹌鹑认定为菩萨。有学者评论道:“哪个是更早的文献,这点毫无疑问;因为《本生经》引用了其来源,并指明了《相应部》中该寓言最初出现的篇章。”一个保存在汉译《优陀那》集中的该故事版本,与两部经一致,也未将故事中的任何动物认定为菩萨。
在对佛教正典历史的研究中,有学者注意到《长部·婆夜私经》(Pāyāsi-sutta)中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在《长阿含》与《中阿含》的对应版本中也以类似形式出现。这两个故事的背景是一位怀疑论者与一位佛教僧侣之间的讨论。讨论中,僧侣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论点。其中一个例子是将一位聪明的商队领袖与一位愚笨的作对比;另一个则描述了某人在掷骰子时试图作弊。
这两个故事也出现在巴利《本生经》集中,该集将每个譬喻中的主角都认定为菩萨。由于《婆夜私经》及其《中阿含》对应版本明确将这些故事作为“譬喻”来引出,我们可以稳妥地假定,它们是后来才成为本生故事的。
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一则关于一匹飞马拯救一群失事商人免遭食人女妖吞食的故事,这在《中阿含》中被明确界定为譬喻。一个保存在汉译《优陀那》集中的该故事版本,也未采取本生故事的形式。然而,在巴利《本生经》集以及《增一阿含经》的一部经中,这个故事记载了佛陀的一个前世。同样的情况也见于该故事的其他几个版本中,但它们在应将飞马还是商人领袖认定为菩萨这一点上存在分歧。
有学者在其对巴利《本生经》集的详尽考察中,强调了一个例子,即巴利律藏中的一个故事,在《本生经》集中被呈现为佛陀的一个前世故事。这个譬喻描述了一只鸟、一只猴子和一头大象如何通过尊重其中最年长者——结果是鸟——而和谐共处。
根据上座部律藏的记载,佛陀曾向一群行为不端的比丘讲述这个故事,他们占据了所有住所,未给年长比丘留下空间。巴利《本生经》集在同一个故事的结尾,由佛陀认定大象和猴子分别是大目犍连(Mahāmaudgalyāyana)与舍利弗(Śāriputra)的前世,而他自己则是那只鸟的一个过去生。
同一故事在大众部(Mahāsāṃghika)、(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a)与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的律藏版本中,与巴利《本生经》集一致,都将此故事呈现为本生故事。虽然(根本)说一切有部与说一切有部的律藏也将鸟认定为菩萨,但根据大众部的律藏,他曾是那头大象。该故事在法藏部(Dharmaguptaka)与化地部(Mahīśāsaka)的律藏版本,以及一个保存在汉译《优陀那》集中的版本,则未将这些动物中的任何一个认定为菩萨,因此在这里此故事并未采取本生故事的形式。
原则上,这类变化可能是譬喻转变为本生故事的结果,也可能是本生故事变为譬喻的结果。然而,从上下文来看,故事的目的是教导尊重长者的必要性。为达此目的,譬喻的形式便已足够,无需将其任何主角认定为菩萨。鉴于那些将此故事呈现为本生故事的律藏,在佛陀应被认定为哪种动物上存在分歧,我们可以稳妥地假定,这些认定是后来的特征。实际上,在早期经典的思想世界里,佛陀的前世通常是人,而非动物,这使得关于这些动物和谐共处的故事,最初可能并非意在记录菩萨的过去经历。
另一个类似的律藏例子围绕着知足的主题展开。根据上座部律藏,一些比丘向当地民众索求这索求那,以致人们一见到比丘便迅速绕道,甚至逃跑。为了给这些比丘一个教训,佛陀讲述了一个那伽(nāga,龙/蛇)王的故事,它曾定期拜访一位仙人(ṛṣi),但在仙人请求给予那伽的宝珠后,便停止了拜访,再也未曾前来。
大众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藏,与上座部律藏一致,都将此故事呈现为譬喻。而在法藏部与化地部的律藏,以及巴利《本生经》集中,这个故事则记录了菩萨的一个过去生。在这种情况下,故事同样无需最初便是记录佛陀的一个过去生,便能达到其目的,因此那些未将主角认定为佛陀过去生的版本,在这方面可能更为原始。
还有一个律藏的例子,与忍辱的主题相关。上座部律藏记载,拘舍弥(Kauśāmbī)的比丘们曾因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规范问题而爆发激烈争吵。为了启发争论的双方保持忍辱,佛陀讲述了一位王子的故事,他的父亲被一位征服了他们王国的国王残忍杀害,他希望为父报仇,便在未被认出的情况下,投身于这位国王麾下服务。当有机会执行他的计划时,他却决定饶过国王。
这个故事在《中阿含》、《增一阿含》、一个保存在汉译的《优陀那》集,以及法藏部、化地部与上座部的律藏版本中,都未采取本生故事的形式。然而,巴利《本生经》集将这位王子认定为菩萨。一个汉译的《本生经》集则将王子的父亲认定为菩萨,并指出王子是阿难陀(Ānanda)的一个过去生。两个《本生经》集在应将谁认定为菩萨上存在分歧,以及在其他版本中没有任何此类认定,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故事最初可能并非本生故事。
虽然在迄今所考察的例子中,上座部律藏的版本与同传承的《本生经》集不同,未将相关故事认定为本生故事,但在另一个例子中它却这样做了。所涉故事是关于一头公牛,因其主人用侮辱性的话语称呼它,而拒绝执行某项任务。根据律藏的记载,佛陀讲述此故事是为了制止比丘们互相辱骂。上座部律藏对此故事的结尾,含蓄地指出这头公牛是菩萨的一个前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上座部律藏与相应的巴利本生故事是一致的。该故事在法藏部、化地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藏版本,以及一个汉译的《优陀那》集中,则无此类认定。
上座部律藏中的这个故事,似乎是巴利经典与正典律藏中唯一记载佛陀前世为动物的例子。鉴于在其他律藏中,该故事并未以本生故事的面貌出现,上座部律藏中现存的这段经文,有可能是在某个口传阶段,受到了将过去故事视为记录菩萨前世经历的倾向的影响。这种倾向在之前考察的例子中清晰可见。这种倾向背后的逻辑,可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佛陀在说法时,是依据他对自己前世的回忆来引述这些故事的。
这种假设背后的理路,可见于《究罗檀陀经》(Kūṭadanta-sutta)及其对应版本中,经中记载佛陀描述了过去一位国王与他的婆罗门国师所举行的一场盛大祭祀。在场的听众中一位杰出的婆罗门听到这番描述后,心生疑惑:佛陀并未声称听闻过此事,这是否意味着他亲身见证了这场祭祀?佛陀确认情况确实如此。这个故事因此为以下理路提供了经典上的认可:当佛陀讲述一个故事而未明确表示是从何处听来时,便可假定这是他从自己过去中回忆起的事件。
除了提供这个先例外,《究罗檀陀经》及其对应版本也例证了某些本生故事形成时所遵循的上述模式:巴利版本将菩萨认定为主持祭祀的婆罗门国师,汉译版本则认定他是下令举行祭祀的国王,而该经的梵文残片则认定他两者皆是。
总而言之,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一些模糊性,但迄今所考察的例子确实指向一种倾向,即譬喻与譬喻故事通过将其中的一位主角认定为菩萨,而演变为本生故事。虽然在一些例子中,通过比较研究,这种倾向相当清晰地显现出来,但在其他情况下,证据尚不足以得出确切的结论。
2.2 乔达摩遇见迦叶佛
在记住了某些正典本生故事似乎是如何形成,以及有时我们只能找到这一过程的迹象而无法得出确切结论之后,我们现在准备转向关于菩萨乔达摩与过去佛迦叶佛相遇的记载。这次相遇发生于乔达摩自己即将成佛之时。因此,从他漫长成佛生涯的传统视角来看,他精神品质的成熟,应在此次与前佛相遇的场合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这次相遇被记载于《中部》的《 陶师经》(Ghaṭīkāra-sutta)中,该经在《中阿含》中有对应版本。除了这两部经的版本外,还可以在大众部-说出世部传承的《大事》、(根本)说一切有部传承的《僧伽施设》,以及一部汉译的《譬喻经》(Avadāna)集中找到进一步的对应版本。下文中,我将基于这两部经的版本,概述故事的整体叙事进程。
《陶师经》及其《中阿含》对应版本始于佛陀展露微笑,阿难陀随即询问其原因。佛陀于是讲述了一个过去的故事,关于两位朋友,一位陶工和一位年轻的婆罗门,他们生活在过去佛迦叶佛的时代。陶工邀请年轻的婆罗门与他同去拜见迦叶佛。作为回应,年轻的婆罗门拒绝了,他的拒绝在《陶师经》及其《中阿含》对应版本中被记载如下:
“见那个剃光头的下贱沙门有什么用?”
“我不想见那个秃头沙门。”
其他版本也记载他用同样类型的贬损性言辞来指称迦叶佛。
在《陶师经》中,陶工随后又重复邀请了两次,当年轻的婆罗门再次拒绝后,他们便去沐浴。沐浴后,陶工再次邀请了年轻的婆罗门三次,后者同样拒绝了三次。
《中阿含》的版本没有记载任何重复的邀请,因为在这里,陶工在邀请后便立即抓住年轻婆罗门的发髻,强迫他从所乘的车上下来。《陶师经》则描绘了陶工为克服朋友的抗拒而采取的身体行动是逐步升级的。在他屡次口头邀请均告失败后,他起初是抓住年轻婆罗门的腰带,只有在后者解开腰带后,他才抓住年轻婆罗门刚洗过的头发。
在两个版本中,年轻的婆罗门最终都同意前往,并因此听闻了迦叶佛的说法。在回家的路上,年轻的婆罗门表达了出家的愿望。陶工将他带回迦叶佛处,后者应陶工之请,为年轻的婆罗门剃度。
接着,场景转至波罗奈斯(Vārāṇasī),迦叶佛在那里受到当地国王的拜访,并为国王说法。在第二天接受了国王与比丘们的饭食供养后,国王邀请迦叶佛与他共度雨季安居,但迦叶佛未接受邀请。
当悲伤的国王询问是否有其他与他相当的护持者时,迦叶佛提到了那位陶工,他已洞悉四圣谛,并具足非凡的德行。迦叶佛讲述了两次,他曾在陶工不在家时,应陶工失明的父母之请,自行取食;以及另一次,他让比丘们拆下陶工作坊的屋顶来修补他自己的茅舍。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陶工得知所发生之事后,都表现出欢喜与愉悦。听闻陶工的善行后,波罗奈斯的国王决定送食物补给给陶工,但陶工礼貌地谢绝了——故事至此结束。
纵观《陶师经》及其《中阿含》对应版本,两部经的一个核心主题似乎是陶工与波罗奈斯国王之间的对比,即从迦叶佛的角度看,由于陶工的德行,他是一位比国家富裕且强大的国王更优越的在家护持者。实际上,在整部经中,陶工都是主角,展现了一位理想在家弟子的典范行为。相比之下,年轻的婆罗门只在故事的第一部分扮演角色,在经的第二部分完全没有出现。
因此,《陶师经》的核心目的,似乎在于描绘一位理想的在家弟子及其对迦叶佛的深厚虔敬,并突显这位典范的在家信徒如何能够说服一位不情愿且有些傲慢的婆罗门去拜见佛陀。
2.3 作为本生故事的相遇
《陶师经》及其所有对应版本都以认定那位年轻的婆罗门是佛陀乔达摩的一个前世作结。然而,《增一阿含经》中一个段落对此一致认定提出了异议,它将迦叶佛时代的年轻婆罗门认定为乔达摩佛时代的一位比丘。这使得年轻的婆罗门不可能同时是菩萨。
虽然《增一阿含经》提供的线索并非决定性的,但它确实足以引起进一步的探究,即它暗示了这个故事可能并非一直被视为本生故事。为了探讨这种可能性,下文中我将从两个可能的角度——年轻婆罗门的角度与菩萨的角度——来审视将年轻的婆罗门认定为菩萨的提法。
从年轻婆罗门的角度来看,一个问题因他明显缺乏拜见迦叶佛的兴趣而产生。从成熟的菩萨理想来看,一位菩萨能够遇见一位佛陀,应是所能想见的最重大的事件,为他初发此道之心及后续对此愿心的确认提供了契机。
根据一个广为人知的传统,其上座部版本见于《佛种姓经》(Buddhavaṃsa),在遥远的过去,菩萨乔达摩曾是一位名叫善慧(Sumedha)的婆罗门。仅仅听闻过去佛燃灯佛(Dīpaṃkara)的名号,便令菩萨充满灵感与信心,以致他渴望未来自己也能成佛,便卧于泥中为桥,让佛陀从他身上走过。
《大事》记载,在更早的时期,菩萨曾以一种奢华的虔敬行为,将价值十万的花粉撒向过去佛 Sarvābhibhū 及其弟子们作为供养,同时发愿自己也要成佛。
这两个故事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描绘了菩萨乔达摩对遥远过去的诸佛所怀有的深切敬意与信心;这一点,与《陶师经》及其《中阿含》对应版本中对年轻婆罗门甚至不愿拜访迦叶佛——乔达摩佛降世前的最后一位佛陀——的描述,难以调和。
关于年轻婆罗门的不情愿,根据《中阿含》的版本,年轻的婆罗门只拒绝了一次陶工拜见迦叶佛的邀请,而在其他版本中,他则屡次拒绝。在《中阿含》的记述中,他的不情愿也更容易理解,因为根据该版本,他正准备向一群聚集在他座下学习的五百名弟子说法。
同样的模式也体现在,根据《中阿含》的记载,当他的朋友抓住他一次后,他便愿意去拜见迦叶佛,而在《陶师经》及其他版本中,他是在被多次抓住后才顺从的。然而,不同版本都同意,陶工最终抓住了年轻婆罗门的头发。
有学者在其对古印度抓住他人头发之内涵的详尽研究中解释道,在打斗情境中,“抓住头发意味着完全控制了对手”,因为“一旦成功抓住对手的头发,他便处于可以斩首对方的境地。”因此,“被抓住头发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羞辱。”
《陶师经》实际上特别指出了这一行为的非同寻常,记载年轻的婆罗门对于一个社会地位远低于自己的人竟敢做出如此大胆之举感到相当惊讶。因此,陶工像《中阿含》版本中所描绘的那样,在一次拒绝后便立刻跳上车,抓住年轻婆罗门的头发并将他从车上拉下来——这一行为还是在年轻婆罗门的五百名弟子面前进行的——会是相当令人惊讶的。从古印度的视角来看,这一叙述似乎极不可能。
《中阿含》中将年轻的婆罗门描绘成很快便被说服去见迦叶佛,因此可能是一种试图缓和这一情节所蕴含的困境的做法,即陶工必须相当坚持才能克服年轻婆罗门拜见佛陀的不情愿。
同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年轻婆罗门表达其反对的方式,他对拜见那些“秃头沙门”表示不愿。因此,根据这一情节,在即将成佛的一个生命中,菩萨不仅不愿拜见另一位佛陀,甚至还诋毁了一位佛陀。在《中阿含》的记述中,陶工实际上相当明确地告诉迦叶佛,那位年轻的婆罗门对佛陀毫无信心与敬意。
整个这一情节的初衷,可能在于描绘一位像陶工这样虔诚的在家弟子,为了度化他人愿意付出何等努力,甚至敢于抓住一位婆罗门的头发,只为让他去拜见佛陀。然而,一旦这位年轻的婆罗门被认定为菩萨乔达摩,这一情节便变得** problematic**。
年轻婆罗门对佛陀不敬态度所带来的困境,也反映在几部著作中,它们将佛陀觉悟前所经历的六年苦行,视为他在前世作为年轻婆罗门时,对迦叶佛作出贬损性言论的业果。汉译《譬喻经》版本的标题也反映了同一主题,其内容预告为“(佛陀行)苦行之前因”。在《僧伽施设》中,佛陀在回答比丘们关于他为何要经历六年苦行是因何前业所致的询问时,讲述了陶工与他年轻的婆罗门朋友的故事。也就是说,在这些版本中,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佛陀为何在证得觉悟前要修行苦行。显然,对于一位菩萨而言,这种相当令人惊讶的行为并未被忽视。
因此,从年轻婆罗门的角度来考察他与菩萨的所谓身份同一性时,可以看出这种认定导致了几个困境。
转向这一认定的另一个方面,从菩萨的生命历程来看,《论事》(Kathāvatthu)提出了一个与此认定相关的问题:如果佛陀乔达摩在不久的过去曾是迦叶佛的弟子,他还能声称自己无师自悟吗?
根据《大萨遮经》(Mahāsaccaka-sutta)及其对应版本中关于佛陀觉悟的记载,乔达摩在证得解脱前,发展了回忆过去生的能力。关于此类回忆的标准描述指出,通过运用这种超常的知识,一个人会记起诸如自己前世的名字、社会地位、所食之物以及当时所经历的乐与苦等信息。
鉴于在菩萨的情况下,这种对过去生的回忆是证得觉悟尝试的一部分,人们会期望他的回忆很快便会聚焦于他作为迦叶佛座下比丘的前世。在迦叶佛座下修行的那段时期,应是菩萨在过去最接近能够导向解脱的教法的例子。根据巴利对《陶师经》的义注,那位年轻的婆罗门实际上已学尽迦叶佛的所有教法,并修习观禅直至临近入流果的边缘。
通过回忆迦叶佛的教法,菩萨乔达摩将亲身体验一位佛陀的解脱之道,这会向他展示如何前进以亲自证得觉悟。从这个角度来看,乔达摩自身的觉悟,实际上并非独立于一位老师而发生的。
这样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圣求经》及一系列其他文献相冲突,这些文献一致记载,佛陀在觉悟后便宣称自己没有老师。虽然有人可能认为这是指没有在世的老师,但另一个困难的段落是,根据《转法轮经》(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及一系列对应版本,他在觉悟后不久开始教导他早期的五位同伴时,宣称自己证悟了“前所未闻”之法。如果乔达摩在他早期于迦叶佛座下的生命中曾听闻过类似的教法,这与“前所未闻”的表述方式便不太契合。
鉴于古印度对师承传承的尊重,如果乔达摩能指出一位过去佛是他的老师,那将是相当有利的。这会增强而非减损他已证得圆满觉悟的主张。因此,如果在他突破觉悟的那一夜,他确实回忆起了从过去佛迦叶佛那里得到的教导,那么在他宣称自己证悟时指明这一点,既自然也方便。
实际上,根据《相应部》及其对应版本中的一部经,佛陀认为他的觉悟是重新发现了一条古道,一条过去觉悟者们所走过的道路。这使他关于证悟了“前所未闻”之法的断言有了更清晰的脉络:他并未声称发现了全新的事物;相反,他认为自己的证悟是一次重新发现。鉴于此,他声称证悟了“前所未闻”之法,必然意在强调他是在没有任何老师直接口头指导的情况下完成觉悟的。正是这种完全自力发现证悟之道的方式,使他成为一位佛陀。
虽然这些考量本身并非决定性的,但上述讨论的段落并未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早期经典将佛陀的觉悟仅仅描绘成回忆起从过去佛迦叶佛那里得到的教法。如果假定在这些段落形成之时,关于佛陀曾是过去佛座下比丘弟子的观念尚未出现,那么这些段落读起来会更为自然。因此,从乔达摩的生命历程来看,他与那位在迦叶佛座下出家的年轻婆罗门的所谓身份同一性,很可能是在较晚的时期才形成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年轻婆罗门与过去佛迦叶佛的相遇,并未进入巴利《本生经》集。这与例如《大善见经》(Mahāsudassana-sutta)或《摩诃提婆经》(Makhādeva-sutta)等情况形成对比,在那些例子中,除了经文本身,佛陀的这些前世版本也可以在《本生经》集中找到。其在《本生经》集中的缺席,会支持这样一种印象,即这部经最初可能并未被视为本生故事。
在对之前研究的几个正典本生故事案例的背景下,《陶师经》并非唯一一个将教化故事后来认定为记录佛陀前世的例子。然而,与上述大多数本生故事不同的是,在《陶师经》的情况下,这样的结论不那么直接,因为所有现存版本都一致地将那位在迦叶佛座下出家的年轻婆罗门认定为佛陀乔达摩的一个前世。
因此,只有《增一阿含经》中提供的线索,以及由此认定所产生的困难,才会支持这样的假设,即年轻婆罗门的故事可能并非一直被认为是记录菩萨乔达摩的过去经历。
无论对此假说的最终定论如何,传统显然将年轻的婆罗门与菩萨认定为同一人。这一认定,连同对其所涉困难的认识,为本章余下部分提供了背景,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转向菩萨誓愿的观念。
2.4 乔达摩在迦叶佛座下之誓愿
在我研究的上一章中,我讨论了《中部·未曾有法经》中的一个段落,该段落指向了菩萨概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发展,即将佛陀通过觉悟所获得的品质,归于新生的菩萨。
《未曾有法经》在《中阿含》中的对应版本,也包含了一个与菩萨概念相关的相当重要的观念。所涉段落记载了菩萨乔达摩为未来成佛所立下的誓愿。这一誓愿,作为《中阿含·未曾有法经》中所列希有事件的第一个出现。根据这第一个希有事件,菩萨是在作为迦叶佛座下比丘时,初发成佛之愿的:
“世尊于迦叶佛时,初发无上正真道意,行梵行。”
鉴于这一特质在巴利版本中没有对应内容,它极有可能与新生菩萨出生后即作宣告一样(后者仅见于巴利版本),是后人增补的。
认为这一特定希有事件可能是后人增补的假设,从对《中阿含·未曾有法经》的更深入考察中得到了进一步支持。菩萨初发成佛之愿,不仅作为第一个希有特质出现,在与第二个希有事件(菩萨重生于兜率天)及第三个希有事件(菩萨超越兜率天其他天人,此处还重复了他在兜率天的重生)相关时也再次被重复。然而,从第四个希有事件开始,该经便只单独列出每个希有事件,不再重复之前已提及的。开头部分关于菩萨誓愿的不规则性,给人的印象是,在该经的传承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变化,极有可能是因将菩萨初发成佛之愿纳入希有事件列表而引起的。
这种纳入菩萨在过去佛迦叶佛座下初发誓愿的希有事件,是《中阿含》经文所采用的更广阔时间框架的自然结果。虽然《未曾有法经》列举了从菩萨在兜率天出生到他降生的希有事件,但《中阿含》版本则涵盖了在他兜率天出生之前发生的希有事件,以及在他降生之后发生的希有事件。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传统,菩萨在兜率天的生命之前,是他在迦叶佛座下的僧侣生涯,因此,《中阿含》版本所采用的扩展时间框架,自然会引入一个发生于那时的希有事件。
支持菩萨初发誓愿是《中阿含》希有事件列表的后人增补的另一个论据,可以从上文讨论的《中阿含》中与《陶师经》平行的那部经中获得,该经记载了迦叶佛与菩萨乔达摩(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婆罗门)的会面。这部《中阿含》的经文丝毫未提及那位将成为佛陀乔达摩的年轻婆罗门,决定走上菩萨的道路。鉴于在同一《中阿含》集的《未曾有法经》中记载了这一决定,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如此重要的决定,在关于菩萨与迦叶佛会面的记述中,是不太可能被忽略的。这表明,《中阿含》中与《陶师经》平行的那部经,很可能源于一个菩萨在迦叶佛时代决定走上成佛之道的观念尚未形成的时期。
其他文献则将菩萨踏上求佛之道,与一个更为遥远的生命时期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述,根据《佛种姓经》,乔达摩早在燃灯佛时代便已获得未来成佛的授记,燃灯佛是一系列二十四位过去佛中的第一位,而迦叶佛是最后一位。其他传统的说法各异,有些也将此授记与燃灯佛时代联系在一起,而另一些则将其置于更早的时期。在这些记述中,一个明显的普遍倾向是,乔达摩踏上求佛之旅的时间点,被不断地推向更遥远的过去。
由于这一转变,在诸如《百喻经》(Avadānaśataka)、《佛种姓经》、《本生经序论》(Jātakanidānakathā)、《大事》及《僧伽施设》等著作中,菩萨与迦叶佛的会面,获得了确认其道业的功能。迦叶佛对菩萨乔达摩未来证得佛果的此番确认,便成了一系列由过去诸佛所作宣告中的最后一环。
现在,大多数记载菩萨乔达摩立下此等誓愿或从其他佛陀那里获得授记的文献,都属于比早期经典更晚的文本层次。这使我们有理由假定,《中阿含·未曾有法经》可能保存了菩萨乔达摩在前世立下成佛誓愿这一观念发展萌芽阶段的残余。也就是说,在这一观念发展的初始阶段,誓愿——可以说很自然地——与紧接在佛陀乔达摩之前的佛陀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对佛陀乔达摩日益增长的神化,他被认为需要用以发展必要资格的时期自然会延长,这导致他求佛之旅的起点被推向了更遥远的过去。
总而言之,菩萨与过去佛迦叶佛的相遇似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 第一阶段,以《陶师经》及其《中阿含》对应版本为代表,菩萨乔达摩仅被认定为一位在迦叶佛座下出家的年轻婆罗门。 - 第二阶段,以《中阿含·未曾有法经》为代表,这次会面激励菩萨立下自己也要成佛的誓愿。 - 第三阶段,菩萨与迦叶佛的会面,通过授记来再次确认他即将成佛,因为他追求佛果的决定早已作出。
若假定《中阿含·未曾有法经》见证了菩萨立下成佛誓愿这一观念发展的萌芽阶段,那么问题便是,此誓愿出现的语境,是否为这一观念的产生提供了任何理据?换言之,《陶师经》及其《中阿含》对应版本中的故事,是否为菩萨当时立下誓愿这一观念的产生提供了任何线索?
从这个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载了菩萨于迦叶佛座下出家后,《中部》与《中阿含》的经文便再未提供关于他的进一步信息。也就是说,在这两部经中,陶工展现了典范的行为并表现出值得称赞的品质,而关于菩萨,则未记载任何特别鼓舞人心之事。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因为菩萨在本生故事中通常——虽然并非总是——扮演着光辉典范的角色。
然而,在当前这个例子中,在菩萨乔达摩的一个与他成佛时期非常接近的前世中,他在故事里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菩萨非但没有展现出鼓舞人心的行为,甚至不愿意见一位佛陀,并对他作出了贬损性的言论。这个故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一旦他生起信心并在迦叶佛座下出家为僧后,便再无下文。在《陶师经》或其《中阿含》对应版本中,关于菩萨作为迦叶佛座下比丘期间,没有记载任何值得记录的典范行为或成就。相反,两部经都聚焦于陶工令人鼓舞的品质。
现在,随着《中阿含·未曾有法经》的出现,这段关于菩萨在过去佛迦叶佛座下为僧的不甚鼓舞人心的记载,通过一个简单而巧妙的视角转换,变成了一种希有且不可思议的品质:他在作为迦叶佛座下比丘期间未取得进一步的成就或殊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在那时他已决定追求未来成佛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作为过去佛座下比丘的时期远非失败,反而变得鼓舞人心且不可思议,因为“在迦叶佛时,(他)初发无上正真道意,行梵行。”这一希有事迹因此解释了为何他没有充分利用从一位圆满觉悟的佛陀那里直接获得的觉悟之道指导,来亲自证得解脱。
《大事》以一种更明确的方式处理了同一问题。它记载,在年轻的婆罗门出家后的一次场合,迦叶佛召集他的比丘们,告诉他们要静坐禅修,不证得烦恼尽除不起座。这一指示戏剧性地突显了从早期经典的视角来看,在佛陀座下出家者应有的行为。然而,《大事》接着记载,那位年轻的婆罗门却发愿自己也要成佛。这显然为他未能成功完成这次决意禅坐提供了理由。
《大事》相当直接地面对菩萨缺乏成就的问题,突显了通过“他当时已决定追求成佛之道”这一观念来解决此困境的巧妙之处。这样一来,便为后来的发展设定了一个明确的先例,而假定菩萨成为迦叶佛座下的比丘,正是为了促进他自己走向佛果,便只是更进一步了,这一步在《论事》与《僧伽施设》中得以体现。
这样,《中阿含·未曾有法经》很可能见证了菩萨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中间阶段,即立下成佛誓愿的观念开始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大本经》及其对应版本中过去诸佛的列表尚未迈出这一步,因为它们并未在菩萨与任何过去佛之间建立直接关系。因此,《中阿含·未曾有法经》似乎反映了菩萨概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发展,为菩萨理想的出现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总结
《陶师经》及其对应版本叙述了一位陶工如何说服他不情愿的朋友——一位年轻的婆罗门——去拜见过去佛迦叶佛。年轻的婆罗门决定出家,之后经文便不再关注他。根据对其他几个正典本生故事的研究模式,这个故事最初可能只是一个描绘陶工作为典范在家弟子的教化故事。然而,根据几乎一致的传统说法,那位年轻的婆罗门被认定为菩萨乔达摩的一个前世。
由菩萨在迦叶佛时代——即离他自己成佛不远的一个前世——行为的不甚鼓舞人心的记载所引起的问题,在《中阿含·未曾有法经》中通过一个视角得到了巧妙的解决。根据这部经,乔达摩在那时作出了追求佛果的决定。伴随这一希有事迹,菩萨理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成佛的决意——便应运而生。
在迄今所考察的发展中,仍然缺失的是一位佛陀向一位有志成为菩萨者授记未来成佛的观念。在早期经典中,并未找到乔达摩获得此等授记的记载。然而,这块拼图中缺失的部分,可以在同一文本库中找到,即《中阿含》的另一部经。在那部经中,佛陀乔达摩向未来的佛陀弥勒(Maitreya)作了这样的授记。这一授记以及佛陀弥勒在早期经典中的普遍角色,是下一章的主题。
第三章 未来佛的降临
本章的主题是佛陀向一位有志成为菩萨者授记其未来成功的观念。在早期经典中,唯一出现此类授记的段落,是在《中阿含》的《说本经》(说本经)中,其第二部分描述了未来佛弥勒的降临。在听闻此番描述的会众中,一位比丘发愿成为弥勒佛,并随即获得了佛陀乔达摩相应的授记。
在对所涉经文进行更深入研究之前,我首先将考察另一处关于弥勒佛的文献记载,该记载见于不同版本的《转轮王经》(Discourse on the Wheel-turning King)。在对该经进行概述并翻译相关情节后(1),我将探讨不同对应版本之间差异的内涵(2)。这构成了我后续研究《中阿含·说本经》(3),以及那位发愿成为未来佛弥勒的比丘所获授记(4)的背景。
3.1 《转轮王经》中的弥勒
未来佛弥勒在佛教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直是宗教灵感与愿心的源泉。他的崇拜在古印度及其他佛教国家的雕塑中显而易见。例如,根据上座部编年史《小史》(Cūlavaṃsa),几位斯里兰卡国王曾建造弥勒像;从法显的游记中我们得知,在现代的达尔迪斯坦地区曾有一尊巨大的木制弥勒像。
弥勒似乎不仅是大众崇拜的对象,也对几位著名的佛教学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卓越的上座部义注家佛音(Buddhaghosa)在其巨著的结尾希望,通过编纂《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所积聚的功德,能使他在弥勒佛时代证得最终解脱。根据多罗那他(Tāranātha)的《印度佛教史》,无著(Asaṅga)在兜率天逗留期间,曾直接从弥勒那里接受大乘教法。
除了作为导师,弥勒还具有护佑的功能。这在玄奘的传记中可见一斑,其中记载了对弥勒的虔诚信仰,如何使这位中国朝圣者从一群意图杀害他的强盗手中获救。
这些例子仅例举了弥勒在整个佛教历史中所扮演的多重功能中的一部分,显示他既是未来成佛后的导师,也是现居兜率天说法的导师,还是虔信者的护佑之源。
毫无疑问,弥勒是佛教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然而,在本章中,我只关注早期经典中关于他的记载。除了《说本经》,弥勒还出现在《转轮王经》中,该经包含了可能是历史上最早关于未来佛的文献记载。《转轮王经》现存三个版本:
- 《长部》中的《转轮(师子吼)经》(Cakkavatti-(sīhanāda)-sutta)
- 《长阿含》中的《转轮圣王修行经》(转轮圣王修行经)
- 《中阿含》中的《转轮王经》(转轮王经)
下文中,我首先将总结这三个版本共通的主要部分,然后分别从《长部》、《长阿含》与《中阿含》的经文中翻译弥勒的插曲。
这三个版本的《转轮王经》都始于佛陀鼓励弟子们要自力更生,以法为唯一的皈依处。《长部》与《长阿含》的版本指出,为遵循此建议,比丘们应修习四念住(smṛtyupasthāna)。通过坚守自己的领域,魔罗将无法侵害他们。
在这段介绍性的教导之后,三个版本都继续讲述了一个故事,作为对刚刚所给建议的例证。故事始于对一位过去转轮王统治时期,人类辉煌的境况与极长的寿命的详细描述,这位国王拥有七种神奇的宝物。其中之一是轮宝,当转轮王的生命将尽时,轮宝会从其位上滑落。
意识到轮宝已从其位上滑落,转轮王决定退位让与太子,并以隐士的身份度过余生。新加冕的国王发现轮宝已完全消失。在请教父亲后,他得知,如果他依法治国,轮宝便会重现,使他能够和平地征服全世界,自己也成为一位转轮王。
同样的模式一直持续,直到最终一位太子在登基后,没有遵循父亲的建议。相反,他按自己的想法治国,导致国家繁荣衰退。在受到大臣们的劝谏后,他修正了自己的做法,但却忽略了照顾穷人,结果导致贫困蔓延。在贫困的驱使下,有人偷窃,被抓后带到国王面前。当得知此人是因极度贫困而偷窃时,国王放了他,并给了他一些财富,使他不必再偷。消息传开,说国王会奖赏偷窃者,结果偷窃行为增加。意识到自己善举的意外后果,国王惩罚了另一名盗贼,这反过来导致了民众中暴力的普遍增加。结果,人们的寿命变短,他们往昔的美貌也消失了。当另一名盗贼被抓后,为免受惩罚而否认其行为时,谎言便出现了。
情况持续恶化,人们的寿命越来越短,道德与外部条件持续衰退。这达到了当今时代的状况,并继续下去,直到未来某个时刻,达到一个低点,那时人们的寿命只有十岁,道德完全消失。一场持续七天的末日之战随之爆发,期间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互相残杀。
在这场战争期间,一些人躲藏起来,并决定戒杀。他们持此戒律的行为,导致他们的寿命与美貌增加,激励他们进而戒盗,寿命因此进一步增加。同样的模式继续,道德的提升导致寿命与美貌的增加,直到最终再次达到长寿与福祉的高峰。正是在这一点上,在描述这个未来时代辉煌境况的背景下,弥勒出现了。下文中,我将翻译每个版本的相关部分。
a) 《长部》版本
“比丘们,在人寿八万岁的时代,在名为鸡都末底(Ketumatī)的王都,将出现一位名叫僧伽(Saṅkha)的国王。他将是一位转轮王,一位如法的法王,四方的征服者,已在其领域实现稳定,并具足七宝。
他将拥有超过一千个儿子,他们勇猛,体格英雄,能击败敌军。他将以法而非刀杖,统治这被海洋环绕的世界。
比丘们,在人寿八万岁的时代,一位名为弥勒(Metteyya)的世尊将出现在世间。他将是阿罗汉、圆满觉悟者、具足明行、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正如我现在出现于世间,是阿罗汉……佛、世尊。
他将以无上智亲自证悟后,宣说这个世界,包括其天人、魔罗、梵天,其沙门与婆罗门,这一代人,包括其天人与人类;正如我现在以无上智亲自证悟后,宣说这个世界……
他将教导初善、中善、后善之法,具足义理与文辞,并阐明一个完全圆满清净的梵行;正如我现在教导初善、中善、后善之法……
他将被数千比丘僧团围绕;正如我现在被数百比丘僧团围绕。
然后,比丘们,那位名叫僧伽的国王将重建由大广闻(Mahāpanāda)国王建造的宫殿,并居住其中。后来,他将舍弃它,并供养给沙门、婆罗门、乞丐、行乞者及贫困者,然后剃除须发,披上袈裟,在弥勒世尊、阿罗汉、圆满觉悟者座下,从家庭生活出家,过无家生活。
比丘们,你们应以自己为岛屿,以自己为皈依,无其他皈依;以法为岛屿,以法为皈依,无其他皈依。”
b) 《长阿含》版本
“那时(当人寿八万岁时),将有一位佛陀出现于世,名为弥勒(Mile)如来,已证得真理,圆满觉悟,具足十号,正如我现在是具足十号的如来。
在这个世界,包括其天人与人类……他将亲自证得;正如我现在在这个世界……已亲自证得。
他将教导初善、中善、后善之法,具足义理与文辞,并教导清净的梵行;正如我现在教导……
他将拥有无数千万的弟子僧团;正如我如今有数百弟子。那时,人们将称呼那些弟子为‘弥勒之子’,正如我的弟子被称为‘释迦之子’。
那时将有一位国王,名为商佉(Rang-ga),是一位灌顶武士、转轮王,将以正法统治世界四方,无需任何武力。他将具足七宝……
那时,这位尊贵的国王将竖起一座巨大的宝柱,周长十六寻,高一千寻。
然后,这位尊贵的国王将摧毁此柱,将其作为礼物供养给沙门、婆罗门及国内的贫困者。然后他将剃除须发,披上三衣,舍家修行。修行无上道,他将在此生此世亲自证得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此后不再有轮回。
佛告比丘们:‘你们应勤修善行。通过勤修善行,你们的寿命将延长,容貌将改善,你们将快乐,财富丰足,并具足威德之力。’”
c) 《中阿含》版本
“比丘们,在人寿八万岁的时代,将有一位国王,名为商佉(Conch-shell)。他将是一位转轮王,聪慧贤明,以其四军随心所欲地统治全世界。他将是一位如法的法王,拥有七宝……
他将绝对地统治整个大地,直至大洋,不依赖刀杖,仅以教导法,以成就(他人)的福祉。比丘们,他将成为所有灌顶武士王之首,通过坚守其祖传的固有领域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他坚守其祖传的固有领域,他的寿命不会减少,他的美貌不会衰退,他的快乐不会消失,他的力量也不会减弱。
比丘们,你们也应如此行事。(既然你们已)剃除须发,披上袈裟,出于信而出家修行,(你们应)坚守你们祖传的固有领域。比丘们,因为坚守你们祖传的固有领域,你们的寿命不会减少,你们的美貌不会衰退,你们的快乐不会消失,你们的力量也不会减弱。”
3.2 从比较视角看弥勒的插曲
除了某些微小的差异,通过比较上述翻译的版本,浮现出的主要一点是,弥勒插曲的安插位置显示出以下变化:
- 在描述转轮王之后(《长部》)
- 在描述转轮王之前(《长阿含》)
- 完全没有(《中阿含》)
《中阿含》版本中完全没有弥勒的插曲,原则上可能是由于该版本文本的缺失,也可能是由于另外两个版本有所增补。我们可以稳妥地排除《中阿含》的传承者有意删减提及弥勒的可能性,因为在《说本经》中,可以找到一个更详尽的关于弥勒降临的版本。
《中阿含》的版本也未给人留下文本意外缺失的印象。实际上,它向最终建议的过渡非常流畅。相比之下,上座部《长部》版本中的训诫“比丘们,应以自己为洲渚”与前一段并无如此直接的联系。《长阿含》版本中的训诫“应勤修善行”也是如此。这两个版本中不甚流畅的过渡,很可能是由于后来将提及弥勒的部分增补进经文而造成的。
这一假说也符合《长部》与《长阿含》版本中提及弥勒的段落,相对于转轮王的描绘,出现在不同位置的情况。这确实给人留下了一段文本以不同方式被增补的印象。与这两个版本相比,《中阿含》的经文似乎见证了在这次增补发生前的经文状态。
所有版本中现存段落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从字面上理解,它对遥远未来个体的名字与行为作出了精确的预言。在巴利经典中,现存的这段不仅是唯一提及弥勒佛的段落,也是唯一作出此类预言的例子。
从早期佛教的因果观来看,对遥远未来某个叫某某的人将做某某事作出精确预言,在某种程度上与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的观念相冲突,后者认为事物是有条件的而非完全决定的。要如此详细地预言遥远的未来,需要一种强烈的预定论。相关人员——尤其是将成为未来转轮王与佛陀的两位个体——的生活中不应有任何自由意志或选择,否则他们最终可能会做出与预言不符的事情。
有学者指出,在早期佛教思想中,我们所见的预言类型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预后”。虽然对阿罗汉可以作出确定的预言,即他不会再有来生,但一旦超出单一生命的范畴,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
《转轮王经》中对未来转轮王的描述——见于所有版本——可能同样并非意在严格的字面意义上理解。其目的未必是作出一个关于遥远未来必然会发生之事的精确预言,而更可能是在寓言故事的背景下,运用古印度世界统治者的象征意义。
实际上,有学者在其对巴利版《转轮王经》的详尽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整个叙述应被视为一个譬喻,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根据巴利义注,佛陀在说此经时,周围聚集了大量的在家众、比丘与天人。面对如此多样的听众,运用一个扩展的寓言叙事来传达教法,是相当恰当的。
《转轮王经》在其各个版本中所传达的实际教导,是鼓励其听众坚守其固有的领域,这是经文开篇建议与结尾的核心主题。巴利义注强调了这一主题,引用了另一部用譬喻来说明同一点的经文节选。该譬喻描述了一只鹌鹑因误入非其领域而被猎鹰捕获。然而,聪明的鹌鹑通过返回其固有领域而智胜了猎鹰。正如鹌鹑应坚守其固有领域,比丘们也应坚守正念的修习作为他们的固有领域。
实际上,从故事的目的——灌输坚守自己领域的重要性——来看,将鹌鹑认定为佛陀的前世并非必要。
同样,在《转轮王经》的例子中,《中阿含》版本对坚守自己领域的转轮王的描述,完全达到了其说明比丘们应坚守自己领域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三个版本所共有的。为达此目的,弥勒根本无需出现。实际上,在三个版本的经文最终建议中,弥勒并未扮演任何角色,而这正是阐述的高潮点。
有学者评论道:“对于那些常以严肃、缺乏幽默的实证主义态度来解读这些文献的人来说,最早提及未来佛的文献出处竟是一个幽默的譬喻,这或许显得奇怪,甚至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这位学者的解读得到了对现存版本进行比较研究的支持,这使得提及未来佛弥勒是后人增补的可能性相当高。也就是说,《转轮王经》的原始形式,可能完全与预言下一位佛陀的降临无关。
3.3 《中阿含·说本经》中的弥勒
虽然弥勒并未出现在《中阿含》的《转轮王经》中,但他确实在该集中的另一部经——《说本经》(说本经)——中出现了。下文中,我将简要概述整部经,然后翻译所涉的插曲。
《说本经》始于比丘们讨论一个问题:是在家人供养一位有德行的比丘利益更大,还是赚取财富利益更大。为了说明供养有德行者食物的优越性,阿那律(Anuruddha)描述了他在一个过去生中,作为一个贫穷的拾荒者,如何供养了一位独觉佛(Pratyekabuddha)一餐饭,结果他七次重生为天王,七次重生为人王。
佛陀以天耳听闻了这次谈话,便加入了比丘们。当被告知阿那律正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时,佛陀提议讲述一个未来的故事,比丘们欣然同意。
佛陀于是详细叙述了在未来人寿达八万岁时,将出现一位名为商佉的转轮王,他最终将出家并证得解脱。听闻此番描述,一位名叫阿耆多(Ajita)的比丘站起来,向佛陀合掌,发愿成为未来那位转轮王商佉。佛陀斥责阿耆多,推迟了本可现世完成之事——即证得解脱——但随后仍授记阿耆多确实将成为转轮王商佉。
佛陀接着描述了商佉将出家于其座下的弥勒佛。另一位也叫弥勒的比丘站起来,向佛陀合掌,表达了成为未来佛弥勒的愿望。佛陀赞叹他发此大愿,授记他确实将成为未来佛弥勒,并赐予他一件金色袈裟。
魔罗登场,试图用一组赞美重生于未来商佉王国内,成为英俊、衣着华丽、享乐的公民的偈颂来迷惑听众。佛陀立刻认出他,并以一组赞美在未来佛弥勒座下为求解脱而修梵行的偈颂作为回应。经文以被击败的魔罗消失,及听法比丘们的欢喜作结。
这部经与《转轮王经》版本中对未来转轮王商佉与弥勒佛的描述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后者并未记载有任何听众在听闻此故事时,发愿成为未来的转轮王或未来佛。
因此,除了《中阿含·说本经》及其对应版本,在巴利尼柯耶与汉译阿含经的文本库中,似乎并未记载此类未来的愿心。鉴于这部《中阿含》经的呈现方式,与同一《中阿含》集中《转轮王经》的版本不同,当前的情况似乎与我研究上一章中讨论的两部《中阿含》经文相似,它们似乎反映了菩萨乔达摩与过去佛迦叶佛相遇故事在文本演变中的后续阶段。
在当前的情况下,两部《中阿含》集中的经文似乎同样见证了一个故事发展中的不同时刻,该故事似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 第一阶段,反映在《中阿含·转轮王经》中,未来转轮王商佉的领域被描述,但完全没有提及弥勒。 - 第二阶段,以《长部》与《长阿含》版的《转轮王经》为代表,未来弥勒的降临已成为叙事的一部分。 - 第三阶段,似乎体现在《中阿含·说本经》中,对未来佛弥勒降临的描述,成了一位听众发愿成为未来那位佛陀的契机。
商佉王未来的故事,与《转轮王经》相当契合,后者始于过去一位转轮王的统治,接着描绘了世间生活条件的逐渐衰退,这反过来又引向条件的逐渐改善,最终在转轮王商佉的统治下达到顶峰。
相比之下,从其标题来看,《中阿含·说本经》最初可能只关注过去,即阿那律的譬喻(avadāna)。这个关于阿那律过去生经历的故事,也与经文的引子部分相符,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说明供养有德行比丘利益的例子,其功德超越任何物质财富。
佛陀随后加入并提议讲述一个未来的故事,这与在其他早期经典中发现的标准模式不同。根据那个标准模式,当佛陀加入一群正在讨论的比丘时,他会继续他们正在讨论的主题。当前的情况则不同,佛陀立刻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主题。这给人的印象是,关于商佉与弥勒的故事,可能是后来附加到一部原本只关注阿那律前世的经文上的,两部分通过佛陀提议他可以就未来讲法而融合在一起。
无论关于《中阿含·说本经》(及其由此引申的其独立翻译的对应版本)的演变的最终定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辨识出对菩萨概念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贡献,尽管“菩萨”一词本身并未被使用:在这两部双胞胎经中,佛陀乔达摩的一位比丘弟子,揭示自己是一位菩萨,他不仅表达了他成为下一位佛陀的愿望,而且还获得了相应的授记。
这涉及到从一种在代表现世或过去诸佛前世经历的菩萨概念中普遍存在的回顾性视角,转向一种前瞻性视角:现世佛陀的一位比丘弟子,将在未来成佛。虽然这种转变是多佛观念的逻辑结果,但只有在这一转变发生后,菩萨概念才能成为一个可被他人效仿的理想。
3.4 对弥勒的授记
根据《说本经》,佛陀乔达摩在回答这位比丘的愿心时所作的授记如下:
“弥勒,在遥远的未来,当人寿八万岁时,你将成为一位名为弥勒如来的佛陀,无执着,圆满觉悟,具足明行、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众祐——正如我现在是如来……众祐。
在这个世界,包括其天人、魔罗、梵天、沙门与婆罗门,从人到天人,你将自行了悟,自行证得而住——正如我现在在这个世界……自行了悟,自行证得而住。
你将教导初善、中善、后善之法,具足义理与措辞,揭示一个具足清净的梵行——正如我现在教导……
你将广泛传播梵行,向无数广大会众,从人到天人,善加揭示——正如我现在广泛传播梵行……
你将拥有无数百千的比丘僧团——正如我现在拥有无数百千的比丘僧团。”
在上述翻译的部分,未来佛弥勒的每一种品质,都在现世佛陀指出他现在也拥有同样品质时重现。除了这种内部的重复——它强调了未来佛弥勒将拥有现世佛陀乔达摩所具备的所有品质与成就——上述全文还出现了四次(伴随着在“将会有”、“我将是”和“你将会是”等表达方式之间的适当变化):
- 首先,佛陀描述了未来佛弥勒,
- 然后,弥勒比丘发愿成为未来佛,
- 接着,佛陀引述了弥勒所发的愿心,
- 最后,佛陀授记弥勒未来的佛果。
也就是说,上述段落中涉及的基本主题,连续八次被提请听众注意。即使对于习惯于将重复视为早期佛教经典一个特征的人来说,这也通过反复确认与加强,传达了相当程度的强调。
很明显,我们无法确定《说本-本生经》及其对应版本是否是授记观念产生的历史首例。然而,鉴于这似乎是早期经典文本库中唯一一例此类授记,探讨这对双胞胎经文可能是这一观念产生的见证,似乎是合理的,至少在能够找到这一观念更早出现的证据——无论是铭文、文本还是图像——之前是如此。
如果佛陀向菩萨授记的观念确实源于我们现在所见的《说本经》及其对应版本中的文本,那么问题便是,当前这个例子是否为这一观念的产生提供了任何理据。
现在,上述宣告所蕴含的核心讯息,围绕着三皈依展开。它始于对佛陀品质的标准列举,这在其他经典中用于忆念佛陀;接着确认了自力证悟,这是使某人成为佛陀的品质。接下来,段落用另一组标准的美称来描述法,然后转向弟子僧团,特别强调了广大的比丘追随者。
这些主题,在《长部》与《长阿含》的《转轮王经》中对未来佛弥勒的描述中,已是其一部分。然而,在《说本经》及其对应版本中,这些相同的主题变得更为具体和生动。这一方面是通过两位将在未来这个理想国度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比丘的主动介入而实现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相同的信息,这在经文的口头表演情境中,必定会对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段经文的要旨,似乎与我在研究第一章中提到的一点有关:信众在佛陀涅槃后,需要以某种方式与三皈依,尤其是第一皈依处——佛陀——建立直接的联系。在上述段落的背后,同样的需求也显现出来,反映在对未来一个所有三皈依都可再次遇到的时代的描述中。在一个辉煌的转轮王统治时期,将会有另一位佛陀,具足与乔达摩佛相同的品质。这位未来佛将向广大会众说法——在一个乔达摩佛已成为遥远记忆,其弟子们在与其他宗教团体的竞争中艰难维持传承的时代,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振奋的前景。
除了对未来佛降临的保证,佛陀乔达摩所作的授记,也确立了弥勒作为一位菩萨的地位,尽管“菩萨”一词本身并未被使用。这意味着他成了诸佛传承的一部分,并因此共享他们的品质。因此,在他最后一世出生时,他将具足《未曾有法经》归于新生乔达摩的同样优越品质,共享所有即将成佛者的法性(dharmatā)。作为同一模式的一部分,他也会在成佛前,如所有佛陀的常规一样,降生并居住于兜率天。
也就是说,除了对弥勒佛降临的明确承诺外,对弥勒未来成佛的预言背后,也隐含着对菩萨弥勒将居于兜率天的保证。因此,现存的这段经文已包含了弥勒两个方面的萌芽:未来的佛陀与现居兜率天的菩萨。这相当有效地填补了佛陀涅槃所造成的真空。
总而言之,《说本经》中上述翻译段落的主要目的,似乎与两部《未曾有法经》相似,即每部经都旨在满足信众在导师涅槃后,为弥补领导与灵感之失而寻求补偿的需求。《未曾有法经》通过培养对已逝佛陀品质的敬畏感来做到这一点。《说本经》则更直接地处理了导师消失的困境,通过为已逝的乔达摩提供一个替代者:菩萨弥勒,他将通过成为下一位圆满觉悟的佛陀,来延续诸佛的传承。
其潜在的信息是对连续性的保证。这样的保证,对于那些现在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或许正是因为缺乏佛陀的指导——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它向他们保证无需绝望,因为有另一位准备好帮助需要援助的人。结尾处魔罗登场的情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发愿亲近弥勒的目的,不应是为了享乐,而应是为了迈向觉悟。
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本经》中上述引文的重复次数——通过发愿比丘的介入及佛陀随后的授记这一叙事框架实现——似乎主要是在口头情境中,加强保证信息的冲击力。上述段落的第四次重复,采取了佛陀授记以确认一位菩萨未来成佛愿心的实际形式,这似乎并非经文的核心,实际上,发愿成为未来转轮王的比丘也获得了同样类型的授记,即他的愿心将成功。核心要点似乎是通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预言,来为听众提供鼓励与 reassurance。
因此,对菩萨未来成佛的授记,可能是该经主要目的的一个副产品。如果当前这个例子确实是授记观念产生的最初契机——这至少是可能的——那么《说本经》中关于弥勒佛的故事,其效果将与乔达摩与最后一位佛陀迦叶佛相遇的故事相似,后者很可能促成了菩萨立下成佛誓愿这一观念的产生。
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关系,在众多弥勒传说版本中的一个版本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优波离(Upāli)向佛陀询问那位被授记为未来佛弥勒的比丘。在他的询问中,优波离表达了他的困惑,即这位比丘既不修习禅定,也不断除烦恼。这让人想起了菩萨乔达摩作为过去佛迦叶佛座下比丘弟子时期的故事所蕴含的问题,而《中阿含·未曾有法经》通过他在那时立下成佛誓愿的观念,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迄今所考察的元素基础上,《增一阿含经》中的经文完成了这幅图景。两部《增一阿含》的经文记载,佛陀将明确被介绍为菩萨的弥勒,作为比丘们的榜样,他们应效仿他的精进。同一集中的另一部经则记载,菩萨弥勒如何向佛陀请教菩萨道,特别是关于修习六波罗蜜(pāramitā)的问题。
总结
对《转轮王经》现存三个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最早的正典中提及未来佛弥勒降临的记载,是后来增补到一个原本具有譬喻功能的叙事中的。
一个更为详尽的关于未来佛弥勒降临的版本,见于《中阿含·说本经》,其中记载佛陀乔达摩向一位发愿成为未来佛弥勒的比丘授记,保证他未来的成功。伴随这一授记,菩萨理想起源的另一个重要元素便应运而生。
结论
我探究的起点,是那些描述乔达摩从出家到成佛期间的段落,其中将乔达摩描绘成一位寻求觉悟的菩萨。随着《未曾有法经》对希有事迹的阐述,佛陀觉悟的品质被与他出生之时联系在了一起。这一希有事迹反映了菩萨概念向着代表一位注定证得觉悟的存在的方向转变。随着《大本经》及其对应版本的出现,菩萨乔达摩的希有事迹成了普遍意义上菩萨的常态,从而引入了注定觉悟的菩萨这一通用概念。
乔达摩前世与过去佛相遇的不甚鼓舞人心的正典记载所引起的问题,在《中阿含·未曾有法经》中通过一个巧妙的观念得到了解决,即菩萨在相遇之时立下成佛的誓愿。
未来佛的降临,则可能引出了向发愿成为下一位佛陀者授记的观念,这一发展反映在《中阿含·说本经》中。
伴随这些思想脉络——菩萨的通用概念、菩萨注定证得觉悟的观念、菩萨立下成佛誓愿的观念,以及菩萨从过去佛那里获得授记——菩萨理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似乎已各就各位。
在这些似乎促成了菩萨理想起源的各种发展脉络背后,一个核心因素似乎是佛陀的逐步神化,这一点在早期经典中已显而易见。这种尊崇佛陀的倾向,应是他涅槃所造成的真空的自然结果,体现在对他希有事迹及其前后传承者的日益关注中。
有研究指出,《大智度论》中提及了“尼柯耶佛教中出家的菩萨,他们像声闻(śrāvaka)一样,遵循尼柯耶佛教所传的著作来修行菩萨道”。类似的迹象也可以在《八千颂般若经》(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中找到。这一发现可能指向了上述发展所带来的实际结果,即菩萨们基于早期经典提供的框架进行修行。
以早期经典为起点,也相当自然地解释了为何菩萨理想成为一个泛佛教现象,吸引了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佛教部派的追随者,包括上座部传统。有学者解释说:
“现存的十八部派经典都允许三种选择:成为阿罗汉、独觉佛或佛陀,并据此修行,这是个人的决定。也就是说,十八或四个部派都包含了三乘(yāna)。在某个不确定的时期,比如说公元前一世纪,一些比丘、比丘尼与在家信众开始专修菩萨乘。最终,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此乘提升到主张其他所有人都应如此的程度。对他们而言,菩萨乘成了大乘(Mahāyāna)。”
与大乘的模糊起源相似,关于菩萨理想确切形成方式的确定性,可能仍将难以捉摸,尤其是因为我们用于研究佛教最早时期的资料,主要是经过长期口头传承后最终成型的文本记录。然而,我希望我对早期经典中相关材料的考察,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引出一个关于菩萨理想起源可能如何形成的可行假说,为进一步的讨论与研究提供起点,以修正和完善我的发现与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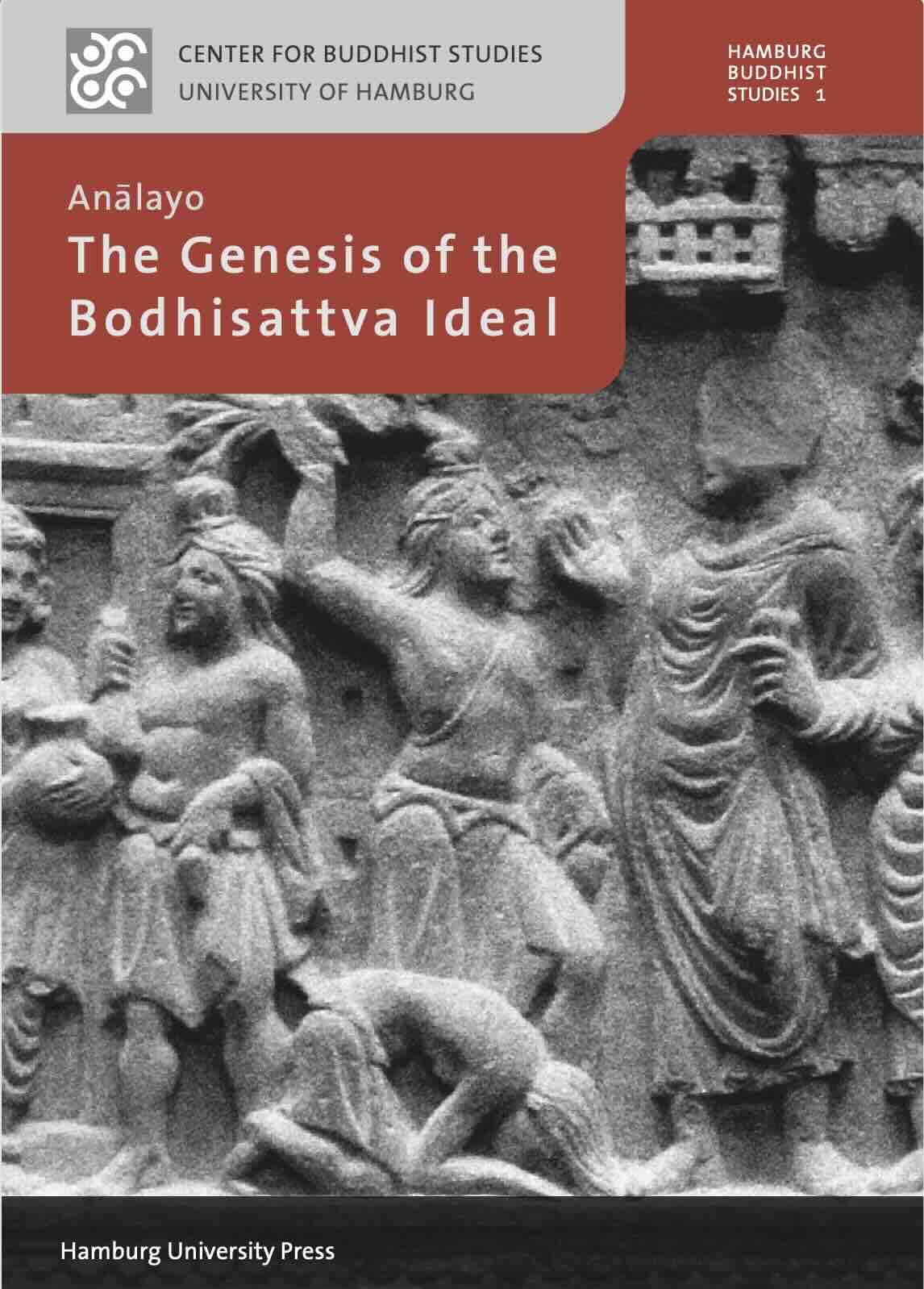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