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之心:从香烟、智能手机到爱情,我们为何会沉迷,又该如何戒断
成瘾与戒断, 心理学, 正念, 精选 ·Index
The Craving Mind: From Cigarettes to Smartphones to Love - Why We Get Hooked and How We Can Break Bad Habits - Judson Brewer
成瘾之心:从香烟、智能手机到爱情,我们为何会沉迷,又该如何戒断 - 贾德森·布鲁尔 - 摘要
一位精神科医生兼神经科学家,揭示了从香烟到智能手机等各种成瘾行为背后共同的大脑机制,并提供了基于正念的强大方法来打破这些坏习惯。
前言 - 乔恩·卡巴金
我们每个人的头颅内,都装着宇宙中已知最复杂的物质组织——人类大脑。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然而,尽管拥有如此精妙的“装备”,我们却常常陷入坏习惯、抑郁和焦虑的泥潭,渴望通过外界事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永无止境的渴求本身就是一个幻象,因为我们生来本自具足。
这本书正是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回归完整的道路。作者贾德森·布鲁尔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也是一位长期的正念禅修者。他巧妙地将西方心理学与古老的佛学智慧结合起来。
从西方心理学角度,我们了解了B.F.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行为如何通过“奖励”被强化。但这个理论过于行为主义,忽视了意识和内在觉知的重要作用。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布鲁尔引入了佛学中心教义——“缘起”——的框架,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如何通过正念,从“渴求之心”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其核心,恰恰是培养一种与“渴求”亲密共处的能力。这需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自己是多么深地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中,并学会用正念去回应,而非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
近期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当我们什么都不做时,大脑会进入一个被称为“默认模式网络”(DMN)的状态,这时我们的大脑主要在进行关于“我”的叙事——我的过去、我的未来、我的成败。而正念训练恰恰可以降低这个“叙事网络”的活动,同时增强与“当下觉知”相关的“体验网络”的活动。
布鲁尔博士的实验室开发了新颖的实时神经反馈技术。在实验中,当参与者在冥想时越是努力“尝试”去达到某种状态,他们大脑中DMN的关键区域——后扣带皮层(PCC)——的活动反而越强。而当他们放弃努力,只是纯粹地安住于当下时,这个区域的活动就会减弱。
这有力地证明了“无为”、“不强求”的力量。
这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打破思维习惯。它并非依靠意志力或强迫,而是通过真正地安住于“存在”本身,与纯粹的觉知空间变得亲密,并发现它就在我们称之为“当下”的这个永恒瞬间里。
毫无疑问,渴求的习惯是我们大部分痛苦的根源。但好消息是,一旦我们亲身认识到这一点,便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中解脱,过上更健康、更有创造力、更真实的生活。现在正是开始实践书中方法的最佳时机,愿它能引领你,走向摆脱“渴求之心”无尽束缚的自由之路。
自序
我人生的转折点,始于大学时期的肠胃问题和随后因分手而来的失眠。医生说这是压力所致,但我当时无法接受——我坚持运动、健康饮食,怎么会有压力?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自己患上的是典型的“肠易激综合征”(IBS),一种由心理因素引发的生理疾病。
正是这个经历,让我对“身心关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选择攻读医学和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希望揭开压力如何影响我们身体的秘密。然而,即便进入了医学院,我的压力和失眠依旧。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乔恩·卡巴金的《正念疗愈力》(Full Catastrophe Living),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开始全身心投入正念练习。每天早晨冥想,在枯燥的课堂上冥想,参加禅修营。我逐渐看到自己压力的来源,以及我是如何不自觉地加剧了这些压力。我开始发现古老的佛学教义与现代科学发现之间的惊人联系。
八年后,我选择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了古今心理学模型在解释行为,尤其是成瘾行为上的共通之处。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在个人、临床和科学三个层面进行探索。我将研究重点从分子生物学转向了正念——它如何影响大脑,又如何帮助改善精神疾病。
我的所有观察,无论是来自科学实验、临床患者,还是我自己的内心,都指向一个基于进化论的简单学习过程。这个过程本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祖先更好地生存,但在现代社会,它却被“劫持”,强化了从分心、压力到成瘾等一系列广泛的行为。
本书旨在将最新的科学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和临床案例。它揭示了这个本有益于进化的学习过程,是如何在现代文化(尤其是科技)的影响下被扭曲或利用的。更重要的是,本书将提供简单、实用的方法,帮助我们所有人靶向这些核心机制,从而摆脱不良的成瘾习惯,减轻压力,或者仅仅是活出更丰满的人生。
引言
人类的学习机制,在最根本的层面,与只有两万个神经元的海蛞蝓,甚至单细胞生物,都惊人地相似。它们都遵循着一个简单的生存法则:趋向营养,远离毒素。我们大量复杂的行为,是否也源于这种趋利避害的深层模式?
上瘾的机制
当我们沉迷于手机游戏或冰淇淋时,我们正在利用一个进化史上最古老的学习过程。这个基于奖赏的学习过程非常简单:
- 触发(Trigger):看到看起来美味的食物。
- 行为(Behavior):吃掉它。
- 奖赏(Reward):感觉很好(大脑分泌多巴胺),身体向大脑发送信号:“记住你吃的是什么,以及在哪里找到的。”
这个“触发-行为-奖赏”的循环,帮助我们的祖先记住食物来源以求生存。但我们富有创造力的大脑很快发现,这个机制可以用于更广泛的场景。比如,当你感觉糟糕时,大脑会建议:“为什么不试试吃点好吃的让你感觉好一些?”于是,我们学会了在悲伤或愤怒时吃巧克力,用同样的方式,只是触发点从“饥饿信号”变成了“负面情绪信号”。
同样,青少年时期为了“看起来很酷”而吸烟,也遵循同样的模式。每一次重复这个行为,大脑中的这条神经通路就会被强化,最终形成一个习惯回路。慢慢地,我们从为了生存而学习,变成了用这些习惯来伤害自己。肥胖和吸烟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几个可预防的致死原因。
从海蛞蝓到人类社会
这个学习过程最早由爱德华·桑代克在19世纪末通过动物实验阐明。到了20世纪中叶,B.F.斯金纳通过他著名的“斯金纳箱”实验,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观察,并将其发展为“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即我们所说的基于奖赏的学习。
斯金纳坚信,人类的许多行为都可以用这个过程来解释。他甚至在小说《桃源二村》(Walden Two)中构想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从出生起就通过“行为工程学”(即基于奖赏的学习)被塑造成和谐共处的公民。
这个过程的核心在于,它会塑造我们的主观偏见。一种行为重复得越多,我们就越习惯于通过特定的“滤镜”来看世界。比如,我们习惯了吃巧克力带来的愉悦,下次就会倾向于选择它。久而久之,我们甚至会忘记自己戴着这副“巧克力很好吃”的滤镜,它成了我们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真理”。这种偏见会从食物偏好延伸到社会观念和个人信仰,让我们不假思索地做出“膝跳反射”式的反应。
正念如何提供帮助?
当我们试图用同样的老办法去解决问题,却发现情况越来越糟时,或许我们应该停下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假设和偏见。这时,正念就能派上用场。
正念,正如乔恩·卡巴金所定义的,是“有意识地、不加评判地,将注意力保持在当下而升起的觉知”。它就像一张地图和一枚指南针,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荒野中导航。
- 指南针: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或“不适感”,就是我们的指南针。通过仔细观察压力在身体上的真实感受,我们可以校准方向,知道什么是“向南”(趋向压力),什么是“向北”(远离压力)。
- 地图:正念本身就是地图。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主观偏见是如何让我们在原地打转的。这种不加评判的觉知,意味着我们不再基于过去的经验自动地趋利避害,而是如实地观察。
当我们迷失在森林里时,本能是惊慌地乱跑,结果只会更迷路。正确的做法是停下来,深呼吸,拿出地图和指南针。同样,正念教会我们在被习惯和情绪裹挟时,停下来,看清楚正在发生什么,而不是盲目地做出反应。
通过结合古代佛学的智慧和现代神经科学的发现,本书将探索正念如何帮助我们看透自己后天习得的联想、主观偏见和由此产生的自动化反应。我们将学会利用压力这个指南针,无论是对配偶大吼大叫,还是因无聊而刷手机,甚至是在成瘾的深渊中,都能找到重新校准方向、回归人性的道路。
第一部分:多巴胺的冲击
第一章:成瘾,直截了当
当我们抓挠伤口、屈服于瘾头时,我们不允许伤口愈合。但当我们去体验伤口那原始的痒或痛,而不去抓挠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让伤口愈合。——佩玛·丘卓
作为一名专攻成瘾精神病学的医生,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成瘾者。成瘾最直接的定义是:不顾不良后果的持续使用。无论是尼古丁、酒精还是赌博,当某个行为已经对你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而你却停不下来,这就构成了成瘾。
我的许多患者,尤其是退伍军人,他们的成瘾故事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模式:触发(如创伤闪回)、行为(如酗酒)、奖赏(比重温创伤的体验要好)。这个习惯回路一旦建立,就会不断重复。他们用物质来“自我疗愈”,麻痹身体的疼痛,或逃避情感的创伤。
为什么戒烟这么难?
许多能戒掉海洛因或可卡因的“硬核”成瘾者,却对我抱怨说戒不掉烟。这背后有几个原因:
- 尼古丁是兴奋剂,不影响认知能力,可以随时随地吸。
- 可以高频重复,一天一包烟意味着这个习惯回路被强化了20次。
- 社会接受度高,不会因此被解雇。
- 危害滞后,吸烟的严重后果要几十年后才显现,而大脑的奖赏机制只关心眼前的满足。
- 吸收迅速,肺部巨大的毛细血管表面积使尼古丁能闪电般进入血液,快速释放多巴胺,强化成瘾。
一位病人对我说,他感觉不抽烟脑袋就要爆炸了。我没有直接给他建议,而是在白板上为他画出了他的习惯回路:触发 -> 吸烟 -> 感觉舒缓。然后我问他,在不能吸烟的情况下(如飞机上),那种“脑袋要爆炸”的感觉后来怎么样了?他想了想说:“好像就自己消失了。”
我随即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倒U形曲线,向他展示:渴望就像波浪,它会升起、达到顶峰,然后自行消退。每一次他选择吸烟,都是在强化“吸烟能解决问题”这个回路。而如果他能像冲浪一样,“驾驭”这股渴望的浪潮,看着它起落,那么每一次成功驾驭,都是在削弱这个旧习惯。
正念戒烟法:RAIN
为了更好地理解并帮助我的病人,我决定将我的正念练习应用于临床。我设计了一项研究,将正念训练与美国肺脏协会的“戒烟自由”这个金标准疗法进行对比。为了能真正共情我的病人,我这个从不吸烟的人,开始练习静坐两小时不动——这让我亲身体验了那种坐立不安、仿佛脑袋要爆炸的强烈渴望。
在正念小组里,我首先教大家识别自己的习惯回路。第一堂课后,我让他们回家只做一件事:带着好奇心去真正“品尝”每一支烟。许多人回来后震惊地分享:“闻起来像臭奶酪,尝起来像化学品,太恶心了!”
这个体验是关键。他们从头脑层面的“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转变为身体层面的“智慧”——吸烟的体验本身是糟糕的。这种发自内心的“醒悟”(disenchantment),让他们不再需要靠意志力去“对抗”吸烟,而是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对它的兴趣。
接着,我教他们一个名为RAIN的练习,来“冲浪”那些渴望的浪潮:
- Recognize/Relax(识别/放松):识别出渴望正在升起,并放松地面对它。
- Accept/Allow(接纳/允许):接纳它的存在,不试图推开或分心。
- Investigate(探查):带着好奇心探查身体的感觉、情绪和念头(“我的身体现在是什么感觉?”)。
- Note(标记):简单地标记当下最显著的体验(如:紧绷、灼热、念头)。
研究结果远超我的预期:正念组的戒断率是金标准疗法的两倍,并且长期维持率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所有正念练习中,RAIN练习是打破“渴望-吸烟”这个链接的最强预测因子。有趣的是,戒烟成功者和未成功者在训练结束时报告的渴望强度相似,区别在于前者学会了与渴望共存而不付诸行动。
古代智慧与现代科学的交汇
这个发现与古老的佛学心理学不谋而合。佛陀教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缘起”(Dependent Origination),它描述了一个由十二个环节组成的因果循环,解释了痛苦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模型与现代心理学的“基于奖赏的学习”惊人地一致。
- 现代模型:触发 -> 行为 -> 奖赏
- 缘起模型(简化版):感官接触 -> 感受(愉快/不愉快) -> 渴爱 -> 执取(行为) -> 生成(新的习惯/自我认同)-> 轮回(痛苦的循环)
两者都指出了一个核心机制:我们基于过去的经验(佛学称之为“无明”,现代心理学称之为主观偏见),对当下的体验产生愉快或不愉快的感受,这引发了“想要”或“不想要”的渴望,驱动我们行动,从而不断强化旧有的习惯,让我们在痛苦中无尽地循环。
原来,佛陀在2500年前就已经“剧透”了斯金纳的发现。而正念,正是看清并走出这个循环的古老智慧。它不是用蛮力去对抗,而是用一种近乎反直觉的方式——带着好奇心转向它、了解它,从而自然地放下它。
第二章:沉迷于科技
科技与奴隶制的区别在于,奴隶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自由。——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2014年,我在巴黎卢浮宫看到一幕:两个女人兴高采烈地用自拍杆合影,而其中一位的男友则百无聊赖地站在一旁,仿佛被一根铝合金杆取代了。自拍,这个看似无伤大雅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成瘾机制。
自拍中的“自我”奖赏
想象一下那个叫丹妮尔的女孩:她在卢浮宫拍了张自拍并上传到脸书。很快,她开始忍不住一遍遍地查看手机,计算收到了多少“赞”和评论。她的大脑正在经历一个经典的奖赏学习循环:
- 触发:想要分享我在卢浮宫的时刻/渴望被关注。
- 行为:发布自拍。
- 奖赏:收到“赞”,感觉良好。
每一次收到“赞”,多巴胺系统都会被激活,强化了这个行为。久而久之,她不仅在感觉良好时发帖,也会在感觉糟糕时寻求这种虚拟的肯定,以此来排解负面情绪。这就是从正强化(为了获得愉悦)到负强化(为了消除不快)的转变,是成瘾加深的关键一步。
我们为何对“自我”如此着迷?
神经科学研究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甚至愿意放弃金钱,只为了有机会谈论自己。在实验中,当参与者谈论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时,大脑中一个与成瘾密切相关的区域——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会被激活。这表明,谈论自我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奖赏。
另一项研究发现,伏隔核对“自我相关反馈”的活跃程度,可以预测一个人脸书的使用强度。也就是说,你的大脑从“被点赞”中获得的奖赏感越强,你就越可能沉迷于社交媒体。
从进化的角度看,这种对“自我”和“他人反馈”的关注,可能与社会性生存有关。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说,同伴的认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重要吗?”“我是否被群体接纳?”这些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巨大的压力。而社交媒体上的“赞”提供了一种清晰、量化的即时反馈,暂时缓解了这种生存焦虑。
脸书成瘾症
社交媒体之所以如此容易让人上瘾,是因为它完美地利用了我们的学习机制:
- 低门槛:随时随地,一键分享。
- 异步性:可以精心编辑、挑选照片,以最大化获得“赞”的可能性。
- 不确定性:你永远不知道何时会收到“赞”或评论。这种间歇性强化(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是赌场老虎机使用的最强大的成瘾策略,它让我们欲罢不能,持续期待。
研究表明,那些在现实社交中感到焦虑或缺乏自信的人,更容易过度使用脸书来寻求社会认同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项研究发现,越是依赖在线社交互动来调节情绪,人们的自我价值感越低,现实中的社交退缩也越严重。人们上网寻求连接,最终却感觉更孤独。
另一个问题是,社交媒体成了“他人精彩生活集锦”的展示平台。当我们看到别人完美的假期、幸福的家庭时,很容易与自己平凡甚至糟糕的当下形成对比,从而感到沮丧。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感觉糟糕 -> 上脸书寻求慰藉 -> 看到别人的精彩生活,感觉更糟。
被误解的快乐
缅甸禅师班迪达长老曾说:“在寻求快乐的过程中,人们将头脑的兴奋误认为真正的快乐。”
多巴胺的释放,本是为了让我们记住食物来源的生存机制,它带来的是一种“兴奋”和“想要更多”的渴求感。而我们却把它等同于“幸福”。广告不断告诉我们,买了这辆车、用了那款护肤品,你就会快乐。这利用了我们的奖赏回路,但这种兴奋是短暂的,它并不能解决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
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都可能在不经意间按下了多巴胺的杠杆,以为这就是快乐。我们可能正在用错误的指南针导航,将自己引向压力的深渊。现在是时候停下来,仔细观察:这种由科技带来的即时满足,在我们身体和心灵上究竟是什么感觉?它真的让我们更快乐吗?还是只是让我们更渴求?
第三章:沉迷于自我
自我,那个他一直信以为真的自己,不过是一系列习惯的模式。——阿兰·瓦茨
我曾经是兰斯·阿姆斯特朗的狂热粉丝。他战胜癌症、七次赢得环法自行车赛的传奇故事深深地激励了我。我将他视为美国梦的完美化身,一个只要努力就能实现任何目标的榜-样。因此,当他被指控使用禁药时,我本能地、激烈地为他辩护,拒绝相信任何负面证据。
我的大脑被一种强烈的主观偏见所蒙蔽。我戴着“兰斯是英雄”的滤镜,不断地进行各种心理模拟来否定那些证据,以维护我内心的故事。直到他在奥普拉的访谈中亲口承认,我的“滤镜”才被彻底击碎。那一刻,我才清醒过来,我对兰斯故事的“瘾”也随之戒断。
这个经历让我深刻地理解了我们是如何沉迷于自己的故事和观念的。
两个“自我”
我们的大脑中存在着两种与“自我”相关的模式:
- 自我 #1:模拟器(The Simulator) 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心理模拟,以预测未来的结果,帮助我们做出决策。比如开车时判断是否能安全变道,或决定是否参加一个派对。这是一种强大的进化优势。然而,当我们的模拟被主观偏见(我们希望世界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它实际是什么样子)所扭曲时,就会出问题。就像我相信自己能考上普林斯顿,却无视自己远低于平均分的SAT成绩一样,这种模拟只会让我们偏离现实。我对阿姆斯特朗的盲目崇拜,就是让心理模拟器在错误的轨道上疯狂运转,直到撞上现实的墙壁。
- 自我 #2:电影主角(The Superstar of the Movie: Me!) 我们在第二章看到,谈论自我本身就是一种奖赏。这种奖赏机制让我们倾向于构建并维护一个关于“我”的叙事,让自己成为生活这部电影的绝对主角。这个“自我”的形象是通过重复和强化建立起来的。比如,小时候考了好成绩,得到父母的夸奖(奖赏),我们就学会了通过努力学习来不断获得这种奖赏,并逐渐内化了“我是个聪明人”的自我认同。久而久之,这种自我观念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病态的人格:奖赏学习的两个极端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人格障碍的极端例子,来更好地理解“自我”是如何被奖赏学习塑造的。
- 自恋型人格障碍(NPD):可以看作是“我是个聪明人”这个奖赏回路失控的版本。这类人极度渴望他人的赞扬和关注,他们的自我价值完全建立在外界的肯定之上。这可能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获得了过多、不当的奖赏,而缺乏必要的纠正性惩罚,导致他们对“赞美”这种奖赏产生了病态的渴求。
- 边缘型人格障碍(BPD):则可以看作是在一个不可预测的、间歇性强化的环境中成长的结果。他们的父母时而关爱,时而虐待,就像一台老虎机,让他们无法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自我认知。因此,他们一生都在不自觉地“测试”人际关系的底线,试图通过制造各种“危机”来获得关注和关爱,哪怕是负面的。他们不断地重复这个行为,因为不确定的奖赏(偶尔得到的回应)会形成最难以戒除的瘾。
通过理解边缘型人格障碍背后的奖赏学习机制,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帮助我的病人。我不再简单地“守住底线”,而是帮助他们看到这种不稳定的行为模式是如何伤害自己的。通过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测的治疗环境(比如严格遵守约定的时间),我帮助他们开始学习建立一种新的、更健康的互动模式。
回到中间地带
我们每个人都在“自恋”和“缺乏自我”这个光谱的某个位置上。了解心理模拟和主观偏见是如何运作的,可以帮助我们觉察并挑战自己固有的自我观念。
我们可以开始练习观察:当别人奉承我时,我身体的感觉是什么?那是一种开放的喜悦,还是一种收缩的兴奋?我是否在不自觉地助长他人的自大,最终却让自己受累?
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所说:“我们觉得自己很棒,不代表我们真的那么棒。”开始留意我们是如何被“自我”这个故事所牵引的,是摆脱这种最深层瘾的第一步。我们可以练习带着觉知,在心中竖起一个警示牌:“警告!请勿投喂自我。”
第四章:沉迷于分心
大规模分心的巧妙噱头,造就了一群沉迷、自我麻痹的自恋者。——康奈尔·韦斯特
你是否曾在等红灯时,看到周围车里的人都低着头,脸上泛着手机屏幕的蓝光?你是否曾在工作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查看邮件的冲动所打断?
我们可以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关于物质使用障碍的诊断标准来测一下自己的手机使用情况,只需将“物质”替换为“手机使用”。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符合“轻度”甚至“中度”成瘾的标准。
这种分心并非无害。数据显示,自2007年iPhone问世以来,五岁以下儿童的非致命伤害率出现了显著上升,这与智能手机3G网络的覆盖率增长呈正相关。这暗示了父母在看护时因手机分心,导致了更多儿童意外的发生。
我们是如何变得如此分心的?
这与我们大脑的奖赏学习机制密切相关,尤其是多巴胺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神经科学家沃尔夫拉姆·舒尔茨的著名实验表明:
- 多巴胺不仅在获得奖赏时释放,更在“预期”到奖赏时释放。闻到饼干的香味,我们的多巴胺神经元就开始活跃,这促使我们去寻找饼干。
- 多巴胺对“意外”的奖赏反应最强烈。一个出乎意料的奖赏(比如第一次考了A+得到父母的惊喜夸奖)会引发最强的多巴胺释放,从而最有力地固化一个行为。
现代科技完美地利用了这两点:
- 新闻标题:像“为什么普京称赞特朗普?”这样的“标题党”,就是利用了我们的预期心理,激发我们的好奇心,诱使我们点击。
- 邮件和短信提醒:每一次不可预测的“叮咚”声,都像是一次意外的刺激,让大脑释放少量多巴胺。这种间歇性强化,正是赌场老虎机让人上瘾的秘诀。我们为了“更高效”而开启的推送通知,实际上是在把自己训练成巴甫洛夫的狗。
胡思乱想的失控
我们大脑的“模拟器”功能,在分心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常见的形式就是白日梦。哈佛大学的一项大规模研究,通过手机应用随机调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 人们在将近50%的清醒时间里,头脑都在胡思乱想(mind-wandering)。
- 一个普遍的规律是:“一个胡思乱想的大脑,是一个不快乐的大脑。”
即使是幻想愉快的假期,其带来的快乐程度也仅仅与专注于手头任务时持平。而当我们考虑到所有中性和负面的胡思乱想时,总体的幸福感就会显著下降。我们不仅在不必要的担忧或兴奋中消耗能量,还错过了眼前真实的生活,比如孩子在足球场上的第一个进球。
老式的自控力(管用吗?)
面对分心的诱惑,我们通常的武器是“认知控制”——用理智来控制行为。这对应于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系统2”思维,即我们大脑中那个更进化、更理性、更缓慢的部分(就像《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先生)。而我们冲动的、情绪化的、快速反应的部分,则是“系统1”。
问题在于,系统2是脆弱的。耶鲁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艾米·阿恩斯滕指出:“即使是相当轻微的、无法控制的急性压力,也会导致前额叶皮层认知能力的迅速而显著的丧失。”
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称之为“自我耗竭”(ego depletion)。我们的自控力就像油箱里的汽油,是有限的。每抵制一次诱惑,就会消耗一些。当油箱空了,我们就失去了控制。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疲惫或压力大的一天结束后,我们更容易屈服于诱惑,吃掉一整桶冰淇淋,或是在社交媒体上浪费数小时。
研究发现,在所有日常诱惑中,使用社交媒体的欲望是最难抵抗的。
那么,如果连自控力都靠不住,我们还有希望吗?答案在于,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不是去“对抗”分心,而是去理解并转化它。我们需要看清分心这个行为背后真正的“奖赏”是什么,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真实感受。当我们不再需要靠“油箱里的汽油”去硬撑时,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第五章:沉迷于思考
最大的瘾之一,是你永远不会在报纸上读到的,因为沉迷于此的人自己都不知道——那就是对思考的瘾。——埃克哈特·托利
在学习冥想的初期,我被告知要“观呼吸”,当心念游走时,再把它拉回来。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在一次禅修中,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念头的激烈搏斗。我越是想控制思想,它们就越是汹涌。汗水浸透了我的T恤,我感到精疲力竭。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正与自己最深的瘾之一作斗争——沉迷于思考。从小到大,我一直因“善于思考”而备受奖赏:解决复杂的化学难题、在医学院的“拷问”中对答如流、发表学术论文……每一次智力上的胜利,都伴随着强烈的愉悦感。我的大脑已经习惯了这种由思考带来的奖赏。现在,我却试图让它停下来,这无异于让一艘全速航行的巨轮立刻抛锚。
思考本身不是问题
思考、记忆、规划,这些都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工具。多巴胺帮助我们记住那些重要的时刻,无论是爱人的眼神,还是攻克科研难题后的喜悦。
问题不在于思考,而在于“被思考所困”(getting caught up in it)。
奥林匹克跨栏运动员洛洛·琼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决赛中,一路领先,眼看金牌在望。但在第九个栏架前,一个念头闪过:“我要确保我的腿伸直。”她开始“过度尝试”,身体随之紧绷,最终失误,与金牌失之交臂。她被自己的念头绊倒了。
这种“被困住”的感觉,在身体和心理上通常表现为一种收缩、紧绷或执取。当我们与同事争论一个想法被否定后,可能会感到肩膀僵硬,并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反复咀嚼这次不快的经历。这种“反刍式思维”(ruminative response styles),即被动地、重复地思考负面情绪,已被证明与抑郁症的加重和持续密切相关。
有趣的是,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甚至会主动选择观看悲伤的图片或聆听悲伤的音乐。这似乎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悲伤的感觉,这种感觉验证了他们的“自我”——“对,我就是那个抑郁的人”。他们被自己的思维模式所“瘾住”了。
我们的大脑默认模式
神经科学为这种“被困住”的状态提供了生理学上的解释。当我们心不在焉、做白日梦或进行与自我相关的思考时,大脑中一个被称为“默认模式网络”(DMN)的区域会变得异常活跃。这个网络的核心是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后扣带皮层(PCC),可以被看作是“自我网络”或“‘我’的网络”。
我的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比较了新手和资深冥想者的大脑活动。我们惊奇地发现,在冥想时,资深冥想者大脑中唯一显著不同的地方,不是某个区域变得“更活跃”,而是DMN的核心区域(尤其是PCC)变得“更安静”。
为了进一步探究,我们开发了实时神经反馈技术,让冥想者可以在扫描仪里实时看到自己PCC的活动图表。实验结果非常清晰:
- 当人们分心、走神或进行自我评价(比如“哦,我做得真好!”)时,PCC活动上升。
- 当人们专注于呼吸时,PCC活动下降。
- 最关键的发现是:当人们“努力尝试”或“试图控制”自己的体验时,PCC活动会上升;而当他们以一种“毫不费力的”(effortless doing)或“顺其自然”的态度安住于当下时,PCC活动会显著下降。
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如何与自己的体验“相关联”,比体验的内容本身更重要。一个念头只是一个念头,直到我们抓住它、认同它、被它钩住,它才成为问题。一个渴望也只是一个渴望,直到我们被它卷入。
PCC可能是我们大脑中将“自我”与体验捆绑在一起的关键节点。当我们被一个想法或一种情绪“钩住”时,我们会感到一种收缩感,仿佛“我”在思考,“我”在渴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与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建立了强烈的认同关系,形成了“自我”的习惯。
而冥想的训练,正是在学习观察这些体验,而不被它们钩住——只是看着它们来来去去,不把它们当成“我”或“我的”。这对应着DMN的平息。我们的大脑数据填补了关键的一环:我们如何与自己的念头、感觉和行为产生关联,决定了我们是自由还是被囚禁。
第六章:沉迷于爱情
爱情如死亡般坚固,激情如坟墓般残酷。它闪烁如火焰,是熊熊燃烧的烈焰。——《圣经·雅歌》8:6
斯坦福大学曾举办过一场别开生面的“爱情竞赛”,用fMRI扫描仪来测量人们在五分钟内“尽其所能去爱一个人”时,大脑奖赏中心的活跃程度。他们为什么要把爱情和与可卡因、海洛因相关的脑区联系起来?
我的化学罗曼史
大学毕业前夕,我和交往多年的女友订婚了。我精心策划了一场寻宝游戏式的求婚,动员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和教授,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为她送上玫瑰和线索,最终在校园最高建筑的顶楼,我单膝跪地。那是一个完美的时刻。六个月后,在即将一同开始医学院新生活的前夕,我们分手了。
回想起来,那段感情充满了强烈的激情,也充满了被我刻意忽略的危险信号:我们有巨大的宗教信仰差异、我们从未讨论过未来、我们在公共场合激烈争吵、双方的亲友都对我们的结合表示担忧。但我完全被爱情的兴奋感冲昏了头脑,就像吸食了爱情的“快克可卡因”,对所有警告信号视而不见。我的大脑沉浸在关于我们完美未来的模拟中,不断地强化着“她就是唯一”的主观偏见。我被爱情“瘾住”了。
浪漫的爱情本身没有错。但当我们被它完全控制,失去理智时,就会坠入深渊。这再次说明,我们常常无法正确解读自己的“压力指南针”,被多巴胺的强烈冲击引向了危险而非安全。
赢得爱情的游戏
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的研究团队通过fMRI扫描证实,强烈的浪漫爱情会激活大脑中与成瘾物质(如可卡因)相同的奖赏回路,包括腹侧被盖区(VTA)——大脑多巴胺的主要来源。她直言:“浪漫的爱情是地球上最容易上瘾的物质之一。”
爱情的体验——欣快感、对伴侣的持续思念、情绪依赖、渴望——与成瘾的症状高度重合。
然而,爱情并非只有这一种面貌。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爱情的阶段”与大脑活动模式相关:
- 在恋爱初期或关系中痴迷程度较高的人,他们大脑的后扣带皮层(PCC),也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自我网络”核心,会更加活跃。这表明,在爱情的这个阶段,“我”的成分很重:“我”如何看待对方?“我”能从这段关系中得到什么?“我”是否被爱?
- 而在长期、稳定且幸福的婚姻关系中,虽然奖赏回路依然会被激活,但PPCC的活动相对更安静。这更像母亲对孩子的爱,其中“自我”的成分减少了,更多的是一种无私的关怀。
这揭示了“热恋”与“成熟的爱”在神经层面的差异。当爱情被“自我”所主导,就更容易变成一种执取和成瘾。
你所需要的只是爱(哪一种爱?)
古希腊人至少有四种词来形容爱:Eros(情欲之爱)、Storge(亲情之爱)、Philia(友谊之爱)和Agape(无私、无条件的爱)。
在与前女友分手后,我开始通过正念来处理自己的痛苦。起初,我对练习“慈心禅”(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一种祝愿自己和所有众生安好的练习——非常抗拒,认为它太过多愁善感。但随着练习的深入,我开始体验到一种与浪漫爱情的兴奋和收缩感截然不同的感受——那是一种温暖、开放、扩张的感觉。
在一次fMRI扫描中,我练习了慈心禅。结果显示,当那种温暖、开放的感觉升起时,我的PCC(自我网络)活动显著下降,而大脑的奖赏回路则保持平静。
这表明,存在一种不依赖于“自我”和“渴求”的爱。它不是为了从外界获得什么,而是从内心自然流淌出来的。它不带来兴奋后的空虚,而是带来一种宁静的满足。
当我们不再将爱情视为满足“自我”需求的工具,不再沉迷于那种抓取式的、令人上瘾的激情时,我们或许才能体验到爱更广阔、更深刻的维度。这种爱,不会耗尽我们,反而会滋养我们,因为它不根植于“我”,而是根植于一种更深的连接。
第二部分:调动多巴胺
第七章:为何难以专注——真的是这样吗?
好奇心是无聊的解药。而对好奇心本身,则无药可解。——多萝西·帕克
在我早期的禅修经历中,我深信专注力就像一块肌肉,需要通过艰苦的、反复的“对抗分心”来锻炼。结果,我常常感到挫败和疲惫。我的大脑根本不认为“关注呼吸”这件事比它脑海里那些精彩纷呈的幻想和计划更有趣。
后来,我从古老的佛学教义中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法,这个方法与我们天生的奖赏学习机制惊人地吻合。它不靠蛮力,而是靠智慧。
误解的快乐,错误的努力
佛陀曾说:“世人所谓的快乐,圣者称之为苦;世人所谓的苦,圣者已证得为乐。”这呼应了班迪达长老的观点:我们常常将“兴奋”误认为“快乐”。兴奋带来的是渴求和不安,而真正的快乐是宁静和满足。
佛陀本人曾是王子,享尽人间奢华。正是因为他“探索了欲望满足的终点”,才发现它永远无法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幸福,只会让人想要更多。这个深刻的“醒悟”(disenchantment),让他看清了奖赏学习回路的本质,并找到了跳出这个循环的方法。
关键在于清晰地看到我们行为的真实后果。当我们沉浸在浪漫幻想中时,那种兴奋的感觉之后,是否伴随着一种不满足的、想要更多的渴求?这种渴求本身就是一种微妙的痛苦。
我们之所以难以专注,是因为我们试图用意志力去强迫大脑做一件它认为“无聊”(即没有奖赏)的事情。这违背了它最根本的学习原则。
专注的正确“配方”
《念住经》(Anapanasati Sutta)中列出了“七觉支”,即导向觉悟的七个要素。它们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一个因果相续、自然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培养专注力的“正确配方”,它不是通过压制,而是通过培养一系列积极的心态:
- 念(Mindfulness):首先,是对当下体验的觉知。
- 择法(Interest/Investigation):当“念”生起时,好奇心或探究心会自然出现。我们会开始对“因果”感兴趣:“我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感觉?是让我更平静,还是更烦躁?”
- 精进(Energy):就像读一本好书,兴趣会自然地带来持续下去的能量。
- 喜(Joy/Rapture):当探究心和能量结合,一种非感官的、内在的喜悦会油然而生。
- 轻安(Tranquility/Relaxation):喜悦之后,身心会感到放松与平静。
- 定(Concentration):在身心轻安的状态下,专注就毫不费力地出现了。它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前面所有积极因素成熟的结果。
- 舍(Equanimity):深度专注之后,一种平稳、不为外境所动的心态便会生起。
这个过程的核心在于第二步:择法,也就是好奇心。
与其把呼吸当作一个枯燥的任务去“盯住”,不如带着好奇心去“探索”它。每一次吸气是什么感觉?每一次呼气又有什么不同?当大脑被好奇心所吸引时,它就得到了它想要的“奖赏”——不是来自外界的刺激,而是来自内在探索的喜悦。
好奇的喜悦与欲望的兴奋有着本质的不同。兴奋是收缩的、有所求的、会带来疲惫的。而喜悦是开放的、无所求的、能带来滋养的。
好奇心与大脑
我们的fMRI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当冥想者被指导去“关注呼吸,并特别留意其中升起的任何兴趣、惊奇和喜悦感”时,他们大脑的后扣带皮层(PCC,自我网络的核心)的活动显著下降。这表明,当好奇心和喜悦出现时,“自我”的执取和干扰就减弱了。
因此,培养专注力的关键,不是去“对抗”分心,而是利用我们天生的奖赏学习机制,将“专注”这个行为与一种内在的、积极的奖赏——好奇的喜悦——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重新定义我们的练习:
- 触发:感到压力或分心。
- 行为:对自己当下的体验(无论是身体感觉还是念头)变得好奇。
- 奖赏:体会到由好奇带来的内在喜悦、平静和专注。
不断重复这个新的习惯回路,我们就能将专注力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享受。
第八章:学会刻薄——与友善
我行善,则我感觉良好;我作恶,则我感觉糟糕。这就是我的宗教。——亚伯拉罕·林肯
Yik Yak是一款匿名社交应用,它允许用户在特定地理范围内发布和评论帖子。因为匿名,它很快成为网络霸凌和恶意言论的温床。学生们可以在课堂上肆无忌惮地对教授发表侮辱性言论,因为“没有人会知道是谁干的,也没有后果”。
喜剧演员路易·C.K.曾敏锐地指出,智能手机让孩子们变得刻薄,因为他们失去了建立共情的关键环节。当一个孩子当面对另一个孩子说“你很胖”时,他能立刻看到对方受伤的表情,这种即时的负面反馈会让他明白“这样做感觉不好”。但当他通过手机发送同样的信息时,他看不到对方的痛苦,他得到的反馈可能是“嗯,这很有趣”。
行为的“即时反馈”
Yik Yak这类应用的设计,完美地利用了奖赏学习的原则:发布刻薄的言论(行为),获得点赞或内心的刺激感(奖赏),却没有即时的惩罚。根据斯金纳的理论,奖赏和惩罚都必须是即时的,才能最有效地塑造行为。在网络世界里,奖赏是即时的,而可能的惩罚(如被学校处分)却是滞后的,这使得负面行为极易被强化。
相反,路易·C.K.指出的那个“看到对方受伤表情”的场景,就是一种即时的、天然的惩罚。它不需要外部规则的介入,我们天生的共情能力就能让我们感受到“伤害他人”所带来的不适感。
正念觉知,正是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行为的“即时反馈”。
在一次禅修中,我被对一位同事的愤怒情绪所困。我反复在脑海中与她争论,每一次都感觉自己“义正言辞”,并从中获得一种病态的、收缩的快感。这种“自以为是的愤怒”本身就是一种奖赏。直到有一天,我问自己:“我从这种愤怒中到底得到了什么?”答案清晰地浮现:“什么也没得到,只有痛苦和消耗。”
那一刻,我像我的戒烟病人“尝到”香烟的恶心味道一样,也“尝到”了愤怒的毒性。我对它“醒悟”了。从此,每当愤怒升起,我能更快地识别出它,并且不再那么热衷于沉溺其中。
基于觉知的伦理
这个体验指向了一种可能性:真正的伦理行为,或许并非源于对外部规则的遵守,而是源于一种内在的、基于清晰觉知的学习过程。
当我们能够不带偏见地、清晰地看到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时——不仅是对他人的影响,也包括对自己内心状态的影响——我们就会自然地趋向于那些能带来真正安宁和快乐的行为,而远离那些只会带来短暂刺激和长期痛苦的行为。
研究发现,在“最后通牒博弈”这个测试公平感的经济学游戏中,禅修者比普通人更愿意接受“不公平”的提议。脑成像研究表明,这是因为他们大脑中与厌恶等负面情绪相关的前脑岛活动较低。他们似乎能够“解耦”负面情绪与行为之间的自动链接。他们看到了“报复”这个行为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奖赏,因此选择了放下。
这表明,通过正念训练,我们可以学会看穿自己的主观偏见(比如“我必须得到公平对待”),从而做出更智慧、更符合长远利益的决定。
给予的快乐
当我们从愤怒、报复等收缩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时,我们会释放出大量的心理能量。这些能量可以被导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比如培养喜悦——这是通往深度专注的关键一步。
培养喜悦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就是练习慷慨。
当我们给予时,我们体验到的是一种开放的、温暖的、令人愉悦的感觉。这种快乐是内在的,它本身就是行为的奖赏。
然而,给予也分两种:
- 有条件的给予:当我们期待回报时,比如为了给老板留下好印象而为他开门。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感谢,我们就会感到失望。这种给予是交易,它的快乐是脆弱的。
- 无条件的给予:当我们不求任何回报地给予时,快乐来自于行为本身。无论对方是否感谢,我们内心都是满足的。这种“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给予,会带来最纯粹的喜悦,并强化我们再次行善的意愿。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练习,来校准自己的“压力指南针”:下一次为别人开门时,留意一下自己的内心。我是期待着什么,还是仅仅享受这个小小的善举?这两种心态带来的感觉有何不同?哪一种感觉更接近真正的、持久的快乐?
通过这样的观察,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对他人更友善,也学会了如何对自己更友善。
第九章:关于心流
你的“我”挡了你的道。——慧海禅师
我母亲在我小时候给电视机上了锁,这迫使我到户外去寻找乐趣。于是我爱上了自行车。从少年时的BMX小轮车,到大学时的山地车,我体验到了在骑行中完全沉浸、物我两忘的时刻。那时我并不知道,这种体验有一个名字,叫做“心流”(Flow)。
进入心流
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将心流定义为“为了活动本身而完全投入其中的一种状态”。当你进入心流时:
- 自我意识消失了。你不再评判自己做得好不好。
- 时间感扭曲了。几个小时感觉就像几分钟。
- 行动与意识合二为一。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毫不费力、自然而然地从上一个动作中流出,就像爵士乐的即兴演奏。
- 体验本身就是奖赏。你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纯粹是因为享受这个过程。
我们都在某些时刻体验过心流,无论是在运动、演奏音乐,还是沉浸于一个项目中。问题是,我们能否有意识地创造进入心流的条件?
心流的条件
极限运动员迪恩·波特曾说,他之所以将自己置于生死一线的情境,是为了“可预见地进入一种高度觉知的状态”。在那种时刻,“自我”没有存在的空间,所有的感官都为了生存而高度集中。
当然,我们不需要冒生命危险去体验心流。契克森米哈赖指出,进入心流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任务的挑战性与个人技能水平之间的完美平衡。
- 如果任务太简单,我们会感到无聊,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DMN)会开始活跃,我们会走神。
- 如果任务太难,我们会感到焦虑和挫败,自我评价的念头会不断涌现。
- 只有当挑战性略高于我们的技能水平,需要我们全神贯注但又力所能及时,心流才最容易发生。
这与我们对大脑的了解非常吻合。心流中“自我意识的消失”,在神经层面很可能就对应着默认模式网络(DMN)的平息。
正念:心流的训练场
心流的许多要素——专注当下、行动与意识合一、体验的内在奖赏性——都与正念练习高度相似。契克森米哈赖本人也曾提到,冥想是训练心流的一种方式。
在第七章我们谈到,喜悦是通往专注的关键。心流体验也充满了喜悦。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在“进入状态”时,常常会不自觉地伸出舌头,这正是他极度放松和享受比赛的表现。他的教练菲尔·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正念禅修推广者,他深知,放下对结果的执着,才能让运动员发挥出最佳水平。
在一次禅修中,我努力了很久也无法进入深度专注。我检查了所有“配方”,发现自己缺少了关键的一味“调料”——喜悦。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并会心一笑时,专注的状态瞬间就出现了。
然而,契克森米哈赖也警告说,态度至关重要。如果你练习冥想是为了“变得神圣”,或者锻炼是为了“练出胸肌”,那么大部分的好处都将丧失。关键在于享受过程本身,而不是为了结果。
这再次指向了“自我”。当我们带着一个强烈的“我想要……”的目标时,我们就已经把自己和体验分开了。“我”在骑车,“我”在冥想。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是心流的障碍。正如尤达大师对卢克·天行者说的:“去做,或者不去做。没有‘尝试’。”
当我们放下“尝试”和“想要达成”的念头,放下对自我的关注,只是纯粹地、全然地投入到当下的行动中,心流之门便会为我们敞开。在一次fMRI扫描中,一位资深冥想者报告说自己进入了心流状态,与此同时,她大脑的PCC(自我网络核心)活动显著下降。我们用影像捕捉到了心流的神经印记。
无论是音乐、运动还是工作,完美的练习造就完美。而完美的练习,不仅仅是技巧的重复,更是心态的修炼:不自我苛责,不急于求成,全然地投入,享受每一个当下。这,就是通往心流之路。
第十章:训练复原力
当你感到与万物相连,你也会感到对万物负有责任。你无法转身离去……你必须学会要么承载这个宇宙,要么被它压垮。你必须变得足够强大去爱这个世界,又要足够空灵去与它最深重的恐怖同坐一席。——安德鲁·博伊德
一个广为人知的禅宗故事:一位老和尚和一位小和尚在河边遇到一位无法过河的年轻女子。老和尚毫不犹豫地抱起女子过了河。小和尚对此耿耿于怀,走了几小时后终于忍不住质问师父为何破戒。老和尚平静地回答:“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为什么还抱着她?”
这个故事完美地诠释了当我们执着于自己的观念和评判时,是如何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负担的。小和尚缺乏的,正是复原力(Resilience)。
复原力,即从困境中迅速恢复的能力,是一种精神上的“弹性”。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而我们的许多痛苦,源于我们试图用僵化的习惯和观念去应对流动的现实。当我们“应该”如何的期望与现实发生冲突时,我们就会产生抗拒(resistance)。
共情疲劳:一种收缩的反应
在医学院,我们被教导要对病人有共情心。共情,即“理解并分享他人的感受”,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然而,研究表明,医学生的共情能力在进入临床实习后会显著下降,高达60%的医生报告有“职业倦怠”。
这种“共情疲劳”的根源在于,当我们不断地“感受病人的痛苦”时,我们自己也会感到痛苦。为了自我保护,我们的大脑会启动一个奖赏学习回路:触发(看到痛苦)-> 行为(情感上收缩或疏远)-> 奖赏(暂时感觉好受一些)。每一次这样的收缩,都让我们变得更僵硬,更缺乏弹性。
这里的悖论在于,我们需要与病人连接,但这种连接又会耗尽我们。出路何在?
答案在于区分共情与慈悲。达赖喇嘛曾说:“真正的慈悲不是一种情绪反应,而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坚定承诺。”它不依赖于我们自己的投射和期望,而是基于他人的真实需求。
共情可能是“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这其中仍然有一个强大的“我”在中心。而慈悲是“我看到了你的痛苦,并希望你能离苦得乐”,这里的“我”退居其次。
当“自我”的成分减少时,自我保护的需求也随之减少。我们不再需要耗费巨大的能量去筑起情感的壁垒。这种开放、无私的状态,不仅不会耗尽我们,反而会带来一种内在的满足和力量。研究证实,对医生进行正念训练,可以显著降低他们的职业倦怠,同时提升共情能力和情绪稳定性。
(不)抗拒训练
贯穿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大部分的痛苦都源于一种“抗拒”的习惯。我们抗拒不愉快的情绪,抗拒不符合期望的现实,抗拒我们无法控制的变化。每一次抗拒,都是一次“抵抗力训练”,让我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僵硬。
佛陀的“四圣谛”,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抗拒训练”的四步指南,由斯蒂芬·巴切勒将其现代化地诠释为一项四重任务:
- 拥抱痛苦(Comprehend suffering):全然地去体验和理解生活中的不如意,而不是逃避它。
- 放下执取(Let go of reactivity):观察到由贪、嗔、痴驱动的自动化反应(抗拒、抓取、回避)是如何升起的,并有意识地选择不去跟随它。
- 体验止息(Behold the ceasing):亲身体验到当反应停止时,痛苦也随之平息的那一刻。这个体验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奖赏。
- 修习道途(Cultivate a path):将这种基于正念觉知的练习,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个过程的核心在于第二步:放下自动化反应。
我们可以像在健身房一样,从三个维度来观察自己的“抗拒”习惯:
- 频率:我一天之内有多少次会自动地抗拒或执取?(可以通过观察内心的收缩感来识别)
- 强度:我执取的“杠铃”有多重?我被卷入的程度有多深?
- 持续时间:我“抱着”这个负担多久才放下?
通过这样的观察,我们不是在评判自己,而是在了解自己。当我们清晰地看到“抗拒”这个行为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负反馈),而“放下”会带来轻松和自由(正反馈)时,我们的大脑就会自然地开始学习一种新的、更具弹性的应对方式。
这种训练不是要我们达到某个终点,而是要我们学会在每一个当下,都能拿出自己的“指南针”,看清自己的方向。我们不再需要与生活搏斗,而是学会了与它共舞。我们开始发现,那份我们一直向外追寻的安宁和喜悦,其实一直都在,只要我们愿意放下阻碍它的东西——我们自己。
尾声:未来即现在
你无法强迫幸福。从长远来看,你什么也无法强迫。我们不使用武力!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充分的行为工程学。——B.F.斯金纳,《桃源二村》
斯金纳在近七十年前就预见到了一个可以通过“行为工程学”来塑造的社会。如今,这个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只不过主导者不是乌托邦的规划者,而是商业公司。
无论是社交媒体、新闻应用还是食品工业,都在运用最前沿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知识,通过A/B测试等方法,大规模、高效率地“设计”我们的行为。脸书曾通过操纵70万用户的信息流,成功证明了情绪可以在社交网络中大规模传染。食品公司精心设计产品的“极乐点”(bliss point),让我们无法抗拒地过量饮食。
这些技术利用了我们最原始的奖赏学习回路,将我们推向一个不断追求短暂刺激的漩涡。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如果我们无法逃离这个被“行为工程学”塑造的世界,那么我们能否利用同样的技术和原理,来帮助自己解脱?
这正是我实验室和我的初创公司Claritas MindSciences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相信,既然人们已经对他们的手机上瘾,那么手机也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帮助他们从成瘾中走出来。
我们开发了一系列基于正念的数字化治疗项目,比如针对戒烟的“渴望戒断”(Craving to Quit)和针对压力性进食的“即刻正食”(Eat Right Now)。这些应用将我们在实验室中验证有效的方法,以每天5-10分钟的简短课程形式,直接送到用户手中。
- 利用痛点:应用直接针对用户的核心问题(如烟瘾、食欲)。
- 情境化学习:用户可以在触发渴望的真实场景中(如在车里、在办公室)进行练习。
- 即时反馈:通过在线社群,用户可以获得同伴和专家的支持与指导。
- 利用奖赏回路:每一次成功地用正念应对渴望,而不是屈服于它,都会带来一种内在的、更持久的奖赏——自由和掌控感。
一位国会议员的助手,在完全没有戒烟计划的情况下,试用了我们的应用。21天后,他成功戒烟了。他写道:“如果没有‘渴望戒断’,这本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在开发便携式的脑电(EEG)神经反馈设备,让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自己大脑“自我网络”(PCC)的活动,直观地了解自己何时“被念头困住”,何时又“成功地放下”。
在一个越来越倾向于用短期奖赏来诱捕我们的世界里,这些工具旨在帮助我们重新校准自己的“指南针”。它们不是要我们去压抑或对抗欲望,而是要我们去清晰地看见。
通过看见,我们得以区分短暂的兴奋和持久的快乐。通过看见,我们得以了解“刚刚好”的智慧,无论是对食物、金钱还是赞美。通过看见,我们得以从被动的、被设计的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有觉知的生命探索者。
未来已来,而改变,就在每一个我们选择“看见”的当下。
附录:你的正念人格类型是什么?
在佛教古籍《清净道论》中,人格特质被归纳为三大类:信/贪行者、嗔/慧行者、痴/寻行者。这部古老的禅修手册可能是最早的“个性化医疗”指南之一,它根据不同的人格类型,推荐不同的禅修方法。
我们的研究团队发现,这三种古老的分类与现代心理学中基于奖赏学习的趋近(approach)、回避(avoid)和僵住(freeze)三种基本行为倾向高度吻合。我们据此开发并验证了一份包含13个问题的“行为倾向问卷(BTQ)”。
通过了解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倾向,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习惯性反应模式,并与家人、朋友和同事更和谐地相处。
以下是问卷问题,你可以借此大致了解自己的倾向。请对每个问题下的三个选项进行排序,1代表最符合你的情况,2为次之,3为最不符合。请凭第一感觉作答。
行为倾向问卷(简版)
- 如果我筹划一个派对……
- __ A. 我希望它充满活力,有很多人参加。
- __ B. 我只希望某些特定的人来。
- __ C. 可能会是临时起意、形式自由的。
- 关于打扫房间,我……
- __ A. 会为把房间弄得漂亮而自豪。
- __ B. 很快就会注意到问题、瑕疵或不整洁的地方。
- __ C. 不太会注意或被杂乱所困扰。
- 我喜欢把我的生活空间弄得……
- __ A. 很漂亮。
- __ B. 很有条理。
- __ C. 充满创造性的混乱。
- 工作时,我喜欢……
- __ A. 充满激情和活力。
- __ B. 确保每件事都准确无误。
- __ C. 思考未来的可能性/琢磨最佳的前进方式。
- 与人交谈时,我给人的印象可能是……
- __ A. 热情亲切。
- __ B. 注重实际。
- __ C. 富有哲理。
- 我的穿衣风格的缺点可能是……
- __ A. 过于奢华。
- __ B. 缺乏想象力。
- __ C. 混搭或不协调。
- 总的来说,我的举止……
- __ A. 活泼轻快。
- __ B. 敏捷干练。
- __ C. 随性散漫。
- 我的房间……
- __ A. 装饰丰富。
- __ B. 布置整洁。
- __ C. 杂乱。
- 总的来说,我倾向于……
- __ A. 对事物有强烈的渴望。
- __ B. 挑剔但思维清晰。
- __ C.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 在学校时,我可能因为……而出名。
- __ A. 朋友很多。
- __ B. 聪明好学。
- __ C. 爱做白日梦。
- 我通常穿衣服的方式是……
- __ A. 时尚且吸引人。
- __ B. 整洁有序。
- __ C. 无忧无虑。
- 我给人的印象是……
- __ A. 热情亲切。
- __ B. 体贴周到。
- __ C. 心不在焉。
- 当别人对某件事充满热情时,我……
- __ A. 会立刻加入并想要参与其中。
- __ B. 可能会对此持怀疑态度。
- __ C. 会思绪跑偏,想到别的事情上。
计分方法:将A、B、C三类选项的得分分别相加。得分最低的类别代表你最主要的行为倾向。
- A = 信/贪行者(趋近型):你乐观、热情、受欢迎,喜欢感官愉悦和美好的事物。你充满激情,但也可能变得贪婪、骄傲,追求表面的东西。
- B = 嗔/慧行者(回避型):你思维清晰、有洞察力,注重逻辑和细节。你做事有条理,但也可能变得挑剔、批判、固执,容易看到事物的缺陷。
- C = 痴/寻行者(僵住/分心型):你随和、包容,富有哲思,喜欢深入思考。你也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思想或幻想中,可能显得心不在焉、犹豫不决或组织性不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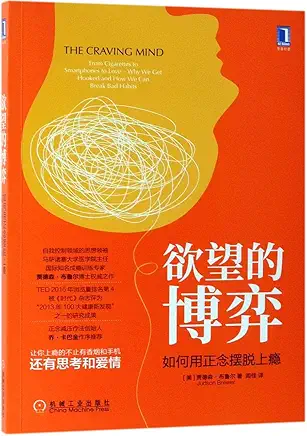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