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佛教的再生观与当代研究
生老病死, 西方世界的佛法 ·Index
Rebirth in Early Buddhism and Current Research - Bhikkhu Anālayo
早期佛教的再生观与当代研究 - 无着比丘(Anālayo)
一位兼具学者与僧侣身份的作者,深入剖析了早期佛教的再生教义,并严谨审视了支持再生的当代研究与案例。
喇嘛尊者序言
我欣见这本探讨再生观念的书籍出版。大多数佛教徒都接受生命无始,我们在一次次的生命中轮回。无着比丘在书中确认,保存在巴利语文献中的佛经是佛陀教法最早的记录,其中清晰地在缘起和业的框架下解释了再生。他还强调,佛陀在觉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体验,便是回忆起自己以及他人的过去生。
五至六世纪的印度伟大逻辑学家陈那(Dignāga)曾深入探讨再生。他指出,物质世界的粒子可以追溯到宇宙大爆炸乃至更早,因此物质世界无始。同样地,识也没有开端。他认为,识的根本因必须与识的性质相同,物质(如我们的感官、大脑和神经系统)只能提供合作条件,而不能成为识的根本因。识的根本因只能是识本身,每一刻的识都由前一刻的识所引生,因此我们说识是无始的。这便是再生理论的基础。
我与作者的目标一致,即如实地理解事物。我很高兴看到他在书中回顾了关于再生的历史辩论,并审视了其他证据。在与现代科学家三十多年的对话中,我注意到他们从最初认为“识仅仅是大脑的功能”转变为承认“神经可塑性”,并认识到心与脑的关系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具相互依存性。
无着比丘提到了儿童回忆前世的报告。我本人也遇到过几个这样的孩子。例如,一个出生在西藏拉萨的男孩,坚持认为自己的家在印度,并最终带领父母找到了他在南印度甘丹寺的前世住所,甚至指出了他藏眼镜的盒子。
作者引用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小男孩能背诵他在此生不可能接触到的古老巴利语经文,这也与我的经验相符。有些人能够背诵他们未曾刻意记忆的文本,仿佛他们早已知晓。对此,“拥有前世的知识”似乎是一个恰当的解释。
我同意作者的观点,本书的目的不是强加某种观点,而是在分析和讨论的基础上提供更好的理解。我相信,随着二十一世纪我们对大脑和心的运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关于再生的问题也会有更多的答案。在此之前,我建议读者遵循佛陀的建议:像金匠检验黄金一样,通过加热、切割和摩擦来审视和探究他所说的话。阅读这里的证据,思考它,并用自己的经验来衡量,然后自己做出判断。
古纳拉塔那长老序言
佛陀在觉悟之夜亲身证知了再生。当他看到自己和他人的无数过去生,以及众生如何根据他们的业而生死轮回时,他开始探究这种生死循环的原因,并由此了悟了缘起(paṭicca samuppāda)。他发现,推动生命进入下一生的力量,是充满了业、爱和无明的识。
由于物质和心理因素不断迅速变化,我们很难通过经验来确切地了解再生是如何发生的。唯物主义者因此断然否定再生的教义。在大多数人不相信再生的社会里,谈论前世经历的儿童会被劝阻和忽视。相反,在相信再生的社会里,人们会特别关注这些孩子。
四十多年前,我听到一盘录音带,是一个小孩用非常甜美的声音唱诵巴利语。他的发音清晰,风格独特,令我深受触动。1985年,我在斯里兰卡多方寻找这个孩子,但未成功。后来在前往澳大利亚的旅途中,我偶然在同行的车上遇到了他,他就是达摩如瓦那(Dhammaruwan)。这次相遇让我第一次有机会与一位能生动、详细地描述自己前世经历的人交谈。后来,他多次来到我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禅修中心,并于2016年4月10日由我为他剃度,法名Samādhikusala。
无着比丘在本书中详细研究了达摩如瓦那(现为Samādhikusala比丘)的巴利语唱诵。这本书适时地出现,为长期以来关于业与再生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学术探讨严谨而深刻,即使是现代的怀疑论者也应予以关注。本书为信者与不信者都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视角来理解业与再生。
前言
本书的缘起是应朋友之请,撰写一篇阐明早期佛教再生学说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我决定深入研究一位斯里兰卡孩子自发凭记忆唱诵的巴利语经文录音,我在1990年代住在斯里兰卡时认识他,当时他已成年。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录音支持了他关于在遥远的过去学习过这些经文的记忆,值得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为了将我的发现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我开始阅读与再生相关的各种研究领域,并由此意识到我进入了一个充满固执己见的雷区。这促使我去探究当前关于此话题辩论的历史渊源。这四个研究轨迹构成了本书的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研究了早期佛教的再生学说,特别是与再生相关的缘起教义、作为佛陀觉悟一部分的宿命通、主导再生的业力法则,以及作为早期佛教觉悟之道基石的正见中,再生学说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第二部分,我转向关于再生的辩论,从早期佛教经典中的相关例子开始,探讨了后来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以及现代的辩论策略。我还讨论了“确认偏误”问题,即人们倾向于以符合自己先入为主观念的方式解读数据。
第三部分,我综述了当前关于再生的研究。我从濒死体验开始,特别关注那些在昏迷状态下获得并得到证实的感知。接着是前世回溯,重点同样是那些似乎得到验证的信息。然后,我转向那些声称记得前世的儿童报告。最后探讨了通晓前世语言(xenoglossy)的现象。
第四部分,我研究了一位斯里兰卡儿童自发唱诵的一系列巴利语经文。在概述相关背景信息后,我将他唱诵的文本与现存的巴利三藏版本进行比较,以揭示这种比较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关于在过去生学习这些经文的记忆。
我写作的兴趣始终是尽可能真实地澄清和呈现信息,而非为佛教教义的接纳而宣传。我个人认为,对这些经典进行字面解读,认为其是现实的精确反映,是不可能的。我个人的生活和修行并不依赖于这项研究的结果来证实我的个人信仰,但作为一名佛教僧侣,我显然对再生的观念抱有好感。而我作为大学教授的学术训练则与这种倾向形成一种制衡。我将自己作为禅修僧侣和学术研究者的双重角色,看作是汇聚于一个共同点:试图如实地(yathābhūta)理解事物。这种对理解的追求贯穿了我所有的研究和个人修行,同样也是本书最核心的关切。
第一部分:早期佛教的再生学说
本部分摘要概述了早期佛教关于再生的核心教义,这些教义主要来源于巴利语《尼柯耶》及其在汉译《阿含经》等中的平行文本。这些文本反映了佛教思想史上最早阶段的再生学说,其关注点是解脱之道,而非提供一个关于再生的详尽无遗的描述性体系。
第一章 缘起
早期佛教思想的核心是缘起(paṭicca samuppāda)学说,被认为是佛陀教法的关键,见缘起即是见法。
十二缘起支
缘起最常见的表达形式是十二缘起支,它们揭示了苦(dukkha)的条件性生起过程,而非世界的创造:
- 无明
- 行(意志的造作)
- 识
- 名色
- 六入(六根)
- 触
- 受
- 爱
- 取
- 有
- 生
- 老死
缘起的核心原则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特定条件性。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十二缘起支的完整列表,也适用于五支、九支或十支等较短的列表。其中的“生”明确指众生的诞生。
后世的论师将十二缘起解释为贯穿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模型,但早期论典如《分别论》(Vibhaṅga)也提出,十二缘起支可以适用于单一心识刹那。这两种解释并非互斥,而是互补的视角,说明缘起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性原则,它既适用于生命过程,也同样适用于再生。
识与名色
《大缘经》(Mahānidāna-sutta)及其平行文本对缘起有详细的阐述。经中指出,识(viññāṇa)与名色(nāma-rūpa)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 识:指心认知事物的能力。 * 色:指经验的物质层面,包括天界的细微物质。 * 名:指心除了识之外的其他功能,包括受、想、行(思)、触、作意。
“名”与“色”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意识所能体验的一切。物质和概念属性需要“识”来被经验;反过来,“识”也需要“名色”作为其认知的内容。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解释了生命期间经验的相续性,而无需一个不变的实体或“我”。这正是无我(anattā)教义的对应面。它并非否认主观经验的存在,而是指出主观经验是一个没有永恒实体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早期佛教所说的“识”,更像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而非后来论典中描述的一系列不连续的微小刹那。
缘起与再生
《大缘经》及其平行文本直接将“识”与“名色”的相互依存关系应用于再生。佛陀问阿难:“如果识不进入母胎,名色会形成吗?”阿难回答说:“不会。” 这表明,在受孕的那一刻,运作的原则与生命期间的经验相续原则是相同的。是“识”的过程“进入”了母胎。
同样,如果识在受孕后离开,胎儿便无法成长。而在死亡时,当身体失去生命力和温度,识便会离开。因此,识(或“认知活动”的过程)似乎是在不同身体之间提供过渡的载体。一部《相应部》的经典也证实了这一点,当讨论一位刚去世的比丘再生去向时,所指的能够再生的主体就是他的“识”。
再生与潜在的烦恼倾向
识在再生时并非一张白纸。根据《相应部》及其平行文本的说法,一个人的思惟与心中潜在的烦恼倾向(anusaya,或称“随眠”)有关,这些倾向为识的建立提供了所缘,从而导致了未来的生、老、死。
这些潜在的烦恼倾向在婴儿时期就已经存在,即使婴儿尚未表现出相应的心识状态和行为。例如,一个躺着的婴儿虽然没有感官欲望的概念,但其心中已存在贪欲的潜在倾向。这些倾向伴随着识在受孕时进入母胎,成为影响新生儿的内在因素之一,与来自父母的遗传和环境影响共同作用。
第二章 宿命通与中阴身
根据早期佛教经典,那些从前世带来的残余记忆,虽然通常在清醒状态下无法回忆,但可以通过修习甚深的定和念来提取。
佛陀觉悟前的宿命通
据说佛陀本人在觉悟之夜就培育出了这种能力。他能够回忆起自己无数的过去生,包括当时的名字、家庭、生活经历和死亡。他毫不犹豫地用第一人称“我”来指代过去的自己,这表明无我教义并不否认个体化的生命相续,只是否认其中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这种回忆能力被认为是一种可以通过禅修实践重复验证的洞见,而非形而上的思辨。佛陀甚至能回忆起曾在早期佛教宇宙观中除“净居天”外的所有境界中生活过。
佛陀觉悟前对他人再生的观察
在回忆了自身的过去生之后,佛陀接着观察其他众生的死亡与再生。他亲眼目睹众生如何根据他们的业行,在善恶道中轮回。善行者生于善趣,恶行者生于恶趣。这种对再生和业力法则的亲证,是他走向完全觉悟的不可或缺的一步。
中阴身(中间存在)
早期佛教思想似乎承认在两次生命之间存在一个中阴身或中间存在(intermediate existence)。这一点可以从对不还者(阿那含)类型的描述中看出。不还者是证得第三果的圣者,他们死后不会再返回欲界,而是会投生到名为“净居天”的天界。
其中一类不还者被称为“中般涅槃者”,即在“中间”状态证得最终的解脱。经中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如同被锤子击打的炽热铁块,飞溅出的火花在空中熄灭,既可以在刚飞起时熄灭,也可以在下落但未触地前熄灭。这表明,证得最终解脱可以在这个过渡状态的不同时间点发生。不过,早期经典并未提供关于这个中间存在可能持续多久的细节。
从一生到另一生的过渡,好比风助火焰,即使没有直接的燃料,也能跨越一段距离。爱就像这股风,支撑着心在生命过渡时期的相续。
第三章 业的法则
业(Karma)在早期佛教中指思(cetanā,即意图或意志),以及由意图驱动的身、语行为,这与通常指“业果”的通俗用法不同。业的法则是,有意的行为(无论是心的、语言的还是身体的)往往会产生相应的结果,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
业与业果
早期佛教认为,我们当下的经历不仅是过去业行的结果,也受到身体失调、气候变化或外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业力法则并非宿命论或一因论,而是在一个复杂的因缘网络中运作。我们当下的意志抉择是影响未来的众多条件之一,但它之所以被强调,是因为它是唯一可以通过心的修习来掌控的因素。
业果的显现形式多样。例如,《小业分别经》(Cūḷakammavibhaṅga-sutta)提出,易怒的倾向会导致相貌丑陋的业果,但这并非绝对,因为这只是一个基本趋势,而非决定性的法则。业果的效应也取决于行为者的整体道德水平,如同一把盐投入一小杯水和一条大河中,其影响截然不同。
业与正见
由于生命在轮回中的流转之久远,无始可寻,因此过去所造的业是巨大的。一个人当下的善行未必立即产生善果,他现在经历的苦难可能是遥远过去某个恶业成熟的结果。反之亦然。因此,仅凭一生的观察,无法证明或证伪业力法则。
临终时刻被认为对业果的走向至关重要。若能在临终时持有正见,则能抵消过去恶业的成熟。《大业分别经》(Mahākammavibhaṅga-sutta)及其平行文本指出,持有正见是影响乃至决定下一生状况的关键因素。
第四章 正见的重要性
在早期经典中,邪见的标准定义明确包括否定再生和业果。《梵网经》(Brahmajāla-sutta)将其列为一种“断灭见”,认为身体死后一切归于寂灭。
对再生的否定
佛陀时代的印度,唯物主义思想已经存在,如六师外道之一就明确否定再生,认为人由四大元素构成,死后即消散。早期佛教将这种观点视为与佛法截然相反的立场。这表明,再生并非当时印度社会普遍接受的信仰,佛陀教导再生学说并非为了迎合大众。
不同类型的正见
正见是八正道的先导。早期经典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正见定义: 1. 世俗正见:承认再生与业果的存在。 2. 出世间正见:洞见四圣谛。
虽然四圣谛的教义建立在再生的观念之上,但即使不完全确信再生,人们依然可以修习其核心内容。这意味着,一个希望修习佛法的人,不必盲目信仰再生。他可以暂时搁置这个问题,只要不陷入断然否定的邪见即可。
佛陀在《Apaṇṇaka-sutta》中建议,面对肯定和否定再生的两种教导,应反思持有这两种观点各自的后果。肯定再生的观点更能鼓励人们行善。而在著名的《卡拉玛经》(Kālāma-sutta)中,佛陀也建议听众根据一种教法是否导致善或不善的后果来判断其价值。
思辨与亲证
《一切漏经》(Sabbāsava-sutta)劝诫弟子们不要浪费时间去思辨“我过去是谁,未来将是谁”,而应致力于禅修改进,亲证实相。早期佛教所批判的是理论思辨,而非再生观念本身。
与思辨相对的是亲证。回忆过去生被视为三明(abhiññā)之一,这三明是佛陀在觉悟之夜所证得的:宿命明(回忆自身过去生)、天眼明(观察他人再生)和漏尽明(断尽烦恼而觉悟)。这种亲身实证的知识(abhiññā)远非理论推测可比。
因此,从需要避免的邪见到修行的最终圆满(四果的证得),再生的观念始终是早期佛教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二部分:关于再生的辩论
再生学说,特别是其“无不变主体”且“依业而行”的特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反复辩论的主题。本部分摘要概述了从古至今围绕这一主题的主要辩论。
第一章 未被阐明的议题
正见与思辨见解
早期佛教经典所处的古印度环境充满了各种哲学思辨。佛陀对许多理论辩论不感兴趣,如《经集》中的《八颂品》(Aṭṭhaka-vagga)就雄辩地表达了对执取见解的排斥。这种态度并非与“正见”相悖,而是“正见”的实践应用,即洞察对自身观点的贪爱与执取。佛陀本人已“舍弃”一切“见”(diṭṭhi),因为他已“见到”(diṭṭha)五蕴的无常本质,或已“见到”四圣谛。
毒箭的比喻
佛陀拒绝就一系列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形而上学问题表明立场,这些问题被称为“未被阐明的议题”或“无记问”。《小摩罗迦经》(Cūḷamāluṅkya-sutta)记载,一位比丘因此困扰,声称若佛陀不回答,他就要还俗。这些问题包括: * 世界是永恒的还是非永恒的? * 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 灵魂(jīva)与身体是同一的还是相异的? * 如来(Tathāgata)死后是存在、不存在、既存在又不存在,还是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
佛陀以著名的“毒箭的比喻”回应:一个人被毒箭射中,当务之急是拔箭疗伤,而不是先去追问箭的材质、射箭者的身份等无关紧要的问题。同样,修行的核心是离苦,而非沉溺于这些对解脱无益的思辨。
搁置思辨见解的原因
佛陀之所以拒绝回答,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建立在错误的预设之上。 * 关于“世界”的问题:在早期佛教中,“世界”是缘起的感官经验,而非一个可以被赋予“永恒”或“非永恒”属性的独立实体。 * 关于“灵魂与身体”的问题:早期佛教分析认为,所谓的“灵魂”(jīva)并不真实存在,因此讨论它与身体的关系(是同一还是相异)是无意义的。这也再次说明,早期佛教的再生观并非简单的身心二元论。 * 关于“如来死后”的问题:提问者将“如来”误解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众生”(satta)。从早期佛教的视角看,如来是五蕴的止息,而非一个实体,因此任何关于其死后状态的论断都无法成立。这就像讨论一个由各部分组成的“战车”,当战车被拆解后,再问“战车”去了哪里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问题属于佛陀所划分的四种问题中的最后一类:应搁置的问题。
第二章 古印度的再生辩论
对再生教义的误解
早期经典记载了佛陀弟子对再生教义的严重误解。一位比丘错误地认为,是同一个、不变的识在轮回。另一位则错误地认为,既然“无我”,那么就没有人会承受业果。佛陀都明确指出这是对教义的曲解,并通过缘起的原则来纠正他们。这表明,对缘起缺乏深刻理解是导致误解的根源。
证明唯物主义立场的“实验”
再生观念在古印度远非被普遍接受。《弊宿经》(Pāyāsi-sutta)及其平行文本记载了唯物主义者弊宿(Pāyāsi)与佛教僧侣鸠摩罗迦叶(Kumārakassapa)之间的一场著名辩论。弊宿为了证明人死后一了百了,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实验”: 1. 密闭蒸煮:将盗贼放入大锅中密封并用火煮,观察是否有“灵魂”或“精神”从中逸出。结果什么也没看到。 2. 逐层分解:活剥盗贼的皮肤,切割血肉、筋脉,敲碎骨头,寻找识的踪迹。结果一无所获。 3. 称量体重:称量一个活着的盗贼的体重,然后慢慢杀死他(不损伤皮肉),再称其尸体。结果发现尸体比活人更重。弊宿据此推断,如果识离开身体,身体应该变轻,但事实相反,因此没有来世。
这些“实验”反映了一种古老的唯物主义观念: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都必须能被物理地观察或测量。
鸠摩罗迦叶用比喻反驳了弊宿的认识论前提: * 不能因为天生盲人看不见某些事物,就断定它们不存在。 * 试图通过肢解身体来寻找死后继续存在的识,就像为了寻找火而劈开木柴、将其磨成粉末一样荒谬。 * 这也好比一个人听到海螺声后,对着海螺要求它再发出声音,甚至去敲打、威胁海螺,这同样是徒劳的。
无不变主体的相续
在后来的《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ñha)中,那先比丘(Nāgasena)用“油灯之焰”的比喻向弥兰陀王解释“无我而再生”的观念。灯焰整夜燃烧,但每一刻的火焰都既非完全相同,也非截然不同。这是一个相续的过程,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火焰”实体。用这盏灯点燃另一盏灯,就如同生命从一世延续到下一世:有相续,但没有一个不变的实体在传递。
这些比喻反映了佛教在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时,需要用善巧的方式来沟通其独特的“无我再生”观。
第三章 中国早期帝制时期的再生讨论
佛教传入中国时,其再生观念与中国固有的观念(如魂魄观念)存在冲突,因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
反对再生与业的论点
与古印度的弊宿类似,中国的一些思想家也持唯物主义立场,他们的论点包括: * 形神关系:“身体溶解,灵魂就消散了;木头烧尽,火就熄灭了。”他们质疑,没有身体,心识如何能够感知? * 存在论困境:如果精神属于“存在”,那么它必然依赖于生命(身体),身体毁灭它也随之毁灭;如果它不属于“存在”,那它就无法被讨论。 * 业力不可验证:认为业力轮回的说法引用了大量无法证实的证据,只是用来进行虔诚宣传的“伪教义”,在科学上站不住脚。
此外,佛教的“个体业力”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家族承负”(祖先的行为会影响后代)观念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一个理解上的挑战。
捍卫再生学说
中国的佛教护法者同样运用了比喻来回应这些质疑: * 薪火之喻:他们用火从一根木柴传递到另一根木柴的比喻,来说明灵魂(心识)从一个身体迁移到另一个身体。傻瓜看到一具身体在生命终结时消解,就认为其求生意志和心识也随之消亡。 * 感官局限:他们指出,反对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受世俗文献影响,认为只有感官能感知到的才是真实的,他们无法看到一生之外的领域。
中国古代的濒死体验
在中国,支持再生观念的一个新元素来自于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s)的记载,这些记载在佛教传入前就已存在。这些故事通常涉及: * 与亡者相遇:当事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遇到已故的亲友或邻居,并获得了只有亡者才知道的信息(如埋藏钱币的地点),当事人复活后,这些信息得到了验证。 * 官僚化的阴间:一个显著的文化特征是,另一个世界被描绘成一个高度官僚化的行政系统。当事人之所以能复活,往往是因为阴间的官吏发现文书记录有误(如抓错了人),于是被遣返回人间。 * 业力记录:有的故事描述了阴间的官吏们忙于核对人们的行为记录,并据此决定他们来世投生为哪种动物。
这些故事反映了再生观念在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演变。
第四章 现代关于再生的辩论
现代关于再生的讨论延续了许多古老的主题,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
对业与再生的误解
- 业力即宿命论: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认为业力意味着“受苦者活该”,这是一种宿命论。然而,早期佛教的业力观恰恰相反,它强调当下的意志抉择(思),鼓励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在当下情境中做出善巧的回应,而非消极地归咎于过去。
- 业力的一因论:另一个误解是认为过去的行为是当下境况的唯一原因。但佛法认为,业力只是众多因缘之一,并非决定一切的唯一因素。
- 再生与身心二元论:有人认为再生必然预设了身心二元对立。然而,如前所述,早期佛教通过“识”与“名色”的相互依存关系来解释相续,这并非简单的二元论。
- 再生与“无我”的矛盾:认为再生与“无我”教义相矛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误解。实际上,缘起和无我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相互依存,而非相互对立。
- 再生与人口增长/物种进化:有人质疑,如果再生存在,如何解释地球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人类的进化?这个问题在早期佛教的宇宙观中并不构成障碍,因为它承认存在多个生命领域(如天界、动物界等),众生可以在这些不同领域之间相互投生,而不仅限于人类之间。
现代新论点:佛陀未曾教导再生
近年来,一些人提出“历史上的佛陀并未教导再生”,认为这是后人添加的内容,此举可能是为了使佛教更能迎合现代唯物主义的口味。然而,这种观点与我们现存的最早文献资料严重不符。如本书第一部分所展示,再生的教义是早期佛教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否认这一点,被一些学者批评为一种“智识上的不诚实”。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在关于再生的持续辩论中,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是“确认偏误”或“我方偏误”。这意味着无论是信者还是疑者,都倾向于选择性地关注、记忆和解读那些支持自己既有立场的数据和证据,同时忽视或批判性地审视那些与自己观点相悖的证据。 * 这种偏误与智力水平和教育程度无关。 * 它使得辩论双方都能从同一组模糊的数据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 * 在评估支持或反对再生的各种研究时,认识到这种认知偏误的存在,对于保持客观和审慎至关重要。
第三部分:支持再生的证据
本部分摘要概述了现代被用来支持再生观念的几类证据。作者旨在呈现一个平衡的综述,承认这些领域存在争议,并提醒读者警惕“确认偏误”的影响,即人们倾向于用证据来证实自己已有的信念。
第一章 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s, NDEs)
濒死体验是跨文化的普遍现象,自古有之。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心脏骤停患者被成功复苏,使得这类报告显著增多。
从古代到当代的报告
古代不同文化中都有类似濒死体验的记载。例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厄尔神话”;早期佛教经典中佛陀及弟子以“意生身”游历天界;中国古代关于“还魂”的故事;基督教中关于耶稣复活、圣保罗游历天堂的记载等。
现代的濒死体验报告与古代记载既有相似之处(如超乎寻常的感知能力),也有显著差异。现代体验通常更为积极、愉悦,而中世纪的记载则充满了炼狱的折磨和严厉的审判。这表明,濒死体验的内容深受体验者所处文化背景和个人信念的影响。例如,古代中国人体验到的是官僚化的阴间,而现代西方人可能会看到计算机在记录其一生。
然而,濒-死体验有时也会与体验者的预期相悖,例如虔诚的基督徒遇到的灵性存有并非耶稣。
帕姆·雷诺兹案例(The Case of Pam Reynolds)
这是濒死体验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帕姆因脑动脉瘤接受了一项名为“低温心脏停搏”的手术。在此期间,她的体温被降至约15.6摄氏度,心跳和呼吸停止,脑干活动监测显示为平线,血液从头部被引流。然而,她报告说自己“灵魂出窍”,飘在身体上方,清晰地看到了手术过程的细节,包括医生使用的骨锯形状,并听到了手术室内的对话。她所描述的许多细节,如医生提到她一侧腹股沟的血管太细而改用另一侧,都得到了医护人员的证实。在那种生理状态下,她本不应有任何意识或记忆形成的能力。
被证实的濒死体验期间的信息
许多案例报告称,患者在心脏骤停等无意识状态下,能够从体外的有利位置观察到抢救过程,并准确描述细节,其准确性远高于没有濒死体验的对照组。其他案例包括: * 超视距感知:患者能“看到”在另一个房间或医院大楼外的特定物品(如一只鞋子)。 * 超常视力:深度近视者在体验中无需眼镜就能看清细节。 * 验证私密信息:患者能获知一些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私密情况。
儿童与盲人的濒死体验
- 儿童案例:一些幼儿,甚至新生儿,报告了濒死体验,并能描述抢救细节,这些记忆在他们学会说话后才得以表达。
- 盲人案例:一些天生失明的人在濒死体验中报告了视觉体验,并且有些视觉信息得到了验证。这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先天失明者的梦境中通常没有视觉图像。
尽管个别案例的细节可能存在其他解释(如信息偶然被听到),但大量报告中一个共同且难以否认的事实是:在脑功能严重受损或几乎不存在的时期,患者拥有了清晰、连贯且生动的意识体验,并在事后能生动回忆。这构成了对“心识完全是大脑产物”这一主流科学范式的严峻挑战。
第二章 前世回溯
前世回溯是通过催眠等方式,引导个人回忆其所认为的前世经历。
记忆的运作机制
在评估前世回溯的价值之前,必须了解记忆的本质。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记忆并非像录音机一样忠实地复制过去,而是一个建构性的过程。记忆的不可靠性源于多种因素,如信息的衰退、注意力不集中、信息提取受阻、来源混淆、暗示以及当前信念导致的偏见等。记忆更像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重建”,人们甚至会对自己从未做过但反复想象的行为产生“虚假记忆”。
治疗效益
前世回溯疗法被一些治疗师用于处理患者当前的心理问题。他们发现,当患者“重温”一个与其当前症状相关的前世创伤时,有时能立即缓解那些慢性的、难以治愈的症状。对于治疗师而言,这些“前世记忆”是真实的还是幻想的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治疗效果。
被证实的前世回溯信息
前世回溯的真实性备受争议。研究表明,催眠中的暗示很容易让受试者创造出虚构的前世,甚至可以追溯到这些“记忆”的信息来源(即潜隐记忆,cryptomnesia)。受试者对前世的信念和催眠师的引导,都极大地影响着回溯体验的内容。
然而,也有一些案例难以用潜隐记忆或幻想来完全解释: * 与人口统计数据的一致性:一项对上千个回溯案例的研究发现,所回忆的前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布,与我们已知的人口增长曲线相符。 * 与已知历史事实的矛盾与证实:在一些案例中,受试者回忆的细节与他们自己所了解的历史知识相矛盾,但后续深入研究却证实这些细节是准确的。 * 具体案例: * 一个案例中,受试者回忆了16世纪西班牙的生活,提供了上百个可通过 obscure 的历史档案验证的细节,而她本人并无相关知识背景。 * 另一个案例中,受试者回忆了18世纪英国某个村庄的生活,准确说出了已消失的村庄名称、过时的方言词汇,并画出了一块地板石头的图案,后来研究团队在该地一间废弃的鸡舍地板下找到了这块石头。
如果这些案例的报告属实,那么它们表明,前世回溯或许不仅仅是幻想和暗示的产物。
第三章 儿童的前世记忆
儿童的前世记忆比催眠回溯更不容易被解释为潜隐记忆,因为这些孩子通常在2-3岁刚学会说话时就开始讲述,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和遗忘那么多关于另一个陌生人的详细信息。
具体的记忆信息与行为的延续性
伊恩·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及其同事记录了大量此类案例。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包括: 1. 陈述具体细节:儿童能说出前世的名字、家庭成员、居住地、职业、死亡方式等大量可供核实的细节。 2. 识别人物和地点:当被带到前世家庭所在地时,他们能自发地认出亲人、朋友、自己的物品和房屋,甚至能指出环境发生的变化。 3. 讲述私密信息:有时,儿童会说出一些只有前世家庭成员才知道的秘密,令当事人震惊。 4. 行为与情感的延续: * 情感态度:对前世的亲人表现出相应的情感(亲爱或憎恨),对前世的仇人表现出恐惧或愤怒。 * 游戏与习惯:游戏内容、饮食偏好、言谈举止等都与前世人物高度一致,但与今生家庭环境格格不入。例如,一个记得前世是日本士兵的缅甸女孩,表现出强烈的男性化行为,怕热、喜欢吃生鱼、对飞机有极度恐惧。 * 特殊技能:展现出前世人物所拥有但今生未曾学习过的技能,如演奏乐器、宗教仪式等。
在验证前被记录的案例
为了排除记忆被污染或夸大的可能性,最有价值的是那些在找到前世家庭并进行验证之前,儿童的陈述就被详细记录下来的案例。 * 印度案例:一个男孩的陈述被其律师父亲公开发表在报纸上,之后才根据这些信息找到了对应的家庭,结果高度吻合。他不仅能独自穿过复杂的街道找到前世的家,还表现出前世婆罗门阶层的饮食习惯。 * 美国案例:一个记得前世是二战飞行员的美国男孩,他的陈述在验证前被录像。他准确说出了航母的名字、战友的名字,并对当时的战斗机有深入的了解。他从小就做飞机坠毁的噩梦,这与前世人物的死亡方式一致。
这些案例表明,儿童的前世记忆现象并非只存在于相信再生的文化中。
胎记与先天缺陷
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领域是,一些儿童身上的胎记或先天缺陷,其位置和形状与他们所回忆的前世人物的致命伤口高度对应。史蒂文森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收集了大量案例,其中许多都附有尸检报告或医疗记录作为佐证。 * 一个土耳其男孩,记得前世被人用刀砍头致死,他脖子上有一圈长长的胎记。 * 一个泰国男孩,记得前世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他头部前后各有一个胎记,与子弹的入口和出口伤吻合,且大小特征也符合法医学规律。 * 一个斯里兰卡女孩,记得前世被公交车碾压胸部致死,她的胸部有一簇胎记,与尸检报告中的伤口位置一致。
这些物理标记的存在,为心识能够影响身体形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线索,也使得这些案例极难用常规的科学理论来解释。
第四章 通晓前世语言(Xenoglossy)
通晓前世语言(识异语)是指一个人能够使用一种在今生显然没有学习过的语言进行交流。这分为两种类型: 1. 诵说型(Recitative Xenoglossy):能够机械地背诵或说出某种外语的词句,但并不理解其含义。 2. 回应型(Responsive Xenoglossy):能够理解并用该外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诵说型案例
一个印度女孩记得两个前世。对于其中一个,她提供了大量可验证的细节。对于另一个,她能用孟加拉语(她的家庭完全不懂)唱出歌曲并跳出相应的舞蹈。这些歌曲后来被证实是泰戈尔的诗歌。
本书第四部分将详细研究一个诵说型的巴利语案例。
回应型案例
回应型案例非常罕见,且证据更具争议性。史蒂文森深入研究了几个案例: * 莎拉达案例:一位说马拉地语的印度妇女(乌塔拉),有时会“变身”为另一个19世纪的孟加拉妇女(莎拉达)。成为莎拉达时,她完全不懂马拉地语,却能流利地使用孟加拉语交谈,并对19世纪孟加拉的各种情况有相当的了解。然而,一位语言学家在分析录音后认为,她的孟加拉语带有后天学习的痕迹。 * 催眠回溯案例:通过催眠,一些美国家庭主妇展现出能够使用瑞典语或德语进行对话的能力。但这些“前世”身份无法得到证实,且她们所说的语言也存在一些非母语者才会犯的语法错误。
总而言之,目前关于回应型通晓前世语言的证据被认为是不确定的。
第四部分:巴利语通晓前世语言的案例研究
本部分摘要详细探讨了一个特殊的儿童前世记忆案例,核心证据是这个孩子能够唱诵大量古老的巴利语经文,其方式和内容暗示了一种独立于现代任何已知版本的古老口头传承。
第一章 案例历史
个人接触与背景
作者无着比丘在1990年代居住于斯里兰卡时,亲自认识了本案例的主人公达摩如瓦那(Dhammaruwan)。当时达摩如瓦那已是成年人,但作者对他儿时自发唱诵巴利语的独特方式印象深刻。他的唱诵风格非常舒缓、悠扬,与斯里兰卡传统快速的念诵方式截然不同。
今生故事
达摩如瓦那于1968年出生。大约两岁时,他会自发地盘腿静坐,然后开始唱诵,有时还会说一种母亲听不懂的语言。三岁左右,家人意识到他唱诵的是巴利语经文。他的继父开始为他录音。许多知名人士,包括当时的斯里兰卡总统、印度禅师以及伊恩·史蒂文森教授,都曾见证过他的唱诵。然而,由于他生性害羞,且在一次被大批围观者惊吓后,他的家人决定对此事保持低调,并要求研究者(如史蒂文森)承诺不公开发表,以免对他造成干扰。成年后,他逐渐失去了这种自发唱诵的能力。
前世故事与录音验证
根据达摩如瓦那的记忆,他在前世学习了这些巴利语经文。他回忆自己曾出生于印度的婆罗门家庭,后出家为僧,在那烂陀寺成为著名论师觉音尊者(Buddhaghosa)的弟子,并作为一名诵经师(bhāṇaka)随同觉音尊者从印度来到斯里兰卡。
虽然这个前世故事本身难以考证,但其唱诵的录音带是客观存在的证据。作者将其中一盘录音带交由专业音频工程师进行鉴定。工程师的结论是: * 录音中没有纸张翻动的声音,表明是凭记忆唱诵。 * 录音带表现出典型的长期储存后才会出现的“磁带印透”现象,这种现象很难用数字技术模拟。 * 录音设备(内置麦克风和自动增益控制)的独特声音特征也难以伪造。 * 录音带的型号(飞利浦,1978-1981年生产)也与时间吻合。
综上,工程师确认这些录音是1970年代或1980年代初的真实口头表演录音,而非现代伪造。
第二章 所诵经文及其背景
巴利经典的传承
巴利语经典最初通过口头传承,后来才被书写下来。在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形成了不同的书面版本,这些版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口头背诵在历史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唱诵的经文
本研究选取了达摩如瓦那唱诵的13部经文进行分析,包括《大缘经》、《大般涅槃经》(节选)、《大念住经》、《无我相经》、《蕴相应·病经》(三部)、《转法轮经》、《耆利摩难陀经》以及《大吉祥经》、《宝经》、《慈经》和《法句经》(节选)等重要经典。
第三章 错误与异本
本章是案例研究的核心,通过将达摩如瓦那的唱诵与现存的四个主要巴利语版本(缅甸版Be、斯里兰卡版Ce、巴利圣典会版Ee、泰国版Se)进行逐字比对,分析其中的差异。
记忆错误
唱诵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这些错误恰恰是口头记忆的典型特征: * 语法错误:例如,在《无我相经》中,当描述五蕴时,他未能根据不同词语的词性(阴性、阳性、中性)来改变形容词的词尾,而是统一使用了适用于第一个中性词“色”(rūpa)的词尾。这表明唱诵者对巴利语语法并不精通,只是在机械地背诵。 * 重复与遗漏:在一些重复性的段落中,会出现词语的错误重复或遗漏。 * 单复数混淆:在需要使用复数的地方误用了单数。
这些错误表明,唱诵并非照着书本朗读,而是一种真实的记忆再现过程。同时,这也说明,如果有人教他,那么教他的人也同样不精通巴利语语法,这在有学者传统的斯里兰卡可能性较低。
异本(Variants)
除了明显的错误,唱诵文本与所有四个标准版本之间存在大量差异(异本)。 * 微小异本:涉及单个词语的拼写或用词不同。统计显示,这些异本的分布不符合任何一个单一版本或地区的传承特点。 * 重大异本:涉及整个词语或短语的增减。
通过对这些异本的详细列表和分析,作者得出结论:达摩如瓦那的唱诵文本不源于任何一个现存的印刷版或手稿版本。如果有人想在1970年代的斯里兰卡教一个孩子背诵经文以伪造前世记忆,他们几乎必然会使用当时最权威的斯里兰卡版本(Ce),但唱诵文本与该版本的差异非常显著。
第四章 遗漏与增补
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来自于唱诵中几处重大的文本遗漏和增补。
文本的遗漏
- 《大念住经》:在描述修行所需时间时,所有标准版本都有一个从七年到七天的递减序列,而唱诵中完全没有这个序列,只提到了七年。
- 《大缘经》:在解释缘起的链条时,标准版本有一段较长的“绕路”讨论,而唱诵中完全跳过了这段,直接连接了前后两个缘起支。
这些大段文本的缺失,是典型的口头传承中因记忆跳跃而导致的遗漏。在1970年代,几乎没有人会知道这种现象是口头传承的特征,因此伪造者不可能故意制造这种“错误”来增加真实性,因为这只会被看作是严重的背诵失误。
文本的增补
- 解剖部分增加了“脑”:在《大念住经》和《耆利摩难陀经》中,当列举身体的31个组成部分(三十二身分)时,唱诵多次加入了“脑”(matthaluṅga)。这在所有标准巴利语经文的正文中都是没有的。然而,研究发现,在后期的巴利论典(如《无碍解道》、《清净道论》)以及汉译《阿含经》的平行文本中,确实包含了“脑”。更关键的是,一部由斯里兰卡僧人传入印度、后在14世纪被翻译成藏文的《耆利摩难陀经》版本中,也包含了“脑”。这表明,达摩如瓦那的唱诵版本,可能代表了一个失传的、但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巴利语口头传承支系。
- 《转法轮经》中增加了天神列表:在《转法轮经》的结尾,描述了佛陀初转法轮的消息在天界逐层传递。所有标准版本在提到梵天界时,只用了一个总称(brahmakāyikā devā)。然而,达摩如瓦那的唱诵却在这里增加了一个详细的、包含15个不同层次梵天界的列表。这个详细列表在其他版本的《转法轮经》中都找不到,但却出现在一本斯里兰卡的护卫经(paritta)合集《四诵分巴利》(Catubhāṇavārapāḷi)所收录的《转法轮经》版本中。
进一步比对发现,尽管在这一点上相符,但达摩如瓦那唱诵的其他经文与这本护卫经合集中的版本仍有大量差异。这说明,他的唱诵并非源自这本合集,而是两者可能共同源于一个更古老的、包含这个增补内容的口头传承。
结论
综合以上证据——典型的口头记忆错误、不符合任何已知版本的异本、反映口头传承特征的重大遗漏、以及与失传的古代版本特征相符的重大增补——作者认为,达摩如瓦那作为一个孩子的唱诵,是一个真实的通晓前世语言的案例。他所再现的,似乎是一个在觉音尊者时代(公元5世纪)印度和斯里兰卡流传,但后来在斯里兰卡主流书面传承中消失了的巴利语口头传承版本。
结论
再生是历史佛陀教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在现存最早的文献资料中得到了证实。早期佛教的再生学说并非基于简单的身心二元论,也不预设一个不变的实体在轮回。相反,生命之内及生命之间的相续被看作是一个由多种相互关联的身心现象构成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它受到包括个人业行在内的复杂因缘网络的影响。
从古至今,关于再生的辩论始终围绕着可信度与验证这一主题。在现代,一方面,一些佛教辩护者试图否认佛陀曾教导再生,以迎合“心识只是大脑产物”的唯物主义观念。另一方面,相关研究也涌现出各种支持生命在身体死亡后以某种形式延续的证据。
- 濒死体验的研究挑战了“所有心识活动都可还原为大脑活动”的假设。
- 儿童前世记忆的记录,特别是那些包含可验证信息、行为延续性以及与前世创伤对应的胎记的案例,将再生从一个纯粹的宗教信条,转变为一个有相当证据支持的、合理的信念。
本书所研究的通晓前世语言案例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证据体系。对一个斯里兰卡小男孩在1970年代唱诵的巴利语经文的严谨分析表明,他不可能在今生通过常规方式学习到这些内容。唱诵的文本特征,指向了一种古老且独立的口头传承。
最终,关于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每个人只有在自己死亡的那一刻才能亲身验证。本书所能做的,是收集信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早期佛教关于再生的教导,并自行评估现有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对死后存在某种相续性的可能性抱持一种开放的信念。
归根结底,真正重要的或许并非在辩论中寻求确定的答案,而是学会坦然面对自身和他人的死亡。这需要我们精勤地修习念死,充分认识到生命必将终结这一确定无疑的事实。在早期佛教思想中,“不死”(amata)是在生之时就可以证悟的境界,而非死后才能达到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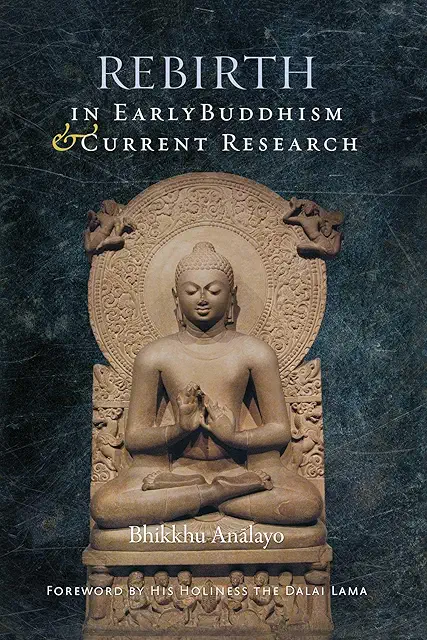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