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清净
隆塔纳荣萨尊者, 南传上座部佛法 ·Index
空空清净 - 隆塔纳荣萨尊者 - 智宁居士译
世间归世间,法归法。……当不执着于世间与法,或不执着于“所知”与“能知”时,便无痛苦。这被称为“涅槃”。
众生皆随业流转
恶业与善业,会带来不同的果报。正如正自觉佛陀在《中部·小业分别经》(Cūḷakammavibhaṅga Sutta)中所开示:
无论是残忍无情、沉溺于伤害、缺乏慈悲、喜欢用手、木棍或武器去侵害、伤害众生的女人或男人;或是易怒、心怀怨恨,稍被言说便心生抵触、暴怒、怀有恶意、显露怨恨之人;或心怀嫉妒,见他人获得利养、恭敬、礼拜、供养时,便心生不快、无法忍受之人;或是不行布施,不愿与人分享食物、饮水、衣物等之人;或是态度僵硬、傲慢自大、轻视他人,对值得恭敬之人不予尊重、礼拜、示好之人;或是从不请教沙门(修行人):“何为善?何为不善?何为有过?何为无过?何为应行?何为不应行?做何事会导致过患与痛苦?做何事能带来长久的利益与安乐?”;或是判决不公、侵占土地、将国家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或是酗酒滋事、伤害他人、焚烧动物栖息的森林、偷盗父母师长与佛教的财物之人;或是心存恶念,因贪、嗔、痴而造业,例如焚烧村镇、寺院僧舍、教堂、佛殿、讲经堂,毁坏佛塔;或与人通奸,违背伦理道德,男与他人之妻通奸,女与他人之夫通奸,或已婚男女行为不轨,与他人通奸,沉溺于感官享受;或伪装自己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以行善之名募捐,却将他人善款中饱私囊、欺骗他人;或曾为执政官员,行为如恶棍般压迫、欺凌百姓,伤害民众身体,征收远超法律规定的财物,对民众毫无悲悯,贪污舞弊、毫无诚信,或制造、贩卖假冒伪劣的食品、用品,以不正当手段获取金银财宝;或辱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口无遮拦,无论长幼,乃至比丘、沙弥;或有恶习的男女打骂配偶,然后随心所欲与人通奸,行为不轨;或偷盗、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或饮酒、吸毒;或觊觎他人之物,对他人心怀恶意;或心行不净,造作粗鄙恶业,内心充满愚痴,怀有邪见,即见解违背法教原则,缺乏正念,没有可以坚定依靠的归宿。
这些人死后,必将堕入苦趣、恶道,在地狱中遭受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直至气绝身亡,随后又复活过来继续受苦,永无宁日,直到在地狱中寿尽为止,而地狱的寿命长达数百万年。或投生为饿鬼、阿修罗、畜生,在那些形态中备受折磨,直至寿终。倘若再生为人,也将会寿命短暂、疾病缠身、身体残疾、肤色鄙陋、权势低微、出身卑贱、贫困潦倒、苦不堪言,或智慧浅薄。
反之,乐于行善的女人或男人,即有慈悲心、常利益一切众生、无加害众生之习性、不易怒、不嫉妒、乐于布施饭食水衣、不顽固、不傲慢、对值得恭敬之人能谦恭礼拜;或是懂得请教沙门何为善恶;或修行奢摩他(止禅)乃至证得禅那。这样的人,死后必生于天界善趣。倘若再生为人,便会长寿、少病、无残疾、相貌端严、威势具足、生于富贵之家,或智慧广大。
人类的五种业行类别
人类所造的善业与不善业,时刻都在发生,可分为以下五类:
- 来自黑暗,去向黑暗:指出生于贫贱之家,生活困苦,谋生艰难,衣食住行、医药等生活所需(五种资具)皆粗劣匮乏,例如食物饮水稀少、衣物破旧、身体丑陋、或身有残疾如疯、瞎、聋,难以找到栖身之所与治病之药。但此人却又在身、语、意上行为不端,死后便会堕入苦趣、恶道。
- 来自黑暗,去向光明:指出生于贫贱之家,肤色粗劣等等,但此人有信心、不悭吝、思想高尚、心不散乱、乐于布施、起身迎接沙门、婆罗门或其他乞者,言行举止得体,不阻止他人行布施。此人死后,便会生于天界善趣。
- 来自光明,去向黑暗:指出生于富贵之家,财宝丰饶,生活资具样样精致,且容貌端正、肤色悦人。但此人却无信心、悭吝、无慈悲心、心行粗鄙、易怒,常辱骂他人,甚至连父母、沙门、婆罗门也不放过,并阻止他人布施食物给乞求者。此人死后,便会堕入苦趣、恶道。
- 来自光明,去向光明:指出生于富贵之家,肤色美好,且身、语、意三业行为端正。此人死后,便会生于天界善趣。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有些人一生下来就在享用过去的福报,这可能让世人觉得:他什么都没做,为何却能如此好运和幸福?其实,那是因为他在很久以前已经付出了很多,只是我们不知道、没看见而已。只要福报还在,那人就会安享幸福,直到恶报现前,才会遭遇痛苦和烦恼。但如果因为不再行善、不积累功德而福报耗尽,那么他将只能承受恶报,饱尝各种巨大的痛苦与烦恼。
有些人一直在造作恶业,但世人却看到他生活得很好很幸福。这是因为恶报尚未成熟,他仍在享用过去的福报。然而,一旦旧的福报享尽,恶业就会显现其果报,导致他遭受各种痛苦与烦恼,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当恶报显现时,大多是多种痛苦与烦恼交织而来,很少只发生一次。古人所说的“祸不单行”,正是此意,即当遭遇不幸时,往往会接二连三地倒霉。这是因为所造的恶业多种多样,都在等待机会成熟。一旦时机到来,便会接连不断地带来或重或轻的果报,这取决于所造的业。
反之,那些行善积德的人,世人有时会看到他们为何总是厄运连连,有时甚至丧命。这同样是因为他们在过去或前世所造的恶业正在显现果报,这部分是我们所不知、不见的。
然而,无论享用的是福报还是恶报,过去所造之业,都可能被当下的善或恶所改变。例如,一个人正在享受福报,生活顺遂,却去诽谤、辱骂圣僧或父母(父母对子女的恩德堪比阿罗汉,即便父母某些行为不善,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业,我们不应去评判、辱骂),这会导致他正在享用的福报被恶业中断,从而堕入世间与法上的衰败。
我们无法通过行善来“洗清”罪恶。善与恶如影随形,各自都会带来果报。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必须加紧行善积德,从行善、布施、持戒、修习奢摩他(止)与毗婆舍那(观)禅开始,并且决不再造新的恶业或不善业。当功德积累得越来越多,获得福报的机会自然就远大于恶报。当一个人只行善、不作恶时,他的心就会充满功德,直到临终。死后,他便能享用福报,不堕恶道。若能在某一世精进修行,直至解脱痛苦、证悟涅槃,便不再轮回生死,那么所有的恶业也无法再带来果-报了。
《基里摩难陀经》法义
正自觉佛陀在《基里摩难陀经》中开示:
谁能带谁去天堂、地狱或涅槃呢?那是不可能的。去地狱、天堂和涅槃,必须靠自己,绝不可能带着别人一起去。谁想从痛苦或地狱中解脱,想获得天堂般的快乐与未来的涅槃,就应当在今生努力让自己摆脱痛苦或地狱,断除一切恶业与不善,只造作善业,积累功德。
功德即是烦恼与欲望的熄灭
经中又开示:什么是功德的本质?功德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烦恼与欲望(Kilesa-Taṇhā)的熄灭。能熄灭多少烦恼欲望,就有多少功德。如果不能熄灭烦恼欲望,那就算不上真正得到了功德。正是这烦恼欲望,驱使我们造作种种业:或是善思、善语、善行,或是恶思、恶语、恶行。然后,我们就必须承受那业的果报,在“烦恼、业、果报”的循环中轮转不休。其结果,或是在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上获得快乐、进步、兴盛;或是导致今生与来世的衰败、痛苦、贫困,这都取决于所造之业。
所谓的功德与罪业、快乐与痛苦,都不在身外。功德与快乐,就是那没有烦恼欲望的心的本来面目。而罪业与痛苦,就是那欲望的集合体。欲望不可能存在于自身之外。功德与罪业的根源,就在我们的心里。
若不想在地狱、饿鬼、阿修罗、畜生道中受苦,或不想成为残疾、贫困潦倒的人,而渴望获得圆满的人生、天界的安乐或涅槃,那就请努力修正自己的心吧!通过努力熄灭内心的烦恼与欲望。烦恼欲望多,痛苦就多;烦恼欲望少,痛苦就少;烦恼欲望灭尽,痛苦也就灭尽,即证得涅槃。这件事必须自己去做。如果我们自己不做,谁又能来帮助我们脱离痛苦、获得快乐呢?因为快乐与痛苦就在我们自身。如果我们自己都找不到,世上哪有别人能找来给我们呢?
有些人认为,功德、天堂和涅槃是通过祈祷、恳求而来的,会有人赐予;而罪业、痛苦、地狱和畜生道,则会有谁或什么东西来解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或者,他们行善布施,积累功德,例如向圣僧供养物品或食物,然后就盯着看尊者是否使用或食用了自己供养的东西。当尊者没有使用、转赠他人或没有食用所供养的食物时,他们便心生不快。或是在佛教中捐资建造,然后执着于那建筑是“我的”,当别人弄脏或改动了它,就心生不悦。或是在工程未完工时,自己却病危将死,心中痛苦万分,想着工程还没完成。)更有甚者,出家为僧,也迷失地以为只要出家就能获得大功德(却忙于建筑工程或各种与解脱无关的活动),内心找不到丝毫快乐,只有无尽的痛苦。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迷失于世间、迷失了道路、迷失在轮回中,因为他们不认识功德就是快乐。行善之后,却去祈求未来的快乐,实在令人同情和惋惜!造作者在行善的当下,就已经获得了功德。(比如,当你决定要供养物品或食物时,功德立刻就产生了,而不是在尊者接受供养时,或在他食用时才产生。也不是说建好佛殿、佛塔才算得到功德。更不是说行善之后,要等很久才能得到福报。)何时做,何时得,但自己却不知道,如同坐在、躺在功德之上,却没有享受到功德所带来的快乐。所以说,生而为人,又值遇佛法,真是白白浪费了。
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将来会享天国之乐,还是会下地狱受苦,只需观察自己当下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快乐多,还是痛苦多?死后,快乐或痛苦的程度也大致如此,不会有太大差别。渴望今生与来世安乐的人,就应当守护好自己的心,让它安住于快乐之中。至于外在的身体,并不重要,无论它遭受何种痛苦,都随它去吧。人死之后,身体被遗弃于大地上,毫无用处。而心,才是跟随自己走向未来的东西。所谓的“死”,只是色身败坏、五蕴分解而已。如果哪一天,心也“死”了,那便不必再生、再死,这即是涅槃。如果还会再“生”,就必然会再“死”,如此怎能解脱痛苦呢?
能做到色身与心同时“死”去的,只有佛陀与诸位阿罗汉圣者。他们不必再回来受生。如果认为人死后才能解脱痛苦,行善积德只是为了求取来世的安乐,那么当死亡来临时,并不能如愿解脱痛苦。天堂与涅 সম্পর্槃,就在我们自身。应当趁着还活在人间,赶紧修行,去证得、去达到,才能真正解脱痛苦。
即使是梵天之乐,也未脱离痛苦
佛陀还开示,即使是天界之乐,无论在哪一层天,乃至梵天,也依然未脱离痛苦。快乐与痛苦总是相伴相随,那是尚未脱离痛苦的快乐。何时心是快乐的,那就是天堂;何时心是痛苦的,那就是地狱。它并非彻底没有痛苦。这与涅槃不同,涅槃只有纯粹的快乐,丝毫不夹杂痛苦。(梵天众生的生命也是“无常”的,即不恒常、不确定、不持久。那是一种暂时的生命,不坚固,必然会变动、败坏、消亡,这是自然法则。他们的生命必然被“生”所追随,被“老”所侵蚀,被“死”所斩断、摧毁。他们安住于一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挡,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庇护。即使是无色界的梵天,在无色界梵天世界中享尽梵福,直到寿终,如果他们的心不清净,在死亡或寿尽之时,若仍是凡夫,即尚未证得须陀洹果,他们仍有可能再次堕入五恶道。)
我们的心,当它痛苦或快乐时,没有任何人能帮我们从心中移走它,也不能将我们的痛苦转嫁给他人,快乐也是如此。快乐与痛苦,谁也帮不了谁。能帮助我们获得快乐的,只有功德善业的力量,如布施、持戒、遵循法教修行等,只有这些才能帮助我们脱离痛苦。人类、天神、帝释天、梵天以及任何人都无法帮助我们脱离痛苦、享受安乐。即使是拥有十力智的正自觉佛陀,也无法帮助任何人,他只能作为指导者,提醒我们认识快乐、痛苦、天堂与地狱。我们必须自己拯救自己。如果知道地狱与天堂就在自身,却无法将自己提升到天堂,那真是白来这世上一遭,也浪费了得遇佛法的大好时光。可悲啊!我们生而为人,身体官能健全,又得遇佛法,本应证得天堂与涅槃,为何却要作践自己,沉沦于地狱之中呢?真是令人悲叹!
地狱与天堂,就在心中
佛陀还开示,所谓的快乐与痛苦,应以心为准。心乐即是天堂,心苦即是地狱。若认为地狱与天堂在心之外,那就是迷失之人。地狱与天堂、罪与福、功与过,全都在这心中。想解脱痛苦,就要守护好那颗造罪受苦的心。若想要天堂,就要做无过失的善业。因为功德善业,做了之后不会有烦恼,每当忆起,都会心生喜悦、安乐、愉悦。如此,我们便可称为“升入了天堂”。
若想获得涅槃之乐,就要放下对“自我”、身体和心,即“色”、“名”,或“色、心、心所”的执着,不要执着它们为“我所有”。如果这个身体是“我们的”,那我们就能命令它:“不许老、不许病、不许死。”但它要老、要病、要死,可曾先征求过我们的同意?从未有过。所以,我们并非它的主人,它也不属于我们(只是我们错误地执着它罢了)。
至于心,同样不属于我们。如果是我们的,我们就能命令它:“只要快乐,不要不快乐。”但它也不听话。它要快乐或不快乐,也从未征求我们的同意。所以我们并非它的主人,它也不属于我们,我们无法控制它,或者说它不受我们的控制。因此,身与心都是“无我”(Anattā)。(应如实地去觉知这一点,善巧地将此认知铭记于心,同时不断地思惟、观察其因果,持续不断,直到心ยอมรับ这个事实,从而放下“是我”或“我的自我”的错误执着。)
让自己像大地一样
佛陀又开示,渴望证得天堂与涅槃的人,就应在有生之年精进努力去达到,因为它们都在我们的心中。其中,涅槃是较为不易的。渴望涅槃之乐的人,当使自己如大地,或如死人一般,即放下快乐与痛苦。(意思是,要具备“忍耐”(Khanti),即忍耐、克制、约束自心,不因色、声、香、味、触、法而沉迷,也不去奋力排斥不喜欢的事物或心境,不试图让已生起的不悦心境迅速消失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也不试图压抑或强迫心保持静止,以避免不悦心境的产生。正如正自觉佛陀所开示:“如来不沉迷于任何事物,因此识便得以熄灭。”又说:“无忍耐者,无法解脱痛苦。”以及“如来既不放弃精进,也不强求,因此得以渡过瀑流(苦海)。”因为若放弃精jin,就会沉沦;若强求要达到、要成为“法”或“涅槃”,就会错过。)
最重要的是要熄灭那一千五百种烦恼。那一千五百种烦恼,若加以归纳,则只剩下五种:即贪(Lobha)、嗔(Dosa)、痴(Moha)、慢(Māna)和见(Diṭṭhi)。 - 贪:是渴望、期盼、想要得到感官之欲,即色、声、香、味、触;以及想要得到物质之欲,即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财产。这些称为“贪”。 - 嗔:是怨恨、伤害、侵扰他人。这称为“嗔”。 - 痴:是迷恋,如迷恋于爱、恨、利、名等。这称为“痴”。 - 慢:是执着于自我,自视甚高,轻视他人。这称为“慢”。 - 见(或Diṭṭhi):是固执于错误的见解,无法放下邪见。
若能熄灭这五种烦恼,就等于熄灭了全部一千五百种烦恼。若不能熄灭这五种,就等于一种烦恼也未曾熄灭。
凡夫之所以难以证得涅槃,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熄灭烦恼和欲望。他们以为只要多做功德,功德就会从天而降,将他们带到涅槃。至于涅槃在何处,他们一无所知,只是如此猜测。因此,证得涅槃是如此之难。事实上,涅槃并不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当贪、嗔、痴、慢、见被彻底根除时,便能证得涅D槃。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不知道并熄灭烦恼欲望,只是渴望证得涅槃,祈求证得涅槃,那么即使经历千百万世,也无法遇见它。因为所有烦恼欲望都在我们自身。如果自己不懂得熄灭已有的烦恼欲望,就无法达到。等待功德来帮助熄灭自身的烦恼,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功德,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才是熄灭烦恼、令其耗尽、消失的执行者,这样才能如愿以偿。愚痴的凡夫之所以难以达到,是因为他们只是空想,所以得不到、达不到。他们不知道涅槃就在自己心中,只想着来世再去获取。他们不知道地狱、天堂和涅槃都在自己心中。因此,他们极难脱离痛苦,在生死轮回中流转不休,在大小三界中不断受生,无有终期。有智慧的人,应当念及自身,调伏自心,使其脱离痛苦与艰难,并挣脱烦恼魔的束缚。如果不这样想,即使有智慧也枉然,不算在有智慧者之列。能够脱离痛苦、挣脱烦恼魔束缚的行为,就是脱离烦恼欲望。当脱离了烦恼欲望,便可称为彻底脱离了苦难。
如理作意(Yoniso Manasikāra)
如理作意,即是善巧地观察色(身体)、受、想、行、识的实相(详见方法三与方法四),然后将其铭记于心,或在心中保持觉知,或善巧地忆念,持续不断,毫不间断。
正如舍利弗尊者回答摩诃拘絺罗尊者时所说: > “见到轮回之可畏的比丘,若能善巧地(如理作意)在心中观照五取蕴——即色、受、想、行、识——视其为无常(Aniccaṃ),即非恒常;视为苦(Dukkhaṃ),即是痛苦;视如疾病、如脓疮、如困厄、如病患、如变异、如败坏……视为无我(Anattā),即是空、非我,那么,他必将证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及阿罗汉果。”
正自觉佛陀在《相应部》中也开示: > “诸位见轮回之可畏者,当你们了知并见到: > - 色是如此,色的生起是如此,色的熄灭是如此; > - 受是如此,受的生起是如此,受的熄灭是如此; > - 想是如此,想的生起是如此,想的熄灭是如此; > - 行是如此,行的生起是如此,行的熄灭是如此; > - 识是如此,识的生起是如此,识的熄灭是如此。 > > 这样,诸漏(即源于无明的烦恼,无明即是执着身心为我、我所有、或我之实体,从而对万物产生爱憎,导致贪、取、有、生及痛苦)便得以断尽。若诸漏与无明熄灭,则贪、取、有、生及痛苦亦随之熄灭,正如在《缘起法》中所开示。”
谁不修习四念处(即观身、受、心、法,或色、受、想、行、识五蕴,见其三法印:无常、苦、无我),就无法从诸漏中解脱,因为他无法放下执着。佛陀在《大念处经》中说:“谁善修四念处,最快三日,最慢不超七年,必证阿罗汉果。”
佛陀在多处开示了如理作意的重要性,总结来说:具足如理作意,将能断除五盖,断除不善法,断除诸漏,断除贪、嗔、痴,并能增长八正道(有时特指正见)、七觉支。未生起的善法得以生起,会生起喜悦(Pāmojja)、轻安(Passaddhi)、乐(Sukha)、定(Samādhi),能如实知见,生起厌离(Nibbhidā)、离欲(Virāga)、解脱(Vimutti)。
既然“念”与“如理作意”如此重要,就应当具备忍耐与精进,去持续不断地进行如理作意,同时配合四念处的修习,这正是戒、定、念、慧的实践。戒,已在善恶业中说明。至于定、念、慧,将在实践部分一并论述。最终,戒、定、念、慧将融为一体,汇于心中,成为一颗自动具备戒、定、念、慧的心,一颗解脱痛苦的心,即是涅槃。
实践方法
正念与正知
遵循法教的实践方法,其关键在于“念”(Sati),即忆持、记起、不忘、将心安住于所缘或与言行相关的事物上,即使事过境迁也能忆起。修习“念”的目标,是为了解脱痛苦,或为了终止对身体和心,即色、受、想、行、识的错误执着,不再认为它们是“我”、“我的”或“我的实体”,这才是符合八正道的“正念”(Sammā-sati)。
“正知”(Sampajañña),即全然的觉知,通常与“念”配合使用。若无“正知”,做事就会颠三倒四、迷迷糊糊。因为心只专注于内在的某个所缘,或只专注于持咒,以至于忘了自己正在做什么。例如:开车开过了家门;到了办公室却径直走过;不记得是否锁了家门或车门;把东西从一处拿到另一处后忘了放在哪;毛巾搭在肩上或眼镜戴在头顶,却到处找毛巾或眼镜等等。
有些人甚至忘了自己正在开车,只专注于持咒,心与所缘融为一体,直至进入“舍禅”(Upekkhā-jhāna),这样极易发生意外。
“正知”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在面对色、声、香、味、触、法(感受、记忆、思想及心境)冲击眼、耳、鼻、舌、身、意时,能具足“念”与“慧”,同时了知,既不沉迷(产生“欲”),也不抗拒(产生“不欲”),不奋力排斥、压抑或阻止。同时,以念与慧即刻了知:这些来触之物皆是“无常”的,它们只是某种事物的自然生起,也必将自然灭去,无法随自己的“想要”或“不想要”而掌控。这便称为具足“念”、“正知”与“慧”。
念与如理作意
念(Sati)的职责是监控、了知心,使其不随心所欲地飘荡,或被烦恼欲望(Āsava-anusaya,即习性、日积月累而成的烦恼)所牵引。念,好比父母,时刻看护、了知自己的孩子,不让他随心所欲地溜出去玩耍或不务正业、荒废学业。有父母时刻看护与了知,孩子就很难溜出去玩或走上歧途。
如理作意(Yoniso Manasikāra)的职责是教导心,让它看见色、受、想、行、识的真相,如前所述。这好比父母教导孩子,让他们知道何为善恶、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做什么会有益,做什么会有害,做什么能脱离过患与痛苦。从小受到良好教养的孩子,会拥有智慧,能自己明辨是非善恶。
如果有“如理作意”或父母时刻教导、熏陶习性,那么“念”——那个负责监控、了知的父母——也就不必那么辛苦地时刻看管了。
因此,当“念”与“如理作意”时刻并存时,就好比父母既看护着孩子,不让他走上歧途,又同时不断地教导他。孩子自然会成为一个品德高尚、富有智慧的人。同理,当“念”与“如理作意”时刻并存,心就不会随烦恼欲望或个人喜好而偏离正道。最终,心将生起智慧,自己觉悟到色、受、想、行、识的真相:它们仅仅是自然现象,有其自然的生起,也必有其自然的灭去。它们不是“我”,不是“我的实体”,不属于“我”,我也不是“它”。同时,心会放下这种错误的执着。当不再执着,便没有痛苦,即从痛苦中解脱。
若念失,则定失;若念在,则定在
“定”(Samādhi),指心的稳固、心的专注,或心专注于所缘的状态,心念合一的状态。它指心坚定地安住于某一事物,不散乱、不游移。何时“念”失,心就会沉湎于胡思乱想,执着于“我”、“我的”或“我的实体”,或“我是这个”、“我是那个”,然后去攀缘、执取各种事物,从而生起贪、嗔、痴,或说痛苦。但当“念”在时,“定”就会在,心就能保持安住、稳固,不沉迷于任何事物而生起烦恼欲望或痛苦。由“念”而生的“定”,才是“正定”(Sammā-samādhi)。
若念失,则慧失;若念在,则慧在
这里的“慧”(Paññā),并非世俗智慧,而是源于对法教的正确理解而产生的智慧,是“正见”(Sammā-diṭṭhi),即见到四圣谛:苦、集(苦之因)、灭(苦之灭)、道(灭苦之道,即八正道)。
何时“念”失,心就会沉湎于胡思乱想,执着于“我”、“我的”或“我的实体”,或“我是那个”,然后去攀缘、执取各种事物,从而生起贪、嗔、痴,这些烦恼欲望正是“集”,是苦的因。
但当“念”在时,心就不会沉迷于任何事物而生起烦恼欲望与痛苦。也就是说,“集”灭则“苦”灭。所以说,“念”在,“定”与“慧”便在;若“念”失,“定”与“慧”亦失。
在“念”尚未成为“大念”(Mahā-sati),即“念”与“心”尚未合一的阶段,必须时刻进行“如理作意”,以防止产生“是我”、“我的”、“我的实体”或“我是那个”的感觉,从而去攀缘、执取事物,生起贪、嗔、痴。同时,要训练“念”,在看、听、嗅、尝、触、知法尘时,都要加以守护,以“念”与“如理作意”的力量,不让自己沉迷于任何事物。如此,“念”、“定”、“慧”的力量会越来越强,直至成为“大念”、“大定”、“大慧”,即念、定、慧融入于心,只剩下“空明觉知”或“纯然的觉知”。
方法一:以“念”将心或觉知持续不断地安住于所缘上
训练“念”的方法是,先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所缘(เครื่องล่อ,直译为诱饵,意指禅修的专注对象或锚点),用“念”将心或觉知安住于其上。所缘可以根据个人习惯选择,例如各种咒语或经文,如“佛陀”(Buddho)或“佛陀、达摩、僧伽”(Buddho Dhammo Saṅgho)。
- 持咒:若选择持咒,如“佛陀”,就在心里持续不断地默念“佛陀、佛陀……”。
- 观动作:或用“念”将心或觉知安住于来回移动的手上,或安住于行走的脚步上。
- 观呼吸:或用“念”将心或觉知安住于出入息上,不必持咒;或者吸气时默念“佛”(Bud),呼气时默念“陀”(dho)。
无论选择何种所缘,关键在于让“念”持续不断地将心或觉知安住于其上,在行、住、坐、卧、饮食、如厕、出行等一切威仪中都保持不间断。(注意:在操作锋利工具或亲自驾车时除外,因为此时心可能专注于内在而忽略外在,导致危险。)
一旦失念,心——即那思想、造作之流——就会溜去对眼前的人或事胡思乱想,或溜去想其他的人、事、过去或未来,或溜去思量自身的生理或心理状态。如果所想的是令人愉悦的人或事,心就会沉迷其中;如果是令人不悦的人或事,心就会挣扎、排斥,想要设法处理或让其消失。当失去“念”时,心就无人看管,会随着欲望或习性(Āsava,漏)四处游荡,并忘记所缘或忘记持咒。
此时,要以“念”觉察到(รู้ตัว)、感觉到(รู้สึกตัว)或了知到(รู้เท่าทัน)这一切,然后重新回来,用“念”将心或觉知安住于咒语或所缘上,重新开始持咒。这就是所谓的“回来”。
但很快,又会失念。那就再次以“念”觉察到、感觉到或了知到,然后再次回来持咒,或让“念”重新安住于所缘上。就这样不断地重复。要以一种放松、放下的心态去做,身心都要放松。不要强迫心停留在所缘上,或强迫它不去想别的事情。不要压抑、不要强求,也不要太刻意。不要渴望宁静,因为我们是在训练“念”,宁静只是自然而然的副产品。不要催促,不要急于求成,不要烦躁。要保持耐心,但不要失念,任由心随万物流转。同时,不要设立不切实际的目标,以为修了之后心就不会再有任何念头,或者心必须永远保持宁静清明。因为心的自然状态就是如此:时而有念头,时而清明,时而阴沉;时而有乐受,时而有苦受,时而有不苦不乐受。这些状态会不断交替变化,这是自然法则。
要耐心地、持续不断地训练“念”。当失念时,心就会对眼前的人或事,或过去未来的人或事,或自己的身心状态进行分别、造作。心会忘记所缘或持咒。此时,就要以“念”觉察到,然后回来将心安住于所缘上。就这样不断地做下去。当熟练之后,或“念”力增强之后,即使有其他念头或任何心境生起,或有任何喜欢或不喜欢的身心状态出现,也不会导致失念。也就是说,心依然在持咒,或“念”依然持续地安住于所缘上。至于那些咒语之外的念头、心境或身心状态,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按照其自然法则在生起和熄灭。
这里必须清楚理解: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念头、心境或身心状态消失。即使训练到“念”能持续安住于咒语或其他所缘上,也并不能使念头、心境或身心状态断灭。如果它们真的断灭了,我们就死了。我们能做的,仅仅是不失念,不让心沉迷于任何事物而忘记了咒语或所缘。
不要试图去消除任何心理状态、念头或情绪,只需“知道”或“仅仅是知道”就够了。因为即使有心理状态、念头或情绪,只要能立刻觉察到,不沉迷、不排斥、不压抑,这就叫依然有“念”。但何时这个“知”消失了,就会立刻失念。
必须同时运用“念”与“如理作意”,持续不断,在行、住、坐、卧、饮食、如厕、出行等一切威仪中都如此。也就是说,当“念”安住于咒语或所缘时,同时也能了知色、声、香、味、触、法,并以智慧如实知见:所有被感知的事物,都只是依循自然法则生起,也终将依循自然法则灭去。它们不是“我”,不是“我的实体”,不属于“我”,我也不是“它”。同时,放下错误的执着,只需“纯然地知”(不是刻意造作一个“纯然”的感觉)、“空明地知”(不是刻意造作一个“空明”的感觉)或“仅仅是知”(不是刻意造作一个坚硬或宁静如穿上盔甲的感觉),或者以中舍之心、以自然平常的舍心去知。(不是刻意造作一个“中立”、“平常”、“漠然”、“静止”或“空无”的感觉,因为这样做是压抑或造作心,使其偏离了自然状态。)
以中舍之心去知,不同于“舍受”
-
许多修行者会误解,以为修行到最后,心中就不会再有任何不愉快的感觉生起,只会剩下纯粹的快乐。因此,他们努力让心中不生起任何不愉快的感受,通过造作各种心理状态,如“静静的”、“空空的”、“宁静的”、“轻盈的”、“舒适的”、“通透的”、“开阔的”等等,以求只保留快乐的感受。或者,当他们在接触眼、耳、鼻、舌、身、意所缘时,心中没有任何感受生起,就误以为“这种感觉就对了,就是这样”,或者以为自己快要证得涅槃了。但当接触外缘时,心中有任何感受生起,他们就错误地认为“我还修得不够好”,然后可能去打坐以求更静,或让心更不动,但这并不能使人解脱痛苦,因为这是“邪见”。
依循自然,当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缘时,必然会生起某种心理感受。如果生起的是合意的感受,就是乐,称为“乐受”(Sukha-vedanā);如果生起的是不合意的感受,就是苦,称为“苦受”(Dukkha-vedanā);如果生起的是既非乐也非苦的感受,称为“舍受”(Upekkhā-vedanā)。
正是在这“舍受”上,人们最容易产生误解,以为“没有感受”,但实际上是生起了一种“不苦不乐的感受”。我们无法选择只保留“舍受”,因为它也是无常的,它必须与乐受、苦受不断交替。也就是说,心中必然会有合意的感受、不合意的感受,或没有任何感受(指舍受)。因为无法选择,所以它们不受我们控制,因此是“无我”(Anattā)。又因为无法只选择合意的感受,必须也承受不合意的感受,即“苦受”,因此它是“苦”(Dukkhaṃ)。
-
另一个误解是,认为“舍受”或“不苦不乐的感受”与那个“以中舍之心去知”的“能知的心”是同一回事。其实不然。“舍受”、“乐受”、“苦受”都只是被感知的心理状态(所知),而“能知者”是心或识(Viññāṇa),它去“知”那个“所知”的心理状态。
“以中舍之心去知”或“以舍心去知”是指,对眼见、耳闻、鼻嗅、舌尝、身触或意知法尘,都以一种自然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去知,不偏向爱或憎,不欣喜也不厌恶,不执取也不排斥。
如果误将“舍受”(所知)与“舍心”(能知)混为一谈,那么每当接触眼、耳、鼻、舌、身、意时,就会努力让心只产生“舍受”,或努力让心不生起任何感受,或让心保持“静静的”、“空空的”、“漠然的”、“空空的”等状态。这是错误的修行,不能导向解脱。
如果强行让心只保持“舍受”,可能会导致心理失常,因为它违背了自然法则。舍受、乐受和苦受必然会随着所缘而变化。当我们强行让心只保持“舍受”时,就违背了实相。心理失常也会导致身体失常,可能因此生病住院。
正确的修行是:当接触眼、耳、鼻、舌、身、意时,会自然地生起某种感受,只需“仅仅是知道”就够了,不要去压抑或造作,也不要挣扎排斥(即希望不愉快的感受消失),或试图将心从那种感受中抽离。同时,不要失念而沉迷于所缘。
试图压抑或排斥,其本质还是“不悦”;而沉迷于所缘,其本质就是“喜悦”。因此,当不压抑、不排斥、不沉迷时,就等于止息了“不悦”与“喜悦”。这才能使人从痛苦中解脱。
比喻:电话铃声
如果把色、声、香、味、触、法尘,或身心的各种状态——感受(受)、念头(行)和情绪,无论好坏、善恶、功过、苦乐、喜恶——比作是电话铃声。如果没有人去“接听”,即只是“空明地知”或“仅仅是知”,那么电话铃声响过之后,自己就会停止。
比喻:日月之光
“知”是一种清净的元素,它是空性的,如同宇宙,无我、无形、无处所。因此,何时能以“中舍之心”去“仅仅是知”,或让“知”从“所知”中独立出来,那么这个“知”就会回归其自然的清净本质。这就像太阳或月亮的光芒,普照寰宇,没有偏袒,不分爱憎,它给予一切光明,无论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快乐还是痛苦,是善还是恶。因此,如果能以中舍之心去知眼、耳、鼻、舌、身、意所缘,不偏不倚,无爱无憎,无喜无恶,即“仅仅是知”,或不造作能知的心使其偏离自然,或以清净之心去知,那么这个“知”就会自动、即刻地回归其自然的清净本质,如同日月之光。
世间与法
世间(Loka):指身体、身心的一切状态,无论好坏、善恶、功过、苦乐、喜恶。包括对当前所见所闻的人或事的念头造作;对自己身心状态的纷乱思绪;对自己的人或物的纠结;对过去或未来的胡思乱想。这些都源于“悦”或“不悦”,“喜”或“厌”,“爱”或“憎”,“忧虑”,或“想要”与“不想要”。无论是沉迷、执着于某事,还是挣扎、排斥不喜欢的事物、心境,或因不喜而压抑,或因不想被情绪牵引而压抑,甚至在没有感觉、感觉空荡荡时,那也是一种状态,即不苦不乐的“舍受”。所有这一切,都是“被知之物”,都是“世间”。“世间”仅仅是因缘和合而自然生起的现象,当因缘消散,它们也自然灭去。它们不是“我”,不属于“我”,不是“我的实体”,我也不是“它们”。
法(Dhamma):是如实地知见“世间”,然后不执取“世间”为“我”、“我的”或“我的实体”,或“我”就是那个“世间”。“世间”必然会时刻造作不休,这是它的常态。而“法”则仅仅是“了知”或如实、自然地“知”世间,即“空明地知”或“仅仅是知”,而不去执取“世间”而生起烦恼欲望或痛苦。
因此,何时“知”消失了,或觉知、了知得太慢(失念),或知到某事后失念、沉迷、随波逐流,落入“世间”,生起“想要获取”、“想要成为”或“不想要”的欲望;或试图压抑、刹车,以防止自己去爱或恨;或因不喜而排斥世间,想逃离、想让它消失;或出于恐惧;或根本不知道自己内心生起了什么状态(如有念无念、有无情绪、有无欲求、喜恶、压抑排斥、随波逐流等都不知道);或随着“想要”或“不想要”、“喜悦”或“不悦”而立刻思想、言语、行动,例如整天沉浸于愉快的思绪中,或随心所欲地说话,或想看、想听、想闻、想吃、想触,或放任自己陷入习惯性的情绪或行为模式中——所有这些,都是在迎合欲望,每一次都如此。这种欲望就会变成习性(Āsava,漏),它是“无明”(Avijjā)之因。
无明,即是不知,不知苦、集、灭、道,不如实知见,从而继续造作,生起烦恼欲望、执取(Upādāna)和痛苦。如果总是这样,就永远看不到那作为“欲望”的念头造作,因为它已经被满足了。这被称为既无“慧”也无“念”,即不觉知、不了知。自然也不会有“定”,只会随业流转。这样,就只剩下“被知之物”,只有“世间”,而没有“法”。因为“法”或“能知者”已经与“世间”混为一谈,或随“世间”而去了,所以“法”就不存在了。
如果处于这种状态,就必须大量、持续、不间断地训练“念”。当“想要”或“不想要”生起时,必须先克制住,这样才能看到那作为“欲望”的念头造作,看到那躁动的心,看到念头与情绪。当欲望未被满足时,心会更加躁动地想要去满足它。此时,必须忍耐、克制、约束自心,同时放下心,使其保持中立。即,既不迎合欲望,也不去排斥、压抑或刹车,只是“仅仅是知”地安住,同时在心中时刻保持觉知:这念头造作、情绪、欲望或不欲,仅仅是因缘和合而自然生起的现象。例如,眼见色,生起识去知此色,然后知此色是可喜的(乐受)、不可喜的(苦受)或是中性的(舍受)。但当缺乏念与慧的守护时,就会生起念头造作,随着喜恶而躁动。当念与慧觉察或了知,即如实知见这“欲”或“不欲”、“喜”或“不悦”是因缘相续而生,不是“我”,不属于“我”,不是“我的实体”,我也不是“它”,同时放下执着,让心保持中立,那么这“欲”或“不欲”、“喜”或“不悦”就会熄灭。然后,就能“空明地知”世间,这才是真正自然的清净之知,称为“法”。就能以念与慧将“能知者”从“所知之物”中独立出来,或将“法”从“世间”中分离出来。然后,世间归世间,法归法。
法超越世间,或不执着于世间。世间与法,都不是“我”,不属于“我”,不是“我的实体”,我也不是“世间”或“法”。世间与法,皆是自然,不属于任何人。当不执着于世间与法,或不执着于“所知”与“能知”时,便无痛苦。这被称为“涅槃”。因此,涅槃超越了世间与法。
但当有必要去思考、言语或行动,以求在世间法上获得成功、进步,并且经过周详考虑,确认不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困扰时,就必须立刻行动,毫不迟疑。因为那是世间之事。
大念、大定、大慧
如果知道某事后,依然失念、沉迷、挣扎排斥或压抑,就要让“念”觉察或了知得越来越快。当训练“念”到这样一个层次:心中任何念头造作、任何情绪、任何状态生起时,念与慧都能了知每一个念头、情绪或状态,这就好比念、定、慧是影子,心是身体。身体如何动,影子就如何跟随。若训练到此,心会非常安住、稳固,能了知每一个念头、情绪或心理状态。
但在此处,许多修行者会误解,抱怨说:“为什么越修,看到的念头、情绪或心中那些琐碎的、乱糟糟的东西越多,不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 事实上,越修越能了知念头、情绪或任何状态,这恰恰是正确的修行。因为了知得越多,就等于念、定、慧越强。若将使人知见念头、情绪或各种状态的念、定、慧比作放大镜,那么当“念”训练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敏锐,能在每一个心刹那都了知时,就等于放大镜的倍数达到了最高,能照见最小的病菌。但修行者非但没有为镜片的品质提升而高兴,反而对看到那么多病菌而感到烦躁、不悦。这好比世间法,钱越多就越富有;在出世间法,知见得越多,就越富有“法”,即成为“大念”、“大定”、“大慧”。
念头造作、情绪或由念头造作而生的心理状态,都只是自然生起的某种事物,它们也自然会灭去。它们不是“我”,不属于“我”,不是“我的实体”,我也不是“它们”。然后放下心,使其保持中立或成为“舍心”。 - “念”的职责与心合一,即以中舍之心,自然地去了知,不造作能知的心使其偏离自然。 - “定”则不偏离这个“知”,即知道某事后,心不随“所知”而散乱、摇摆。 - “慧”,不是那种思索、探寻“法”或寻找证悟涅槃方法的智慧,而是如实觉悟后,不再执取任何事物而生起烦恼、欲望或痛苦的智慧。
诚如佛陀所言:“诸比丘,一切痛苦的根源,皆来自欲望(Taṇhā)、执取(Upādāna),即那躁动不安的渴望与执着‘是我’、‘我所有’,以及沉迷于各种心境。凡是执着为‘我’、‘我所有’的事物,无一不带来痛苦与过患。何时,一个人能做到:见,仅仅是见;闻,仅仅是闻;知,仅仅是知;与万物接触,仅仅是接触,不迷恋、不纠缠、不沉醉。那时,心便从各种执着中解脱,变得通透、明亮、喜悦。”
修习“念”的成果
当寻(Vitakka)与伺(Vicāra)止息后,心与所缘合一,进入禅那(Jhāna)。此时,只剩下作为所缘的那一件事物。有时会感觉手、脚、身体逐渐消失,不必惊慌,只需“仅仅是知”地安住。有时身体或所缘会随心念变大或变小,也不必惊慌。有时会感觉身体迅速下坠,如坠深渊,也不必惊慌,只需“仅仅是知”地安住。这称为证得“初禅”。接着,会生起遍满全身的“喜”(Pīti)。有些人感觉如毛发竖立,有些人感动得几乎流泪,有些人身心轻盈如能飞翔。这称为证得“二禅”。
“喜”也是无常的,它会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大的内心“乐”(Sukha)受,一种满足感。此时,也只需“仅仅是知”地安住。这称为证得“三禅”。接着,“乐”受也无常,会逐渐消退,连同作为所缘的事物也一并消失,只剩下宁静、空明。有时会感觉一片光明,持续很久。这称为证得“四禅”。
四禅也是无常的,它必然会消退,或变化,回归常态。然后,可能会得到一些“附赠品”,如天眼通、天耳通、能知过去未来、他心通(能知他人念头与情绪)、宿命通(能忆起自己或他人的前世),或能示现神通。这些成果让许多修习者沉迷于此,甚至可能因此迷失自我、堕落。这里所证得的禅那,只是“世间禅”,尚不能解脱痛苦。如果修行者满足于此,若在心不暗昧时死去,会投生于梵天;但若在心暗昧时死去,且来不及进入禅定状态,则会堕入恶道。这与修习毗婆舍那(观禅)并证得须陀洹果以上的圣者不同,圣者不会再堕恶道。
方法二:以“念”觉知或了知,无需所缘
有些人可能不需要咒语或任何所缘。其训练方法如下:
2.1 面对强烈情绪 当生起强烈的情绪,如贪欲、嗔恨、愚痴,或非常烦躁、散乱、不耐烦,或非常困倦、消沉,或内心极度痛苦时,要以“念”与“正知”觉察或了知,同时通过活动身体的某个部位,如动动手指、脚趾,或将目光投向远处并让感觉也停留在远处,然后快速地眨眼,频率要快过那盘旋的念头,来将觉知从情绪中抽离出来。然后起身去做点什么,或找朋友聊天,或请教善知识。
或立即转移注意力,例如去看喜剧、轻松的纪录片、运动,或看电影、听音乐,或大声唱歌等。这样做是为了不将情绪压抑在心里,不排斥它,也不随它而去,不让念头围绕着引发情绪或痛苦的事情打转。切记,不要独自静坐,也绝不要试图通过打坐让心静下来,因为那只会让情绪更加激烈,因为心会不断地想着那件事,或将情绪压抑在内心,变成压抑。
要点观察:
a. 如果一开始就选择不使用持咒或所缘的方法(即方法一),那么当情绪或痛苦生起时,不要试图通过快速持咒来熄灭它。因为心不习惯所缘,且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执着——不悦于当下的情绪或痛苦。这可能会使胸闷、头痛或眩晕的症状与原有的压力情绪交织在一起,变得更糟。必须了知,同时活动身体,并立刻转移注意力。
b. 选择此方法的修行者有一个弱点:每当有事触动内心,他们会先将其压抑在心里,导致感觉胸闷、压抑。因为他们不像方法一那样有熟悉的咒语或所缘作为依靠,也不像方法三那样对身体进行过思惟。因此,他们缺乏一个熟悉的心灵支柱。解决之道是:当接触事物引发情绪时,一旦以“念”觉知或了知,必须立刻眨眼或活动身体,并立刻转移注意力。
2.2 面对日常念头 当心中暗自对眼前的人或事、过去或未来的人或事、自己的身心状态产生念头造作,从而生起喜悦或不悦、爱或憎、忧虑或犹豫不决、烦躁散乱或厌倦、消沉、昏沉,或有流入禅定之相(因习惯所致)等时;包括压抑或排斥(因不欲或不悦),或随着念头造作或心理状态而去的习性(因欲或喜悦)时,都要以“念”尽快地觉察或了知,同时活动身体的某个部位,如动动手指、脚趾,或立刻眨眼。
要点观察:
这样做之后,不要回头去检查念头或那些状态是否消失了,因为那会是另一种欲望或“贪爱”的再生。也不要试图按自己的意愿去加速那些状态的熄灭。例如,如果生起了愤怒,不要试图去消除愤怒,因为那只会让愤怒更盛。而是要了知那可能导致更愤怒的念头造作。如果实在无法忍受,就立刻起身去做点什么,不要与那情绪纠缠。
2.3 提升觉知的速度 训练“念”与“正知”,去了知第2.2点中所述的念头、情绪或心理状态,使其速度越来越快,直到能在念头、情绪或状态刚开始生起时就能觉察或了知。这将使“定”力更加稳固。
要点观察:
“定”,即心的宁静、专注、稳固,是指心不轻易随色、声、香、味、触、法(感受、记忆、念头造作及各种情绪)而动摇,而非指心中没有任何状态。如果心中没有任何状态,那就像无生命的物体。在此处,修行者极易误解,以为有“定”的心是没有任何状态的心,然后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排斥或消除心中的任何状态。正确的做法是,只需了知,然后立刻放下,不再关注。
2.4 觉知即解脱 凭着专注稳固的宁静之心,当第2.2点中所述的任何念头或心理状态生起时,包括那些探寻“法”、渴望变得更好、渴望达到或成为“涅槃”的念头,都会有“念”与“慧”即刻了知,或恰好同时了知。每一次都如此。这称为念、定、慧与心合一。知后即刻放下,或以中舍之心去知,不生起任何“想要”或“不想要”。或者说,安住于“能知者”,而不去安住于作为“所知”的念头、情绪或状态。或者说,“知”从念头、情绪或各种状态中彻底独立出来。
方法三:观察身体生起厌离,然后转向观察心
身体只是组合物
身体由毛、发、爪、齿、皮、肉、筋、骨、骨髓、脾、肝、肺、心、粪、尿、血、黄水、唾液、汗液等组成。逐一审视,会发现它们无一恒常,都在不断衰败、脱落、腐坏或变化。想让它们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因此是“无常”。当它们要变化时,从不曾征求我们的同意,不受我们控制,因此是“无我”。有些人可能对某个部分观察得特别清楚,那就专注观察那个部分,如头发、皮肤或骨骼等,见其“无常”与“无我”。例如,观察头发不断变化、脱落;或皮肤必然会起皱;死后会腐烂。至于骨骼,也必然会腐朽、脱落,如牙齿,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死后,只剩下骨灰。想让它不变是不可能的。它要脱落、要起皱、要腐朽,从不曾顾及我们,也从不曾先征求我们的同意。因此,它不属于我们。
身体是不净之物
身体是不净的,只有一层皮包裹着污秽。在这层皮上任何地方钻个洞,都会有臭秽之物流出。如毛孔有汗垢;头皮有头屑;大便道更是如此,有最臭的粪便;小便道有腥臭的尿液流出。仔细观察,去公共厕所时,会闻到尿骚味弥漫。臭秽之物不断从各个孔道流出。要让心明明白白地看到:活着的时候尚且如此腥臭腐朽,死后又将是何等景象?
身体必将老、病、死
身体是无常的,必将经历老、病、死。死后,必然会腐烂、败坏,这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因为变化无常而痛苦,因衰老而痛苦,因病痛而痛苦,因临死前的折磨而痛苦。我们无法执着地命令它“不许老、不许病、不许死、不许衰败”,它不听我们的。它不受我们控制,因此是“无我”。
我们也将如逝者一般
思惟已故的祖父母、亲友或父母,他们死后的状况是怎样的。然后反观自身,我们的这个身体,五十年、一百年后,也将和他们一样。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配偶还是子女,也都将如此。问问自己:一百年或两百年后,我们所爱、所恨的人,能避免像那些逝者一样死亡、腐烂、败坏吗?死后,他们的身体又是怎样的状态?
身体只是元素或食物
这个我们误以为是“我”或“我的实体”的身体,实际上只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每天饮食、呼吸进去的元素或食物而已。无论是食物、水、空气还是热量,全都属于自然。我们一生要伤害、吞食多少大小动物的血肉和器官,多得数不清。我们可曾善待过它们,或将功德回向给它们呢?我们全身的毛发、指甲、牙齿、皮肤、肌肉、骨骼和内脏,全都由他者的血肉长成。但我们却执着它为“我所有”。即使再怎么珍惜、爱护、牵挂自己的身体,最终也难免一死,腐烂败坏,将元素归还给自然。坚硬的部分,将回归土大;液体的部分,将回归水大;风、火二大也将回归其自然本性。因为我们只是向自然借来使用。至于心或识,它也是一种自然元素,最终会消融于空性之中,回归自然。除非心中还有执着,即尚未断尽烦恼欲望,或尚未证得涅槃,那么识元素就会再次与地、水、火、风、空元素结合,至于会投生为何物,则由善恶之业所决定。
观察时必须保持“念”
在观察身体实相的过程中,如果失念,心就会对眼前的人或事,或过去未来的人或事,或自己的身心状态产生念头造作,从而生起喜悦或不悦、爱或憎。这会使“念”偏离对身体实相的观察,即忘记了要观察身体的实相。此时,要以“念”觉察到、感觉到或了知到,然后回来继续观察身体的实相。但很快,又会失念。那就再次以“念”觉察到,然后回来继续观察。就这样不断地做下去。必须在观察中时刻保持“念”。因为若“念”失,“定”就失,“慧”也失;若“念”在,“定”就在,“慧”也就在。也就是说,心会接受实相,不再错误地认为身体是“我”、“我的”或“我的实体”,或不再误以为这个身体里有一个“我”或“我的”。
必须有精进与忍耐
必须有精进(Viriya)和忍耐(Khanti),去成千上万、百万次地反复观察上述实相。每一次观察,都必须终结于死亡、腐烂、败坏,化为地、水、火、风、空元素,荡然无存,不留下任何可以执着为“我”、“我的”或“我的实体”的东西,直到心接受这个事实。不要刚开始观察,就去制造一种“放下”的情绪,以至于哭泣或对生活、工作产生厌倦。也不要刚开始观察,就用心力去强行压制,以求快速产生“看破、放下”的感觉。这样做会导致胸闷、身体冰冷或各种不适。
当心接受身体的实相时
何时心完全接受了对身体实相的观察,那种观察的念头就会立刻从心中消失。一种奇妙的感觉会生起,当事人自己能够体会到。只有一种轻盈的感觉,仿佛没有了身体,或如同能在空中行走。同时,心会自己放下对身体、对“我”是“我”或“我的”的错误执着,彻底放下。这并非我们刻意制造一种“放下”的情绪,以至于哭泣或厌倦生活,但内心其实依然执着、厌恶或渴望。那种状态是迷失。
当达到这个阶段,即使再试图去思惟身体的实相,心也不会再起这种念头了,无论怎么努力都想不起来。因为心已经觉悟、饱足于对自己和他人身体的实相的认知了。但如果还能思惟身体的实相,就必须继续思惟下去,不要轻易被烦恼欺骗。即使感觉再空、再轻,也要尝试继续思惟下去,直到那种奇妙的感觉生起,并且真的无法再继续思惟为止,才能放下那个念头。
转向观察心的生灭
接下来,要观察心这一边,即名法(Nāma-dhamma),包括: - 受(Vedanā):乐受、苦受,或不苦不乐受(中舍受)。 - 想(Saññā):记忆。 - 行(Saṅkhāra):念头造作及一切情绪,无论是善的还是不善的。
观察它们生起又灭去,生起又灭去……持续不断,毫不间停。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一闪即逝,一闪即逝……看不到任何东西是恒常的。心就会逐渐放下“心有实体”或“心是我的实体”的错误执着。
当能清晰、持续地看到生灭之后,接下来要专注观察感受、记忆、念头造作和一切情绪的“灭去”的那一面,不断地看到它们灭去、灭去……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光亮一闪即逝,持续不断。直到心对“心”或“名法”的实相感到饱足,认识到没有任何东西是恒常不变的实体,只有生起又灭去……最终空无一物,没有任何核心可以执着。心就会接受这个事实,同时彻底放下对“心”或“名法”是“我”、“我的实体”或“我就是它”的错误执着。心会自己放下,而非我们制造一种“放下”的感觉,但内心其实并未真正放下。
区别在于:如果是制造的感觉,心中依然会有对各种情绪的“厌恶”与“渴望”;但如果是如实知见后心自己放下,就不会再有对任何情绪的“厌恶”与“渴望”。心回归其清净的自然本性,即与宇宙同一的空性,无边界、无实体、无形相、无处所。这可称为“心即是法”,或“法与心合一”,或称为心成为“佛陀”(Buddho),即觉者、醒者、喜悦者。
方法四:观察五蕴或四念处
色(Rūpa)或身体
对于有些人来说,放下对身体的执着或许不难。仅仅是看到老人、病人、死人,看到火葬或土葬,看到尸体火化后只剩下骨灰,就可能心生感悟:身体是无常的,没有任何实体可以执着。于是他们便放下了错误的执着。或者,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某种思惟方式,能不难地让心放下对身体的执着。或者,当自己身患重病、住进医院时,可能立刻就能看清事实:这个身体就像一辆破车或一艘破船,坏了就要送去修,修好了就继续用,修不好了就得报废,就像废车、废船的残骸。从而觉悟到:身体并非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它必然会老、病、死、败坏,这是不可避免的。心便会放下对身体的执着。
受(Vedanā)
身体的执着放下了,但还有“受”,即乐受、苦受和不苦不乐受。在病痛中,必然只有剧烈的疼痛,即“苦受”。此时,必须加紧观察“受”的实相:这疼痛不适的感受,仅仅是“心所”(Cetasika),即当“识”元素生起,去了知色、声、香、味、触、法时,与识同时生起的一种状态。每一次“识”生起,必然伴随着三种“受”中的一种。“受”无法单独生起,也不会有漂浮的“受”而没有“识”去感知色、声、香、味、触、法。反之亦然,“识”元素也不会在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来触对眼、耳、鼻、舌、身、意时凭空生起。
因此: - 当“色”从眼前消失,“知色”的眼识也随之熄灭,“受”也必然同时熄灭。 - 当“声”从耳边消失,“知声”的耳识也随之熄灭,“受”也必然同时熄灭。 - 当“香”从鼻端消失,“知香”的鼻识也随之熄灭,“受”也必然同时熄灭。 - 当“味”从舌上消失,“知味”的舌识也随之熄灭,“受”也必然同时熄灭。 - 当触身的物体离开,“知触”的身识也随之熄灭,“受”也必然同时熄灭。 - 当心中的念想消失,“知此念想”的意识也随之熄灭,“受”也必然同时熄灭。
因为“受”无法单独漂浮存在。
一切“受”,无论是乐受、苦受还是舍受,都是无常的。它们因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缘而生起,生起“识”元素去了知。当因缘消散,“受”也必然熄灭。因此,无法禁止“受”的生起,生起后也无法禁止它熄灭。也无法只选择合自己心意的舍受或乐受,而不要苦受。
“受”仅仅是“名法”,无实体、无形相,因缘而生,因缘灭而灭。因此,它是“无常”。它不属于任何人,不是“我”,也不属于“我”,因为它只是随因缘自然生灭。因此,不是“我”有“受”,也不应执着“受”为“我所有”。当不执着它为“我所有”时,就不会有因“受”而痛苦的“我”。“受”就只是“受”而已,随因缘生灭不息。无法禁止它生起,也无法只选择自己喜欢的快乐之受,而排斥痛苦之受。当痛苦之受生起时,无法随心所欲让它快点消失;当它消失后,也无法保证它不再生起。因为只要有因缘,“受”就必然会再生。它不受我们控制,因此是“无我”。只要我们还没死,就必然会有色、声、香、味、触、法来触对眼、耳、鼻、舌、身、意,因此必然会有乐受、苦受、舍受轮番交替。这使得我们必须也承受“苦受”,无法只选择“乐受”或“舍受”,因此它是“苦”(Dukkhaṃ)。
要如实地了知这一点,善巧地将此认知时刻铭记于心,直到心接受这个事实,自己放下对一切“受”的错误执着。因为它看到,无法只选择自己喜欢的乐受或舍受,而把苦受丢掉。这就好比,越是挣扎着想脱离痛苦,反而越痛苦。如果还“爱乐憎苦”,就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必须放下乐与苦,因为看到它们无法被选择。这样,才能从痛苦中解脱,即不再有心的痛苦,只剩下身体的痛苦。
身体的疼痛依然存在,是因为导致身体疼痛的因缘还存在。当导致身体疼痛的因缘消失时,身体的苦受也随之消失。当医生给了止痛药,疼痛处的神经系统被暂时阻断,疼痛就暂时消失了。或者当医生治愈了疾病,刺激神经的事物不存在了,疼痛就消失了。或者,导致疼痛的原因消失了,疼痛也就消失了。但它必然会因其他原因而再生起苦受,因为乐受、苦受、舍受必然会不断地生灭轮转。
因此,不要试图将心保持在“中性”、“正常”或“空空”的状态,那只是“舍受”,无法只保留这一种。因为每当“识”生起去了知色、声、香、味、触或念头时,必然会伴随乐受、苦受或舍受。如果试图只保持舍受,会更加痛苦和焦虑,因为它不随心所欲,违背了自然实相。这样做,每当有人或事来触动,情绪爆发会比正常情况更严重。这是很多修行者会遇到的问题。如果不向外爆发,就会更加压抑心,使其更加死寂。这样,一受刺激,就更容易烦躁,然后会误以为是“定”力不够,于是更加努力让心死寂,直到身体出现异常,例如:厌食、舌苔白厚、消化不良、头晕目眩、胸闷、无力、无故发烧、身体系统紊乱、五蕴失调,甚至需要住院。解决之道是:停止让心保持“静静的”、“漠然的”、“空空的”、“轻盈的”,不要试图让心感觉“中性”,也不要试图将心一直保持在“正常”状态,或试图让心中没有任何感受。
正确的修行是,必须“如理作意”,即持续不断地、不间断地观察“受”的实相。在观察的过程中,如果失念,心就会对眼前的人或事、过去未来的人或事,或对自己正在观察的身心之“受”产生喜恶、爱憎,或担忧、排斥、想让不悦的苦受消失等念头。这会使“念”偏离对“受”之实相的观察。此时,要以“念”觉察到,然后回来继续观察“受”的实相。就这样不断地做下去,在观察中时刻保持“念”。因为若“念”失,“定”就失,“慧”也失;若“念”在,“定”就在,“慧”也就在。当念、定、慧圆满时,只需静静地、空明地观察“受”的实相,不生起任何“想要”或“不想要”,放下乐与苦,只见到无常、苦、无我。
心、想、行
心或意,在进行思惟、考量时,是无实体、无形相、无处所的,它只表现为一种能量,然后就消失了。每当思惟生起,就会有一种称为“意识”(Mano-viññāṇa)的“识”元素自动、即刻地生起去了知那个思惟。每一次都如此,这是自然法则。不可能只有思惟而没有“识”元素同时生起。当思惟灭去,了知此思惟的“识”元素也同时灭去。
在“识”元素生起去了知思惟的同时,也必然会伴随乐受、苦受或舍受(即中性的、不苦不乐的感受)中的一种。不可能不生起任何一种“受”。例如,当我们思考工作或日常事务时,感觉不到苦乐,那是因为生起了“舍受”,而非没有“受”。当每一次思惟灭去,了知此思惟的“识”也随之灭去。因此,“受”,无论是乐受、苦受还是舍受,也必然同时灭去。因为“受”无法单独漂浮存在。所以,“受”无法停留在那个仅作为“名法”进行念头造作的心中,也无法停留在那个无实体、无形相、无处所、生灭迅疾的“识”元素中。因此,苦受(如疼痛、压抑、心不清明、心慌、消沉等)、乐受和舍受,都无法停留在心或识中。
为何感受或情绪能长久停留在心中?
我们之所以感觉某个“受”或情绪能长久停留在心中,是因为我们不断地、频繁地将那个“受”或情绪“记忆”起来,同时错误地执着那个“受”或情绪为“我所有”,或“我”就是那个“受”或情绪,而没有以念与慧去了知。
频繁地“记忆”起某个“受”,实际上只是对过去喜欢或不喜欢的“受”的念头造作,并非五蕴中那个作为自然记忆功能的“想蕴”(Saññā-khandha)。如果只是自然的记忆功能,就不会夹杂心的痛苦,因为它只是在当前接触色、声、香、味、触、法时,了知“这是什么”而已。 - 想(Saññā):只能了知“这是人”、“这是女人/男人”、“这是动物/东西”,没有更多细节。好比照相机拍出的静止照片。 - 行(Saṅkhāra):是念头造作,它接续“想”,添加了细节,让我们知道“这是谁”、“做什么工作”、“与谁有关”,或“这是谁的宠物”、“这是谁的东西”等。它会补充细节,使信息完整。好比摄像机拍出的动态影像,信息比照片更丰富。
如果只有“记忆”,而没有念头造作去执着“受”或情绪为“我所有”,就不会有烦恼欲望或心的痛苦。因此,将过去感受过的苦乐或情绪“记忆”起来,并非真正的自然记忆,而是对过去感受的“念头造我”,并同时错误地执着它为“我所有”,而没有以念与慧了知。
心与心所(Cetasika)
心或意,其含义相同,即“思”与“知”。“知”,指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去知(知感受、知记忆、知思想、知情绪)。其中,具有“知”这个状态的心,有另一个名字叫“识”(Viññāṇa)。
心理状态是“心所”,即与心相伴的事物,在心或识去了知眼、耳、鼻、舌、身、意所缘时,与心同时生灭。这也就是受、想、行。
在修行中,必须以智慧将作为身体感受的“身受”与作为心理状态的“心受”彻底分开。如果分不清,修行会遇到很大困难。因为“心受”生灭迅速,而“身受”熄灭缓慢,需要等身体的病痛痊愈才行,这需要对症治疗。因此,对于身体的感受或一切身体状态,我们不要去纠结,不要排斥、希望它快点好。应随缘治疗,并时常思惟,让心接受事实:病痛有时不治也能自愈,有时需要治疗才能好,有时治也治不好,最终人人都有一死。如果能时常这样思惟并让心接受,就不会因身体的“受”而心生痛苦。如果纠缠于“身受”,就无法解脱痛苦,因为一直在挣扎、排斥它。无论排斥多久,也无法让“身受”彻底消失,这会成为证悟的巨大障碍,可能使证悟推迟多生多劫,并且会听不进法,因为心一直在烦躁地排斥“身受”。
当看到这个巨大的障碍后,就应当在每一个当下,让心接受“身受”的实相,然后放下它,这样才不会延误证悟。
心或意的“思”以及一切心理状态,都是“名法”,无实体、无形相、无处所。只有心理状态显现时我们才能感知到,例如:念头造作、思、量、寻、伺;排斥不喜之受或情绪的念头;想要获取事物或喜爱之情绪的念头;沉迷;记忆;意图;专注;心的苦乐舍受;念、定、慧;观照自心的造作;任何心理上的努力;守护自心的行为;努力让心保持宁静、空明、轻盈、舒适;“是我”或“我的”的感觉(这本身也只是念头造作,并非真有“我”);心的清净与不清净;信;惭、愧;慈、悲、喜、舍;嫉妒;厌倦;贪、嗔、痴、慢、见等等。总之,一切非身体、非身体状态、非身受的事物,都归入心理状态或心的范畴。
心或意的“思”以及一切心理状态都是“无常”的。它们仅仅是某种状态的显现、一种反应、一种出现、一种波动或一种悸动,是自然的常态,不属于任何人,不是“我的”,我也不是“它”。它们生起,然后灭去,生起,然后灭去,这是自然法则。没有任何东西是恒常不变、可以执着的。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死亡。必然会有合意与不合意的状态。无法选择只生起喜欢的状态,而不生起不喜欢的状态,因为它们是按其自然法则运行的。必须随缘承受痛苦,因此是“苦”。但当心能接受实相时,就不会痛苦。之所以无法选择,是因为它不属于“我”,不受我们控制,称为“无我”。
因此,不要试图去控制,或做任何心理操作来阻止任何状态的发生,即使是贪、嗔、痴。当任何情绪生起时,也不要因为不喜欢而强行让它快点消失。不要试图让心中再也没有任何状态,误以为只要一直观照,一切状态都会消失,只剩下空。这种错误的努力会让人感到压抑,可能导致头痛、眩晕、恶心、呕吐、肩颈酸痛、腹胀、消化不良、舌苔白厚、无故发烧、过敏,或引发某种身体疾病,并且无法导向解脱。
识(Viññāṇa)
识,即心或意在执行“知”或“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所缘时的功能。它是一种自然元素,是“名法”,即只有名字,不属于任何人,无实体、无形相、无处所,也不是“我们的识”。它有不同的名称: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样命名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识”并非从生到死只有一个,也并非人死后的“鬼魂”。它只是自然元素,只有在因缘具足时才会生起去了知,即:有色触眼、有声触耳、有香触鼻、有味触舌、有触触身、有法(念想)触意。当触对的因缘消失,“识”也必然熄灭,无法单独存在。无法禁止它生起,也无法禁止它熄灭。只要有因缘,“识”就会生起。当因缘消失,“识”也必然熄灭。它不受任何人控制,也无法被执取。因此,它不是“我的识”,也不是“我之识”。不要误解“识”是人死后的鬼魂,从身体里飘出去。如果心中一直有这种错误的忆念,就会把“识”元素当成一个有实体、有形相的东西,像我们自己一样,或当成“我们的识”,然后就会误以为“我”就是那个“识”。这样,就会一直感觉有一个“我”或“我的实体”存在。这都是因为心中一直有那种错误的忆念,称为“不如理作意”。
“识”是无实体、无形相的元素。因此,当“识”元素生起去了知色、声、香、味、触、法时,是看不到、感觉不到“识”元素的形相或状态的,只会了知“被知之物”,即色、声、香、味、触、法而已。
举个例子以便更清晰地理解:现在有些房子门口装有自动感应灯。当有人站到门口,灯就会自动亮起,无需人去开开关。当那人离开门口,灯也会自动熄灭。可以这样比喻:何时心或意生起念头造作,就好比有人站到了门口。“识”,这种无实体、无形相、无处所、不属于任何人的自然元素,就好比门口的灯光,会立刻、自动地“亮起”或生起,去了知那个念头。这是自然的常态。因为只要有念头生起,就必然会有“识”元素自动、自然地随之生起。并非“识”是“我们的”,然后由我们去造作让它生起。当念头造作熄灭,就好比门口的人离开了,“识”元素——那盏门口的灯光——也立刻、自动地熄灭了。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念头生起,“识”就生起;念头熄灭,“识”就熄灭。这都是自然的常态。因此,“识”是无实体、无形相、无处所,时刻生灭的元素,不属于任何人,也不是“我们的识”或“我之识”。并且,每当“识”元素生起去了知念头时,也必然会同时、自动地伴随乐受、苦受或舍受中的一种。这也是自然法则,不受任何人控制,因此是“无我”。
必须训练心
必须以“念”与“如理作意”来训练心,使其理解色、受、想、行、识(五蕴)或身、受、心、法(四念处)的实相,以及它们的生因与灭因,如前文所述,持续不断,不间断地用训练有素的念、定、慧去观察。
当任何念头造作或状态显现于心时: - “念”会立刻觉察。 - “定”之心不会动摇。 - “慧”会如实了知每一个念头造作或显现的状态,无论那状态是合意的还是不合意的,是乐受、苦受还是舍受,是清净还是暗昧,是善还是恶,是功德还是罪业。包括那种“是我”、“我的实体”、“我所有”的感觉或念头(实际上这本身也只是生起或造作的状态,并非真有“我”),了知所有这些状态,都只是自然生起的某种事物,也必将自然灭去。没有任何东西是恒常不变、可以执着为“我”、“我的”或“我的实体”的。它们只是随因缘自然生灭。即使是合意的状态,也无法永远保持;即使是不合意的状态,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排斥、令其消失。因为它们是“无常、苦、无我”。
必须这样了知,直到心接受这个事实,才会放下执着。(隆布曼·布里达陀在《蕴解脱相应法》中写道:要知于“心之源头”或“躁动的心之源头”,若知于“心之末梢”则立刻错了。这大概意思是,如果一个念头造作或状态生起后,没有从它开始时就了知,而是事后才知,就叫“知于心之末梢”。)
“想解脱痛苦”是必须放下的最后一道欲望
即使心已经接受了实相,也必须停止“想要”或停止挣扎着探寻“涅槃”,或彻底停止“想解脱痛苦”的欲望,才能遇见涅槃。因为如果心还不停止“想要”,或不停止探寻涅槃,就会一直感觉“我”或“我的实体”还没达到、还没证得涅槃。因此,就会继续探寻下去。越是探寻,就越是痛苦,因为它总是不随心所欲。越是痛苦,就越是挣扎着寻找出路。就这样循环往复,像小孩玩“蛇吃尾巴”的游戏。他们不知道,无法解脱痛苦,正是源于那“想解脱痛苦”的欲望或挣扎本身。
何时他停止了“想要”,停止了探寻出路,他才能解脱痛苦。这是因为,“想解脱痛苦”或“想证得涅槃”的欲望,本身依然是“欲望”(Taṇhā),是必须放下的最后一道欲望。只要还有“欲望”,就还未尽痛苦,因为“欲望”是苦的“集因”。当“欲望”彻底熄灭,痛苦才彻底熄灭,这称为证得涅槃。
要点观察:
放下“想解脱痛苦”或“想证得涅槃”这道欲望,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易。因为“修行到最后会证得涅槃,即痛苦的熄灭”这句话,会让渴望涅槃的人错误地去修行,试图只留下快乐,而完全消除痛苦,以为这样才能解脱痛苦、证得涅槃。因此,只要自己的心还未止息痛苦、只剩下快乐,他就不会停止探寻。一探寻,就无法止息痛苦;越是痛苦,就越是探寻出路。这就是“爱乐憎苦”本身。只要还有爱憎,就还未尽烦恼欲望。只要还有“欲望”(躁动之欲),就必然有痛苦。必须训练心,让它看到这个过患:无法解脱痛苦或证得涅槃,正是源于“想解脱痛苦”或“想证得涅槃”的欲望本身。何时能停止这个欲望,停止探寻出路,才能真正解脱痛苦、证得涅槃。直到心完全接受这个教导,彻底放下“想证得涅槃”或“想解脱痛苦”的欲望。
正如正自觉佛陀在《基里摩难陀经》中对阿难尊者所说:“阿难,最初,当如来尚未觉悟苦与乐是相伴相随时,我也曾执取善心(想获得善与乐),期盼时时快乐,而不要有痛苦,于是便精勤修习善心。但结果是,得到多少快乐,就伴随产生多少痛苦。后来,我以智慧眼观察,清晰地见到苦与乐是相伴的。了知之后,我思量对策,想将苦与乐分开,那真是艰难无比,几乎无计可施。于是如来便放下了,将乐还给了苦,即将心交给了欲望(放下心,使其成为中立或舍心。但不要误解这“舍心”与作为“不苦不乐”感受的“舍受”是同一回事。详见方法一中的相关标题)。当我将心交给欲望之后,涅槃之乐便前来接引我,使我在那一刻即证涅槃(即生证得涅槃)……”
因此,要放下那“将乐从苦中分离出来”的努力,或放下那“只留乐”的努力。必须不“爱乐憎苦”,放下善与不善,即“喜”与“憎”。心中没有任何为了解脱痛苦而暗中进行的修行或操作。不沉迷于任何事物,不自己胡思乱想,而是了知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情绪,从它开始生起时就了知。例如,“是我”、“我的实体”、“我所有”的念头;意图、专注、努力、探寻、思量、忧虑、犹豫、烦躁、厌倦、消沉、想要、不想要、喜欢、不喜欢等。同时,不排斥不喜欢的事物或状态,也不试图压抑。并彻底放下心中隐藏的“想要”或“不想要”,断绝一切探寻因果的念头。即,只是静静地知、空明地知、仅仅是知。或能将“知”从“念头”中分离,或将“念头”从“知”中分离。任由色、声、香、味、触、法(即感受、记忆、念头及一切情绪,无论是乐受如通透、轻安,还是苦受如压抑、沉闷,或是舍受如不苦不乐、空荡),以及善、不善或中性的念头与情绪,自然地触对眼、耳、鼻、舌、身、意,然后自然地灭去。
这就像电话铃声不断响起,因为一直有人打进来,但如果没有人接听,它自己就会停止。即,没有“我”去承受或享用那些来触之物,也就没有了痛苦的“我”。然后,心的本来面目或清净之心就会自己显现,或与自然合一,那是一种与宇宙同一的空性,无边界、无实体、无处所。至此,无明、欲望和执取(即执着或不愿放下)将彻底熄灭。当无明、欲望、执取熄灭,痛苦亦熄灭。这称为证得涅槃。
诚如佛陀在《缘起法》中所言:“诸法因缘生,如来说其因,亦说其灭法。”或“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即:缘于无明,故有行;缘于行,故有识;缘于识,故有名色(五蕴);缘于名色,故有六处(眼耳鼻舌身意);缘于六处,故有触;缘于触,故有受;缘于受,故有爱(Taṇhā);缘于爱,故有取;缘于取,故有有;缘于有,故有生;缘于生,故有老死。如此,忧、悲、苦、恼、愁闷便具足了。
当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如此,忧、悲、苦、恼、愁闷亦随之熄灭。一切苦蕴的熄灭,便是如此。
当临近死亡时,感知眼、耳、鼻、舌、身的“识”会先熄灭。因为临死时,眼不能见,耳不能闻,鼻不能嗅,舌不能尝,身体对疼痛没有反应(例如,患有严重癌症的人,在即将命终心空寂时,身体对剧痛毫无反应)。只剩下“意识”,去了知当时刻意想的念头,例如“佛陀”等。(对于已证涅槃者,作为欲望或散乱的念头造作早已不存在。)最重要的是,念、定、慧始终圆满具足。当念头生起,意识便生起;念头灭去,意识便灭去。当新的念头再生,新的意识也再生;当那念头灭去,那意识也灭去。直到最后一个念头灭去,了知这最后一个念头的意识,也与念、定、慧一同熄灭,如同烛火熄灭一般。不会再有一个作为“我”的心或识从身体里飘出去投生到任何地方,或成为任何东西。
对于那些在当时已无必要再思考任何事情、也无任何散乱念头的人,他们可能安住于越来越微弱的出入息上。当呼吸停止,了知呼吸的“识”也与念、定、慧一同熄灭。而对于那些已能时刻保持“空明觉知”的人,当死亡来临时,他们也只是安住于“空明觉知”中,直至熄灭。
曾有人请问正自觉佛陀:正自觉佛陀及诸阿罗汉圣者,在“灭度”(ดับขันธ์ปรินิพพาน,蕴灭般涅槃)之后,其“识”的状态是怎样的?正自觉佛陀回答说:“识,如薪尽火灭。”
吉祥生活三十八事
(《吉祥经》 Mangala Sutta)
- 不与愚人为伍。
- 结交智者。
- 礼敬值得礼敬之人。
- 居住于适宜之地。
- 曾积福德。
- 立身端正。
- 博学多闻。
- 掌握技艺。
- 言语善巧。
- 奉养父母。
- 养育子女。
- 善待配偶。
- 工作不拖延。
- 乐于布施。
- 奉行正法。
- 扶助亲族。
- 从事无过失之业。
- 远离罪恶或不善。
- 不饮酒(包括毒品与赌博)。
- 于法不放逸。
- 心怀恭敬。
- 谦卑柔和。
- 知足常乐。
- 心怀感恩。
- 适时闻法。
- 坚毅忍耐。
- 易于教诲。
- 亲近沙门(寂静者)。
- 适时论法。
- 修持苦行(Tapa)。
- 修持梵行。
- 彻见圣谛。
- 证悟涅槃。
- 心不动摇于世间八法。
- 心无忧愁。
- 心离尘垢(烦恼)。
- 心得安稳(证得涅槃)。
(注:最后的捐赠者名单及印刷信息在此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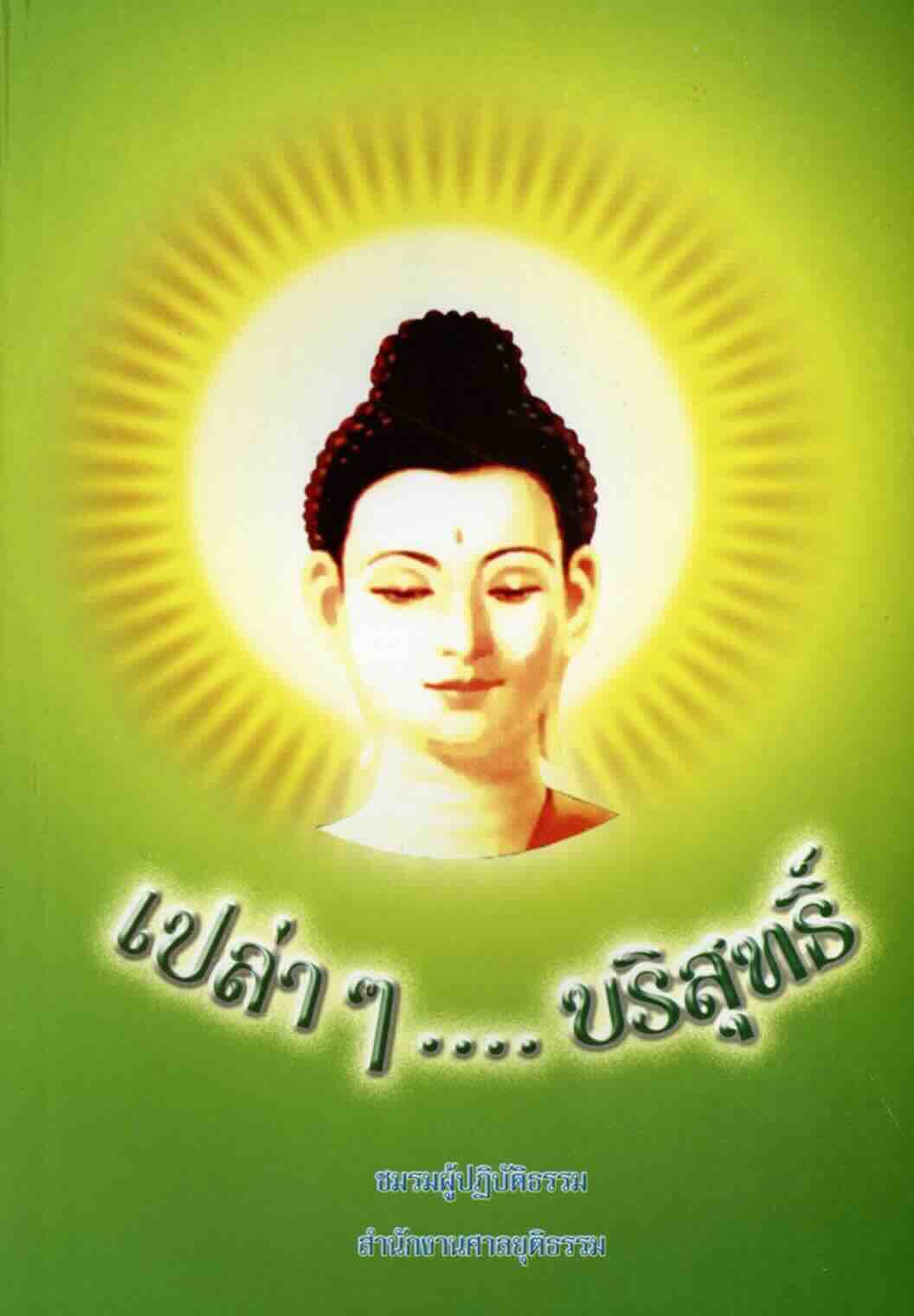 |
本文翻译自泰语书籍如感兴趣请下载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