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结束吧
隆塔纳荣萨尊者, 南传上座部佛法, 精选 ·Let It End - Luangta Narongsak Kheenalayo
彻底结束吧 - 隆塔纳荣萨尊者 - 智宁居士译 - 摘要
修行是放下一切,没有人得到什么,没有人成为什么,那个‘渴望者’彻底熄灭,毫无剩余。
目录
- 前言
-
第一章 以正见及对五蕴的理解为开端
- 正见是走向离苦之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对佛法原则有准确清晰的理解,就如同指引正确禅修方向的罗盘。
-
第二章 念、定、慧
- 念、定、慧是五蕴中的“行”,我们必须依靠它们作为修行的重要工具,理解其不同层次有助于为通往涅槃彼岸的整个旅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
第三章 引蛇出洞,看见那个“我”在解说
- 经咒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工具,以保持正念,从而能够观察到在心中思考或“解说”的那个“我”,这是为了看清识蕴与心所运作的过程,从而放下对五蕴的错误执取。
-
第四章 “我是知者”,这即是心
- 修行者必须及时了知正确的目标。那个所谓的“我”,就是心或识蕴,但它实际上并非“我”,而只是“蕴”。我们必须全面了知所有蕴,才能完全放下。
-
第五章 所缘存在,但心是空寂的
- 只需单纯地了知五蕴或“行”的生灭,不执取,不随之流转,也不排斥各种状态,便会见到那空寂的“心”,它好比空寂的天空,飞鸟掠过,不留任何痕迹。
-
第六章 做个观众,而非演员
- 观心,要像看电影戏剧一样,不要自己跳进去当演员。只需做个观众、知者,只是单纯地了知、看见念头在空寂的心中生灭,其中没有一个“我”去参与。
-
第七章 理解至心
- 要有念与慧,及时了知生起的迷失,不必害怕。只需觉醒过来,趋向那个能知者或识蕴,观察那个试图挣扎探寻的主体,当停止迷失造作时,就会达到本来清净心。
-
第八章 智随法后
- 让心的造作生灭先行,不要有一个“我”预先去发起念或慧。让它作为心的自然造作先行生起,然后“智”会自然跟在其后,直至迷失的造作终结。
-
第九章 何为无明
- 试图保持正念、努力不让自己迷失,这本身立刻就是迷失和无明。当执取终结时,会见到空寂的“心”。并且,连那纯净空寂的“心”也不执取,才是真正地终结无明。
-
第十章 彻读自心
- 要用正念在每个当下彻读自心,观察并及时了知是否有烦恼、贪爱。放下执着,放下欲望,放下那个“索取者”,而非为了“索取”而放下。
-
第十一章 当下知,当下舍,当下放下一切
- 欲望是极大的痛苦。必须及时了知自心,在每个当下放下欲望,即便是对涅槃的渴望。修行是放下一切,没有人得到什么,那个“渴望者”彻底熄灭。
-
第十二章 越寻越堵(即“贪”)
- 挣扎探寻“法”是烦恼,是贪爱。越是寻找,越是堵塞。停止思考,停止造作,停止挣扎探寻,并时刻放下那个“我”,便会见到那空寂的知元——“心”。
-
第十三章 有一个“我”去获取
- 时刻保持念、定、慧,及时了知那错误地执取五蕴为我们自我的迷失。放下那个“我”,放下那“身为我”的感觉。没有一个“我”去获取,当承受者终结,烦恼便终结。
-
第十四章 守护正念,放下能知者
- “念”是贯穿始终最重要的核心。要让念观察“能知者”,不要关注“所知者”。见到能知者,才能真正地放下能知者,最终,连那“放下者”本身也必须放下。
-
第十五章 三种知以及次第放下
- 知有三种:心或识蕴,念定慧,佛陀或识元。放下亦有三对:放下所缘与能知者;放下念慧与五蕴;放下对空寂之心的执着与在其中生灭的五蕴。
-
第十六章 彻底结束吧
- 对五蕴的错误执着,以及错误地造作出一个“我”去守望、去探寻,是无法终结造作之行的。要重新正确地理解自然,放下一切,彻底结束吧。
-
第十七章 言语道断
- 当不再执取造作的自然为“我”,当错误的执着终结时,便会即刻见到空寂的“心”。当对这两种自然都不再执取时,心自然了知于心,苦尽、烦恼尽,无需再有任何言语解释。
-
第十八章 解脱中的假名
- “假名”是心的造作,“解脱”是“心”。无需用假名去探寻解脱。只需停止对假名的执着,当下即是解脱。既放假名,也放解脱……即是涅槃。
-
第十九章 无明是障心之幕
- 心即是法,见心即见法。空寂的心本已存在,只因“无明”障蔽。放下对一切“行”的错误执着,当无明熄灭时,如同无明之幕被揭开,便会即刻见到空寂的“心”。
-
第二十章 恒常空性之因
- 恒常的空性,必须源于智慧的审视,视世间为空,并且空于错误的执着,彻底根除“我”和“我所”的见解,而非迷失地去创造一个空性。
-
第二十一章 无字天书
- 文字也是假名安立。当理解至心时,放下一切,放下执着,甚至放下“知”。没有谁在知,从一开始就没有谁在修行。这部经书,便不再需要任何文字……空寂,纯净。
前言
寻求法、寻求涅槃、寻求离苦之道的人,却不知道什么是“法”,什么是“涅槃”,什么是“苦”,什么是苦的起因,以及如何才能灭苦,于是便盲修瞎练,浪费了许多年的漫长时光。
“法”即是谛法或自然的实相,它有两种:一种是造作的自然,称为“行”(Sankhara),包括身体之外的一切事物以及五蕴,即色、受、想、行、识。所有的“行”都遵循三法印的法则,即无常、苦、无我。它们是变化的、是苦的、无法保持原状,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自我。另一种自然是“知元”(dhatu-ru)或识元(viññāṇa-dhātu),它是不造作的自然,称为“无为法”(Visankhara),是自我的空性,如同宇宙或自然的空性一般,没有形状,不显现任何作为或状态。它有许多假名,如“本来清净心”、“法界”(dhammdhātu)、“不死界”(amatadhātu)、“大空”(mahāsuññatā)或“佛陀”(Buddha)。
我们无法用属于造作自然的五蕴去挣扎探寻“心”,因为“心”没有任何标记或目标。唯一的方法就是“停止”——立刻停止成为造作者,那么“心”就会自动地、即刻地变为不造作。因为造作与不造作不可能在同一心识刹那中并存。或者,当不再错误地执着五蕴是我们、是我们的自我时,就会见到“心”,并且连“心”也不执取,苦便会熄灭,这被称为“涅槃”。
因此,在每个当下的心识刹那,不要迷失地将心外送,去关注被感知的所缘。要让念住于心、观照于心、知晓于心、观察于心、舍离于心、放下于心。在每个内六处与外六处接触的刹那,心或识蕴会去了知所缘,即色、声、香、味、触、法所缘(受、想、行),然后会持续传递新的法所缘。但我们常会迷失地感觉“我们自己”是知者、是思虑造作者,如同在心中自言自语。
如果能时刻让念住于心、观照于心,在每个当下心识刹那不失念地去关注被感知的所缘,就会看见作为能知的“心”(识蕴)与作为所知的“法所缘”,在心中持续地生灭。此时,智慧就会生起并了悟:那种“我……”的感觉,例如,我是看者、是知者、我是思考者,我高兴,我伤心……都仅仅是“行”的造作,其中并无众生、个人、实体、我们、他们。这样,无明便会终结,不再错误地执取五蕴是我们、是我们的自我。
如果已经用心修行了很长时间,却仍然困顿迷惑,就应该警觉:修行了这么久,为什么在当下看不到任何解脱的可能?这样就必须去请教真正的善知识,请求指点。不要带着自己的知见和傲慢去见他们,而应以谦卑恭敬之心前去。
当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指点,而我们自己也以忍耐之心精进不懈,但如果仍然模糊不清,那么在每次阅读、听法、修行之前,就必须发愿:撤回过去一切生世中所发下的任何愿望,并向过去所有生世的佛、法、圣僧,以及父母、师长和恩人忏悔,因为这些可能是阻碍我们生起正见智慧的障碍。之后,再发愿,祈请佛法融入自心。要反复发愿……然后专心致志地阅读、听闻,并以信愿和精进持续不断地修行,必定能亲身体证其成果。
第一章 以正见及对五蕴的理解为开端
要到达目的地,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如何去以及为何而去。同样,走向离苦的旅程也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实践方法。如果有了清晰的理解,就能确保旅程不走弯路。
因此,正确的理解或拥有“正见”(Sammā-diṭṭhi)就如同一座主罗盘,指引我们不偏离航道,迅速地趋向目标。对于修行者来说,正见是走向离苦之路最重要的一环。
首先,我们来为六处(Āyatana)和四圣谛的修行打下理解的基础。
“六处”,意为连接处或沟通的工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外在的,被称为“外六处”,如色、声、香、味、触、法所缘。另一部分是能感知的主体,被称为“内六处”,如眼、耳、鼻、舌、身、意根。但在修行层面,真正去感知的主体,其实是“心”或“识”(Citta)。因此,各种状态,无论是身体的感受还是心的感受,乃至念头(行)、记忆(想),这些都是心可以感知的,总称为“法所缘”(Dhammārammaṇa),都属于“外六处”。
至于“四圣谛”,包括:
- 苦谛(Dukkha):身心的不适、苦恼。
- 集谛(Samudāya):苦的起因。
- 灭谛(Nirodha):离苦或诸苦的熄灭。
- 道谛(Magga):走向离苦的正确道路。
修行必须透彻地理解四圣谛的两对关系。第一对是“苦与集”,第二对是“灭与道”。
如果我们修行时,总是关注各种状态,介入各种状态,去调整它们,想要乐受而排斥苦受,这样的修行是“心向外送”。心随外六处而去,这便是“集”,是导致痛苦生起的原因。其结果便是“苦”。
正确的方法是,我们必须进入“灭与道”。经云:“心清楚地看见心,即是道;心清楚地看见心的结果,即是灭。”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先清晰地将心与所缘分开。心是“能知者”,所缘是“所知者”。
当于每个当下去了知任何所缘时,要安住于“心”,不要去关注被了知的所缘。“心清楚地看见心,即是道”,就是看见那个“能知者”,即心或识蕴。通常,心或识蕴去了知任何所缘时,会与受、想、行(称为“心所”,cetasika)一同运作。这与阿毗达摩(Abhidhamma)中所说的“色、心、心所、涅槃”是一致的。“色”即是身体,“心”即是识蕴,“心所”即是受、想、行,而“涅槃”则是终止对这一切的错误执着。
因此,当我们了知任何事物时,就好像我们心里总有一个人在说话、解说、思考、揣摩,持续不断。这个过程永无止境,除非生命终结。我们了解这些,是为了看清这只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应让生命的过程随其自然地运作。这是五蕴的运作过程,它本身并非烦恼贪爱,也并非涅槃。
许多人理解错误,试图在五蕴上下功夫,想让五蕴成为涅槃。他们去造作一个心境,不让乐受或苦受生起,只让它保持舍受(upekkhā-vedanā),最终变成了执着于舍受。
正确的做法是,必须记得事物是什么就是什么。五蕴是自然的过程,它不是烦恼贪爱,不是导致痛苦生起的原因。执着的痛苦,是附着在“心”上的“无明”(Avijjā)。
无明是缘起法(Paṭiccasamuppāda)的起点。因为无明为缘,生行;行为缘,生识;识为缘,生名色(五蕴)。五蕴是后来才生的。因此,五蕴本身不是烦恼,五蕴本身也不是涅槃。错误地执着五蕴,那才是无明。要灭,就要灭无明,即灭除附着在那个知元上的错误执着。
当无明终结,知元便成了纯净的知元,即成了了悟、解脱之知,被称为“佛陀”(Buddha),意为觉者、了悟真理者、迷失尽除者。
“佛陀”即是本来清净心,它恒为佛陀,但并非涅槃。熄灭的,是附着在知元上的无明。无明尽除,即是对五蕴的执着尽除,以及对那个知元或空寂之心的执着尽除。隆塔玛哈布瓦长老开示:“本来清净心,在五蕴之外,当对五蕴的执着尽除后,如果还执着于心,想让它空寂,那还不是涅槃。”
因此,“涅槃”不是一个地方,不是某种状态。仅仅是附着在知元上的无明熄灭了而已。剩下的,是无明已尽的知元,被称为“佛陀”,并且不执着“我的实体是佛陀”。
这个佛陀,这个知元,本已存在于佛陀、阿罗汉、凡夫、畜生之中,存在于所有仍在轮回的众生之中。只是,存在于凡夫和众生中的知元,仍是迷失的知。直到无明尽除,它才变成觉悟之知、解脱之知。
这才是“正见”,是八正道中的正见。如果你修行,却没有对存在的自然实相有清晰的了悟,你的修行就会偏离。因此,八正道必须以正见为首。接下来的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才会全部正确。
第二章 念、定、慧
首先要好好理解“念”(Sati)。这个“念”是五蕴之一,它在整个修行过程中都至关重要。
如果刻意去设置一个“念”来守候观察心,这就是迷失地用五蕴根据欲望来造作“念”,这是无明。当预先迷失地造作出一个“念”时,就没有“念”来了知我们自己的迷失。在迷失地造作“念”的当下,如果能有“念”来了知,这样才是真正的“念”。
五蕴中的“念”、“定”、“慧”,仍然是“行”,遵循无常、苦、无我的法则。因此,当错误地执着“我们自己”是有念者、有觉知者时,就是错误地执取五蕴为“我”。
“念”
五蕴中的“念”,在内观(Vipassanā)的层面,有两个阶段:
-
迷失后觉知的“念”:这是一种念和慧,能了知那个迷失地将“我”投入思考造作的心识刹那。心迷失于思考造作,称为“迷失于行”。
- 总结:此阶段的“念”,是了知迷失的念。
- 不再迷失时的“念”:这是一种念和慧,来观察并看见五蕴,即色、受、想、行、识,全都是“行”,是无常、苦、无我。直到心如实地接受这个实相,然后放下对五蕴的错误执着。
“定”
“定”(Samādhi)有两个层次:
- 奢摩他(Samatha)阶段的“定”:这是训练“念”的阶段,控制心安住于一个所缘,如念诵“佛陀”或出入息,直到心不间断。当有了定的情绪,也可能会迷失于内在的定境之中,例如喜、乐、舍等情绪,这些都只是法所缘。此阶段的定,无论达到何种深度,都必须出定。任何层次的定境中的宁静,都必须出定,因为定的情绪也遵循无常、苦、无我的法则。当从定境中出来后,心力会非常强大,这时就应该立刻、持续地进行内观。
-
由内观阶段的“念”所生的“定”:
“念断,定断,慧断,法断……是苦。” “有念,有定,有慧,有法……不苦。” “念为大念,为大定,为大慧,为涅槃……离苦。”
“慧”
“慧”(Paññā)与念和定紧密相关,有三种层次:
-
闻所成慧(Sutamaya-paññā):这是通过反复听闻、阅读而成就的智慧,拥有正确、精准的基础知识,是八正道中第一项“正见”的智慧。要理解身心的自然法则:有造作的自然,即“行”;和不造作的自然,即“无为法”。没有任何一方是“我”。五蕴皆是“行”,五蕴不是烦恼,五蕴不是涅槃。痛苦源于错误地执取五蕴。
“心向外送……是集。” “心向外送的结果……是苦。” “心清楚地看见心……是道。” “心清楚地看见心的结果……是灭。”
- 思所成慧(Cintāmaya-paññā):这是将从听闻、阅读中透彻理解的知识,拿来全神贯注地分析、研究,趋向正道的智慧层次。以正念为统帅。“让念住于心,观照于心,知晓于心,舍离于心,放下于心。”逐渐将心与所缘分开,见到心,认识心,才能走上“道”。精进观察心或识蕴与心所一同运作的过程。我们会感觉“我们自己”是知者,然后思考揣摩,如同在心中解说或自语。要以理解之心,放下一切流过。放下所知之物和新的能知者,持续不断。不要用能知者去执行“放下”的动作,而是要放下那个能知者本身。
-
修所成慧(Bhāvanāmaya-paññā):当心宁静清凉时,智慧看见心的所有状态都只是五蕴,一切都是造作之物,只有“心”是不造作的。智慧了悟并深入那不造作的心,这是放下对造作之物(五蕴)和不造作之物(心或本来清净心)的错误执着的智慧。这是证悟,是修行的成果。
如果没有谁去执着于“有”,心便会空。 无需做更多,只需揭开无明之幕。 了知当下的心,舍离当下的心,便会舍离过去、舍离未来、舍离所有情绪。单纯地了知。
第三章 引蛇出洞,看见那个“我”在解说
“念住于心,观照于心,知晓于心,观察于心,舍离于心,放下于心。” “了知所有念头而不执着,心是怎样,只是了知。” “不迷失于念头,不迷失地用‘我’去思考,而是了知‘我’在想什么,了知于能知者。”
但如果无法做到,而总是忙于安住于被感知的所缘,念却没有观察到作为能知者的心或识蕴。当了知任何所缘时,我们没有观察到我们自己那个思考、揣摩、造作的主体。
当不时刻了知、看见并放下这个“我”时,就会错误地执取五蕴为我们、我们的自我,然后迷失地用“我”去思考、去造作,持续不断,直到成为烦恼、贪爱和痛苦。
如果不能时刻“念住于心”,而总是将心外送,那么就必须有一个解决方法:即无论行、住、坐、卧,都必须有一个经咒,如“佛陀”(Buddho),作为诱饵,以保持正念、正知,觉知全身。然后,要观察那个念诵“佛陀”的“我”,看它在思考什么、揣摩什么、唠叨什么、解说什么。
只是了知,或单纯地了知,或放下。但要求必须有正念、正知,觉知全身,安住于每个当下正在做的事务,并且不放弃那个诱饵。然后就会观察到那个念诵“佛陀”的“我”在思考、揣摩、造作、说话、解说……持续不断。
可以使用任何经咒或诱饵来作为心的引子,只要能引诱它,让心不散乱,就算有效。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必须时刻觉知全身,知道自己当下在做什么,以防意外事故。
再次强调:必须有正念、正知,即觉知全身,知道当下在做什么,并觉知自己正在念诵“佛陀”,同时观察那个念诵“佛陀”的“我”在思考、揣摩、造作。只是单纯地了知或时刻放下,这就等于舍离了五取蕴。
许多修行观心的人却迷失于思考,但他们误以为自己正在观心。他们分不清“了知在思考的心”和“用心去思考”。
正确的观心,是观察心或识蕴与心所一同运作,以期放下对五蕴的错误执着。而不是迷失地用五蕴来造作出一个“我”,然后迷失地用这个“我”去观心或观念头。
第四章 “我是知者”,这即是心
许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当我们有强烈的情绪,比如生气或愤怒时,应该如何修行?”
对于初学者,当情绪“噌”地一下上来时,来不及看见念头,必须立刻转移注意力。比如哼起歌来,或者起身去喝水,起身去做任何事,迅速地活动身体。一会儿情绪就会慢慢淡化。这不是压抑,而是转换。
但对于进阶的修行者,必须成为那个情绪的观察者、了知者。在没有强烈情绪的正常状态下,我们有足够的念和慧去观察心或识蕴(能知者)与法所缘(所知者)。舒适是乐受,不舒适是苦受。如果我们选择一方,排斥另一方,修行就会停留在“受”的层面,厌苦爱乐,无法前进。
因此,当“受”生起时,无论是乐还是苦,我们要问自己:“是谁在知晓?” 就是我们自己是知者。我们是了知各种状态的人。这个所谓的“我”,就是心或识蕴。
要看见的就是这个主体。“心清楚地看见心,即是道”,就是要看见这个“去感知的我”。这个“能知者”,就是“心”或“识蕴”。但它作为能知者只存在于刹那之间,一旦了知,立刻就会有“喜欢”、“不喜欢”,然后分析、解说、思考、揣摩。
在阿毗达摩中,谈到了四样东西:“色、心、心所、涅槃”。“色”指身体。“心”指识蕴。“心所”指受、想、行。心与心所是协同运作的,同生同灭。
修行的办法,就是来了知这个“我”,了知识蕴。我们不要只去了知作为所知对象的所缘,而是来了知这个“去感知的我”。观照这个“我”,这个一直在解说、一直在说话的“我”。把它整个放下。它了知什么,解说什么,都随它去。把它全部放下,只是单纯地了知它。这就等于放下了五蕴。当能放下所有五蕴时,称为舍离五取蕴,便会见到那空于造作的“心”。
许多人修行错了,他们把“能知者”固定住,然后努力去放下每一个念头,或者努力切断每一个念头,禁止它传递受、想、行,努力让它只是“漠然地知”。这是大错特错。这变成了努力去放下念头或所缘,而没有放下那个“放下者”。
因此,必须看见心或识蕴与心所(受、想、行)一同运作,并且没有迷失的执着者。或者,放下心中所有的所缘,并放下那个作为心或识蕴的“能知者”。
“放下”这个词,并非什么都不知道。而是指了知一切,但什么都不执着。即,它全都知道,然后将所知者和能知者在每个当下都放下。放下所缘,然后也放下能知者或识蕴。它是五蕴,是必须造作的自然,生而后灭,随它去吧。只是单纯地了知。
这就是佛陀对婆酰(Bāhiya)所说的话:“如果你只是单纯地了知,就不会有你的实体。你将烦恼尽除,立刻证得涅槃。”或者像隆普笃·阿都罗(Luang Pu Dul Atulo)所说:“见到能知者,杀死能知者。” 或者隆塔玛哈布瓦所说:“见到能知者,放下能知者。”
第五章 所缘存在,但心是空寂的
修行者通常带有贪婪、欲望,预设着要去获取什么,并迷失地造作出一个“我们的实体”要去获取。例如,预设涅槃是静止、空寂,便迷失地用五蕴来造作出一个“我”,然后努力让这个“我”去达到那个静止、空寂。这样的修行,充满了迷失的执着,是与涅槃之道背道而驰的。
“修行”是怀着念和慧,勤于审视,以看见身心五蕴的实相:它们是由四大元素和仍混杂着无明的知元所构成的和合造作之物。它们是无常、苦、无我的。
必须在每个当下彻读自心:修行是出于欲望,还是迷失地执取五蕴为“我”?即便有一个“我”要去获取“法”、获取“空性”、获取“涅槃”,那也是无明、烦恼、贪爱、执取。
只是单纯地了知。心有任何念头或状态,无论合意(乐受)、不合意(苦受)或中性,都只是心或识蕴所了知的对象。而心或识蕴本身是能知者。就让它们如其所是,不要迷失地去执着。
当不合意的所缘或状态生起时,不要迷失地有一个“我”去努力调整、修正或排斥它。这是不对的。这会变成排斥,厌苦受、爱乐受。乐受、苦受或舍受,善或不善,都不迷失地有一个“我”去执着。
必须放下能知者。即了知一切,但没有一个迷失的“我”去执着合意或不合意的状态。让“行”自行显现其作为状态,然后自行熄灭。自生自灭……没有执着者,没有承受者。 当执着者的实体终结,便会见到那没有实体、没有形状的“心”或本来清净心,只有一个如宇宙空性般的空寂之知。
“心”或本来清净心,好比空寂的天空。而各种状态或所缘,就好比飞过天空的鸟或飞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但如果迷失地有一个“我”去对飞过天空的事物做些什么,就会让天空多出一个“我”,于是便不空于“我”了。天空便不空于“有我”的迷失,然后迷失地用这个“我”去思考、造作执着,便会生起烦恼、贪爱、痛苦。
这就像苏跋陀(Subhadda),他后来成为最后一位阿罗汉圣弟子,曾请教佛陀:“踩在空中的脚印是否存在?”世尊回答说:“空中并无脚印。”苏跋陀便了悟了实相:烦恼和痛苦并非本来就有的,而是因为在当下心识刹那生起了错误的执着。如果没有错误的执着,“心”或本来清净心便会如空气般空寂。
第六章 做个观众,而非演员
“观心,要像看电影戏剧一样, 不要自己跳进去参与,不要自己当演员。 只需做个观众、知者。”
生活中的问题或纷扰,时刻存在。任何事情,如果我们全身心投入而没有念和慧看见自己,就只有痛苦。因为有一个“我”迷失地成为演员,有一个“我”成为“行”(Sankhara),于是便失去了成为“无为法”(Visankhara,不造作的自然)的机会。
我们从观众、知者、见者的身份,变成了演员。这样,无论如何教导,都无法理解。因此,必须警觉,必须将自己从演员的身份中撤出。觉醒过来,只是单纯地了知。 没有一个“我”是演员,即没有一个“我”是思考者、是挣扎探寻者。而是作为“能知者”,作为“心”,作为那不显现任何状态的本来清净心。
会看见,只有念头,有状态在心中生灭,但“心”本身并不动摇。当成为一个空于造作、空于实体、空于“我”的“心”时,就没有一个“我”去执取,使其成为烦恼。
那种“我既知又想又理解”的感觉,实际上是识蕴与心所一同运作,并非“我”。而“心”或“本来清净心”,它无法思考,无法说话。它是无为法,不生、不灭、不老、不病、不死。
于是会发现,心中有动、有造作生灭,但“心”本身不动、不造作、不生不灭。它们是如此并存的一对。“心”也没有实体。既然没有实体,就没有一个实体去执取任何事物。
好比攀登涅槃之山,如果没有“念、慧”看见那个迷失地成为演员的“我”,就无法从“假名”(samutti)中解脱。当不再迷失于假名时,便会自动地、即刻地成为“解脱”(vimutti)。自然就只有这两种东西:“行”,即造作;和“无为法”,即不造作。这两种自然的本性,不可能在同一心识刹那并存。
修行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念和慧去观察:是否错误地执取五蕴为“我”,然后迷失地“有我的实体”要去获取什么?是否迷失地有一个“我”是造作者、是演员?如果终止了对“五蕴是我们或我们的实体”的错误执着,就会成为一个空寂的、无法造作执取的“心”。当各种状态生起时,无论是合意的、不合意的或中性的,都不会迷失地执着“我的心舒适”或“我的心不舒适”。只会是各种状态在空性中生灭,没有承受者或执着者,便会离苦。
第七章 理解至心
修行者通常难以避免地会对生起的迷失感到烦躁。不要期望我们能一下子就压制住迷失,那只会更烦躁。只需慢慢地、持续地了知就够了。迷失了,就重新了知,没什么大不了的。 念力增强了,迷失自然会变短。
另一件必须正确修行的事是:当接触发生时,必然会生起乐、苦或中性的感受。要让心接受这个依缘而生的自然常规,而不是逃避去做一个静止、空寂、漠然的心。那等于厌苦、爱乐,是烦恼、贪爱,与涅槃背道而驰。
必须终止错误的执着。无论心中有何状态,都必须趋向那个“心”或识蕴,那个了知乐、了知苦、了知舍受的能知者,去了知心或识蕴对当下所知之物是如何思考、揣摩、造作的。了知于心或识蕴。
如果有一个“我”作为基础去观心或观念头,那是迷失地用五蕴来造作出一个“我”,然后用这个“我”去观心。因此,必须有念和慧了知这种迷失。
不必害怕迷失。如果迷失了,就觉醒过来。无法强迫自己不迷失,只能做到迷失了就觉醒过来。如果努力让自己不迷失,就会迷失于造作“努力”。
当愤怒生起时,不要去关注那个愤怒的情绪。要用“念”观察那个“了知情绪者”。被了知的愤怒情绪,对心而言便失去了意义。因为我们只关注那个去感知的心或识蕴,看它在心中思考什么。我们不迷失地用“我”去思考、造作,心便会空寂。
如果永久地终止了“造作出一个我”的迷失,并终止了“用那个我去迷失地思考造作”,便证得涅槃了。不逃避,不退缩,全神贯注地看着它,就在这里。
问答录
隆塔:能分得清吗?
信众:是的。看见这样,它就从迷失切换到了知。知了一会儿,它又迷失去继续探寻了,是吗,隆塔?
隆塔:是的,没错。我们再了知它。我们的任务就是持续地了知。
信众:那就是没有尽头了。
隆塔:有尽头的!如果不再将心外送,而是时刻让念住于心、观照于心,直到见到那不造作的“心”。当频繁地见到那不造作的“心”后,就会生起智慧,了悟并能分辨出哪个是造作的心,哪个是那空于造作的“心”。至于我们的实体,并不存在。于是便会终止“迷失地用造作的自然来迷失地造作出一个我”的状态,永久地,便成为涅槃。
信众:有什么办法可以见到“心”吗?
隆塔:每个当下,当眼、耳、鼻、舌、身、心有接触时,问自己:谁是了知的主体?你会得到答案:我们是知者,是思考揣摩造作者。实际上,那个能知、能思的主体,是心或识蕴与心所在五蕴中一同运作。
如果每个当下,不失念地将心外送,就会有念和慧看见心识刹那的运作。要有念和慧,守着观察那个思考揣摩的“我”,持续不断。无法禁止它,只能“只是单纯地了知它”,以免随它而去。
信众:如果是这样,那就要一直看着或了知着心了。
隆塔:不要预先去努力观心。因为那是迷失地用五蕴来思考造作出一个“我”,然后用这个“我”去观心。真正的念和慧,是了知那样的行为,然后觉醒过来。
信众:隆塔您给我解释的,我都理解了……但总有一个怀疑的东西在。
隆塔:那只是“想”(Saññā,记忆、概念),还不是“慧”(Paññā,智慧)。
信众:怎样才能成为“慧”?
隆塔:智慧必须在当下从心中看见实相。看见将有思考揣摩者或将有造作,在心中显现任何状态。就好比一个人心里有鬼,想做点什么,却被当场抓个正着。
信众:那该怎么办?因为什么都是迷失于“行”。
隆塔:什么都不做。
信众:什么都不做,那会怎样?
隆塔:没有人会怎样。
(弟子与隆塔……长久地宁静……)
隆塔:怎么停止思考、停止说话了?
信众:问不出来……想不出来了……说什么都是造作,想什么都是造作,努力做什么也是造作。
隆塔:这就有“慧”了。
(智慧在当下豁然开朗:真实的说不出,能说出的不真实。)
隆塔:没有任何言语出来,因为它没有造作任何东西。心停止了造作。这个停止的心,就是“心”或那不造作的本来清净心。
是自己停止了迷失的造作,是出于对心的理解,而非强迫。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全都停止了。是当下的造作终结了,承受者终结了,执着者终结了。没有观察者,没有了知者……“空寂……纯净。”
第八章 智随法后
对于有高等智慧的人,可以直接理解这一点:如果迷失地有一个“我”预先去发起任何作为状态,那就等于“无明”。不要迷失地有一个“我”预先去思考、揣摩、努力、行动。
只需有正念、正知,即觉知全身,不迷失地将心外送。让心自行思考或造作生起,然后自行熄灭。让造作的自然先行造作,然后“智”(Ñāṇa)会立刻随其后了知。
随造作的自然之后了知,称为“随法之后了知”,或“智随法后”。它只是“知”,没有谁是知者。它是随造作之法(即造作的心)之后了知。这个“知”,没有实体,没有形状,甚至没有“空”的感觉。它空于实体,空于任何状态。
但当正念、正知断了,就会迷失地用“我”去思考、造作。这时就必须有正念、正知生起。让心自行造作出念头或各种作为状态,然后“智”随法后。如此持续,直到正念、正知不再间断,称为“大念”,便会成为“大定”、“大慧”。于是便会终止“迷失地用我而造作”,或无明熄灭。这个作为“知”的“智”,便会成为“纯净的知元”,称为“心”或“本来清净心”。
隆塔曾打过一个比方,这好比法律中的“正当防卫”原则。如果我们先拔出武器,我们是发起者,便是有罪。但如果是对方先拔刀,我们在当下为保护自己而进行适度的防卫,便可以主张正当防卫而免责。
在内心中,让心自行显现其状态,不要有一个“我”预先去显现状态。如果迷失地有一个“我”预先发起,即便是一个“我”去显现“念”的状态,即我们预先去观心或观念头,这便是“无明”,即错误地执取五蕴为“我”。
如果没有一个“我”预先去发起、去表演,就说明我们尚未去执取五蕴为“我”,只剩下“智随法后”。直到正念、正知不再间断,“智”便是纯净的知元,因为无明已尽。
第九章 何为无明
“念为大念,为大定,为大慧,为涅槃。” “念断,定断,慧断,法断。” “就在当下的这一个念。”
“念”是禅修的核心。但对“念”的错误理解,导致我们修行不正确。“念”是“在当下不迷失”。但许多人理解错了,害怕迷失,然后去维护、努力做“念”。只要有一个“我”去做什么,立刻就迷失了,是“无明”。
必须先迷失,才能看见迷失是什么样子,最终才会不再迷失。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核心。但如果我们迷失地去努力保持“念”,以免迷失……这从保持“念”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迷失了。
修行的原则必须牢固。所有的“行”,所有的作为状态,所有的念头,无论它是怎样,如果没有“有我”去参与其中有得有失的感觉,没有一个“我”去参与,一切就都只是普通的“行”的造作,不成无明。但所有的“行”,在每个当下,无论它多好、多善,一旦有一个“我”去参与其中有得有失,立刻就成为“无明”,成为烦恼贪爱。
“无明”,就是有一个“我”真实地去参与其中有得有失。
隆普查·苏跋陀(Luang Pu Chah Subhatto)曾说过:“最好的修行,就是什么都不做。” 只需有念而已。而不是要去修行,让它成为什么。放下它,时刻放下。即,只是觉知心中生起了什么,无论是乐还是苦,善还是不善,都必须放下。“放”,就是让它如其所是,没有谁去干预。导致痛苦的烦恼,只来自于心的造作去执着而已。不进去执着,就没有无明、烦恼、贪爱。
问答录
隆塔:你试着去造作点什么……无明、烦恼、贪爱、执取……和痛苦立刻就包裹上来了。因为它违背了纯净的自然。纯净的自然,它没有造作执着。我们错误地以为,要去做,让它成为……越是想做让它成为,无明、烦恼、贪爱就越是层层加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让我们终止迷失的造作,我们反而去增加造作。
终止迷失的造作,仅此而已。缘起法就断裂了。它终止了什么?终止了“迷失地用我去造作”。如果用“我”去做什么,那立刻就是“无明”。
信众:明白了。包括那个努力保持正念的“我”。
隆塔:嗯,那个努力保持正念的“我”,那个问题更严重。
信众:害怕失念,害怕迷失,那该怎么维持呢?
隆塔:喏!害怕迷失,这不就成了“无明”了吗?迷失了,就只是觉知,不是去害怕迷失。 迷失了,我们就只是觉醒过来。频繁地觉醒过来,每次迷失都会有念生起。如果我们不迷失,又怎么会有念呢?必须先迷失,然后才有念。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核心。我们已经迷失了,但我们以为我们在保持念,以免迷失……这从保持念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迷失了。
信众: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我”去做什么,就是迷失。
隆塔:嗯,没错。如果有一个“我”去做什么……立刻就迷失了。有一个“我”去保持念,立刻就迷失了。
信众:隆塔,那如果什么都不做,它不就随波逐流了吗?
隆塔:哎!迷失了才能了知啊。这就是“与知同在”。
信众:当有个念头生起,想做什么、想修行什么的念头,就……只是了知……!
隆塔:嗯,说过了,原则必须牢固。即便是苦受,它也仅仅是一个状态,不是烦恼贪爱。但当有静、空、舒适的状态,然后有一个“我”去参与其中有得有失,立刻就成为烦恼贪爱。
那问,来修行得到了什么?回答:“什么都没得到。” 只是烦恼,即贪、嗔、痴消失了而已。或,那个“想要去获取什么”的实体,在当下终结了。“无明”便熄灭了。
第十章 彻读自心
我们常常看不见或不觉知自己“修行是为了去获取什么”。总有一个“索取者”或“渴望者”。喜欢时,就想要、想得到。不喜欢时,就不想让它那样。即便是要去获取涅槃,或不想要老、病、死,这都是烦恼,与涅槃背道而驰。
在修行中,如果它想去获取什么,就要有“念”了知,不要随它挣扎。如果念不间断,只是单纯地了知,那就等于在当下放下了,无需再去做“舍离、放下”的动作。
如果只要乐,不要苦,即“好则爱,坏则憎”,那是“烦恼”。如果有念和慧看见这个原因,就在当下把两边都放下,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执着,一切便空寂了。
如果还有希望、欲望,还想去获取什么,即便是想去获取涅槃,在当下也无法离苦。必须在当下、此刻,放下那个“索取者”或“欲望”,才能在此刻离苦。
因此,我们必须彻读自心:是为了“获取”而放下,还是真的放下? 放下那个“索取者”,那个“想得到、想成为”的主体。放下了就放下了,不是为了再去获取什么而放下。
挣扎探寻想达到“心”或“本来清净心”,这在当下就是烦恼。要有“念”立刻了知。
最极致的迷失,是努力用五蕴或心的造作(行)去挣扎探寻、去执着于“无为法”,那是一个无法被感知到的状态。又怎能用“有”(有可被了知的造作)去寻找、去执着于“无为法”(不造作,无可被了知之物)呢?必须停止寻找,停止执着,停止欲望。必须既放“行”,也放“无为法”,并放下那个“能知者”、“放下者”,因为能知者、放下者也是“行”。
“无明”,是错误地执着五蕴为我们、我们的自我。或是不知始、不知中、不知终。
- 不知“始”,即不了知、不见“心”或“本来清净心”。
- 不知“中”,即没有念和慧了知那个“迷失造作、迷失思考揣摩、挣扎探寻”的心识刹那。
- 不知“终”,即不了知心已对当下的所知之物生起了烦恼、贪爱。
因此,必须有“念、慧”了知烦恼、贪爱,即了知那个“迷失思考造作”。如果在当下终止“有我这个索取者”的迷失,那所有烦恼就都结束了。不修行的人,想得到世俗之物。而修行的人,也想得到“法”,得到“好心”,得到“涅槃”。全都一样是烦恼。如果在当下终止“有我”要去获取任何东西的迷失,立刻就烦恼尽除了。
第十一章 当下知,当下舍,当下放下一切
“过去是令人沉醉的法,未来是令人沉醉的法。 唯有当下知、当下舍,才是真正的法。”
无论心中生起何等奇妙的境界,无论多么殊胜,都绝不能随之迷失。必须了知,只是放下。因为已经发生并过去的事物,已成过去。我们必须了知于当下,并放下于当下。
了知当下的心,舍离当下的心。 只是单纯地了知当下的心。当承受者终结,执着于当下的心者终结,实体便终结了。
不仅仅是放下境界,我们必须彻读自心:在当下,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去获取什么?必须将欲望彻底放下。即便是渴望离苦、渴望涅槃的人,如果不如意,会是最大的痛苦。
佛陀在证悟成佛时曾自忖:“当对快乐的欲望,或对涅槃的欲望,消失时,痛苦也随之消失。”
我们不知道,对涅槃的这个欲望,正是让我们极度痛苦的原因。而让我们无法证得涅槃的原因,也正是这个。我们反复思索,慢慢地放下它。但这可不是轻易就能放下的。
放下,放下,放下,即便是对快乐或涅槃的欲望。如果愿意放下,是为了去获取涅槃,那说明放得不真。真正的放下,是没有“索取者”。
修行就只是这样。最好的修行,是终止“索取者”,即在心中没有任何为了去获取什么而做的行为。必须在每个当下彻读自心。
Bhārā have pañcakkhandhā (五蕴实为重担)
Bhārahāro ca puggalo (世人背负五蕴,实为重负之行)
Bhārādānaṃ dukkhaṃ loke (背负五蕴,是世间之苦)
Bhāranikkhepanaṃ sukhaṃ (能放下五蕴,是为安乐)
Nikkhipitvā garuṃ bhāraṃ (既已放下五蕴重担)
Aññaṃ bhāraṃ anādiya (不再执取他物为重担,即终止“索取者”)
Samūlaṃ taṇhaṃ abbuyha (便能根除贪爱)
Nicchāto parinibbutoti (熄灭欲望、渴求,熄灭烦恼之火,彻底无余)
第十二章 越寻越堵(即“贪”)
当“贪”(Taṇhā)熄灭时,执取(Upādāna)、有(Bhava)、生(Jāti)……乃至苦、忧、恼也随之全部熄灭。
而贪,源于“无明”,即错误地执着五蕴为我们的实体。
挣扎探寻,越寻,越不见。因为“寻找”就是烦恼、贪爱,障蔽了眼,障蔽了心,障蔽了涅槃。越寻越堵,因为它就是“贪”。
只需刹那之间,我们去“寻”,那便是贪了。必须有念,看见那个“心识刹那开始用我去思考、去造作,显现‘寻’的作为状态”。当开始寻找时,要有念和慧立刻了知,贪便熄灭了。
任何你认为“对了”的东西,例如,轻安舒适或这个空性对了,那正是在执着。我们努力去熄灭那些导致不舒适的状态,以期让自己更舒适,那便是烦恼、贪爱。
任何自行生起的东西,就让它自行熄灭。正如经云:“凡是生法者,皆是灭法。”(yaṃ kiñci samudayadhammaṃ, sabbaṃ taṃ nirodhadhamman’ti)。
苦了又苦,不知悔改。然后用别的东西来暂时掩盖痛苦,最终也无法逃脱衰老、病痛、对死亡的恐惧。
必须精进修行,以期从对身心的错误执着中解脱。必须有念和慧,如实地看见:五蕴是由诸界和合造作而成,是无常、苦、无我的。
因此,必须停止思考、停止造作、停止挣扎探寻,因为那等于执取五蕴为我们的实体,然后用“我”去思考、去造作,是无明、烦恼、贪爱。
因此,必须在每个无需刻意思考的时刻有念。在那个心识刹那,不要有一个“我”预先思考或造作任何状态。让心自行思考或显现状态,然后自行熄灭。或,自生自灭……自生自灭…… 没有一个“我”去执着,便会见到那空于造作的“心”。
期望、欲望,那也是烦恼、贪爱,要全部放下。只要终止“错误地执取五蕴为我们的实体”,每个当下,就只有五蕴照其自然常规造作,没有一个“我”要去获取任何东西,不成任何东西,便空寂了。
第十三章 有一个“我”去获取
我们曾问过自己吗:“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许多人总是用“我”去找、去看、去探寻,努力挣扎,让“我”陷入烦恼之中。既有一个“我”要去获取涅槃,又只要快乐,那样,从一开始就是烦恼了。
即便我们没有进行形式上的修行,也必须时刻有“念”。念不可断,因为:
“念断,定断,慧断,法断……是苦。” “有念,有定,有慧,有法……不苦。” “念为大念,为大定,为大慧,为涅槃……离苦。”
如果“念”在,定和慧也都在。
但必须牢记的是:当我们刻意有念,或刻意动手修行以期有念,却不了知有一个“我”要去获取什么——即便是要去获取“心静、心空”——那就等于没有念。因为有一个“索取者”,是烦恼。想要有念,想要有定,想要宁静,想要有慧,想要烦恼尽除,想要证得涅槃,这些全是烦恼。
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工作,我们也必须让念住于心、观照于心、知晓于心、观察于心、舍离于心、放下于心,时刻如此。要有念和慧观察并看见:每个当下的接触,心或识蕴会与心所一同运作,然后会感觉“我们自己”是知者、是思考揣摩者,如同在心中解说或自语。只是单纯地了知、看见那个感觉“我们自己是知者、是思考者”的主体,持续不断,便能放下那个“我”。
因此,每个当下的接触,不要只关注所知之物。要有念、慧观察那个感觉“我们自己是知者、是思考者、是表现各种状态者”的主体。只是单纯地了知,便能放下那个作为“我”的感觉,然后会见到那空于状态的“心”。这便是“放下‘身为我’的感觉之法”。
因此,无论内心在说什么、解说什么,都随它去吧。没有谁去感受或去承受。它会自行熄灭。那个能知、能记、能理解的主体,也是五蕴中的“行”。不要迷失地执着“我”是知者、见者、理解者。要全部放下。
必须看见,那个去观察、去了知的主体,是造作的“行”。但“心”或本来清净心,是“无为法”,无法造作。它只有一个“烦恼已尽、执着已尽”的知。所有存在、显现之物,都生而后灭。但“心”,无生无灭。
因此,要时常思索:如果我现在死了,是否已放下所有“行”或五蕴?让心照其五蕴的自然常规思考或造作,自生……自灭,没有执着者,或承受者终结,便会烦恼尽除,离苦得乐,涅槃。
第十四章 守护正念,放下能知者
修行者常问:“我们如何放下能知者?”当我们听到父母师长教导说:“见到能知者,杀死能知者”或“放下能知者”时,便理解错了,于是把念全都丢了。
这是不同的能知者。“念”这个能知者必须保持,“念慧”是五蕴,我们必须依靠“念”作为渡船去涅槃,不能全放了。所说的“放”,是放那个感觉“我们是能知者”的心或识蕴。但我们还没到彼岸,就中途把念丢了,好比舍船跳水,于是就淹死了。
识蕴必须通过六门去了知。问谁在知?就是我们这儿在知。这个“我们知”,是心或识蕴。它与心所(受、想、行)一同运作,同生同灭。当心或识蕴去了知任何事物时,必然会有“喜欢”、“不喜欢”,然后思考揣摩,如同独自一人说话、解说。
修行的办法是,让念住于心、观照于心。观察识蕴,就在那个感觉“我们自己”当下了知任何事物时,会思考揣摩的状态。不要去关注所知之物,全部放下。必须关注、观察那个能知者,它既知又思考揣摩。只是单纯地了知,才不会有迷失地随之而去的主体。
之所以必须看见那个思考揣摩的能知者,是因为要放下能知者。如果不放下能知者,就无法放下识蕴以及与之一同生灭的受、想、行。
因此,“身为我”的感觉,每一次都仅仅是五蕴一同运作而已,并非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因此,必须放下“错误地执取五蕴为我们的实体”的迷失。
而用来观察看见这个实相的,就是“念、慧”。我们不能丢掉这个观察者。我们必须时刻观察那个感觉“我们是知者、是思考者”的主体。而能了知它的,也必须依靠“念”。因此,这个“念”不能放下。
当别的都放下了,就必须依靠念、定、慧,来放下它自己,即那个“放下者”。因为念、定、慧也是五蕴,是造作之行。当别的都放下了,就必须放下自己,即不迷失地执着“我是了悟者,我是放下者”。
当执着者终结,烦恼便尽除,离苦得乐,涅槃。
因此,“念”是至关重要的核心,不可间断。
第十五章 三种知以及次第放下
“知”有三种:
第一种“知”,是心或识蕴。 它是生来去了知所缘的造作自然。它与心所(受、想、行)一同运作,生灭不息。当“无明”还存在时,就会错误地执取五蕴为我们、我们的自我,感觉“我是能知者”,然后迷失地用“我”去思考、造作、执取。
第二种“知”,是念、定、慧。 它们是五蕴中的造作之行,但借来用于以“觉知”观察“我”。用念、定、慧来观察并看见实相:那个作为“我”的感觉,实际上是五蕴的运作。只是单纯地了知并放下那个思考、揣摩的“我”,不迷失地用“我”去放下别的东西。但如果迷失地执着“我”是知者,或“觉知者是我”,这会成为“无明”。
第三种“知”,是佛陀(Buddha)或识元(Viññāṇa-dhātu)。 它是不造作的自然。佛陀,意为“解脱之知”、“觉醒之知”、“喜悦之知”。心是空性,是大空,不生不灭。
在修行中,必须观察并放下所有错误的执着。放下所知者和能知者,这要放下三对:
第一对:放下色、声、香、味、触、法所缘(所缘)与作为心或识蕴的“能知者”。
第二对:放下“错误地执着念、定、慧(作为观察者)与五蕴(作为被了知者)”。 念、定、慧也是五蕴中的“行”,借来用于如实地了知五蕴。不迷失地执着其为实体、为我。当有念、定、慧了悟五蕴的实相时,心便放下对五蕴的错误执着。
第三对:放下“对作为空寂知元的‘心’的错误执着”,与“放下对那在空寂心中生灭的五蕴的错误执着”。 要终止对“空寂的心”的错误执着,就必须深刻理解:五蕴不是涅槃,“心”也不是涅槃。必须既放五蕴,也放空寂的心,才能离苦,称为涅槃。
当具备最高等的念、定、慧后,就不会迷失地用五蕴来造作执着于作为空性的“心”,或迷失地执着于心想让它空。当终止执着于五蕴,并终止执着于“心”时,那个借用的念、定、慧,就不再需要用来观察了。只剩下五蕴的状态在空寂的“心”中生灭。那个作为空性的“心”,会自行了知执着已尽或离苦得乐,称为涅槃。
第十六章 彻底结束吧
修行了这么久,学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没见到法呢?之所以还没结束,是因为理解不正确。
用来提炼掉“无明”以剩下“纯净的知元”的工具,就是“念、定、慧”。
“念断,定断,慧断,法断……是苦。” “有念,有定,有慧,有法……不苦。” “念为大念,为大定,为大慧,为涅槃……离苦。”
当提炼掉作为“迷失造作执着”的“无明”后,便只剩下“纯净的知元”,假名称之为“心”或“本来清净心”。
但我们反而迷失地执取五蕴为“我”,然后迷失地用“我”去看作为五蕴的“我”,或迷失地用五蕴来造作出一个“我”,然后用“我”去看心或看念头。它在五蕴中打转,无法从五蕴中解脱。能放下那个观察者、能知者吗?放下它。放下这个五蕴。哪有什么“我”,就是五蕴。
“在念头中,有不念。 在造作中,有不造作。 它们在同一处。”
我们只需看见:有念头、思考、揣摩、挣扎或任何在内心中生起的状态,全都不是“我”。因为“我”并不存在。要看见的,是只有“行”或造作的自然,在不造作或无法造作的“心”中生灭。
因此,只有一件事。必须有念和慧如实地看见:自然中有两种,造作的自然(行),和不显现造作的自然(无为法)。在“行”和“无为法”中,都不是我们、我们的自我。因此,没有一个“我”能得到或达到涅槃。
“涅槃”,是终止执着于“行”和“无为法”。
因此,如果努力挣扎探寻、分析评判、努力做什么以期得到、达到、成为什么,那全是迷失地造作“想获取……”,又怎能是涅槃呢?因为涅槃是终止“执着者”或终止“索取者”。
问答录
隆塔:还是迷失地造作出一个“我”去看“我”。那个有“我”的,就是那个“用我去看我”的。
信众:每次努力去看,都有一个“我”。
隆塔:没错。那个“去看我”的,才导致了“我”。
信众:那怎么看,才不会有“我”呢?
隆塔:哎,就别去看它了。因为每次看,都有一个“我”去看它。能放下那个“观察者”吗?能放下那个“能知者”吗?放下它。
信众:不看。
隆塔:立刻放下那个“观察者”。不要去寻求理解。全部丢掉。现在就丢掉。
信众:那该怎么办?
隆塔:哎!该怎么办?都说让你别做了,还非要做。
信众:有正念正知,是吗?还是什么都不用做?
隆塔:什么都不用做。 别提什么假名安立的词。现在就全部放下。停、停、停……最高回归到最普通。
信众:因为思考本身就是造作,是吗?
隆塔:但思考,是在不造作的“心”中造作。
信众:它会怎样,都随它去吧。放下它。
隆塔:没错。它就像宇宙,是空性,但它必须与所有在宇宙中的造作之行共存。而我们的身心,就在地球表面。身体是造作的自然,受、想、行、识也是造作的自然。它在哪里造作?它就在那如同宇宙空性般的、空寂的“心”中造作。 但“心”有知,是知元。它了知心中有何物在造作,但“心”本身是空寂的、不造作的。
信众:那就要丢掉黑色。
隆塔:对、对、对。
信众:想到白色……哦!……也不用想了。
隆塔:对、对。想了,又造作了。
第十七章 言语道断
自然有两方面:能造作的自然,称为“行”;和不能造作的自然,称为“无为法”。
造作的自然或“行”,它造作出“是我们”的感觉,让我们感觉“我们是修行者,尚未了悟解脱”。当我们不了知,随“行”而去,便迷失地执着、迷失地造作。
修行者必须以念和慧看见:上述生起的感觉,全都属于“行”的造作。不要把造作的自然当作“我”。并且,至关重要的是,不要用“我”去熄灭那个正在造作出“我”的、造作的自然。否则,会变成迷失地再次叠加造作。
当没有谁去执取“行”为我们、我们的自我时,让造作的自然随其自然去造作。当执着者终结,“心”便会自动地成为不造作的自然或“无为法”。当自动地成为不造作的自然后,智慧便放下,没有主体来执着于这个不造作的自然,便会烦恼尽除,痛苦尽除,证得涅槃。
修行者应谨记此实相原则:
“知者不思(依其本性,知无法思),思者不知。”
必须训练,直到某个心识刹那,见到那无意图之知,见到那无意图之思。自行思起,而无意图去思;同时知此思,而无意图去知。这称为“见真法”。
最终,只剩下自心了知,是“自证自觉”(paccattaṃ),没有任何假名安立的语言。当心终止迷失的造作后,便再无可称呼之物,再无言语可述,再无话可说。
第十八章 解脱中的假名
内心自然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假名”(Samutti,生灭之物),一部分是“解脱”(Vimutti,无生无灭)。“假名”是心的造作,而“解脱”是“心”或那不造作的本来清净心。
我们用作为“假名”的、造作的心来使用。而作为“解脱”的“心”,只是宁静空寂、空于造作,无法拿来使用。当终止迷失的念想、迷失的造作,或终止执着于“假名”时,便会自动地、即刻地成为“心”,成为“解脱”。
而不是迷失地用“假名”去找“心”或找“解脱”。 因为“心”没有标记,或没有可被探寻发现的目标。只有一种方法能见到“心”,那就是“停止”。停止用五蕴去思考、去造作。
“假名”和“解脱”本已在我们心中,但我们理解错了。我们努力用“假名”之身,去帮助“解脱”之身或“心”。我们无需去帮助“心”,因为“心”是空性,无法造作去执着于任何事物。无法离苦的问题,不在于“心”,而在于我们尚未停止“努力去帮助心”。何时“停止”帮助心,何时便见到空寂的心。
如果“心”能说话,它大概会说:“你能不能别帮我了?你啊,最会添乱了,你这个造作的心。你别再管我了,仅此而已,我就结束了。”
当不迷失地造作,便会成为那不造作的、解脱的“心”。让它在当下的“心”中终结。放下一切,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即便是当下,也不维护任何东西。
世界终结,只剩法(空寂之心)……对世界和法都终止执着,即“涅槃”。
第十九章 无明是障心之幕
“全部丢掉,全是‘行’。心中生起任何事,全都是造作之行。”这个理解至关重要,因为自然有两件事:造作的自然与不造作的自然。
“行”,是造作的自然。任何事物,从无到有,从不显现到显现,能变化,有相反的状态。这些有成对相反状态的事物,全都是“行”。
而另一部分自然,是不造作的自然,即“心”。它只是“知”,无法造作。心中生起任何事,“心”舒适也知,不舒适也知;有念头也知,没念头也知。它全都知道。任何事物,都在这个“心”里生灭。“心”了知有何物在它里面生灭,但“心”没有状态,没有“心”的实体,如同宇宙的空性。
许多人错误地把在心中生滅的各种事物或状态当作“心”。但实际上,生灭的,是受、想、行、识,是五蕴的自然。
我们不要只关注所知之物,要关注那个“用它来思考、揣摩、造作、解说”的“我”。了知是为了什么?为了看见那全都是“行”。只有“行、行、行……”放下它。它是五蕴,只能放下它。当真正厌倦了它,便生起“厌离智”,放下五蕴。只需放下错误的执着,无明立刻熄灭。当无明熄灭,便立刻见到那空寂的“心”。
好比我们坐在一个拉着窗帘的房间里,一旦拉开窗帘,立刻就看见外面的空性。“心”的空寂本已存在。而“无明”,就好比障蔽心眼的窗帘。
隆普曼·普利达陀(Luang Pu Mun Bhuridatto)写道:“不了知,蕴障法。” 这个“法”,是不造作的自然,或“心”。它本已存在,但我们用五蕴去干预五蕴,蕴便障蔽了法。当障蔽心眼的窗帘被拉开,蕴便无法再障蔽那不造作的法。
我们不会死,因为我们从未生。我们不生不灭,是如同宇宙空性般的、空寂的知者。只有五蕴分解。因此不必害怕死亡,而要害怕再次出生。
第二十章 恒常空性之因
“心”的空寂本性或“佛陀”本性,本已存在于所有众生之中。但除了佛陀和阿罗汉,所有众生都仍有“无明”,它好比一道障蔽心的窗帘。
能见到作为空性的知元或“心”的方法,只有一个,别无他法。即,必须终止对“行”或五蕴的错误执着,便会见到那本已存在的、空寂的“心”。
任何不空之物,都化为“行”。当放下所有作为“有”的“行”时,便见到“空”。但又会迷失地来执着于“空”。而能来执着于“空”的主体,必须是迷失地用五蕴来造作。当彻底放下造作或五蕴后,就不会迷失地用造作来执着于“空”,于是便化为真正的空。
许多人喜欢去做一种“空如太空”的感觉。这种由造作自行创造出来的空,这个主体就是“无明”。它必须是“因执着终结而空”,而不是去创造一种空的感觉。
正念正知,即觉知全身,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真正的正念正知,是依其自然常规的“觉知”,而不是迷失地造作出来以期努力去观察或了知什么。
当终止对五蕴(造作的自然)和“心”(不造作的自然)的错误执着后,“心”便依其本性空寂地存在。而五蕴,则继续造作,执行生命的职责。有之物自有,空之物自空。熄灭的,只是错误的执着,或承受者终结而已。
许多修行者常常误解,去创造一个“空”,把一切都看成空气。这是误解。实际上,它是空于“可被执着为我们、我们的自我或我们的实体的核心”。当不迷失地执着时,便等于放下。当放下后,便见到空寂的“心”。然而,即便见到空寂的“心”,仍有迷失者,即去努力执着于空寂的心。
“涅槃”,是执着者终结,心因此空。我们误解为“涅槃是空性”,因此迷失地去执着于空性。这会成为无明。实际上,它是空于“迷失执着者的实体”,心因此空。
它之所以空,是因为在那个心识刹那,它终止了“迷失地思考、造作成为能知者”的迷失。没有找任何理由,不努力去做什么以期成为什么,于是便见到那空寂的“心”。但当努力找理由时,它反而不空了。
第二十一章 无字天书
当终止执着于“行”,或终止迷失的造作时,自然的实相便向心显现:在造作中,有不造作的“心”,它们本已并存。
“空”,或“不造作”,本已在自然中存在。但我们看不见,是因为我们去执着于造作。我们不放下造作,反而用造作(即五蕴)去做各种事,想让心空,想让五蕴达到涅槃,而实际上,涅槃是终止执着于五蕴。
只要还以“索取者”的心态修行,“要得到、要得到……”,就会迷失地执取蕴为我们、我们的自我。经行、静坐,都是为了去获取涅槃,去获取心中预设的空、通透、轻安。这些全是烦恼,无法离苦。必须彻读自心,必须终止“索取者”,才能终止痛苦。
修行,并非为了让谁得到什么奇妙的东西。最奇妙的,是……
……放下,即便是那奇妙之物!……
这本书,走到了最后一章。通过文字(造作之物,假名安立)来解释法。有之物、波动之物、显现之物,全都是造作之行,生而后灭。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行者”,没有一个“到达者”。只有知……知……知……理解……理解……放下……放下……错误的执着。从封面到最后一页,这部经书,便不再需要任何文字……从心到心,空寂。
最终,全部放下。放下“错误地执着我是知者、见者、理解者、了悟者”的迷失。只剩下无人执着的“知”。无明便熄灭了,五取蕴熄灭了。“行”放下了,便全部空了。便见到“心”的“空”,即作为知元的“心”。
达到空寂的心后,不迷失地执着于“空”。放下“错误地执着、迷失地维护心让它空”的迷失。放下重担,便空寂了。放下对“空寂”的错误执着,不背负“空寂”,没有谁既背负着“空”也背负着“行”,因此离苦,称为“涅槃”。
Nibbānaṃ paramaṃ suññaṃ 涅槃是空于错误的执着,既空于假名(行),也空于解脱(空)
Nibbānaṃ paramaṃ sukhaṃ 涅槃是超越“感觉为乐”与“感觉为苦”的至高之乐
当四大五蕴必须分解之时,便将五蕴、地、水、火、风四界和知元,归还于自然。无明已尽的本来清净心,便成为空寂的知元,回归并与自然的空寂合一。
彻底结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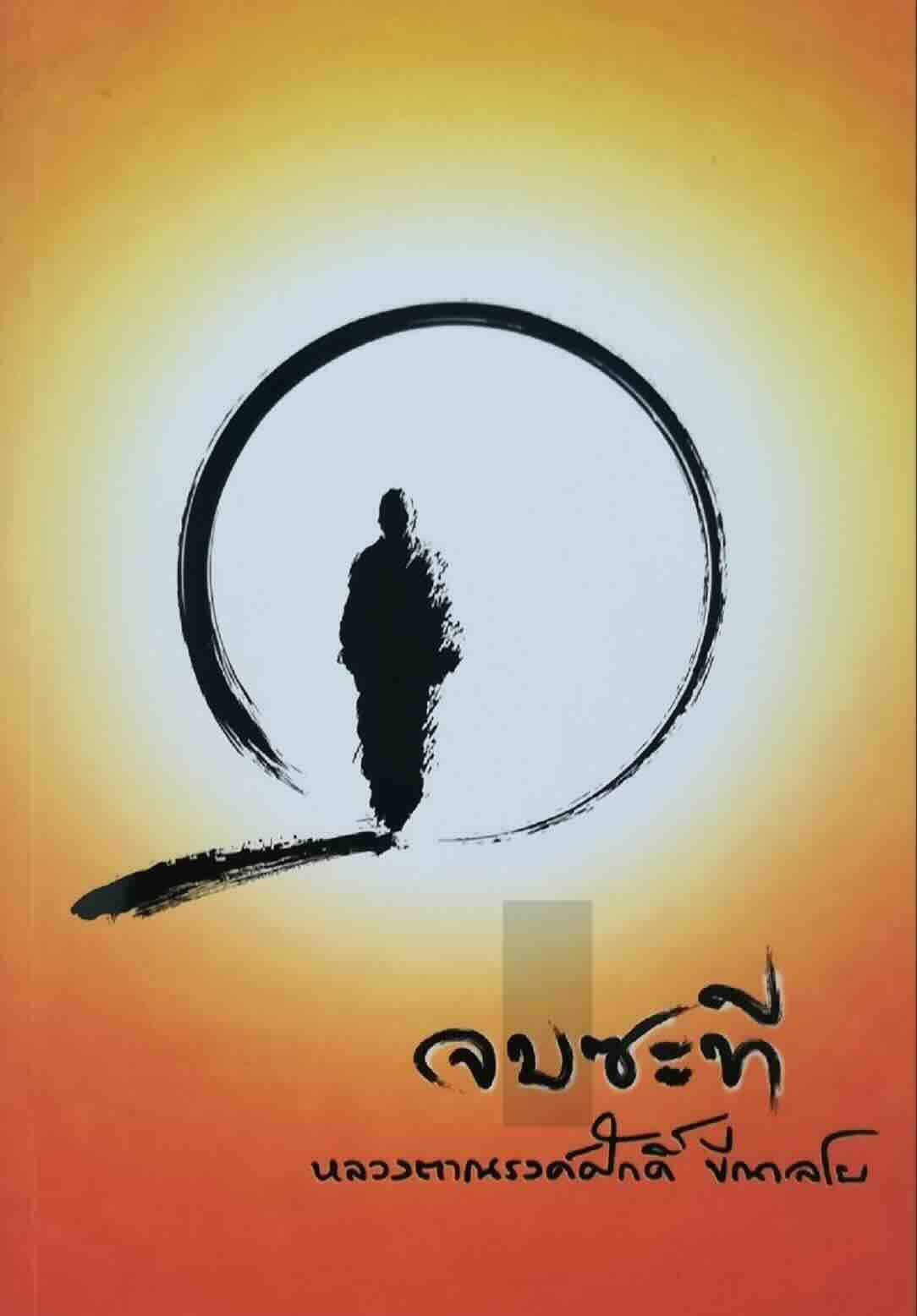 |
本文翻译自泰语书籍如感兴趣请下载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