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轮回
隆塔纳荣萨尊者, 南传上座部佛法 ·Index
终结轮回 - 隆塔纳荣萨尊者 - 智宁居士译
无需“我”来干预它们——根本无需卷入其中。既然一切现象都依照其本性自然生灭,那么事实上,我们根本无需卷入其中。
读前提示
每次阅读本书前——
下定决心以“敞开心扉”的方式阅读。
发愿“用双眼阅读,用心领会佛法”:
以佛法僧三宝的力量,愿我能用双眼阅读,用心领会佛法。 愿佛法直达心底,自动消除一切无明与邪见,从现在开始。
序言
本书中的所有佛法,旨在帮助我们“了知自我”——了知真相,即根本没有恒常的自我。自我——那个“我”、“我的”或“我所”的感觉——只是在每一个当下,由无明和执取所造作的一个念头。当所有这些心念造作(有为法)生起时——例如:任何为了帮助自我达到、证悟、成为或从中解脱的努力,它们都应被视为无我的、因缘和合的有为法(saṅkhāra),它们自然生起,自然消逝。无需“我”来干预它们——根本无需卷入其中。
如此照见时,我执(attā)的错觉就不会生起并导致痛苦:痛苦只源于当下对“我”、“我的”或“我所”的迷惑执信。
如果没有执取——即使是对欲望或烦恼的执取——就不会生起新的无明(avijjā)、贪爱(taṇhā)、烦恼(kilesa)或执取(upādāna)。这些是痛苦的根源。然而,如果有人卷入这些现象,并将其据为己有,那么这应被视为另一种自然生灭的有为法。无需试图干预或改变它。只是不要卷入其中。
如果修行能以信(saddhā)、精进(viriya)、念(sati)、定(samādhi)和慧(paññā),以及忍耐(khanti)、惭愧(hiri-ottappa)来进行——并且在每个当下,不跟随烦恼的思维、语言或身体行为,那么自我的感觉就不会生起并执取任何事物——甚至不会执取那些导致欲爱(kāma-taṇhā)或有爱(bhava-taṇhā)的愉悦感受——也不会为了试图阻止或逃避某种心理状态而产生厌恶,继而生起无有爱(vibhava-taṇhā)。
所有这些形式的贪爱(taṇhā)都是苦集(dukkha-samudaya)的来源。为了止息痛苦,我们必须遵循中道(majjhimā paṭipadā),即八圣道分(ariya magga),它由戒、定、慧组成。不跟随妄念,不压制或抵抗妄念,也不逃避妄念——这就是止息无明(avijjā)、贪爱(taṇhā)、烦恼(kilesa)和执取(upādāna)的方法——随着这一切的止息,所有的痛苦也随之止息:这就是涅槃。
以这种方式在每个当下修行,可以比作持续不断地偿还贷款的复利和本金。复利就好比一个人在每个当下,卷入烦恼,跟随或排斥妄念。而本金就好比从无始轮回以来,那些深植于我们存在的随眠烦恼(anusaya)和烦恼习气(āsava),它们产生了各种烦恼。当复利和本金都偿还完毕时,轮回的因就停止了。
如果没有人将生起的事物据为己有,就没有人会承受痛苦。但如果在任何当下生起了执取,只需以心慧(paññā-ñāṇa)将其视为一种无我的有为法,它自然生起,自然消逝。无需干预——无需介入。无需纠缠。既然一切现象都依照其本性自然生灭,那么事实上,我们根本无需卷入其中。
*
我一直以来试图教导的, 是为了帮助修行者理解 轮回的生起和终结—— 并帮助修行者清晰地看清 全貌和地图——因为如果他们看不清, 修行者就会以“我执”为基础进行修行—— 总会有一个“我”在修行, 为了证得,为了拥有某种状态—— 这并非在正确的道路上—— 并非在八圣道分上—— 也无法证得任何果位—— 也无法证结痛苦的终结。
我现在年事已高,生命将近终结—— 所以我决定在这本书中分享真理, 以便向人们和所有众生—— 无论已经出生还是尚未出生—— 忠实地传达所有佛陀所证悟和教导的真理。 如果修行者按照正法正确修行, 他们就有可能像佛陀一样证悟真理。
我愿鼓励大家精进修行。
隆塔纳荣萨·奇纳拉尤 2025年4月
第一章 轮回与无明的心
让我们试着描绘一个充满执取和攀附的无明之心,并讲述它从无明(avijjā)转化为明(vijjā),证悟最终真理,直至轮回(saṃsāra)——无始以来的生死循环——终结的故事。
举个例子:我们来看看一个仍受无明(avijjā)影响、充满强烈执取和攀附的心。这是一个蒙蔽、黑暗、被污染的心——充满痛苦。
一个人执取得越多,他们的痛苦就越大。
这样的人的心变得越来越黑暗,就像无月之夜漆黑的天空。
一个心怀邪见、执着于“我”、“我的”、“我的心”感觉的众生,在每一个心识的当下,都会持续不断地形成图像和故事,它们生灭不息,就像一部电影。
仿佛身体内部——五蕴内部——隐藏着一个微小的自我,充当这部电影的主角。
当一个人紧紧抓住任何事物时,就像这个心中的小人抓着一根绳子,一端系在自己身上,另一端系在执取的对象上。
如果执取很多事物,就像有许多绳子系在许多人和许多事物上——例如,系在父母、兄弟姐妹、儿孙、丈夫、妻子、地位、财富和财产上。
由于对自己的五蕴和他人的五蕴的迷惑执取,绳子像蜘蛛网一样四处系着——将自己和他人以及各种事物联系在一起。
执取得越多,心就越黑暗、沉重、昏昧——被痛苦和压力所压垮。
在每个心识的当下持续的迷惑执取,可以比喻为被困在有(存在)的领域之内——由土星状的球体代表,它代表了轮回的三界(Three realms of saṃsāra),众生在其内部存在并轮回:欲界、色界和无色界。
环绕球体的是一个光环,像土星的光环,象征着缘起(paṭicca-samuppāda):轮回(saṃsāra)和所有形式的痛苦。
一个没有任何执取——没有攀附者,也没有执取物——的心(citta)不投射任何图像:没有任何图像可以代表这样的“心”、“心识”或“觉知”;其内部不出现任何东西——甚至不出现一个空的心、空的心识或空的觉知。
但是,当带有“自我”感觉的心抓住某种东西的瞬间,它同时创造了自我和被抓住的对象。因此,它立即在心中投射出土星状的图像(代表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这三界)。土星被旋转的光环所包围,这光环代表缘起(paṭicca-samuppāda)——一个因果过程,它持续不断地产生无明(avijjā)、贪爱(taṇhā)、执取(upādāna)、烦恼(kilesa)和持续的痛苦。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心中造作的心理图像,我们错误地认为它们是真实的。这种错误的认知是身见(sakkāya-diṭṭhi)——认为确实存在自我的观点——这是将众生束缚在轮回中的十种束缚(saṃyojana)之一。
观照自然的真相
当一个人有机会听闻正法——佛陀的教导——他就会明白:一切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一切事物都走向衰老、疾病和死亡;没有真实的自我,没有什么真正是“我们”或“我们的”——最终,一切都消逝、止息为“无我、无我所”的状态,因为它们从“无我”而生,最终也回归到“无我”的状态。
在听闻这些教法后,如果一个人将心向于所听闻的佛法,他就会开始观照真理。在观照之前,这个真理的实相尚未在心中扎根。但一旦心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向于真理,理解就会加深。
我们反思,尽管我们的生活看似静止——无论我们是坐着还是站着——事实上,我们站在时间的传送带上,它总是在向前移动。尽管我们可能站着不动,但我们总是在被向前运送。我们认为自己是静止的,但世界却在不断旋转。我们脚下的土地处于地球表面——而地球从未停止过旋转。它不断地将我们推向衰老、疾病和死亡。没有人能够逃脱。
我们并不是真正静止不动。无论我们是坐在家里还是开车,一切都处于地球表面,地球的运转携带着我们。它将我们所有人推向腐朽和死亡——无一例外,无论国籍、宗教,无论孩童、成人还是老人。世界不断地运转,朝着腐朽、死亡和分离前进,一直如此。
我们许多人已经被邀请参加过无数次葬礼——祖父母、父母、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子女——甚至孙辈。然而,我们很少想过,下一个离开的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同样受制于同样的命运,无法逃脱。同样的状态也等待着我们。
当观照这些真理时,无论我们在做什么工作——无论是去洗手间、吃饭喝水、还是四处旅行——心都向于这个真理。我们不断地观照它,直到它化为一种真实的感觉,真正在心中生起——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或想法。我们反观自我,了知:“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当心向于此时,真切的了知就会生起:“我必将死去。”
在信心的支持下,我们相信佛陀的话——我们所执信的自我的感觉并不真实存在。佛陀早已从他自己的心中证悟了这个真理,并来教导我们。
自我的这种感觉并非真实存在。它从一开始就从未真正存在过,即使现在,在当下,它也并非真实存在。
存在的是五蕴,它们被约定俗成地称为“我们”。这些事物生灭不息——它们生,然后灭。
每个人都逐渐成熟、变老、死亡——一个接一个地腐朽。他们像树叶一样,在旱季落下,一个接一个地,迅速地凋零。
没有所谓真正恒常的自我……完全没有。没有任何人或事物拥有持久、不变的自我——没有稳定、永恒的身体;没有稳定、永恒的心或心理状态。最终,一切都止息,无所剩余。
曾经充满人的繁忙的房屋——一个人接一个人死去。然后亲戚被叫来帮忙整理和分发他们的物品。剩下的是空荡荡的房屋。一个又一个房屋——最终,它们都变得荒无人烟。
每个房屋里曾经住着许多人。但现在,那里不再住着任何人。它变成了一栋废弃的、被遗弃的房屋。另一栋房屋——有人死了——亲戚聚集,来帮忙整理东西。每个人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个房子也变得空置。
曾经有人住在里面。曾经,我们也住在里面。最终,我们将不再在那里。曾经有母亲和父亲住在里面。但后来,母亲和父亲也不再那里。曾经有某些东西——但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们曾经在这里——但未来,我们将不再在这里。
当我们死去时,我们将变得和所有人一样。当尸体从太平间出来时,它会变绿——就像所有其他的尸体一样。从太平间取出尸体时,会用白布覆盖。身体僵硬——所以手臂必须从布下弯曲出来,让其他人能够进行浇水洗浴仪式。
当我们活着时,我们试图聚集越来越多的东西,拥抱并执取所有事物。我们想要一切。但当我们死去时,我们什么也带不走——甚至带不走人们在告别仪式上浇在我们尸体上的水。无论我们囤积了多少,无论我们拥有了多少——我们都将与家人分离,与地位和荣誉分离,与财富和财产分离;甚至与我们自己的“自我”分离——与我们的思想、记忆和感受分离。
我们必须不可避免地与这些被执取为“我”和“我的”的五蕴分离。
一遍又一遍地将心向于此……
即使有时心对观照感到厌倦,也只需改变观照的角度——但永远不要偏离自然的真理:无常、腐朽、衰老、疾病、死亡和瓦解的真理。所有生起的事物都必须死亡。所有生起的事物都只为了消逝。没有人能逃脱这个真理。相遇就是为了分离。如果没有分离,就不会有相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最终我们都必须留下。最终,到了离开的时候,我们两手空空地离开——正如我们空手而来。我们什么也带不走。
最终,我们会被运到火葬场。我们的尸体膨胀,被放在葬礼柴堆上,僧侣们被邀请来吟诵不净颂(Paṃsukūla):
aniccā vata saṅkhārā, uppāda-vaya-dhammino uppajjitvā nirujjhanti, tesaṃ vūpasamo sukho.
诸行无常,有生灭法,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教法告诉我们,所有的有为法(saṅkhāras)——身心、自我和他人、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生灭不息。
当执着于有为法(saṅkhāras)——将其视为“我”和“我的”——停止时,至上的快乐就证悟了。
要从根本上熄灭有为法,无明(avijjā)——也就是邪见——必须被熄灭——通过正见,即智慧(vijjā)——它洞穿了所有执着的根源。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执着于儿孙更大的痛苦了。第二大痛苦是执着于丈夫和妻子。第三是执着于地位、财富和财产。所有持续在生死中轮回的众生,都是因为这三种巨大的执着——在每一次生命和每一个界域中带来悲伤、痛苦、艰辛和泪水。
执着于孩子就像脖子上套着绞索——就像一根绳子紧紧地系在自己的心上。执着于丈夫或妻子就像将双臂捆绑在一起,如同戴着手铐。执着于财富和财产就像脚踝戴着镣铐,如同被法庭判刑并用铁链束缚。这三种执着的束缚不仅束缚脖子、手臂或脚——它们束缚了心。它们直达内心深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如此难以解开——也是为什么众生在三界中不断轮回,陷入悲伤、忧愁和绝望,泪水泛滥如海。我们无量劫以来因痛苦而哭泣的泪水,如果还没有干涸,将远远超过所有海洋的水总量。痛苦是所有众生最大的负担。
谁能斩断这三种束缚内心的执着,这样的人就能从三界中解脱出来。
如何斩断这三种执着的束缚?必须通过观照——将我们自己和他人都视为有为法(saṅkhāras),无常的。如果我们只观照他人而不向内观照,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我们自己是不朽的,而只有他人必须死亡。这会导致当我们所爱的人不可避免地离世时,产生悲伤。
因此,从心底观照自我。看到我们自己也是无常的。他人只是例子——我们自己也和他们一样,必须灭亡、分解、消逝。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其本质都是腐朽,其终结都是瓦解。
无论我们拥有多少财产或住所,都无法逃脱衰败。一栋新建的房子从建造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老化。一辆车,即使购买当天是全新的,很快也会成为一辆旧车。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任何被造作、构建或组装起来的事物——都从最初的无中生起。
一旦它生起,它就不可避免地衰退、腐朽、恶化、瓦解和崩溃。它会衰老、生病、死亡——这是它的自然规律。最终,它彻底消失。
这是自然的法则。没有人能逃脱这个真理。
必须观照,直到三法印(无常 anicca,苦 dukkha,无我 anattā)的实相被清楚地理解——这是自然的法则。无论是人、动物,还是物体——任何被建造、形成、造作或创造的事物,都受制于衰败的法则,并最终走向终结。
当以这种方式观照时,反思转向内在的自我。最终,我们到达老年、疾病和死亡——分解为灰烬和尘土——以及自我感觉的彻底止息。
如此反思,我们开始明白:我们内在和周围的一切,所有亲近的人——我们的孩子、配偶,甚至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最终都必须死亡并与我们分离。无论他们多么富有,无论他们拥有多少亿万财富——我们所见过的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恨的人——他们都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祖父母、曾祖父母、长辈、叔叔阿姨——他们都稳定地从这个世界上离去。我们亲自认识的有多少人已经逝去?而我们仅认识的又有多少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当他们活着时,如果我们真的仔细观照,我们会看到他们每个人都爱过,但也痛苦过。他们因孩子而痛苦,因孙辈而痛苦,因自己而痛苦,因父母而痛苦,因财产而痛苦,因配偶而痛苦,因无休止地争取财富和物质而痛苦。他们的生命充满了痛苦。而他们所追求的,他们试图执着的东西,最终,他们都与它们分离了。他们来自无——最终他们必须回归无。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例外于这个真理。我们来自无——最终我们也必须回归无。深刻地反思这个真理。让它更接近内心。
逐渐地反思——一件一件地——反思我们自己和他人。
从我们受孕时起:我们是由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的结合,在子宫里形成的。我们逐渐发展成一滴血。从那滴血,我们通过母亲食用的动植物尸体——死肉——所滋养,并通过脐带进入卵子,那滴血,我们长成胎儿。母亲吸入空气——吸收风界和火界——并继续每天消耗死去的动植物残骸。那些动植物的尸体变成血液和体液,滋养那滴血,使其扩张和生长。我们长大了。但是由什么长大的?由母亲摄入的风、火、地、水四界——以及众生的尸体。我们将这些东西吸收为血液和体液。这使得那团血块扩张和生长。我们现在居住的身体——它真的是“我们”吗?
我们长大了,然后出生。但是我们以这种精确的形态从子宫里出来了吗?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所相信的那个“我”是谁?即使现在,每天,我们仍在继续食用动植物的残骸。我们消耗死尸——用它们的残骸一层层地堆砌这个身体。如果我们不吃,我们就会死。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吃。我们吃牛、水牛、猪、鸭、鸡、虾、贝类、螃蟹和鱼的尸体——每天无数的生命。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运转。但即使如此,这个“自我”也并非真正的我们自己。
我们一出生,就立即将这个身体抓住为“我们的”。我们将这个肉体,以及生起的思想、情绪和感知,认同为“我”和“我的”。识界——心识——与地、水、火、风四界结合,形成了一团血块,一滴源于精子和卵子的生命。我们认为这是“我”。但事实上,那个“我”并非真正的我们。心识——当被邪见纠缠时——错误地感知到了一个自我。它与四大——地、水、风、火——混合,产生了感受、认知和心行(mental formations)。当身体出生时,我们就抓住这个身体——带有思想和感受的身体——作为“我”,作为“我的自我”。
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忘记了,从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自我。
然后这个身体以及所有的思想和情绪都瓦解了。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被构建和造作的东西,最终都会止息。色法(rūpa-dhamma)和心法(nāma-dhamma)都走向终结。由于无明,我们在每一生中都抓住形成的身体作为“我们”。因此,我们继续前进,在新的身体中获取新的形态。我们在一个新的身体中过上新的生活。
我们已经出生为几乎所有存在的动物。
即使我们出生为一条蠕虫,我们仍然会执着于那个蠕虫身体作为“我”——因为执着于每一个有为法(saṅkhāra)的身体作为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们也会执着于周围的环境——执着于周围的人,执着于所有亲近和熟悉的事物。每一生都是如此。一旦我们死了,周围的环境又会改变——取决于我们所造的业,它决定了我们下一世会投生到何种形态。然后我们会在那个新的身体中拥有新的记忆、新的思想和感受、新的心行造作。我们认一个新的形象作为我们的母亲。我们认一个新的形象作为我们的父亲。我们认一个新的身体作为我们的身体。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新的儿女,新的孙辈——完全新的身份。
但是,只要我们没有了知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就会不断地将新创造、新形成的身体误认为是“我”。因此,我们不断地更换身体,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以每一种新形式受苦——永无止境。
直到我们真正了知我们是谁的那一天。
佛陀和阿罗汉早已了知他们是谁。但在任何一生中,我们从未真正了知我们是谁。只有当我们真正从心底里了知根本没有真实的自我时——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从痛苦中解脱。这种了知——了知一种永恒不变的实相,它从未生起也从未死亡——这才是真正将我们从痛苦和生死循环中解放出来的。这是对不生、不灭、不死的解脱(deathless)的证悟。只有那时,才有真正的自由。
一旦我们投生到其他形态,离开人道,我们就会失去听闻和理解我们是谁的真相的机会。我们将不再能够寻找了知我们的“自我”。只有通过智慧,并且在人道的形态下,我们才能发现真理——事实上,根本没有自我。通过智慧和善知识的引导,通过我们现在听闻的佛陀的正法——这才是我们发现我们是谁的途径。我们发现根本没有真实存在的自我。这就是佛陀所证悟的。他自己证悟后,来教导我们放下对身份和自我的执着。
那些贪婪、愤怒、迷惑和自私的人,是因为他们从未观照过这个真理。他们的心只充满了“我”和“我的”——最终,什么也没留下。
我们是被世界遗忘的人。我们的孩子深爱我们。我们的丈夫爱我们。我们的妻子爱我们。但一旦我们死了,他们可能会在寺庙旁边为我们建造一座小舍利塔,或者在墓地里立一块墓碑。我们的儿孙可能在最初的几周来祭拜。之后,杂草丛生。坟墓,祖先的墓地——人们一年只去一次。而那些曾经来祭拜的人——他们也逐渐死去。最终,没有人留下纪念。不仅逝去的人被遗忘,甚至那些曾经来纪念他们的人,自己也走了。
我们所执着的一切,视为“我”或“我的”——甚至我们脚下的土地——都只是地球表面。我们已经生生死死了无数次,我们的骨骸现在充满了大地。无论我们挖到哪里,都能找到我们自己堆积的骨骸层。我们声称属于我们的土地——这块地,这片领土——只是地球表面的一块,我们曾在这里生生死死了无数次。但它从未真正属于我们。最终,我们都会死去,离开这个地球。然而当我们活着时,我们为它而战。亲戚和兄弟姐妹因土地纠纷而互相残杀。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时,地球早已存在,但我们却来争夺它——争夺财富,争夺土地,争夺地球表面。然后我们都死了——一个接一个——从未从我们的无明中醒来。那么,这个所谓的真实存在的“自我”在哪里呢?
根本没有需要毁灭的自我。它只是无明——迷惑——执着于“我”和“我的”的观念。它完全是自然。地、水、风、火——它们都是自然。它们聚集在一起,呈现为一个自我,一个人。每天我们消耗动植物的尸体——无数的生物。它们成为我们身体中的地界。我们喝水——无数瓶——但我们执着于那是“我们的水”,是“我们的水界”。我们从自然中吸入空气——并声称这呼吸是“我们的”。我们身体中的温暖和热量,我们称之为“生命”——我们也声称是我们的。最终,我们声称所有的自然都是我们自己的自我。我们执着于这一切。但是当这个身体被焚烧时,它会变成灰烬和骨骼。这些残骸被撒入河流或海洋——回归自然。
从土地来,回归土地。 从水中来,回归水。
这个身体——地、水、风、火——必须回归自然。
因为执着于“我”和“我的”,我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最终,我们仍然必须与这一切分离。一生又一生,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迷惑,一次又一次地重生,仍然执着于“我”和“我的”。并且必须再次与一切分离。执着于无法抓住的东西——这是迷惑,这是疯狂。
将无法拥有的事物视为可以拥有的。将无我视为自我。将无常视为永恒。将痛苦——不稳定、无法维持自身——视为快乐。将不美视为美。这被称为颠倒见(vipallāsa)。以这种方式“颠倒”的认知是邪见(micchā-diṭṭhi)。
邪见就是无明(avijjā)——未能看到自然的真相。一个没有看到真相的人生活在迷惑中。自然的真相永远不会改变。它如其所是,永恒不变。自然如其所是。它一直都是如其所是。每个众生,一个接一个地,执着于这种自然为“我的”——这被称为“无明”(avijjā)。
所有的佛陀都证悟了自然的真相。它不属于任何人。它不是任何佛陀的所有物。它只是所有众生共有的真理——不变、永恒。
看见真理时,放手就会生起
当一个人密集地修行止(samatha)和观(vipassanā),观照身心——五蕴——他会看到它们是无常、苦、无我的,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疾病和死亡。最终,一切止息——回归无我,无法被拥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视为“我”或“我的”。它从无我而生,然后止息,再次回归无我。
通过持续不断的观照,迷惑执取的抓握开始松动。束缚内心的许多绳索开始消失。它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脱落。最终,只剩下一根绳索: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执着——通常是配偶——由于执着于自己的五蕴和他人的五蕴。曾经黑暗而沉重的心,开始变得轻盈——从漆黑变为较浅的灰色。
随着一个人不断地观照真理,一个接一个地放下执着,内心执着的东西越来越少。如果一个人不再执取,就像不再将绳子系在任何东西上。或者即使仍有联系,它们也不会被紧紧地系住。心中可能仍有对其他人的念头,但不再有束缚性的执着。心的颜色不再是黑色。即使一个人有亲人——比如一个家庭——心也不再紧紧地执着。一个人活在当下。工作时,心不被家庭的念头所占据。然后,心的颜色逐渐从黑色或灰色变为白色,因为它不再以导致痛苦的方式执着。
所有的执着逐渐减少。剩下的是平静和宁静。但即使找到了平静,修行者也不会停在那里。他会不断地将心向于真理——一遍又一遍——永不停止。直到一种深刻、真实的放下自然地从心中生起。
当一个人观照身心(有为法)的无常(anicca)、苦(dukkha)、无我(anattā)时,导致“自我”邪见的错误认知就会消失。当不再执着于“自我”的观念时,就没有“自我”去系绳索了。即使一个人观照到其他事物是无常的,如果他仍然执持“我是恒常的”信念,绳索仍然会存在,随时准备系在另一个事物上。
因此,当不再执着于“自我”的观念时,绳索消失了,系绳子的人也消失了。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从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自我”。
我们所抓住的一切,视为“我”或“我的”——都是由无明(avijjā)所造作、心行(saṅkhāra)所形成的迷惑,由“自我”的感觉、贪爱和执取所形成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无休止地在轮回(saṃsāra)的循环中循环——每一次都相信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新的故事、一个新的身份。
我们所承担的所有身体——都生于母亲,母亲用来自死者的食物滋养了一滴血。我们的生命一直由动植物的尸体维持。
然而我们竟然敢将这个东西称为“我”;我们竟然敢声称它是“我的”。
我们战斗以保护它、喂养它、装饰它、满足它——却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它。
一次又一次地重生。
每一次都以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家庭、一个新的故事受苦,然后再次失去一切——被扔回循环中,却不知道出路。
但是,当一个人开始深入观照时,当心开始向于真理,开始斩断执着的锁链时——从看透今生自我的幻觉开始——
就可以终结这个循环。
可以从三种执着的束缚中解脱:执着于孩子、执着于配偶、执着于财富和财产。
这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镣铐——它们是缠绕在心上的链条。
当这些链条断裂时,心就解脱了。
当心解脱时,就没有更多的轮回。
不再被束缚在三界中。
不再执着,不再悲伤,不再寻求。
只有寂静。
只有自由。
只有平静。
涅槃。
第二章 无明(avijjā)——痛苦之循环的根源
土星状球体中的小人形象代表了对自我的无明信念(avijjā),它在心中(土星球体)形成了一个无明的核心(身见)。它滋养着缘起(paṭicca-samuppāda)的循环——痛苦和再生存的循环。这种无明导致了业行的造作、贪爱、执取和有(“成为”)的创造,从而导致了未来在各种形态和生命中的投生。这个循环由土星环代表,它围绕着土星球体旋转。
如果一个人相信自我,这个缘起(paṭicca-samuppāda)的循环就会不断地旋转,这种无明(avijjā)产生:
→ 业行(saṅkhāra) → 识(viññāṇa) → 名色(nāma-rūpa) → 六入(saḷāyatana) → 触(phassa) → 受(vedanā) → 贪爱(taṇhā) → 执取(upādāna) → 有(bhava) → 生(jāti) → 老死(jarā-maraṇa)以及所有形式的苦(dukkha)。
这个循环像一个光环,围绕着土星——其核心是自我,或无明——永无止境地旋转。
什么是“世间”?
“世间”是那些在世间被执着、被攀附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外在事物,还是自己的身心、五蕴(khandhas)——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人的“世间”。内在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也是“世间”。我们的身体也是“世间”。外在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也是“世间”。色界和无色界的禅那也是“世间”。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执着的所有众生都是“世间”。任何事物,无论是什么,在三界——欲界(kāma-loka)、色界(rūpa-loka)或无色界(arūpa-loka)——中被执着,都会成为我们的“世间”。
当我们执着于世间时,我们就创造了一个世间。由于迷惑的执取,一层无明的壳形成了,围绕着心,形成了一个分离的自我,从无为法(visaṅkhāra)的自然、无边际的状态中分离出来。缘起(paṭicca-samuppāda)的循环然后开始围绕着它旋转,在每一个当下产生痛苦。死亡时,一个新的有(存在)被产生,一个新的形态和领域,继续接受业的果报和体验痛苦。
因此,我们必须看清那些被执着的事物,它们导致了“自我”的感觉在心中生起。如果没有东西被执着,那么就不会有执着者的自我生起。那么,带有自我核心的土星——心中无明(avijjā)的核心——就不会出现。围绕土星旋转的缘起(paṭicca-samuppāda)光环也不会出现。
如果心中有任何执着的东西,它就会产生三界的“成为”(有):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它们在心中被创造。因此,它们就像被心造作的“世间”——随着心识的每一个变化瞬间而生灭。
如果一个人执着于任何与感官相关的事物,代表心的球体就成为欲界——称为欲有(kāma-bhava)。
欲界(kāma-loka)是众生仍然沉迷于五欲——通过眼、耳、鼻、舌、身——的领域。这包括动物、饿鬼(peta)、阿修罗、地狱众生(niraya),以及人类和天界的天神。土星球体反映了相应的界域。如果一个人在执着于色、声、香、味、触觉时死去,他就会在欲界(kāma-loka)中投生。
如果一个人执着于色界禅那,代表心的球体就成为色界梵天(rūpa-brahma),称为色有(rūpa-bhava)——成为沉迷于四禅的禅支者:寻(vitakka)、伺(vicāra)、喜(pīti)、乐(sukha),以及一境性或舍(ekaggatā or upekkhā-jhāna)。如果一个人在死亡的最后时刻仍然沉迷于这些色界禅那,他就会在色界梵天中投生。
如果一个人执着于无色界禅那(arūpa-jhāna),代表心的球体就成为无色界梵天(arūpa-brahma),称为无色有(arūpa-bhava)——成为沉迷于四无色定者:空无边处(ākāsānañcāyatana)、识无边处(viññāṇañcāyatana)、无所有处(ākiñcaññāyatana)和非想非非想处(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如果一个人在死亡的最后时刻仍然沉迷于无色界禅那,他就会在无色界梵天中投生。
这三界是在心的当下造作的心理有为法,在死亡的最后时刻亦然。如果一个人在死亡时仍然沉迷于这些对象,那么来世就会相应地到来。
但是,如果没有执着的对象,没有沉迷——那么就没有沉迷者的自我,就没有执着者的自我。如果一个没有沉迷者的自我,没有执着者,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执着。
当既没有执着的对象,也没有执着者的自我时,由土星球体代表的三界——欲界、色界和无色界的存在(kāma-bhava, rūpa-bhava, and arūpa-bhava)——以及围绕土星旋转的缘起光环,就会彻底停止。
土星及其光环只在一种情况下消失:当没有执着的对象和没有执着者的自我时。如果没有东西被执着,就不会有执着者的自我留在心中——不是因为自我被摧毁了,而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从未真实存在过。
sabbe dhammā anattā “诸法无我”
没有“我”;事实上,没有真实存在的“自我”。
所有界域——从下三道、动物、饿鬼、阿修罗、人类,到天界的投生——都以执着和痛苦为特征。在每个当下,心的光明或黑暗以及心的品质代表了一个人当前居住的界域——以及,如果在那一刻死去,将投生到哪个界域。思想、言语和行为是由心中随眠烦恼和烦恼习气(anusaya-āsava)在每个当下的习性决定的,这些习性反映了当前居住的界域以及未来的投生界域。
如果在某个当下,心像动物的心,像地狱众生的心,像饿鬼的心,或者像阿修罗的心,那么在死亡时,就必须相应地投生为动物、地狱众生、饿鬼或阿修罗。
然而,通过布施、听闻佛法、持戒和禅定(samatha)等善行,心的外观会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白皙明亮。一个人可能生活在人道,但心却呈现出光明和白色,反映出天界的品质,与天界相对应。心中微小的自我形象可能是一个天神般的天人,其光明和内在光芒的程度表明了天界的层次。
尽管身体留在人道,心却居住在天界。如果心的颜色是明亮的银白色,则表明心已经培养了禅那(深定)并能够提升到更高的天界,如色界或无色界(rūpa brahma loka or arūpa brahma loka)。
当一个人观照身心(有为法)的无常(anicca)、苦(dukkha)、无我(anattā)时,导致“自我”邪见的错误认知就会消失。当不再执着于“自我”的观念时,土星内部微小的自我形象就会消失。即使一个人观照到其他事物是无常的,如果他仍然执持“我是永恒的”信念,这个形象仍然会存在,而产生“成为”(有)、轮回的缘起循环将继续。
因此,当不再执着于“自我”的观念时,土星消失了,心中微小自我的形象也消失了。
最终,甚至连一个空心也不复存在——根本没有任何心。如果一个人仍然觉得一个“空心”存在,这意味着仍然有一个“自我”,一个“我”执着于那个空心。在这种情况下,土星及其光环仍然不会从心中消失。
最终,当没有执着的对象时,就没有人去执着——心(土星)就消失了。但这并非留下一个“空心”的消失——如果仍然有一个空心存在,它将再次充当一个攀附者和一个被攀附物的容器。没有“空心”留下,就像没有留下一个空的罐子或空的酝酿罐——所以没有留下任何容器,让任何人再存储任何东西,或浸泡和酝酿任何东西。因此,没有“空心”留下,像一个等待被填充的空罐子。没有任何容器可以容纳任何东西了。
这并非自我消失了,对象消失了,但空的土星球体仍然存在,其内部现在是空的。事实上,整个土星都消失了。它完全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甚至球体内部的“空性”也消失了。因此,没有留下“空心”。既没有“内部”,也没有“外部”。只剩下自然——没有自我,没有身份,没有“我”或“我的”。
如果我们错误地修行,试图摧毁执着者的自我,这就会变成自我试图摧毁自我的案例。我们引入一个自我来摧毁另一个自我——试图消灭“我”以便“我”能够证得涅槃。这变成了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一个我在另一个我之内,一个我在另一个我之内——永无止境。
相反,一个人必须培养智慧和洞察力,以了知:生起“自我”感觉的心识当下仅仅是一种有为法——在当下生起和止息。
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理解,没有恒常的无明(avijjā),没有持久的自我,没有永恒的“我”或“我的”。只有刹那刹那的迷惑——一系列迷惑的心识瞬间不断生灭,让人感觉仿佛没有任何生灭。即使在死亡的那一刻,正是这个迷惑的心识瞬间即刻造作一个新的有(“成为”)——一个新的存在。因此,没有恒常的“心”,没有持久的“自我”,没有永恒的“灵魂”从一个界域漂移到另一个界域。
当对自我观念的执着——执着于五蕴为“我”或“我的”——减少约25%时,这样的人被称为“入流”(须陀洹 sotāpanna)。如果减少了50%,“一来”(斯陀含 sakadāgāmī)。如果达到75%,“不还”(阿那含 anāgāmī)。减少100%就是“阿罗汉”。(注:这些数字只是假设性的,仅用于说明执着和攀附的程度。)
心的颜色变得像阳光一样的金色,并且越来越明亮——从25%到50%,到75%,最终,在证悟阿罗汉的那一刻,像太阳本身,或100%的纯金。
当一个人朝着涅槃的“流”前进时,沉重的土星状球体变得不那么致密,更加透明。它的质地发生变化——从坚硬如岩石变为柔软如海绵,最终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
了知没有真实的自我可以被抓住,这动摇了无明的核心。土星的外壳开始破裂,粉碎并与无边的宇宙合为一体。
每一次连续的爆炸都使土星更小、更透明。
从坚硬如铁球,它变得不那么致密,多孔,像海绵。最终它变得像玻璃一样薄而透明——容易破碎。
随着每一次连续的爆炸,球体本身变得更小、更微细,围绕着它快速旋转的光环也变得更慢。它所代表的缘起循环——不断产生无明、贪爱、执着和烦恼,有、生和苦——也开始减速。痛苦减少。
随着自我的感觉开始与外在事物分离,那些系在外在对象上的绳索,如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地位、财富、名誉和财产,也开始褪色并消失。
最终,执着只剩下对自己的身心。没有绳索向外延伸;无论剩下什么绳索,都只系在自己身上。
一个人开始将身心——五蕴——视为自我创造的牢狱,带来痛苦,并渴望从中解脱。但在内心,对想要从五蕴中解脱的自我的执着,在土星中创造了一个形象:一个人被困在牢狱中。他试图摇晃并打破牢狱的铁栏杆,以便从五蕴中逃脱,将五蕴视为痛苦。但试图解脱自我的尝试只会使自我的感觉变得更大,牢狱也变得更坚固。
一个人开始观照三十二身分,身体的不净相(asubha),或死随念(maraṇānussati),以便从心中看到五蕴中没有真实自我的真理。当解脱的智见了知这个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因此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实体)时,对身体的执着——将其视为“我”或“我的”——就彻底止息了。然后,土星“爆炸”了。当无明的外壳开始破裂时,身体内部发生爆炸性的反应。感觉身体消失了,变得没有重量。剩下的是心(心识和其他心行,共同运作)以及执着于它,并相信“我是了知者”(即被视为“自我”的“觉知者”)的迷惑自我感。
然后慧智(paññā-ñāṇa)就会生起,从心底了知心和心行(所有有为法)是自己生起和自己止息的;自己生起,自己止息……之后,注意力不再放在生起上;只看见止息——一遍又一遍……在自然的空性中,没有观察者。
最终,解脱的智见得以实现,了知心和心行——所有有为法——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或“我的”。随之,无明的外壳爆炸并融入宇宙,一场反应发生了。
第三章 最终的觉知
一些修行者在放下对心的执着后,仍然继续执着于“觉知者”(knower)。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执着于色、心行或心所(cetasikas),但他们仍然执着于“我是了知者”、“了知者是我”、“这个觉知属于我”的观念。他们试图净化自己的心,以帮助这个所谓的觉知的心。由于这种执着,会显现出各种形式的心理行为模式和特征表达。例如:
案例一
表现出焦躁不安、四处奔走、像疯子一样寻找涅槃的行为——到处寻找阿罗汉,问他们涅槃是这样还是那样,以至于旁观者认为他们精神失常了。
有一次,人们拦住了这个疯子,问他:“你到处乱跑寻找什么?”但第一个叫喊的声音他甚至没有听到。于是他们围住了他,挡住他前进和后退的路,大家一起喊道:“你到底在急着找什么!?”
这种突然的对抗造成了冲击,震撼——他震惊地沉默了。惊叹生起,随之而来的是正念。一个法音在他心中爆发:
像疯子一样到处乱跑、挣扎—— 终极真理了知无挣扎。 停止挣扎——停止疯狂的寻找, 你就会找到佛法。
在那一刻,仿佛他撞上了一堵无形的、无相的墙壁。仿佛心——宇宙,内外——彻底停止了,一切都瓦解了。剩下的只是深邃、不动的寂静。一道金光在整个世界中短暂地绽放,没有边界,遍布宇宙,然后消失了。
感觉一切都陷入了寂静,持续了永恒的时间……当寂静过去后,不再有无明,不再有无为法的概念,甚至不再有“解脱的心”去了知任何东西,或证得任何东西。所有的贪爱都止息了。
案例二
即使感觉牢狱已经消失,但仍然存在一种微妙的自我感,仿佛在四处游荡,寻找涅槃。
在这种情况下,思绪不断围绕着这个问题旋转:“我已经放下了一切——为什么我还没有证得涅槃?”这是因为仍然执着于心为“我”、“我的”或“我所”。所以这样的修行者要么试图帮助自我,要么试图帮助心证得涅槃。这通常发生在那些修行决心很大的人身上——他们不再执着于世俗事物,而只执着于对涅槃的渴望。他们是比丘、比丘尼或在家居士,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真诚、精进的修行中。土星中的形象不再是一个被囚禁的自我——而是一个微妙的存在:一个在透明的土星状球体中行走的人的形象。
但是,当一个人注意到这个“我”仍然执着于涅槃,仍然试图帮助“自我”证得涅槃时,一种微妙的信念形成了:“如果自我不执着于涅槃,自我不执着于心,那么我就会解脱,并证得涅槃。”
只有当慧智从心底看到真理时——那个“涅槃”的概念——以及那个努力追求涅槃的“我”——都是在当下不断生灭的心行造作(saṅkhāra)时——无明(avijjā)、贪爱(taṇhā)和执取(upādāna)才会止息,了知根本没有真实的“自我”。当不再有“我”将要证得涅槃的感觉时,不再有“我”要去证得涅槃的感觉时,甚至不再有对涅槃的渴望时——甚至不再有一丝一毫“我将达到”或“我尚未达到涅槃”的感觉时——当不再有任何“自我”的感觉混入其中时——这才是真正的涅槃。
现在,整个世间及其三界即将进行最后的爆炸——土星状的球体将被彻底粉碎——因为了知导致了其中的自我消失。土星内的自我被震撼到了核心,震撼到流泪,震撼到整个世界系统都颤抖。整个宇宙都停止了。这是一种像真实的爆炸一样的爆炸——这种爆炸摧毁了心中执着于三界——欲界、色界和无色界——的自我最内核的核心——执信于“我”的存在,并与之执着于世间。
当执着于三界的自我终结时,土星及其光环爆炸并消失。最终,什么都不剩下——既没有执着者,也没有被执着物。当所有的执着都结束时——甚至是对涅槃的执着——心的颜色和光芒彻底消失。没有颜色留下。没有无明的核心留下。没有球体,也没有缘起的土星环。如果没有球体,就不可能有光环。无明核心内的自我——它既是土星球体又是其光环、缘起循环的根源——同时彻底消失了。
案例三
在最后的案例中,被执着为“自我”的“清净的心”可能仍然存在,清晰地漂浮着。慧智将了知,这个“清净的心”也是一种有为法(saṅkhāra),它生灭不息——无常、苦、无我。不关注它的“生起相”,只看到它的止息——一遍又一遍……直到对这个“清净的心”的迷惑和执着终结。然后,土星的最后痕迹将发生最终的爆炸。没有“我”作为这个“清净的心”留下来了知任何东西,去证得,去达到,或者去成为任何东西, anymore。当没有“我”作为这个“清净的心”时,就没有执着者,没有贪爱或烦恼,也没有更多的痛苦。
即使是“清净的心”,看起来是纯净的顶峰,也是被执着的东西。
解脱的最后阶段是,即使是看起来最纯粹的觉知(清净的心),也不再被执着为“我”或“我的”。如果一个人仍然相信“我是清净的心”,或者“清净的心是我的”,那么无明(avijjā)就没有完全止息。
我们无明地将清净的觉知视为“我”或“我的”——但这种微妙的执着可以通过我们内在的纯粹识界了知,它仅仅是另一种被了知的有为法。纯粹识界是一种自然,它没有“觉知者”,没有执着地了知——它已经存在于我们内在。
但只要存在无明、贪爱、执着和烦恼,就会有迷惑,将觉知视为“我”或“我的”。
只有当智慧生起时——真实的、穿透性的了知——它从心底清楚地看到,当下的觉知者或观察者的“我”,仅仅是一种有为法,它自己生灭,空而无实——才会了知心、识或“觉知”,它们没有无明、贪爱、执着和烦恼。
这只是觉知——了知自我——没有觉知者或观察者的觉知,没有执着者。就像眼睛看见色法——只有色法显现,而不是眼睛本身。
事实上,那个看见“我们”的识界——被称为“清净的心”、“纯粹的识”或“觉知”——只是了知,不带自我。
无论在哪个当下,迷惑导致心将自己视为“觉知者”——一个了知的自我——心中就会立即生起一个带有光环的土星的形象。
土星环代表缘起(paṭicca-samuppāda)的循环,围绕土星旋转——这个过程在每一个当下不断产生无明、贪爱、执着和烦恼;痛苦、忧虑、悲伤和苦恼。
我们可能在修行时,错误地相信最终会有一个最终的觉知者成为不死——一个最终的、“空性的觉知者”。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消除自我的感觉,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空性的、平静的觉知者”,并以此方式证得涅槃。但这本身就是无明(avijjā)。
事实上,没有自我会成为最终的、不死的觉知者。在每一个当下生起的每一个“觉知者”,都是生起然后止息的有为法。
即使是那个所谓的清净觉知者或空性觉知者,看起来与被看到生灭的觉知者截然不同——事实上,它本身仍然是一个有为法的觉知者,同样生灭不息。它不是一个空性的“自我”,不是一个不死的“我”。如果被当作如此,一个人不仅将有为法视为无常的,而且仍然秘密地执着于一个据说是空性的“自我”。
没有“空心”或“空性自我”漂浮在万物之上,作为独立于它的存在。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清晰漂浮的“空性觉知者”,那么仍然有一个“自我”无知地执着于它。
没有自我可以执着于任何觉知者——无论是“觉知者”,还是观察那个觉知者的另一个觉知者,如此无限延伸。无论有多少层觉知者——没有一个,没有存在自我去执着于它们;没有“人”在体验它们或与它们互动。
没有执着的对象,没有执着者的自我的那一刻,土星及其光环彻底消失。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任何状态中感到愉悦——在觉知、看见或存在中——如果他再次对任何事物感到高兴或执着——即使只是短暂地相信“我已经觉醒了”,“我有了洞察力”——那么心中又会生起一个新的土星状球体,以及不断围绕它旋转的缘起光环。瞬间,三界全部在心中重新出现。
土星及其光环并非真实存在。它们只是在执着时,在当下造作的心理图像。当一个人完全了知执着的根源并熄灭那个根源时,土星及其光环就会彻底消失。三界在那个当下止息。因此,三界的生起并非真实存在。它们在每个人的心中造作——根据所执着的事物而形成和改变。
如果心中没有形成任何界,那么那个心识就不会投生到外在的界中。例如,如果心识将其当下的执着从地狱状态转向天界状态,那么之前正在造作的地狱界就不再存在于那个人身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界——天界——形成。如果对天界的执着止息,并且随着执着的终结而证得涅槃,那么根本没有任何界留下——没有地狱,没有天界,没有人间。
最终的觉知
最微细的觉知,最终的觉知者, 清晰地漂浮在空性中, 不执着于任何东西,难以辨别, 但仍然以一种微妙的、隐藏的方式存在。
慧智从心底了知 即使是这个被执着为自我的纯粹识, 这个清净的心——“最终的觉知者”—— 也只是一种有为法(saṅkhāra), 生灭不息, 无常——苦——无我。
无需抗拒,无需让它消失。 只是不要关注它的“生起相”。 让清净的觉知,这个“最终的觉知者”, 止息……止息……止息……
直到没有任何清净、了知的觉知者留下 去了知任何东西。
当没有觉知者时, 就没有执着者, 没有受苦者。
只剩下纯粹的自然—— 无需了知, 无需存在, 无需达到。
最后的爆炸…… 最后的无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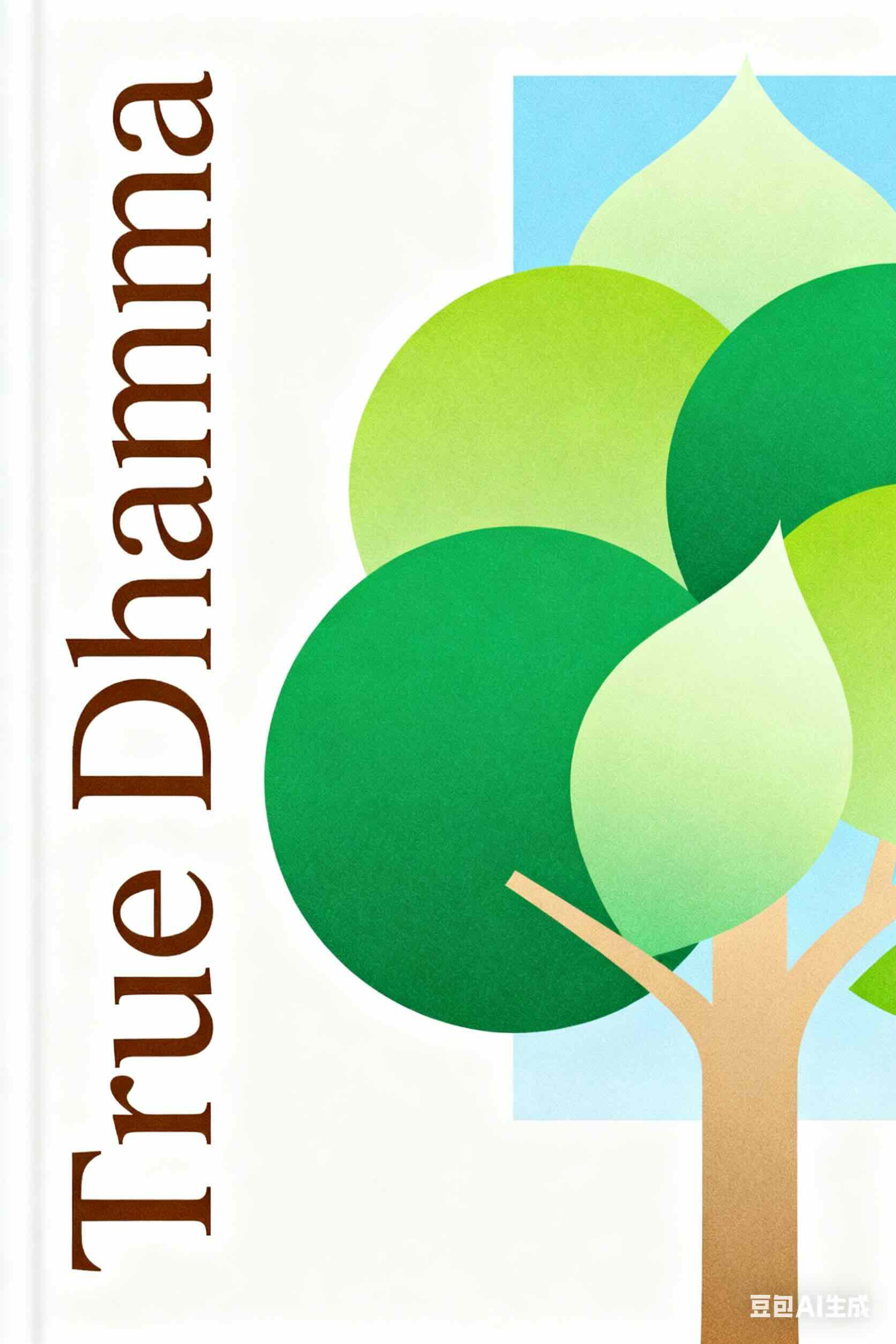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本书并非最终版本成品,是隆塔纳荣萨尊者最新的著作,尚在内部审阅之中,并未提供公开下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