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自心,从苦中解脱
隆塔纳荣萨尊者, 南传上座部佛法 ·Index
训练自心,从苦中解脱 - 隆塔纳荣萨尊者 - 智宁居士译
停止寻觅真理,才能发现真理。因为真理本身,是不挣扎的。
第一次前言
我曾得到多位恩师的指点与教诲,他们之中既有僧侣也有在家居士,但我自己的修行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反复复、时对时错。这是因为我曾尝试过太多不同的方法。然而,我从未气馁,坚持不懈地修行,持续地观察并修正自己内心的烦恼。每当遇到不解之处,我便向具德善知识请教,他们都慈悲地给予指点,直到我的修行渐有成效,依次体验到了不同层次的安乐与自在。
后来,我受邀在司法官员发展学院为助理法官们授课,于是便撰写了这本《训练自心,从苦中解脱》,希望能对法官及广大有兴趣者有所裨益,并以此报答佛、法、僧三宝,以及父母和各位恩师的深恩。我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依次阐述了修炼内心、涤除烦恼的各个次第。书中所写,皆是基于修行过程中内心生起的真实状态。
另外,我并未上过阿毗达摩学院或巴利文高级佛学院,因此,书中一些必须引用的巴利文术语,我是根据内心所呈现的状态来阐释的。如果其中有任何错漏,恳请各位善知识慈悲指正,予以法布施,我将不胜感激。
那荣萨·尼亚玛纳(作者俗家名)
第二次前言
多年前印刷作为法布施的《训练自心,从苦中解脱》已经分发完毕。由于有许多人希望再次印刷此书以作法布施,我便将原书进行了修订与补充,旨在更清晰地阐明心解脱(Cetovimutti / ฉฬภิญโญ)与慧解脱(Paññāvimutti / สุขวิปัสสโก)这两条修行路线,以避免修行者之间产生无谓的争论与冲突。无论选择哪种方法,最终都能证得成果。自佛陀时代以来,阿罗汉中便兼有这两种类型。无论哪种,都必须具备真实不间断的信、精进、忍耐、念、定、慧,才能见到成果。
我所写的,是自己近三十年来精进修行的经验之谈。能有今天的修行成果,全赖于各位恩师的一路指点与教诲。
如果此书尚有些许益处,我愿将此功德回向给所有恩师。本书的完成,亦得益于许多人的热心帮助,从誊写我的手稿、协助校对,到捐资印刷,以作法布施。愿佛、法、僧三宝、道与果、涅槃以及各位所做的一切善业功德,连同各位所有的善心帮助,尤其是为印刷此书所做的布施——此乃超越一切布施之举——能够庇佑各位及家人身心安乐,远离一切苦、忧、病、患与不祥。并愿各位的念、定、慧增长,在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上日益精进,直至最终共证涅槃。
那荣萨·尼亚玛纳
“知”,但不关注
“如果我们关注某件事,那件事就会进入我们心里,我们便会因心中的那件事而苦。 如果我们不关注任何事,心中便无一物,我们也就不会苦。 不要去责怪是外在的什么事物让我们痛苦,因为如果我们不走进去关注它,我们就不会痛苦。”
“知”:指通过眼、耳、鼻、舌、身、意了知。 “关注”:指进入其中去执取、计较、赋予价值、赋予重要性,或生起喜爱、憎恶,或根据自己的喜好与否进行评判。
如果能够“知”而不“关注”,那么任何修行方法都不再需要,这本书也无需再读下去了,因为您已经解脱了痛苦。
“妄想或各种纷飞的念头,好比刚刚在空气中形成的微小水汽。若不从一开始就觉知它,这些水汽就会聚集成为厚重的乌云,随时可能降下雨来。同样,各种纷飞的念头,若不从它微少时就觉知,它就会越发纷乱,情绪也会越积越厚,如同乌云一般,最终化为内心的痛苦,有时甚至会伤心哭泣,就像那降落的雨水。”
“觉知妄想,唤醒心灵,清新、明亮、喜悦。”
减轻痛苦,缓解压力
练习只思惟能让心安乐之事
通常,人的心不习惯安住于自身,总喜欢思惟造作,想到他人他物或其他事情,有时是过去,有时是未来,以致产生痛苦,例如担忧、不安等。而很少会去思惟那些能带来安乐的事情。因此,必须训练自己去思惟那些令人安乐、自在的事情,首先要学会用安乐来代替痛苦。
练习快速切断思惟
当有令人不悦的事情冲击内心时,心便会不清明,感到不安、担忧或痛苦。这时,必须想办法让那份痛苦得以缓解或放下。例如,可以这样想:“随它去吧,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或者想:“算了吧,或许是我以前欠过他。”或者想:“算了吧,就当是布施了。”或者想:“算了吧,东西已经坏了,再想也无益。”或者想:“算了吧,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或者想: “算了吧,他的福报也就这么多了。”或者想:“算了吧,慢慢来解决。”等等。总之,要寻找善巧的思惟或言语方式,让自己感到舒心,这样才不至于长久地陷于痛苦之中。
找点业余爱好来做
通常,人如果无所事事地闲着,就会胡思乱想,各种念头纷飞,往往是自寻烦恼。因此,必须找些自己喜欢的业余爱好来做,例如:运动、饲养宠物(如狗、猫)、养护观赏植物、刺绣等。但这种业余爱好不应是给自己增添痛苦的,例如,收藏昂贵的物品直到倾家荡产。
看看电视或听听歌
看看肥皂剧或喜剧,或者听听歌、唱唱歌,也能极大地缓解紧张情绪。如果只看或只读时事新闻或犯罪新闻,可能会增加或累积更多的压力。
不谈论令人紧张的话题
不要只思惟或谈论他人他事的负面,或一味地指责他人他事,无论是对动物、物品,甚至是天气。这样做会让人不想与你交往,也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紧张、爱抱怨、爱唠叨,且不见减少。同时,也不要过分自责,以至于产生压力或对自己失去信心。
练习成为给予者,而非索取者
练习放下,或练习割舍各种事物,可以从简单的事情开始。例如:将不再使用的东西送给穷人或有需要的人;将不穿的旧衣服捐给比自己贫困的亲友;之后,再练习捐赠给其他穷人;将旧书、不再使用的物品捐给需要的人。这样做会让内心感到快乐。尤其是当看到接受者由衷地欢喜时,我们会感到更大的快乐。
给予或捐赠物品时,必须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否则,当看到接受者不情愿地收下,或随意丢弃我们捐赠的物品时,我们自己反而会感到难过。
作为给予者的快乐,可以回味很久;而作为接受者或索取者的快乐,则很短暂,并且会想要得到更多,欲望不断增长,最终变成一种痛苦。
练习不放纵自己
练习克制自己,从容易做到的事情开始。例如:想吃昂贵的食物,想去旅游,想多收藏某样东西,或想买新的装扮,如衣服、鞋子、香水、饰品等,如果已经足够了,就适当地克制一下。
练习修正自己的习性
自己的习性或习气常常会引来痛苦。例如:脾气暴躁、易怒、性子急、做事快的人,容易感到不顺心、不如意,从而产生压力,经常心情不好。或者,性格敏感、爱记仇的人,会把事情เก็บ在心里,让自己心烦意乱、怨恨不已,有时甚至会发展到怀恨在心或伺机报复。或者,在感官欲望上贪得无厌的人,必须不断地追求,以获得喜爱的色、声、香、味、触或感受,并且喜欢思惟、谈论、聆听或接触那些能激起欲望的事物。
当觉知到自己有怎样的习性时,就必须努力寻找方法、善巧或技巧,来逐渐减轻自己的习性。慢慢地练习,不随心所欲。例如,想思惟、想说、想看、想听、想接触或想做时,就克制住自己的心,不随心所欲地去想、去说、去做。
练习宽恕,不计较
练习宽恕他人,不计较,直至能宽恕身边最亲近的人,如丈夫或妻子。对于身边最亲近的人,反而最难宽恕或不计较。必须从简单的事情开始练习宽恕,不计较。不要把每一件小事都闹大。丈夫或妻子是我们修行进展的绝佳检验工具。也就是说,如果争吵或烦躁的次数越来越少,就表明我们的修行有了很好的进步。
行善积德
训练内心开始向往行善积德,例如:做功德、供养僧侣、听闻佛法、阅读佛法书籍。不断地练习行善,并努力断除恶行,内心会逐渐变得柔和。
开始念经、拜佛、修习禅定,内心就会开始变得宁静与清凉。
守护诸根
要守护好诸根,即:眼、耳、鼻、舌、身、意,以防止内心被欲望、嗔恨、报复或愚痴之火焚烧,而躁动不安、渴求不止。
饮食睡眠要适度
要知道在饮食和睡眠上有所节制。要观察吃什么、吃多少,身体才会轻快,心才会轻快。睡眠也是如此。
当有痛苦或压力时,快速眨眼
如果因为失去正念、无法觉知,放任心随喜好或不喜好而长时间地妄想,从而产生了痛苦或压力;或者虽然觉知到了,却无法将痛苦或压力从心中甩开,那么,就应将目光投向远处,然后快速地眨眼,速度要快过思绪,持续一段时间,直到痛苦或压力爆发消散。然后,要立即起身去做些什么,绝对不要静坐或静躺。
心沉浸于轻安之感时,也必须觉知
有些人在感到轻安舒畅时,便会对此产生喜爱与满足,于是就坐着或躺着沉浸在那份自在安乐中。当喜爱之心生起时,这等同于迷失、执取,也就是关注、赋予价值或重视那份轻安舒畅的感觉。这本身就是一种苦,但它是一种非常微细的苦,只有当它影响到身体时才能察觉到,即会产生昏沉、困倦或轻微的压抑感。此时也应觉知,并活动身体,同时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或快速地眨眼。
当感到昏沉、困倦或压抑时,不要试图将心外放,不要试图驱散昏沉或压抑感,也不要试图忘记那份压抑感。因为这样做等同于在关注或重视那份压抑,这样是无法从作为苦的压抑感中解脱的。就如同被爱人抛弃后,努力想忘记那个爱人,但越努力想忘记,反而越忘不掉,正所谓“想忘偏难忘”。因为努力去忘记,本身就是还在关注、赋予价值或重视。
必须做到不再关注、不再赋予任何重要性。找些事情来做,一会儿自然就忘了。但每当妄想又开始在内心盘旋关注时,就要觉知它,同时活动身体,并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或快速地眨眼。
快速眨眼的方法
- 进行快速眨眼时,不要用在内心观察思绪和情绪,然后试图通过提起觉知来驱赶它们的方式。因为那就像在卧室里掸灰尘,尘埃根本无法离开卧室,痛苦也无法离开内心。正确的方法是:将感觉安放在远处所见的各种事物上,但并不真正地去关注所看的东西,然后快速地眨眼,速度要快过思绪,持续一段时间。
- 快速眨眼必须在放松的状态下持续进行,让身心都感到舒缓。如果在做的过程中有丝毫的紧绷或压力,那么痛苦就会由这份紧绷本身产生,可能会感到头脑迟钝、麻木。
- 快速眨眼适用于以下情况:
- 心对某人、某物或某句话反复思惟、执着不放。
- 心反复思惟造作,执着于自己或自己的事情,以致形成顽固的痛苦或压力。
- 心凝滞于内,开始不想任何事、不想做任何事、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此时必须立刻快速眨眼,同时将感觉投向远处,如树梢、天空的云彩。
- 心沉浸于某种情绪或感觉中。此时也应快速眨眼,将感觉投向远处。
但如果只是普通的妄念纷飞、心不在焉,只要觉知或提起觉照,那些妄念就会熄灭,无需使用快速眨眼的方法。
备注:
- 如果没有那种反复思索、挥之不去的妄想,就不必使用快速眨眼的方法。因为仅仅是觉知,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就足够了。
- 不要为了防止妄想生起而快速眨眼,那样做等同于已经提前在妄想了。
以身体的活动消解心的状态
通常,当内处(眼、耳、鼻、舌、身、意)与外处(色、声、香、味、触、法)没有接触或碰触时,心中不会有任何状态生起。但当它们接触或碰触时,心中就会生起某种状态。为了沟通方便,我们给这些状态起了不同的名字,例如:贪欲、贪婪、嗔恨、报复、恼怒、烦躁、愚痴、掉举、疑惑、愉悦、厌倦、气馁、消沉、不悦、心苦等。
当各种心的状态生起时,如贪、嗔、痴,也就是沉迷于某事,例如掉举、疑惑、犹豫不决、昏沉、厌倦、消沉等,要立刻觉知,同时活动身体或身体的某个部位。例如,立刻起身去做些什么,或跑步,或跳跃,或大笑,或活动手脚,或弹指,或晃动身体,或快速眨眼,并且必须立刻将注意力转移去看或了知别的事物。
转移了注意力之后,就彻底转移,不要再回去观察那个心的状态是否消失了,或者为什么它还不消失。如果总是回头去观察,就会再次陷入那个心的状态之中。
以身体的活动消解妄想
当产生各种会引发“喜爱”或“不喜爱”的妄想时,或沉迷于某事时,或会引起心苦的妄想时,要立刻活动身体或身体的某个部位,或眨眼。
- 引发喜爱的思想:例如,关于淫欲的思惟,或贪婪到内心躁动不安、如火焚心的思惟。
- 引发不喜爱的思想:例如,关于报复、恼怒、嫉妒、诽谤、挑剔他人或自责(导致自己越来越没自信)的思惟。
- 沉迷的思惟:例如,毫无益处的胡思乱想。
以身体的活动来消解妄想,必须同时将感觉从那件事物上立刻移开。如果活动了身体,但心依然沉溺、专注、关注或重视那个引发心之状态的妄想,那么就无法消解那反复生起的妄想。但如果心又回到了那件事物上,就再次活动身体,或快速眨眼。就这样反复做,直到心不再回到那个引发心之状态的事物上为止。
练习拴住内心
通常,人的心总是在各种事物中纷飞不定,少有宁静,总是在渴求地追逐烦恼——即贪、嗔、痴,或说欲贪、嗔恚、愚痴。或者说,心就像猴子,不得安宁,时刻都在躁动摇摆。因此,必须练习将心拴在一个“诱饵”上。可以从佛陀开示的四十种业处中任选其一,例如:出入息、身体三十二分、各种界、各种颜色、佛法僧(可通过念诵,如“Buddho”,或持续念诵忆念佛法僧的经文,或忆念佛像,或忆念脖子上挂的佛牌),或将心拴在行走的脚步上,或拴在正在做的工作上,或拴在来回摆动的手上也可以。此外,也可以用其他事物,但不能拴在会引发烦恼的事物上。例如,女性不应将心拴在男性身上,男性也不应选择将心拴在女性身上。
如果选对了与自己心性相合的事物,就容易将心拴在作为“诱饵”的事物上。我曾让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修行者将心安住在她喜欢的器乐上,效果非常好。做的时候,必须放下一切欲望,放松身心,让自己尽可能地感到舒适。要有一种感觉,仿佛是要让内心在作为“诱饵”的事物上长时间地休憩,不要做得太刻意。并且,不要有任何想得到什么或想成为什么的欲望,即便是想让心宁静的欲望也不要有。否则,会感到压抑、头昏、眼眶痛、眉心痛、后颈痛、肩膀酸痛或呼吸不畅等。
要观察,如果做得正确,心会越来越宁静,身轻心安。内心必须感到通透、空阔、轻安、舒畅。这份宁静不能是通过压抑内心,或强迫心凝住或保持安静而得来的。否则,就会出现上述的身体异常,甚至可能全身发热。
“佛陀”(Buddho)可用于训练定、念、慧
如果精进地让心持续专注于念诵或默念“佛陀”(Buddho)或其他作为“诱饵”的事物,不间断,并且不关注其他任何事物,直到心与“佛陀”或“诱饵”完全融合为一,不再感觉到有一个念诵者和另一个“佛陀”或“诱饵”这二元对立的存在,这称为主修定学,念与慧为辅。因为此时更重视的是觉知,而将重点放在让心只与“诱饵”同在,即训练心与“诱饵”合一,直至达到舍俱行禅(Upekkhā-jhāna)或安止定(Appanā-samādhi)的层次。
但如果只是将“佛陀”或某事物作为“诱饵”,以便观察到心不在“佛陀”或“诱饵”上的时刻——例如,心溜出去偷想、偷念、偷思、偷虑、偷评判、偷诽谤、偷嫉妒某人某事(无论其在场与否),无论是喜爱还是不喜爱,或因失念而无意识地神游,或纠缠于、喜爱或不喜爱自己的身心,或只纠缠于自己的事——然后立刻以正念正知或念慧觉知,并立即提起觉照,这样称为主修念与正知或主修念慧,定是随念而来的果,不强调深入的打坐禅定。
念诵或默念“佛陀”(Buddho)的方法
如果无法做到“纯然的知”、“仅仅是知”或“知而不关注”,那么就应时时刻刻安住于默念“佛陀”(Buddho),这样心就不会去纠缠于外在的任何人或事,也不会纠缠于自己内在的感受、念想和各种情绪,或自己的事情。直到能够做到“纯然的知”、“仅仅是知”或“知而不关注”了,才放下“佛陀”的默念。
每次默念“佛陀”时,要忆念佛、法、圣僧、父母恩、师长恩、道与果、涅槃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业功德。同时,将美好的祝愿无边无际、无量地散播到所有方向,给予我们所有的冤亲债主,以及所有同为在生老病死苦中轮回的众生,不分亲疏爱憎,无论远近。愿他们皆得安乐,远离痛苦,彼此宽恕,不再冤冤相报。如果业报未熟,且彼此又能互相原谅,便能免除各种灾祸。
训练心达到舍倶行禅或安止定的层次
训练方法:在心中持续不断地忆念作为“诱饵”的事物。如果因失念去想别的事而导致所忆念的事物消失了,就要以正念觉知,然后回来继续忆念。就这样持续不断地忆念下去。
(对于闭眼禅坐者:如果出现并非“诱饵”的其他影像(禅相),或听到任何声音,都必须不予关注,不赋予价值或重要性,因为这会让人迷失。例如,曾有一位僧人在禅坐时见到佛陀向他招手,他便起身追去,结果从楼上摔下身亡。)
如果因失念去想别的事,所忆念的事物会再次消失,要有正念觉知,重新忆念它。如此反复进行,直到作为“诱饵”的事物再也不从心中消失,这称为心与“诱饵”合一。
(到此阶段,有些人会感到身体像坠入气穴般突然下沉,同时所忆念的“诱饵”会显现为巨大的影像,这称为“取相”(Uggaha-nimitta),不必惊慌。可以尝试让它变大或变小,如果影像能随心意大小变化,则称为“似相”(Paṭibhāga-nimitta)。)
在此期间,会产生“喜”(Pīti)的情绪,身体会有遍身清凉或毛骨悚然的感觉。“喜”是在身体上感受到的。对此,只需了知身体上的喜受,保持中舍,不惊奇,不予以任何关注。之后,身体上的喜受和心中的影像会逐渐消退,转变为内心的一种安乐、满足的感觉,这称为“乐”(Sukha)。当内心的“乐”受增长圆满时,身体上的“喜”受会完全消失,只剩下内心的“乐”。再之后,内心的“乐”受也会逐渐消退殆尽,只剩下一种宁静的感觉,既无身之“喜”,也无心之“乐”,这称为“舍”(Upekkhā)或“安止定”(Appanā-samādhi)。
当心在“舍”的状态中饱足圆满后,心会自行退定,恢复常态。它无法一直保持在那种状态,因为处于“舍”的心就像在休息,如同睡眠。休息够了,或睡饱了,就必须退出或醒来继续工作。心会自行退出,我们无需刻意去作出退出的感觉。
当心退出恢复常- 态后,要立刻从那份专注中出来,不要留恋地回到“喜、乐、舍”的感受中,因为那样会让你执着于乐(定乐)。之后,应立刻以念慧观察身体的实相。
清洗焚心的烦恼之火
烦恼,即贪、嗔、痴,或说欲贪、嗔恚、愚痴,如同火焰,时刻在焚烧我们的心。当任何一种烦恼生起时,心便会躁动不安,必须挣扎渴求,以求如愿。若不如愿,便是痛苦。因此,必须寻找方法来熄灭心中的烦恼之火,即贪欲之火、嗔恚之火、愚痴之火。
每种火的熄灭方法都不同,就像扑灭不同物质或化学品燃烧的火一样。必须使用与之相对应的水或化学品才能有效灭火,否则火势可能蔓延,造成更大损失。
- 贪欲之火:应通过思惟、观察、审视身体各部分器官的实相,见到其充满不净。如果皮肤上任何地方有孔洞穿透,流出的都是污秽之物。例如:头皮屑从毛孔流出,污垢从毛孔流出,眼屎从眼角流出,耳屎从耳道流出,鼻涕从鼻孔流出,口水唾沫从口中流出,尿液从尿道流出,粪便从肛门流出。这些无一不是恶臭污秽至极,连自己都无法忍受,必须时刻清洗,否则会令他人厌恶。试着七天不洗澡,没人会想靠近,因为恶臭难闻。每次排便时要仔细观察,仔细闻,你会亲身体会到它的污秽与恶臭,无需问任何人。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同样都是腐臭的。活着尚且如此腐臭,如果死后一天、两天、三天……下去,就会开始腐烂发臭,令人无法忍受。要如此反复、持续不断地观察,并以正念正知全程跟随,亲见此实相,不让心失念飘走,直到内心接受此实相为止。“贪欲之火”将会熄灭,几乎不留任何火种再燃。
- 嗔恚之火:必须练习对他人有慈悲心,谦卑柔和,不傲慢。持续不断地思惟慈爱。散播慈心的方法,例如:先对自己散播,想自己希望得到什么,就多想一些,例如:希望得到财富、地位、金钱,希望得到快乐,不被伤害,不被疾病所扰。之后,再想到父母、夫妻、爱子,愿他们得到我们所希望的一切,甚至比我们得到的更多。接着,再想到亲戚朋友,然后是其他人、冤亲债主,以及所有同为在生老病死苦中轮回的众生,无论远近,遍及十方,无边无际,无有穷尽。乃至那些曾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仇人,也愿他们得到一切,比我们想得到的还要多。这样做,心会变得柔和,内心开始宁静清凉,因为“嗔恚之火”、“报复之火”或“嫉妒之火”的燃料会逐渐熄灭。
- 愚痴之火:那些“愚痴之火”旺盛的人,可以观察到他们的特征是:爱胡思乱想,心常飘忽不定,对任何事都忧虑不休。应练习将心拴在某一个“诱饵”上。将心拴住,是为了不让心去思惟造作那些会带来痛苦、不安或忧虑的事情。
当持续不断地做完上述所有练习后,就等同于清洗了内心大部分的污秽或烦恼,内心的痛苦将大大减轻。
身体仅是营养元素的集合
要观察并见到这个实相:身体是由不断摄入和排泄的营养元素构成的,包括肉、奶、蛋、蔬菜、水果、脂肪、蛋白质、矿物质、水、空气、氧气、呼吸的气息,以及燃烧食物产生的热量和从空气中吸收的热量等。它并非一个恒常不变的“我”或“自我”。它必须不断地衰败、耗尽,然后重新摄入或吸收新的元素。因此,不应迷失地执取它为“我”或“我的自我”。
身体仅是各种成分的组合
身体由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骨髓、脾、肺、心、小肠、大肠、新食物、旧食物(此为地界);血、水、脂肪、唾液、汗、尿等(此为水界);呼吸、上行气(打嗝)、下行气(放屁)等(此为风界);体内的热量(此为火界);以及空界组成。因此,不应迷失地执取它为“我”或“我的自我”,或生起一个“我”的实体感。
身体是无常的
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无常”(Anicca),它们必须时刻在坏灭、变化,无法保持恒定,因此是“苦”(Dukkha)。并且它们不受我们的控制,因此是“无我”(Anattā)。它们都循着衰老、生病、死亡的规律不断演变。
必须见到发生在内心的实相,而不是靠想象。修行方法是:忆念覆盖身体的这层皮肤,同时将心导向它腐烂、脱落的认知。必须反复忆念,直到能真实地感受到那种状态。然后会感到只剩下一副骨架立在那里。接着,再忆念这副骨架像旧物般开裂,逐渐腐朽,化为尘土,与大地融为一体。我们的身体本就是靠摄取来自土地的营养物质才长到今天的。即使是吃肉,动物也是靠摄取土地的养分生存的,所以终究是来自尘土,复归尘土。
思惟死亡
要专注地思惟一件事:祖父母、外祖父母、叔伯姑姨、父母、兄弟姐妹、所爱之人,都已相继离世。最终,我们自己也必将在不久后与所有人和所有事物死别。不要以为自己会长命百岁,从不曾想过死亡,或迷失地以为自己会活到老而不死。因为死亡可能在任何时刻突然降临,不可掉以轻心。例如,突发心肌梗塞,或遭遇意外当场死亡,来不及留下任何遗言。
要持续地忆念死亡,通过善巧的思惟方式,直到内心真实地生起一种感觉:我必将与一切死别。在思惟死亡的过程中,初期可能无法持续,因为还不习惯,其他念头会不时地插入。要有正念,提起觉知,切断那些插入的念头,直到只剩下“所有人终将死亡,最后轮到我自己”这一个念头。这是无常、苦、无我的真理,是所有众生生、住、灭的规律,无人能逃脱。
最终,当心中只剩下“我必将与所有人和所有事物死别”这一个持续不断的念头时,心会逐渐接受这个事实:我将像其他人一样死去。就在内心产生这种感觉的一刹那,会生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极其奇妙的感觉。然后,心会获得真正的宁静。到了这个阶段,即使再试图去思惟死亡,心也不愿再想了。任何纷乱的念头都会瞬间熄灭,并且会感到身轻心安,仿佛没有重量,或像身体能漂浮起来一样。
名法生起后即灭去,无有实体
当对色法(即身体)的实相见到再无疑惑之后,接着要见到名法(即感受、记忆、思惟和情绪)的实相。当修行到这个阶段,会感到生起的感受、记忆、思惟和情绪都非常微细或轻微,几乎对内心没有影响。对于这部分微细的心法,只需持续不断地、不间断地、如实地、静静地观察、了知它们的实相:感受、记忆、思惟和情绪,生起后即灭去,生起后即灭去,生起后即灭去……整个过程由正念正知贯穿始终,不让心失念飘走。
应只见到名法的灭去相
之后,应只见到感受、记忆、思惟和情绪的灭去相、灭去相、灭去相……,而不去关注它们的生起相。心便会逐渐放下一切事物。任何躁动,即各种心苦,都会逐渐消退殆尽。心中将只有极致的快乐。
停止或放下,才能放下
如果还不停止妄想、挣扎、寻觅,就还未真正离苦。必须彻底停止寻求解脱的挣扎,才能解脱痛苦。
想要求得解脱的欲望,是件好事。但最终,必须放下那份想要解脱的欲望,或停止渴求解脱。因为寻求解脱的挣扎,本身就是一种导致内心躁动不安的因,它本身就是一种苦,是最后一种苦。当寻求解脱的挣扎熄灭时,苦也随之熄灭。或者说,停止寻觅真理,才能发现真理。因为真理本身,是不挣扎的。
备注(心解脱路线的修行)
以上所述的修行,是心解脱(Cetovimutti)或六通(Chalaññā)路线的完整修法。此方法的要点在于:
- 必须在止禅(Samatha-kammaṭṭhāna)的禅定修行中达到舍俱行禅或安止定的层次,心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见到身与心(识)的实相。
- 在观身的阶段,必须精进地以正念控制心,让心持续不断地观察身体,直到心对身体的实相——即它仅是元素的组合,时刻在衰败、老化、生病、死亡——感到饱足,内心彻底断除对身体的执着。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当心断除了对身体的执着后,它便不再愿意去观察身体的实相,无论你如何强迫心去观察,它都绝不情愿。另一个观察点是:到此阶段,会感到身轻心安,仿佛毫无重量,并一直如此。这样,关于身体的修行才算完成。之后,再观察名法(感受、记忆、思惟和情绪)的实相,见到它们唯有无常、恒常灭去,直到对名法也断除执着。
备注:第一种方法,如果对身体的观察没有中断,那么对名法的观察也不会中断。困难在于观察并见到身体实相的阶段。如果能断除对身体的执着,那么后续观察名法实相的阶段也就不难了。
方法二:慧解脱(Paññāvimutti)或纯观行者(Sukkhavipassako)
胜义法(Paramattha-dhamma)
胜义法:作为真理的法性,即自然的实相。它不是有情、个人、自我、我们、他们。它是没有主人的法性,也没有任何人能改变每种法各自特有的相状。佛陀与阿罗汉们发现了本已存在的胜义法之实相,因此得以成就正等正觉或阿罗汉果位。胜义法包括:心、心所、色、涅槃。
五蕴与胜义法的对比
| 五蕴(Khandha-pañca) | 胜义法(Paramattha-dhamma) | ||
|---|---|---|---|
| 色(Rūpa) | = 色法(Rūpa) | ||
| 受(Vedanā) | |||
| 想(Saññā) | = 心所法(Cetasika) | ||
| 行(Saṅkhāra) | |||
| 识(Viññāṇa) | = 心法(Citta) | ||
| = 涅槃(Nibbāna)(非蕴,是“蕴解脱”,即离苦) |
五蕴、胜义法、内处与外处
| 外处(Bāhirāyatana) | + | 内处(Ajjhattikāyatana) | + | 识(Viññāṇa) | = | 心之了知 | ||
|---|---|---|---|---|---|---|---|---|
| 色尘(Rūpa) | + | 眼根(Cakkhu-pasāda) | + | 眼识(Cakkhu-viññāṇa) | = | 了知色 | ||
| 声尘(Sadda) | + | 耳根(Sota-pasāda) | + | 耳识(Sota-viññāṇa) | = | 了知声 | ||
| 香尘(Gandha) | + | 鼻根(Ghāna-pasāda) | + | 鼻识(Ghāna-viññāṇa) | = | 了知香 | ||
| 味尘(Rasa) | + | 舌根(Jivhā-pasāda) | + | 舌识(Jivhā-viññāṇa) | = | 了知味 | ||
| 触尘(Phoṭṭhabba) | + | 身根(Kāya-pasāda) | + | 身识(Kāya-viññāṇa) | = | 了知触 | ||
| 法尘(Dhammārammaṇa) | + | 意根(Manas) | + | 意识(Mano-viññāṇa) | = | 了知所思之事 |
每一次心或识生起以“了知”或“思惟”时,必然有心所(Cetasika),即受、想、行,与心或识同时生起、同时灭去。
例如,心通过眼根见到色尘的每一次,都会感受到乐(乐受)、苦(苦受)或不苦不乐(舍受或不苦不乐受),这是每一次都必然发生的,不可能没有受。然后会记得那个色尘(想),知道它是什么,或知道是谁,例如是某人的丈夫或妻子,或是某人的父母或子女等。心在每一次的“见”中,完整地造作了知此事的过程,这称为“行”。
这整个“见”的过程,是五蕴的自然常规运作,尚未达到因之而生起烦恼、贪爱或痛苦的妄想造作阶段。
在听声、闻香、尝味、身触或思惟到任何人、事、物的情况下,其运作过程也是如此。
应有的正确理解
- 通过眼根见色,是色尘冲击眼睛之事。但沙子入眼,则是尘埃作为触尘,冲击到身根(身体的神经系统)。
- 心或识了知身体的疼痛、了知身体的紧绷压抑或肩颈酸痛、头痛等,也属于触尘,即有某物冲击到身根。例如:热、冷、软、硬、紧绷,或身体内的活动,如上行气、下行气(放屁)或心跳等。然后心或识来认知那个冲击到身根的触尘。如果在身体的那个区域,没有任何东西冲击到神经,心或识就不会生起来了知那份身体的疼痛。例如,医生或牙医在做手术或钻牙时,必须在那个部位的神经上注射麻药,这样在手术或钻牙时,就不会感到疼痛或牙酸。
- 了知触尘或身触,也和通过眼根了知色尘一样:必然会有受,即了知后感到乐,或了知后感到苦,或了知后是舍受(不苦不乐)。不可能禁止“受”的发生。并且会记得所触之物(想),知道是什么(行)。至此为止,是五蕴的自然常规运作,不会有产生痛苦的因,即还没有作为烦恼、贪爱或痛苦的妄想。
- 法尘接触意门,即心想到某人、某物或某事时,那个被想的人、物或事是外处,而思惟本身是心。
- 当心想到某人、某物或某事时,也必然会生起心所,即受、想、行等,每一次都伴随思惟而来,就像了知色、声、香、味、触一样。不可能禁止乐受、苦受或舍受的发生。例如,想去见一个熟悉的人,就会伴随着乐受;如果正在思考当前一项困难的工作,就会感到是苦受;如果只是在正常地规划工作,或想站起来去拿个东西,就会是舍受,即不感到乐也不感到苦。
以上这些情况,称为五蕴的正常思惟,是自然的常规。但如果根据想要或不想要而进行妄想造作,这就成了带有烦恼和贪爱或痛苦的妄想,而非正常的思惟。
色、心、心所、涅槃
-
“色”(Rūpa):指被了知之物,包括色、声、香、味、触(冲击身根之物)和法尘(心所想到的事物或事情)。色、声、香、味、触和法尘本身无法了知自己,必须依靠心才能被了知。
- 自己的身体也是色,它无法自己了知自己,必须依靠心来了知。当低头看自己时,身体是冲击眼睛的色尘,心便通过眼根了知身体。但如果感知到身体的疼痛或沙子入眼,则是触尘,即有某物冲击到身根的神经系统,心是通过身根的神经系统了知的。
- “心”(Citta):其状态是“知”与“想”。它是一种“名法”(nāma),无实体、无形状、无住处、无边界,生灭极快。心每一次生起,都必须“了知”被了知之物,即色、声、香、味、触和法尘。心不可能凭空生起了知而无被了知之物,也不可能只有“能知者”而无“所知之物”。
-
“心所”(Cetasika):指与心同时生起、同时灭去之物。例如:受(乐受、苦受、舍受或不苦不乐受)、想、行等。心所无法自行生起,必须依心而生。
- 必须清楚地理解:心所不是心,不要错把心所当成心。例如:
- “心安乐”:安乐是乐受,它与“了知”某物的心同时生起。因此,“安乐”本身不是心。
- “苦受”(Dukkhavedanā)是心所,与“能知”之心或“思惟”之心同时生起、同时灭去。而“心苦”(或因执着而苦),则不与“能知”或“思惟”的心同时生灭。即使“能知”或“思惟”的心已经灭去,那份“心苦”(或因执着而苦)仍未熄灭。因此,心苦不是苦受,苦受也不是心苦。佛陀与阿罗汉们没有心苦,但有苦受。
- “舍受”(Upekkhāvedanā):指不苦不乐的感觉,是心所,与“能知”或“思惟”的心同时生起、同时灭去。而那种持续保持的“空空”的感觉或“不苦不乐”的感觉,是一种由执着心所产生的“放下”之感,即努力让自己保持“放下”或“不苦不乐”的状态,因此它不与心同时生灭,也不是涅槃。因为涅槃不执取任何事物,包括那种“放下”的感觉或“不苦不乐”的感觉。
-
“涅槃”(Nibbāna):不是蕴。涅槃是蕴解脱(khandhavimutti),即从苦中解脱。涅槃是无为法(asaṅkhata-dhamma),即没有因缘造作使其生起,因此不生不灭。而色、心、心所是五蕴,是有为法(saṅkhata-dhamma),即有因缘造作使其生起,当因缘灭尽时,它们也会灭去。因此,色、心、心所是行法(saṅkhāra-dhamma),即时刻在生灭,或生起后必将灭去,无法随心所欲地执取让其恒常存在,不受我们控制,因此不是我,不是我的。不要迷失地执取它们为“我”、“我的”或“我的自我”。当彻底断除了对色、心、心所的执取,并且亦不执取涅槃时,才能证见涅槃,那是非行法(visaṅkhāra-dhamma),即不生不灭。
- 如果执取“色”或被了知之物(色、声、香、味、触、法尘),包括自己的身体,认为它是“我”、“我的”或“我的自我”,就无法证见涅槃。
- 如果执取心所(受、想、行),认为它是“我”、“我的”或“我的自我”,也同样无法证见涅槃。
- 如果执取心(能知者或能思者),认为它是“我的心”、“我就是能知者”或“我就是能思者”,也同样无法证见涅槃。
- 并且,“纯然的能知”(รู้เปล่า ๆ)也不是涅槃,因为它仅是未造作去执取任何事物的心,是五蕴中“识”的正常运作。如果执取这个“纯然的能知”为涅槃,那就仍是迷失地把“心(能知)”当作涅槃,就会努力地去保持“纯然的知”,这叫作执取能知或执取心为涅槃。只有当既能“纯然了知”,又没有执取者时,才是涅槃。
佛陀将心、心所、色与涅槃分离开来。因此,涅槃不是“心(能知)”。涅槃超越了能知或能思,以至无所标示。如果标示说“涅槃”必须是这样、必须是那样,那就还有一个“我”或“自我”的执取者存在。
当不执取“能知”,亦不执取涅槃时,才能证见涅槃,即苦的熄灭或从苦中解脱。
慧解脱(Paññāvimutti)或纯观行者(Sukkhavipassako)的修行
修行此法门者,不需闭眼禅坐,也不需观身至见其腐烂败坏。但必须内心从一切躁动中得以宁静,并有智慧能够观察到,在每一个“知”或“想”的心识刹那中,纯净的心掺杂了些什么。例如:
- 如果纯净的心中掺杂了心苦、压力或不安,必须先将它清除。方法是觉知它,同时活动身体或将注意力立刻转移到其他事物上,例如去找些轻松的事情做,或看喜剧,或唱歌,或听歌等。或者用这个方法:望向远处的树梢或天上的云,然后快速眨眼,速度要快过思绪,持续一段时间,直到痛苦和压力爆发消散。(注:当有痛苦或压力时,严禁静止不动或禅坐,因为那会导致压抑,然后可能会将情绪爆发在他人身上。)
- 如果纯净的心中掺杂了贪欲、贪婪、嗔恨、烦躁、掉举、疑惑、昏沉等,即所谓的“五盖”或烦恼,也必须将其清除。方法是觉知它,同时活动身体或将注意力立刻转移到其他事物上。
- 心中有贪爱(Taṇhā),即渴求、挣扎的妄想。例如:想要得到、想要占有,或希望变成那样、希望变成这样。或是排斥、挣扎的妄想,因为不想要。例如:不想说话、不想见面,或不希望他比我好,或不希望是那样、不希望是这样。这些都掺杂在纯净的心中,必须将其清除。方法是觉知它,同时活动身体或将注意力立刻转移到其他事物上。
- 当清除了第1至3点所述的烦恼、贪爱和痛苦之后,“色”(被了知之物,包括色、声、香、味、触、法尘)便不会对心产生任何影响,或者说心上再无任何压迫。此时,心会生起受(vedanā),即先产生喜(pīti)的情绪,身体上会有反应,如遍身清凉,类似汗毛竖起。然后那份“喜”会逐渐消退,转变为乐(sukha),即内心充满喜悦和满足。接着,内心的喜悦和满足也会逐渐消退,转变为身体和内心都宁静的状态,这称为“舍”(upekkhā)或不苦不乐受(adukkhamasukhavedanā)。然后,要从对内心“受”的觉知中撤出注意力,这便等同于已将受与心(能知)分离开来。
- 接下来,只剩下“心(能知)”。要见到心或能知者无实体、无形状、无住处、无边界。不执取“能知者”为“我”或“我的”。与此同时,也不执取涅槃,即停止寻觅涅槃的妄想挣扎,便能从苦中解脱。解脱之后的状态如下:“知”,但不关注;或“纯然的知”;或“仅仅是知”,而无“能知者”的实体感,直至死亡。
妄想(思想的造作)
“妄想”是指思想中掺杂了烦恼、贪爱或痛苦。例如:
- 暗中思惟、暗中忆念、暗中审度、暗中评判、暗中指责、暗中嫉妒、暗中诽谤在面前的某人或某物。无论是面前的色、声、香、味、触,如果喜爱,就会生起贪欲或贪婪;如果不喜爱,就会生起嗔恨、报复、烦躁、恼怒、心结、不宽恕的情绪。或者,即使未达到贪欲或嗔恨的程度,而是愚痴(即迷失),例如,无意识地沉迷于胡思乱想。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当与一群人说笑时,谈论的话题过后,内心还在继续回味;或者看电影、戏剧,结束后心却不结束,还在继续思惟或谈论,沉浸其中,这是无意识的沉迷。
- 正在工作、读书或与某人交谈时,心却妄想纷飞,或沉迷地飘向了不在面前的他人他事。
- 心妄想着那些会引起心苦、不安、担忧或焦虑等的事情。
以上第1、2、3点,称为向外妄想。
- 妄想着纠缠于自己的事或自己的内心,或纠缠于自己身体的状况或心的状态,或妄想着对五蕴(色、受、想、行、识)产生喜爱或不喜爱。如果喜爱,便妄想希望变成那样、希望变成这样,这称为“有爱”(Bhavataṇhā)。如果不喜爱,便妄想挣扎、排斥,希望它消失,或产生“不想要”之感,这称为“无有爱”(Vibhavataṇhā)。
这第4点,称为执取五蕴的妄想,或向内造作,或妄想着向外执取自己。
- 压抑心或努力强迫心不妄想,或在内心时刻观察、防备,以防止心去妄想执取任何事物,这也称为向内妄想或执取五蕴。这是一种“不希望心妄想”的欲望,本身就是一种贪爱。
无明是产生“漏”与“随眠”的缘
每当妄想生起时,若没有念慧去觉知它,这称为“无明”(Avijjā),即不知苦(由妄想产生的苦)、不知集(妄想本身)、不知灭(无法熄灭苦)、不知道(不知如何觉知妄- 想)。心便会妄想挣扎,渴求地去执取内外的人或事,直到成为习性,演变为越来越强的惯性,最终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气,这称为烦恼的浸染(“漏”,Āsava)或潜在的烦恼(“随眠”,Anusaya)。
“漏”与“随眠”是产生无明的缘
如果“漏”与“随眠”,即惯性习气,力量强大,即使觉知到了,并活动身体、转移注意力,也无法将心从内外所执取的事物中拔出。或者,每当妄想生起时,有正念觉知,却没有智慧能从那妄想所产生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或者觉知到了,却败给了自己的心,于是便随顺着那引发烦恼、贪爱和痛苦的妄想去思、去说、去做,这也称为“无明”。
有正念觉知却败给自己的心,是因为长期放任自己随顺烦恼、贪爱或随心所欲地妄想,以至于已成为习性、习气或惯性(“漏”、“随眠”)。
无明是产生“行”的缘
无明是产生“行”(Saṅkhāra)的缘。“行”在此处指在母胎中形成生命,也指心行(思惟)、语行(言语)和身行(行为)。
“行”是产生“识”乃至“受”的缘
因为“行”是缘,所以产生“识”(Viññāṇa)。当有色、声、香、味、触(冲击身根之物)和法尘(心所思之事)来冲击眼、耳、鼻、舌、身、意时,识便会生起来了知那个冲击之物,然后灭去。并且每一次都会产生受,即乐受、苦受或舍受。
“受”是产生“爱”与“取”(执着)的缘
- 乐受与舍受,会成为产生妄想的缘,发展为想要得到、想要占有的“欲爱”(Kāmataṇhā),或希望变成那样、希望变成这样的“有爱”(Bhavataṇhā)。
- 苦受,则会成为产生妄想的缘,发展为不想要,即挣扎排斥的“无有爱”(Vibhavataṇhā)。
因此,如果从“受”的基础上继续妄想下去,就会变成烦恼、贪爱和取(执取为“我”或“我的”),然后产生苦。如果放任其频繁发生,直到成为惯性习气,即所谓的“漏”或“随眠”,那么即使有念慧觉知,也会败给自己的心。
因此,必须具备“念”,觉知那份妄想,同时具备“慧”,从那件事物中撤出喜爱或不喜爱。然后,那份因乐受或舍受而产生的、想要得到、想要占有或希望变成那样、希望变成这样的内心躁动,或是那份因苦受而产生的不想要、挣扎排斥的内心躁动,便会熄灭。心便会回归“常态”。这份“常态”之心,称为有“戒”和有“定”(即从任何内心躁动中得以宁静)。心能有戒有定,是源于有“念”觉知了那份会产生烦恼、贪爱或痛苦的妄想。但如果有了正念觉知妄想,还必须有“慧”能从烦恼、贪爱或痛苦中解脱出来,否则无法离苦。
或者,如果内心只有躁动,没有宁静,因为缺乏“定”,包括急于证见涅槃的躁动,那么无论如何以“念”去觉知,也无法熄灭那份躁动,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慧”来熄灭内心躁动的人。
“漏”、“随眠”与“无明”是产生“爱”与“取”的缘
“漏”、“随眠”是产生“无明”的缘;“无明”是产生“行”的缘;“行”是产生“识”乃至“受”的缘;“受”是产生“爱”的缘;“爱”是产生“取”(迷失地执取为“我”或“我的”)的缘;“取”是产生“苦”的缘。因此,可以说,因为有“漏”、“随眠”和“无明”作为缘,才产生了“爱”、“取”和“苦”。
所以,必须精进地以“念”和“慧”觉知那份从“受”延续而出的妄想,同时活动身体,并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以削弱那份执取内外人或事的惯性或习气(“漏”、“随眠”)。这需要忍耐(Khanti)的帮助,即克制、忍住,否则很容易败给自己的心。
当惯性或习气因为强大的念慧觉知而力量减弱后,之后再有妄想生起时,只需一觉知,妄想便轻易熄灭,无需再用活动身体、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并且,它来不及发展为内心躁动的烦恼、贪爱和取。
念、定、慧因此是时刻互相支持的,缺一不可。若念缺,定则缺,慧也缺;若念具足,定则具足,慧也具足。或若定缺,念则缺,慧也缺;或若慧缺,念则缺,定也缺,无法离苦。因此,必须训练自己时刻以“念”和“慧”觉知那产生烦恼、贪爱、取和苦的妄想,直到成就大念(Mahā-sati),即自动化的觉知。若念成为大念,便会成为大定(Mahā-samādhi)和大慧(Mahā-paññā),即能够撤出喜爱或不喜爱,并能熄灭产生烦恼、贪爱的妄想。当“爱”熄灭时,“苦”也随之熄灭,因为“爱”是产生“苦”的缘。
要熄灭妄想,必须知道在想什么
心的自然功能是“知”和“想”。因此,心总是在思惟,不可能完全禁止它思惟。但如果放任心去想那些会产生痛苦的事,就会产生痛苦;如果想那些会产生贪欲的事,就会产生贪欲的情绪;如果想那些会产生嗔恨、报复、烦躁、焦虑的事,就会产生嗔恨、报复、烦躁、焦虑的情绪;如果想那些会产生厌倦、无聊的事,就会产生厌倦、无聊的情绪;如果无意识地想那些令人愉悦沉迷的事,就会迷失沉迷。以上所有这些思惟,都称为“妄想”,即思惟中掺杂了烦恼、贪爱或痛苦。
还有一种思惟,是关于工作的思惟,或关于生活中正常事务的思惟,例如计划或想去做某事等,这称为“正常的思惟”。要观察,自然的正常思惟,不会掺杂烦恼、贪爱或痛苦。
因此,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只思惟正常的事,不妄想那些会产生烦恼、贪爱或痛苦的事,就不会痛苦,或从痛苦中空出来。但不要错误地理解为“不思惟”才不会有苦。阿罗汉和佛陀也必须思惟,例如,想要做什么,想要如何教导某人等。但他们不会妄想那些会产生痛苦或烦恼(如贪欲、贪婪、嗔恨、报复或愚痴)的事。
要熄灭妄想,只留下正常的思惟,必须精进地以正念觉知自己当下正在想什么,无论是正常的思惟还是妄想,并且不能迷失地随之产生情绪共鸣。如果迷失地产生了情绪共鸣,也要觉知并提起觉照,同时从那件事物中撤出喜爱或不喜爱。
如果不迷失地随妄想所执取的事物产生情绪共鸣,就能了知、见到或理解哪种是正常的思惟,哪种是妄想。
但如果已迷失地对妄想之事产生了贪欲、贪婪、嗔恨、报复或愚痴(迷失)的情绪,以至内心躁动不安、渴求不止——例如,因为喜爱而想要得到、想要占有,或希望变成那样、希望变成这样;或因为不喜爱而不希望是那样、不希望是这样,或挣扎排斥(这些都是“爱”)——那就没有念慧去理解哪种是正常的思惟、哪种是妄想了。除非先用觉知、提起觉照的方法,同时转移注意力到其他事物上,从那件事物中将心撤出。
但如果未达到内心躁动、渴求不止的程度,那么只需精进地以正念纯然地了知实相,即它是哪种类型的思惟:是正常的思惟,还是妄想。然后智慧会自行生起,洞察到:正常的思惟可以任其继续;而妄想,只需被觉知,它便会自行消失。
通过如此这般地持续不断、不间断地精进修持念慧——不是时而了知、时而不知,或时而见到、时而不见(这称为失念者)——当念缺失时,定(心的宁静)也会缺失,便会随烦恼而内心躁动,慧也随之缺失。但当念持续不断地了知思惟的实相,包括正常的思惟和妄想,这称为大念,它也将成为大定和大慧。凭借大念、大定、大慧的力量,所有妄想将不再有任何力量影响内心,使其产生作为内心躁动、渴求的“爱”,或说“爱”熄灭了。而“爱”是“集”,是产生苦的因。因此,当“爱”熄灭时,“苦”便熄灭。
备注(关于思想)
-
如果没有任何思惟生起,表明你已将心压抑至不自然的状态。因为心的本性就是思惟。
- 纠正方法:如果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思惟,心静止不动,必须立刻想点什么。想什么都可以,但必须觉知它是正常的思惟还是妄想。
- 不是练习“熄灭”思惟,而是练习“了知”思惟,了知它是正常的思惟还是妄想。
- 如果“盯着”要看思惟,心会被压抑住,不去思惟,也就见不到或了知不到思惟。
- 不是在内心“时刻防备”,以防止心妄想。那是在压抑心。
微小的苦变成巨大的苦
通常,我们整天都在各种妄想中纷飞。问题在于,当每一次妄想纷飞时,我们是否觉知到了?如果我们没有觉知,就称为“迷失”(愚痴)。如果我们不从一开始就觉知那份妄想或纷飞的念头,那份妄想或纷飞的念头就会变得越来越纷乱。微少的妄想是微少的愚痴烦恼,当妄想多了,就成了巨大的愚痴烦恼。
正是这份纷飞的念头,会把我们引向贪婪或贪欲的烦恼,以及嗔恨或报复的烦恼,包括烦躁不安。这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失去正念,没有觉知,放任心念纷飞。最终,那些念头会转向那些能引发喜爱(即贪婪或贪欲)或不喜爱(即嗔恨、报复或烦躁不安)的人、事、物,成为随烦恼而来的渴求与挣扎。当不如意时,便成了心苦、伤心、不安、怨恨或焦虑等。
妄想或各种纷飞的念头,好比刚刚在空气中形成的微小水汽。若不从一开始就觉知它,这些水汽就会聚集成为厚重的乌云,随时可能降下雨来。同样,各种纷飞的念头,若不从它微少时就觉知,它就会越发纷乱,情绪也会越积越厚,如同乌云一般,最终化为内心的痛苦,有时甚至会伤心哭泣,就像那降落的雨水。
因此,必须时刻觉知妄想或纷飞的念头。即使是关于自己身心的念头,例如关于感受、思惟和各种情绪,是空还是不空,是轻安还是不轻安,甚至是在那里妄想怀疑“我是否在妄想呢?”或“我没有在妄想”,这也叫作“纷飞”。或沉浸于法义中,以致产生压力,或在法义中纷飞以致心无宁日,也叫作“纷飞”。
但如果将读到或听到的法义,或发生在内心的状态,拿来分析研究以求理解,这样不叫妄想或纷飞,而叫“择法”(Dhamma-vicaya)。
需注意: 我们无法立刻禁止所有纷飞的念头,就像我们无法禁止空气中产生水汽一样。我们只是在每个当下,以正念觉知那份纷飞的念头。微少的纷飞念头便会熄灭,无法演变成会产生痛苦的巨大纷乱。空气中的水汽也是同理,虽然无法禁止其产生,但若在每个当下觉知,不让水汽聚集,它就不会变成会降下雨来的乌云。
但如果刻意防备,不让任何妄想或纷飞的念头产生,就会变成压抑自己的心,导致身心出现异常,例如头昏、头痛、肩颈酸痛、胸闷或身体时冷时热等。
常见的错误
即使时刻觉知妄想,但如果理解有误,也无法离苦。
导致错误或误解的,就是试图让心保持中舍、空寂、凝滞,或试图维持那份空。这将是陷入执取,即喜爱那份空。如果你关注空,或关注于让心变空,那恰恰是心未从苦中空出来。
关注任何事物、赋予任何事物价值或重要性、计较任何事物,都表明了迷失与执取。因为如果我们关注、赋予价值、重视或计较某事物,那事物就会进入我们心里,我们便会因心中的那件事而苦。如果我们不执取、不关注、不赋予价值或重要性、不计较任何事物,心中便无一物,我们也就不会苦。
错误的理解导致无法离苦
有以下这些错误的理解:
- 误以为必须“不思惟”才不会痛苦。 实际上,正常的思惟并非产生痛苦的因。
-
试图“熄灭”妄想。 这是错误的修行,因为它是在压抑心,并且会给身心带来许多后遗症。
- 正确的做法是:持续观察,看哪种是正常的思惟,哪种是妄想。如果心不去妄想,那是它自身的正常状态。如果心要妄想,那是它惯性或习气的正常表现。我们的责任只是持续地觉知,同时撤出对那件事物的喜爱、不喜爱或沉迷。
- 不理解通过眼、耳、鼻、舌、身或思惟所产生的了知,每一次都必然伴随着“受”:包括乐受(感到快乐)、苦受(感到痛苦)或舍受(感到不苦不乐)。这是自然的常规,是五蕴的正常运作。不可能在通过眼、耳、鼻、舌、身和意了知时,不伴随“受”。也不可能只选择乐受,而不要苦受。如果喜爱乐受、憎恶苦受,将永远无法离苦。
- 误以为在通过眼、耳、鼻、舌、身或意了知任何事物时,所产生的不苦不乐之感(即舍受),就是“放下”或“涅槃”,或错把“舍受”当作涅槃。当有了这样的误解,修行便会出错。无论如何精进忍耐,都无法离苦。因为当眼、耳、鼻、舌、身接触到色、声、香、味、触,或想到任何事物时,他会努力让心只保持“舍受”,即不苦不乐的感觉,而见不到这个实相:舍受、乐受和苦受,是时刻伴随“能知”之心或“思惟”之心生起,然后与那个“能知”或“思惟”之心同时灭去之物。它们无法被执取,是无常(不恒常)、苦(无法维持原状)、无我(不受我们控制)。不可能只选择舍受或乐受。即使喜欢舍受或乐受,也无法强迫它们恒常存在,它们必然会灭去、变化,时而是舍受,时而是乐受,时而是苦受。并且,受不是心,也不是涅槃,它仅是心所。佛陀已将其划分为心、心所、色、涅槃。因此,所有的“受”,无论是舍受、乐受还是苦受,都必须不予关注、不赋予价值、不赋予重要性、不迷失执取,才能证见涅槃。
-
误以为“苦受”与因妄想执取而生的“心苦”是同一回事。
- 苦受是五蕴之一,与生俱来。它与心了知眼、耳、鼻、舌、身或思惟任何事情时同时生起,然后与那个“能知”或“思惟”之心同时灭去。它是苦谛,是自然的苦。佛陀与阿罗汉也必须承受这种苦受。例如,佛陀碰到什么东西,也会像凡夫一样感到痛;当没有饮食时,也必须感到饥饿,因为胃液(一种身体的触尘)分泌出来,冲击到身根(胃壁神经),心或识便生起来了知胃液与胃壁神经的接触,然后生起身体的苦受。但佛陀与阿罗汉没有心苦。
- 心苦不是五蕴,它源于妄想执取某事某人,才会产生心苦。因此,心苦只存在于凡夫。佛陀与阿罗汉已断尽妄想执取,故不再有心苦。
如果误以为“苦受”是因妄想而生的苦,就会时刻妄想、挣扎、排斥“苦受”,希望“苦受”熄灭,或想尽一切办法要熄灭“苦受”。而不理解,“苦受”是五蕴之一,不可能彻底熄灭,除非死亡。但如果死时心中仍有妄想执取,那么“心苦”不会熄灭,只会熄灭“苦受”。由此可见,苦受不是心苦。
-
身体内部的压抑感,源于将心专注于自己身体内部。当心专注时,会产生能量或心力,去压迫身根(神经系统)。这股心力也是一种冲击身体的触尘。心会生起来了知这种触碰。当心生起了知触碰时,就会伴随着苦受,即感到痛苦,例如肩颈酸痛。如果心力触碰在头部,就会头痛;如果触碰在腹部,就会腹胀;如果触碰在胸口,就会胸闷。
- 但如果心妄想、挣扎、排斥那份“苦受”,就会随之产生心苦。但如果了知那仅是“苦受”,而不产生任何想要它消失的妄想挣扎,就不会有心苦,只会有苦受。并且,当不再将心专注在身体或自己内部时,心力就不会去压迫或冲击神经系统,由专注而生的“苦受”也就不再生起。
有时,不仅是心力在触碰或冲击神经系统,自然界或宇宙的能量也可能压迫到神经系统,心也会生起来在神经系统上认知,同样伴随着苦受。如果不理解这是“苦受”,而误以为是“苦”,就会试图挣扎、排斥那份“苦受”,导致心苦随之而来。
当心苦与苦受混杂在一起时,会导致苦受加剧,因为那份挣扎排斥的心会增加能量去压迫神经系统。当苦受加剧时,就会更加挣扎排斥,导致“苦”(心苦)加剧。当心苦加剧时,就会更加挣扎排斥,就会增加心力去压迫神经系统,导致苦受更加剧。这就像蛇吞自己的尾巴,永无止境,无法找到出离那份痛苦的道路。
当正确地、如实地理解了上述道理后,便能从那份迷失的执取中将心撤出,即撤出那份不喜爱,因为见到那并非离苦之道。并且见到,“苦受”仅是心所,不是心,不是色,也不是涅槃。因此,如果心还纠缠于“苦受”——它仅是一个心所——就无法证见涅槃。
- 误以为当心了知眼、耳、鼻、舌、身之事或思惟某事时,必须让心保持“凝滞不动”才是对的,即在内心有一个凝滞不动的“我”或“心”作为另一个实体存在。这又称为“心动而意不动”或“心动而意安住”。如果是这样,必须在每一次有这个凝滞不动的心叠加出现时,觉知它。我曾见过一些修行者,在看喜剧节目时,别人都在正常地笑,而他却不笑,瞪着眼睛看,内心一直保持着紧张。然后说他正在练习“仅仅是看,不让心参与进去”。这是极大的误解。因为这样做,等同于心已经在妄想执取了,内心深处有一种恐惧或“不想要”,即不希望心去妄想。
巨大的无明
试图让心宁静、凝滞,或试图让心空寂、中舍、不动,无论达到多么宁静的程度,都仍是迷失地安住于禅那的境界中,那份宁静、通透、空阔、轻安会依次越来越深。当轻安达到非常微细的程度时,其他的情绪和妄想几乎不再显现,或说,极其微少的情绪和妄想几乎在感觉中不存在了。感到心持续地清明自在,或感到心持续地空寂、轻安、舒畅。以致于大部分修行者都迷失在这种状态中,试图不断地打磨心、粉碎心,让它越来越微细,或让心越来越空于妄想和情绪,直到感觉自己是活在一种没有思惟、没有任何情绪的状态中。然后便以为修行已到终点,或接近终点。
这样,便是一种巨大的无明,即迷失地进入了无色界禅。或者说,这就像在卧室里掸灰尘,灰尘无处可去。也就是说,烦恼和痛苦无处可去,只是在心中盘旋而已。这样,将永远无法离苦。因为痛苦被粉碎,与心融为一体,包括那份渴求挣扎的、作为生苦之因的“爱”,也被粉碎,与心融为一体,以致无法将它们从心中分离出来。
总结来说,无论是作为生苦之因的渴求挣扎的妄想,还是痛苦本身,都被粉碎在心中,直到感觉它们丝毫都不再显现。但实际上,生苦之因和痛苦并未从心中消失,它们只是被压抑住了而已。这是一种错误的修行。
妄想发展为“爱”与“取”,将会产生“自我”
每一次妄想生起时,如果仅是喜爱或不喜爱,或沉迷愉悦,然后立刻觉知,尚未达到“爱”与“取”的程度——即尚未产生一个“我”或“自我”的执取,去渴求、占有,或希望变成那样、希望变成这样,或挣扎排斥,因不想要而不占有、不希望变成那样、不希望变成这样——那么,就不会生起一个与肉身(五蕴)重叠的、形如我们自身的透明光身之心或识。
但如果妄想发展到成为“爱”与“取”,却没有念慧去觉知,或者觉知了却无法将心从所执取的事物中撤出——无论是外在的色、声、香、味、触,还是内在的色、受、想、行、识(即自己的五蕴、自己的事或关于自己内心之事)——那么,就会生起一个作为“自我”的心或识,其形如我们自身,是一个透明光身,与自然的肉身(五蕴)重叠,成为另一个实体。然后它会去附着在内外所迷失执取的事物上。
例如,当与英俊的男子或美丽的女子交谈时,心暗中妄想,希望与面前之人发生性关系,那么就会生起一个作为“自我”的心或识,是一个形如我们自身的透明光身,去与那人亲近纠缠。
或者,如果执取自己的五蕴,那么就会有一个透明光身与自己的肉身(五蕴)重叠。例如,当我们看电视时,心却在妄想、挣扎、排斥,希望某种身体或心的状态消失,因为不喜欢它;或者暗中希望那份安乐的感觉能持续存在,然后心便沉浸、执着于那份感觉。此时,就会生起另一个作为透明光身的心或识,在向内看着自己,而肉身则在看电视。有高深天眼通的人能够观察到这一点。
因此,必须觉知,同时撤出喜爱或不喜爱,或撤出对内外任何事物的迷失、执取、沉迷。那个透明光身,或作为“自我”的心或识,每一次都会熄灭,回归到单一的身心(五蕴)。当再次迷失执取时,那个形如我们自身的透明光身又会生起。但当觉知并撤出喜爱、不喜爱或迷失执取时,那个作为“自我”的透明光身或心识便会熄灭,只剩下单一的身心(自然的五蕴)。如此反复。
因此,当妄想生起,成为一个“我”或“自我”,去执取内外的人或事,以至产生“爱”(即渴求挣扎,想要得到、占有,希望变成那样、希望变成这样,因为喜爱;或因不喜爱而挣扎排斥)时,就会立刻生起一个作为“自我”的心或识,是一个形如我们自身的透明光身,去附着在所执取的事物上,无需等到死后。
不在“能知”之上叠加思惟
当通过眼、耳、鼻、舌、身了知任何事物时,不应在那份“了知”之上再叠加妄想,并且没有一个“我”或“自我”去纠缠于那个“能知”。了知了什么,就让它自行结束,或随其自然灭去。这是一种单一层次的了知,或只有一个了知,或仅仅是知,或纯然的知,没有在“能知”之上叠加任何评判思惟。
例如:通过眼睛了知了某个色尘,然后叠加评判说:“不要对这个色尘起妄想啊。”或者,了知了什么,然后叠加评判说:“我真厉害,见到色尘居然不起任何妄想。”或者,了知了什么,然后叠加评判说:“我真没用啊。”或者,了知了身体内部神经的触碰,例如肚子痛,然后就妄想说:“我会不会死啊?”等等。这些都称为“在能知之上叠加思惟”。
或者,当见到一个色尘后,暗中忆念、思惟、审度、评判,对其产生喜爱或不喜爱,而没有去关注正在交谈的事情,这也称为“在能知之上叠加思惟”。
每当“在能知之上叠加思惟”时,就要觉知它,让其只剩下单一层次的“知”(了知色、声、香、味、触、法尘),或只了知被了知之物,或只有纯净的五蕴在运作,不在那个“了知”之上叠加第二层评判或妄想。这称为“仅仅是知”或“纯然的知”。
不在“知”之上叠加“知”
即是说,当心通过眼、耳、鼻、舌、身和意了知了什么,就让它停留在单一层次的了知,不再进入内心去叠加一个第二层次的“知”。
例如,看见某人,或正与某人交谈,然后心妄想,时刻在内心去“知”自己的心是怎样的状态:是安乐还是不安乐?我现在是在妄想还是没有妄想?我宁静吗?我有定力吗?我有正念吗?这种情况,称为“双重了知”或“知上加知”,这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修行。
了知什么,或与谁交谈,都不必时刻去看自己的心,或时刻去防备自己的心。让了知安住于被了知之物上,即被看见之物,或我们正在交谈之人。这称为单一层次的了知。而不是了知了眼、耳、鼻、舌、身或意之事后,再来了知自己的心。这样是无法离苦的。
如果了知了眼、耳、鼻、舌、身和意之事后,又去了知内在的心——这内在的“了知”,其实是心妄想执取,形成了一个“自我”,在内心时刻“知”着——那么,必须以“念”觉知那个去“知”着自己内心的心,每一次都要觉知。直到只剩下心通过眼、耳、鼻、舌、身或意单一层次的了知。
不在“想”之上叠加“想”
当心想到某事时,就让它单一层次地想。如果不小心妄想了那些是烦恼、贪爱或痛苦的事,就觉知它,不再叠加一个自责。如果又生起自责,例如:“我真不该这么想”,这种情况就称为“想上加想”或“双重思惟”,即在正常的思惟之上又叠加了一层妄想。
不在“感受”之上叠加思惟
当心妄想,以致生起了贪欲、嗔恨或沉迷的情绪后,不再叠加一个自责说:“我怎么能有这种情绪呢?”或“刚才生起的贪欲情绪真不该啊”,或“刚才生起的嗔恨情绪真不好啊”。这种情况,称为“在感受之上叠加思惟”。必须以“念”觉知这个叠加在感受之上的思惟。
当有了情绪,就觉知它,同时从那件事物中撤出喜爱或不喜爱。对于初学者,可能需要通过转移注意力到其他事物上,才能从那件事物中撤出喜爱或不喜爱。
但如果是时刻防备内心会有情绪,这种情况虽未妄想执取贪嗔痴的情绪,却是在妄想执取自己的心,这同样是不对的。
总结:只保持单一层次的了知
如果看见什么、听见什么、闻到什么、尝到什么、触到什么或想到什么,就让心随其自然的常规,单一层次地去“知”或“想”。只有当它将要妄想以产生烦恼、贪爱或痛苦时,才去觉知它。不是预先去拦截、觉知,以防止它去妄想烦恼、贪爱或痛苦。也不应时刻去觉知,以防止生起贪嗔痴的情绪。那样做是无法离苦的。因为心去时刻防备心,不让它妄想,或时刻防备心,不让它有贪嗔痴的情绪,那本身就是一种苦。
并且,要让其只剩下单一层次的“知”(了知色、声、香、味、触、法尘),或单一层次地了知感受、思惟和情绪(这些是被了知之物),或只有纯净的五蕴在运作,不在“能知”之心或“思惟”之心上叠加第二层任何妄想。这称为“仅仅是知”或“纯然的知”。
关于“仅仅是知”或“纯然的知”的误解
对于“仅仅是知”或“纯然的知”这句话,修行者们有很大的误解。即,当通过眼、耳、鼻、舌、身了知任何事物时,试图让心保持中立,或试图让心空寂,试图不让自己对被了知之物产生乐受或苦受,试图时刻让心对被了知之物保持“舍受”。
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或理解。因为不理解自然的“触”(phassa)。即,当有任何事物冲击到眼、耳、鼻、舌和身根神经系统,或冲击到意时,每一次都必然会伴随“能知”之心或“思惟”之心而生起乐受、苦受或舍受。这取决于冲击之物会引发哪种受。我们无法强迫它只产生舍受。
例如,见到一个熟悉的人,就会伴随着“能知”色尘的心而生起乐受(尚未达到任何贪爱的程度),然后它与“能知”色尘的心同时立刻灭去。但如果看见车祸死人,就会伴随着“能知”色尘的心而感到是苦受,然后它与“能知”色尘的心同时立刻灭去。但如果看见砖、石、沙、路,就会生起舍受或不苦不乐受(不感到乐也不感到苦的感觉,或中立的感觉),伴随着看见那个色尘而生起,然后与“能知”色尘的心同时灭去。
在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身根了知任何触碰,或想到任何事物时,也同样会有乐受、苦受或舍受伴随“能知”之心或“思惟”之心而来,每一次都是如此,无法只选择舍受。
如果仅是乐受、苦受或舍受,这是纯净的自然常规,是五蕴的自然常规。因为生来三十二分具足,有眼、耳、鼻、舌、身、意,就必然有见、闻、嗅、尝、触、思惟,也必然每一次都伴随着乐受、苦受或舍受。
行蕴造作的终点
要从苦中解脱的最终点,是必须熄灭那个时刻防备者或时刻跟随了知者——了知将要想什么或将要有什么情绪。因为那个时刻防备、或时刻跟随了知思惟、或时刻觉知情绪的心,本身就是妄想执取之心,它会让你持续痛苦。
因此,每当有那个时刻防备者、或有那个时刻跟随了知思惟或情绪者出现时,就要持续地觉知它,直到那个时刻防备者、时刻跟随了知者和时刻觉知者彻底熄灭。
但如果有一个“能知”在时刻防备着那个“时刻防备者”、“时刻跟随了知者”或“时刻觉知者”的产生,那么就会有“能知”叠加“能知”,永无止境。如果是这样,就要觉知每一个叠加生起的“能知”,直到再也没有在自然的“能知之心”和“能思之心”上叠加的“能知”为止。此时,便只剩下纯净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心)——在单一层次地、自然地运作,再无任何第二层妄想叠加。
将五蕴中的“色”(身)与“心”分离
修行慧解脱或纯观行者路线的人,并未在眼前观身至见其腐烂败坏。因此,必须有智慧能通过其他方法从对身体的迷失执取中解脱出来。例如,有智慧见到身体仅是自母胎以来所食营养元素的组合;或见到身体仅是心的被了知之物。因此,若想契入作为“能知”的纯净之心,就必须不关注、不赋予价值、不重视身体,才能契入纯净之心。
如果将纯净之心比作树心,身体比作外层的树皮或表皮。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树心,就必须先剥去外层的树皮或表皮,才能见到树心。如果总是在可惜那树皮或表皮,就永远没有机会见到树心。
将作为心所的“受、想、行”与“心”分离
受、想、行是心所,与心同时生起、同时灭去。例如,眼见色,就必然伴随着乐受、苦受或舍受,然后会记得那个色尘(想),并且是以一种混合造作完成的方式记得,例如,他是谁的父母、夫妻、子女,在哪里工作等,这称为行。
在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身触或思惟任何事物时,其过程与眼见色相同。
受、想、行因此不是作为纯净“能知”的心。因此,若我们想契入纯净之心,就必须不关注、不赋予价值、不重视受、想、行,才能契入纯净之心。
如果将纯净之心比作树心,身体比作外层的树皮或表皮,那么受、想、行就如同树的内膜。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树心,就必须先剥去外层的树皮,然后再剥去内膜,才能见到作为“心(能知)”的树心。如果总是在可惜树皮,又可惜内膜,就永远没有机会见到树心。
不执着“心(能知)”,亦不执着“涅槃”,方能证见涅槃
当剥尽了外层的树皮和内膜后,才了知这是一棵没有树心的树。即心中彻见:心(能知)仅是名法,无实体、无形状、无住处、无边界,生起来了知后,便极快地灭去。也就不必再去关注、赋予价值或重视那个“能知”了。让它经过,去找些事做,而不是坐在那里与“能知”为伴。
当不赋予“能知”任何重要性时,也必须不赋予“涅槃”任何价值或重要性。即必须停止寻觅涅槃的妄想挣扎,才能证见涅槃。因为涅槃超越了“能知”。佛陀已将其划分为心、心所、色、涅槃,因此,涅槃不是心(能知),必须超越“能知”,以至无所标示。
因此,如果修行者停在某个点上,标示说“这种状态就是涅槃了”,这表明他已执取了“涅槃”作为一个标示点,因此并未证见真正的涅槃。而涅槃不是任何可以被标示的状态。涅槃是无为法,不是会生灭或变化的状态。不是今天它是涅槃,到了明天就不是了。一旦是涅槃,便永远是涅槃。而证见涅槃者,会自证其知(paccattaṃ),如同尝过一道菜的人,自然知道菜的味道,其理亦然。
不执取,即是空
当心不再妄想执取,形成喜爱、不喜爱或沉迷于任何内外事物时——无论是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尘],还是内在的[色、受、想、行、识,即五蕴]——那么,五蕴便会随其自然的常规,纯净地运作,直至死亡之日。
当没有了执取者,便能理解或见到,实际上只有五蕴在生起,然后灭去。除了五蕴,再无其他执取者。而这五蕴,时刻在生灭,是无常、苦、无我。不可能用五蕴去执取色、声、香、味、触、法尘,也不可能用五蕴去执取五蕴(色、受、想、行、识)。
当通过眼、耳、鼻、舌、身、意接触或碰触任何事物时,便仅仅是触碰,不会生起一个作为“自我”的执取者——那个形如我们自身的透明光身,或一个与肉身(五蕴)重叠的作为“自我”的心或识。将只有单一的身、单一的心,即五蕴。当五蕴坏灭或死亡时,便再无那个形如我们自身的透明光身之心或识存留下来去承受业报,或在任何形态中再次受生。
如果将那冲击眼、耳、鼻、舌、身、意,包括每一次生起的感受、思惟和情绪的色、声、香、味、触、法尘,比作响起的电话铃声,如果没有接听者(没有一个作为“自我”或透明光身的心识去接听),那电话铃声便会自行停止。这称为“纯然的知”、“仅仅是知”或“知,但不关注”。心便会通透、明亮、喜悦,并且只有极致的快乐。
正如佛陀所言:
“诸比丘,一切痛苦,其根源皆来自爱、取,即渴求、挣扎与执着其为‘我’、‘我的’,包括对各种情绪的沉迷。凡是进入其中,执取为‘我’、为‘我的’之物,无一不招致痛苦与过患。何时有人能做到见仅仅是见,闻仅仅是闻,知仅仅是知,与诸事接触,仅仅是接触,不迷失、不纠缠、不沉醉,那时,心便空于诸种执取,通透、明亮、喜悦。”
以及:
“若人能平息或熄灭行(妄想),彼将证得极致之乐。”
“仅仅是知” 或 “知,但不关注” 没有“能知者”的实体 “纯然的知”
世间的责任
以上所说,全是关于内心离苦之事。但世间的问题,仍需用世间的知识、能力和智慧来解决,同时必须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不能只顾内心不苦,而忽略自己应尽的责任。
例如,夫妻的责任:仍需互相扶持、供养,给予鼓励、金钱和心灵的慰藉。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必须抚养、教育,教导他们断恶修善。但不仅仅是言教,父母必须以身作则,而不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子女也有报答父母恩的责任,要赡养父母,让他们开心、安心,不给父母带来麻烦或痛苦。并且必须努力求学,以利于学业或工作,让自己在世间法上日益进步,这才是让父母欣慰或快乐的事。这样做,才算是报答了他们养育我们的恩情。
除了家庭责任,还有工作责任、社会责任,也必须以正确、恰当的方式去履行。否则,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痛苦或麻烦。直到死亡,所有责任才告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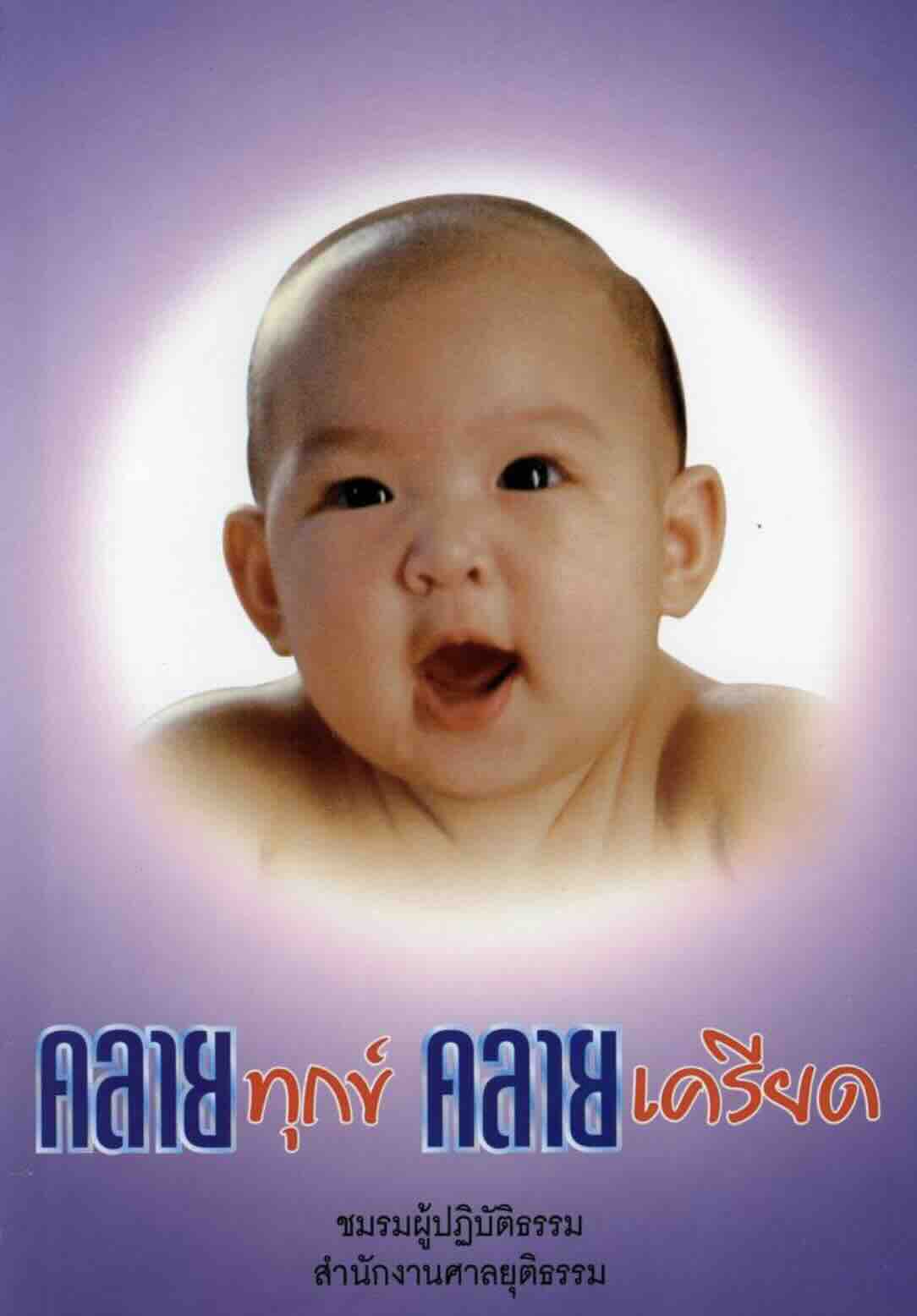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下载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