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修行之道
隆波帕默尊者, 南传上座部佛法 ·Index
วิถี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 - พระปราโมทย์ ปาโมชฺโช
佛法修行之道 - 隆波帕默尊者 - 摘要
修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为了看见身心的实相,然后将它归还给世间,放下执取。
序言
本书得以问世,是由于Dhitanaruchi Patthanakun女士(“解脱之声”善法园的理事)将本人于佛历2549年7月13日在善法园所作的题为“佛法修行之道”的开示,制作成了CD,以飨感兴趣的听众。之后,医师Palapat Lothierakitti(绰号Motui或Morthop)又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本人对文稿略作了修订,而后才付梓印刷。
希望朋友们能够深思:佛法要产生至高的利益,唯有将其付诸实践,直至能够真正根除内心的苦。
隆波帕默 佛历2552年9月9日
佛法修行之道
前言
我们有心修行佛法,这非常好。但在开始修行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为何而做?以及如何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也必须保持觉知,不迷失、不放逸,不因无知而误入歧途。
这四个方面的了解,称之为“正知”(Sampa-jañña),它是指导修行、防止偏离正道的基础智慧。
佛法修行分为两类:一是奢摩他禅修(Samatha-kammaṭṭhāna),二是毗婆舍那禅修(Vipassanā-kammaṭṭhāna)。这两者都必须依靠“念”(Sati)来觉知禅修的所缘,并依靠“正知”这一智慧来时时指导修行。否则,我们就很容易修错。
奢摩他与毗婆舍那
无论是修习奢摩他还是毗婆舍那,我们都必须清楚地具备正知,明白自己要修习哪一种禅法,并且也要知道修习它的目的何在。
奢摩他的目的是让不平静的心获得平静,让不快乐、不舒适的心获得快乐与舒适,以及让不善的心转变为善心。
而毗婆舍那的修习目的并非以上这些,而是为了生起正见(Sammā-diṭṭhi),或者说,只是为了看见身心的实相。
身与心,也就是五蕴,正是佛陀所说的“苦”(Dukkha)。而“苦”是必须被了知的。因此,我们的职责就是持续地去了知身、了知心,这便是所谓的“培育毗婆舍那”。必须持续不断地去了知,直到生起智慧,了知身心的实相。这种智慧,称之为正见。它是一种能够透彻理解身心实相的智慧——即它们是无常的、是苦的、并且非我。
一旦我们拥有了智慧,真正地看到身与心是无常的、是苦的、或非我,届时,心便能够放下对身心的执取,然后将自动地亲证涅槃。
那些精进觉知身、觉知心的人,有一天会看到身与心并非“我”,它们仅仅是元素(四大),是五蕴,是世界的一部分,而非我们所有。当看到真正的“我”并不存在时,便能证得须陀洹果。若继续觉知身心,直至放下对身心的执取,则被称为阿罗汉。
因此,阿罗汉并不是那些将心训练得恒常善良、恒常快乐、恒常宁静的人。因为他们并不追求这些,一切快乐、宁静、美好,皆是世间法。而阿罗汉是那些了知身心实相,从而完全根除了对身与心执取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培育毗婆舍那,也就是学习和了解我们自身的身与心,直至领悟其真实本质,从而得以放下。真正的离苦,正在于这“放下”之处。
三学
要学习了知身、了知心,佛陀教导了三门课程,称之为“三学”(Tisikkhā)。第一门是关于戒的课程,即“戒学”(Sīla-sikkhā);第二门是“定学(心学)”(Citta-sikkhā);第三门是“慧学”(Paññā-sikkhā)。如果我们学得不完整,问题就会产生。
一、戒学
我们多数人认为,如果去寺庙从比丘那里请求受戒,戒学就算完成了。事情并非如此浅薄。对于修行者而言,除了五戒、八戒、十戒或二百二十七戒之外,还有另一种至关重要的戒律,我们应当了解,那就是“根律仪戒”(Indriya-saṃvara-sīla)。
“根律仪”指的是守护六根。也就是说,当眼见色、耳闻声时,如果心中生起了愉悦或不悦,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念”及时地觉知那份愉悦或不悦。这样,烦恼就无法掌控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便能自然而然地生起戒行。
看到了吗?“念”是如此重要,甚至连持戒都必须依靠它。“念”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不可或缺的。所有善心都必须由“念”构成。要有戒行,必须有“念”;要有正定,必须有“念”;要培育智慧,也必须有“念”。
因此,如果我们保有“念”,比如,眼睛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子,心中生起贪爱。一旦我们以“念”觉知到贪爱的生起,贪爱就无法掌控心。我们保证不会犯第三条学处,也不会为了欺骗她而犯第四条学处(妄语)。戒行便会自然生起。
又或者,我们走在路上,看到别人掉了一部手机,哇,这个型号我正好想要!此刻,我们看见心中生起了贪婪,想要占为己有。一旦以“念”及时觉知到那份“想要”的心,觉知到贪心,贪心就会立即熄灭。贪心无法掌控心,我们保证不会拿走别人的东西,即使物主不在场,我们也不会拿。
又或者,有人骂我们,我们生气了。一旦以“念”觉知到生起的嗔恨,嗔恨便无法掌控心。我们保证不会骂回去,不会打他、踹他、伤害他或杀害他。戒行之所以能生起,是因为我们有“念”,能够及时觉知到自己内心中生起的状态。
因此,根律仪戒的教导核心在于此。经中说道:“诸比丘,眼见色时,心中生起愉悦或不悦,当以‘念’及时觉知。若觉知不及时,烦恼将掌控心。” 心会失去常态,变成一颗没有戒行的心。被烦恼掌控的心,就是一颗不正常的心。这种戒对于修行者至关重要。
耳听到声音,比如,听到别人称赞,我们的心立刻膨胀起来。若能觉知到心的膨胀,并及时看穿它,我们就不会沉醉于那句称赞。若被别人辱骂,我们的心火冒三丈,若能看见那愤怒的心,我们就不会去伤害那个人,心会保持中舍。
一个人独坐时,也会胡思乱想,时而想好事,时而想坏事。有些念头会产生善法,有些念头则会产生不善法。只要我们有“念”及时觉知,任何事物都无法掌控我们的心,心就会处于正常状态。这就叫做“我们的心有戒”。
二、定学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门课,名为“定学”(Citta-sikkhā)。这门课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很少有人学习它,尽管它非常重要,以至于不学习它,就无法培育智慧。
一些修行者不学习定学,只是一味地打坐,以为持续地坐着、昏昏沉沉地坐下去,就叫作定学。这可不是。另一些人则认为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持续地标记名色,心自然就会有定。唉,定学可没有那么肤浅,不只是打坐那么简单。
定学,是学习关于心的知识:哪种心是善的,哪种心是不善的;哪种心可以用来修习奢摩他,哪种心可以用来修习毗婆舍那;以及哪种心完全不能用。我们必须学习每一种心的状态,清晰地了解它们,才能知道我们当下的心,究竟适合哪一种修行。
学习的方法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从经典中学。那些学习阿毗达摩的人,他们学习心法有52种。心本身是52种心所法中的一种状态,但仅仅这一个心,就可以细分为89种或121种心识。实际上没有人能拥有全部种类的心。这样学起来有点困难,但了解一下也很好。
还有另一种更简单的学习心的方法,那就是直接去觉知真相。但在初始阶段,我们必须先掌握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哪种心是善的,哪种心是不善的。这需要一点教理知识,需要善知识的教导。否则,我们就会不了解,有时我们甚至会无意中造作出不善的心,却误以为那是善心。这种事在修行人中非常普遍,他们喜欢造作不善心,这真是件奇事。
我们还需学习另一个原则:哪种心适合修习奢摩他,哪种心适合修习毗婆舍那。否则,在实际修行时,我们常常会用不具备足够品质的心去修习毗婆舍那,结果是徒劳无功。
许多不了解奢摩他与毗婆舍那的修行者,想要修毗婆舍那,却不自觉地陷入了奢摩他。这种情况最为普遍,在每个禅修中心、每个道场都屡见不鲜,大同小异。因此,我们必须先听闻,了解奢摩他与毗婆舍那的原则。一旦掌握了原则,无论选择哪个道场的修行方法都可以,并没有哪个道场一定优于另一个。除非那个道场根本不教导如何觉知身心,那样的道场就没有培育毗婆舍那禅修的可能。
如果我们学习并掌握了原则,修行就会变得不那么困难。如果不了解原则,不了解自己的心,修行将是最困难的事,如同在大海里捞针。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什么样的心是善的,什么样的心是不善的。善心,是不被贪、嗔、痴所掌控的。因此,任何时候心有贪、有嗔,或者心迷失、放逸,那颗心必定是不善的。这样看似乎很简单,但有些心的状态,我们看不出它是否有贪、嗔、痴。那是一些微细的不善心,我们就需要通过观察其他辅助因素来判断。
真正善的心,必须是轻盈的(Lahutā)。如果我们修行后,心变得越来越沉重,那就要警惕了,肯定修错了,不善心取代了善心。当我们开始修行时,有些人会感到非常沉重,如同背负大山一般。如果心变得沉重,说明肯定修错了。善心必须是轻盈的。
善心必须是柔软的(Mudutā)。如果修行后心变得僵硬、迟钝,那是不善的,要小心。善心是柔软的。
善心必须是适业的(Kammaññatā),即敏捷、灵活。如果心变得呆滞、僵硬,那是不善的。整天呆若木鸡,这是不善的,要小心。
因此,在修行时,你是否感觉到,每当刻意造作时,心就会变得沉重、紧绷、僵硬、呆滞、迟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贪欲生起了。想要修行,这就是不善的,因为贪欲生起了。当想要修行时,你着手去做,就会依照那份“想要”来修行。在那一刻,“想要”仍然掌控着心。
在阿毗达摩中教导说:“烦恼是业的近因。”烦恼与业同时生起,烦恼导致了行为(业)的发生,但它们是同时生起的。因此,当我们想要修行时,立刻就开始修行。那一刻,“想要修行”的欲望仍然掌控着心。那颗心就是不善的心,它会变得沉重、紧绷、僵硬、呆滞、迟钝。那么,真正的“念”能否生起呢?绝无可能。因为那一刻,那片土地已经变成了烦恼的领地。“念”是不可能与烦恼同时生起的,两者必有一失。
因此,如果我们修行时,心变得僵硬、迟钝,那是源于贪欲,是“贪根心”。想要修行,然后当心变得僵硬、迟钝时,又生起了新的“嗔根心”——不想要它,不喜欢这种僵硬、难受的感觉,想要变好、想要快乐、想要舒适。这些全都是烦恼。
因此,我们必须学习认识心的各种状态,哪种是善,哪种是不善。
隆波坦率地说,几乎所有的修行者,都在迷迷糊糊地造作不善。想要获得善,却迷糊地造作出不善。他们的心变得僵硬、迟钝、沉重、紧绷、难受。有些人夹杂着贪,有些人夹杂着嗔,但作为基础的,是痴,它始终夹杂其中,只是我们从未看见。因为不了解心的真实状态,这就是“痴”在蒙蔽着我们。
又比如,有时我们修行,当我们专注地、用力地观照时,心会变得呆滞、宁静。但有时也会生起柔软的状态,生起光明,生起柔软。但是,我们的心却迷失进去,执取于那份源自修行的快乐与宁静。
因此,修行者中还有另一类人,他们非常专注、用力地标记,然后感觉到心变得轻盈、舒适、快乐、光明。但要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凝滞”感,有一种不自然的“凝滞”。
事实上,最适合修习毗婆舍那的心,就是普通人的平常心。普通人的心,就是最好的心。“人”(Manussa)是指心高尚者,他们的心已经准备好接受佛法。但是我们这些修行者,一旦开始修行,就刻意去用力、去标记,结果失去了作为“人”的心,反而变成了一颗“梵天”的心。梵天的心是柔软、喜悦、快乐的,但它有点陶醉。它会有点陶醉,有点快乐,柔软而快乐,贪欲就夹杂其中,只是我们看不见。
因此,为数不少的修行者,一部分人修到后来产生不善,变得非常紧张、僵硬、沉重、紧绷。另一部分人修到后来则飘飘然,感到快乐、愉悦。后者已经不是不善心了,而是善心,是世间善心。而这个,恰恰是阻碍道、果、涅槃在微细层面深入的障碍。
因此,必须小心一点。有些人修得很精进,心会变得非常柔软,柔软得不真实。整日整夜,三日三夜,都保持着那份柔软。许多修行者都是这样,贪欲夹杂进来了,愚痴夹杂进来了,却再也看不见了。而另一类用力标记的人,刚开始是愚痴和嗔恨夹杂,等到标记到位、专注到位时,就变成了愚痴和贪欲夹杂。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学习直到我们认识心的状态,这样我们的修行才不会走偏。
接着,我们会有一颗中舍的心,只是知,只是见所缘。具备这种品质的心,在阿毗达摩论典中被称为“大善心,智慧相应,无行”(mahā-kusala-citta ñāṇa-sampayutta asaṅkhārikaṃ)。意思是,由智慧组成、自然生起、并非刻意造作的善心。这类心具有最强大的善的力量,最适合用来培育毗婆舍那禅修。相关的细节还有很多,需要慢慢听闻、慢慢学习。
三、慧学
学习了知心之后,就进入到为了生起智慧、看见名色/身心实相的课程。在了解如何培育智慧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那些阻碍智慧培育的错误修行方法。
有两种错误的或极端的修行方式,会阻碍毗婆舍那的培育。一是强迫心,直到心变得粗糙、僵硬;或是强迫它,直到它变得完全柔软、顺滑。这是其中一种极端。另一种极端,则是放任心跟随烦恼,随波逐流。这两种方式都会阻碍毗婆舍那的培育。
第一种方式称为“苦行”(Attakilamathānuyoga),即自我折磨,强迫身体、强迫心,让自己受苦,让心干涸。
另一种方式称为“欲乐之行”(Kāmasukhallikānuyoga),即随心所欲,顺应烦恼,让心沉浸在烦恼之中。
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隆波要强调心的这两种极端?因为我们听闻过的关于两种极端的教法,通常指的是身体上的极端。比如,当我们谈到“苦行”时,我们通常只想到对身体的折磨。当我们谈到“欲乐之行”时,则侧重于身体上的感官享受。这里所说的也同样正确,但我想让大家也思考一下心方面的极端。因为一切法,心为首,心为主,由心而成。无论是折磨身体,还是放任身体随顺烦恼,都必须始于心。敞开心扉听隆波讲,然后试着按照隆波所说的去修行,看看那份苦是否能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要想认识中道,就得慢慢学习,直到真正的“念”生起。“念”源于心能够记得境界。“念”不是通过标记生起的,“念”不是通过专注生起的,“念”也不是通过命令它生起而生起的。阿毗达摩明确教导说:“‘念’以能够准确地记得法(境界)为其近因。”
因此,我们来修习四念住的初步阶段,其目的就是为了拥有“念”。我们练习觉知身体,直到我们了知“色”的境界;练习觉知感受,直到了知“受”的境界;练习觉知心,直到了知“心”的境界。一旦了知之后,“念”就会自动生起。
大多数人来隆波的寺庙学习,隆波喜欢让他们练习觉知名法。因为我们大多数是城市人,我们的主要职业就是“想”,只会想。大多数人从事的工作都需要思考,整天都在思考。对于那些想法多的人,适合觉知心。对于那些贪欲重、爱享受、爱舒适、爱美、爱漂亮的人,适合觉知身体。
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不知不觉地想去某个道场,就去了。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根性是什么样的。朋友去了哪个道场,我们也跟着去。哪个道场人多,我们也跟着去。或许那个道场很好,老师可能很厉害,但如果他们的教法与我们的根性不符,我们修行也不会有结果。因此,在修行之前,必须先分析自己,看清自己的根性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们是那种爱享受、爱舒适、爱美、爱漂亮、爱宁静,整天不想和任何人打交道的人,这类人必须觉知身体。因为身体很容易让我们看到它是不舒服的、不舒适的、不美的、不漂亮的。
而那些喜欢想很多、心思散乱的人,则应该觉知自己的心。觉知自己的心,对于想法多的人来说。
人的根性主要有两种,可以用来作为选择毗婆舍那初始所缘的依据,即贪行根性者(Taṇhā-carita)应觉知身体,而见行根性者(Diṭṭhi-carita)应觉知心。至于受念住和法念住,暂时不建议初学者去修,因为受念住和法念住是适合那些智慧猛利者的禅修所缘。我们还没到那个被称为智慧猛利的程度。所以我们先从觉知身体和觉知心开始,这是比较容易的基础,但觉知身体是有条件的。身念住适合于止行者(Samathayānika),适合于修习禅定的人。如果不擅长修禅定而去觉知身体,心往往会深陷其中,停滞在身体上。
比如,我们觉知腹部的起伏,心就会流过去,黏在腹部不动了,什么也做不了,就黏在那里。抬脚、移步,心就会黏在脚上。觉知呼吸,心就会沉入呼吸之中,然后忘失了自我。因此,觉知身体,如果心不够稳固,是很难修的。所以,身念住的教导中说,它适合于止行者,即修习禅定的人。
当我们把心修到宁静,达到第二禅(二禅),就会生起一个东西,寺院里的祖师大德们称之为“能知的心”。这颗能知的心,是一颗ทรงสัมมาสมาธิ(具备正定)的心,它有“心一境性”(Ekaggatā),即心的专注与统一。
当我们修行奢摩他,会以为那只是折磨身体。当我们谈到欲乐之行,则侧重于身体上的感官享受。这里所说的也同样正确,但我想让大家也思考一下心方面的极端。因为一切法,心为首,心为主,由心而成。无论是折磨身体,还是放任身体随顺烦恼,都必须始于心。敞开心扉听隆波讲,然后试着按照隆波所说的去修行,看看那份苦是否能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要想认识中道,就得慢慢学习,直到真正的“念”生起。“念”源于心能够记得境界。“念”不是通过标记生起的,“念”不是通过专注生起的,“念”也不是通过命令它生起而生起的。阿毗达摩明确教导说:“‘念’以能够准确地记得法(境界)为其近因。”
因此,我们来修习四念住的初步阶段,其目的就是为了拥有“念”。我们练习觉知身体,直到我们了知“色”的境界;练习觉知感受,直到了知“受”的境界;练习觉知心,直到了知“心”的境界。一旦了知之后,“念”就会自动生起。
大多数人来隆波的寺庙学习,隆波喜欢让他们练习觉知名法。因为我们大多数是城市人,我们的主要职业就是“想”,只会想。大多数人从事的工作都需要思考,整天都在思考。对于那些想法多的人,适合觉知心。对于那些贪欲重、爱享受、爱舒适、爱美、爱漂亮的人,适合觉知身体。
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不知不觉地想去某个道场,就去了。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根性是什么样的。朋友去了哪个道场,我们也跟着去。哪个道场人多,我们也跟着去。或许那个道场很好,老师可能很厉害,但如果他们的教法与我们的根性不符,我们修行也不会有结果。因此,在修行之前,必须先分析自己,看清自己的根性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们是那种爱享受、爱舒适、爱美、爱漂亮、爱宁静,整天不想和任何人打交道的人,这类人必须觉知身体。因为身体很容易让我们看到它是不舒服的、不舒适的、不美的、不漂亮的。
而那些喜欢想很多、心思散乱的人,则应该觉知自己的心。觉知自己的心,对于想法多的人来说。
人的根性主要有两种,可以用来作为选择毗婆舍那初始所缘的依据,即贪行根性者(Taṇhā-carita)应觉知身体,而见行根性者(Diṭṭhi-carita)应觉知心。至于受念住和法念住,暂时不建议初学者去修,因为受念住和法念住是适合那些智慧猛利者的禅修所缘。我们还没到那个被称为智慧猛利的程度。所以我们先从觉知身体和觉知心开始,这是比较容易的基础,但觉知身体是有条件的。身念住适合于止行者(Samathayānika),适合于修习禅定的人。如果不擅长修禅定而去觉知身体,心往往会深陷其中,停滞在身体上。
比如,我们觉知腹部的起伏,心就会流过去,黏在腹部不动了,什么也做不了,就黏在那里。抬脚、移步,心就会黏在脚上。觉知呼吸,心就会沉入呼吸之中,然后忘失了自我。因此,觉知身体,如果心不够稳固,是很难修的。所以,身念住的教导中说,它适合于止行者,即修习禅定的人。当我们把心修到宁静,达到第二禅,就会生起一个东西,寺院里的祖师大德们称之为“能知的心”。这颗能知的心,是一颗ทรงสัมมาสมาธิ(具备正定)的心,它有“心一境性”,即心的专注与统一。当我们的修行正确时,就会有一个能知的心升起。它会看到,身体是一部分,感受是一部分,心是一部分,念想造作、善与不善是另一部分。心会稳固,成为一个观者。它会看到身体在移动,而心是观者。就像阿毗达摩学者喜欢教导的,比如,坐着的是色,能知的是名。他们会这样教。坐着的是色,能知的是名;站着的是色,能知的是名,等等。
意思是说,当我们觉知色法时,我们的心不能沉溺于色法之中,我们的心是独立的,远远地看着,仿佛在看别人。我们看到这个身体在站、走、坐、卧,而心是远远地看着的那个。我们会立刻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会立刻看到,不需要思考。这个身体不是我。因为它站、走、坐、卧,是色法在移动,心是能知者。
如果我们这样去觉知身体,有一天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它只是一个物质,一堆元素。这个身体时刻被苦所逼迫。这个身体的移动是因为心命令它移动。我们会了知和看见身体的实相。
至于觉知心,则比那更容易。觉知心时,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无法直接觉知到心本身,所以我们先觉知感受,这叫做觉知心所。觉知不到心,就觉知心所,因为心本身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去看的,没有一个所谓的“心的色身”可供我们观察。我们所谓的“名身”,实际上就是受、想、行。
因此,我们先依靠觉知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与心俱生俱灭,也就是那些心所。比如,我们会说,有时我们的心是善的,有时是不善的。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心是善的,心是不善的,心贪,心嗔,心痴。刚开始是这样感觉的。但再后来,当念与慧更敏锐时,我们就会看到:心是一部分,贪是另一部分;心是一部分,嗔是另一部分;心是一部分,痴是另一部分。它们是各自独立的。这就叫作法的分离。它会趋向于法念住。它会直接看到境界本身。
初期阶段,还无法看到那么深的境界,没关系。练习去感觉,练习去觉知我们自己的感受。
隆波建议,大家无论以前修习过什么禅法,只要那个禅法与自身的身心相关,就继续修下去,不必放弃。来跟隆波学习,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谁擅长什么,就用那个。但要抓住原则。学习原则就行了。掌握了正确的原则,然后把它融入到我们已有的修行模式中去,都是可以的。如果原则错了,即使模式再优美,它也不是毗婆舍那。否则,如果走得优美就能证悟佛法,那么军乐队的成员们早就全部证悟了,因为他们走得非常优美。这不相干。行、住、坐、卧这些威仪,根本不相干。
因此,谁曾经修习过什么禅法,就继续修下去。
举个例子,谁曾练习过觉知出入息,就继续觉知下去,不必停止。如果觉知了感到舒适,那很好。但如果觉知了感到难受,就说明不适合,去找另一个所缘来替代。所以,继续觉知呼吸。在觉知呼吸的过程中,心会分化出四种类型。
第一种,觉知呼吸,或其他禅修所缘也一样。觉知呼吸,或者看腹部起伏,或者经行,做着做着就心生愉悦,飘飘然,忘失了自我,失去了觉知。这种情况是不能用的。大部分觉知呼吸的人,都是第一种:修着修着就飘了,忘失了自我。这是不能用的。
第二种,当觉知呼吸时,心会移动,贴附在呼吸上。试着呼吸,然后慢慢观察。如果我们觉知呼吸,仔细观察,心会滑落下去,停留在呼吸上。心会移动,心其实并不稳固,心会流动。或者有些人看腹部起伏,心会流到腹部。有些人经行,用隆波田(Luangpor Teean)的方法,心会流到手上。觉知四威仪——站、走、坐、卧,心会专注在整个身体上。现在,心流过去黏住了整个身体。做这个有什么用?没什么用。这些专注的人,心滑进去专注在所缘上。专注呼吸,专注腹部,专注脚,专注手,专注整个身体,甚至专注心也可以。有些人觉知心,也并非真的在觉知,而是去专注心。紧盯着,紧盯着,紧盯着,心就变得宁静。
这些非常专注的人,会产生奢摩他的状态。比如,汗毛竖立、身体膨胀、身体飘浮、身体轻盈、身体摇晃、身体变大,这些状态都是奢摩他的状态。或者身体突然一震、一亮,那不是毗婆舍那。我们却误以为那是“观智”(Vipassanā-ñāṇa)。那根本不是观智。“智”(Ñāṇa)是智慧的范畴,它不是身体的感受。“智”是了知,是智慧的范畴。因此,我们身体突然一震、一亮、汗毛竖立,这些都是奢摩他的范畴。为什么我们修毗婆舍那,结果却变成了修奢摩他?因为我们迷失于专注。比如,我们持续地专注腹部,持续地专注呼吸,一会儿身体就飘起来了,身体变轻,身体摇晃之类的情况就会出现。这并不奇怪。但要问这好不好?好……但是是奢摩他那种好。哪天我们的心烦乱、疲惫不堪,做什么都做不下去,就可以修习奢摩他,让心得到休息,得到力量。
我们已经讲了两种情况了。第一种,完全迷失。第二种,陷入奢摩他。去专注身体,专注手,专注脚,专注腹部,专注心,都可以专注。每个道场都有。现在来到第三种。
第三种,我们觉知呼吸,或者觉知腹部起伏,或者移动手之类的。为了以觉知身体来培育毗婆舍那,这也是可以的。第三种情况是,如果我们看到身体在起伏,而心是观者。看到吗?必须有心作为观者,心是稳固的。我们看到身体在起伏,身体在起伏。看到这个身体在呼气,看到这个身体在吸气。看到这个身体在站、走、坐、卧。看到身体在动手动脚,移动、弯曲、伸直之类的。看到身体在做这些,而心仅仅是观者。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色法在移动,心是观者。”这不再是我们了。这个在移动的,不是我们了。这不再是手了。这种感觉,它不会觉得这是手,它会觉得只是一个在移动的色法。如果能感觉到只是一个色法在移动,我们就会发现一种状态,我们的心会变轻。但如果感觉是“我的手”在移动,心就会变重。但一旦我们感觉到,“色法”在动,心是能知者,这时心就会豁然开朗,心会有“念”,它会觉醒过来,看到那个正在移动的色法不是我。
(隆波对一位在场者说:感觉得到吗?你这个,很重。心会变重,因为去做了第二种,去专注手。它去专注……现在就迷失于思考了。是第一种,迷失了。看到吗?只有第一种和第二种。要达到第三种,看到色法在移动,心是观者,这几乎已经没有了。如果有,就能证得圣果了。)
第四种,我们练习觉知腹部起伏,觉知呼吸,然后观察名法的状态。比如,我们呼气-吸气,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想了。呼吸时,心去专注腹部,心去专注呼吸,知道心去专注了。呼吸时,生起了喜悦,知道有喜悦。呼吸时,感到快乐,知道有快乐。呼吸时,心烦意乱,知道烦意乱。或者看腹部起伏,心烦乱起来,也知道烦乱。
心是什么样的,就持续地去了知它。以一个禅修所缘为基础,然后持续地去了知心的变化。最终,我们将能记得各种心的状态。我们会记得,放逸是这个样子的,专注是这个样子的,善、不善、贪、嗔、痴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记得了,接下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念”就会自动生起。这样我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培育“念”。
那些觉知心的人,做起来很容易。那些觉知身体的人,要在日常生活中培育“念”会有点难。身体是粗重的所缘,它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但是,如果我们觉知心,我们看到朋友走过来,还没来得及刻意修行,看到朋友走过来,一阵欢喜之心“噗”地冒出来。“念”立刻就能忆持起来,欢喜心生起了。然后智慧就会看到,它熄灭了。只有生起和熄灭。
和朋友聊天,哇,真开心,真好玩。感觉到快乐“噗”地生起。看到了吗?快乐生起了,然后也熄灭了。聊着聊着,朋友意见不合,生气了。看到愤怒“噗”地生起。“念”忆持起来,愤怒也熄灭了。只有生起,然后熄灭;生起,然后熄灭。因此,如果我们这样练习,我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培育“念”。
如果练习第一种,在哪儿都能做,整天整夜地迷失。这是常态。迷失有六个途径:迷失于看,迷失于听,迷失于闻,迷失于尝,迷失于触,以及迷失于想。如果再加一个,就是迷失在心,即迷失于修行,迷失于专注,迷失于标记。所以,迷失有七个途径。第二种,专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专注。尤其喜欢去寺庙、参加禅修课程或喜欢独处的人,更擅长专注。第三种和第四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如果是第三种,即身体在站、走、坐、卧,心作为观者,持续不断地去看,就会看到,那个站、走、坐、卧的,不是我们。是用一颗柔软、温和、敏捷、灵活、适合作业的心去看的。
修行的原则
听懂了吗?听隆波讲法,要听第二遍、第三遍才能听懂。听第一遍就懂的人,很少。听第二遍、第三遍懂的人,比较多。但要持续地听,不要今年来听一次,然后消失三年再来一次,那还是老样子,早就忘光了。
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当隆波换了个话题,不再谈论佛法时,我们的心就开始移动了。感觉到了吗?开始散乱了。就这样去觉知。别去管它,不要看到任何东西。我们太爱思考了,总认为佛法必须是那样,必须是这样,“超越”平凡。超越平凡,就看不到平凡了。佛法,就是这个平凡本身。
觉知身体,就会看到那个正在呼吸的,不是我们。觉知呼吸,然后持续地觉知心的状态,这就转向了觉知心。
用隆波田的方法摇动身体,摇动时心跑掉了,这不行。第二种,摇动时去专注,心专注在手上,专注、专注、专注,可以得到奢摩他。第三种,看到色法在移动,心是观者。第四种,摇动时觉知心,隆波田的目标是教导这个:“身动觉知心,心动要觉知。”但很多人都到不了他教导的核心,都卡在了第二种,或者甚至卡在了第一种,就是沉浸在念头里。摇动这个姿势,然后就想,下一个姿势是什么来着?哦,是这个。嗯,接下来又是什么?一直在想。虽然是在想“法”,想“法”,但还是没有效果。那还是在想。
要练习去觉知境界,每个人的道路都不同,不要模仿别人。但要听隆波讲解的“三学”这个原则,要搞懂。学习眼、耳、鼻、舌、身、意,当所缘来触及时,要及时觉知到变化的感受。练习去看,然后学习关于心的知识,什么样的心是善的,什么样的心是不善的。
我们大家,感觉到了吗?现在在这个房间里的大多数人,心是轻盈的。感觉到了吗?而且不是那种飘忽不定的轻。是那种柔软的轻。也有些人是专注型的,他们的心就会迟钝,没有任何感觉,就是呆呆的。那是专注型的。
(隆波转向一位在场者说:你的就有点专注,要小心一点。它习惯于沉浸,有点呆滞。呆滞不好。心必须是觉知的、觉醒的、喜悦的。明白了吗?不明白也得忍着。隆波不收听法费,不要求任何东西。唯一的请求,唯一的呐喊,就是“忍耐”。忍着,不勇敢就别怕,怕的是没有忍耐力的人。学习佛法不是为了获得快乐,也不是为了获得博学多闻的智慧,而是为了看见实相。仅此而已。不要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学了之后就必须通晓三藏。没有哪个弟子能通晓全部三藏,除了佛陀。因此,我们作为弟子,只知道我们所修行的那部分。
修行就像我们爬山。假设有座山,当我们要爬上去时,我们就会观察大多数人走哪条路,我们就跟着走。如果一直往上爬,总有一天会到达山顶。我们起初会认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最好的。但当我们登上山顶,回头环顾四周,就会知道,上山的路四面八方都有。走哪条路都行,去哪个道场都行,说真的。但原则要正确。
看腹部起伏,看的时候心飘了,这不能用。看的时候去专注,得到奢摩他。看的时候看到身体在移动,心是观者,这就用毗婆舍那来觉知身体,知道身体不是我们。看腹部起伏时看到心,时而快乐,时而痛苦,时而好,时而坏,这是以腹部起伏为基础,然后来了知心,可以修心念住。觉知呼吸也一样。觉知时失念了,不能用。觉知时专注呼吸,得到奢摩他。觉知时看到身体在移动,心是观者,这是修毗婆舍那。觉知时看到心的变化,时而善,时而不善,这是修心念住。所以,一种禅修所缘,可以分化出四种结果。
隆波从森林派的祖师大德那里学习禅法,师承多位尊长,从隆布敦(Luang Pu Dun)、隆布特(Luang Pu Thet)、隆布辛(Luang Pu Sim)、阿姜摩诃布瓦(Than Ajahn Maha Bua)、隆波普(Luangpor Put)、阿姜Boonjan,到隆布苏瓦(Luang Pu Suwat)等等。早期的祖师大德们,在培育“念”方面非常严格。到了阿姜曼的徒孙辈,很多人反而沉迷于奢摩他。不只是这一派,甚至我们这些修腹部起伏的,几乎全部都沉迷于奢摩他,沉迷于专注。因为我们以为,“念”就是去标记。“念”是“能够忆持”,这才是关键。“念”不是“标记”。“标记”这个词,它夹杂着刻意的贪欲。它有贪欲夹杂其中。
因此,在我们的义注中才会教导说:“以标记名色为所缘的念,是苦。渴爱潜伏在将念用于标记名色这一行为的背后,此即集谛。”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修行时,立刻就开始标记,苦立刻就生起了。有烦恼——即想要修行;着手标记——即是造业;产生的结果——即是苦。但如果标记得很厉害,有烦恼,也着手造业了,完成了,做得恰到好处,心中生起了快乐,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不善可以是善的助缘,不善也可以是不善的助缘,善也可以是不善的助缘。比如,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跑出去在路边玩,或者在雨里玩,我们生起悲心,怕他受伤,怕他生病,怕被车撞,怕他感冒。我们有悲心,叫他回家。叫他回家他不肯回,我们就生气了。可能会抓过孩子来……(听众笑)。必须让身体舒适。如果修行了觉得难受,那肯定是不善的。难受的心,是不善心的特征。但如果修行了心很轻,也未必是善的,要小心。有人说心整天都很轻。轻的心不一定就是善的,但重的心肯定是不善的。或者有苦的心,肯定是不善的心。快乐的心,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不善的。它们不能互相替代。不要以为“噗”地轻了,就“噗”地对了。
(隆波说:忍着点,忍着听。跟这位女士,还有这位0号女士,你们修来的,没有白费,可以用。但是多听一点,就能向前迈进,进入真正的毗婆舍那。我们大多数人都卡在奢摩他,卡在奢摩他的“相”上。我们以为奢摩他的相就是毗婆舍那的“智”。“智”是智慧的名字,不是身体感受的名字。它是关于知和解的。
但早期的祖师大德们有他们的善巧方便,他们可怜我们这些懒惰的修行人,于是就称赞我们说,我们得到了那个“智”、这个“智”。他们是给我们鼓励。曾经有一位长老,是早期祖师的弟子,他教导关于“智”的知识。有人告诉他,曾经和那些老一辈的祖师聊过,当他们开始教导这些“智”的时候,他们问尊者说,这其实是奢摩他,不是真正的毗婆舍那“智”吧。尊者回答说:“知道。”他们说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教,是为了让人们有毅力坚持下去,至少能得到奢摩他。谁有足够的福德和波罗蜜,能够从奢摩他中解脱出来,就可以继续培育毗婆舍那。因此,希望我们能慢慢学习。从哪个道场修来的,都同样好,也同样会错。
(隆波转向另一位在场者说:)你的心是恒定的。感觉到了吗?心整天都是恒定的。一天一夜,心都恒定。其他的,才是不恒定的。心是恒定的。这样就把“常见”修出来了。这不行。要修行的正确中道,要觉知错误的地方。练习去觉知境界,时而放逸是这样,时而专注是这样,时而贪、嗔、痴是这样。持续地去了知,有一天真正的“念”就会生起,它会自动走上中道。中道,是无法刻意走进去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在哪里。
有些人努力寻找那个“中”点,以为“中”点一定在胸口中央,或者在额头中央。那是什么“中”啊,不知道。那是身体的中间。或者在肚脐之上,之类的地方。不是的。中道,不是那样走进去的。如果有真正的“念”,心就会走上中道。那一刻,心就会有“念”。因为它了知境界。因此,要练习去了知境界。
练习去看腹部起伏也行,然后会看到,色法在移动,心是观者;色法在移动,心是观者。不要去“想”,要去“感觉”。毗婆舍那不是用想的。有些人喜欢想。比如,生了气,在生气的那一刻,心是不善的。在知道“生气了”的那一刻,是善的。到这里,修行就结束了。接下来,又开始错了。比如,念诵“生气了,生气了”。这时是在想。能知的心和能想的心是不同的心。在想的那一刻,已经从毗婆舍那中掉出来了。
关于修行的探讨与问答
问:当我观看时,看到的外部景象多于自己的心。感觉上,对心的觉知只是一瞬间,然后又会去看新的东西。有时看很久,才意识到自己在看。其实,对心的觉知很短暂。我们不知道那算是觉知心,还是没有。
隆波:这种看,还不是真正的觉知。它更像是一种“刻意”的观看。
问:就像我们向外看一样,能看到外面的东西。但有时我们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心,只是感觉到我们正在看。
隆波:你感觉到“正在看”的那个点,心还不是平常心,它超越了平常。它有点迟钝。
问:有时它也想回来觉知心。
隆波:不要“想”……如果“想”,就要知道是“想”。当“想”了之后,要知道是“想”,好,这就觉知心结束了。
问:那就像我,看隆波您讲法时,还是觉知过头了,是吗?
隆波:是的,有点过。你现在的心,还是比正常的要过一点。看得出来吗?它有点迟钝。
问:那如果这样,我们该怎么办?
隆波:什么也做不了……知道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且,不要去讨厌它。如果讨厌它,就要知道你在讨厌它。如果想修正它,就要知道你想修正它。持续地、如实地去了知。毗婆舍那,我们能知道多少,就了知多少。没有“应该知道多少”这回事。“应该”这个词,只是我们自己的期望罢了。如其本然地了知它当下的真实状态。
问:它还是无法脱离出来。
隆波:因为它还在“想”要脱离。隆波每次都说,什么也做不了,只是去觉知它。知道自己“想”要脱离出来,就这样。知道,就结束了。至于它会不会脱离,取决于它的因缘。它为什么会黏住?因为我们刻意去修行,导致心变得迟钝。
问:现在,当我知道自己“想”时,那个“想”的所缘不是很清晰,不像什么都看不见,但知道是“想”。
隆波:知道那么多就够了。然后就看到,那个“想”已经消失了。知道那么多就够了,不必去看到它的实体。
问:所缘很模糊,但那个“想”,几乎看不见。
隆波:没关系。能看到多少,就看多少。因为四念住,看哪个都可以。
问:有时,当我们回来觉知心时,它会“唰”地一下切断。
隆波:那个“回来觉知心”的点,如果是刻意回来的,就要知道是刻意的。贪欲又生起了,烦恼又生起了。
问:现在,当我知道我刻意回来觉知时,就会看到那个“想”要回来的心。第一个所缘就淡忘了,之后就没什么了。
隆波:它淡忘了,因为它已经成为过去了。那个所缘已经熄灭了。
问:但是那个“想”的心,也看不见它的熄灭,因为从一开始就没看见它。
隆波:那你怎么知道你在“想”要看呢?就在那个“知道”的地方,那,就叫“觉知”。不是看见“想”……昨天,有个小孩来问隆波:“隆波,您说要去看烦恼,烦恼长什么样?它个子大吗?”(听众笑)隆波告诉他,不是的,不是去看它的形状,只是去觉知“感受”。而已。那孩子就“哦……”一声,说:“这样就是‘看’啊!”
问: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频繁地生起呢?
隆波:要让它频繁生起,就要练习观察我们自己的感受,持续地。过正常的生活,眼、耳、鼻、舌、身、意接触所缘,这是很自然的。和朋友聊聊天,做些别的事,然后慢慢地觉知那份变化的感觉。最终,心就会记得越来越多的境界。
问:在我们“留意”的那一刻,我们也是在“刻意”地去觉知,是吗?
问:那像我,看外在的色法,这叫“外散”吗?
隆波:不叫。你的情况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得出来吗?既不真正地出去,也夹杂着想把它拉回来的心。
问:如果完全出去,就会迷失很久。
隆波:那就迷失去。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迷失了。
问:但它迷失得太久了。
隆波:那,它太久了,对吗?看到了吗?“它应该比这个短一些。”看到了吗?又有“应该”了。是“应该”了。过多了,过少了,过头了,那些都源于我们自己的期望。怎么做才能让它迷失得短一些?如果心能够准确地记得境界,它迷失的时间就会变短,“念”就会生起得更频繁。
因此,各位,留个家庭作业给大家。以前修过什么禅法,不要放弃。坚持去做。除了那些真正外散的,去专注蜡烛、专注外在的东西,那些与我们身心无关的,可以暂时放一放。但如果是任何与身心有关的禅法,就继续做下去。
隆波建议,晚上,礼佛、念经、打坐、经行。以前怎么修,就怎么修。禅修什么,就继续修什么。但是,修是为了练习去了知境界。这一点和以前有点不同。以前我们练习看腹部起伏,祖师们让看,就只看。希望有一天能变好。现在调整一下,看腹部起伏,然后心跑去想了,也知道。心专注进去,也知道。心是快乐、是痛苦、是善、是不善,也知道。练习去觉知境界。我们每天练习觉知境界,心就会准确地记得境界。当心准确地记得境界,当那个我们熟悉的境界生起时,“念”就会自动生起。因此,每天都要练习。
问:如果我回来觉知心,也是有“想”要回来觉知心的意图。
隆波:那也还是不对。
问:但那不也是在觉知境界吗?
隆波:不是的。那是去“紧盯”境界。觉知心,要“跟随”着觉知。意思是,境界先生起,然后才觉知到它的生起。先迷失了,然后才觉知到迷失。先生气了,然后才觉知到生气。不要刻意地把心安住在那儿等着看。要跟随觉知,不要刻意地去紧盯。
问:那怎么做才能让它频繁生起呢?
隆波:要让它频繁生起,就要练习观察我们自己的感受,持续地。过正常的生活,眼、耳、鼻、舌、身、意接触所缘,这是很自然的。和朋友聊聊天,做些别的事,然后慢慢地觉知那份变化的感觉。最终,心就会记得越来越多的境界。
问:在我们“留意”的那一刻,我们也是在“刻意”地去觉知,是吗?
隆波:不是的,不是的。是先有感觉生起,然后才去觉知。因此,最初只能觉知到比较强烈的感受,比如,生气了,才会知道。后来,不高兴了,也知道。再后来,只是有点烦,也看到了。它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微细。不要刻意去觉知那些微细的。就这么“玩玩”地觉知下去。
因此,留个家庭作业。晚上,礼佛、念经、打坐、经行,修习自己以前修的任何禅法,但是要练习去了知境界。心跑去想了,也知道。心去专注了,也知道。心是快乐是痛苦,心生起贪、嗔、痴,都要去觉知境界。这样练习,不要去考虑什么时候会变好,什么时候“念”会生起,根本不要去想。每天练习。谁不方便晚上修,早上也可以,看情况。抽一部分时间来练习。当练习多了,心就能准确地记得境界。接下来,“念”就会在日常生活中生起。在这个房间里,跟隆波学习后,“念”自动生起的人,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了,非常多。“念”自动生起,然后会立刻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身体只是一个移动的色法而已。身体不是我,立刻就看到了。心,是不恒常的,立刻就看到了。心是不恒常的,感觉到了吗?看到了吗?心是被逼迫的,无法控制的,会这样看到。
到这个阶段,我们是在学习。我们把实相喂给我们的心去学习。天天喂它,让它学习下去,觉知身、觉知心,觉知身、觉知心。到某一个点,真正的智慧会生起。它会豁然开朗,啊,这个身体、这个心,不是我。而它豁然开朗的过程,就像隆波说的那样,它会汇集进去,然后去斩断结,去斩断那个认为身心是“我”的邪见。
那是一种“我们”。一旦斩断了,再退出来,此刻,“我们”的感觉就不会再生起了。就不会再感觉到身体是“我”,心是“我”。它会彻底斩断。再也不用去守护了。继续练习下去,到某一点,它会放下对身体的执取。心就会稳固、突出、明亮。不用去守护,心也会在定中一整天,而无需去守护。这是阿那含的境界。
再继续练习下去,直到看到那个心本身,那个能知的元素,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它会放下心,它会放下,它会归还心。它会归还出去。到那个点,就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做了。但不会称自己为阿罗汉。为什么不称,知道吗?……因为已经没有了那个需要去称呼什么的执着了。
(隆波对坐在后排的一位在场者说:喂,新来的……新来的怎么样了?)
(隆-波-说:喂,谁回头去看新来的,然后忘失了自己?坦白说……已经不错了。这两位已经不错了,明白了,对吗?隆波所说的。很好。跟隆波学习,只要看到境界,心迷失于眼,心迷失于耳,心迷失于想。你们练习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好了。因为,真正的“念”生起了。)
每天都不要放弃禅修。就像拳击手,即使成为了世界冠军,也还是每天练习打沙袋,不会停止。我们修行人,无论水平多高,也不会放弃禅修。曾经念“佛陀”,就继续念。曾经观呼吸,就继续观。曾经看腹部起伏,就继续看。隆波以前就是看腹部起伏的,每天都看。到了某一天,它会放下对身的执取,再到放下对心的执取。
问:法喜充满的心,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这样可以吗?
隆波:可以,如果知道它。但别去沉溺其中。如果持续很长时间,就要知道它持续很长时间。然后智慧会教导自己,哦,连善法也是不恒常的。
问:在那种感觉里,心是觉醒的、喜悦的,并且有念、有正知。
隆波:嗯,那很好。但别去粘着它。继续觉知下去。
问:就是说,觉知那种状态,然后它会自己变化的。
隆波:对。我们的责任,就是去觉知。不是去干预,不是去维持,不是去装饰,不是去驱赶。
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觉知时,有时觉得修行进步了,有时又退步了。
隆波:那是因为还有“想”要去得到好,不想要坏。因此,当修行顺利时就高兴,修行不顺时就伤心。实际上,好与坏是平等的,它们都是无常、苦、无我的。
问:我们这些居士,在修行上有什么建议吗?
隆波:一样。在家修行和出家修行,原则是一样的。但出家人有更多的时间。居士们,就利用零碎的时间。晚上抽出时间来专门修行,白天就在日常生活中觉知。
问:当妄念生起时,我们去觉知,但有时妄念太强,拉不回来。
隆波:知道它拉不回来。就只是知道。我们的职责是“知”,不是“拉”。
(隆波转向另一位在场者)你的心有“常见”,认为心是恒常的。要多看心的生灭。时而快乐,时而痛苦,时而善,时而不善。不要只安住于那个“知者”。安住于知者,会变成无色界定。
问:我喜欢去想善法,这算不善吗?
隆波:我们是好人,所以放弃恶比较容易,放弃善比较难。看到了吗?我们想变好,所以就难放弃。这就是。佛陀早就说过了,好人行善易,行恶难。坏人行恶易,行善难。我们是好人,所以要放弃“想”要作恶的念头,很容易。看一眼就断了,一眼就断了。但是那个“想”要好的念头,我们是好人,所以就难放弃。不要为它烦恼。
问:感觉那些念头都必须是好的,所以当它想去不好的方面时,就不知道了。
隆波:实际上,当“想”生起时,它已经不好了。
问:当时不知道。只想着我正在做好事。
隆波:那个,是我们还不了解的状态。但现在我们了解了,看到了吗?以后它就骗不了我们了。它会拿别的东西来骗我们。任何被念和慧看穿的,它就骗不了我们了。我们还没看穿的,它就会继续骗我们。但实际上,我们修行不是为了去得到任何东西。修行,直到看见一切的实相,即无常、苦、非我,然后归还给世间,我们的责任就到此结束了。因为我们已经放下了。所以,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东西。
有一位博士曾经来告诉隆波:“我修行,有‘念’,时刻觉知自己。一直与觉知同在。”隆波转头看着他的脸,笑了笑。然后继续修行,继续觉知境界。哪天心疲倦了,它就会转入奢摩他。哪天它有力量了,它就会出来觉知境界。就这样练习。当在日常生活中时,“念”就会生起。
问:说到心的四圣谛,很流畅,但到了时候,还是被“想”的威力所控制,没有念,没有觉知。还以为阿姜们教的就是这个。但自己的修行肯定不好,才会变成那样。
隆波:及时知道它,就很好。实际上,“念”也是无我的。如果它不生起,它就是不生起。而且,我们修行也不是为了要一天24小时都有觉知。我们之所以需要有觉知生起,是为了去了解,不善也是不恒常的,善也是不恒常的。这个,才是智慧的总结点。智慧的总结点不在于一直有“念”。明白吗?以前我们没有觉知,所以不知道自己放逸了。但当我们会觉知了,我们就会知道,刚才放逸了,现在觉知了;刚才放逸了,现在觉知了。这两者都是不恒常的,这两者都是无法控制的。最终,心会放下,放下这两者。不是放下放逸,而保留觉知。它会放下两者。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的心有时还被烦恼掌控,这是很自然的事,没什么奇怪的。看到了,就很好。
问:我觉得不自然是因为,那些微小的“想”生起时,都知道。但当涉及到与法相关的“想”时,它会让我走偏。因为如果是在法的方面“想”,那一定是对的。
问:(另一位在场者)另一个问题是,这是件好事。当念头“噗”地生起,就及时知道。念头生起,就不会继续造作。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是觉知力比较弱,或者没有“念”,它会继续造作一会儿,然后才,“啊,我正在想”。觉知到了,所以我想请教阿姜,看到这个优点了。
隆波:很好。我们不是为了“不想”而修行,而是为了当它去想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知道。这样它就不会漫无目的地造作出不善。有事情需要思考,我们就可以思考。如果没有事情,我们也不会放任它去造作不善。当心流去想时,就是心失念了。当及时知道时,心就生起了“念”。我们就会看到,一切都是生起然后熄灭,无法控制。都一样。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请大家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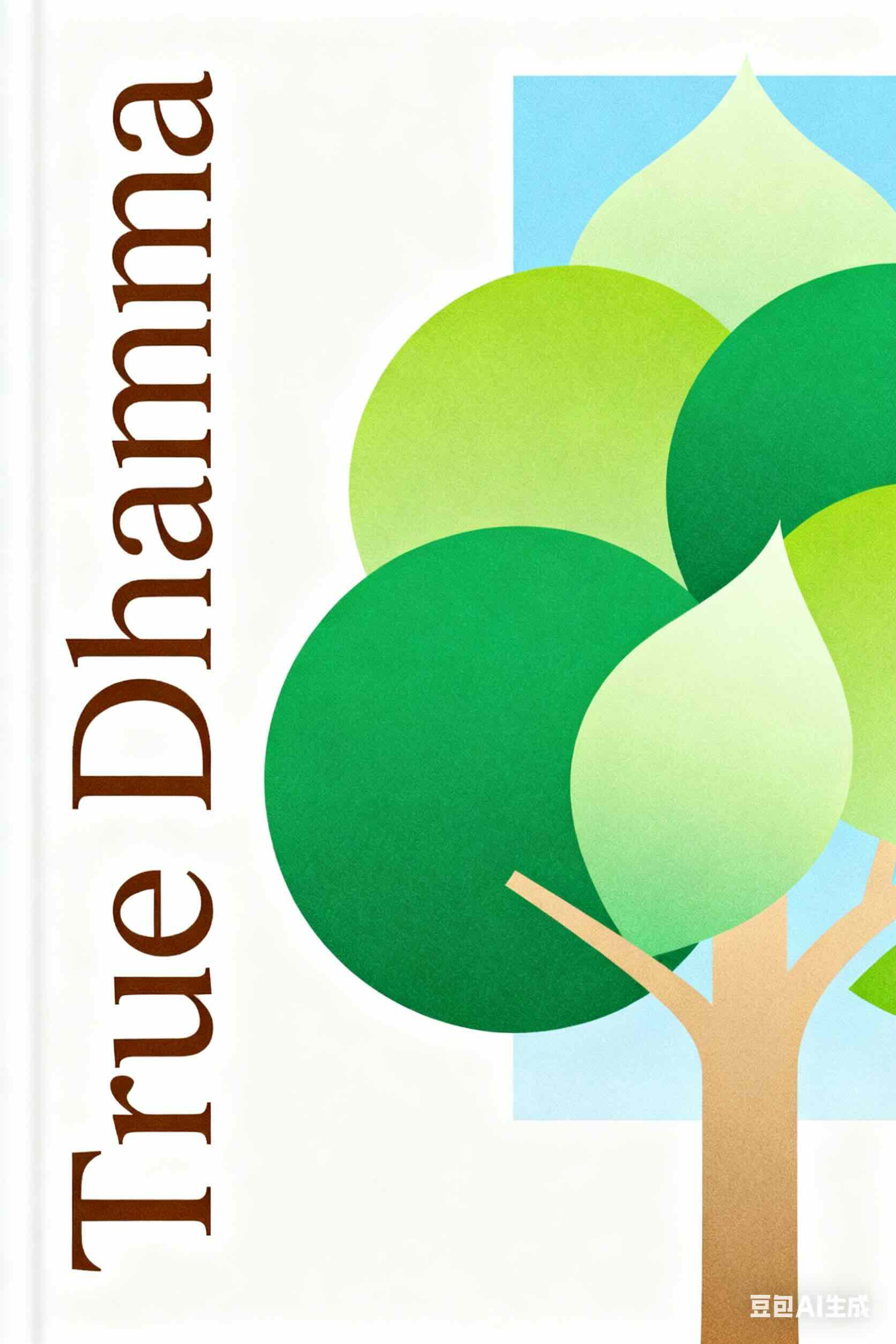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下载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