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习成对之法,以了知单一之法
隆波帕默尊者, 南传上座部佛法 ·Index
เรียนธรรมคู่เพื่อรู้ธรรมหนึ่ง - พระปราโมทย์ ปาโมชฺโช
修习成对之法,以了知单一之法 - 隆波帕默尊者 - 摘要
佛法的奇妙之处在于,让我们学习成对的法;当彻见成对之法后,我们便会了知那单一之法。
前言
今天隆波苏金(Luang Por Sujin)来看我,他是隆布敦(Luang Pu Dun)的弟子,在我之前就去拜见了隆布敦。隆布敦是为他剃度的戒师。他最初跟随隆布峦(Luang Pu Luay)学习,之后在隆布敦座下出家。我从1983年就认识他了。如今,他住在湄宏顺府(Mae Hong Son)。谁若是不怕疟疾,不怕象腿病,不怕登革热,都可以去拜见他。
他的心很坚强,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以前,他住在巴吞他尼府(Pathum Thani)的稻田里,那片地属于阿姜提瓦(Phra Ajahn Thiva)。我曾经去看望过他。抵达时已是下午,他正在烈日下行禅,皮肤被晒得黝黑,几乎都焦了。
第一章 修习成有对之法,以了知单一之法
隆波帕默于佛历2551年3月8日星期六在是拉差สันติธรรม园林的开示
几乎都要死了。轻松的修行方式也有,比如像这样坐着玩,做些让人平静下来的事,然后带着觉知,从早到晚持续地去觉知身、觉知心,这称之为“乐行道”(Sukhāpaṭipadā)。但不要以为这种修行方式就是懒散的,“乐行道”并不意味着懒散,而是指修行已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在古籍中提到,这种方式适合那些烦恼已经减轻的人。如果烦恼炽盛,就必须精进地训练自己。有些人需要减少睡眠、节制饮食、行禅、从早到晚地坐禅,这称之为“苦行道”(Dukkhāpaṭipadā)。但总的来说,无论是“乐行道”还是“苦行道”,都必须在修行中具备坚定的决心。决不让修行中断,必须从早到晚持续地保持觉知,同时又不给自己施加过度的压力,这样才能取得好的结果。修行不是拿生命去交换,那样是不会有真结果的。
曾经有一位长老问我:“你教导了这么多在家居士,他们的弱点在哪里?”我回答说:“在家居士的弱点在于常常缺乏持续性。”他们并非不认真,如果下定决心,也能做到,但多数人内心尚未达到那种程度,总是懒懒散散,做一下,停一下,做一下,停一下。不认真的人,只会得到不真实的东西;而认真的人,内心必须真正达到那种程度。内心真正坚定的人,必须坚强,有毅力,有耐心。忍耐(khanti)非常重要。即使你再聪明,如果修行懒散,也一无所获。必须真正地精进努力。
而且,各种教导也令人困惑。必须好好学习。仅仅认真是不够的,如果像牛像水牛一样盲目认真,也无法成功。必须学习。有人问长老:“为什么修行这么苦?”他回答:“苦,是为了离苦。”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每一位长老大德,在获得成就之前,无一不是侥幸得来的。他们都经历了极其艰辛的磨砺。还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长老,他曾经在缅甸的森林中托钵行脚时迷了路。他 raccontò 道,他看到一条小溪,便沿着溪流走,以为它会流向泰国的城镇。但越走,树木越高大,他才知道走错了方向。找不到回头的路,断食了好几天,又下起了大雨。他全身浮肿,只好躲进一个山洞里避雨。他感觉这次必死无疑,于是整理好自己的衣物,披上僧伽梨,把洗浴用的布巾绑在胸前,心想这样死后,穿着的袈裟才不会散开。然后,他就躺下来观察自己的心。他躺着观察,心是否还有牵挂?是否还执着于什么?他没有发现心有任何执着。他持续地观察……之后的事情,我必须得问他本人……讲太多也不好,不然你们会说我……但还是再讲一点吧,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重要经验(在家居士们笑了)。
他继续说,他观察着心,发现心什么也没执着。但继续观察下去,最终发现有一层非常微细的薄膜。他一直看,一直看,哦……原来心执着于那个“空无一物”。它不执着这个,不执着那个,却去执着那个“空无一物”。你们看到了吗?烦恼是多么微细啊!就像我们修行,有些人心空空的,那是什么空?心流到了“空”的境界,去迷恋和执着于“空”,以为这就空了,真的空了吗?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空。
之后,他的病痛就消失了,也找到了返回泰国的路。每一位长老,没有一个是侥幸成功的,都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修行。
涅槃,因为它那时没有烦恼。但现在有烦恼。并非因为它那时没有心。它有的是“物”(色法),只有身体,没有烦恼。如果好好学习,就会发现,佛陀并没有教导要熄灭感受(受)。确实,佛陀说过:“因受灭,故爱灭;因爱灭,故取灭。”但他并没有教导要熄灭感受。人们自己把它搞混了。听到“灭”,就以为要去把它熄灭。
事实上,“受”是一种心所,它与每一颗心一同生起。只要有心,就必然有心所;而必须存在的那个心所,就是“受”。想要熄灭“受”,唯一的办法就是熄灭心。而熄灭心,只有一个境界可以达到,那就是梵天中的无想有情天。这样走就偏了。把教导的含义理解错了,以为“受灭,则爱灭,取灭,有灭,生灭,苦灭”,就想着要通过熄灭“受”来灭苦。请问,“受”是哪一种法?
“受”是“果报”(Vipāka)。“果报”是业(kamma)的结果。“果报”是无法被熄灭的。只有当它的果报穷尽时,它才会自己熄灭。“受”不是烦恼,所以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去熄灭它。即使是烦恼,实际上也无法被熄灭。万物皆由因缘而生,若因缘灭,果法则随之而灭。没有人能随心所欲地去熄灭任何东西。所以,有些人致力于熄灭“受”,这是行不通的。
在缘起(Paṭiccasamuppāda)中,有十二个环节。这些环节可以分为三类:一些是烦恼(kilesa),一些是业(kamma),另一些是果报(vipāka)。
属于烦恼的部分有哪些?有无明(avijjā),有爱(taṇhā),还有取(upādāna)。
实际上,佛陀教导的是什么?要透彻地学习。那些被曲解的教导实在太多了。许多追求离苦的人,非但没有离苦,反而比以前更苦,这也是很多的。有些人修行到发疯,修行到身体残疾、背驼颈歪、浑身疼痛,像个残疾人一样,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修行后发疯的也很多。没有好好学习,只是听信某个人,或者自己想当然地认为某种方法好,然后就投入全部身心去做。越是投入,就越是痛苦。这是走错了路。就像走路撞墙,还使劲用头去撞,以为能撞穿。这是不行的。如今,那些歪曲、错误的教导比比皆是。那不是真正的培育念住(Satipaṭṭhāna)。如果是真正的培育念住,结果会来得很快。“快”这个词也很重要。如果能如实地觉知身、觉知心,结果会很快出现。有些人不愿如实地觉知身心,反而去做别的事情。比如,有人教导要熄灭感受,熄灭心,熄灭行蕴(即造作),或者去执着于“空”等等。
熄灭感受,可以通过专注色法来修习。比如,当我们准备拿起或抓住什么东西时,就将注意力集中在手上。持续地观照,让心专注于手,不去关心身体的感觉,也不去关心心,这叫做“无想离欲”(saññā-virāga)。专注色法,并且“无想离欲”,最终当心进入第四禅时,它就能熄灭感受。
熄灭感受的同时,也熄灭了什么?当然是心。修行到最后只剩下身体,僵硬地待在那里,没有了心。只有一个境界是没有心的,那就是“无想有情天”,即色界第四禅天的梵天。修行成了色界梵天,还以为是涅槃。
无明(avijjā)是指对四圣谛没有清晰的了知。爱(taṇhā)是心的渴望,是想通过六根门(眼、耳、鼻、舌、身、意)获得所缘的欲望。这种欲望有三种形态:一是欲爱(kāma-taṇhā),即渴求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获得感官所缘;二是有爱(bhava-taṇhā),即渴求某个境界能够永恒存在,这倾向于“常见”(sassata-diṭṭhi);三是无有爱(vibhava-taṇhā),即渴求断灭、消失,希望所有境界都断绝,这倾向于“断见”(uccheda-diṭṭhi)。比如修行时,希望心完全熄灭,认为这就是“涅槃”,这种欲望就称为“无有爱”。只要还有“爱”在驱动行为和造业,就不可能真正证入涅槃。至于取(upādāna),它就是力量强大的“爱”。在缘起中,无明、爱、取,这三者属于烦恼的部分。烦恼的作用是驱使我们造业。
在缘起中,属于业(kamma)的是什么?是行(saṅkhāra)和有(bhava)。
行(saṅkhāra),以无明为缘而生起造作,正如佛陀所教导的:“缘于无明而有行”(Avijjāpaccayā saṅkhārā)。“行”即是造业,也就是所谓的“造作”。造作些什么呢?造作善的,造作不善的,也造作那些无记的。
另一个属于“业”的要素是“有”(bhava)。“有”的全称是“业有”(kamma-bhava),它是在“爱”的驱动下,心所进行的工作。
成对之物, 会显现三法印。
单一之物, 不显现三法印。
所谓的“单一之物”,就是 “单一之法”与“单一之心”。
缘起中除了烦恼和业之外,剩下的部分全都是果报(vipāka)。从“缘行生识”(saṅkhāra-paccayā viññāṇaṃ)开始,“识”是“行”的缘。“识”是“名色”的缘,“名色”是“六入”的缘,“六入”是“触”的缘,“触”是“受”的缘,这五者都是果报。对它们我们无能为力,它们是业的果报,无法修改,只能去觉知。下一个由“有”产生的果报,就是生(jāti)和苦(dukkha),即生、老、死等,这些苦。
所有这些都是应该去觉知的,而不是应该去断除的。因为苦是果报。
佛法非常深奥。所以,在断除烦恼时,并非随心所欲地去熄灭这个、熄灭那个。必须看到真正的根源。真正的根源是无明。那么,要如何断除无明,熄灭无明呢?没有人能熄灭无明。但是,一旦“明”(vijjā)生起,无明就会自行熄灭。“明”就像光明,“无明”就像黑暗。光明生起的瞬间,黑暗便自行消失。
因此,我们不必致力于熄灭无明,而应致力于让“明”生起。“明”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彻知苦谛。如果能清晰地了知苦,那么集谛(samudaya)就会被自动断除。当集谛被断除时,就会亲证灭谛(nirodha)。当亲证灭谛时,道谛(magga)就会生起。因此,真正的禅修任务,就是了知苦。当彻底了知苦之后,“明”就生起了,无明也就被断除了。
所谓的“苦”,就是这个名色、身心本身。我们有责任去觉知身、觉知心,如其本然地去觉知,这就是所谓的“念住”(satipaṭṭhāna)。因此,佛陀教导说,四念住是通往清净解脱的唯一道路。我们的任务是觉知身,觉知心,如其本然。持续地去觉知,总有一天,真正的智慧会生起。“无知”,即无明,就会熄灭。然后,那个因“无知”而运作的过程,即所谓的“缘起之生起链”,也会随之整条链地熄灭。因为随着无明的熄灭,缘起的“缘起之寂灭链”也整条链地随之寂灭,这是以无明的寂灭为开端的。
还有取(upādāna),正如佛陀所教导的:“缘爱生取,缘取生有”(taṇhāpaccayā upādānaṃ, upādānapaccayā bhavo)。“爱”是贪(lobha),“取”也是有强大力量的贪。它们都是烦恼,并导致造业,即在心中塑造出“有”。我们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塑造“有”,塑造出或大或小的“有”,比如人趣之有、畜生趣之有、饿鬼趣之有、阿修罗趣之有、地狱趣之有、天人趣之有、梵天趣之有。我们的心就在这些“有”中不断地轮转。这些“有”若加以分类,可分为三类:一是在欲界(kāmāvacara-bhūmi)中的“有”,包括天人、人类、饿鬼、阿修罗、畜生,下至地狱众生;二是在色界(rūpa-bhūmi)中的“有”,即色界梵天,他们仍有色身;三是在无色界(arūpa-bhūmi)中的“有”,即无色界梵天,他们没有色身。无论在哪一界,“有”都是由心所造作的。这是因为有“爱”和“取”在背后驱动。因此,只要还有“爱”和“取”,就还有“有”。何时“爱”与“取”止息了,“有”也便止息了。这个造作“有”的工作,就是造业。如果“爱”熄灭了,心就会停止造业;如果还有“爱”,心就会继续造业。
稍微有点间接。实际上,他安住于“单一之心”。所谓的“知”,就是那个“单一之心”本身,那个无所造作、不与任何法成对的心。我们的心仍在成对的法中轮转,例如,时而快乐,时而痛苦;时而善,时而恶;时而粗糙,时而微细;时而在内,时而在外;时而在近,时而在远;时而在过去,时而在现在,时而在未来。心有其轮转之处。但“单一之心”没有轮转之处。它就是那样。单一之心,单一之法,是同一回事,不是成对的。为什么?因为它超越了造作。为何能超越造作?因为圆满了四念住的修习。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修习四念住。当四念住的修习圆满时,我们的心自然会从苦中解脱,从烦恼中解脱,并且日夜都从造作中解脱出来。空,空,恒时清净。为什么?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再造作了。正如佛陀所说,心达到了无为之境,心无边无际,心广大无垠,无点无相,无所住立。而我们的心,还有边界,你们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了吗?心仍有边界,仍有限制。当真正放下心时,将无边无际。心不再执取任何身心境界。所有的身心境界都化为一体。如果执取,就会立刻产生“成对”的境界。例如,执取这个,就有了“我们”;不执取那个,就有了“他们”。如果不执取任何东西,就只有一个。心是一,法也是一。单一之心,了知单一之法。这就是舍利弗尊者曾问根达萝格塔(Kuṇḍalakesā)的:“什么被称为‘一’?”
因此,我们要抓住修行的要点。除了“了知苦”之外,没有其他任务。没有熄灭感受的任务,没有熄灭行的任务,没有停止思考的任务,没有“如何不思考”的任务,没有“如何让心安住于空”的任务。修行只取空境,只将心导向空境,这是完全行不通的。佛陀从未教导要将心导向空境。佛陀教导的是四念住。他教导身随观念住(kāyānupassanā),要有念持续地觉知身;教导受随观念住(vedanānupassanā),要有念持续地觉知受;教导心随观念住(cittānupassanā),要有念持续地觉知心;教导法随观念住(dhammānupassanā),要有念持续地觉知身心境界。
他没有教导“空随观念住”(suññatānupassanā)。四念住里没有这个。他没有教导去觉知空。但是,当我们清晰地、如实地觉知身心时,我们就会见到涅槃,它自己就是空的。隆布敦教导说:“空,空,清净,停止造作,停止追寻,停止心的活动。什么都没有,一无所剩。”他会这样教导。这是结果,是我们在圆满修习四念住之后,心成为“单一之心”的结果。“单一之心”,如果不是阿罗汉,是不会有的。即使有,也只是刹那间的。在证得圣道圣果的每一阶段,都只有片刻。
实际上,“单一之心”是阿罗汉的心,是空的、空的、清净的。有位比丘问隆布敦:“您安住于什么?”他回答,安住于“知”。比丘问:“知是什么?”他回答:“空,空,清净,停止造作,停止追寻,停止心的活动,什么都没有,一无所剩。”其实,他的回答稍微回避了一下,是间接的回答。
单一之心,单一之法, 是同一回事,不是成对的。 为什么? 因为它超越了造作。 为何能超越造作? 因为圆满了四念住的修习。
第二章 成对之法与单一之法
隆波帕默于佛历2551年2月22日星期五在是拉差สันติธรรม园林的开示
……在家居士们不必做什么工作吗?每天都来得这么满满当当。我以前有机会去顶礼隆波普(Luang Por Put)一个月也就一次。而且三、四个月里,当有长假时,才会去顶礼隆布敦、隆波帖,或隆波辛这些住在远方的长老。所以我属于那种“蜻蜓点水”式的弟子。那些侍奉长老的比丘们称我为“蜜蜂”,因为我只是飞来采一下花蜜,然后就飞走了。让长老们当莲藕的守护者,而自己却不去采食花蜜。我不会依附于某一位长老。但我会用心去探求、去观察。我跟隆布敦学了两次就足够了。
在了解了佛法的核心要点后,并且对它有了深入的理解和信心,之后就去拜见其他的长老,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经验。
为何要去学习那么多东西呢?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才想到,哦,我的意图是从事弘法的工作。人是多种多样的,法也必须是多种多样的。我几乎学遍了所有法门。我去过各个有名的道场,或者至少是读过他们的书,听过他们的录音带,几乎全部都涉猎过。除了那些邪见的道场,我内心不会接受,也不会去接近。如果某个道场还在正见的范畴内,我就会去。比如,我去拜见过隆波田(Luang Por Thian),他是动中禅的创始人,他不是森林派的。我从森林派的长老们那里学习,这是事实,但我并未将自己局限于此。隆波田,人们说他很好,我就去拜见他。他确实有他的好。如今,传承他核心教导的人,就是隆波堪钦(Luang Por Kamkian)。所以,其他派系中也有杰出的长老,并非说其他派系就没有。隆布布达(Luang Pu Buddha)我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也有他的好。他真的很好。隆布克鲁巴彭差(Luang Pu Khruba Phrommachak)也很好。阿姜普塔塔(Ajahn Buddhadasa)也有他的好。我后来只通过收音机听过他的法,因为他已经去世很久了。
我四处游学,向数十位长老学习。实际上,如果我们理解了修行的核心,然后只修习其中一个法门,也就是只觉知一个成对的法,也就足够了。例如,心迷失了与心觉知自己,只觉知这个就够了。把这个作为原则。然后其他的你就会自己了知。等一下它生气了,你也会自己知道;它贪婪了,你也会自己知道。只要知道一个对就够了。在我们修行业处时,修习四念住,我们并不是单独地修习某一个。我们是成对地、成组地修习。这称为修习“成对之法”(Dhamma-khu)。所谓的成对之法,例如,出息与入息,这是一对。为什么要修习这一对?因为它在变幻,在变化,让我们看到。
比如出息,然后它又入息。或者,站、行、坐、卧,这是另一组,也算是成对之法。站、行、坐、卧,一会儿站,一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卧。一天之中,只有站、行、坐、卧。如果站、行、坐、卧时能觉知自己,那么一天之中都能觉知自己。出息、入息时能觉知自己,那么一天之中也都能觉知自己。因此,修习任何一组,或任何一对,都足够让念整日存在。或者,观察受,也就是乐、苦、舍的感觉。如果有乐,就有念;有苦,就有念;舍,也有念。也就是整天都有念。当有了念,又会失去念。有念与失去念,又是成对的。修习也是成对地修。心有贪与心无贪,也是成对地修。
我们修习时,修习哪一个呢?就修习那个显着的。比如贪心生起了,它突然冒出来,我们就看到,哦,心有贪。看到的瞬间,贪就消失了,变成了无贪的心。但我们的心往往喜欢专注在有贪的心上,因为它更粗显。我们不会来专注无贪的心。而且,如果我们只专注无贪的心,往往会专注到“空”里去。因此,隆波有时会简短地说:“心有贪,要觉知;心有嗔,要觉知;心有痴,要觉知。”那个自动会包含进来的,就是“心无贪、无嗔、无痴”。因此,如果某人脾气暴躁,就观察有嗔的心,然后一天到晚就会看到,心只有两种状态,就是有嗔的心和无嗔的心。某人很贪婪,欲望多,就观察有欲望的心,一会儿有欲望,一会儿又消失了。如果觉知到欲望,欲望就消失了。实际上,是成对地在观察。
佛法的奇妙之处在于,让我们学习成对的法;当彻见成对之法后,我们便会了知那单一之法。
而那个单一之法,需要我们自己去领悟。它会“叮”地一下自己生起。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些成对的东西。这些成对的东西,会向我们展示三法印。而那个单一的东西,不展示三法印。所谓的“单一之物”,就是“单一之法”和“单一之心”。因此,在修行时,佛陀才教导要觉知五取蕴。“单一之心”,不属于五取蕴。在阿毗达磨的语言中,称为“大作用心”(mahā-kiriya-citta)。大作用心是阿罗汉的心。我们不会拿它来修毗婆舍那。因为阿罗汉不需要修毗婆舍那。而那些不是阿罗汉的人,也没有“单一之心”可以拿来修毗婆舍那。
因此,我们要学习这些成对的、成组的东西。那么,要选择学习什么呢?任何我们擅长的,就用那个。没错。但最初,如果我们修行还不熟练,或者对法还没有清晰的理解,我们就会固执地认为只有我们走的路才是对的,其他的路我们往往会先排斥掉。这使得每个道场、每个人都心胸狭隘,认为必须用我的方法才能证悟,必须用这种方法才能证悟。就像我们上山,我们相信我们选择走的路是最好的。我们就会往上爬,往上爬。当我们真正到达山顶时,才会发现,哦,原来可以从四面八方上来。可以从四面八方上来。因此,真正的业处是很多的。都在四念住里。也就是,可以从四个方向上来。任何一个方向,只要上来,都能到达山顶。当我们登上山顶后,就会知道,原来可以从四面八方来。我们不会再去排斥其他的方法。
比如我,以前跟隆布敦学习,然后就去森林派的寺院。有些寺院里是年轻的比丘、沙弥,他们问我从哪里学来。我回答说从隆布敦那里学来。他们就嘲笑我。他们告诉我说:“不对,不可能去看心。必须从奢摩他开始,然后来看身。”隆布敦教错了。他们有时甚至称呼隆布敦为“老眼昏花”。这样侮辱长辈。有些长老问我修行方法,我告诉他们我看心,他们就斥责我,说我是邪见。但当我们去拜见那些真正彻知法、证悟了的长辈时,比如隆波帖(Luang Por Test),阿姜摩诃布瓦(Ajahn Maha Bua),或者隆波辛(Luang Por Sim)等等,他们从来不说一个字。他们不会说错了。虽然他们教导寺里的比丘们“Buddho,观身”,但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看心、看念头时,没有一位长老说错了。没有一位。为什么?因为法是相通的。走哪条路都能到达。只要是走在佛陀所设定的原则之内。为什么?因为,无论修习哪个念住,无论是身、受、心,还是法,都会同时了知色法和名法。比如,做身随观念住做得正确,就会见到色法和名法。做受随观念住做得正确,也会见到色法和名法。做心随观念住做得正确,也会见到色法和名法。并非只见到一个。
许多人试图只了知一个。比如,试图了知腹部的起伏,或者了知呼吸,不让心偏离腹部的起伏,不让心偏离呼吸。那是专注所缘,而专注所缘,称为“所缘专注”(ārammaṇūpanijjhāna),那是一种奢摩他业处。但是,如果要修毗婆舍那,就必须从见到身体是一个部分,而心作为纯粹的能知者是另一个部分开始。身体在另一边。比如阿姜念(Ajahn Naeb)的法脉,他教得很好。他教导说:“坐是色法,知是名法;行是色法,知是名法。”这也是分离色法和名法。但实际上,大多数人还是在专注。我见过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专注。如果不专注色法,就专注名法。比如有些修习四威仪的人,了知“坐是色法,知是名法”。长老是这样教的。但实际上坐的时候,就会刻意地坐着不动(隆波做出示范的姿势),坐着等酸痛。当酸痛了,想动了,想动了要先觉知到想动,但先不要动。必须先思考,为什么要动。然后自己回答,因为有必要才动。这样用理智思考后,才可以动。然后就换个姿势,再静静地待着。这不是毗婆舍那。
做这样的练习,如果要问是在修什么业处?说是了知四威仪。了知四威仪,为什么要等感受?站、行、坐、卧,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吗?为什么要坐着等感受?如果这样,那应该是想了知感受吧。也不是。因为感受是一直都存在的,为什么要坐着等它?他又说,了知感受是为了了知心,看它有想换姿势的欲望。哦,那又是心随观念住了。总之,到底在修什么业处?是身随观念住,受随观念住,还是心随观念住?我也不知道。
如果还认为修行业处,只见色法或名法其中之一,或单一的某个,那是理解错了。那是专注了。如果不专注,就会同时见到色法和名法。举个例子,身随观念住,我们觉知身体。我们见到出息的色法,入息的色法。或者我们见到站、行、坐、卧的色法。现在流行腹部起伏,我们就见到腹部起伏的色法,移动的色法。如果仅仅见到色法,那是专注色法。专注色法不是毗婆舍那,那是专注所缘,只能得到奢摩他。因此,后来的修行者大多都ติด在奢摩他里。去哪里都只见ติด在奢摩他里的人,虽然他们都说不修奢摩他。越是这样说,越是ติด在奢摩他里。
因此,如果修行正确,必须同时了知色法和名法。因为它们是一直存在的。比如,看到身体在呼吸,这是色法。觉知到呼吸的心,这是名法。身体站、行、坐、卧,这是色法。觉知身体站、行、坐、卧的心,是名法。必须把色法和名法分开。心是能观者,身体是被观者。身体在动,在移动。当心是能观者时,身与心就会分离开。立刻就分开了。“我”的感觉就不会存在。会立刻看到,身体只是身体的部分,心只是心的部分。身体不再是“我”了。身体不再是“我的自我”,而变成了“我的身体”。看,地位从“我的自我”降级为“我的”了。再继续看下去,就会看到,色法和名法都无法被控制。到某一点,“叮”地一下生起,名色都不是“我”。初果须陀洹就会了知这个实相:色法和名法都不是“我”。并非只了知色法或名法其中之一。
我们的任务就是修习四念住。 当四念住的修习圆满时, 我们的心自然会从苦中解脱, 从烦恼中解脱, 并且日夜都从造作中解脱出来。 空,空,恒时清净。
第三章 禅修须知
隆波帕默于佛历2551年2月16日星期六在是拉差สันติธรรม园林的开示
……今天很多人来。有没有谁没来过?哦,也挺多的。那些没来过的,有没有谁修过腹部起伏的?有吗?腹部起伏……有没有谁修过隆波田法脉的?有吗?……也有。有没有谁修过阿毗达磨法脉的?有吗?阿姜念法脉的?有吗?念“Buddho”的呢?……哦,这个最多。
修习任何禅修法门,都可以。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形式可以是好看的,也可以是不好看的,那只是包装而已。如果我们不是要拿产品去卖,那么形式只是次要的。禅修必须抓住要点。
今天早上有位居士来看我,他跟着一位尊者学习,我非常敬重他。他学习了很多,实践得也很好。他说他能分离色法和名法了,比如看见手在动,知道心是能观者。他做了很多,做得也很好,但没有进步。他就来问我:“为什么我修行没有进步呢?我每天都做,很精进,一天做好几个小时。”
我问他:“你看手的时候,心是怎么样的?”他说:“心就只是看着。”我告诉他:“你再仔细看看,心是不是僵硬的?”他就把心往里看,看到心之后,说:“哦,是的,心是僵硬的。”我说:“你再仔细看看,心是不是在用力?”他观察后说:“是的,心在用力。”我又说:“你再看看,心是不是在专注?”他说:“是的,心在专注。”我说:“你看,心僵硬、用力、专注。这是什么?这是贪心。”有欲望,想看手。有欲望,想分离色法和名法。以贪欲作为禅修的出发点,是行不通的。
修行的核心内容,是断除烦恼。但我们却带着烦恼去修行。带着欲望去修行,想要好,想要平静,想要智慧,这些都是欲望。欲望,就是贪。当我们带着贪欲去修行时,心是不善的。不善的心,是没有力量的。即使有力量,也是不善的力量。不善的心,是不正常的。当心不正常时,我们如何能见到正常的境界呢?
我们修行是为了见到身心的常态,也就是见到身心的三法印。如果我们用一个不正常的心去观照身心,我们是不可能见到真相的。因此,修行必须用正常的心。正常的心,就是既不善也不恶的心,或者是善的心。最好是善的心。善的心,是轻松、柔软、敏捷、适业的,并且在觉知所缘时是正直的。
因此,真正的修行,心必须是善的。如果心是善的,那么当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色、声、香、味、触、法时,心就不会喜欢或不喜欢。喜欢,就是贪;不喜欢,就是嗔。如果心处于善的状态,它就会保持中舍,既不喜欢也不讨厌。这时,心就会有力量,会清醒,会喜悦,会安住。然后,我们再用这颗安住的心去觉知身、觉知心。当身发生任何变化时,我们要觉知;心发生任何变化时,我们也要觉知。
觉知,是为了什么?为了看到真相。身心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它们都是三法印:无常、苦、无我。不断地去觉知,就能看到身是无常、苦、无我;受是无常、苦、无我;想是无常、苦、无我;行是无常、苦、无我;识也是无常、苦、无我。这样去看,看到身心的真相,即它们都具有三法印的特性。当智慧圆满时,心就会放下对身心的执取,解脱就产生了。
修行,要抓住这个核心。修行,是为了放下对身心的执取。我们之所以执取身心,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身心的真相。我们看到的是,身心是“我”,是“我的”。我们之所以有这种错误的见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身心的真相。如果我们能看到身心的真相,即三法印,心就会放下执取。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原则。所以,我们修习任何法门,都必须导向于见到身心的三法印。如果哪个法门不能导向见到三法印,那个法门就不是佛陀的教导,不是通往解脱的道路。
那么,如何才能见到三法印呢?三法印是身心的特性,所以我们必须觉知身、觉知心。但不能带着贪欲去觉知。要以中舍的心去觉知,轻松、自然地去觉知。
比如,我们呼吸。我们看到身体在呼吸,心是能知者。身体不是“我”,呼吸不是“我”。呼吸只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也只是物质的组合,是地、水、火、风四大的组合。心是能知者,它也不是“我”。心只是一个知道的作用,来了又去。
这样轻松地去觉知,不用力,不专注,不期待。只是觉知。当心跑了,我们就知道心跑了。当心生气了,我们就知道心生气了。当心有欲望了,我们就知道心有欲望了。只是这样觉知。
持续地、不间断地觉知下去。这种持续性非常重要。如果断断续续,力量就不够。就像烧水,烧一下,停一下,水永远也烧不开。修行也是一样,必须持续。
但持续,并不意味着要紧张。要以一种放松、舒适的方式去持续。觉知身,觉知心,带着轻松、喜悦的心。
这样修行,心就会慢慢地变得有力量,会安住。当心安住时,智慧就会生起。智慧会自己看到身心的三法印。我们不需要去思考“这是无常,那是苦,那是无我”。智慧会自己看到。
当智慧看到三法印时,心就会感到厌离,会放下。当放下对身心的执取时,苦就熄灭了。这就是修行的全部过程。
所以,无论你修习哪个法门,腹部起伏也好,念“Buddho”也好,动中禅也好,关键在于,是否导向了见到身心的三法印。如果导向了,那就是正确的。如果没有,那就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自己的修行是否正确呢?很简单,观察自己的心。修行之后,烦恼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心是更轻松了还是更沉重了?心是更清明了还是更迷糊了?
如果修行之后,烦恼减少了,心变得轻松、清明,那就是走对了。如果修行之后,烦恼增多了,心变得沉重、迷糊,那就是走错了。
要经常这样检查自己。不要盲目地修行。修行,要有智慧。
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误解了毗婆舍那。以为毗婆舍那,就是去“看”什么东西。毗婆舍那,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用智慧去了知。了知什么?了知身心的真相,即三法印。
毗婆舍那的智慧,不是通过思考得来的。它是通过直接的观察、直接的体验而生起的。
所以,我们必须亲身去实践,去觉知自己的身心。不要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理论很重要,它能给我们指明方向。但最终,我们必须自己去走这条路。
不要害怕犯错。修行,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调整的过程。关键是,我们要有觉知,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知道自己的心处于什么状态。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以正确的心态、正确的方法去修行,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目的地。
现在,你们有什么问题吗?……(问答环节)……
好,时间到了。希望大家都能精进修行,早日离苦得乐。
第四章 解脱道要略
隆波帕默于佛历2551年3月20日星期五在是拉差สันติธรรม园林的开示
……我们有责任行善,然后稻谷会自己结穗。我们有责任去做那些有益的事情,然后有一天,心会自己证得道与果。正如佛陀所教导的那样。没有人能让心证得道与果。心,是它自己证得道果的。我这么说已经说了将近二十年了,但一直没能找到教理的依据来证实。直到前几天,一位长老刚好找到了相关的经文,其中佛陀将修行者比喻为农夫。农夫耕田、播种、灌溉田地,然后稻谷自己结穗。就像修行者必须修习三学(戒、定、慧),然后心会自己生起道与果。
实际上,心是无我的。谁也无法命令心去证悟道果。如果我们能命令心去证悟道果、涅槃,那么心就是有我的了。但我们必须去创造证悟道果的因,那就是修习三学。持续不断地造因,总有一天,当因与果相称时,也就是心在洞察苦蕴(即名色)方面生起了成熟的智慧时,心就会自己证得道与果。
不要说命令心去证悟道果是不可能的,就连命令心生起哪怕一刹那的念,也是命令不了的。那些我们刻意去“规定”出来的念,并非真正的念。“规定”这个词,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压制”。“规定”是高棉语,意思是压制。去压制它,去强迫它。那就是“我慢随眠”(attakilamathanuyoga),是偏向强迫自己的极端。这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有了因,念就会生起。即使是烦恼……
佛法的修学,分为教理(pariyatti)和实践(paṭipatti)两个部分。“教理”是指通过听闻、观察和阅读等不同方式,从他人那里接受知识的传承,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实践的方法。“实践”则是指按照佛陀所教导的方法,亲身去觉知自己的身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产生通达(paṭivedha),即亲自证悟,从而彻底放下对身心的执取,并证入涅槃,那是至高无上的安乐。
心要证得道果涅槃,是通过修习戒学、定学和慧学来达到的。因此,必要的教理学习,就是学习并了解这三件事。而必要的实践,就是修习这三件事。
我们佛教徒真正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这三门功课。第一门功课叫戒学(sīla-sikkhā),学习关于戒律的知识,直到知道怎样做,我们的心才会正常,不被粗重的烦恼所染污。第二门功课叫定学(citta-sikkhā),学习关于心的知识,直到知道怎样做,我们的心才会有力量,安住,成为修习毗婆舍那的工具。第三门功课叫慧学(paññā-sikkhā),学习关于开发智慧的知识,也就是修习毗婆舍那的方法。如果我们修习了戒学、定学和慧学,总有一天,圣道会生起。佛陀将修行者比喻为农夫。农夫耕田,他的职责就是去耕地,去播种,然后给田里引水。水少了就引进来,水多了就排出去。总有一天,稻谷会自己结穗。稻穗有责任结穗,农夫没有责任去结穗。农夫代替不了稻穗去结穗。
戒学
因此,我们要好好检查自己的心。我们还有哪些戒律不圆满,哪些戒律有瑕疵,就要努力去守护。每个人都可能曾经犯过戒,但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要再犯。未来尚未到来。不要去想。要立志于当下,好好地发愿,去守护。不重复犯错。这样就可以了。
曾经有个人,他做虾塘,养虾。他心里很难过,来学习佛法,但怎么学也学不进去。因为每当他学习佛法时,就觉得自己不配学法,因为他在养虾。隆波就告诉他,要把他的生命分成小段。去抓虾的时候,那肯定是恶业。其他时候,没有去抓虾,那时候就可以行善。所以,要把我们的生命分成小段。哪一段犯了错,就让它过去。能避免的就去避免。就像我们,不可能命令它不生起。烦恼,不是在我们掌控之下的。如果有了因,烦恼就会生起;如果没有因,烦恼就不会生起。比如愤怒,它要生起,我们必须先有暴躁的潜在习性,有嗔的习性。然后,去接触到一个不合意的所缘。然后,心就会判断那个所缘,“这不好,不对,不该是我们的”,心这样想等等。然后,心就会造作出愤怒来。如果没有暴躁的潜在习性,就算被骂了三天,也还不会生气。如果暴躁的习性很强,他只是看我们一眼,我们就生气了。有时候,我们想让他看,他却不看,我们又生气了。或者,有暴躁的潜在习性,但遇到的所缘很好,都是些讨人喜欢的人,我们也不会生气。或者,遇到不讨人喜欢的人,但我们没去想,忘了去想,我们也不会生气。看,有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愤怒才会生起。我们所驾驶的汽车,有人在我们面前抢道。我们正在心不在焉,或者正在听隆波的CD,没有注意到他抢道,没有去想,就不会生气。但如果稍微想一下,判断一下,觉得不对,就会生气。或者,判断觉得对,然后就会爱上它。所以,万物皆由因缘而生。没有什么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一切都有因有果。
真正的佛教徒,是充满理性的。但假冒的佛教徒,是没有理性的。比如,认为拜了某个天神就能发财。天神吃饭的地方在哪儿?天神还得让人给他摆祭品,不是吗?不会发财的。拜天神不会发财的。想发财,就要努力工作,并且懂得储蓄,懂得投资,懂得结交善友,懂得过适度的生活。如果不工作,或者工作了却不懂得储蓄,或者交了坏朋友,一起去赌博,或者生活奢侈,超过了自己的经济能力,就算有一百个天神,也不会发财。因与果必须是相符的。想证得道果涅槃,就必须造作能证得道果涅槃的因,那就是修习三学。以戒为基础,能让心更容易安住。以安住的心去觉知名色,直到生起智慧,了知名色的真相,然后放下名色。心就能证入清净解脱,这是通过智慧达成的,而智慧又以戒和正定为基础。
定学
学完了戒,接着就要学习心。佛教徒必须学习心。很多人有偏见,很多人有邪见,说:“不要学心,因为心很难。留到最后再学。要先学身。”他们可能忘了,佛教徒必须学习的第二门功课,名为“定学”。我们要学习自己的心。要了知什么样的心是善的,什么样的心是不善的。要了知什么样的心可以用来修奢摩他,什么样的心可以用来修毗婆舍那。必须了知。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拿不善的心去修奢摩他和毗婆舍那,或者迷失于造作不善心,却以为自己在修行。
有相当多的修行者没有好好学习心法,结果修行错误。举个例子,我们想修行,我们立刻就去规定名色。我们的心就立刻变得沉重起来。比如,我们去规定呼吸,心就变得僵硬起来。规定腹部起伏,心就变得沉重起来。规定脚步,规定手,规定任何东西,心都会变得沉重起来。如果我们学习了心法,学得精通,我们就会知道,沉重的心、沉闷的心、僵硬的心、迟钝的心,这些都是不善心的特征。
为什么修行佛法会产生不善心呢?因为做错了。是贪心在前面引导。想修行那一刻,贪心就生起了。因此,一旦开始修行,真正的念,那种能觉知身、觉知心的念,就不会生起。能做到的,无非是专注身、专注心,这属于我慢随眠,也就是强迫自己。你们注意到了吗?当我们开始修行时,我们会强迫自己。比如,我们从小就呼吸,我们不觉得累。但当我们必须去规定呼吸时,反而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疲惫。我们的腹部,从出生起就在起伏,没什么问题。但当我们来规定腹部时,就变得沉重起来。我们走路逛商场好几个小时都没事,但行禅却不行,全身酸痛,因为走路的姿势不对,去改造了自己的走路姿势。以贪欲为前导的修行,是行不通的。
在阿毗达磨中教导说:“烦恼,是业的近缘。”也就是说,烦恼是导致我们造业的原因,这没错。但在造业的同时,如果有烦恼的驱动,烦恼会与那个造业的行为同时存在。因此,如果我们想修行,然后我们开始修行,在修行的时候,那个欲望仍然存在。当心被欲望,一种不善法所笼罩时,真正的念就不会生起。因为念,是不会与不善心同时生起的。因此,那些我们修行时感到紧张、感到疲惫、感到僵硬、感到痴呆等情况,都是因为做错了。没有好好学习,就迷失于造作不善心、不善业,却以为自己在修善。
但如果心是真正的善,心就会是柔软的,心就会是轻盈的,心就会是敏捷的,心就会是不被烦恼、不被五盖所笼罩的,心会正直地觉知所缘。心会正直、坦诚地觉知,不会去干预。干预,是源于对所呈现的身心境界的喜欢或不喜欢。比如,看到贪心生起,不喜欢它,这是烦恼,是嗔心在干预。看到心中生起平静、宁静,喜欢它,这是烦恼,是贪心在干预。或者生起快乐,努力去维持它,这也是干预的发生。
真正修习毗婆舍那的心,不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修行了,心变得沉重,那是做错了。修行了,心变得僵硬,也是做错了。如果它沉重,就不是轻快(lahutā)。如果它僵硬,就不是柔软(mudutā)。如果它迟钝,修行了就变得迟钝,像个僵尸,你们见过吗?僵尸。有很多修行成这样的人。你们去精神病院看看。那不是我瞎说。如果修行了,心变得僵硬,像个僵尸,那就错了。不对了。不敏捷,不活泼。就是没有适业性(kammaññatā),即不适合工作,也就是不被烦恼所笼罩。善的心,有练达(pāguññatā),即在觉知所缘方面是敏捷、不迟钝的。不善的心,是迟钝的。还有正直(ujukatā),即在觉知方面是正直的,不会去干预。只是觉知,只是看见。
因此,修行者必须观察自己的心,看心是善还是不善。如果心是善的,还要进一步了知,这颗善心适合用来修奢摩他,还是适合用来修毗婆舍那。这件事,我必须先声明,我学习的教理不多,所以我还没有在任何经典中直接找到关于这件事的论述,即用来修奢摩他的心和用来修毗婆舍那的心有何不同。因为当经典论及用来修奢摩他和毗婆舍那的心时,都笼统地称为“与智相应的善心”(mahā-kusala-citta ñāṇa-sampayutta)。但根据我的观察,我发现用来修奢摩他的善心,和用来修毗婆舍那的善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用来修奢摩他的善心,是需要刻意去营造的。而在阿毗达磨的术语中,称为“有行”(sa-saṅkhārika)。而用来修毗婆舍那的善心,是它自己生起的,因为有因让它生起。它的因是什么?是念,也就是心能准确地忆持身心境界。然后念就会自己生起,而不需要刻意去营造。这种自己生起、无需刻意营造的善心,在阿毗达磨的术语中称为“无行”(a-saṅkhārika)。
我实际观察到的一个例子是,当我们要修习奢摩他业处时,我们必须先有修习奢摩他的意愿,然后才刻意地将心导向一个单一的所缘,而这个所缘不能是不善的。直到心紧贴、宁静、安住于那个所缘,并逐步进入精细的层次。比如,我们想让心平静,我们就刻意去觉知呼吸,去觉知腹部的起伏,去觉知脚步的移动。这是刻意去觉知。但真正修习毗婆舍那的心,它必须是念自己生起,觉知名色。我们不必刻意让念生起。如果刻意让念生起,那颗心就不够格,它会有点迟钝。
我们必须勤于创造让念生起的因,也就是勤于觉知身心境界。当念自己生起时,那颗心就具备了高品质。这是因为它是一颗善心,或者是任何不善心,如果它是被引诱而生起的,那么它就是一种力量较弱的善或不善。但是,如果一颗善心或不善心是自己生起的,而不需要被引诱,那么它就是一颗力量强大的善或不善。比如,因为有信仰而布施的人,会比因为被劝说而布施的人获得更大的功德。凭着自己的本性去伤害众生的人,会比为了自卫而伤害众生的人造下更重的恶业,等等。
慧学
时间快到了,我得简短地讲。接着是戒学和定学之后,就是修习慧学。修习慧学的方法,就是以念为工具,去觉知名色/身心当下的状态,并且要以一颗安住的、有正定的心去觉知。看,必须有念和正定。念是觉知到一切呈现在身心之中的境界的工具。在觉知一切呈现于身心之中的境界时,心必须安住,有正定。心才会只是觉知、只是看见,而不会迷失、沉溺于任何所缘之中。如果缺乏正定,智慧就不会生起。
我们持续不断地修习四念住,也就是勤于觉知身,勤于觉知心,勤于觉知境界。持续地去觉知,直到心能够准确地忆持境界,这称为有“坚固的想”(thira-saññā),是念生起的近因。当心所觉知的境界生起时,念就会自己生起,去觉知那个境界,而无需我们邀请,也无需我们刻意让它生起。比如,手一动,我们就觉知到身体。一呼吸,我们就觉知到身体、觉知到心。看腹部起伏,我们就觉知到身体、觉知到心。我们不是去强迫它。我们这样持续地练习。或者念“Buddho”,然后我们就勤于觉知身、觉知心。有一个禅修所缘作为背景就够了。然后就来觉知身、觉知心。这样持续地练习下去,心就能准确地忆持境界。当身体一动,念就生起。心一动,念就生起。它是自己生起的。
当真正的念生起时,心就会生起正定。心会自动安住。因为它在那个当下没有被五盖所笼罩。心就会生起定。当念生起时,心是善的。善的心,会有喜俱受(somanassa-vedanā)或舍俱受(upekkhā-vedanā),这两者都属于乐受的范畴。乐是定的近因。当我们做任何事情有快乐时,我们就会在做那件事时有定。我们有快乐地觉知身,有快乐地觉知心,它就会生起定,也就是在觉知身、觉知心时,心会安住。
这里又得学习了。因为定有两种。一种是正定(sammā-samādhi),即心的安住。另一种是邪定(micchā-samādhi),即心沉溺于所缘之中。安住的心和沉溺的心是不一样的。安住的心,能见到三法印。而沉溺的心,会进去紧贴着所缘。比如,觉知呼吸,心就会流进去和呼吸待在一起。只剩下呼吸,忘记了世界。整个世界只剩下呼吸。心就平静地和呼吸待在一起。觉知腹部起伏,心就流到腹部去。走路行禅,心就流到脚上去。这称为心沉溺于所缘之中。当心进去执着于所缘时,称为“所缘专注”(ārammaṇūpanijjhāna),这是一种奢摩他业处。因此,有些人行禅,走着走着,身体就飘了,身体轻了,身体摇晃了,感觉像有电一样,这都不是毗婆舍那的智慧。毗婆舍那的智慧,是一种智慧的名称,不是身体症状的名称。那些症状是定的结果,是奢摩他的结果。比如我们规定脚步,走着走着;规定腹部;规定呼吸,走着走着,就会产生定,产生喜悦,产生ขนลุกขนชัน(鸡皮疙瘩),身体飘,身体轻,身体摇晃,身体变小,身体变大。身体飘,我曾经听人说,有人真的飘起来了,身体离地而起。那都是喜悦的结果,是定的结果。
因此,我们要了知,哪种心用来修奢摩他,哪种心用来修毗婆舍那。我们因此必须学习定学,要学懂。
如果有了正确的念和正定,智慧就会生起。它会见到三法印。当以一颗具备这种品质的心见到三法印时,它就会震撼、撼动到心。去洗涤烦恼。但如果觉知了却没有达到心,没有达到念,只是用思考去觉知,这样是无法洗涤烦恼的。因为烦恼不在头脑里,烦恼在心里。
因此,有三件事需要学习:学习戒,直到有戒;学习心,直到清楚了知哪种心是善或不善,哪种用来修奢摩他,哪种用来修毗婆舍那;然后来学习开发智慧,觉知到要如实地觉知色法,而对于心,要持续不断地去跟随觉知。但必须以一颗安住的心去跟随觉知,只是觉知、只是看见,也就是要有正定。这样,才能见到名色的三法印。毗婆舍那,不是觉知名色。要记住,毗婆舍那不是觉知名色。有念地觉知名色,还只是奢摩他。必须见到名色的三法印,才是毗婆舍那。也就是见到名色生起แล้วก็ดับไป(生了又灭),见到它有了又没有,见到它没有了又有。这称为见到“无常”(aniccaṃ)。见到所有境界都无法恒住,被逼迫着一直变化,这称为见到“苦相”(dukkha-lakkhaṇā)。见到所有境界都不是“我”。比如色法只是物质,只是四大之聚,不是我,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名法都无法被控制,不是“我”。这称为见到“无我”(anattā)。色法的无我,和名法的无我,角度上有些许不同。色法不是“我”,因为它只是四大之聚。而名法不是“我”,因为无法被真正控制。
要掌握三学的要点。如果掌握了隆波所说的要点,修行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最简单的。简单到我们什么都不用做。除了觉知或看见。也就是看见这个身体在工作,看见这个心在工作。而我们,除了觉知身、觉知心之外,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只是看见,只是觉知。因此,在四念住中,只有一个动词,就是“知”这个词。例如,“出息时知,入息时知”,“站、行、坐、卧时知”,“乐、苦、舍时知”,“心是善或不善时知”。看,修行的动词只有一个词,就是“知”。我们修行,直到我们进入“知”这个词,也就是觉知名色,如其本然地觉知,也就是觉知它的三法印。而不是去规定它。规定,心就会静止,沉溺下去,这是行不通的。这肯定是错误的。那是奢摩他。
好,八点了。今天开示的,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全部范围了。去学习吧。去读《解脱道》这本书,会有点难。但如果坚持听CD,就会读得容易。如果不听CD,直接去读,会有点难。听隆波不断地敲打这个人,敲打那个人,听下去,就会理解《解脱道》。这很奇怪,是吗?好了,请去吃饭吧。(隆波转向一位来访的比丘)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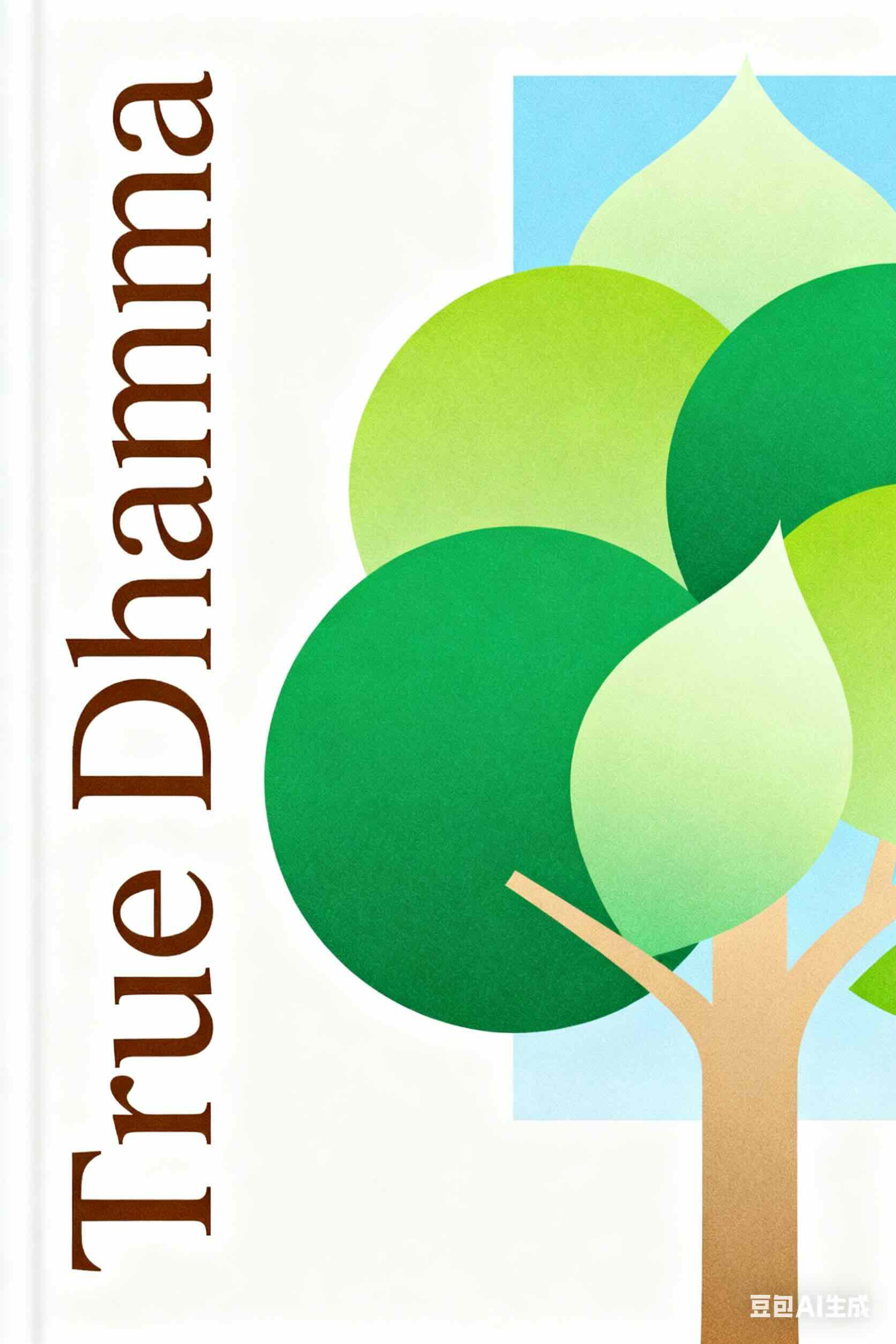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下载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