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圣谛:离苦之道
隆波帕默尊者, 南传上座部佛法 ·Index
四圣谛:离苦之道 - 隆波帕默尊者 - 摘要
何时彻知了苦,即蕴、界、身、心纯粹是苦的集合,并非美好珍贵之物,而是无常、苦、无我的,心便会放下对名色的执取,于是“集”便被自动断除,一旦断除,永不再生。
圣谛
我们对圣谛的职责: 1. 苦,应知。 2. 集,应断。 3. 灭,应证。 4. 道,应修。
圣谛:圣者们的真理
佛陀彻悟了“圣谛”,这是一项无人能辩驳的真理。当佛陀转动法轮,宣告圣谛之时,无人能与之抗衡。
圣谛好比大象的足迹,是陆地上所有动物足迹中最大的。佛陀曾说:“一切走兽的足迹都能被包含在大象的足迹中,同样地,一切善法也都含摄于四圣谛之中。”
佛陀通过修习安般念,让心成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然后他观察缘起,这其实就是观察圣谛,二者是同一回事。
缘起有两条路径:生起之流转与熄灭之还灭。涵盖生起路径的是苦谛与集谛;涵盖熄灭路径的则是灭谛与道谛。因此,圣谛涵盖了全部的佛法。
以我们的心智与法行水平,无法自行了知这一切,必须清晰地聆听佛陀的教导。他教导了圣谛,即苦、集、灭、道。
有时,佛陀会更详细地阐述我们对圣谛应尽的职责:苦应遍知,集应断除,灭应实证,道应修习。
佛陀进一步将每一圣谛分为两个方面:
他教导说,应被了知的“苦”,就是名与色。应被断除的“集”(苦因),他细分为无明与有爱。应被实证的“灭”,他细分为明与解脱。至于应以无上智慧修习的“道”(八正道,虽为一道,含八道支),在实修层面,他细分为奢摩他与毗婆舍那。
佛陀是法王,他能将法从一分为二。若要分为三,他也能做到。例如,他可能将“苦”分为心、心所、色;将“集”分为无明、爱、取;将“灭”分为道、果、涅槃;将八正道的“道”分为戒、定、慧。
我们凡夫俗子不可能自己找到道路,那不是我们能企及的认知范畴。我们只需努力学习名法与色法,这便是“知苦”。当我们听说“苦谛应知”时,若只是去知道“老了”、“病了”,这并不算真正的“知苦”。知道某人老了,某人病了,某人死了,某人正与所爱别离,某人正遭遇怨憎,这些只是世俗谛的苦,其中有“人”老、“人”病、“人”死、“人”别离的概念,这还不是圣谛中的“苦”。
圣谛中的“苦”,没有“人”的概念,只有名法与色法。名法与色法本身,就是苦的实体。 何时彻知了苦,何时便断除了集;何时断除了集,何时便实证了灭;何时实证了灭,何时圣道便生起。因此,苦、集、灭、道虽有四个方面,四种职责,但这四项任务是在同一个心识刹那间完成的。
有一次,一群阿罗汉聚在一起,他们是耶舍尊者的朋友,共有五十五位。在这一生成为阿罗汉之前,他们的主要善行是收集并火化无人认领的尸体。有一天,他们捡到一具刚死去的美丽女子的尸体,尚且新鲜美丽,看着便生起了欲望。火化时,火焰燎过,皮肤剥落,耶舍尊者便唤朋友们来看:“快看,刚才那位美女,现在就像一头斑驳的牛,不再美丽了。” 当尸体烧至白骨,他又再次呼唤朋友来看。这一善行与观察,使他们团队所有人的心中都深深地种下了不净想的种子,明白了女人的美丽并非真实。
当耶舍尊者的波罗蜜成熟时,他半夜醒来,看到他的侍女们横七竖八地睡着,不净想油然而生。看到她们流着口水等丑态,他无法再待下去,便走到了仙人堕处鹿野苑,遇见了佛陀。听闻佛法后,他证得了阿罗汉果。他的朋友们后来寻他而来,也全部证得了阿罗汉果。
其中一位名叫伽梵波提的阿罗汉,在证果后与多位阿罗汉同住。他们每日托钵归来,用斋后便坐下交谈。为何不去修行?因为他们已是阿罗汉,再无修行之事可做。
一位阿罗汉提出一个话题:“我修行时了知到,何时知苦,何时便断集;何时断集,何时便证灭;何时证灭,何时便修道。” 所有在场的阿罗汉都表示赞同。
伽梵波提尊者则说,他曾听佛陀开示道:“何时知苦,即是断集、证灭、修道。何时断集,即是知苦、证灭、修道。何时证灭,即是知苦、断集、修道。何时修道,即是知苦、断集、证灭。” 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可以。由此可见佛陀的智慧圆融无碍。声闻弟子只能从“知苦”这一个角度来看,因此我们也不要自作聪明,想在知苦之前先去证灭。
实际上,佛陀能从四个角度宣说,因为它们发生在同一心识刹那。但在修习八正道中的智慧时,包含了戒、定、慧,我们应从持戒开始,然后修习禅定,也就是训练心安住于自身,不散乱,不呆滞,训练心觉知自身,这便是“有定”。开发智慧,就是了知名法与色法的实相,即分离蕴、界。
当能够分离蕴、界,了知蕴、界、身、心、名、色的实相后,就会明白名色的实相即是三法印(无常、苦、无我),而非不净。如果只是思维修习身体的不净,那不是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必须见到三法印。如果我们想让“道”得以培育,就要通过“知苦”来实现。当我们彻见蕴、界为三法印时,那便是对苦的透彻了知。
何时彻知了苦,即蕴、界、身、心纯粹是苦的集合,并非美好珍贵之物,而是无常、苦、无我的,心便会放下对名色的执取,于是“集”便被自动断除,一旦断除,永不再生。
因此,知苦之时,便是断集之时。例如,我们了知到名色即是苦的实相,那么想要名色快乐、想要名色离苦的欲望(集)便不会生起。因为智慧已经明了,知道名色是苦,想让它不苦是不可能的;想让身心快乐也是不可能的。最终,因为洞察实相,拥有智慧,彻知了苦,便能摧毁欲望(爱),断除集。若能断除集,当心无爱染时,心便会见到涅槃。正是爱染障蔽了心,使其无法见到涅槃。若能彻底断除爱染,便能见到涅槃,因为涅槃即是爱染灭尽的境界。
彻知苦,即是在培育道。彻知身心、名色是苦,并非美好珍贵之物,就会断除集,即断除爱。爱彻底熄灭之时,便能了知涅槃——那无爱的境界。
因此,对苦、集、灭、道的理解,源于我们修习道,即时常以正念觉知身心。但这种觉知,必须基于一颗稳固、中舍的心,也就是一颗有定的心,不是沉寂的定,而是稳固的定。
要彻见圣谛,必须有正念,如实觉知身心,且要以一颗稳固且中舍的心去觉知,持续不断地观察身的工作、心的工作。 直至某天,心会彻悟,但这彻悟是循序渐進的。智慧并非一蹴可几,瞬间就看到五蕴皆苦。最初,智慧先生起,见到五蕴并非人、非众生、非我、非他,只是生灭不已的法,其中没有一个恒常的“自我”。仅凭这一洞见,便可证得须陀洹果。
须陀洹的初步智慧,是见到“凡是生起之法,皆有灭去之性”这一实相,了知在蕴、界、身、心中,没有一个恒常的“自我”。
之后,继续修行,培育正念,以稳固且中舍的心,如实觉知身心。心会了知到更微细深奥的实相,会见到这个身体纯粹是苦,并非像过去所想的那样时而苦时而乐。
如今我们认为身体时而苦时而乐,所以我们还在逃避苦、追求乐,因为还有选择的余地,心就会不停地挣扎,永无休止地造作。于是,爱身、惜身,希望它快乐,希望它离苦,心便不断地折腾,越折腾造作越多,心的痛苦也越重。
直到智慧成熟,才会发现这个身体并非时苦时乐,实际上,它只是在“大苦”与“小苦”之间变换。见到这一点,心便不再执取身体。
所谓的身体,可以分解为眼、耳、鼻、舌、身。心不执取眼,也就不执取耳、鼻、舌、身。当不执取眼时,自然也不会执取色、声、香、味、触。连眼睛都不执取了,怎会去执取色尘呢?心也不会执取色,因为色是外在的,不如根门那般值得执取。比如我们,若要在看见美色与失明之间选择,我们宁愿不要美色,因为我们更爱惜眼睛。现在连眼睛都不爱了,又怎会去爱色呢?
因此,心会放下对色、声、香、味、触的执取。(触,即碰触身体之物,包括冷、热、软、硬、紧、动,也就是地、风、火三界。至于水界,是原子间的引力,需由心来了知。)若不执取眼,便不执取色。见到任何色,既不贪爱,也不厌恶,贪欲与嗔恚便不生起。连耳朵都不爱了,听到声音时,便不会迷恋声音,不会对某种声音喜欢,对另一种声音不喜欢,贪欲与嗔恚便不生起。(贪欲,即对色、声、香、味、触的喜爱;嗔恚,即不喜爱。)
阿那含圣者会感到,若心安住于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状态,便有乐受;若心迷失,流向眼、耳、鼻、舌、身,便有苦受。因此,心仍有两种状态:乐的心与苦的心。这仍未见证实相,如同我们凡夫认为身体时而乐时而苦。
阿那含圣者已见到身体是在“大苦”与“小苦”间变换,但仍认为心是时而乐时而苦。若心有欲望、有执取,流向眼、耳、鼻、舌、身的所缘,便有苦受;若心安住于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状态,便有乐受。因此,他会尽全力守护这颗心。
祖师大德曾教导,修行到此阶段,会珍视、爱护这颗心,甚于眼镜王蛇守护它的蛋。他珍爱心,因为感觉心能带来快乐。他必须继续修行,以稳固且中舍的心,如实觉知身心。看,还是用同样的方法。但此阶段的修行,会主要集中在心上,因为身体的实相已经彻见。于是,修行变为:以一颗稳固且中舍的心,如实觉知心。
观察到某个阶段,将会见到一个实相:这颗心,纯粹是苦,并非时而苦时而乐。 这颗心本身,无一可依。那被认为是美好珍贵、被阿那含圣者守护的“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之心,正是带着无明的心。
当修行继续,正念、定、慧具足时,将会见到这颗心实不可依,因为它不恒常,它会生起,也会熄灭。它不恒常,仍受三法印支配。凡受三法印支配之物,皆不可依。但具有独特“自相”之物,则可为依怙,那就是涅槃。涅槃超越了无常、苦,因为它是恒常、快乐的,但它也是无我的,即无人能拥有它,也不受任何人掌控。
隆布敦曾教导隆波帕默:“若有一日,你见到心与周遭的自然现象实为一体,那一天,你将离苦。”
我们通常认为心与周遭的自然现象是两回事。但当有一天我们了知,这颗心与周遭的自然现象实为一体,都是外在的、无主之物,同样地无主,便会彻底放下心。
证得阿罗汉果的圣者,有些是见到心的无常,有些是见到心的苦,有些是见到心的无我,方式不尽相同,但结果一样:他们都放下了心,不再执取心,因为他们见到了心之不可依,无有实义。
我们修行,从始至终都必须开发智慧。佛陀教导:“众生因智慧而得清净。”智慧是循序渐進地彻见实相。
阿说示尊者教导优波提舍(即后来的舍利弗尊者),当时他还是个外道修行者。起初,舍利弗向阿说示尊者请法,尊者说自己刚出家,所知甚少。
优波提舍说:“知道多少就说多少,简短即可,不必多言。理解是我的事,您的责任只是开示。” 于是,阿说示尊者说:“诸法从因生,如来说其因;诸法从因灭,是大沙门说。”
听闻此偈,优波提舍当下便初步了悟了圣谛,证得须陀洹果。
我们听了这话,并未证悟,但舍利弗尊者听后,便初步理解了圣谛。“诸法从因生”说的是什么?名法与色法由因而生,名色即是苦的实体,这便是“知苦”。学习不在别处,就在这因缘和合之法本身。因缘和合之法,即是名法与色法。色法有其生因,名法亦有其生因。“诸法从因生”这一句,即是教导要了知苦。
“如来说其因”,这个“因”即是集谛。他了知万物并非凭空而生,必有其因。
“诸法从因灭”,法的熄灭即是名色的熄灭,也就是涅槃。
因此,阿说示尊者的偈语涵盖了多条圣谛。“诸法从因生”即是“苦谛”;如来“说其因”,即是“集谛”;“诸法从因灭”,即是“灭谛”。大沙门如是说,那“道谛”在哪里?了知苦而断除集,实证灭的过程,即是修习道。看,舍利弗尊者那样的智慧,一听便懂。
舍利弗尊者是在听闻佛陀教导“受”时,才彻底彻见圣谛。而目犍连尊者去请教佛陀时,佛陀也同样教导了关于“受”的法门。佛陀说,了知“受”是趣向于“不执取世间一物”的最快捷径。佛法的核心便是:“诸法实相,不应执取。”
我们为何会执取诸法?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能带来快乐与痛苦。当痛苦时,我们会执取吗?若无足够的智慧,是的,我们会执取。想要离苦,正是因为我们执取名色为“我”或“我所有”。当名色生起痛苦时,我们便想让它离苦。当名色带来快乐时,我们便执取它,希望它能长久。
我们感觉身体时而乐时而苦,对吗?有谁感觉身体百分之九十是乐,百分之十是苦吗?若见乐多苦少,便会长久沉沦于世间。但我们尚未见到它百分之百是苦。若能见到名色百分之百是苦,才能放下名色。
现在我们仍有选择,仍见到身时而乐时而苦,故不肯放手。但若见到此身纯粹是苦,便不执取身,即证阿那含果。那么我们的心呢?若能见到心纯粹是苦,便不执取心。苦的终点,就在于不执取心。
隆波帕默最后一次拜见隆布敦是在他圆寂前的三十六天。隆布敦嘱咐他要记住:“见知者,毁知者;见心,毁心,方能达至究竟清净。” 因此,修行的终极目标在于摧毁“知者”,摧毁“心”。但这句话很危险,若理解不当,会真的去试图摧毁它。我们没有责任去摧毁五蕴,五蕴有因则生,无因则灭。所谓“摧毁知者,摧毁心”,意指不执取知者,不执取心。 这是隆波帕默从隆布敦那里听来的教诲,后来隆波布特·塔尼哟又为他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第一章 苦
这个世界充满问题, 人们充满痛苦。 若无正念与智慧,便无法分辨 问题与痛苦是两回事。 生命中充满了无常, 若心能接纳“世间一切皆无常”的实相, 心便不苦。 问题归问题,而心不苦。
佛法中的“苦”
佛陀曾开示过许多难得之事。例如,能生而为人且诸根具足,如我们这般,是难得的;生而为人后,能遇到善友,即有戒有德之人,也是难得的;遇到之后,能生起信心去亲近,是难得的;亲近之后,能听闻佛法,是难得的;听闻之后,能如法修行,更是难上加难。
初学修行时,会感到极大的快乐,无所事事也感到快乐。那快乐如微风般轻轻拂过,整日涌现。每当有正念时,便有快乐。但随着正念与智慧的增长,情况会发生变化。心不再像最初那样充满飘飘然的快乐,而是开始更多地看到苦。越是修行,越是看到更多的苦,这很奇特。
当我们觉知自身,心安住于身心时,为何会快乐?因为那是奢摩他,是有定的奢摩他。心安住于身心,便有快乐。
但到了开发智慧的阶段,那是“知苦”的阶段,而非享受快乐的阶段。当我们开始开发智慧,会见到各种各样的苦在身心中不断地轮转,此时见到的不再是乐,而是苦。
苦有多种形式、多个层次。在教理上,苦被分为十种,但作为修行者,我们只需了知几种苦便已足够。最粗显的苦称为“苦受”,如生病、疼痛、酸胀、过冷、过热、饥饿等,这些都是苦。有身苦,有心苦,这都属于“苦受”,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人都曾经历,动物亦有身心之苦。
如果我们修行,就会看到无数的苦受。坐着会酸,吸气是苦,呼气也是苦。若我们的正念足够快,正念与智慧足够强,就会见到我们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呼吸,只是为了解除痛苦而已。之所以不停变换威仪,也只是为了解除痛苦。持续吸气是苦,必须呼气来解苦;持续呼气也是苦,必须吸气来解苦。
久坐会酸痛,是苦,就必须变换威仪,左右移动,或站起,或行走,或再坐下,累极了便躺下。变换威仪,是为了解除痛苦。
心也是如此。心中不断有苦生起,便会挣扎着去寻找快乐。每当欲望生起时,痛苦便随之而来,但我们看不见,只觉得不舒服。不舒服了,就去寻找愉悦的所缘来喂养它,去看电影、听音乐、与朋友聊天、看东看西,或找本书来消遣,或去喝酒,不断变换所缘。实际上,这都是在寻求快乐,逃避痛苦。心,本无快乐可言。
持续地觉知、观察,会发现任何所缘都只是暂时的,没有一个能持久。变换到某个威仪,以为会舒服,但也不舒服,也无法持久。心也是一样,接触到某个所缘,以为会舒服,但也只是片刻的舒适,很快又无法忍受。万事万物皆无法恒常持久,这种无法持久的状态,便是另一种苦,称为“苦相”,这已不是苦受了。
“苦相”指的是万事万物皆无法恒常。若它们能恒常,那痛苦会更重,会生起更剧烈的苦受。
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变化,并非恒定。当我们修行日深,不仅会看到身体的苦,更会见到身心中生起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生起后便会消失。例如坐着,坐姿无法持久,它被苦受逼迫,且具有苦相,即无法长久保持坐姿,必须换成卧姿。卧姿也无法持久,又必须再换。
快乐无法持久,生起后不久便须改变。因此,快乐也具有苦相,即它无法恒常。 我们的正念与智慧开始成熟,甚至能见到快乐也是苦的一种。见到苦受,人人都能,那是世俗之事。而见到苦相,则已进入毗婆舍那的修行。若进入毗婆舍那,必会见到名色的三法印(无常、苦、无我)。若未见三法印,即使见到名色,也未真正进入毗婆舍那。
当我们持续观察,对苦的洞见会越来越微细。在见到苦相的阶段,便已可能证悟,可证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因为见到了苦。
这个世界充满问题,人们充满痛苦。若无正念与智慧,便无法分辨问题与痛苦是两回事。世界是无常的,它在不断变动,问题也随之不断产生。例如健康,我们悉心维护,不久又会生病,因为它无常。
生命中充满了无常。若心能接纳“世间一切皆无常”的实相,心便不苦。问题归问题,而心不苦。若无法接纳世界无常的实相,当问题出现时,心便会苦。这取决于我们的心能否接纳。
我们来修习毗婆舍那,正是为了见到世界、生命、身心的实相,见到它们是无常的。若心能接纳,连这个身心都无常,那所谓的“我所有”便毫无意义,只是暂时的依附物罢了。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房子、我的车、我的工作,我们有太多的“我的”,但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依附。
若有智慧,便会了知,我们真正的要务并非维护这些无常之物。无论投入多少,辛苦多少,它们终将变异。
因此,我们来训练自己的心,让它能够接纳实相。实相就是:万事万物皆无常,万事万物皆在不断变异,并非恒定。 要带领我们的心,去时常、频繁、长久地观察这个实相。
到了阿那含的境界,将会见到此身纯粹是苦。我们凡夫尚未见到,我们仍认为身体时而苦时而乐,心时而苦时而乐。阿那含圣者已见到此身纯粹是苦,因此,他不再对身有任何迷恋。
何为身?眼、耳、鼻、舌、身,此为身。当不迷恋眼、耳、鼻、舌、身时,连眼睛都不迷恋了,自然也就不迷恋色、声、香、味、触(碰触身体之物)。不迷恋色,便对色无有喜恶,对色的贪欲与嗔恚便不生。不迷恋声,便对声无有喜恶,对声的贪欲与嗔恚便不生……
如此持续修行,持续观苦,最终心会圆满,不再渴求外在的所缘。外在的所缘有何可取?它们纯然是苦。心不再渴求外在所缘,不攀缘,不散乱于外境,因为那里纯然是苦。
当心不攀缘,心便宁静、稳固、明亮,成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心中只有快乐。因此,阿那含圣者视身为纯苦,不执取身,但执取心。其实,从须陀洹阶段起,他已知心非我,知其为暂借世间之物,但因为它能带来快乐,便迷恋不舍,不愿归还世间,也看不到归还的途径。修行至此,便是决断之时:如何才能放下此心?
若持续修行,直到感觉心缺少了某样东西,因此无法放下心,即使放下,片刻又会拾起,并非真正放下。心中只知缺少,却不知缺少什么。持续修行,终有一日会明白,缺少的是对圣谛的理解,尚未见到心本身即是苦。他认为心时而乐时而苦,若修行得当,只见心有乐,无有苦,无法见到心本身即是苦,因为尚未见到“知者之心”的三法印。
若能见到“知者之心”的三法印,才能了悟实相:心本身也处于苦之中,处于苦的境界。 当我们彻见此身是苦,此心是苦,这便是了悟“苦圣谛”。何日见到心是苦,那日才算真正彻知了“苦”。 只有当我们彻见圣谛时,此境界才会生起。
佛陀教导苦圣谛说:“简而言之,五取蕴即是苦。”五蕴概括起来就是名法与色法。我们必须见到名色是苦,才能放下名色。若能放下名色,便能离苦。
最初,我们听说生、老、病、死是苦,便以为是“人”在生、老、病、死,是“人”在受苦。
当我们修行更进一步,会感到不是“人”在生老病死受苦,而是我们若执取五蕴,便会受苦。会这样感觉。
当听到“简而言之,五取蕴即是苦”,便会认为,若对五蕴有执取,才会苦;若只有五蕴而无执取,则不苦。会这样理解。此时,已不再认为是“人”在受苦,不是“人”生、“人”老、“人”病、“人”死,而是“我的”五蕴生、“我的”五蕴老、“我的”五蕴病、“我的”五蕴死,才会苦。理解已发生变化。
再继续修行,便会见到,五蕴本身即是苦。无论心有无欲望,有无执取,五蕴本身就是苦的实体。
所以佛陀说,简而言之,五取蕴即是苦。
“取蕴”一词,并非指“被执取的蕴”,而是指“能作为执取之所缘的蕴”,也就是我们凡夫所拥有的五蕴。
某些蕴不属于取蕴,例如出世间心(道心、果心),它们不属于取蕴,因此不能作为毗婆舍那的所缘,因为它们不是苦的实体。
并非所有五蕴都是苦,唯有被称为“取蕴”的五蕴,即能被执取、能作为执取之所缘的五蕴,才是苦的实体。并非执取之后,五蕴才变成苦。
事实上,所有取蕴皆是苦。无论执取与否,它本身即是苦。
由修行而来的理解,极其微细。仅仅阅读,以为理解了,实则谬之千里。
若理解仅停留在“有欲望、有执取,便有苦;执取五蕴便苦”,我们便会致力于如何不执取五蕴,寻找不执取的方法。
其他宗教也在寻求不执取的方法。例如那些苦行者,他们爱惜身体吗?他们折磨身体,好让自己不爱它。心想吃,便折磨它不给吃。想尽办法折磨,不随顺烦恼,试图去控制那想要执取名色的心。这都是因为对圣谛的理解不够透彻,最终导致修行方法的偏差。
当我们认为“有欲望、有执取便苦”,便会想方设法消除欲望。想吃,便不吃,折磨它,好让欲望不再生起,直接去对治欲望本身。
若能透彻理解佛陀的教导,便会了知,蕴本身即是苦。 它并非时而苦时而乐,而是纯粹的苦,只有“大苦”与“小苦”之分。
若彻知了苦,那想让蕴快乐的欲望便不会生起,想让蕴离苦的欲望也不会生起。 想让它快乐?为何如此愚痴?它不可能快乐,因为它本身即是苦。想让它离苦?为何如此愚痴?它终究是苦,无从逃离。
所有的欲望,不过如此。所谓的“一千五百烦恼,一百零八爱”,其实就是“想让蕴快乐,想让蕴离苦”,概括起来就是“乐爱憎苦”。
一旦了知蕴的实相,欲望便自行熄灭。不必折磨身心去ดับ爱,只需彻知苦,爱便会自动熄灭。
若能理解这一点,理解便会极其微细。心会主动将蕴归还给世界。当心见到蕴并非美好珍贵之物,此蕴纯粹是苦,连心本身也是纯粹的苦——心也属于蕴,属于识蕴。当它放下蕴,便再无物可执取,于是便解脱了五取蕴。五取蕴仍在那里,归于世界,不必去摧毁它。它有因则生,无因则灭,无法掌控。但心已不再执取它。心之所以不执取,是因为彻知了苦,了知所有蕴皆是苦的实体。
因此,“知苦”是佛教修行的最重要之事。不仅仅是打坐,期望通过持续打坐而离苦,那是不可能的。打坐只会创造出更微细的生命境界。除了“知苦”,再无他法可见道。
第二章 集
每当欲望生起,痛苦便随之而来。 因此佛陀教导,爱是苦的起因。
若要彻底根除爱, 若要彻底断除集,必须了知苦。 因此说,何时知苦,何时便断集。
欲望是苦的起因
所有的痛苦,皆源于我们的心无法接纳已发生的境界。若能接纳,则不甚苦;若不能接纳,则痛苦万分。
不仅是负面的境界,正面的境界亦然。若还无法接纳“不够好”、“不够快乐”、“不够富有”、“不够有权势”、“尚未证得道果”,此时没有便想要有;已有的又想让它消失,便苦了。
最终,苦从何而来?苦,源于欲望。
不想老,却老了;不想病,却病了;不想死,却死了。想年轻,却不年轻了。有所求而不得,便是苦。有欲望,便是苦。
我们来修习毗婆舍那,直至心能接纳一个实相:万事万物,无论是色法还是名法,都无法真正被掌控。
若心能接纳,色法如此存在,便能接纳;此色法消失,也能接纳。名法如此存在,便能接纳;此名法消失,也能接纳。此色法生起或不生起,皆能接纳;此名法生起或不生起,皆能接纳。
万事万物,无论生、住、灭,若能接纳,则不甚苦。若不能接纳,心中便生起欲望(爱),想让它变成别的样子,于是便苦。
欲望有多种,例如:没有的,想要有;已有的,想让它永存;或想让它消失。
每当欲望生起,痛苦便随之而来。因此佛陀教导,爱是苦的起因。
我们来学习,是为了见到一个实相:所有境界皆无法阻止、无法掌控、无法命令、不在掌控之中。要持续这样观察。
因此,无论发生什么,心都能接纳。会老,能接纳;会病,会死,也能接纳。因为每当心中生起欲望,痛苦便随之而来。
想快点长大成人,但一长青春痘就不高兴了。只想取其一面,另一面却不要,只选择自己喜欢的一面。要长大,就得长青春痘;不长大,自然没有青春痘。心一旦生起欲望,便有了痛苦。
欲望源于无知,不了知、不见生命、蕴、界、身、心、名、色的实相,即它们皆是无常、苦、无我。
因此,若要彻底战胜它,必须战斗至智慧生起,见到蕴、界、身、心、名、色的实相。若能如此见到名色是无常、苦、无我,见到得清清楚楚,欲望便不会再生。
知道终将老去,老了便是寻常事;知道终将生病,病了也是寻常事;知道终将死去,死了也是寻常事。知道终将与所爱别离,别离了也是寻常事。知道终将不时遭遇不如意事,遭遇了也能接纳,也是寻常事。看,心已回归平常。
何时回归平常,心便离苦,心便不再挣扎。
因此,若想彻底断除爱,必须有智慧,见到名色、蕴、界的实相是三法印。见到名色、蕴、界是三法印,是苦的实体,并非值得执取的珍宝,这便是对“苦”的透彻了知。彻知苦者,必有“明”来破除“无明”。
爱的根源,正是无明。若能破除无明,便能彻底根除爱,爱便不会再生。但若无明未除,我们仍认为此身此心是珍宝,仍然爱它、惜它,欲望便会生起。仍爱身,身老了便不愿它老;身病了便不愿它病;身死了便不愿它死。
心亦然,只想取乐,只想取微细的所缘,不愿受苦,不愿接触粗糙之物,这都是因为不见实相。
若要彻底根除爱,若要彻底断除集,必须了知苦。因此说,何时知苦,何时便断集,这是自动发生的。 此番洗涤,一了百了,无需再洗。但若知苦不彻,爱仍会不时生起,此时便需以正念与智慧来对治,因为尚无“明”可与之抗衡。
“明”,即了知圣谛。若“明”不足,便先以正念、智慧来对治。例如,心中生起欲望,觉知到它。欲望,实为爱。此爱的法相,即是贪。但“贪”扮演两个角色:一是作为烦恼,属于苦谛;另一是作为欲望,即“爱”,属于集谛。
因此,“贪”兼具两职。若是普通的、微弱的贪,则归于苦谛,应去了知它。若是强烈的贪,则成为“爱”。若强烈至极,则称为“取”,其本质仍是强烈的贪。
若我们有正念,能觉知到生起的爱,爱便能ดับ。但只是暂时ดับ,爱的因——无明尚在,它很快又会再生。就像我们有些人去逛街,看到新款手机便想买,觉知到想买的心,欲望便ดับ。欲望消失了,转头再看,又想买了。
因此,若以正念对治,只能一次次地对治。正念生起,爱便ดับ;失去正念,爱又再生,并非永久。必须破除无明,才能永久根除爱。
观察有欲望的心而贪欲ดับ去,实则是贪欲的因ดับ了。即使不观察心,去看别的东西,那个贪欲也会ดับ。但我们回观自心,其益处在于能亲见烦恼生起,烦恼消失。这一点对修行大有裨益。其实,转去看别的东西也可以。例如,正想买手机,又带着孩子,孩子想买玩具,你转而去骂孩子,没再看手机,想买手机的欲望便ดับ了,代之而起的是想打孩子的欲望。
烦恼本身并无特别之处,它也是因缘生灭。有因则生,无因则ดับ。但当烦恼生起时,回观心中的烦恼,是很好的修行方法。将来我们会见到,心中生起的一切,皆是暂时的。乐、苦、善、恶,皆是暂时的。将来无论心中生起什么,我们都不会因此而苦。
回观自心是好事,因为烦恼生于心,善法生于心,道果亦生于心,不生于别处。要常来观察此处,恶法才会消失,善法才会增长,道果才会生起。
第三章 灭
何日我们的心脱离了爱,那日便会见到涅槃。
涅槃就在眼前, 只是我们自己看不见。 不必去别处寻找涅槃。 持续地修行,培育正念、定、慧, 直至心的造作完全止息。 当心以智慧超越了造作, 便会见到涅槃。 我们整日与涅槃擦肩而过,却视而不见。
灭即是涅槃
要守护并传承佛法,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佛教是属于意志坚强者的宗教,是需要真正自力更生的宗教,是相信业与业果、一切皆需亲身去做的宗教。它难以理解,并且极大地挑战了我们的固有观念。
其他的信仰体系,通常教导说,若我们遵循其教诲,终有一日将获得永生。人人都渴望永生,但佛教却说“无我”,听来令人沮丧。
谁读过《朝圣者伽摩尼》的故事?伽摩尼渴望见到佛陀,四处寻访,希望能听闻永生之法。当他终于见到佛陀,佛陀却教导他“无我”,他无法接受。因为在“自我”的深处,无论人与众生多么艰难困苦,都仍然珍爱着这个“自我”,因为它仍有其甘美之处,尚未见到它的苦与过患。
而佛陀教导我们要放下“自我”,要回观身,回观心,回观这个所谓的“我”,见到其中只有苦与过患。当见到所谓的“我”,即此身心的苦与过患后,心便会放下,不再执取此身心。当心放下,不再执取身心时,身体的苦便无法侵入我们的心。
心中有造作,无论生起什么,都不执取,造作生起后便任其流过,不染污心,无法触及心。就像阳光穿过虚空,虚空不会因此变热,它依然如故,因为虚空不执取阳光,不像地球的大气层,能因物质的相互作用而储存热量。当不执取身心时,万事万物便只是流过,了无痕迹。
这非常困难,因为人人都只知道依赖身心而得的快乐,我们不知道超越身心的快乐是何种滋味,连想象都无法想象。并且,超越身心的方式也与世俗的超越不同。世间众生,都执着于二元对立。当此身心存在时,若要超越它,便认为必须让它不存在,在“有”与“无”的两极间摇摆。
佛陀的法,深奥微细,难以思议,既“有”又“无”,难以理解,极大地违逆了烦恼的习性。
五蕴并非不存在,身体并非不存在。若认为“无我”即是断灭虚无,便是邪见。
佛陀的法难以理解,即:有因则有,因灭则灭。无因则无。 因为有因,所以有果;因为无因,所以无果。万事万物,皆依因果相互依存。
因此,并非说结果是“有”或“无”。有人说一切皆空,五蕴空,涅槃后一切断灭,这便落入了“无”的极端。
其他人则试图教导“恒有”,认为有某种永恒不灭之物。佛教不谈“恒有”或“永灭”,只说:有因则有,无因则无。 这更难理解。
例如我们,想到死亡时,是否会想两件事:要么死后重生,要么死后断灭。总是落入这两个极端。
“有因则有,无因则无”是难以理解的。何为因?贪、嗔、痴是因;无贪、无嗔、无痴亦是因。因有两面:恶因与善因。恶因导致恶的造作,善因导致善的造作,并非一无所有。
因此,如果我们打坐、经行、布施、持戒,便能涅槃吗?我们造作善因,便会生于善的境界,这与涅槃是两回事。这里面有微细深奥的究竟实相,并非凭空想象的哲学。
若我们修行,便能了悟这究竟实相。万物由因而生,无因则不生。若因已生起,后来因又不恒常,因会ดับ。若因ดับ,果也随之ดับ。因此,没有一个所谓的恒常“自我”。它只是在有因时暂时存在,因灭时便随之ดับ。这正处于“有”与“无”的中间,既非恒有,也非断灭。
万事万物,有因则有,无因则无。世间的一切,皆遵循此法则。即使是房屋失火,也无人能直接熄灭火焰本身。“火”是果,火的“因”是高温等条件。灭火时,我们是熄灭火的因,而非火本身。我们用水浇灌,降低温度,火才熄灭。
当我们想灭苦时,我们不是去ดับ苦本身,而是去ดับ苦的因。 苦的实体即是五蕴。五蕴有因则生,无因则不生。若因已生起,后来因ดับ,五蕴也随之ดับ。因此,我们无法ดับ五蕴,必须ดับ五蕴的因,即ดับ我们心中导致再生的种子。
最微细深奥的种子,名为“无明”。无明是种子,如同芒果核中的胚芽。我们吃掉果肉,剩下果核,核中有能发芽的胚芽。无明便是这种子,心便是那果核。心中有种子,即心中有无明,这颗心便还能再生,再生出完整的五蕴,如同芒果核中的一个胚芽能长成一棵结满果实的大树。
因此,若要真正摧毁“生”,必须摧毁它的种子,而非芒果核本身。即使摧毁了芒果核,如今科技发达,还能用基因、DNA来培育。所以,要摧毁,必须摧毁生的根源,即无明。
无明是什么?无明即是不了知实相,不彻见实相的邪见,即不了知“五蕴是苦”这一实相。 因为我们不了知五蕴是苦,反而认为它是美好珍贵之物,所以我们爱它、惜它。
佛陀与圣者们教导我们不要执取五蕴,因为执取五蕴便是苦。我们不信,难以相信。我们反而认为必须拥有五蕴,并且要好好经营它,才能快乐。
何日我们的心脱离了爱,那日便会见到涅槃。爱会驱使心不断地挣扎造作。何时爱尽,何时便超越造作。 爱尽,称为“离染”;造作尽,称为“无为”。这都是同一回事。
涅槃就在眼前,只是我们自己看不见。不必去别处寻找涅槃。持续地修行,培育正念、定、慧,直至心的造作完全止息。当心以智慧超越了造作,便会见到涅槃。我们整日与涅槃擦肩而过,却视而不见。
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心的品质不够。我们的心品质如何,我们看到的世界便如何;我们的心品质如何,我们看到的法便如何。谁曾伤心失意过?失恋时,是否感觉整个世界都黯然失色?我们一人伤心,却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悲伤。当我们的心开朗起来,又觉得整个世界都阳光明媚。正是这颗心,造作出了世界。心是怎样,它便创造出怎样的世界。若心超越了造作,我们便会见到那无为的境界,便会见到涅槃,并体验到至高的安乐。
涅槃有主人吗?没有。它自古以来便如是存在。当智慧生起,放下心,即是放下所有五蕴,还剩下什么?另一种境界会生起。那境界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从未见过。
问:它是否像蕴、界那样存在?答:不是。若涅槃后仍以蕴、界的形式存在,如同一个“涅槃世界”,那便是“常见”的邪见。若涅槃后一切断灭,一无所有,那便是“断见”的邪见。实则有一种“法界”存在,心会散开,与虚空融为一体,与宇宙的空性合一,称为“涅槃”。这是祖师大德们的教导。
有人说隆布敦教导观心,是保持心宁静、空无,念头生起便扫除,还说阿罗汉的心是永恒光明、空寂的。实际上,若仍有内外之分,仍有二元对立之法,那绝非隆布敦的教导。那仍是二元之法,非“一心”,而是“二心”,有内心,有外心。
若心为一,心与法为一体,那是在爱已尽、已证涅槃的境界。心会达到清净,法亦是清净,心亦是清净。忆念佛陀,即是忆念清净。佛、法、僧皆是清净,是同一清净。唯有一事,声闻弟子与佛陀平等,即是清净。会感到,见到的是同一体,无有分别。
当佛、法、僧与心融为一体时,必须是已证涅槃。心会消融,无边、无界、无点、无形、无所住,消融于涅槃,与宇宙的空性合一,称为涅槃。
要证得涅槃,必须如实了知名色,从而断除对名色的欲望,直至断除对名色的执取。断除欲望,便能证得涅槃。心会与涅槃合一,与空性合一,不执取任何事物,空寂如是。有时,这被称为“法界”。
像阿姜摩诃布瓦等祖师,称安住于涅槃的心境为“法界”。隆布敦称之为“一心”。已故僧王(智护尊者)称此境界为“识界”。佛使比丘称此境界为“本来清净心”。隆波帖称此境界为“心”。隆波布达称之为“一心”。各位祖师所言,实为同一境界,只是世俗谛的名称不同。若我们不修行,便无法理解,只觉得各位祖师所说不同,那是执着于言语了。
我们有些人误解,以为每个众生、每个人的心,都有趣向涅槃、自然流向涅槃的趋势。实际上,佛陀并非如此教导。
有一次,佛陀与众多比丘在恒河边,他指着河中漂浮的木头说:“诸比丘,若这块漂浮在恒河中的木头,不靠左岸,不靠右岸,不在中流沉没,不搁浅,不被漩涡卷住,不被人捞起,不被非人捞起,不腐烂,这块木头便有流向大海的趋势。”
心亦是如此。若心行于圣道之轨辙,即行于戒、定、慧,心便有趋向涅槃之势。
大海好比涅槃,恒河好比戒、定、慧。但还有条件:不靠左岸,不靠右岸,不在中流沉没,不搁浅,不被漩涡卷住,不被人、非人捞起,不内腐。如此,它才能顺着道的洪流而去。
即使心已入道流,努力布施、持戒、打坐、观身、观心,但若靠了左岸、右岸,便无法前行;若搁浅了,也无法前行;若被漩涡卷住等等,也无法前行。
每一个比喻都有其深意。佛陀解释说,“左岸右岸”意指执着于内六处、外六处,简言之,即执着于二元对立之法。例如执着于心的迷失,或执着于强行专注,这都是二元。随顺烦恼与强行压制也是二元。若不能始终行于中道,便会偏向左右,偏离中道,落入二元。若不落入二元,便有机会到达大海。
所谓的“漩涡”,即是五欲之乐,对色、声、香、味、触的享乐与喜爱。我们是否感觉自己仍沉溺于欲望,仍享乐于世间?这便是被漩涡卷住了。这块木头无法继续前行,原地打转,在眼、耳、鼻、舌、身之间打转。
有些人执着于人我之见,这阻碍了進步。例如,自认为比别人优越,便去轻慢他人;自认为不如人,便自卑,不思進取;或认为与人平等,便不肯让人,贡高我慢。这便是“搁浅”了,木头无法再顺流而下。
“中流沉没”指的是乐于、执着于自己所生的境界,或在修行过程中执着于某个境界。我们常执着的境界是“空”境。是否感觉修行时,心向前漂移,或向内沉入,然后空寂舒适,便不再继续觉知身心,以为“我已舒适,我已快乐”?
“被人捞起”例如挂念同伴、子女、配偶、亲属,挂念一切,挂念这个,挂念那个,因此无法前行,因为执着于人。独处不得,独行不得。然而,这条路是个人之路。若无人与我们戒、定、慧相当,我们便独自前行,不等他人。我们的时间不多,若等待他人,佛教或许已然消逝,便无法成就。
“被非人捞起”,有些人修行是为了生天。布施求生天,持戒求生天,打坐求生梵天。这便是被非人捞起,迷失于这些境界。
“内腐”指的是破戒之人,不持五戒。若缺五戒,便不必谈论道果涅槃了。
因此,并非每个心都有趣向涅槃的趋势,唯有行于戒、定、慧之心,才有此趋势。如同恒河中的木头,若不被各种障碍所阻,才有顺水流向大海的趋势。
第四章 道
道是唯一的道路, 是唯一能导向离苦的道路。 当行于此唯一之道, 便能到达那唯一的法, 那独一的法(即涅槃)。
八正道, 可概括为三学:戒、定、慧。
又可概括为二学:奢摩他与毗婆舍那。
4.1 道:唯一的离苦之路
佛陀的法,初善、中善、后善。它悦耳动听,沁人心脾。我们越是学习修行,越会发现痛苦不可思议地从我们心中消散。
佛陀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不求他人帮助,不依赖外物。他让我们以佛、法、僧为皈依处,但皈依并非意味着他们会来帮助我们离苦,而是他们是离苦者的榜样。
他们教导了他们已经走过的离苦之路,他们能做的仅此而已。剩下的,我们必须自己去做,自己去修行。
他们所教导的道路,清晰明确,无有含糊,无有可疑之处。只要我们正确地去实践即可。这其中有两点:第一,方法要正确;第二,要如法地精進,而非浅尝辄止。许多人心急,累积了无量劫的烦恼,修行三个月便想证悟。
修行必须走对路。走对之后,必须精進。做做停停,只能得到马马虎虎的法。若想修行至心达彼岸,离苦得乐,不再挣扎,便须决一死战。这对我们凡夫俗子而言,并非遥不可及。遥不可及的,只是那些不知路、盲目挣扎、徒劳无功的人。
例如,去练习打坐,期望通过大量打坐而有朝一日解脱。坐来坐去,只得到宁静。久而久之,又会散乱,又得再坐。这些不知路的人,辛苦无尽。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了知道路。此路名为“唯一道”。知路之后,必须勤奋行走。若不知路,切莫勤奋,否则会偏离轨道,越走越远。例如,身在室利罗阇,想去清迈,必须朝正确的方向走。若向东走,只会到达金边,到不了清迈。
“唯一道”可译为“唯一的道路”,但此词有多重含义。其一,这是“独一无二者之路”,即唯有佛陀一人发现的道路。其二,这是“唯一能导向离苦的道路”。其三,这是“一去不返者之路”,即走一次便到达终点,无需再走。看,它有多重含义。
当行于此唯一之道,便能到达那唯一的法,那独一的法。
二元对立之法,尚非可依之法,仍是变异之法。例如“宁静”,并非究竟依怙,因为“宁静”有其对立面“散乱”。“善”亦非究竟依怙,“善”有其对立面“恶”。
我们将学习二元之法,最终趣入独一之法。
这唯一之道,概括起来只有一个,即“圣道”。若展开,有八道支。若八支太多,可概括为三学,即戒、定、慧。因此,戒、定、慧必须圆满。若戒、定、慧不圆满,八正道便不圆满。
道只有一个,但有八个组成部分,如同蜘蛛一身八足。概括起来便是戒、定、慧。其中,正见、正思惟属于慧学;正业(即持守第一、二、三戒)、正语(即持守第四戒)、正命属于戒学;正精進、正念、正定(心之稳固)属于定学(即心的训练)。
八正道,概括起来就是戒、定、慧。若不圆满,圣道不生。 因此,若只有戒,不修心、不开发智慧,便无圣道。若只修心,无戒,也无圣道。若只开发智慧,一味思维修习,而无戒、无定作为基础,也无圣道。
修行时,必须圆满修习。但有八支,如何圆满修习?这非易事。因此,须先了知,一切善法的根源是“念”。若有正念,便会有戒;有正念,心便会稳固,定便会生起;正确地培育正念,智慧便会生起。
第一步,是开发工具,即训练自己时常有“念”。“念”并非儿戏,如今我们常借用佛陀的词汇,却用在极浅的层面。例如说“饮酒导致失念”,其实不饮酒也失念。世人本无正念,只有普通的念,例如走路不掉进坑里,开车不掉下马路,便自以为有念了。这与佛法所说的念,层次不同。
佛陀以“四念住”来解释“念”,以“禅那”(安止定)来解释“定”。若我们要修习念,便须学习“四念住”。
四念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了生起“念”,另一部分是为了生起“智慧”。
修习四念住以生起念,要练习时常觉知境界。例如,觉知四威仪:站立时感觉,行走时感觉,坐着时感觉,躺卧时感觉。这称为以身为处,即见到身体在行住坐卧。若以呼吸为处,呼气时感觉,吸气时感觉。如此呼吸,是为了生起念,而非强迫心宁静,必须呼吸时能感觉自身。若觉知细微威仪,例如身体移动、静止时都能感觉,这一切都是为了觉知自身,这属于身念住中的“正知”部分。
因此,并非为了生起定,并非只为宁静,而是为了觉知自身。当时常觉知自身,久而久之,心便习惯于觉知。当迷失时,只要身体一动,便能觉知到。
若曾练习呼吸时感觉自身,当烦恼生起时,你是否注意到呼吸的节奏会改变?例如,愤怒时,呼吸会改变,变得急促。越愤怒,呼吸越急促。若曾练习呼吸时感觉,当迷失时,呼吸节奏稍有变化,我们便能觉知到“我迷失了”。在觉知到那颗迷失的心时,我们便回归了觉知。 如此时常练习,以正念安住于身,便能获得觉知,获得稳固之心。
以正念觉知受,练习观察,身体时而乐,时而苦;心时而乐,时而苦,时而舍。持续观察,当感受变化时,便能觉知。
训练自己以正念觉知境界。所得到的,是“觉知”。这“觉知”包含了“念”与“定”。有“念”作为觉知的功能,有心稳固起来的“定”。心会成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我们要持续这样训练。
当我们开发出“念”与“定”这两个工具后,下一步便是开发智慧。智慧,是见到三法印。 这一点必须牢记。智慧并非见到名色。有人说观腹部起伏是修毗婆舍那,那不是毗婆舍那。智慧必须见到名色的三法印。坐着思维修习身体不净,这并未见到名色,并未开发智慧。若要生起智慧,必须见到名色的三法印。
要生起见到名色三法印的智慧,也需依赖修习四念住。觉知自身后,以正念觉知名身心的变化,以一颗稳固的“知者、观者”之心。这便是以“念”与“定”为工具来开发智慧。
“定”即稳固。有定的心,会从“思者、想者、造作者”转变为“知者、观者”。这可以通过修习四念住的基础部分来训练。例如,呼吸时,心跑了,觉知到;呼吸时,心跑了,觉知到。这样既能得到念,也能得到定。得到念与定之后,便来开发智慧,不要只是停留在觉知自身。有些人停留在觉知自身,保持着那份觉知,那仍是奢摩他,尚未進入毗婆舍那。
要進入毗婆舍那,必须见到名色的三法印。要见到名色的三法印,必须依赖正念觉知名色,以及心的稳固,即心从名色中分离出来,成为名色的观察者,观察身心的运作。
心能分离出来成为观察者,是能否真正观察的关键。
过去,隆波帕默拜师学法时,祖师们都会教导一个词:“知者之心”。无论去哪里,每位祖师都说同样的话:“知者之心”。即要让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之心生起。
那时,祖师们教导要有“知者之心”。若心成为知者,当心以正念觉知身时,便会见到身的三法印。若心成为知者,以正念觉知受时,便会见到受的三法印。若心成为知者,以正念觉知行(即善恶的造作)时,便会见到行的三法印。若心成为知者,见到识(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门生灭的了别作用)时,便会见到识(即心)的三法印。(“心”与“识”是同一回事,都指了别所缘的作用。)
若心稳固,成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便能见到名色的三法印。例如,当我们的心成为观察者,见到身体在呼吸,我们会立刻感觉到身体与心是两回事。身体是一部分,心是另一部分,是两回事。身体在呼吸,这不是“我”,只是心所觉知的对象而已。它从“我”的地位,降级为“我的”。
它降级了。从身体即“我”,到心稳固成为观察者时,身体便降级为“我的”。持续观察,终有一日会彻见,它也非“我的”,我无法掌控它。于是连“我的”也摧毁了。
当无“我”无“我所有”,它又属于谁?它属于世界。它又是什么?只是法,是色法,是地水火风四界,不再是“我”,也非“我所有”,它属于世界。
要练习观察。当心能分离出来成为观察者,便会见到身体非我、非我所有。
再观察受,即身体的乐受、苦受,以及心的乐受、苦受、舍受。起初,我们会觉得是“我”乐、“我”苦,乐与苦即是我。持续观察,当乐、苦与心分离时,便会见到乐与苦属于世界,非我所有。如此,一步步地破除邪见,从“我”到“我的”,从“我的”到属于世界,与我无关,只是法而已。要这样一步步观察。
或观察行,即心中的各种造作,如贪、嗔、痴。过去以为是“我”嗔。持续观察,便会见到嗔与我是两回事。若懂得观察,会见到它们分离。嗔是一部分,心是另一部分,不再是“我”嗔。那是什么在嗔?嗔是一种境界,是心在嗔,非我嗔。甚至,嗔还不是心本身。
持续观察,越是修行,越会发现,无处有“我”。身体非我,受非我,行(各种造作,如贪、嗔、痴)亦非我,只是心暂时造作出来然后消散的境界。例如,当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不如意的所缘,嗔便生起。嗔之生起,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并未命令它生起。即使命令它“不要嗔”,它仍然会嗔。它自行生起,是无我的。它也不恒常,前一刻的心无嗔,此刻的心有嗔,看,心也不恒常了。
要深入地观察,以正念、智慧来洗涤,而非思考。是要亲见境界,有真实的法作为所缘,亲见色法,亲见名法,亲见它们的生灭,亲见心的运作,即它如何自行运作,如何执取所缘,如何造作所缘,造作之后,所缘又反过来造作心,如此相互造作,共同在心中创造出生命与轮回。
持续观察身心中的实相,只会见到无常。观察身心中的实相,只会见到苦。身体时刻被苦逼迫,心也时刻被烦恼、爱染逼迫,持续受苦。并且无法掌控。身体非我,我们只是暂借世间的物质元素来使用。例如,待会儿要吃饭,便是借用物质元素来用,吃完后排泄一部分,储存一部分,如此循环。实际上,我们是在借用世间的物质。
心也整日旋转不休,时而烦恼造作,时而善法造作。但无论何物造作,皆是生后即灭。
如此,持续地觉知身,觉知心,以一颗稳固的心去觉知,心只是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心只是一个观察者,观察身体的现象,观察心的现象,时常观察,频繁观察。最终,心会生起智慧,会“叮”地一下醒悟,总结出:此身,无有实义。 有些人是因见其无常而知其无实义;有些人是因见其是苦而知其无实义;有些人是因见其无法掌控而知其无实义。观察心,亦然,无有实义,因为它无常、是苦、是无我。
当我们见到自己的身心、名色无有实义时,执取便会自行消除。我们无法命令心停止执取身心,心会自行停止执取。但心不会平白无故地停止执取,我们必须带领心去学习身心的实相。身心的实相即是三法印。 它会见到,身心无有实义,因为它无常、是苦、是无我。
当了知实相,心便会自行放下对身心的执取。身归身,心归心,不再执取。然后,另一种境界会生起,是一种“纯净的觉知”生起。我们凡夫的“知”是混杂的,非纯净之知,是被烦恼、爱染、无明所覆盖的。另有一种“知”,无点、无形、无边、无界、无所住,无来无去,无生无灭,是另一种奇特的界。此界与“空性”——宇宙的“无我性”融为一体。
要慢慢练习,这并非我们凡夫俗子遥不可及之事。只要知路,并勤奋修行,便能做到。若行于歧途,则无法成就。要好好学习。
佛陀是引路人。此路即是戒、定、慧。若想圆满戒、定、慧,便要好好修习正念,好好觉知自心。任何烦恼生起,我们觉知到它,烦恼便无法覆盖心,“定”便生起。任何五盖生起,我们有正念觉知到它,五盖便无法覆盖心,“定”便生起。心稳固成为知者、观者,以正念觉知身心的实相,见到三法印的“智慧”便生起。
但智慧无法凭空而生,必须有戒、定作为基础。戒、定、慧必须协同运作,在心中圆满、平衡,称为“道支俱生”,即共同生起,共同运作,共同完成同一任务:洗涤烦恼。
洗涤之后,圣道便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会与被杀死的烦恼一同ดับ灭。它们一同ดับ滅,代之而起的是“圣果”。圣果是出世间果,圣道是出世间因。当出世间果生起后,它也会ดับ,因为因已ดับ,它也无法长久存在,也随之ดับ。唯有涅槃不ดับ。道是一回事,果是一回事,涅槃又是另一回事。虽同为出世间法,却不相同。道与果有生有灭,涅槃无生,故涅槃无灭。它们是不同的境界。
4.2 戒、定、慧的职责
我们凡夫的心,其本性是明亮的,但并非纯净。它潜藏着无明,即“不了知”,潜藏着各种各样的随眠烦恼。但当随眠烦恼尚未被激起时,我们感觉心是明亮、舒适的。
若我们将水注入水缸,久置之后,会看到缸底有沉淀物。当沉淀物未被搅动时,水是清澈的;当沉淀物被搅动时,水便浑浊。
心的境界亦是如此。我们累积了随眠烦恼,我们累积的恶行,会储存在我们的有分心中。
当尚未受到强烈的感官接触干扰,或尚未有强烈的所缘来触及时,如同无人去搅动缸中之水,沉淀物便不会泛起,随眠烦恼不运作,水便是清澈的。
因此,心之本性是明亮的,它之所以浑浊,是因为受到所缘的干扰。一旦受到干扰,潜藏的随眠烦恼便会泛起,成为粗显的烦恼,心便污浊,不清净了。
我们的心,其本性如同缸中清水,而非纯净之水。我们必须逐步地培育正念、培育智慧,如同我们不断地过滤水。最终,将所有杂质、沉淀物过滤掉,便能得到纯净之水。
过滤水中沉淀物的工具,如同过滤心中烦恼的工具,即是戒、定、慧。
- 戒,如同粗滤网或筛子,过滤掉我们心中粗显的杂质,过滤掉强烈的贪、嗔、痴。
- 定,是过滤中等杂质的工具,即五盖。
- 慧,是处理深藏于习性中的随眠烦恼的工具。它不必等待烦恼泛起,而是像一根吸管,直接伸入缸底,吸走沉淀物,这是非常精细的工作。
若我们能从心中清除污垢,我们的心便会既明亮又纯净。
有时我们图方便,听到佛法说“心之本性是明亮的,因客尘烦恼而污浊”,便想当然地认为无需做什么,心本就明亮,只需防止客尘烦恼侵入,或避免接触所缘即可。
佛陀的教导并非如此肤浅。若要不断地清除客尘烦恼,那将是永无止境的负担,因为缸底的沉淀物尚在,并未清除。若要避免接触所缘,也不可能,因为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必须以戒、定、慧来清除烦恼,才能真正地清除污垢。 此时,无论水如何晃动,都不会有沉淀物泛起。如同已善加训练的心,阿罗汉的心,无论接触何种所缘,都不会有任何沉淀物泛起,它永远是光明、清澈、纯净、圆满的。
因此,并非逃避接触,或刻意保持心不动。有些人的教导有所偏差,说“不要搅动水,静静地待着,避免接触所缘,沉淀物就不会泛起”。也有人说“什么都不用做,静静地待着,不要接触它,水就会保持明亮清澈”。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心本清净”吗?实际上,它尚未清净,只是烦恼尚未显现出来而已。
刻意保持心不动、空无,不让它接触所缘,或避免接触,或接触后控制心不让它波动,这些做法有多种形式。避免接触所缘,好比“别碰这水缸,让它静置,沉淀物就不会泛起”,然后说“心已清净”,已成阿罗汉。然而沉淀物尚在缸底,随眠、烦恼、结使仍潜藏于心,这还不是阿罗汉。
避免接触所缘,不看、不听、不闻、不尝、不触、不想、不念、不造作,期望烦恼不被激起,这并非佛陀所教导的道路,因为它永无止境,只是暂时地隐藏了烦恼。
避免接触所缘的最佳方式有两种,它们都会创造出微细的生命境界:
- 训练心直至证得“无想有情天”,此时无心,自然无所觉知,也就无所谓接触了。
- 减少接触,即進入无色界定。当進入无色界定,眼、耳、鼻、舌、身五根门不起作用,便切断了五种接触,只剩下意门,便感到舒适,因为无物干扰,便沉迷于那份舒适中。
造作出更微细的生命境界,并非离苦之道;避免接触所缘,亦非离苦之道。
若我们想真正地培育正念与智慧,不要怕水浑浊。让它自然地接触所缘,只是不要再向其中添加污垢即可。 让眼、耳、鼻、舌、身、意自然地接触所缘,沉淀的烦恼便会运作起来,此时我们要以正念觉知它。
这好比污垢浮起,我们有正念觉知,便将其捞出。烦恼浮起,我们有正念觉知,烦恼便“唰”地一下消散了。看,它开始亏本了。污垢,即随眠烦恼,开始逐渐减弱。当眼、耳、鼻、舌、身、意接触所缘,随眠烦恼运作,造作出粗显的烦恼,我们觉知到它,烦恼便消散,随眠烦恼便不断亏本,力量逐渐减弱。
因此,我们以正念觉知自心,并非直接为了断除烦恼,我们不必去断除烦恼,因为(在觉知的那一刻)烦恼已经消失了。
我们以正念觉知心,在眼、耳、鼻、舌、身、意接触所缘、烦恼运作之时,随眠烦恼投资造作出烦恼,若我们觉知到它,随眠烦恼便会亏本,力量会逐渐减弱。但若未能觉知,烦恼运作之后,便会在我们的潜意识,即有分心中,储存下沉淀物——随眠烦恼。
我们培育正念,并非直接旨在摧毁烦恼,但其结果是随眠烦恼的力量逐步减弱。这便是从缸底逐步过滤沉淀物的过程,是一项精细的工作,需要理解。若非佛陀的彻悟智慧,极难理解这条道路。
普通人会想当然,即使听了佛陀的教导,也还是想走捷径,认为不接触所缘便好。若不接触所缘心便能好,那盲人岂不善哉?聋人岂不善哉?患麻风病皮肤无感者岂不更善哉?舌头断了尝不出味道的,这些人岂不更快成阿罗汉?因为他们没有接触所缘。
事实上,正因为有眼,接触所缘后却无烦恼,这才是更殊胜的。 有耳,接触声音却无烦恼,比没有耳朵更好。因此,并非逃避接触所缘,也非接触后刻意保持心不动、强迫心空无、守护心永恒宁静。只要还需刻意守护、保持、控制、照看心,工作便尚未完成。
佛教中的修行任务,到某一阶段会完成,称为“所作已办,梵行已立,不受后有”。但若我们一直守护心,便需永远守护下去,工作永无止境。
谁听过慧能的故事?慧能到寺院,师父没怎么教他禅法,只让他去砍柴、做饭。有一天,师父说自己老了,让大家各作一偈,看谁最了得,便传衣钵,立为六祖。
大弟子神秀,出家已久,便在墙上题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守护心,保持明镜洁净。谁读了都赞叹,哦,这已彻悟,深解佛陀教法,能守护自心。确实,若能守护心,烦恼便无机可乘,便可离苦。
慧能不识字,看到众人喝彩,说如何殊胜,便凑过去让人读给他听。听完便知,此偈不对。若心如明镜,烦恼如尘埃,需时时拂拭,何时工作才能了结?
慧能便请人代笔题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若无明镜,尘埃何处落?
听起来好似无心。隆布敦教导说:“见知者,毁知者;见心,毁心,方能达至究竟清净。” 教的是同一法。但“毁心”、“毁知者”,并非真的去摧毁,而是培育正念、智慧直至圆熟,直至不执取心。当不执取心,心便非我,也无需守护。但起初不能不守护,否则会被烦恼吞噬。必须长期训练,戒、定、慧必须真正圆熟,才能放下对心的执取。
慧能请人题偈后,众人更是惊叹,哦,这比神秀的境界又高一层。那个要守护明镜,这个连明镜都没有,太酷了。师父(五祖弘忍)看到后,脱下草鞋,将慧能的偈语擦掉,然后让众人去向神秀的偈语烧香礼拜。众人便说慧能不行,师父用鞋子把他的法都擦掉了。
第二天,五祖悄悄到碓房去找慧能,稍作交谈,便知慧能已堪受法。于是用杖敲碓三下,慧能便知师父让他三更时分去见。
到后,师父为他讲法,他便悟道。师父将衣钵传给他,这衣钵自达摩祖师(即菩提达摩,少林寺初祖,从印度到中国传法)代代相传。慧能便成为禅宗六祖。然后师父说,快走,再不走必遭杀害。师父送他到江边,让他快快渡江逃走。慧能想请师父上船,自己划船,师父说,是师父的责任送你到彼岸。最后,慧能逃走,与猎人同住了许多年,才回到家乡南方。
到了南方,听到僧人争论寺院旗幡被风吹动之事,争论“是风动,还是幡动”,相持不下。慧能便裁决道:“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 看,又回归到心了。
住持一听此言,便知此人即是六祖。他也是一位智者,一听便知是何等境界。若心不造作,谁来造作?风动幡动,皆是外境,无有实义。争论外境,却忽略内境,自己的心在动,为何不见?
这是教导我们要回观自心。心动而不知,潜藏的烦恼便会运作起来。凡夫的心,接触所缘,若非阿罗汉,必然会动。接触微细所缘,则微动;接触粗糙所缘,则大动。有时在内旋转,轮回在内旋转不休。但若修行至究竟,接触后不动、不摇、不波、无内旋。
隆布敦因此教导:“心之常态,是向外攀缘,随之波动。但圣者之心不外求,亦不波动。”(此处的圣者指阿罗汉)。它不波动,因为不执取。
为何不外求?不外求如何了知所缘?因为阿罗汉的心遍满法界,并非像我们凡夫的心那样有边、有界、有点、有形、有所住,跑来跑去。你们是否感觉到,自己的心跑来跑去?实际上,心并未跑来跑去,那只是幻象。心在眼门生起,然后ดับ;在耳门生起,然后ดับ;在意门生起,然后ดับ。 但它在不同根门间快速地生灭交替,我们便感觉是同一个心在跑来跑去。如同动画片,卡通人物并未动,只是一张张静止的画面,但快速连续地生灭,我们便感觉卡通人物是同一个,并且在动。心便是如此。
我们凡夫的心,其本性便是时刻在六根门间流转,在眼、耳、鼻、舌、身、意间流转。去看,然后回来想;去听,然后回来想。你们是否注意到,此刻听隆波帕默说法,听与想在不断交替,并非只听。若只听,便听不懂。我们之所以听得懂,是因为我们在想。听,只是接收声音信号而已,然后才到意门来解读,这个声音信号是什么意思。
当心尚有烦恼(漏)的外壳包裹,尚有边有界,它便会去到这里那里。但若心圆满,如阳光普照,阳光便无需从室利罗阇移到曼谷,无需从曼谷跑到清迈,因为它已遍满一切。因此,无所谓来去,无所谓送往迎来,它不再是只照亮一点的聚光灯。
我们凡夫的心,如同聚光灯,照向这里那里。我们必须逐步训练。第一步,练习觉知自身,不散乱,然后可以觉知身,或觉知心。若觉知心,便觉知心的变化,时而乐,时而苦,持续观察,时而善,时而恶。持续观察,便会见到心在生灭流转。乐心是暂时的,苦心是暂时的;善心是暂时的,恶心是暂T时的。反复地见,智慧便生,会了知一切心皆是暂时的。
当见到心本身也受三法印支配时,对心的执取便会消除。 不知为何要执取,它只是暂时之物。我们之所以对心执取最深,是因为我们感觉自己的心是永恒的,今天的心与过去的心是同一个。
但若我们见到心是时刻生灭的,可以通过观察受、观察行来了知。乐心生后即灭,苦心生后即灭,舍心生后即灭。善心生后即灭,贪心生后即灭,嗔心、痴心、散乱心、昏沉心,皆是生后即灭。最终,智慧生起,会彻知一切心皆是生后即灭。
当智慧圆熟,见到一切心皆是生后即灭,对心的执取便会消融。不知为何要执取。这是针对见到心之无常而解脱者。
有些人是见到“知者之心”是苦,便不执取,不知为何要执取苦。
有些人是见到心自行运作,无法命令,无法掌控,不知为何要执取,它随时可能背叛,便消除了对心的执取。
至此,才算摧毁了那面明镜,尘埃便无处可落。
因此,“毁心”、“毁知者”,并非一念之间便能做到。那样做只会精神错乱。要持续地培育正念、智慧。 第一步,练习觉知自身。能觉知自身后,便觉知心的变化。心乐时知,心苦时知,心舍时知;心善时知,心恶时知。时常觉知,时常觉知,终有一日,智慧会“叮”地一下生起,会了知“凡是生起之法,皆有滅去之性”。
须陀洹圣者了知“凡是生起之法,皆有滅去之性”,一切生起之法,皆必ดับ灭。这是须陀洹的认知境界。
若了知得更深,它会不断地向内回溯,在此身心中,会见到此身无有实义,消除对身的执取,这是阿那含的法行境界。
修行的终点,必将收窄至心。我们可以直接从心开始,最終也回到心;也可以从观察身开始,然后回到心;也可以观察身、受、行,然后回到心。但最终,都会回归到这颗心,因为这颗心是所有蕴的起源。仅有一颗心,便能再造作出五蕴。若此心消融,便再无物可造作五’蕴。
要慢慢练习。若能放下心,便无事可做,也无需再拂拭尘埃了。
4.3 奢摩他与毗婆舍那
佛陀教导说:“应以无上智慧修习之法(即道),即是奢摩他与毗婆舍那。” 既然有两者,便说明两者不同。奢摩他是一回事,毗婆舍那是另一回事,必须加以区分。
奢摩他是一种让心宁静的方法,同时也是让心宁静并稳固的方法。因此,奢摩他(定)有两种:
-
第一种名为“所缘专注定”,即心专注于单一所缘,从而达到宁静。例如,练习念诵“佛陀”,让心宁静不动;或觉知呼吸,心专注于呼吸,呼吸便越来越浅、越来越短,最终只在鼻尖处留下一丝,化为光明。当心转而觉知那光明,而非来去的呼吸时,心便進入禅那。这是修习奢摩他以求宁静,心安住于单一所缘,先是呼吸,后是光明。
练习念诵“佛陀”,心安住于“佛陀”而不散乱,也是安住于单一所缘。将心导向单一所缘,称为“所缘专注定”。这是为了休憩,有其益处。但若修习不当,也不至丧命。只需达到近行定或刹那定,便足以开发智慧。
-
还有另一种定,最为难得,即心稳固成为“知者、观者”,名为“相专注定”,鲜为人知。但三十年前,隆波帕默无论去拜见哪位祖师,他们都着重教导这种定。无论去哪座寺院,他们都讲“知者之心”。要练习直至心成为知者,此时心便具有稳固的定。这种稳固的定,正是用来开发智慧的。
我们的心,其常态是不稳固的,即时刻流转。例如,我们打坐觉知呼吸,心常流向呼吸;有些人观腹部起伏,心流向腹部。若心仍在移动,便非真正稳固。若心稳固,它便只是一个观察者,会见到身体在远处,心成为观察者。 当乐、苦或善、恶生起时,它会见到乐、苦或善、恶在远处,心会分离出来成为观察者,心会分离出来成为知者、观者。
训练心稳固成为知者、观者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固定的形式中修习禅定,直至证得第二禅。当寻、伺止息,心便会稳固起来,成为知者、观者。另一种,是简单的方法,例如,练习见到身体在呼吸,见到身体在起伏,或见到身体在移动,将这些都视为心所觉知的对象(如同观察他人在呼吸、他人的身体在起伏、他人的身体在移动)。时常如此练习,久而久之,身与心便会开始分离,心会稳固起来,成为知者、观者。
若要通过观心来训练“知者之心”,可先修习一个禅法,然后觉知心的动态,便能得到稳固的观察者之心。例如,观察呼吸,心动了便知;念诵“佛陀”,心动了便知;经行,心动了便知。在觉知到心移动或迷失去想的那一刻,“知者之心”便会生起,便能得到稳固的心。 这才是正确的修定方法。当心稳固后,要能分离五蕴。若波罗蜜足够,五蕴会自行分离;若不足,则需助其分离。
安住于单一所缘的宁静之定,并不能生起智慧,它只是一个休憩之所,让人恢复精神。若恢复精神后不懂得开发智慧,当心从定中退出时,会比常人更加散乱,因为它静止了太久,此刻便想躁动。
因此,祖师们便设计了一个善巧方便:既然它想躁动,与其让它随烦恼胡思乱想,不如引导它去思维修习身体。
若修习了宁静之定,安住于单一所缘,便须出来思维修习。这种思维修习尚非毗婆舍那。 隆波布特曾明确教导:“奢摩他始于意图止息之时,毗婆舍那始于思维修习止息之时。” 隆布敦也教导:“思之愈多,愈不能知;止息思维修习,方能了知;然亦需借由思维修习。”
我们必须加以区分。有时人们的教导过于肤浅、粗糙,教人念“佛陀”,呼吸,宁静后出来思维修习身体,便说是毗婆舍那。这完全是两回事。那只是一个善巧方便,为了防止心沉溺于静止,或散乱去想别的事情,但也有其益处,它能引导心去学习观察蕴、界的三法印,是一种善巧。
若能進阶至了知蕴、界的实相,能分离蕴、界,才是真正的开发智慧。若只修宁静,如何能有智慧?
我们必须训练出“知者”,训练出第二种定。 第一种定在佛陀出世前便已存在,人人皆可修,仙人隐士也能修,但它不能导向道果涅槃。否则,仙人们早在佛陀之前便已证悟了。阿罗逻·伽蓝与郁陀迦·罗摩子都是修定高手,为何未能证悟?因为他们修的是心专注于单一所缘的定。
悉达多太子年幼时,有一次观耕犁节,他的侍从将他置于树下,自己跑去看净饭王犁田,将他独自留下。他便起来打坐。凭借他累世所积的波罗蜜,他起来坐下,呼吸,然后“知者”生起,并未走向禅那,而是生起了觉知。然后,他便忘了此事。这是人之常情,即使是菩萨,波罗蜜已近圆满,即将在这一生证悟成佛,旧习生起,心觉醒后,也还是会忘记。直至二十九岁,他出家后,首先去寻访仙人,如同我们想到修行,首先想到的便是打坐。悉达多太子也是如此想。
出家后,他首先去寻访名为阿罗逻·伽蓝与郁陀迦·罗摩子的仙人,学习打坐。他的智慧锐利,数日便学完了老师的课程,证得非想非非想处定。然后他发现,这并不能离苦。他了知,即使是最高深的第八定,也无法离苦。
如今人们只教打坐,相信只要持续打坐,终有一日会离苦。连第八定都无法离苦,悉达多太子在两千六百年前便已知晓。如今却仍只教打坐,如何能离苦?
悉达多太子发现单靠打坐无法离苦,便转向苦行。修心不成,便修身。想吃不给吃,想睡不给睡,折磨它,以折磨烦恼、爱染。折磨身,是为了折磨心,折磨烦恼、爱染。他如此想。实际上,苦行主义与禅定主义一样,源远流长。然后他发现,那也不是正道。
在他即将证悟成佛的那一天,他忆起了童年之事,忆起了那种他早已遗忘的定。从童年到二十九岁出家,再到六年后,他才再次忆起。这是他的宿业。他曾轻慢迦叶佛,当时他已是菩萨,却讥讽佛陀说:“你是在林中饿肚子才得到法的吧?” 这番言语的业力,导致他苦行了六年,因为他冒犯了有戒有德之人。我们要小心,最好不要冒犯任何人,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善谁是恶。
六年后,他才忆起,还有另一种定,是童年时曾修习过却已遗忘的。于是他重新呼吸。这次呼吸,不再是追随光明進入无色界定,而是带着觉知去呼吸,直至心進入第一、二、三、四禅,仍保持着觉知,并非呼吸时迷糊失念。若对定足够熟练,即使心進入无色界定,也不会迷糊。心安住不动,只剩下觉知,法界ดับ灭,身体消失,但觉知不失,他仍保有觉知。
从定中出后,他便引导心去思维修习:“何物存在,故有苦?” 他发现,是“生”存在,故有苦。“生”即是获得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获得眼、耳、鼻、舌、身、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出生之“生”;另一种是心执取眼、耳、鼻、舌、身、意之“生”。为何有“生”?因为有“有”。“有”即是造作。有三种造作能导致在此世间、或梵天、或天界、或恶道中再生。由出生而来的“有”,称为“生有”。而刹那刹那的“有”,称为“业有”,即心生起造业之意。
“生有”从何而来?来自心造作的三种业:1. 造恶业;2. 造善业;3. 造作“空”。所以要小心,那些教人造作“空”、引导心趣向“空”的,那是“无动行”,会导致生于“空”境。若造恶,则生于恶境;若行善,则导致生于善境。这心的运作,佛陀称为“行”。而刹那刹那的运作,那运作的心,称为“有”。它其实是同一种“行”,只是生起的时机不同。
“行”导致我们生于此处。我们生于此处后,我们的心又造业,这是刹那刹那的“行”的造作,这导致我们刹那刹那地“生”。例如,我们由“生有”而为人,但有时我们贪欲生起,便由“业有”而为饿鬼;有时我们愤怒生起,便为地狱众生;有时我们充满我见,便为阿修罗;有时我们心散乱、昏沉,便为畜生。有时我们有戒有德,便为人;有时我们享受福报,便为天人;有时我们心入禅定,便造作了梵天的“有”。这些都是在大“有”中的小“有”,即使我们此生的“生有”是人。
因此,“有”有两种。由出生而来的“有”,来自过去的“行”的造作。曾累积善行多,便生于善境;累积恶行多,便生于恶境;累积“空”多,便生于“空”境,但仍会再生。而此刻心识刹那间的造作,同样是善恶的造作,是在大“有”中再造作小“有”。
缘起中的“有”与“行”,实为同一回事,只是生起的时机不同。“行”是过去的部分,导致我们现在的果报;“有”是我们现在的造作,导致未来的苦。
他观察思维修习,发现这是名法与色法相互关联的过程,其中无人、无众生、无我、无他。当他见到此,便证得须陀洹果。再继续观察,便证得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果,一气呵成。
要走这条路,必须先准备好心。心必须稳固,而非呼吸时迷糊。 他呼吸时,持续地感觉,直至心成为知者、观者,然后他思维修习。思维修习并非思考,而是观察实相,有实相在眼前作为所缘。他有自己的名色在眼前作为所缘,于是了知名色相互关联地运作,遵循缘起的法则,于是他彻见了缘起。
缘起,实际上就是名色。“无明”是名法,“行”是名法,“识”是名法,“名色”是名法与色法。“名色”为“六处”之缘,眼、耳、鼻、舌、身、意,亦是名法与色法。“触”是名法,“受”是名法,“爱”是名法,“取”是名法,“有”是名法(心之造业),“生”是执取眼、耳、鼻、舌、身、意,亦是名法与色法,然后有苦生起。
缘起,实际上就是名色而已。他见到了,并了知它们如锁链般相互关联地运作,有因有果,无一物是凭空而生。万物有因则生,无因则ดับ,无法掌控。
若有人见到万物有因则生、无因则ดับ、无法掌控,此人将因见到“无我”而证得阿罗汉果,称为“空解脱”。
“无我”,并非指一无所有。“无我”指,若有因则有,但无法掌控。万物有因则生,无因则ดับ,无法掌控,非我所能命令。彻悟之智慧便生起了。
我们不可能坐着修一些不得要领的定,然后期望有一天自然而然变好。那样的修习是没用的,只会让心外求,时而迷糊,忘失身心,时而见到各种幻象。出定后便坐着思维修习,却不知必须先训练心稳固,才能开发智慧。这不像过去的祖师们,他们非常强调“知者之心”,心必须成为知者,心必须成为观者。无论去哪座寺院,他们都如此教导。因此,我们必须成为“知者”。“知者”即是“佛陀”。 我们念诵“佛陀、佛陀”,若如鹦鹉学舌,便无真正的“佛陀”,能有何成就?
我们必须念“佛陀”,直至生起真正的“佛陀”,即那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之心。何为“佛陀”?心即是“佛陀”。 曾听过吗?“心即是佛”。心即是“知”。这“知”起初是污浊的,潜藏着烦恼。必须依赖这“知”,来了知蕴、界的实相。
若不观察蕴、界的运作,便非毗婆舍那,永无可能证得道果涅槃。若只是思考蕴、界,那是奢摩他,尚未真正進入毗婆舍那,但它能激发我们去学习观察。例如,有些老师教导思维修习身体,这是在激发心去学习观察。后来,当心稳固起来,它会自行观察,因为它已经练习过了。因此,思维修习只是一种善巧方便。
真正的毗婆舍那,非思而得,乃知而得。 所谓“知”,即是以正念、智慧去“见”。但有些人需借由思考来引导,这也是有的。若有人前世已善修智慧,当“知者”生起,五蕴便会立即分离,并不困难。
4.4 四念住
佛陀将修行方法概括为“四念住”。例如,若我们听说要“了知蕴、处、界、根、圣谛、缘起”,我们便不知如何修行。因此,他将修行方法分解到四念住中。
四念住必须如实了知名色,方为毗婆舍那。但在四念住中,某些部分、某些主题属于奢摩他,佛陀也将奢摩他穿插其中,是一些简单的奢摩他,例如思维修习不净。或某些法门既是奢摩他也是毗婆舍那,例如安般念,这是大丈夫的无上禅法,既可修奢摩他,也可修毗婆舍那。
四念住有四种,但不必四种都修,因为它不是四级台阶,而是像城池的四座城门,是通往涅槃之城的入口。 我们可以从任何一门進入,不必总是从身念住开始。只需选择一种作为“安住之法”,可以是身、受、心或法。
选择安住之法可分为两组:身与受为一组,心与法为另一组。我们应根据自己的根性来选择。
-
身念住与受念住,适合“贪行者”,即喜爱快乐、舒适、美丽、优雅之人。这类人应观察身或受,因为身与受会教导他们,何为不乐、不适、不美、不雅。例如,极度执着快乐者,应观察受,会见到快乐转瞬即逝,实无可爱恋之处。喜爱美丽者,应观察身,持续观察,身体行住坐卧,实无美好之处,只有物质的流入流出,时刻被苦受逼迫,不见其美,不见其殊胜,不见其乐。
为何同为贪行者,却有两种所缘——身与受?并非修完身再去修受,而是要看,智慧锐利者,可观察受,因其更有趣。智慧尚不锐利,即培育正念、智慧见三法印尚不纯熟者,可观察较简单的,即身。身无太多可观之处,观察身体,见到身体呼气,身体吸气,仅此而已。便会见到,身体呼气非我,身体吸气非我,仅此而已。或观察身体行住坐卧,见到身体行住坐卧非我。终年累月,只做此事,并不困难。
但若智慧锐利者,可观察受,因为受或与身有关,或与心有关,需联系到身心,比单单了知身更为广阔。受生于身,亦生于心。并且,并非只了知于此。了知受,还会了知受的相续运作。
例如,当受生起,便生起爱;有爱,心便去执取;心便苦。当彻见受是无常、苦、无我,受只是来来去去,无法掌控,乐、苦便无有分别,快乐是暂时的,痛苦也是暂时的。见到此,心便不再挣扎。因此,观受比观身更难,适合正念、智慧锐利者。观受的典范是舍利弗尊者与目犍连尊者。而阿难尊者则主修身念住。
-
另一种根性是“见行者”,即思虑过多、充满我见之人。有两种禅法可供选择:心念住与法念住。
心念住,直接观察心的变化,所观不多。贪心重者,便去观察,整日只有两种心:贪心与无贪心。贪心生起,正念觉知,贪心便ดับ,变为无贪心。嗔心重者,便观察嗔心。心正嗔怒,观察嗔心,嗔心便ดับ,变为无嗔心。整日观察嗔心与无嗔心。散乱者,便去观察,有散乱心与不散乱心。当我们觉知到心散乱、流失,心便稳固,不散乱了。就这么简单。修习心念住,所观不多,只观某一对法即可。
若智慧更锐利,只观此不足以满足,便可進阶至法念住。其中既有名法,又有色法,并且不只见到名色本身,更见到名色的运作过程。例如,观察心中生起的五盖,要了知五盖从何而生,如何运作,如何令其不再生起。这比修习心念住者所观更为微细深奥。或观察五蕴,当见到五蕴,它便会分解,各蕴依其职能运作。或观察七觉支,即觉悟之要素。或观察圣谛。
实际上,隆波帕默所教导的观心,并非单纯修习心念住,而是包含了受念住、心念住与法念住的交叉修行。因此,我们所修习的,并非纯粹的心念住。心念住范围很小,例如,有贪心与无贪心一对,有嗔心与无嗔心一对。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我们见到的也远不止于此。例如,我们见到受生于身,见到受生于心,或身体移动我们感觉,心移动我们也感觉。
因此,隆波帕默所教导的,实际上已达到法念住的层次,例如见到缘起。当眼、耳、鼻、舌、身、意接触所缘,便生起受;有受,烦恼便插入;烦恼插入,爱便运作;爱运作,心便跳过去执取所缘,称为“取”;心便在所缘上挣扎造作,称为造作“有”;心便执取“自我”,即执取眼、耳、鼻、舌、身、意为“我”或“我所有”,称为“生”;心便苦了。会见到这样的过程。
为见行者划分的两种禅法——心念住与法念住,其原则与为贪行者划分的身念住与受念住相同,即智慧尚不强者,可观察心,所观之事甚少;智慧锐利者,可進阶至法念住。
佛陀的法极其微细,但他将修行方法简明地概括在四念住中。他教导“身中身、受中受、心中心、法中法”,教导要以此为“安住之法”。
“安住之法”,即心之居所,心之家。若心无家,便会流浪。但心住家,并非心坐牢。若心流浪,离家远去,便是过于放纵,落入“欲乐之行”。若心坐牢,即被强迫安住于单一所缘,不得离去,便是过于紧张,落入“苦行”。
因此,必须了知,“安住之法”意指不松不紧,恰到好处。如同人居家,既非流浪在外,亦非如坐牢般紧张。若修禅法而整日紧张,便非正道,无法真正开发智慧。
“家”,意指常住于此,时常觉知此法,但并非不了知他法。若不了知他法,便是坐牢了。若念“佛陀”而不肯放,世间只有“佛陀”,雷劈不知,车撞不觉,在路边念“佛陀”,眼不见,耳不闻,这是不行的。
佛陀教导说:“于身观身而住,具足正勤、正知、正念,于世间调伏贪忧。”
首先,我们必须了知名色(身心),并且要以“安住之法”的方式了知。佛陀用词是“于身观身而住”。“观”意指“随观”,即时常随观“身中身”。
何为“身中身”?非指灵体。“身中身、受中受、心中心、法中法”意指随机抽样来学习。
不必学习整个身体,只需学习身体的一部分。例如,学习呼气的色法,吸气的色法,站立的色法,行走的色法,坐着的色法,躺卧的色法。若见到身体呼气非我,身体吸气非我,则整个身体便非我了。若见到身体行住坐卧非我,则整个身体便非我了。若见到身体移动非我,见到身体静止非我,则整个身体便非我了。只需学习某一角度即可,但当心彻悟,便会了知全体。
“心中心”亦然。学习某些心。贪心重者,主观贪心,便会见到整日只有贪心与无贪心。嗔心重者,有嗔心与无嗔心,以此为主来观察。
“正勤”,即有精進以烧尽烦恼,并非修行来满足烦恼。修行必须能烧尽烦恼,令其焦灼,而非修行后我们因烦恼而焦灼,想着何时才能证悟,这便不是遵从佛陀的教导了。必须烧尽烦恼,令其焦灼,也非满足烦恼,非修行以保持心不动、空无,然后安住于不动、空无中享受永恒的快乐。那种修行没有“正勤”,而是满足烦恼的修行。
“正知”,即有觉知,了知何为有实义,何为无实义;何为有益,何为无益;何为适合我们,何为不适合我们。然后只做适合我们之事。这称为“正知”。
世间万物有两部分:有实义与无实义。无实义的部分应舍弃,我们只取有实义的部分。能做此选择的,称为“正知”。在有实义的部分中,一部分有益,大部分无益,知道了也只是好玩。例如,云有几种,目前对我们无益。有些人饶有兴趣地研究云有几种,也很好,但那只是对世俗生活有益。
在所有有益之事中,只有一部分既有益又适合我们,大部分不适合我们。
因此,若我们懂得选择,便会了知何种禅法适合我们。因此,必须了知,必须聪慧,即有智慧。当了知此事适合我们,我们便不放弃,时常觉知,不迷失、不忘记适合我们之事。这是最高的正知,名为“不痴正知”。“不痴”,即不为痴所染,即不愚痴,了知何事适合我们,且不迷失忘记它。若舍弃适合我们之事,便是愚痴了。
有“正知”,然后有“念”。以正念觉知名色的实相,时常观察名色的实相运作。
有些人从五蕴的角度看,有些人从六处的角度看,有些人从十八界的角度看,有些人从二十二根的角度看,有些人从四圣谛的角度看,有些人从十二缘起的角度看(有顺观十二支,逆观十二支)。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概括起来,都只是名色。只需观察适合我们、必要、有益的部分。
我们不必了知所有禅法,只需了知适合自己的禅法。如何能了知?第一,若有佛陀在世,可去请教。但我们已无佛陀可问。因此,我们不知道何种禅法适合我们。能帮助我们的,是“如理作意”,即善于观察。若做什么事,正念时常生起,便做那件事。若做什么事,不善法减退,善法增长,便做那件事。 例如,我们修行后,戒行越来越好,这对我们有益。我们修行后,心能安住于身心,过去总是散乱,不知心跑了,现在修行后心能安住,能觉知心,心迷失了便知,这说明此法适合我们。过去无法分离名色,现在修此法能分离名色,说明此法适合我们了。
我们观察修行的成果,看能否对治烦恼,善法是否增长,不善法是否减退。自我审视,何种禅法适合我们,便选择那一种。
所获之果,即是“于世间调伏贪忧”,即能断除对世间的喜恶,也就是不执取名色。佛陀曾说,若世间仍有人修习四念住,世间便不会空无阿罗汉。因此,我们觉知身心,要以佛陀所教导的正确方法去觉知,终有一日,我们会因不执取名色而解脱于诸漏烦恼。
4.5 修行:训练正念与智慧
培育正念、培育智慧,必须以一颗恰到好处的心来做,以一颗行于中道的心。走向两极的心,是无法培育正念、智慧的。
导致人们无法培育正念、智慧以至证得道果涅槃的,便是“欲乐之行”与“苦行”。
- 欲乐之行,即放纵身心随顺烦恼,迷失于眼、耳、鼻、舌、身、意,迷失于世间,迷失于欲望,迷失于色、声、香、味、触的享乐,不回观自身,忘失身心。
- 苦行,即强迫身心,令身受苦,令心受苦。修行时,例如觉知呼吸,便去专注,直至全身紧绷,身苦心也苦。初学者是否曾有此经历?กำหนด呼吸没几下便累了,生来呼吸从未累过,一修安般念反而累了,因为去干预了自己的呼吸,改变了呼吸的节奏。
佛陀并未教导要改变呼吸的节奏。他教导说:“诸比丘,出息长,知出息长;入息长,知入息长。出息短,知出息短;入息短,知入息短。” 即,它怎样,便知它怎样,而非去干预它。若去干预,便落入“苦行”,强迫自己受苦。
我们一想到修行,便会开始强迫心不动,控制心不动,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以为必须严肃。佛陀并未如此教导。
他如何教导我们了知心?“诸比丘,心有贪,知心有贪。” 心有贪,便知它有贪。并未教导说:“诸比丘,要强迫心不动,要专注心不动,自然会好。” 那绝非佛陀的教导。
若我们不落入两极——即迷失自身、忘失身心、随世俗烦恼而去,以及强迫身心直至僵硬不动——我们只需去“感觉”,感觉身,感觉心,感觉自身,不迷失,不散乱。感觉之后,观察身的工作,观察心的工作。观察身的工作,例如,身体呼气,见到身体呼气;身体吸气,见到身体吸气。身体行住坐卧,见到身体行住坐卧。
如同佛陀所教导:“诸比丘,行时,了知正在行;坐时,了知正在坐。” 看,行时,便了知正在行;坐时,便了知正在坐。并非要做什么,只是如其所是地了知。但他用了一个很酷的词:“了知”。并非呆滞地知。我们行住坐卧,或感觉身体时,有时说“我知道”,但我们并非真知。
“了知”并非指“清楚地知”。有些人试图“清楚地知”。例如,坐着要动,要拿水瓶,便盯着……“清楚地知”。渴了要喝水,移动……一小时还拿不到水瓶,只顾着“清楚地知”。这不是佛陀所说的“了知”。
“了知”意指同时了知两件事,即以“念”了知,并以“智慧”了知。
- 以念了知,即了知色法在站立、行走、坐着、躺卧。
- 以智慧了知,即了知那站立、行走、坐着、躺卧的色法,只是色法,非人、非众生、非我、非他。这称为“了知”,即了知实相,了知直至见到三法印,而非只知色法,非只停留在身体上。
呼吸时,将觉知专注于呼吸,问:了知色法了吗?了知了,但未“了知”,即尚未真正了知那呼吸之物非人、非众生、非我、非他。
此事并无难处,本是简单之事。过去身体行住坐卧,我们本就能感觉到,只是我们忽略了去觉知而已。
身体呼气吸气,我们本就能感觉到,只是我们忽略了去觉知。从今往后,行住坐卧,我们便时常觉知,但要“了知”,意指觉知之下,见到身体在站立,非我站立;身体在坐,非我坐;身体在行,非我行;身体在卧,非我卧。身体呼气,身体吸气;身体左顾右盼,身体进食,身体排泄,非我,非我吃饭。 若吃饭时只知“在吃饭”,这并非以正念、智慧了知,只是世俗之知,与修行无关。
因此,不要只停留在“念”,必须也以“智慧”了知。例如,有些人观腹部起伏,腹部一动便知,却无智慧,不见此物非我。因此,了知必须有两层:以“念”了知,并以“智慧”了知。
观心亦然。嗔心生起,我们觉知到它,称为有“念”。我们又见到,嗔并非心,只是暂时混入的法,有因则生,无因则ดับ,无法掌控,来了又去,只是心所觉知的对象而已。如此见,便是以“智慧”见,了知嗔受三法印支配。
观色也好,观名也好,都必须观察直至见到三法印。 若是“欲乐之行”,便忘失身心,不观身心,只顾想别的事情。若是“苦行”,便专注身心,以念感觉身心,却不见其三法印。
要见到三法印,必须行于中道,不迷失,也不专注。 身体移动,我们是观察者;心运作、变化,我们的心是观察者。慢慢地观察,便会见到,身体自行运作,非我。身体行住坐卧,非我,是心去觉知它。
贪、嗔、痴、散乱、昏沉生起,乐、苦生起,善法生起,这些皆是被知、被观之物。若有心作为知者、观者,便会见到乐、苦、善、不善等,皆非人、非众生。
我们会见到,嗔心生起,当我们觉知到它,便见到嗔非人,嗔亦非我,只是心所觉知的对象。
若修行,便会了知嗔非我。不修行者会认为“我嗔”。若能知“我嗔”已算不错,大多数人连自己嗔怒了都不知道,直到大发雷霆后才想起“刚才我嗔怒了”,或已将人杀害,才想“唉,刚才不该嗔怒杀了他”。这不叫“知”,已来不及了。
我们来训练心,不迷失,不专注,舒适地觉知自身,观察身的工作,观察心的工作,如其所是地观察。终有一日,会见到一切皆无我。身体非我,心亦非我。如此见到,苦又何处安立?苦立于“我”,若无“我”,苦便归于名色、身心,那是它的事。身苦而心不苦,至此便安乐了。即使世界毁灭,也是世界的事。此刻尚在呼吸,尚有正念、智慧,这便是福报了。
大家要练习。将来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我们都能应对,不会苦。困苦或许会降临于我们的身体,但不会成为淹没内心的痛苦。
4.6 开发智慧
生命的实相,时刻显现于我们的身心之中。因此,修习禅法,不必远求,只需在此身心中学习,日复一日,反复学习。
学习身体,时而乐,时而苦;时而这里痛,时而那里疼;时而呼气,时而吸气;时而站,时而行,时而坐,时而卧;时而冷,时而热;时而饥,时而渴;时而饱,时而排泄。此身之中,时刻变化。时而生病,年轻力壮时,难观病苦;身体衰败后,便易观察。年老后,时常能见到病苦,见到身体衰败。观察身体的实相,只有变异,只有逼迫。
这变异,即是“无常”。这逼迫,即是“苦”。无法命令它,不受掌控,即是“无我”。学习这些实相。
单学身体的实相尚不足够,我们不仅有身体,还有名法的部分。要深入观察,乐受、苦受亦是无常。过去我们不观察,快乐生起便欣喜,痛苦生起便厌恶,心不中舍。要持续地觉知、观察,快乐生起,是暂时的;痛苦生起,也是暂时的。万事万物,皆是暂时的。再深入观察,有时心会生起舍受,舍受也是暂时的,很快又会被乐、苦所取代,如此循环,只有无常。要这样观察。
观察心中时而善时而不善。心生起善法,例如对佛陀生起信心;有时又生起不信。谁曾有过这种经历?信心摇摆不定。今天信心满满,明天又不信了;今天厌烦佛陀,不想听法,想去看电影听音乐;明天又法喜充满,愿将身心供养佛陀,供养了两天又收回了。看,对佛陀的善信亦是无常,仍会变异。有惭愧心,羞于作恶,畏惧恶果,但愤怒起来,便不畏惧,不羞愧了。是吗?惭愧心亦是无常。
善法无常,不善法亦无常。无人恒嗔,无人恒贪,无人恒痴。嗔是一时的,贪是一时的,痴也是一时的,同样是无常。
看,我们的身心充满了无常,充满了逼迫,充满了无法掌控。
受,即乐受、苦受,亦是无常,来了又去。快乐无法持久,痛苦也无法持久。它被逼迫,此为“苦”。乐之有无,苦之去留,皆无法命令,此为“无我”。这便是实相。
善法或不善法的生灭,亦无法命令,此为“无我”。善与不善循环往复,时有时无,此为“无常”。善法、不善法,每一法都只能暂时存在,然后ดับ灭,它时刻被逼迫。贪被逼迫,嗔被逼迫,痴被逼迫,一切善法亦被逼迫,只能暂时存在,无法永恒,此为“苦”。不如心意,无法命令,此为“无我”。
色、受、行,皆受三法印支配。
我们持续观察,还剩下“心”这一法。心是了别所缘的自然现象。问:心从何处了别所缘?心从六根门了别所缘,即眼、耳、鼻、舌、身、意。
- 眼,见到色,即颜色。当颜色对比出现,便形成形状。然后“想”介入,标记此形状为何物。例如,金色与后面的红色对比,哦,这金色即是佛像。“想”介入标记。眼所见的,实为颜色,非见人、众生、我、他,非见佛像。人、众生、我、他或佛像、树木、山川,皆是世俗谛,是依赖“想”的记忆而生,标记此物为何。
- 耳所闻,非故事,乃声音,高低之声波。但闻声后,“想”介入解读,将此声与彼声连接,如此便有了意义。此为赞美之声,此为辱骂之声。实际上,耳闻声,非闻赞美辱骂。
- 鼻闻香,舌尝味,身触衣物。衣物亦非实相,乃世俗谛,“想”介入标记此物为衣物。实际上,身体所触,乃冷、热、软、硬、紧、动之感。冷热即火界,软硬即地界,紧动即风界。
因此,我们所触,乃地、火、风三界。至于水界,非由身了知。“水”非我们所见之水,水是分子间、原子间的引力,需由心来了知。
因此,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身了知地、火、风三界。其余所缘,由心来了知。
由心来了知的有四种:
- 第一,我们想出的故事,称为“世俗谛”。 世俗谛无实法支撑,不能作为毗婆舍那的所缘。例如,我们想“身体不净”,这“不净”并无实法支撑,是世俗谛。例如,我们说死老鼠腐烂肮脏,但苍蝇却很喜欢,说它香,乐于其中。看,各不相同。但火是热的,人碰到或苍蝇碰到,都一样热,因为它是实相。心所能触及的第一种,称为“世俗谛”。
- 第二,某些色法,例如水界,或站、行、坐、卧之色法,需由心来了知,非由眼了知。 大家可闭上眼,举起手,知道手举起来了吗?我们并未用眼看,对吗?因为是心了知,由感觉了知,称为由心了知。因此,某些色法由心了知,并非所有色法都由眼、耳、鼻、舌、身了知。
- 第三,所有名法,皆由心了知。 例如,乐、苦、贪、嗔、痴、善、不善,以及心本身,皆由心了知。
- 心所了知的,称为“法所缘”,有四种:1. 世俗谛;2. 某些色法;3. 所有名法;4. 涅槃。
问:涅槃是名法还是色法?答:涅槃非名色,涅槃超越名色。涅槃的境界由心来了知,但能了知涅槃的心,必须是无爱之心,方能见到涅槃;必须是无造作之心,方能见到涅槃;必须是不执取万物,乃至不执取涅槃本身之心,方能见到涅槃。
现在我们来观察心之无常,如何观察?时常觉知心时而去了别眼门所缘,时而去了别耳门所缘,时而去了别鼻、舌、身、意门所缘。心时刻流转。 例如,坐着听隆波帕默说法,时而看看他的脸,时而专心听,时而思考,边听边想,偶尔看一眼。不看能听吗?能。闭眼能听吗?能。闭眼听时能想吗?能。
看,心在六根门生灭。时而在眼门生起然后ดับ,时而在耳门生起然后ดับ,时而在鼻、舌、身、意门生起然后ดับ。心一次次地了别所缘。
心与所缘恒常俱生。有心必有所缘,有所缘必有心。缺一则另一亦消失。
心时刻生灭,由各种物质或所缘作为激发点、作为心之所缘。心本身亦生灭。若我们有正念,便会见到,时而心去了别眼门然后ดับ,时而心去了别耳门然后ดับ,时而心去了别意门然后ดับ。如此练习观察,只见无常。心本身亦无常。
心生于眼门,无法持久,此为苦。心要去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或意门,皆无法命令,它自行而去,此为无我。
大家可看着佛像,大尊的,然后下定决心:我只看,不想。能做到吗?看,无法命令心。
万事万物皆受三法印支配。 无一物生而不灭,只是不按心意ดับ,不如心意,即是无我。生后必ดับ,即是无常。存在但无法恒常,即是苦。
观察身,只有无常、苦、无我。观察受,即身之乐苦、心之乐苦舍,亦受三法印支配。善、不善法,无论贪、嗔、痴,皆是暂时生起然后消失。宁静无常,散乱亦无常。心本身亦无常、是苦、是无我。无法命令其生,无法命令其久住,无一可控。
持续观察,见到名色的三法印,这便是“开发智慧”。若我们开发智慧圆熟,练习日深,直至心接纳实相:身心中一切皆无常,身心中一切皆是苦(即无法恒常),身心中一切皆无法命令(是无我,不在掌控之中)。 如此深入观察,便是修习毗婆舍那。
毗婆舍那非指坐着思考三法印。若去坐着思维修习三法印,心尚未進入毗婆舍那。真正的毗婆舍那,必须去“见”。 毗婆舍那,意为“彻见”、“真见”、“殊胜见”。“见”,非“思”,非“寻”,非“伺”。因此,毗婆舍那已超越了思考。
让我们来时常觉知自身。第一步,持戒。然后时常觉知自身。 觉知自身,心不散乱,也不专注身心使其不动。
觉知自身,必须不做两件事:不迷失忘失身心,不专注身心使其不动。 即“不迷失”与“不专注”。不忘失身心,称为不迷失;不专注身心使其不动,此为不专注。若不迷失且不专注,便能达到“知”,如其所是地了知身心。
反复地知,日复一日。有些人心急,看了三天,便想何时能证须陀洹果。累积烦恼时漫不经心,要累积正念、智慧时却急于求成。
我们要练习观察身,观察受(即乐、苦、舍),观察行(即善恶造作),观察心(即了别眼、耳、鼻、舌、身、意门所缘的自然现象)。观察它们运作,见到所有色法运作皆受三法印支配,见到受运作,见到行运作,见到心运作,会发现一切皆受三法印支配。
反复地看,如同我们要洗涤自心,使其洁净,如同洗涤深层污渍。这深层污渍,巴利语称为“随眠”。我们轻易便能累积污垢,要洗净却难。必须耐心持续地洗,且不再弄脏。
因此佛陀教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 若我们一边作恶,一边洗心,是无法抗衡的,因为弄脏容易,洗净难。
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作恶,从身、语不作恶开始,即持戒。我们不作心恶,不放纵心散乱于恶所缘,此为有定,让心安住于善所缘。然后,再来彻底地洗涤心,即开发智慧,观察身的实相,观察心的实相,也就是观察三法印,这便是开发智慧。
若能做到,我们的心便会圆满洁白,而非一半白一半斑驳。在三藏中常用“圆白”一词,即洁白无瑕。当我们洗去恶,清净便自然生起,明亮也自然生起。
当我们断除恶,便已是行善,心便会明亮。何时断恶,即是行善,自净其意。《教诫波罗提木叉》虽分三部分,实为一体。若洗去恶,心自然善;心善,自然明亮。
4.7 修习毗婆舍那的成果
开发智慧,修习毗婆舍那,并非神秘之事,它只是训练心从不同角度去看。 原本,心只看“有我”,时刻如此看。我们来训练心,学习从不同角度看,见到“五蕴非我”的实相。要持续地看。
起初,可以稍加思维修习,对于某些前世未曾修习智慧、只修禅定的人。当心有了力量,心稳固起来,即使心已稳固成为知者、觉醒者,它仍不愿去观察蕴、界的运作,只是静静地觉知、空寂地觉知,这样的心是没用的,心尚未开发智慧。
若它不开发智慧,便需助其思维修习,助其思考,引导它学习从不同角度看,教它去看:此身无常,此身是苦,此身非我。当它学会从不同角度看,熟练之后,它便会自行观察。
引导它观察的阶段,尚非毗婆舍那。它能自行观察时,才是毗婆舍那。
若根性不锐利者,需助其思维修习。若根性真正锐利,一旦抓住“知者”,五蕴便会立即分离。
曾有一位居士,去拜见一位祖师,早上学法,晚上五蕴便已分离。因为他从小便能做到“知者”,曾修奢摩他,修入息“佛”、出息“陀”、数一,心便稳固起来,成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但不知如何继续,不知如何开发智慧,便停滞于此。当他遇到祖师,教他继续观察心,便来观察“心在身中何处”,在发、毛、爪、齿、皮、肉、筋、骨中吗?如此一路探寻,最终身体便分离为一部分,因为心本已是知者。当他刻意来观察身,便见到身分离出去,独立存在;来观察受,见到受分离出去;来观察行(即心的造作),乃至所思之事,也分离出去。例如,默念经文“Buddho susuddho karuṇāmahaṇṇavo”(佛陀,至净,慈悲如海),心便成为知者,念头与心便分离了。当心与念头分离,“知者”便会再次涌现,这是一个更高品质的“知者”,此时不只是静静地知,而是知且能见五蕴运作。但当我们有了“知者”,见到五蕴运作,若正念、智慧仍不足,不了知毗婆舍那的修行原则,我们便会去干预五蕴,干预心。例如,见到心流向所缘,便想“如何让心与所缘分离?”“如何让心整日稳固明亮?” 脑中尽是“如何做?”
我们修行时,内心深处是否总有“如何做?”这个念头?它一直在想,人人皆然,都会想如何做,无法禁止,因为它想做,认为做了才能得到。甚至还会自我安慰:“有志者事竟成。” 如此持续地努力,直至智慧与能力达到极限,那时才能得到实相。
但借由曾经的努力修行,这是在开发正念,使其更加敏锐;开发定,使其更加稳固;智慧也随之累积,见到名色自行运作。在我们刻意修行、想做的过程中,正念、定、慧便被逐步地训练得更加强大。到某一阶段,正念、定、慧成熟,便会自动运作。身体翻个身,便自行感觉到,无需刻意感觉;心中生起任何乐、苦、善、不善,便自行了知,无需刻意去了知。各种境界生起,它都能自行了知。此时,正念已自动生起,无需刻意。但在这自动生起之前,必须经过刻意的阶段。
因此,我们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并努力去做,这是在开发正念、定、慧。持续地做,终有一日会发现,“如何才能好”也是不恒常的。乐不恒常,静不恒常,“知者”亦不恒常。“知者”生起后,又会变为“思者”,或变为“专注者”,只有不恒常之物。于是便想求得恒常的好,恒常的乐,恒常的静。
若正念、智慧足够,便会想求道果涅槃,以求恒常的好、乐、静。若愚痴一些,便去修定,也很好,但只是在有定时好,有定时静,有定时乐。当定退失,一切便又消失,又得再修。这取决于正念与智慧的水平,能做到何种程度。
有些人想求道果涅槃,也是因为它好、它乐、它静。于是便挣扎着去寻求这些,认为若我们修行圆满,终有一日我们的心会恒常地好、乐、静。我们便认为“心即是我”,想把它做好,想把它做乐,想把它做静。暂时的好、乐、静不满足,要恒常的。
最终,拼尽全力,却发现好是暂时的,乐是暂时的,静是暂时的,“知者之心”也是暂时的,万事万物皆是暂时的,无一恒常。若心能接纳此实相,心便不再挣扎。 为何要挣扎?挣扎求好、求乐、求静,如何挣扎也得不到,即使得到也只是暂时的,很快又会消失。心便不再挣扎。
心之所以不再挣扎,是因为已挣扎到了极限。正念已至极限,定已至极限,智慧亦已至极限。正念至极限,即无需刻意了知,却整日整夜地了知。定亦是,心稳固,成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如此觉知,不迷失,至多是瞬间迷失,然后迅速回归觉知。想修更深的定,不知如何修;想修更强的念,不知如何修;想开发更深的慧,亦不知如何思维修习。已然穷途末路。念已修至无以复加,定亦修至无以复加,慧亦不知如何再深入思维修习。当心修行至极限,便会進入一种穷途末路的境界,它会停止挣扎,会断除“如何才能离苦”、“如何才能恒乐、恒好、恒静”的欲望,因为它已竭尽全力,却发现无能为力。
当心不再挣扎,心便只是“如实知见”。此时,才生起真正的“如实知见”。我们口中说的“如实知见”,并非真的,我们不肯“如实知见”,心中只有“如何才能更好”、“如何才能正确”。你们是否感觉到,修行者每日醒来便想“今天该如何做?” 便是如此想,直至智慧与能力达到极限,再也无法更好了,于是便接纳现状。心不再挣扎,心不再造作。
当心无造作,无挣扎,便在此停留片刻,有人是十五天,或多或少,称为心達“行舍智”。当心不再挣扎,便不造作,心会自动進入安止定。无论生起什么,只是了知,了知而不继续造作,称为心達“随顺智”。意指,无论生起什么,皆随顺它。随顺非指随之迷失,只是见到它生起,然后消失,仅此而已。不抗拒,不随之迷失,不接纳。它来则来,它去则去。此为心有“舍”,真正地随顺法之实相。
随顺一切实相,只见一实相:万物来了又去。心只见于此。
在心停止造作的阶段,若戒、定、慧、波罗蜜圆熟,心会自动進入安止定。为何能自动進入安止定?因为心不流向欲望,禅那便会自行生起。
心的本性,是必须在“有”中流转。“有”有三种:欲界有,即在欲望中流转,通过眼、耳、鼻、舌、身寻求享乐,持续不断。我们凡夫的心,在眼、耳、鼻、舌、身间旋转不休,是吗?这便是“欲有”,全称“欲界地”。若脱离欲有,便進入“色有”或“色界地”,即安住于了知色法。例如,觉知呼吸,心便不再理会外在世界,眼、耳、鼻、舌、身的所缘已无实义,心便汇集于内在单一所缘,或许只觉知呼吸,或只觉知身体,或只专注色法,专注光明、光相。
若心专注于色法,称为“色界地”。若心不在欲界地,不在色界地,便必入“无色界地”,舍弃色法,安住于名法,例如,心安住于“空”,安住于“一无所有”。
因此,有些人教导修行要安住于“空”,那是错误的,并非佛陀之道。那是“无色界地”,是另一种境界,另一种“有”而已。
现在,若我们正念、智慧足够,我们了知心向外攀缘眼、耳、鼻、舌、身是苦,心便不攀缘。当心不攀缘,心便脱离欲界地,進入色界地或无色界地,自行進入。
例如我们,持续培育正念,当正念、定、慧圆熟,心便不再迷恋色、声、香、味、触,它们已无法吸引心流失。至少在某个刹那是如此。当心了知流失是苦,心便稳固明亮,心便自动進入禅那。
因此,即使我们培育正念、智慧而不会入禅那,在即将生起圣道圣果的最后关头,从须陀洹道至阿罗汉道的每一阶段,心都会自行進入禅那。
除非是那些在禅那中开发智慧者,当圣道将生起时,无需退出禅那回到世间,无需回到欲界地,心可在禅那中直接断惑,这是另一类人。
但总而言之,圣道不生于欲界心。像我们凡夫,圣道必须生于色界地或无色界地,在那里断惑,心会自动進入禅那。
当心進入禅那,此时正念觉知于心,并非刻意觉知,它自行了知,因为它不攀缘眼、耳、鼻、舌、身、意,也不攀缘念头,它便止于一心。念安住于心,心稳固于心,定已圆满,稳固于心;念已圆满,觉知于心;慧已圆满,见到心中变动的一切实相。此时,心会波动两三刹那,有造作生起,但不知造作何物,只见某物生起,然后ดับ灭。会见到如此。
心会接纳生灭的法,不加干预。心会了知它无有实义,心已淡然,不再执取。只见心中造作浮现两三刹那,心保持真正的中舍,如实地、中舍地了知,不继续造作,心便会放下那生灭之法。
当它放下,便会逆流而上,趋向“知界”。“知界”即是心,但那是另一种心。旧心已ดับ灭,处于各种生命境界的心已ดับ灭,它逆流而上,趋向超越生命境界的心。在它放下旧心,逆流而上,但尚未到达“知界”,尚处于临界状态,已不执着五蕴,即不执着于心,但尚未到达“知界”,尚未到达“不死界”、“不死法”,尚未到达涅槃。
“知界”非涅槃,“知界”是见到涅槃。
它逆流而上,尚未到达“知界”,既非凡夫,亦非圣者。为何非凡夫?因为它已放下五蕴,最后放下的是心。为何非圣者?因为它尚未到达“知界”,尚未到达涅槃。“知界”是见到涅槃。此处称为“种姓智”,跨越种姓的智慧,从凡夫种姓跨越到圣者种姓。
因此,证得道果后,种姓已变,从凡夫种姓跨入圣者种姓。既非凡夫,因正在跨越;亦非圣者,只有一刹那心处于此临界状态。当它跨越,逆流而上,到达真心、法界、真知,此时圣道便会生起,包裹心的诸漏烦恼会被圣道劈开、摧毁,烦恼在瞬间被洗涤,刹那间断尽。如同按下电灯开关,瞬间光明,黑暗在那一刹那消失。
之后,会再见到涅槃两三刹那,但所见不同。有人见两刹那,有人见三刹那。根性极为锐利者,见三刹那;根性尚不锐利者,见两刹那。
因此,同一果位的圣者,其了知与理解亦不尽相同,其辩才亦不相同。见到涅槃,了知它就在眼前。涅槃从未消失,就在眼前,只是我们愚痴,所以不见。为何不见?因为只见到欲望,只见到色界有,只见到无色界有,心不知放下。
在“种姓智”,心从凡夫跨越为圣者的那一刻,它舍弃了一切,舍弃了欲界地、色界地、无色界地,跨入了圣者地、出世间地。
我们的任务,只是修行至圆满。何时圆满,何时便跨越种姓。在世俗谛上,姓氏未变;但在胜义谛上,已成为佛陀之子,有了新的种姓。
要逐步修行,需断四次。
断第一次后,当心从见到涅槃两三刹那的圣果中退出,心会回到我们所在的欲界地。心会退出,然后逆流思维修习:“刚才洗涤了什么?还剩下什么?” 如此反复思维修习。
我们有些人,平白无故地以为自己是圣者,却没有圣道生起的过程,只是自己想当然地认为证悟了。不要让心执着于任何生命境界,尤其不要让心执着于色界有、无色界有,执着于不动、空,保持心不动。
缘起
缘起至关重要, 若能彻见缘起,便能跨越生死轮回。
佛陀修习安般念,直至他的心稳固、轻安、柔软、敏捷、堪能,心成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然后他用这样的心来开发智慧,思维修习缘起。
开发智慧并非思考。我们读佛陀传记,会以为他是思考出来的,或当他的心稳固后,他提出问题:“何物存在,故有苦?” 然后以为他是想出答案:“因为‘生’存在,故有苦。”
若他能坐着想出来,那便不叫证悟了。他必须见到实法作为印证,才能证悟。
他必须亲见,所谓的“苦”,立于何处?“苦”立于名色,立于此身心,不立于别处,不立于虚空,不立于河水,苦立于此身心。
为何能得到名色?因为有“生”。“生”即是获得名色,获得六处:眼、耳、鼻、舌、身、意。何时心执取名色,何时便有“生”;何时有“生”,何时便执取了苦。因此,“生”为“苦”之缘。
“生”即出生,但不仅指从母胎出生,“生”是获得六处,即眼、耳、鼻、舌、身、意。简言之,即获得名色,心去执取名色,执取五蕴,此为“生”。
为何心会去执取名色?因为心造业,心挣扎,心造作。心挣扎造作之处,称为“有”。“有”即是心造业。心造业,即心有意图地运作,心思考、造作,称为心造作“有”。
若造作善,则为善有;造作恶,则为恶有。若造作时伴随贪,则为饿鬼有;若伴随嗔,则为地狱众生;若伴随痴,则为畜生有;若自我感强烈,则为阿修罗有。
贪心重者,整日修饰打扮,即是我们的心在造业,称为造作“有”。
“有”有两种。第一种称为“生有”,即由出生而来的“有”。例如我们生而为人,有人的“生有”。但另一种“有”是“业有”,是心一次次的运作。何时我们心生贪欲,我们的身体仍是人的“生有”,但我们的心已是饿鬼的“业有”。在我们的大“有”中,潜藏着这样的小“有”,不断循环。
当心造业,我们缺乏正念、智慧,心便会去执取某物。因为正念、智慧不足。
心之所以能造业,之所以能有“有”,是因为心去执取所缘。这执取所缘,称为“取”。
“取”的特征,是强烈的“爱”。“爱”是心的渴求。
因此,“爱”为“取”之缘。“爱”与“取”,实则皆是贪。爱是欲望,当欲望生起,心便去执取。执取,即是强烈的欲望,不只是想,而是跳过去抓住、执取所缘。
例如我们想修行,是否感觉到,早上醒来想修行,便已有了爱,然后跳过去抓住心,甚至揉捏它,翻来覆去地研究它。那便是造业,或造作“有”。
去执取它,占有它,那便是“生”。然后痛苦便在执取心的那一刻立即生起,沉重、负担感立即出现。痛苦与执取名色同时而来。
普通人时刻在伤害自心。欲望生起,便时刻在伤害自心,却看不见。因此,人们时刻有压力,却看不见。即使在欢笑时,压力仍潜藏其中,却看不见。实实在在的苦,但正念、智慧不足,便视之为乐。
他继续观察,“爱”从何而来?有烦恼便有爱。贪欲生起,便想得到、拥有、成为;嗔恚生起,便想让它消失;愚痴生起,便迷失。
烦恼紧随“受”而来,与受一同渗入。乐受生起,贪欲便生起;苦受生起,嗔恚便生起;乐、苦、舍受生起,愚痴便生起。它如此渗入。
他回溯观察,发现是“受”,即乐受、苦受,导致了烦恼的渗入,“爱”才因此生起。
因此,“受”为“爱”之缘。
“爱”是心的渴求。当心渴求,心便去抓住所缘,称为“取”。抓住后便来运作,造作这,造作那,造作善,造作恶,称为“有”。造作后便执取,执取名色,称为“生”。痛苦便因执取名色而生的负担而起,称为“苦”。
他继续观察,受能禁止吗?看,这难以理解。其他宗教总是想方设法去ดับ,但佛陀智慧,他了知“受”我们也无法断除。有“受”,即非乐则苦,非乐非苦则舍,时刻存在,因为“受”与每一心识刹那俱生。
若无法断除受,岂不也无法断除爱、取、有、生、苦?
他又继续观察,“受”从何而来?发现“受”来自“触”。眼见色,便生起乐受、苦受;耳闻声,便生起乐受、苦受;鼻闻香,舌尝味,身触物,亦生起乐受、苦受。
哦,“受”亦无法禁止,它由“触”而生。那接触所缘,能禁止吗?有眼便会见色,有耳便会闻声,有鼻便会闻香,有舌便会尝味,有身便会触物,有意便会思维修习。无法真正禁止。
只要“六处”尚在,六处尚能运作,“触”便存在,亦无法禁止。
佛法的艰深,是否感觉到,尽是无法控制之物。整个过程都无法控制。“受”无法禁止,“爱”之生起亦无法禁止,心去执取所缘亦无法禁止,心去造作亦无法禁止。爱、取、有,皆无法禁止。“生”,也无法命令禁止,无法控制。他发现了这个无法控制的过程。
其他人试图控制,试图断除爱,例如通过苦行。但他发现无法断除,只有一个无法控制却环环相扣的过程。
他又观察,何物存在,故有“触”?是眼、耳、鼻、舌、身、意存在。这亦无法禁止。若有眼、耳、鼻、舌、身、意,便会有“触”。眼、耳、鼻、舌、身、意此刻已存在,能禁止它不存在吗?亦无法禁止。
他又观察,何物导致眼、耳、鼻、舌、身、意的存在?发现当有“名色”,即有五蕴,便有眼、耳、鼻、舌、身、意。有眼、耳、鼻、舌、身、意,便有“触”。
名色由“识”而生,即心之投入。此处已难观察。
我们现在修行,能见到的是从有名色,有身心,有眼、耳、鼻、舌、身、意,然后接触所缘,直至生起烦恼、爱、取、有、生、苦。我们初学修行,能见到的是缘起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很难观察,即“无明”为“行”之缘,“行”为“识”之缘,“识”为“名色”之缘。
若曾修行,便会了知,若心处于有分心状态,无识生起来了别眼、耳、鼻、舌、身、意的所缘,眼、耳、鼻、舌、身、意便不显现,虽有如树木、石块,不感觉眼、耳、鼻、舌、身、意为我或我所有。
当识投入,触及心,心便生起;触及心所,各种感受、念想便生起。识扩展,遍及色法,色法便显现。
此法已难见,超出我们现阶段修行的智慧所能及。只能依逻辑推断,有名色、身心,是因为识投入母胎,才生为“我”,有了身心。
实际上,识亦可刹那刹那地投入,刹那刹那地生起名色。但此法已难观察,即识之投入,能生起,能投入名色,是因为有造作。若我们修行,会见到造作之流从内在浮现,从空无中,念头从空无中浮现,从空无中蔓延。当念头从空无中蔓延出来,心去了别它,识便生起,识便扩展,将了别作用遍及,如同按下开关,触及内在感受,内在感受便生起;触及身体,如同按下电灯开关,全身亮起。识投入名色,便有了名色,眼、耳、鼻、舌、身、意便同时获得。
造作从何处蔓延出来?从“无明”,即“不了知”中蔓延出来。
他观察直至“无明”,然后彻见,一切皆源于“不了知”,即“不了知苦”。
苦,即是五蕴。但我们认为五蕴是“我”。
还不了知什么?不了知集,不了知欲望是苦的起因。依赖欲望,心便投入新的生命境界,获得新的五蕴。或依赖欲望,心生起刹那的“业有”,造业,在那一刻便苦。
因此,“生”有两种。一种是生而为人,另一种是刹那的心生,皆是造作。欲望驱使挣扎造作,驱使造作有、生、苦。
缘起至关重要。若能彻见缘起,便能跨越生死轮回。缘起有十二支,十二支皆是名色之事。
佛陀教导了因果相续之法。万物之显现,非凭空而来,必有其因方能生。一物之显现,由众多因缘和合而成,非一对一。实际上,每一因缘,所有名色,皆是无我,依其职能相续运作,无人能控。
例如,贪欲将生,亦有其因。欲贪以欲寻为因,即思虑欲望之事。嗔恚以嗔寻为因。等等。每一法皆有因果相续,且有多重缘。例如,嗔恚生起前,基础是必须有嗔的随眠烦恼,必须接触不如意的所缘,接触时又无正念生起。一个境界的生起,有多种条件,皆无法控制、无法掌控。
有些佛陀,见到“识生名色”便彻悟,证得阿罗汉,成为佛陀。但我们的佛陀,追溯至“无明”才彻悟,成为阿罗汉。他彻见了万物因果相续的过程,了知每一法,无论色法、名法,皆无法禁止、无法掌控。只有一个自行运作、相续不断的造作过程,直至造作出“自我”,造作出苦。只有名色的造作,所有名色皆无法控制、无法掌控。
他的心见到了名色的实相,了知它们造作出苦。因此,他断除了对所有名色的执取。之所以能跨越生死轮回,证得阿罗汉果,是因为断除了对所有名色的执取,因为他已彻见苦的聚集。
所有名色,如锁链般生灭相续,循环往复。万物有因则生,无因则ดับ,无法控制。
他因彻见缘起而证得阿罗汉果,即是彻见名色。但他是在“无我”的角度彻见名色,即无法控制、无法掌控。当他的心不执取名色,他的心便不再执取世间任何事物,他便成为世间第一位阿罗汉。
只要尚未了知苦,集,即欲望,便不会永久ดับ灭,只会暂时ดับ灭。例如,我们想得到某物,买来满足欲望后,那个欲望便消失了,这称为暂时ดับ灭。
心想得到某物,直接观察它,烦恼便ดับ,爱便ดับ,欲望便消失。这也是暂时ดับ灭。
如今我们也是暂时ดับ灭烦恼,如同不会灭火之人,见到火焰消失便停止浇水,不久又会复燃,因为火种尚在。必须ดับ至根源,摧毁无明。
彻知苦,才能彻底断除集。 彻知苦,即了知所谓的“我”,纯然是苦。除了苦,无物生起;除了苦,无物住立;除了苦,无物ดับ滅。 只有苦在生、住、灭。它并非美好珍贵之物。
当了知此实相,那想让蕴、界快乐的欲望便不会生起,想让蕴、界离苦的欲望也不会生起。
为何不想让它快乐?因为知道它不可能快乐,它本身即是苦。
为何不想让它离苦?因为知道它无法离苦,它本身即是苦。
看,何时彻知苦,集便被自动断除,欲望便不复存在。它本身即是苦,想让它离苦是不可能的。如同想让火不热,但火必须热,因为热是它的属性。无法想让火不热,也无法想让火变冷。
因此,若彻知苦,集便被自动断除。想让蕴快乐的欲望便不复存在,想让蕴离苦的欲望亦不复存在。它无法离苦,无法快乐,因为它本身即是苦;它无法离苦,因为它本身即是苦。
结语
佛陀出世,难中之难。 佛法显现于世,难中之难。 僧伽,即凡夫俗子, 能自我提升至究竟清净,难中之难。 这是难中之难的机缘。
此刻,我们已得此机缘, 因为佛法尚住世。 我们的责任,是精勤学习佛法, 并付诸修行。 所应修行的,即是戒、定、慧。
我们学习佛法,是为了付诸修行,而非为了消遣。佛法是崇高的,是稀有的。
佛陀时代,有一位国王,名为“摩诃劫宾那王”。他从商人处听闻:
“佛陀已出世于世间。” “佛法已出世于世间。” “僧伽已出世于世间。”
他几乎震惊,连问三遍:“你说的什么?” 确认后,他命商人去向王后领赏,然后将王位禅让给王后,自己骑马出城,去拜见佛陀。而王后,得知佛、法、僧已出世,亦不愿为王,也出家修行,最终二人都证得阿罗汉果。
他们二人都见到了此事的重大意义:佛陀出世,难中之难;佛法显现于世,难中之难;僧伽,即凡夫俗子,能自我提升至究竟清净,难中之难。 这是难中之难的机缘。
此刻,我们已得此机缘,因为佛法尚住世。我们的责任,是精勤学习佛法,并付诸修行,而非为了听着好玩,或为了炫耀,或为了争辩。所应修行的,即是戒、定、慧。
要训练持戒,先下定决心断除身、语的恶行不善。起初,下定决心断除,便能持守五戒、八戒。
然后,要多有正念,觉知心中生起的烦恼。若我们有正念,能觉知心中生起的烦恼,戒便会自动生起。人之所以犯戒,是因为烦恼覆盖了心。但若烦恼生于心,我们有正念觉知,烦恼便无法覆盖心,我们便会自动地不犯戒。持戒便会变得容易,此时已非五戒,因为若能守护一心,不为烦恼所染,便不会犯戒,多少条戒都不会犯。
接着,来学习自心。若心安住于单一快乐所缘,便得宁静;若心能觉知心的流失,便得稳固之心。
如此训练,直至心稳固。若无力,便训练心宁静。但最好每日都分出时间让心宁静,然后再训练心稳固。当心稳固,便致力于开发智慧。
开发智慧的方法,亦是依赖正念了知名色、身心,了知每一境界。以一颗稳固的心、中舍的心去了知。起初,心稳固起来,我们见到境界,例如见到贪欲生起,心尚未中舍,但心是稳固的,见到贪欲在远处,心是一部分,但心仍厌恶贪欲,心不中舍。要觉知这不中舍的心,心便会中舍起来。
当善法生起,见到善法在远处,心是一部分,心与善法分离。若心对善法生起喜爱,要觉知生起的喜爱,喜爱便ดับ,心便会中舍。
当乐受生起,要觉知,见到乐受在远处,乐受与心是两回事。当乐受生起,心喜爱起来,要觉知它。当苦受生起,心厌恶起来,要觉知它。
觉知境界是第一步。觉知境界后,觉知心是第二步。
若心喜爱,要觉知;若心厌恶,要觉知。若觉知,心便会自行進入中舍。
修行便会归结为隆波帕默所说的一句话:“以一颗稳固且中舍的心,如实觉知身心。” 若心不稳固,便不见身心的实相,即不见三法印。若说得最简短,即是“如实觉知身心”。仅此而已,便是“毗婆舍那”一词的含义。“实相”即是三法印。隆波帕默之所以补充说“必须以一颗稳固且中舍的心了知”,是为了强调,我们要开发智慧,必须有一颗具有正定的心,即一颗稳固且中舍的心,而非宁静之心。
若以沉浸或迷失于所缘的心去了知,便不见实相。心必须稳固,分离出来成为观察者,中舍地观察,远远地、舒适地观察,观察后不迷失于喜爱,不迷失于厌恶。
我们持戒,修定,训练心成为知者、觉醒者、稳固者,只是为了让心有足够的品质来了知蕴、界、身、心的实相而已。当我们见到蕴、界、身、心的实相是受三法印支配,无一可依,只有生灭,只有变异,只有逼迫,只有无法掌控,不再是美好珍贵之物,此蕴、界充满了苦,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逼迫,心便会放下执取。
因此佛陀教导:因为如实见到名色(即见到三法印),故生厌离;因厌离,故离染(即放下执取);因离染,故解脱。 心便放下名色、蕴、界,解脱出来。解脱后,自知已解脱,心已无负担。“生”(即获得眼、耳、鼻、舌、身、意,获得名色)已尽,不再执取。梵行(即学习修行,如我们持戒、修定、开发智慧,此为修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再无为了脱而需做之事,便得安乐。
我们学习了佛教的原则,不要浪费这宝贵的机缘。浪费了生而为人的机缘,浪费了得遇佛法的机缘。听隆波帕默或各位祖师说法,是教理。必须亲身修行,亲身离苦,才能了知佛法的价值,才会敬爱佛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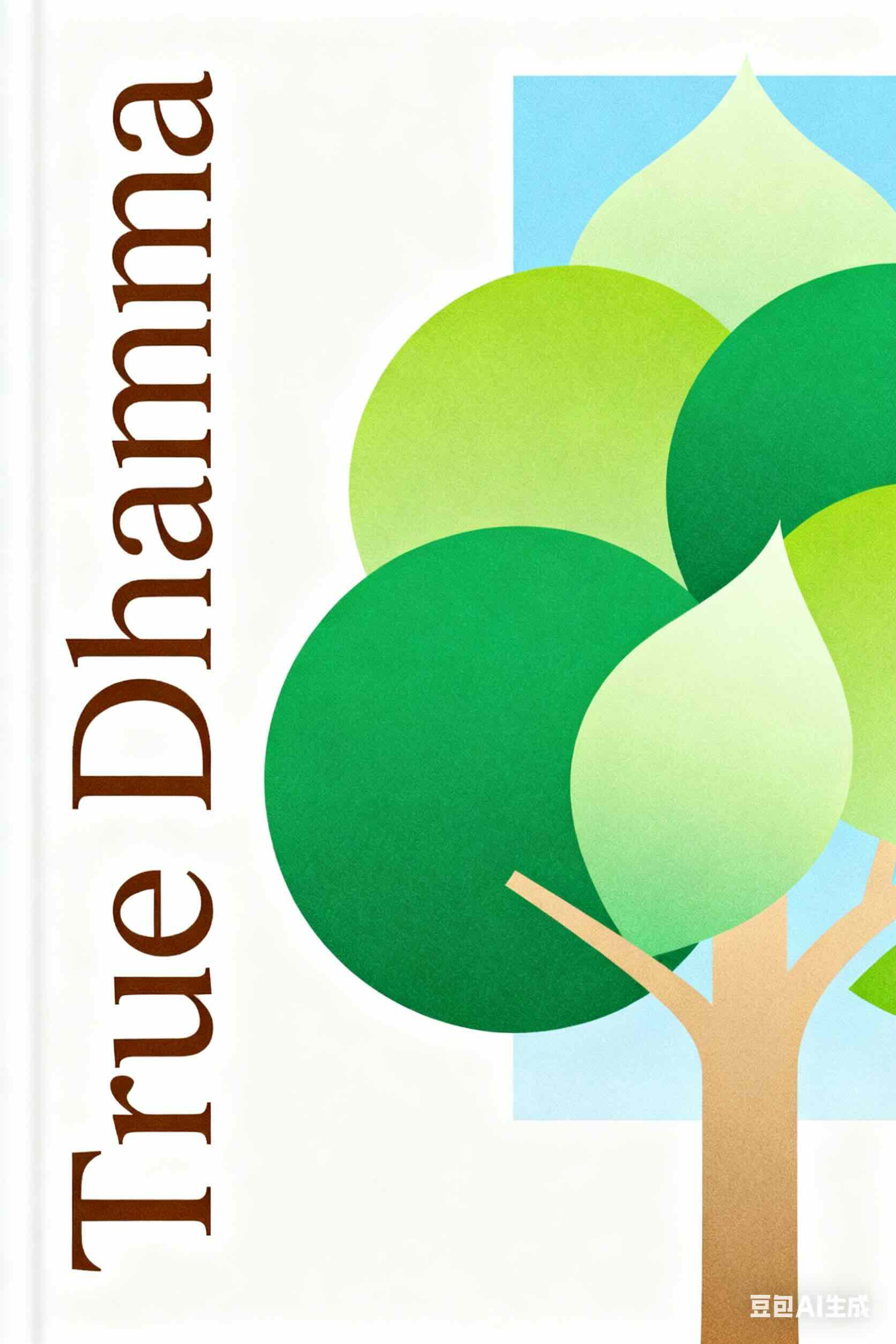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下载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