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住
隆波帕默尊者, 正定, 南传上座部佛法 ·Index
心安住 - 隆波帕默尊者 - 摘要
本书教导如何培育一颗安住、觉醒的心,通过觉知身心的实相,逐步开发智慧,最终从烦恼中解脱。要及时地觉知那颗溜走去思考的心。心溜去想了,我们觉知到它。在觉知的那一刹那,那个念头就灭了,取而代之的是“知者之心”生起。
我们都是烦恼的奴隶
我们佛教徒有幸得遇佛法,就必须学习佛陀的教法。佛法并非儿戏,我们要学习佛陀教导了什么。佛陀教法的核心目标是导向离苦。因此,我们佛教徒所得到的答案,就是掌握一种让生命减少痛苦乃至彻底无苦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善巧地修行,内心的痛苦就会彻底消失。
我们每个人都被一个“老板”所控制,事实上,我们的老板就是“贪爱”,它整天都在给我们下达指令。一会儿心想要这个,欲望无时无刻不在生起。一会儿想看,一会儿想听,一会儿想闻,一会儿想尝,一会儿想身体有所触碰,一会儿想思考、回忆,一会儿想造作。心里只有各种“想要”在不断生起。
每当心中生起“想要”时,心就会开始挣扎,变得躁动不安,失去平衡,痛苦便随之而来。烦恼与贪爱是摧残我们的元凶,它让我们失去自由。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谁也命令不了我们。但事实上,烦恼和贪爱整天都在控制着我们,欲望整天都在命令我们,而我们却对此浑然不觉。它是世间最高明的“老板”,这个所谓的“贪爱”,它命令我们去做一切事情:去看电影,去听歌,去这里,去那里,做这个,做那个。
如果我们顺从它的意愿,就会得到片刻的快乐和舒适。比如它叫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去看了,就感到片刻的轻松。但电影终将结束,剩下的只是身体自然的疲惫和痛苦,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即使是修行高深的祖师大德,他们的身体依然会经历痛苦,但他们的心却不再受苦。
我们来修行,就是为了将痛苦从我们的心中根除。那个让心产生痛苦的罪魁祸首,就是所有的烦恼。一旦这些烦恼,比如贪爱,侵占了我们的心,痛苦便会在心中生起。至于身体的痛苦,那是无法彻底根除的,只能时时去应对。比如困了就去睡,饿了就去吃,不舒服就去看医生。但是,由烦恼和贪爱引起的心中之苦,我们必须起来与它抗争,不要向它投降。烦恼和贪爱主宰这个世界已经太久太久了,我们不知不觉地沦为它的奴隶。
这个“贪爱”非常厉害,它是一个我们从未真正认识的“老板”。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没人能命令我。但实际上,烦恼和贪爱整天都在折磨我们,压迫我们,命令我们。它实在是太狡猾了,它统治着整个世界。当我们顺从它的时候,它会给我们一点点快乐作为奖励,然后又下达新的命令,让我们去做别的事情。我们做了那件事,又感到一点点满足,它就又命令我们去做新的事。一天到晚,我们都在被它指使,完全没有自我,失去了自由。
那我们该如何将自己从这些烦恼和贪爱中解放出来呢?答案是:必须去觉知它。烦恼和贪爱在哪里?它就在我们的心里。它累世累劫地积聚,力量非常强大。烦恼分为很多层次,有粗重的烦恼,比如强烈的愤怒、强烈的贪婪、强烈的迷茫、强烈的散乱、对三宝强烈的怀疑。比如今天还信佛,过几天就不信了,甚至怀疑佛陀是否真的存在,就这样不断地怀疑。强烈的烦恼会让我们违犯戒律。比如强烈的贪婪生起,就可能去偷盗;强烈的欲望生起,就可能去邪淫。它会让我们违犯戒律和道德。
它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老板”。它懂得奖罚分明。如果我们听从烦恼和贪爱的话,就会感到片刻的快乐;如果我们不听从它,就会感到痛苦。它命令我们去看电影,不去看,心里就烦躁;想看电影的念头让心烦乱,想听歌的念头让心烦乱,想做这做那,而一旦想做的没做成,心里就充满了烦恼。
修行的第一步:持戒
首先,对于粗重的烦恼,我们无法禁止它的生起,但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无论烦恼多重,都要守持五戒。不要因为烦恼而犯戒。每天醒来,就要下定决心:“今天我绝不犯戒。”
粗重的烦恼,比如强烈的嗔恨心生起时,就会去骂人、打人。这些粗重的烦恼必须用“戒”来对治。粗重的烦恼是无法用“定”或“慧”来对治的。当粗重的烦恼生起时,定力和智慧都会被摧毁,根本无力对抗。因此,我们要先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犯五戒。我不会要求太多,不要求你们持八戒或十戒,能把五戒持好就行,但要真正做到。
五戒非常重要。八正道中的正语就涵盖了戒律的第四条;正业涵盖了第一、二、三条;正命指的是以正当的方式谋生,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这也包含在戒律之中。因此,五戒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舍弃了五戒,心就会散乱。比如我们想去偷东西,心是不可能平静的。但如果我们想布施,心就会平静,对吗?想去拿别人的东西,心是静不下来的,想去骂人、打人,心也静不下来。但是,如果我们原谅别人,心就平静了。
因此,持戒至少能让我们获得另一种善法,那就是更容易获得禅定。有戒,则定易成。心平静了,有了定力之后,再来修习开发智慧,去觉知身心的实相,也就是名法与色法的实相。
作为佛教徒,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布施和持戒的层面,那太可惜了。我们生而为人,得遇佛法,这是一个殊胜的机缘。布施、持戒是善法,但还不是最好的。有更高层次的善法。如果心有了定,那就是比单纯持戒更高的善法。
- 戒,是对治粗重烦恼的工具。
- 定,是对治中等烦恼的工具。
- 慧,是对治微细烦恼的工具。
中等层次的烦恼,就是心的各种散乱。比如,心散乱到色声香味触中,这称为“欲乐”;心散乱到不满意的人事物上,这称为“嗔恨”;心散乱地一会儿抓这个所缘,一会儿抓那个所缘,看不清也跟不上,这称为“掉举”;心散乱,然后烦躁不安,懊悔自己没能断恶修善,这称为“追悔”;心过度思考而产生怀疑,对三宝摇摆不定,这称为“疑”;以及心散乱地沉湎于萎靡昏沉的所缘中,这称为“昏沉睡眠”。
心散乱,就是没有禅定。没有禅定的心,是无法开发智慧的。所以,我们要先来训练我们的心,让它不散乱。首先要持戒,这样心就容易平静。持戒之后,再来训练让心安住于单一的所缘,心就会生起禅定。
培育禅定:让心平静下来
训练心安住于单一所缘的方法并不难。比如有些人习惯念“佛陀”,那就持续地和“佛陀”在一起。在心里默念“佛陀”。修习奢摩他或者说让心宁静,有一个秘诀,那就是不要去强迫或压制心,非要让它静下来,它是不会听话的。
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顽皮的孩子,我们命令他“要乖”,他不会听话的,他会偷偷溜到外面去玩。就算你拿着棍子去追打他,一不留神,他又跑出去了。心也是这样,它总是喜欢到处游荡。所以,我们必须用一些东西来“引诱”它。比如,不想让孩子跑到屋外去玩,就要找些他喜欢的玩具或零食来吸引他。如果孩子喜欢玩具,就给他玩具玩,他就不会跑出去了。如果孩子喜欢吃零食,就给他零食吃,他就待在家里了。
我们的心也像孩子一样,我们必须用一些东西来“引诱”它,而不是任由它毫无目标地到处攀缘,流浪到外在的世界。我们要找一个我们自己熟悉的所缘。有的人习惯念“佛陀”,那就念“佛陀”;有的人习惯觉知呼吸,那就觉知呼吸;有的人练习观察腹部起伏并且觉得很舒服,那就可以观察腹部起伏。有的人习惯经行,那就可以去经行。但目的不是为了念诵“佛陀”、不是为了觉知呼吸、不是为了看腹部起伏,也不是为了经行而去强迫心。试着改变方法,不要总是强迫心静下来——它不会静下来,反而会更紧张。我们转而轻松地觉知一个单一且舒适的所缘,心自然会平静下来。心必须是舒适的。这是一个秘诀。
大家要记住,要让心能够平静,必须为它找一个舒适的所缘来引诱它。就像引诱小孩子让他不再顽皮,必须给他喜欢的好东西。他才会不乱跑。有的人喜欢念“佛陀”,那就用“佛陀”这个所缘。轻松地念“佛陀”,不是为了强迫心而念,而是念“佛陀”的同时,时时去觉知自己的心。念着“佛陀”,心跑去想了,就要及时知道心跑去想了。
有些人习惯觉知呼吸,那就觉知呼吸,轻松地觉知。心随着呼吸进,随着呼吸出,心跑了就及时知道。有些人习惯观察腹部起伏,那就观察腹部起伏。心跑去想了,就及时知道;心跑去紧盯腹部了,也及时知道。要及时地觉知自己的心。当我们能及时地觉知自己的心,而又不强迫它时,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慢慢地变得听话,然后慢慢地安住下来,汇集起来。
我从小就开始练习这个法门,小时候跟我的父亲学习。入息念“佛”,出息念“陀”。他还让我数数,入息“佛”,出息“陀”,数一;入息“佛”,出息“陀”,数二。找任何你习惯的所缘都可以。谁习惯念“佛陀”,就念“佛陀”;谁习惯觉知呼吸,就觉知呼吸;谁习惯念“佛陀”并配合呼吸,那就念“佛陀”并配合呼吸;谁习惯观察腹部起伏,那就观察腹部起伏。这些方法都一样,没有好坏之分。
但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强迫心静止下来。心越是强迫,越是静不下来。我们是“引诱”它。轻松地念“佛陀”,心跑了,就及时知道。轻松地修行,心就会快乐。心一快乐,它就不会到处乱跑了。或者来觉知呼吸,轻松地呼吸。有些人喜欢呼吸,呼吸的时候感到快乐,心就会平静地和呼吸待在一起。不要去强迫它。
每天花一点时间来让心平静。对于在家人来说,每天十分钟、十五分钟也很好。慢慢地,时间可以自己增加,因为心在修行中尝到了法喜。
我自己在寺庙教导弟子,大部分都是像你们这样的都市人。都市人每天想的都是工作,各种各样的事情,头都大了。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每天打坐三个小时,恐怕没人会来。坐下来心里就烦躁,根本坐不住。所以一开始,我只要求每天五分钟、十分钟。来观察自己的心,念着“佛陀”,及时地觉知心;呼吸着,及时地觉知心;看着腹部起伏,及时地觉知心。比如观察腹部起伏,心跑去想了,及时知道;心跑去紧盯腹部,也及时知道。来觉知呼吸,心跑去想了,及时知道;心跑去紧盯呼吸,也及时知道。要时时地觉知自己的心。
当我们能够及时地觉知自己的心,而不去强迫它时,它会慢慢地平静、驯服,然后慢慢地安住、汇集,成为一个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一开始练习,一天十分钟,不要太多。如果一开始就要求一天一小时,不出两三天就放弃了。跟我学法的,我先让一天十分钟。当心开始平静下来后,现在就能坐很久了。现在,打坐、经行一天好几个小时都可以,因为他们感到了快乐。
呼吸的时候感到快乐,呼吸多久都可以。念“佛陀”的时候感到快乐,念多久“佛陀”都可以。
这是一个秘诀:修行若要获得宁静,修习奢摩他禅,要做得轻松,但不是懒惰。要对自己有诚信,每天都要坚持做。比如像你们这些穿白衣的修行者,一天一小时能做到吗?看,已经开始泄气了。要求一小时就不干了。半小时行吗?行的有几个人?剩下的都沉默了。十分钟行吗?十分钟,只要求十分钟。这是为了你们自己,不是为了我。你自己坐,你自己受益。
开发智慧:毗婆舍那的修行
当我们的心平静、安适之后,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一步,那就太可惜了。很多后来的佛教徒修行只为了求得快乐和宁静。
我们修习奢摩他,是为了对抗中等层次的烦恼,也就是五盖。当心散乱于喜爱或不喜爱的所缘,散乱于摇摆不定,散乱于怀疑,散乱于昏沉时,我们就把心拉回来,安住于一个舒适的单一所缘,心不散乱了。这就是对治中等层次烦恼(五盖)的方法。
接下来,就要对治微细层次的烦恼。微细层次的烦恼就是无明,或各种邪见,其根源是“无明”。它不知道什么?它不知道生命的实相。不了解生命实相的人,就会在苦海中沉沦,痛苦会不断地侵袭内心。如果我们了知生命的实相,心就会慢慢地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构成我们生命的,就是名法与色法,也就是身与心,也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我们来学习和觉知这些被称为“自我”的东西,学习我们自己的生命。构成我们生命的就是身与心。我们来学习觉知身、觉知心,来时时地分离名色、分离五蕴。
然后,我们会进一步去觉知身心的实相。学习身心实相的过程,称为“毗婆舍那”。这是开发智慧的核心部分。“人因智慧而得清净”,人不是靠戒和定而得清净。戒和定是基础,是过程,是帮助我们进而开发智慧、觉知那个被称为“自我”的实相的工具。
我们所谓的“自我”,其真相是什么?“自我”真的存在吗?我们来学习,直到亲见这一点。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自我”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自我”,这个“自我”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身份,有什么背景等等。我们觉得“自我”真实存在。但它其实只是世俗谛层面的真实。
让我们见到名色、五蕴实相的方法,见到它们并非“我”、非“我所”的方法,就是毗婆舍那。它的原则很简单,就是:“要有念住,如实地去觉知身,觉知心,要用一颗安住且中舍的心去觉知”。安住且中舍的心,就是有“定”的心,但这种“定”和前面讲的宁静的“定”又不一样。
两种定:奢摩他与毗婆舍那
“定”有两种,大家要好好学习。 第一种定是奢摩他,追求心的宁静。 第二种定是毗婆舍那,追求心的安住,但在安住中又包含了宁静。
大家有谁见过隆布特吗?他教导过关于“禅那”和“定”的区别。他所说的“禅那”,指的是心专注、紧盯于单一所缘,心与所缘合一、安住在所缘中,从而获得宁静。这种定,隆布特称之为“禅那”。在教理上,这称为“所缘专注定”。隆布特把它简化为“禅那”。就是心去紧盯一个所缘,比如持续念“佛陀”,心不离开“佛陀”,从而获得快乐和宁静。观察腹部起伏,心不离开腹部,心就平静了,获得了快乐。观察呼吸,心不离开呼吸,心就平静了。心紧盯在单一所缘,安稳地待在单一所缘中,隆布特称之为“禅那”。这种“定”是带着“愚痴”的快乐,无法开发智慧。
第二种定,隆布特称之为“定”。在教理上,它称为“相专注定”。
- 隆布特所说的“禅那”,在教理上称为“所缘专注定”。心安住于单一所缘,感到舒适、快乐,但有些“愚痴”,无法开发智慧。
- 隆布特所说的“定”,在教理上称为“相专注定”,也就是心安住,成为知者、观者。心不再是思考者、造作者。
隆布特将心分为“想蕴之心”和“觉知之心”。“想蕴之心”是思考者、造作者;而“觉知之心”是安住的知者、观者。这是隆布特的核心教法,分为两对:“想蕴之心”与“觉知之心”,“禅那”与“定”。“禅那”是导向宁静的定;“定”是心的安住,它不只是宁静,而是安住并抽身出来成为知者、观者。
开发“知者”之心
二十多年前,我刚开始参访善知识,去任何寺庙,无论是拜见隆布特、隆布廉,还是阿姜摩诃布瓦,或其他任何一位大德,都会听到他们反复提及一个词——“知者之心”。到这个寺庙听到“知者之心”,到那个寺庙也听到“知者之心”。这个“知者之心”,就是隆布特所说的有“定”的心,也就是具备“相专注定”的心。心安住,成为知者、观者。
我们必须训练自己,让心成为这个“知者”。如何训练呢?
对于那些禅定功夫很好的人,有一个方法。先修习禅定,心平静下来。一开始念“佛陀”或觉知呼吸,当心平静下来后,呼吸的感受消失了,“佛陀”的念头也消失了,心会“腾”地一下凸显出来,成为知者、观者。如果通过修习禅定而证得了这个“知者”,那么出定之后,这个“知者”的状态可以维持很长时间,有时可以持续好几天。
但如果我们无法进入那么深的禅定,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有一个训练的方法。那就是去及时地觉知那颗溜走去思考的心。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帮忙记住,非常重要。要时时地觉知那颗跑去想的心。
心溜去想了,“嗖”地一下,觉知到它。“嗖”地一下,觉知到它。就这样不断地练习。最终,心会安住下来,成为知者。但这个“知者”是刹那生灭的,维持不久。心跑去想了,我们觉知到它。在觉知的那一刹那,那个念头就灭了,取而代之的是“知者之心”生起。
我们每天的心,都沉沦在念头的世界里,对吗?整天都在想。有谁一天不想事情吗?没有。就算是阿罗汉也思考,他们不是木头石块。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从未觉知到它。一旦我们觉知到“心刚才偷跑去想了”,心“嗖”地跑去想了,就在那一刻,心会“啪”地一下弹回来,成为知者。它不再是思考者,而是转变为知者。
所以我们必须去训练,训练让心成为知者、观者。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慢慢忘记了祖师大德们的这些珍贵教导,以为禅定就是坐着让心宁静。宁静的禅定(第一种定)也很好,不是不好,但它不是最好的,因为它无法开发智慧,只是停留在那里而已。
我们来训练让心安住,成为知者、观者。训练的方法就是用“念”去及时地觉知那颗流去想的心。我们的心整天都在跑去想。当心“嗖“地一下流去想时,我们保持觉知。我们可以念“佛陀”或觉知呼吸作为辅助。念着“佛陀”,觉知着呼吸,当心跑去想了,就及时地知道。就在我们知道“心跑去想了”的那一刻,心会立即停止思考,那个能知的“心”就会生起作为替代。
分离名色
最终,我们会生起一个“知者”,心会安住下来,成为知者、观者。这时,我们就可以开发智慧了。当心安住成为知者、观者之后,接下来的功课就是分离名色、分离五蕴。不能只是安住在那儿,傻傻地待着,那样就浪费了机会。
阿姜摩诃布瓦教导说:“如果不观察、不分离名色五蕴,就别吹牛说自己在开发智慧。”那不是真的开发智慧。所以我们必须来学习分离名色五蕴。
如何分离呢?当我们的心安住成为知者、观者之后,不要只是静静地待着,那样太浪费了。要来开发智慧。静静地坐下来,现在大家就正在坐着,心是安住的。一会儿它又会想新的东西,想了新的东西,又去觉知它。当心跑去想,我们频繁地去觉知,慢慢地,觉知会变得相续。
这个觉知的相续,就像电灯的光。电灯的光其实是在不断地熄灭的,一秒钟之内熄灭几十次。但因为它熄灭得太快,灭了又亮,我们会感觉光是持续的。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训练它一刹那、一刹那地觉知,心跑了就觉知。最终,我们会感到一种相续的觉知生起,心会安住、凸显出来,成为知者、观者。这也是一种选择,适合那些无法修习“禅那”的人。
无论是比丘还是居士,如果禅定修得好,我都会建议他们先修习禅定,让心成为知者。这样是最好的。但如果做不到,比如在家的居士没有太多时间打坐,一天坐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一开始就慢慢练习,但最关键的是,要及时地觉知那颗溜去想的心。记住这一点,这非常非常重要。心溜去想了,就觉知它。
毗婆舍那的方法,就是学习分解这个所谓的“自我”,将它分解成不同的部分,称为“分离名色、分离五蕴”。首先,先将身和心分开。
就像我们有一辆车,我们认为“车”是真实存在的。但如果我们把车拆开,先把轮子拆下来,轮子不是车,对吗?但车不能没有轮子。看,我们把它拆解。车身也不是车,座椅也不是车,方向盘也不是车,发动机也不是车,油箱也不是车。你看,当我们把车拆成一个个零件时,会发现“车”已经不存在了。“车”只是我们将这些零件组合在一起后,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而已。
毗婆舍那的方法,就是学习分解这个所谓的“自我”,将它分解成不同的部分,称为“分离名色、分离五蕴”。首先,先将身和心分开。
慢慢地坐着,去感觉。不要让心飘走,要先感觉到这个身体。当你感觉到这个身体,看到这个正在坐着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坐着,不断地去观察,不要急着动。坐久一点,就会看到,身体只是身体的部分,心只是心的部分,身和心是两回事。
能感觉到吗?这个正在坐着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而我们的心是观者。它会自己分开。心会自己分离出来成为观者。看到身体在坐着,心是观者;看到身体在点头,心是观者;看到身体在举手,心是是观者;看到身体站、行、坐、卧,心是观者。
就这样不断地练习,不断地分离,就会看到心是观者,它会慢慢地分离。身体是身体的部分,心是心的部分。慢慢地分离,就会发现身和心是两回事。这样,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所谓的“自我”分解成了两个部分。
心是知者、观者。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当我们坐久了,身体会酸痛。看,这个酸痛和麻木,本来是没有的。我们的身体本来坐得很舒服。酸痛和麻-木是后来插入的、冒出来的东西。所以,酸痛和麻木不是身体,它们是后来冒出来的另一回事,是与身体不同的东西。这个酸痛和麻-木,在佛法里称为“受”,即苦受、乐受。在身体上可以有,在心里也可以有。身体上的苦受、乐受,以及心里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个“受”,它不是身体,也不是心。
比如我们坐久了,会酸痛。就慢慢地观察,安适地观察。这个“痛”,是心去觉知的对象。“痛”是插入到身体里的东西,它不是身体本身,也不是心,因为它是被心所觉知的。
看,我们正在逐步分解。当痛得很厉害的时候,不要急着动,忍耐一下。一开始忍耐,心会开始挣扎,比如会担心身体:“这么久了,会不会瘫痪?以后走不了了,谁来照顾我?” 心开始散乱了,开始胡思乱想,各种担忧生起。这个身体的“痛”,是在身体上;而这份挣扎、烦躁,是在心里。所以,“痛”和“烦躁”是两回事,属于不同的“蕴”。这份烦躁不安,佛法称之为“行蕴”。它们是不同的蕴。
我们来学习分离这个所谓的“自我”。我们会看到,挣扎是心去觉知的对象,它不是心,也不是身体,也不是“受”(身体的痛)。它们是各不相同的东西。就这样慢慢地去分离。
每天慢慢地练习,慢慢地分离。无论是在工作,扫地,拖地,洗衣服,行、住、坐、卧,都去观察身体在工作,而心是观者。身体酸痛了,觉知它;心里快乐、安适,觉知它;心里生起贪、嗔、痴,觉知它。最终,我们会把名色、五蕴分离开来。我们会看到:
- 身体不是“我”。它只是心去觉知的对象,就像一个机器人在走来走去。身体里没有“我”。
- 快乐和痛苦也不是“我”。它们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无法命令它们生起或消失。比如,命令自己“要快乐”,是做不到的;禁止痛苦生起,也做不到。当快乐生起时,想留住它,也留不住;当痛苦生起时,想赶走它,也赶不走。它们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 善法和不善法,比如贪、嗔、痴的生起,也是暂时的。有谁能一直生气吗?有谁能一直贪婪吗?没有。它们都是生起,然后就灭去了。
就这样去观察,我们会看到,身体不是“我”。这个身体是不稳定的(无常),一会儿出息,一会儿入息;一会儿站,一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卧。身体充满了苦,坐着也苦,走着也苦,躺着也苦。晚上睡觉要翻身大约四十次,因为它酸痛、不舒服。我们从未觉知,从未看见,以为我们的身体不苦。事实上,它时时刻刻都在苦中。
照见五蕴的实相
至于心本身,要怎么观察呢?也要慢慢地去学习观察。心,一会儿跑到眼睛,去“看”;一会儿跑到耳朵,去“听”。它不只是跑去“听”就完了,大家仔细观察,现在正在听我说法,一会儿看看我的脸,对吗?一会儿又认真听,对吗?一会儿又跑去想了,对吗?看、听、想交替进行。不只是听,听着听着就跑去想了,对吗?然后又看看我的脸,然后又认真听。在认真听的时候,并没有在看我的脸。听了一会儿,又跑去想了。
看,心是变化的。一会儿是看的心,一会儿是听的心,一会儿是想的心。心生灭变化,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门头不断地生灭。心生于眼、耳、鼻、舌、身、意。这是无法命令的,它是自己生起的。一会儿去看,一会儿去听,一会儿去想。
大家现在就如实地观察下去,是真的吗?听着听着就跑去想了,是真的吗?要学习觉知这一点。我们会看到,一会儿听,一会儿想。心跑去听,我们并没有“意图”要去听;心跑去想,我们也没有“意图”要去想。它是它自己的事。
- 当我们看到它在六根门头生灭,这就是“无常”。
- 当我们看到它在任何一个根门,比如在眼睛,也无法持久地停留,这就是“苦”。
- 当我们看到我们无法驾驭它,这就是“无我”。
看,我们来观察这个所谓的“自我”,也就是五蕴:色蕴(身)、受蕴、想蕴、行蕴,以及识蕴(心)。我们会看到它们都只是生灭、生灭,不断地变化。反复地去观察,就会看到:
- 这个正在呼吸的身体,不是我。
- 快乐和痛苦,不是我。
- 善法与不善法,不是我。
- 心本身,也不是我。
当你这样修行,你就会亲见,这个身体里没有“我”,这个心里也没有“我”。“自我”是由“想”而生起的。必须先迷失,然后才会去想。心一旦迷失,就会去思考;心一思考,“自我”就生起了。如果心有念住,觉知自己,心就不会迷失在念头里,“自我”就不会生起。“自我”纯粹是由念头产生的,就像“车”这个词一样,我们以为有车,但实际上它只是许多零件的组合。这个所谓的“自我”也是一样,我们以为有“我”,但当我们分离名色五蕴之后,就会发现,它不是“我”。
这就是所谓的“开发智慧”。听起来好像很难,但其实不难。现在跟我学习的人很多,我都训练他们,教导他们。他们的戒行变好了,定力也增强了,智慧也增长了。他们能够分离名色五蕴了。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做到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大家去听听我的光盘,在网站上可以下载。把光盘复制了去分发。听了之后,就要下定决心守持五戒,每天下定决心修习禅定。一开始,每天十分钟、十五分钟,念“佛陀”。然后,学习观察那颗溜走去想的心。心会觉醒,成为知者、观者。当心觉醒成为知者、观者之后,就来学习分离名-色、分离五蕴。看到身体在呼吸,心是观者;酸痛生起了,心是观者;善与不善法生起了,心是观者;心跑到眼睛去看,跑到耳朵去听,跑到鼻、舌、身、意,都有另一个心作为观者。
走向解脱之路
不断地练习下去,就会发现“自我”是不存在的。如果某一天,你真正地、透彻地见到了“自我”不存在,你就会成为须陀洹。但不是那种一闪而过的念头,比如现在听我说“没有我”,然后就想“哦,没有我”,这不是的,这还是念头。必须亲身去观察,不断地观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只会得到念头。
佛法必须真实地去体验,必须有耐心。不断地观察,日复一日地练习。我们已经迷失了无数个生命,无数个轮回,一直都活在迷茫的世界里。现在刚刚开始学习觉知自己,就想证得道果、涅槃,那未免太心急了。
但是,这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努力去觉知自己,不要迷失,不要让心漂浮不定。时时地觉知自己,守好戒律。观察身体在工作,观察心在工作。让自己仅仅成为一个知者、观者。到某一个点,智慧会爆发,你会亲见:“我”是不存在的。
这是最初步的智慧,见到“自我”不存在,破除“身见”,成为须陀洹。继续练习下去,智慧会更加成熟。最终有一天,智慧会彻见四圣谛。一开始,它会先彻见身体。看到这个身体纯粹是苦,没有任何美妙之处。像我们现在,还觉得身体时而苦,时而乐,对吗?如果还有这种感觉,是无法放下身体的。但如果有一天,智慧成熟了,就会看到这个身体纯粹是苦,只有很多苦和很少苦的区别,并没有丝毫的快乐。
当智慧见到这个程度时,就会放下身体。心会退回来,安住于心。然后我们继续在心这里修行。不断地修行下去,我们会看到,当心还有“想要”时,心还有执取时,心本身就是苦;当心不“想要”,不执取时,心就不苦。心因此也分为两种:苦的心和不苦的心。这说明还没有彻见。如果继续修行下去,就会彻见:心本身,就是苦。就像我们曾见到身体纯粹是苦一样,有剧烈的苦和轻微的苦。心也是纯粹的苦,有剧烈的苦和轻微的苦。
如果见到这一点,心就会放下“心”。当身心都已放下,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可执取的了。以世俗谛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被称为“阿罗汉”。内心的痛苦将不复存在,只剩下身体的痛苦,但那终将消失。
我们慢慢地修行。我们是佛教徒,我们有福报,生在佛陀的庇荫之下。我们的祖师大德们,一代代地将法传承下来,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来学习觉知身,觉知心。从持戒开始,训练心宁静,训练心安住。有念住去觉知身,有念住去觉知心。如实地了知它们是无常、苦、无我的。让心仅仅成为知者、观者。这样不断地练习,智慧生起了,心就会放下。
当智慧生起,看到了苦,它怎么还会执取呢?今天我们之所以执取名法、色法,执取身、心,是因为我们以为它们能带来快乐。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智慧彻见了“这个身是苦,这个心是苦”,它就不会再执取了,它会抛弃它们。当它抛弃了之后,剩下的就是“法”。我们这个身心,隆布特称之为“世间”。他有一本临终前写的书,书名叫《世间尽,法存》。大家有谁读过这本书吗?
如果想终结“世间”,也就是终结苦,就必须有戒、定、慧,直到能够放下身、放下心,也就是放下名、色。不执取身,不执取心,不执取五蕴。这个五蕴,就称为“世间”,它是苦的集合。如果终结了“世间”,也就是终结了五蕴,就能证入“法”。这个“法”是不死的,它不老、不病、不死。“法”是纯粹的快乐。“法”是空,但不是孤苦伶仃的空,而是充满快乐的空。隆布特因此说:“世间尽,法存”,而不是世间尽了,法也跟着灭了。
现在,我们慢慢地修行。没有人能像佛陀那样善于教导。佛陀所教导的法,是能帮助我们自己将痛苦从心中根除的法。我们生而为人,注定要不断地受苦。离苦之路就在眼前,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行走,那就太愚痴了。必须去奋斗,去学习。持戒,训练心宁静,及时地觉知自己的心。
当心成为知者、观者,就去观察身心的运作。身体怎么样,如实地知道;心怎么样,如实地知道。不断地去观察。当看得足够清晰,就会发现它们都不是“我”。它们都纯粹是苦。当智慧看得清晰、透彻,心就会放下,不再执著名、色、名、蕴。
这就是所有圣者们走过的路。祖师大德们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我所在的寺庙是隆布廉的寺庙,我也是隆布廉的弟子。我第一次去拜见他的时候,他教我念“佛陀”,观察身体。后来再去拜见他,他教导关于心的法门,回归到心。所有的祖师大德们教的都是同一个法。
我们就去修行吧。谁修行,谁就受益。谁不修行,就继续受苦,仅此而已。
问答环节
问: 顶礼隆波。刚才听您说法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心在强迫它自己,它想要这样,想要那样,然后又跑去想。当我强迫它的时候,会感到很压抑。但这种感觉时而减轻,时而增强。请隆波开示。
隆波帕默: 知道自己在强迫,这已经很好了。但你无法命令自己“不要强迫”,命令不了。要及时地觉知它。你看,心是无法禁止的,是无法强迫的,看到了吗?而且,你看到心在不断地变化吗?这种变化无常,正是在向你展示“无常”。那个无法被强迫的状态,正是在向你展示“无我”。去觉知它。当“想要强迫”的念头生起时,就去知道“想要”。想要它好,想要它快乐,想要它宁静。去知道这个“想要”。只是如其本然地去知道,不要去维持它静止。
修习奢摩他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点,奢摩他不是强迫心静止。那样的“定”是紧绷的,不是真正的定。修习禅定,不能丢掉念住。要有念住地去呼吸,心平静地与呼吸待在一起。有时候,物质世界消失了,呼吸也消失了,心变得空明,但念住并未丢失,也没有去强迫它。所以,轻松地去呼吸,觉知自己,舒服地待着。觉知到自己在强迫,就慢慢地放松。
问: 顶礼隆波。我现在在观察五蕴的运作,但不知道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隆波帕默: 你的心现在是否太兴奋了?如果太兴奋,就先让它玩一会儿,不要禁止它,禁止不了。你现在的心和刚才一样吗?不一样。它是不稳定的。就这样去观察。但心必须先真正地安住。你现在的心有点向外散。 (问者:还没有向外散。) 你的心必须先回归到觉知的根基。很多修行人,尤其是观心的人,容易在这里犯错,要小心。不要迷失在“空”里,看到心然后在“空”里粘住,那是不行的。那样修下去,死后会投生到无色界梵天,没有耳朵,没有眼睛,无法听闻任何佛陀的教法。
所以,我们修行,不要让心粘在“空”里。要努力地去觉知自己的身、心、名色、五蕴的运作。但是,当观察久了,心散乱了,就要让它回来休息,修习奢摩他。当宁静足够了,不要停留太久,出来继续观察身心的运作。就这样交替地练习。
问: 隆波,成为知者、观者的状态,是否就像在五蕴和知者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
隆波帕默: 是的,但不要刻意去维持那个距离。它自己会保持距离。如果我们刻意去拉开或推远,心就会变得紧绷。它自己会分离。
要开发智慧,心必须有“定”,也就是安住。在家的居士有一个弱点,就是定力通常比较弱,心不太安住。心喜欢向外散,变得空明、漂浮。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天到晚要处理很多散乱的事情,心很累。当心疲惫、紧张时,一旦开始修行,感到轻松了,就容易粘在那个轻松、空明、漂浮的状态。
纠正的方法就是:及时地觉知到心粘在了外面,那个空明、漂浮的状态。心必须回归到它的根基,才能真正地开发智慧。阿姜摩诃布瓦曾经教导我,他说可以念“佛陀”,念“佛陀”的同时觉知自己的心,心跑了就觉知。心会自己转回来。不要去拉它,它自己会回来。当它回到根基,成为观者时,它会看到名色五蕴在运作。真正安住的心,是处在中间的。
你可以观察身体,但观察身体时要小心一点,心可能会流到身体那里去。如果观察身体时,心流到了身体那里,那说明心还是不安住。如果观察身体,就像我们坐在这里,看一张地图。我们的身体就像地图。心是安住的,看到身体在坐着。如果心流到呼吸那里,那就意味着心已经跑出去了,心并没有真正地安住成为知者。这是在家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因为定力不足,心会散乱、漂浮出去,然后感到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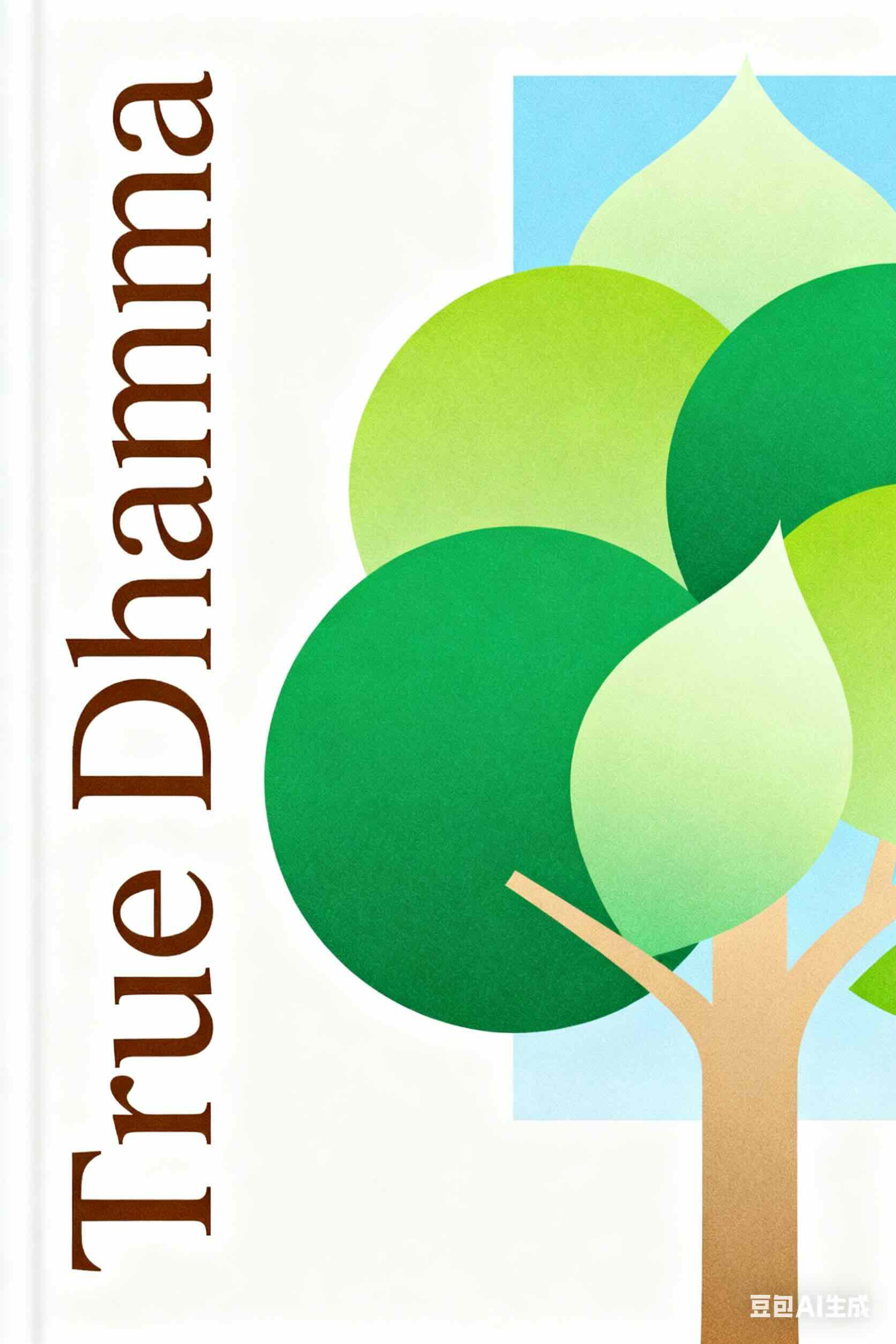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下载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