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时照顾好自己的心
隆波帕默尊者, 生老病死, 南传上座部佛法 ·Index
รักษาใจ ยามเจ็บไข้ - 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ทศนา หลวงพ่อปราโมทย์ ปาโมชฺโช
疾病时照顾好自己的心 - 隆波帕默尊者 - 摘要
身体的病痛,是医生的责任,让他们去照顾。我们的责任,是照顾好自己的心。
前言
源于助理教授、医学博士诺帕多·斯里塔纳拉塔纳库医生(Asst. Prof. Dr. Nopadol Sirithanarattanakul)恭请隆波帕默·帕默丘于佛历2560年3月18日,在诗里拉吉医院(Siriraj Hospital)为病患及家属进行了一场佛法开示。隆波的众多弟子一致认为,这次开示的内容对广大病患及家属极具助益。因此,法音基金会(The Dhamma Media Foundation)决定将此次开示整理出版。
本书内容包含了两场法谈的录音整理稿:一场是于诗里拉吉医院的开示,另一场则是次日(佛历2560年3月19日)上午在善地法苑(Wat Suan Santidham)的开示。
我们期望本书能利益所有读者——无论是病患、病患家属,还是尚未生病的人们,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得内心的力量,并将佛陀的教法付诸实践,为生命中那场重要的“考试”做好准备。
法音基金会 佛历2560年12月5日
第一场法谈:于曼谷诗里拉吉医院
佛历 2560 年 3 月 18 日
祝福各位。在座有哪些是血液科(Hemato)的病人?请举手。有吗?你们是我的“学弟学妹”,我比你们更早生这个病。
开示的时间大约半小时,不会超过。我会尽量简短,不然大家就要“饿到发怒”了。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饥饿时容易发怒?疲惫时也容易发怒,困倦时同样容易发怒。比如现在,大家就开始“饿到发怒”了。如果让你们先去吃饭再来听法,又会“困到发怒”。当我们接触或感受到不合意的事物时,烦躁感就会生起。这就是瞋恚,佛法称之为“โทสะ”(Dosa)。愤怒、烦躁、不耐烦都会随之而来。
因此,当我们生病时,不仅仅是身体在受苦,内心也会随之烦躁不安,也就是说,心里会生起瞋恚。比如,刚听到自己得了癌症,第一个生起的烦恼就是惊慌。有些人会害怕、惊慌、焦虑——这些都属于瞋恚一类的烦恼。
试问,惊慌失措能治好癌症吗?不能。害怕能治好吗?也不能。焦虑不安能让病好起来吗?同样不能。所以,这些属于瞋恚的情绪,完全是多余的,它们没有任何益处,只是在不必要地消耗我们的心力。
然而,只是简单地告诉别人“放宽心”,通常是没什么用的。我们很喜欢这样安慰人:“放轻松,放轻松。”如果自己是病人,恐怕会想顶回去:“不然你来生病看看?只会说风凉话。你要是病了,说不定比我闹得还厉害。”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身体生病或不适时,心也往往会跟着不舒服。所以佛陀教导凡夫说:“身体的病痛,如同被第一支箭射中;接着,我们又用第二支箭射向自己的心。”也就是说,内心也会跟着痛苦起来。但如果是佛陀真正的弟子,痛苦只会停留在身体层面,而不会侵入内心。
有些人误解得更离谱,以为阿罗汉的身体不会生病。简直是胡说!连佛陀都会生病,都会经历身体的困顿。别自己想当然了,阿罗汉又不是机器人,他们当然也会生病。
但圣者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是身病,心也跟着病,内心充满了煎熬。而一颗煎熬的心,反过来又会放大身体的痛苦。心能够影响到身体。这一点,我很久以前就观察到了,那时我还是居士,在教导朋友们禅修。有几位女性朋友,每次生理期都非常疼痛,必须吃止痛药,痛到难以忍受。我告诉她们,试着去观察自己的心,看看心是如何放大那份疼痛的。去及时地觉知那颗不喜欢、烦躁、焦虑的心。
比如,生理期来临时,身体确实有一部分真实的疼痛,但那颗不舒服、烦躁的心,却把疼痛感放大了。我让她们去试着观察,结果发现,心确实生起了瞋恚——一种不喜欢的状态。她们去练习观察之后,从此就不再需要吃止痛药了。
因此,当我们生病时,比如身为癌症病人,每天都会被抽血检查。医生总是充满好奇,想知道各种数据。每天护士来抽血时,我们甚至会想:也去抽抽医生的血嘛!只会发号施令。有时医生这里怀疑,那里怀疑,而他们的怀疑,却让我们承受痛苦,不是吗?
如果我们不懂得修行,内心会烦躁得不得了。我曾经因病住院,四个多月没能回寺庙。接受化疗后,常常会发烧,医生就不让我回去。烧退了,再过两三天又要化疗了,医生问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回了,懒得来回折腾,反正马上又要回来了。
在医院住了四个多月,护士和医生们总喜欢问我:“隆波,您住院这么久,觉得无聊吗?”他们问我无聊吗?我不无聊,因为无聊也是一种瞋恚。医生和护士听了都一头雾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只有修行的人才会懂,不修行是不会明白的。
就算我们感到无聊,就能出院回家吗?并不能。医生无论如何都不会放我们走的。一旦落入他们的“魔爪”,就别想轻易逃脱,他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直到确认绝对安全了才会放行。
当我们内心不舒服时,往往会焦虑、郁闷。比如要抽血、要动手术,内心的恐惧会让实际的疼痛感加剧。但如果我们懂得修行,当医生或护士对我们的身体进行操作时,比如在这里穿刺,在那里切开,疼痛感本身是一回事。而且,现代医学非常先进,其实并不会很痛,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惊慌、害怕而感觉到的痛。科技已经帮了我们很多,真正的疼痛已经很少了。跟以前的病人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以前的病人是真痛,而我们现在有各种止痛药、麻醉药,应有尽有。尤其是得了癌症,甚至还会有各种“鬼神牌”偏方,这个说、那个说,让你吃这个、吃那个。如果都信了,那真是死定了。吃医生开的药就够了,再乱吃别的,身体可受不了。
当内心焦虑时,比如要动手术了,会感到很郁闷。假设要在身上装一个人工血管注射座(Port-A-Cath),还没动刀就开始郁闷了,一听说要手术就心烦意乱。手术后更是难受。有一次,我化疗结束后,肛门长了脓疮,需要动手术。术后,医生提前嘱咐护士说,当天晚上一定会非常痛,让我准备好吗啡,必须给我注射。到了傍晚六点,护士来了:“隆波,来打吗啡了。”我问:“为什么要打?”护士说:“等下会痛。”我说:“嗯,等痛了我会告诉你的。”
结果,原本准备好的吗啡根本没用上,我只吃了一颗普拿疼(Paracetamol),好让护士安心,觉得我已经用药了。为什么我感觉不那么痛呢?一方面是医生技术好,医疗水平高;另一方面,是我的心很安稳,没有惊慌。如果心没有照顾好,它就会把疼痛感不成比例地放大。
所以,我们要时刻守护好自己的心。但要如何守护呢?我们连心在哪里都不知道。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持续地去觉知自己的感受。请牢牢记住这句话:只是去觉知自己的感受。
- 感到无聊,就觉知它。
- 感到焦虑,就觉知它。
- 感到害怕,就觉知它。
无论心里生起什么感受,都只是去觉知它。当痛苦在心中生起时,也只是去觉知它。
那有快乐生起吗?当然有。比如哪天医生没有来下令抽血检查,就会感到快乐,因为之前天天被抽。今天没被抽,就快乐了。快乐生起时,我们也去觉知它;痛苦生起时,我们也去觉知它。就这样,持续地去觉知自己的心。
- 它害怕,就觉知。
- 它生气,就觉知。
- 它焦虑,就觉知。
- 它烦躁,就觉知。
无论它呈现什么状态,都只是去觉知自己的感受,不断地、反复地去觉知。
如果我们能清晰地觉知到自己的感受,那么这些感受就无法掌控我们的心。比如,恐惧生起了,我们一觉知到,恐惧就会从心中分离出去;焦虑生起了,我们一觉知到,焦虑也会分离出去。我们的心将从各种情绪(所缘)中解脱出来。
这些情绪还会存在吗?当然会,我们无法禁止它们生起,因为我们还不是阿罗汉。要说完全没有烦恼,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当瞋恚、恐惧、焦虑等情绪生起时,只要有“念”(Sati)及时地觉知到自己的心,它们就不会将痛苦和折磨不成比例地放大。痛苦会减轻很多,我们能够轻松地承受。
在医院住久了,甚至会觉得很舒服。有些人甚至不想回家了,因为医院的护士比家里的人还漂亮,开玩笑说不想回家了。
因此,对于病人来说:
- 身体,是医生的责任,让他们去照顾。不要太相信朋友们的各种建议,那些五花八门的偏方——中医、泰医、印度医、西医、巫医……各种医生都会来给我们推荐各种药物,压力非常大。这个说:“你必须吃这个,这是最好的!”那个也说:“我这个才是最好的!”如果把所有“最好的”都吃了,那死后都不用打福尔马林了,因为身体里的细菌早就待不下去了,不会腐烂的。
- 心态,要认识到病痛是暂时的。 没有人会病一辈子,痛一辈子。疼痛只是暂时的,它来了,也终将过去。当然,对于一些身体非常虚弱的人来说,病痛或许会与生命一同终结。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未曾输给它,充其量只是打个平手。
比如我们得了癌症,如果我们死了,癌细胞也跟着死了,它也活不下去。所以,我们可以跟它好好商量:“喂,你别闹得太过分了。”多给它散播一些慈爱。当我们散播慈爱时,心就不会憎恨它,心就会安稳。心安稳了,定就会生起,心就会清凉、安乐、有力量。
我们不必想太多。当面临漫长的治疗过程时,有人会说:“天啊,医生说我要做6次、8次化疗,听了就让人心灰意冷。”我们应该只活在当下,活在每一天、每一刻。今天需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去想还剩下多少天,还要做多少次化疗。想太多没有任何好处。只活在当下,一天一天地过。时间过得很快。就像有些人结婚久了,(现场有人笑)这里有结婚很久的人吗?一天天过,没什么特别的,唯有“舍”而已。一年很快就过去了。然后跟别人说:“我结婚30年了,感觉就像跟桌子、椅子生活在一起,心是平静的。”心如如不动,不挣扎,不焦灼。
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接受现实。已经病了,如果病了还想着“但愿我没病”,那只会让自己更郁闷。因此,心的痛苦,并非源于得了癌症,而是源于“不想得癌症”却偏偏得了。
既然已经得了,那就去治疗。治疗是医生的责任。治好了,是医生高明;治不好,那医生也就不过如此。所以,我们不必郁闷。该郁闷的是医生,身为科室主任,怎么治的,病人都没救活。
因此,负责治疗的是医生,而我们负责照顾自己的心。医生无法代替我们来照顾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明白,心的痛苦源于“不想得癌症”,或得了病“想立刻就好”(最好三天就康复回家,那简直像演戏一样),那么当这些欲望无法实现时,痛苦就会生起。治疗的过程是漫长的,但如果我们的心能接受现实,就不会那么痛苦。
心的痛苦,源于“渴爱”(Taṇhā);渴爱,源于执取;执取,源于对身心实相的无知。这个道理太深奥了,我就不展开讲了。但举例来说,得了癌症,却“想要”它不是癌症,必然会痛苦,因为它已经是了。得了癌症,“想要”立刻痊愈,也必然会痛苦,因为它不可能立刻痊愈。
一天一天地活在当下。今天还活着,就让心保持愉悦和开朗。对于身体,就放下它,彻底地放下。
我有一个弟子,今天也来了,是我的“癌症老学长”。他曾来告诉我,医生说他时日无多,很快就要死了。那时他已经无法修行,内心一片混乱。我告诉他:“那就别修了。别想着要去打坐、经行,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你就这样发愿:我愿将此身供养佛陀,把这个身体当作供佛之花。”就这样下定决心,这个身体不再是“我的”了,而是已经供养给佛陀的东西。当他的心不再为身体焦虑时,奇迹发生了,他活得非常久,让医生大跌眼镜。医生说他很快会死,结果他到现在还活着,都好几年了。看起来反倒是我快要先死了,幸好我的医生医术高明,把我治好了。
对于病人,要时刻觉知自己的心。当心烦躁时,当心里生起“不想要”或“想要”这样、那样的念头时,要频繁地去觉知它,然后心就会安稳下来。这样,痛苦就只会停留在身体层面,心将不再受苦。
现在谈谈病患家属,你们也很重要。我曾经有一个弟子,年纪很小,还不到20岁,得了淋巴癌,病情发展得非常快。这个孩子从小就学习修行。他来告诉我:“我现在非常累,每天都要花很多力气去安慰我妈妈。”一个病人,却要反过来安慰家属。家属悲伤不已,而病人却要耗费巨大的心力去安抚他们,直到妈妈恢复平静,孩子已经筋疲力尽。
所以,病人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病患家属同样要照顾好自己的心。家属也会焦虑、害怕,担忧、关爱……各种情绪纷至沓来。有些人还担心医疗费用等问题,有太多需要考虑的事情。治疗费用非常昂贵。
方法是一样的:去觉知自己的心。心焦虑了,就去觉知;心呈现任何状态,都去觉知。及时地觉知自己的心,能让我们不把痛苦和折磨在心里扩大。痛苦将仅限于身体层面。家属也很辛苦,要陪护,要跑前跑后,要买药,有太多的“必须”要做,也有太多的“禁止”要做——禁止吃这个,禁止吃那个……家属辛苦,病人也辛苦。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如何帮助自己减轻痛苦?答案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心。守护心的工具,称之为“念”(Sati)。“念”就是那个能及时知道心中生起了什么的“知者”。因此,我们要时常观察自己的心。
心中生起的状态,主要有两大类:
- 乐受与苦受。
- 善法与不善法。
乐与苦,善与恶,整天在我们心中轮转不休。一觉醒来,想到这件事,感到快乐;想到那件事,感到痛苦。见到这个人,快乐;见到那个人,痛苦。这种感受会不断在心中生起。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触觉、意思法,都会伴随着乐或苦。
有时,六根接触六尘,会生起善心。比如,看到僧人托钵,心中生起善念。有时,看到僧人托钵,也会生起不善心,怀疑这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心里烦躁,觉得还是别布施了。所以,我们的眼所见,可以导向善心,也可以导向不善心。
总结一下,练习去及时地觉知自己的心。
此时此刻,你感到快乐吗?觉知到这份快乐。试着去观察那颗快乐的心。你注意到了吗?它在慢慢平息下来,快乐的程度在逐渐减弱,看到了吗?
下次,当痛苦生起时,也用同样的方式,以一颗中舍之心去观察它。痛苦的程度也会随之减弱。万事万物,生起,然后灭去;生起,然后灭去。
无论是病人,还是病人的家属、亲朋好友,都请活在当下,持续地去觉知自己的心。
最后再补充一点:如果有的病人真的无法治愈,这是自然规律。有人会问:“如果我快要死了,该怎么办?”这一点也需要学习,非常重要。我们如何才能安详地离世?
要持续地去觉知。身体在病痛,就去觉知它;内心在焦虑,无论心是什么状态,都去觉知它。就这样观察身、观察心,我保证,你的来世会比现在更好,会去往善处(Sugati)。
我的开示已经涵盖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从生病,到治愈,再到无法治愈,都提供了选择和方法,让我们能走向更好的归宿。观察自己的心,病痛会减轻,折磨会减少,焦虑会消失,甚至康复得更快。一个内心充满压力的人很难康复,而一个内心安稳的人,康复得更快。
就这样持续地练习下去,不断地去觉知自己的感受。
第二场法谈:于春武里府善地法苑
佛历 2560 年 3 月 19 日
昨天我去诗里拉吉医院开示,邀请我的医生为血液科(Hemato)的癌症病人——比如血癌、淋巴癌等——以及他们的家属安排了这场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听过佛法,所以我昨天的开示讲得非常简单。但即便是隆波的“简单版”,对于初次接触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些难度。
我告诉那些癌症病患,如今得这种病的人非常多。淋巴癌在所有癌症中排名第五,但如果把所有癌症加起来,它绝对是导致我们死亡的首要原因,非常普遍,连医生也无法解释原因。
有些人,在得知自己生病的第一阶段,本能地会感到震惊,接着便是害怕、迷茫、压力重重,这些情绪会接踵而至。这时身体甚至还没开始疼痛,真正的疼痛往往是在去医院之后,医生对你进行各种治疗时才开始。
如果我们是修行人,我们就会去及时地觉知自己的心。大多数时候,当我们感到疼痛时,一颗没有品质的心,会把疼痛感不成比例地放大。比如,实际的疼痛只有10%,心却能将它放大到100%。
你们可以试验一下。比如有些女性生理期腹痛严重,必须吃止痛药。我曾经教过好几位朋友(那是我还是居士时,不是出家后去管她们的私事),告诉她们去观察自己的心。当她们练习持续地观察心之后,原本需要吃很多药的状况,后来都不需要了,疼痛感大幅减轻。她们因此以为禅修能消除疼痛,但并非如此。禅修的作用,是让我们的心不再将疼痛感不成比例地放大,它并不能消除“受”(Vedanā),让它不生起。
身体生病时,心也跟着生病,会变得紧张,比平时更加关注身体。就像我们坐着发呆时,被蚊子叮了可能都没感觉。但如果我们看到蚊子,时刻提防着它,一旦被叮,就会觉得比平时更痛。这就是心在放大感受。
因此,如果我们能善巧地训练自己的心,就能如实地了知当下的状态。比如疼痛生起了,就如实地了知它的程度,那么它就不会那么难以忍受。
我昨天还跟那些癌症病人分享了我的经历。在我第二次化疗时,出现了副作用,肛门长了脓疮,需要动手术。主刀医生技术很好,照顾得也很周到。但手术后他告诉我:“今天晚上一定会非常痛。”他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吗啡,说:“今晚必须用吗啡。”到了晚上,护士来了:“隆波,现在要用吗啡吗?”我说:“还不用。”“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还不痛。”最后,睡前我只吃了一颗普拿疼,好让护士安心,觉得已经给了药。
当我们需要动手术或接受治疗时,如果能守护好自己的心,不让它去放大感受,其实并不会那么痛。之所以不那么痛,并非因为我有多勇敢,而是因为现代科技很发达。这个时代的医疗技术,已经很少让病人遭受巨大的折磨了,有各种各样的药物可以帮助缓解痛苦。问题在于病人自己害怕,一点点的疼痛,就被心放大了,变得惊慌失措。
所以,如果我们能及时地觉知自己的心,当生病时,心害怕,就觉知它;心焦虑,就觉知它;无论心是什么状态,都去觉知它。这些状态,大部分都属于瞋恚一类的烦恼,是一种抗拒和排斥。当这种排斥心生起时,内心会立刻感到痛苦。因此,每当以瞋为根的心生起时,必定会伴随着“忧受”(Domanassa-vedanā),即心的苦受。所以,身体生病时,心也跟着受苦。
佛陀教导说:“这就像身体被第一支箭射中,然后我们又被第二支箭射中,伤及内心。”内心的煎熬与痛苦随之而来。佛陀说:“阿罗汉只中一支箭”,身体会中箭,但心不会再进行ปรุงแต่ง(造作),不会再感到痛苦。如果我们也精进修行,同样可以减轻心的痛苦。
去看牙医可怕吗?有些人很怕。有的医生手重,有的手轻。有些手轻的医生其实治得并不好,为了取悦病人,洗牙时只洗表面,藏在牙龈下的牙石根本没清理。而有些追求卓越治疗效果的医生,会把牙石刮到牙根深处。去看牙医时,内心总是七上八下。
如果我们能保持中舍心,那么痛苦就只会停留在身体层面。如果身体的疼痛实在难以忍受,可以借助奢摩他(Samatha)的方法。有很多种方法,比如,把注意力集中到大脚趾上,因为医生不会动你的大脚趾,对吗?那时,医生只在你的头上忙活,我们就可以把心安放在别处。心不去接收那个疼痛的信号,就不会觉得那么痛了。除非疼痛非常剧烈,心才会偶尔瞥过去看一眼。
隆达摩诃布瓦尊者也曾分享过,他喝一种非常难闻的中药,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气味刺鼻。尊者说,喝药时,他会把心安放到屋梁上。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可能没有屋梁,只有天花板,但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把心安放在高处。心一旦不去接收那个所缘,触(Phassa)就不会生起。 比如拔牙、治牙,有“触”吗?没有,因为心没有安住于那里,没有作意到它,触就不会生起,因此就不会感到疼痛。除非我们的心很焦虑,它会不断地跑回来看,每回来看一眼,就痛一次。
慢慢地练习。总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面临病痛。平时就要训练自己,学习观察心,观察身。如果能修习奢摩他,那就更好。如果不能修奢摩他,就只是观察它的运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自己。但过度修习奢M他也有问题。有些尊者禅定功夫很深,心一沉入定境,医生就无法给他抽血或动手术,必须要把他摇醒:“长老,长老,请出定。”一出定,当然就痛了,但必须出定。有些尊者的心力太强,甚至出现抽血针打不进去,或者针头弯掉的情况。
因此,我们要在生病之前就开始训练自己,这样当病痛来临时才能自救。尤其是得了癌症,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亲戚、朋友,那些非常关心我们的人,反而会给我们增加巨大的压力。
我以前有个小弟子,很小就得了淋巴癌,但他修行很久了。他来向我报告修行功课时说,他每天都非常疲惫,因为要花很多力气去安慰妈妈。孩子自己得了癌症,已经很辛苦了,却还要去安抚妈妈,耗费巨大的心力。有时,亲戚朋友反而让病人更加痛苦。所以,当我们的亲人生病时,要小心,不要给他们增加痛苦。
另一类增加压力的人,是那些“全民医生”。我生病时才发现,几乎每个泰国人都是医生,会给出无数的建议。有人会拿来神奇的“特效药”:“这个药最好,是银杏提取的,您一定要吃!”我不是一个轻易吃药的人,会先拿给我的主治医生看。医生说,这个药的副作用是容易导致出血。化疗期间血小板本来就很低,再吃这个药,非常危险。这就是我们的“民间医生”,每个人都成了医生。有人推荐中药,去找陈医生、李医生……幸好没让我去找妇科医生。
中医、泰医,甚至还有巫医,说这个药是鬼神指示的,吃了这个药,自己也快变成鬼了。这些过多的建议,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因为我们必须不断地拒绝和解释。有人说:“隆波,您吃黑芝麻吧,是最好的,我买来供养您。”其实在我得癌症之前,我每天都吃黑芝-麻,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吃黑芝麻才得的病。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学说”。我只相信科学,任何没有真实研究数据支持的东西,我都不信。而且,即便是研究,也要看背后是否有利益驱动。医学界也有很多背后隐藏着利益的研究,比如他们让我们对胆固醇感到极度恐惧,告诉我们必须吃药,到了一定程度,每个人都得吃,目的就是为了卖药。其实胆固醇并没有那么可怕。
生活需要理性,盲目跟从不是佛教徒的方式。我们要守护好心,保持觉知,用智慧去审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凡事都要有理有据。家属也一样,照顾病人时,不要给病人增加问题。很多人不仅增加问题,自己甚至比病人还痛苦,让病人压力更大。
昨天我讲的内容和这个类似,但比这个简单得多。今天在这里讲,要讲得难一点,才配得上是在寺庙里开示。
如果我们坚持修行,痛苦最终只会停留在身体层面,心的痛苦将不会生起。即便我们的修行还不够纯熟,心的痛苦生起了,它也会很轻微,且持续时间不长。我们能够帮助自己。我们没有理由让自己承受那么多的痛苦,不应浑浑噩噩地活着。
身体的痛苦是无法避免的,但现代医学能帮上大忙。我们这一代的病人,比祖辈们在得同样疾病时,疼痛感要轻得多,但病程却更长,因为不容易死。所以,如果真的治不好了,就不要再强行治疗了,只需为病人减轻痛苦即可。有些人把年迈的父母留在医院,像是在培养组织细胞,全身插满管子,靠机器维持生命。那真是太痛苦了,呼出的每一口气是苦,吸入的每一口气也是苦。他们不懂得观察苦,只是在白白受苦。就这样维持着,花费了数百万,甚至数千万。我认识一个人,在一家著名的医院,花了几千万元。医生确实厉害,就是不让他死,就那样“养”着。最后,子孙后代快被拖垮了,实在无力承担,只能让他自然离去。自然规律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必承受太久的痛苦。
临终之时,看似非常痛苦。但如果我们训练有素,就只是观察身体的痛苦。昨天我也教了他们,如果真的要死了,就让心安稳下来。这是教给那些没有修行基础的人的,让他们想着美好的事物。但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如果死亡来临,就去观察那个正在死去的身体,而我们的心,是独立于外的“观察者”,它如如不动,不摇不晃。痛苦和折磨的程度会比普通人轻得多。
隆达摩诃布瓦尊者曾说,把修行修到极致,临终时,心会自动脱离出来,不会感到任何折磨,从死亡之苦中解脱。我们的心可能还无法完全脱离,只是在进进出出。但当心真的脱离时,是它自己脱离的,不是刻意逃避身体。心会彻底放下,并切断对身体的感知。它知道这个身体已经无法再用了,于是就舍弃它,切断对身体的感知。那时,身体会变得平静,即便有抽搐,也只是物质的运动,而心是宁静、安详的,契入了“远离”(Viveka)。
我们不是无依无靠的人,我们是佛陀的弟子。从现在起就要训练自己。生病时,让医生去治疗身体,我们来治愈自己的心。如果治不好,就放下它,但要持续治愈自己的心。如果修行到了极致,心还会再次放下它自己。苦的尽头,就在那里。
所以,如果我们的修行还未圆满,临终时,先放下身体。放下身体后,心会显现出来。如果你的波罗蜜足够,在那个点上,心会放下它自己。
放下心,我们中有些人曾经体验过,心“啪”地一下放下,但又会重新捡起来,因为那时死亡的因缘未到,旧业未尽,必须重新执取心。但当了知身体必死无疑时,它会先放下身体。而那颗训练有素的心,在那一刻,所有的挣扎都将止息。它会彻见:心本身,就是苦的根源。如果没有心,就不会有五蕴,剩下的只是躺在那里的物质。没有心,就只是一堆物质,一堆元素。一旦有了心,它就变成了众生、人、我们、他们。所以,佛陀在描述时会说:“此身一寻、一尺、一庹,有想与心为王。”有了身和心,才有了人、众生、我、他。但佛陀努力指出,这并非人、非众生、非我、非他,而只是物质、一堆元素,以及作为“识界”的心。看透这一切都是元素,无人、无众生、无我、无他——这是阿罗汉的境界。
只要还执着于心,就还有“我”在,还会继续轮回。仅仅一颗心,就能重新创造出新的五蕴。一颗结生识,就能创造出全新的名色。但如果我们连心也放下了,结生识就不会再生起。我们死了,就是彻底的寂灭,不再有轮回的种子,不必再去寻找新的痛苦,以经历下一次的死亡。这是最后一次死亡。
慢慢地练习。一颗训练有素的心,会为我们带来安乐。所以,努力训练自己吧,没有人能代替我们。痛苦无处不在。比如你住进医院就会知道,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我甚至跟阿姜阿开玩笑说:“我们可能不必再去地狱了,但业报现前时,穿着白衣的‘阎罗王’(指医生护士)会准时来用针刺我们。不善业总要结果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欠下的债必须偿还。如果不在真正的地狱里还,就得在死前提前还了,还没死,还没下地狱,就先活在地狱里了。”
有些病人不懂得修行,压力大到精神崩溃,疯狂地摇晃病床。一开始他希望病好,摇床是因为愤怒,为何迟迟不好;后来病重了,痛苦久了,他又摇床,是因为愤怒,为何迟迟不死。这就是没有训练过的心,无依无靠,无法自救,只能凭着原始的本能反应,但这只会让痛苦加剧,让周围的人也更加焦虑。陪护的人也焦虑,彻夜不眠。阿姜阿来照顾我,自己都憔悴了,比我还像病人。每次有不认识的医生进来,一进病房,第一反应总是先去检查阿姜阿。这是真事,不是编的。因为他照顾我,眼睛都熬成了黑眼圈。我不舒服,醒来一会儿就又睡着了,因为没力气。而阿姜阿醒了,眼睛就一直睁着,到了早上,眼圈发黑。医生每次进来,都先冲向他。等发现看错了病人,就尴尬地掩饰说:“隆波,您怎么一点也不像病人啊?”我说:“我身上插了这么多管子,你自己不看,光看面相。”
做陪护的人,也需要修行。那段时间反而是修行的大好机会,因为不用做别的工作。
因此,生病,就是进入考场的时候;没病的时候,是我们在教室里学习。但有些人还没学好,病一来就要进考场了。有些人生病了来问我:“我该怎么调整心态?”我只能说:“姑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那时已经来不及了。痛苦已经降临到身上,才想起来要修行,是没用的。
必须在身体还健康、在日常生活中就开始训练。要好好地在“教室”里学习,我们的“课本”就是“名与色”。深入地去学习它们,多观察自己的身,多观察自己的心。能观察心,就观察心;观察不了心,就观察身。身心都观察不了,就修奢摩他,念“佛陀、佛陀”(Buddho)。心能平静也好,不能平静也罢,只要能坚持念下去,就已经非常好了。或者念经也可以,做任何一件事,让心安住在一个善的所缘上。
生病时,就是进考场考试。你们上学时有没有遇到过老师突然袭击,搞突击测验?我们的人生也常有这种突击测验。很多人开着车,突然翻车了,这就是一次测验。还不是终极大考,还没死,脖子还没断。为什么没断?因为“念”很好。头快要撞到这边了,赶紧躲一下,只是耳朵擦破了一点,而不是头骨开裂。这就是有“念”,说明你通过了这次的“随堂测验”。
当我们临终时,那才是真正的期末大考。是及格还是不及格,谁也说不准。但总有一天,我们都必须进入那个考场,谁也逃不掉。有些人进场得比预想的要早,有些人则看似早该进场了,却迟迟不进,因为他的“功课”还没修完,还不肯毕业,不肯病重,不肯死。有很多人,看起来好像快死了,却活了很久。阿姜阿说:“他们是在持续地承受着不善业的果报,把业报平均分配了,今天这里痛,明天那里病。”
以前隆布特尊者有一位弟子叫杜姥姥,她体弱多病,各种时髦的病她都有。她会很自豪地跟别人讲,来看她的人都说:“哎呀,杜姥姥,你的手指又被截掉啦?”杜姥姥说:“那些对我唉声叹气的人,没过多久,自己就死了。”他们真的死了,她并没有诅咒他们。像这样看起来体弱多病的人,反而比那些看起来强壮的人活得更久。所以,不要以为自己身体强壮,就能一直活下去。唯一确定的事,就是“不确定”。
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考试”,而且这场考试没有补考。及格就是及格,不及格就是不及格。不会有跟阎罗王求情说“让我复活一次,回去重考”这种事,虽然我们读过一些死而复生的故事,但那是没有补考的。
所以,要尽全力做好准备,修习业处(Kammaṭṭhāna)。业处有两种:奢摩他业处(Samatha-kammaṭṭhāna)和毗婆舍那业处(Vipassanā-kammaṭṭhāna)。
- 奢摩他必须“做”。心不好,让它变好;心不乐,让它变乐;心不静,让它变静。要用与烦恼相反的所缘来对治。比如,心贪欲重,就修不净观,观想不净之物,因为美好之物会引生贪欲。心瞋恚重,就修慈心观,慈心与瞋恚是直接对立的。心愚痴重,就多训练理性思维,凡事讲求理据,否则就会被愚痴吞噬。心散乱,就把心安住在一个所缘上,心跑了,就觉知它,心就不会散乱。这就是奢摩他,用与当下烦恼相反的所缘来安住内心。
- 毗婆舍那则不是“做”出来的。它不是去“做”什么,而是如其本然地去“知”。如实地了知身的实相,如实地了知心的实相。
所以,奢摩他需要“做”,做了之后还要“维护”,否则就会退失。而毗婆舍那,没有什么必须做,也没有什么禁止做,只有“如其本然地去觉知”。这两者是不同的。
有些人听了我的开示,就说:“隆波帕默说,什么都不用做。”不是的。我说的是:“要去训练自己,做到‘感觉自己’,不迷失,不紧盯。”这是需要去“做”、去“训练”的。但当心能够“感觉自己”之后,就要去观察名色(身心)的运作,不要去干预它,不要迷失于喜欢或不喜欢的干预中。如果生起了喜欢或不喜欢,也要及时地去觉知它,这样就不会去干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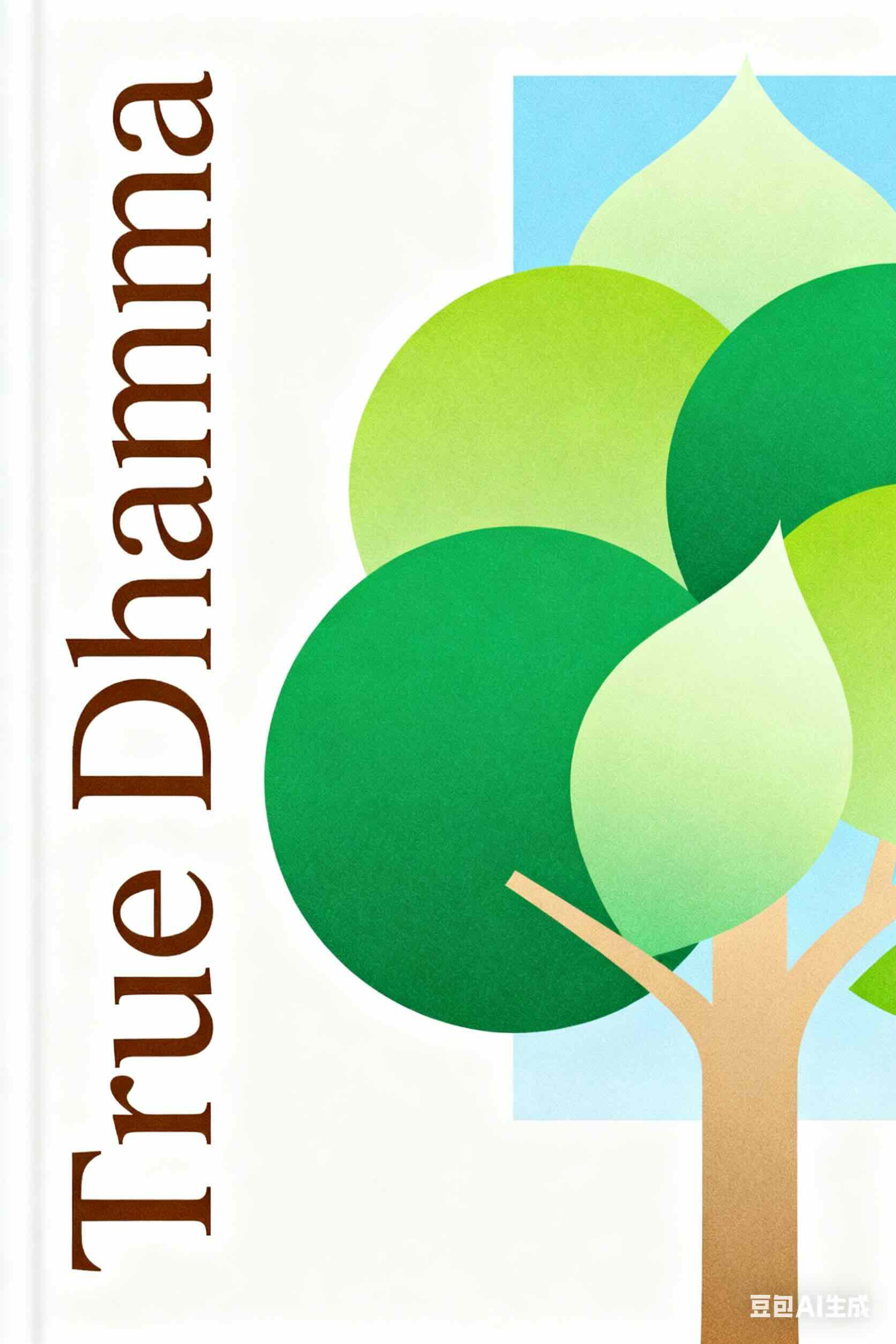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下载完整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