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糖的理由:上瘾、疾病与糖的故事
成瘾与戒断 ·Index
The Case Against Sugar - Gary Taubes
吃糖的理由:上瘾、疾病与糖的故事 - 加里·陶布斯 - 摘要
只要糖消费量上升,并跨越代际,它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并触发向肥胖、糖尿病及相关疾病发展的进程。
作者前言
本书旨在提出一个论证:糖——包括蔗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是导致那些最可能在21世纪致我们于死地或加速我们死亡的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 本书的目标是解释为什么这些糖类是最大的嫌疑犯,以及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肥胖,三分之二超重,近七分之一患有糖尿病,四到五分之一的人将死于癌症;然而,直到近十年,这些疾病的饮食诱因中的主要嫌疑犯,却一直被看作不过是无害的乐趣来源。
如果这是一桩刑事案件,《反糖斗争》就是控方的结案陈词。
引言:为何是糖尿病?
本书开篇追溯了著名糖尿病专家艾略特·乔斯林(Elliott Joslin)在19世纪末的观察,他当时就发现糖尿病病例呈上升趋势。在1824年至1898年间,麻省总医院的记录显示糖尿病病例从罕见到逐渐增多。乔斯林最初认为这只是因为更多患者寻求医疗帮助,但到了1921年,他已将此现象称为一场“流行病”。
糖尿病从一种罕见病演变为全球性的流行病。 历史上,从古印度到19世纪的欧洲,糖尿病一直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急剧上升。例如,在美国,如今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肥胖,近七分之一患有糖尿病,儿童肥胖率也急剧增加。这种流行病并非局限于西方国家,中国、因纽特人、美洲原住民等群体在接受西式饮食和生活方式后,糖尿病发病率也经历了爆炸性增长。
早期的怀疑指向了糖。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许多公共卫生专家和临床医生都将糖尿病的流行归因于糖消费的激增。工业革命带来了糖果、软饮料等行业的兴起,糖的消费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当一个地区的人们开始消费西式饮食,尤其是含糖产品时,糖尿病流行病便随之而来。甚至在战争期间因食糖配给导致消费量下降时,糖尿病死亡率也相应下降。
然而,科学界的焦点后来转向了膳食脂肪和总热量。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膳食脂肪被认为是心脏病的元凶,营养学界随之否定了糖在慢性病中的作用。主流观点变为:
- 肥胖导致2型糖尿病。
- 肥胖的根本原因是“能量失衡”,即摄入的热量超过消耗的热量。
这种“卡路里即卡路里”的观点让糖得以脱罪,它被视为仅仅是“空热量”——除了提供能量外不含任何营养素。这种逻辑对食品工业极为有利,因为它意味着问题不在于糖本身,而在于人们“吃得太多”。可口可乐等公司也乐于将问题归咎于消费者的行为,而非其产品。
本书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论点: 糖(蔗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本身就是糖尿病和肥胖的根本原因,其作用机制类似于吸烟导致肺癌。这并非因为我们吃得太多,而是因为糖在人体内具有独特的生理、代谢和内分泌(激素)效应,直接引发这些疾病。 它是一种慢性毒物,其危害经过数年、数十年甚至代际传递累积而成。
糖可能是一系列“西方疾病”的共同诱因。 肥胖和糖尿病患者也更容易患上脂肪肝、高血压、心脏病、癌症、中风,甚至阿尔茨海默病。这些疾病常常集聚出现,并都与一种名为“胰岛素抵抗”的状况有关。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最可能是正确的。如果糖是导致胰岛素抵抗、肥胖和糖尿病的元凶,那么它很可能也是这一系列相关慢性疾病的共同膳食诱因。
本书旨在聚焦于糖的独特作用。 尽管其他精制碳水化合物也可能存在问题,但糖是启动这一系列病理过程的关键。只要饮食中的糖含量足够低,即使富含碳水化合物,人群也可能保持相对健康。一旦糖的消费量上升,胰岛素抵抗就会被触发,进而导致肥胖、糖尿病及相关疾病。因此,预防和逆转这些疾病的首要步骤,就是从我们的饮食中去除糖。
作者承认,现有科学证据尚不能像证明烟草与肺癌关系那样“明确无误”地判定糖的危害,这主要是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不摄入糖的对照人群。然而,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自己和家人远离糖,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
最后,书中明确指出,“糖”一词指代蔗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HFCS)这两种热量甜味剂。尽管两者在化学结构上略有不同,但对人体的影响基本相同,它们都是葡萄糖和果糖的组合。将HFCS单独妖魔化,只会模糊真正的焦点:这两种糖都可能有害。
第一章 药物还是食物?
本章探讨了糖的双重属性:它既是一种营养物质,又具有类似成瘾药物的特质。作者通过生动的比喻开篇:如果有一种物质,口服即可带来愉悦甚至“陶醉”感,能安抚儿童、缓解疼痛,并成为庆祝和表达爱意的象征,那它是什么?答案就是糖。
糖具有类似药物的成瘾性。 从儿童对糖果的渴望,到成年人在压力下寻求甜食的慰藉,人类对甜味的反应常常被比作药物依赖。历史学家也将糖与咖啡、茶、烟草等一同归为“药物性食物”,这些源自热带的商品共同构建了欧洲的帝国。朗姆酒由甘蔗酿造;茶、咖啡和巧克力在加入糖后消费量才在欧洲爆炸性增长;甚至最初的可口可乐也是古柯碱、咖啡因和糖的混合物,糖的作用是掩盖其他成分的苦味。
糖在烟草成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现代美式混合型香烟之所以能被吸入肺部,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烟草经过了加糖处理。糖使烟雾的酸碱度改变,变得不那么刺激,从而更容易被吸入,这大大增强了尼古丁的吸收效率和成瘾性,同时也增加了致癌风险。
人类对甜味的偏好似乎是天生的。 新生儿在接触母乳前,尝到糖水就会表现出满足和愉悦的表情。这种“甜牙齿”的进化优势通常被解释为帮助我们识别富含热量的水果或母乳。然而,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热量。它能安抚婴儿的哭闹,甚至在临床试验中,其镇痛效果比母乳更强。
科学研究支持糖的成瘾潜力。 糖能激活大脑中与尼古丁、可卡因、海洛因等成瘾物质相同的“奖赏中枢”,刺激多巴胺的释放。动物实验显示,大鼠对糖水的偏好甚至超过了可卡因。许多戒毒或戒酒的人会转向甜食,这可能是一种成瘾的转移。禁酒令时期,美国糖果和冰淇淋的消费量翻倍,也佐证了这一点。
糖已深度融入现代生活和文化。 随着价格下降和工业化生产,糖从奢侈品变成了日常必需品。它不仅存在于甜点和饮料中,还被广泛添加到面包、酱料、加工肉类等各种食品中。食品工业发现,几乎所有产品加点糖都会更受欢迎。同时,糖也成了爱、奖励和庆祝的代名词,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和情感表达中。
本章的结论是,我们不能仅仅将糖视为一种提供“空热量”的普通食物。它对大脑和行为的强烈影响,使其具有了药物的某些特征。正是这种类似成瘾的特性,解释了为什么糖能在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中占据如此主导的地位,也预示了其背后可能隐藏的健康代价。我们对糖的渴望,可能并非简单的口味偏好,而是一种被深度“点燃”的、贯穿一生的渴求。
第二章 最初一万年
本章追溯了糖从一种稀有植物到全球性商品的宏大历史,揭示了其如何从一万年前在新几内亚被首次驯化,最终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甘蔗到结晶糖。 甘蔗最初被人类驯化是为了咀嚼其茎秆以获取甜味和能量。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北印度人发明了将甘蔗汁通过加热和冷却制成粗糖的技术,这是制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技术让糖得以储存和运输。经过不断改良,精炼技术能够生产出纯净的白色结晶糖——一种除了盐之外,人类唯一消费的纯化学物质。
糖的多重用途。 除了提供甜味和能量,糖在食品制备中极为有用。它是一种优良的防腐剂(如果酱、炼乳),能中和腌制肉类的咸味,是酵母发酵的理想燃料(用于面包制作),还能改善饮料的口感和质地。
糖的全球传播。 制糖技术从印度经由佛教僧侣传至中国和日本,后被穆斯林探险家带回阿拉伯世界。随着伊斯兰帝国的扩张,甘蔗种植遍布地中海地区。十字军东征则将糖带回北欧。起初,糖在欧洲主要被用作药物、香料、防腐剂和地位象征,是仅限于王室和富人的奢侈品。
糖、奴隶制与帝国。 糖的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环境极其恶劣,这使其与奴隶制紧密相连。从穆斯林在中东的甘蔗园,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新世界的种植园,奴隶劳动一直是制糖业的基础。哥伦布将甘蔗带到美洲,开启了加勒比“糖岛”的时代。为了满足欧洲对糖日益增长的需求,数百万非洲人被贩卖为奴,在甘蔗种植园里劳作至死。可以说,我们的祖先为了满足对甜味的渴望和从中牟利,容忍并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
糖的经济与政治力量。 从17世纪到19世纪,糖的经济地位相当于20世纪的石油,被称为“白金”。它成为帝国之间战争的导火索,也是殖民地经济的核心。英国和美国政府都通过对糖征收高额关税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
糖的平民化。 两个关键因素使糖从奢侈品转变为大众消费品:
- 甜菜制糖业的发展:19世纪初,欧洲,特别是法国和德国,成功实现了从甜菜中大规模提炼糖。这使得温带地区也能生产糖,打破了热带地区对甘蔗的垄断。
- 工业革命:蒸汽机等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制糖效率和产量,使糖的价格大幅下降,人人都能负担得起。
新糖品产业的诞生。 随着糖变得廉价和普及,19世纪下半叶催生了全新的食品工业,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糖果、巧克力棒、冰淇淋和软饮料这四大产业相继崛起。这些产品通过大规模生产、铁路运输、现代包装和广告营销,将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向了市场,并首次将儿童作为主要目标消费者。
到20世纪初,糖已经无处不在,从一种罕见的珍品,经过漫长而血腥的旅程,最终成为现代饮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分。
第三章 烟草与糖的联姻
本章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糖在现代香烟的成功及其导致的肺癌大流行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如果没有糖,香烟的危害和成瘾性都将大打折扣。
肺癌与糖尿病的平行历史。 在20世纪初之前,肺癌和糖尿病一样,都是极为罕见的疾病。然而,随着一种新型香烟——美式混合型香烟的流行,肺癌病例开始呈指数级增长。1913年,雷诺兹公司推出了第一款混合型香烟“骆驼牌”,肺癌的死亡人数也从此开始飙升。
糖是香烟能够被吸入肺部的关键。 传统雪茄和烟斗的烟雾是碱性的,非常刺激,难以吸入肺部深处。然而,香烟之所以能带来强烈的尼古丁“快感”并导致严重致癌,恰恰是因为其烟雾可以被轻松吸入,使肺部巨大的表面积充分吸收尼古丁和致癌物。
这一“可吸入性”的秘密就在于糖:
- 烤烟技术(Flue-Curing):19世纪60年代,烟草业发明了烤烟技术。通过加热烘烤烟叶,烟叶中的淀粉会大量转化为糖。高含糖量的烟叶燃烧时产生的烟雾是酸性的,而不是碱性的。酸性烟雾温和不刺激,可以被轻易吸入肺部,这是香烟成瘾和致癌的第一步。
- 加糖处理(Saucing):“骆驼牌”香烟的创新之处在于混合了不同类型的烟草,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名为“白肋烟”(Burley)的烟草。白肋烟尼古丁含量高,但本身几乎不含糖,烟雾呈碱性,难以吸入。然而,烟草制造商发现,白肋烟叶多孔的特性使其能够吸收大量糖分。于是,他们将烟叶浸泡在含糖(以及蜂蜜、糖浆等)的“酱汁”中。
烟草与糖的致命联姻。 “骆otuo牌”香烟将高尼古丁的加糖白肋烟与高糖分的烤烟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完美的尼古丁输送工具。加糖不仅中和了碱性烟雾,使其变得温和可吸入,还在燃烧时产生焦糖化的香甜气味,对女性和青少年更具吸引力。
正如一份1950年糖业内部报告所言,正是“烟草与糖的联姻”,才造就了美式混合型香烟在20世纪的巨大成功。可以说,糖为通往肺癌的道路铺上了“甜蜜”的地毯。 若非如此,香烟的成瘾性和危害性都会大打折扣,全球的肺癌流行病也可能不会如此惨烈。
第四章 一种奇特的恶
本章探讨了糖及含糖产品如何在20世纪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市场韧性的“奇特的恶”,即使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其消费量也未曾衰减,反而持续增长。
糖是一种“抗萧条”的商品。 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观察到的,当人们生活困苦、精神空虚时,他们不会选择平淡健康的食物,而是渴望一些“有点味道”的廉价奢侈品。糖果、冰淇淋和软饮料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在大萧条期间,美国人均食糖消费量不降反升,可口可乐等公司的股票甚至逆势大涨,因为人们会放弃许多必需品,却不愿放弃这些能带来片刻欢愉的“恶习”。
糖业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力量。 糖业存在一个独特的经济周期:战争或天灾导致供应短缺,价格上涨,从而刺激全球范围内的增产。一旦供应恢复,市场便会充斥过剩的糖,导致价格暴跌。为了应对价格下跌,糖业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实施保护性政策(如进口配额和补贴),并积极开拓市场,刺激消费。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糖业游说团体已变得异常强大,罗斯福总统称其为他任期内见过的“最强大的压力集团”。
技术进步与消费模式的变革。 20世纪30年代以后,冰箱的普及和自动售货机的出现,使得冷饮和冰淇淋等含糖产品能够轻易进入家庭,消费变得前所未有地便捷。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开始推出家庭装,并专门针对女性和儿童进行广告宣传,软饮料销量在二战前呈爆炸式增长。
战争成为糖全球化的助推器。 与一战类似,二战虽然暂时导致了民用糖的配给,但却极大地推动了糖的全球化。美国军队的糖配给量远超平民,糖果被宣传为提升战斗力的“战斗食品”。可口可乐公司更以此为契机,在全球建立了64个瓶装厂,确保“让全世界的士兵都能以5美分的价格喝到可口可乐”,成功地将1100万美国大兵培养成了战后忠实的消费者,并为战后的全球扩张奠定了基础。
早餐的“糖化”。 战后,糖的消费领域进一步扩大,早餐成为新的重灾区:
- 果汁的兴起:最初为解决水果过剩问题而出现的罐装果汁,在“新营养学”的推动下,被宣传为获取维生素的健康饮品。冷冻浓缩橙汁的发明,更是使其成为美国家庭早餐的标配。到90年代末,美国人每年仅通过喝果汁摄入的糖就相当于8磅。
- 谷物早餐的堕落:原本作为健康食品出现的谷物早餐,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一场“糖化”变革。食品公司发现,在谷物表面裹上一层糖(即“预加糖谷物”)能极大地促进销量。尽管公司内部的营养师曾表示担忧,但在巨大的市场利润面前,这种担忧被抛到脑后。Kellogg’s的“糖霜玉米片”(Sugar Frosted Flakes)和Post的“糖脆”(Sugar Crisp)等产品大获成功,整个行业迅速跟进,推出了大量含糖量超过50%的“早餐糖果”,并利用卡通形象向儿童进行疯狂营销。
就这样,通过经济、政治、技术和营销的合力,糖——这种“奇特的恶”——不仅抵御了经济危机和战争的影响,还成功占领了人们的餐桌,将早餐这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也变成了甜蜜的陷阱。
第五章 早期的(糟糕)科学
本章深入探讨了20世纪初以来,科学界对糖与慢性病关系的认知是如何形成并最终走上歧途的。尽管早期有许多医生怀疑糖是多种现代疾病的元凶,但最终,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错误观念使得糖得以“脱罪”。
早期的怀疑与科学的局限。 20世纪初,随着糖消费量的急剧增加,医生们开始将其与糖尿病、风湿、肝病甚至癌症等多种疾病联系起来。然而,当时的营养科学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工具(如热量计)只能测量食物的能量(卡路里)和维生素、矿物质含量。科学家们无法测量食物对激素(如胰岛素)的影响,这导致营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能量平衡”的框架,即只关注热量的摄入与消耗,而忽略了食物对身体内分泌系统的深远影响。
糖作为“快速能量”来源备受推崇。 早期的研究发现,糖,尤其是其中的果糖和蔗糖,能被人体迅速代谢,提供“快速能量”。这一特性使其在运动员和士兵中备受青睐,甚至被德国军方用作提高士兵体能的配给。糖能缓解疲劳的“刺激”特性,使其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营养品,甚至被推荐给活动量大的儿童。
共识的形成与转变:从“致胖”到“无害”。 最初,尽管糖被视为有益的能量来源,但医学界普遍认为它会“致胖”。因此,医生们建议肥胖者、糖尿病患者和注重身材的女性应“像躲避毒药一样”避免食糖。人工甜味剂糖精的出现,最初也是为了服务于这些需要限制糖摄入的人群。
然而,随着糖尿病逐渐流行,关于其病因的争论也日益激烈。最初,许多欧洲和美国的权威医生都认为,糖消费的增加与糖尿病的流行有直接关系。 他们观察到,富裕阶层和食糖量大的族群糖尿病发病率更高。
关键的错误转向:乔斯林与希姆斯沃斯的理论。 这一观念的转变主要归功于两位极具影响力的糖尿病专家:美国的艾略特·乔斯林(Elliott Joslin)和英国的哈罗德·希姆斯沃斯(Harold Himsworth)。 1. 乔斯林:作为美国糖尿病领域的泰斗,他的观点几乎被奉为圣经。他错误地认为所有碳水化合物(无论是糖还是淀粉)对人体的影响都一样。他以日本人为例,认为他们以米饭为主食(高碳水化合物)但糖尿病发病率低,因此得出结论: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不会导致糖尿病。这个论证的致命缺陷在于,他忽略了当时日本人饮食中的糖含量极低。最终,乔斯林将糖尿病的罪魁祸首归咎于肥胖和膳食脂肪。 2. 希姆斯沃斯:他进一步发展了脂肪致病论,认为高脂肪饮食会导致糖尿病。
这两位权威人物相互引用对方的研究,构建了一个看似坚固但实际上是错误的理论体系。他们的观点通过教科书和学术文章广泛传播,最终使“糖不导致糖尿病,脂肪才是元凶”的观念成为医学界的正统。
本章的结论是,由于早期科学工具的局限性、对内分泌学知识的缺乏,以及少数权威人物基于错误假设和不完整证据所做的影响力巨大的论断,科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错失了识别糖作为慢性病主要诱因的机会。这种错误的科学共识不仅为糖业的扩张铺平了道路,也为未来几十年的公共卫生灾难埋下了伏笔。
第六章 持续赠予的礼物
本章深入剖析了两个在20世纪深入人心的营养学观念,它们不仅塑造了我们对健康饮食的认知,也成为了糖业巨头用以自卫、对抗所有指控其产品有害的“持续赠予的礼物”。
第一大支柱:膳食脂肪是万病之源。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60年代之后,营养学界逐渐形成共识,认为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是导致心脏病、肥胖、癌症等现代慢性疾病的主要元凶。这一观念源于观察到随着社会富裕和西化,人们的脂肪摄入量增加,慢性病发病率也随之上升。然而,这一理论忽略了许多反例,例如:某些高脂肪饮食的群体(如因纽特人、马赛人)在未西化时非常健康;以及法国人高脂肪饮食但心脏病发病率低的“法国悖论”。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经历西化过程的群体,无论脂肪摄入量如何变化,其糖的消费量都无一例外地急剧增加。但由于脂肪有害论已占据主导地位,糖作为嫌疑犯被轻易放过了。
第二大支柱(糖业的终极护身符):肥胖源于“能量失衡”。 这个观念,即著名的“卡路里摄入多于卡路里消耗”(calories-in/calories-out)模型,认为肥胖的唯一原因是吃得太多、动得太少。它将肥胖视为一种行为失当(贪食和懒惰)而非生理失调。
- “卡路里即卡路里”的谬误:这种思想认为,一卡路里的糖和一卡路里的西兰花对体重的影响是相同的,完全忽略了不同宏量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对人体新陈代谢和激素(尤其是胰岛素)的截然不同的影响。
- 糖业的完美辩词:这一理论对糖业来说是天赐之礼。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糖本身并不致胖,问题在于消费者摄入了过多的总热量。他们甚至反过来宣传糖有助于减肥,因为糖能“快速满足食欲”,从而“防止暴饮暴食”。
被遗忘的欧洲智慧:肥胖是激素失调。 在“能量失衡”理论在美国成为教条的同时,二战前的德奥临床研究学派早已提出,肥胖是一种激素调节障碍。他们认为,肥胖者的脂肪组织有一种“内在的囤积脂肪的倾向”,它们会“贪婪地”从血液中攫取能量并储存起来,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能量不足,从而引发饥饿和疲倦。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吃多而变胖,而是因为身体内在的变胖过程让我们感到饥饿而去吃多。 可惜的是,随着二战的爆发,这一深刻的见解连同其背后的科学思想一同被历史的尘埃掩埋。
内分泌学的革命与被忽视的真相。 1960年放射免疫分析法的发明,使得精确测量血液中的激素水平成为可能,内分泌学迎来了革命。罗莎琳·耶洛和所罗门·伯森的研究揭示了两个颠覆性的事实:
- 胰岛素是主要的“脂肪生成”激素:它命令脂肪细胞储存脂肪,并阻止其分解。只有当胰岛素水平下降时,脂肪才能被释放和燃烧。
- 2型糖尿病和肥胖者并非缺乏胰岛素,而是体内胰岛素水平过高(高胰岛素血症),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对胰岛素产生了抵抗(胰岛素抵抗)。
这一发现直接指向了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 这很可能就是肥胖和糖尿病的共同根源。最合理的推测是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糖,因为它们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主要因素。
然而,已经深陷“能量失衡”思维的美国主流研究界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一可能性。他们宁愿相信是肥胖本身导致了胰岛素抵抗,从而维护了“卡路里即卡路里”的教条,将肥胖的原因继续归咎于个人的意志力薄弱。
这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看似科学却极其天真的“能量失衡”观念,成为了糖业及其产品(如可口可乐)最坚实的保护伞,使它们得以在引发全球健康危机的同时,始终将责任推给消费者。
第七章 糖业巨头
本章揭示了糖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从20世纪20年代起,如何通过公关、广告和资助科研等手段,系统性地应对公众对其产品健康危害的担忧,并成功塑造了社会对糖的认知。
早期的行业自卫。 1928年,为应对市场供过于求和恶性竞争,糖业成立了第一个行业协会——糖业研究所(The Sugar Institute)。其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广告向公众宣传糖是一种健康食品,能“补充能量、对抗感冒”。然而,该组织因涉嫌价格垄断于1936年被解散。
二战期间的形象危机与对策。 二战期间,由于营养科学的进步,人们开始认识到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性。糖因不含这些营养素而被贴上了“空热量”的标签,甚至被政府和美国医学会视为“最糟糕的食物”。为了应对这种“反糖宣传”,糖业于1943年成立了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糖业研究基金会(SRF),后更名为糖业协会(SAI)。其明确目标是“捍卫糖作为一种食品”,并资助“有利于”糖的研究,以扭转公众的负面印象。
糖业协会的多线作战。 糖业协会投入巨资,在顶尖学术机构(如哈佛、麻省理工)资助科研项目,并与一些著名营养学家建立了长期“友谊”。其公关策略主要集中在两个战场:
- 对抗蛀牙指控:面对糖导致蛀牙的铁证,糖业协会的策略并非否认,而是模糊焦点。他们资助研究,试图证明其他碳水化合物(如淀粉)也同样致龋,从而得出结论:问题不在于糖本身,而在于所有碳水化合物,因此单独限制糖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转而提倡通过刷牙等其他方式来预防蛀牙,而不是减少糖的摄入。
-
对抗肥胖指控:20世纪50年代,随着减肥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潮流,糖业面临巨大威胁。他们发起了大规模的广告攻势,巧妙地利用了当时流行的营养学理论:
- 利用“卡路里即卡路里”理论:广告宣称“没有所谓的‘致胖食物’”,所有食物都提供热量,来自糖的热量和来自牛排或葡萄柚的热量没有区别。
- 利用“血糖假说”:他们宣传糖能快速升高血糖,从而“迅速满足食欲”,并以此逻辑声称在饭前吃点甜食可以“帮助你少吃”,是一种有效的减肥工具。
对人工甜味剂的致命打击。 20世纪60年代,随着无糖和低糖产品(使用糖精和甜蜜素)的流行,糖业的市场份额受到严重威胁。糖业对此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策略:资助研究以寻找人工甜味剂有害的证据,从而迫使FDA将其封杀。
- 策略:他们利用了1958年通过的《食品添加剂修正案》中的“德莱尼条款”,该条款规定任何被发现能在动物或人身上诱发癌症的添加剂都必须被禁用。
- 行动:糖业协会投入巨额资金,资助了一些研究机构专门寻找甜蜜素和糖精的健康危害。这些研究使用极大剂量的甜味剂喂养老鼠,最终“成功地”诱发了膀胱癌。
- 结果:尽管这种剂量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达到(相当于每天喝550罐无糖汽水),但根据德莱尼条款,FDA在1970年全面禁止了甜蜜素。糖精也险些被禁,虽最终得以保留,但其声誉已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
一位糖业高管后来毫不讳言地将这一策略形容为:“如果你的对手能以十分之一的成本与你竞争,你最好找块砖头砸向他。”通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糖业不仅成功地捍卫了自身产品的市场地位,还通过“科学”和法律手段,打击了竞争对手,深刻地影响了接下来几十年的公共卫生政策和消费者选择。
第八章 为糖辩护
本章详细叙述了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当科学界对糖的危害提出严峻挑战时,糖业如何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关和科学战,成功地扭转了局势,将糖从被告席上解救出来,并为之后几十年的糖消费量飙升铺平了道路。
糖面临的新挑战。 到了60年代,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糖与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直接联系起来。英国著名营养学家约翰·尤德金(John Yudkin)成为这场“反糖战争”的旗手。他基于流行病学和生化研究提出,糖而非脂肪,才是导致这些“文明病”的元凶。与此同时,美国的消费者运动兴起,要求FDA重新审查被“普遍认为安全”(GRAS)的食品添加剂,糖也名列其中。
糖业协会的全面反击。 面对生死存亡的威胁,糖业协会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
- 攻击批评者,塑造“伪科学”形象:糖业协会主席约翰·塔特姆将尤德金等批评者斥为“兜售营养垃圾的骗子”和“利用戈培尔‘弥天大谎’技巧的投机者”。他们努力将反糖理论描绘成没有科学根据的“伪科学”。
- 利用并巩固“脂肪有害论”:糖业协会最大的盟友,就是当时日益盛行的“膳食脂肪导致心脏病”假说。该假说的主要推动者是营养学家安塞尔·基斯(Ancel Keys),他与糖业协会有着长期的资金往来。基斯公开抨击尤德金的理论是“一堆废话”。由于科学界和公众的注意力都被引向了脂肪,对糖的怀疑自然就被边缘化了。
- 组建“科学”顾问团:糖业协会成立了“食品与营养咨询委员会(FNAC)”,招募了一批与行业关系密切的“权威”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学营养系主任弗雷德·斯泰尔(Fred Stare)。斯泰尔的院系长期接受糖业、糖果协会和可口可乐等公司的资助。他利用哈佛的声望,在各种场合为糖辩护,声称“糖导致不健康的说法连边都沾不上”。
- 发布“权威”报告,混淆视听:在糖业协会的资助和组织下,这个顾问团撰写了一份名为《人类饮食中的糖》的白皮书,系统性地反驳了所有对糖的指控。这份报告被广泛分发给媒体和政府官员,并刻意隐瞒了其行业背景,以“独立科学”的面目出现。
FDA的“盖棺定论”。 这场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来自于FDA。1976年,FDA对糖的GRAS(普遍认为安全)身份进行了审查。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乔治·欧文恰好是国际糖业研究基金会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大量引用了糖业协会的白皮书和其资助的科学家的观点,最终得出结论:除了蛀牙外,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糖在当时的消费水平下对公众构成危害。
一场公关的巨大胜利。 FDA的这份报告被糖业协会奉为“科学圣经”,并以此为武器,大肆宣传“糖是安全的!”。他们宣称“科学家消除了对糖的恐惧”,并将所有对糖的批评都打上了“营养骗子”的标签。
尽管仍有科学家(如美国农业部的研究人员)不断提出警告,认为糖对相当一部分人群是危险的,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糖业通过这场成功的“防御战”,不仅赢得了生存空间,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营养政策和公众认知。这场胜利的后果是,关于糖的真正危害的研究被推迟了至少二十年,而在此期间,糖的消费量达到了历史新高,肥胖和糖尿病的流行也随之进入了失控状态。
第九章 他们所不知道的
本章探讨了科学研究的局限性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证据,这些证据本应颠覆对糖的“无害”结论,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营养学界所忽视。
科学的困境:假设与检验。 营养科学,尤其是关于慢性病的研究,面临一个巨大挑战:耗时极长且成本高昂。要明确证实某种食物(如脂肪或糖)是否导致需要数十年才会显现的疾病(如心脏病),需要进行规模庞大、持续多年的临床试验,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因此,公共卫生政策常常基于不完整的证据和“信念的飞跃”。例如,美国政府推广低脂饮食的建议,就是基于一些间接且模棱两可的研究,后来的大规模试验证明这种饮食并无益处,但已形成的教条却难以改变。
80年代前的科学共识与盲点。 在1986年FDA宣布糖“安全”时,主流科学界普遍接受了以下观念:
- 肥胖是由总热量过剩引起的(“卡路里即卡路里”)。
- 糖尿病是由肥胖引起的。
- 心脏病是由膳食脂肪(特别是饱和脂肪)引起的。
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因为当时的科学家不知道或忽略了糖在体内的独特代谢途径及其对激素的深远影响。他们认为,一卡路里的糖和一卡路里的其他碳水化合物没有本质区别。
被揭示的真相:果糖的独特代谢。 到了80年代,生化学家已经清楚地揭示了蔗糖(由一个葡萄糖和一个果糖分子构成)的代谢真相:
- 葡萄糖:可以被身体几乎所有细胞直接利用作为能量。
- 果糖:几乎完全在肝脏中代谢。其代谢途径缺乏有效的反馈抑制机制,极易转化为脂肪(特别是甘油三酯和饱和脂肪酸)。
这意味着,摄入糖会直接导致肝脏生产更多的脂肪,这就是所谓的“果糖诱导的脂肪生成”。这解释了为什么高糖饮食会导致血液中甘油三酯水平升高——这是心脏病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新概念的出现:代谢综合征与胰岛素抵抗。
- 代谢综合征:斯坦福大学内分泌学家杰拉尔德·里文(Gerald Reaven)在80年代末提出了“X综合征”(后称代谢综合征)的概念。他指出,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疾病——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高血压、高甘油三酯、低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和2型糖尿病——实际上都源于一个共同的根源:胰岛素抵抗和随之而来的高胰岛素血症。
- 果糖与胰岛素抵抗:研究人员很快发现,在实验室中诱导大鼠产生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给它们喂食大量的果糖或糖。
新的关联:脂肪肝。 与此同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病例急剧增加,甚至出现在儿童和婴儿身上。研究表明,脂肪肝与代谢综合征和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很多科学家现在认为,肝脏中的脂肪堆积可能是导致全身胰岛素抵抗的始作俑者。而正如前述,果糖是导致肝脏脂肪堆积的主要膳食因素。
高果糖玉米糖浆(HFCS)的登场。 恰在此时,HFCS开始大量替代蔗糖进入食品供应,尤其是在软饮料中。由于其代谢特性与蔗糖几乎相同(都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它的普及进一步推高了总糖消费量,与肥胖和糖尿病的流行浪潮完美重合。
本章的结论是,在主流营养学界宣布糖无害之后,生化学和内分泌学领域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揭示了糖(特别是其中的果糖成分)如何通过在肝脏中转化为脂肪,从而引发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进而导致一系列慢性疾病。然而,这些“他们所不知道的”或者说“他们选择忽略的”知识,并没有及时改变公共卫生政策,使得人们在错误的饮食建议指导下,继续走向更深的健康危机。
第十章 “如果/那么”问题:一
本章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亚利桑那州皮马印第安人(Pima Indians)的经历,生动地展示了糖尿病如何在短短几代人之间从一种罕见病演变为一场灾难性的流行病。这个案例为我们理解全球范围内糖尿病和肥胖的爆发提供了关键线索。
皮马人的悲剧:从健康到病态的快速转变。
- 历史上的健康: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包括著名糖尿病专家艾略特·乔斯林在内的多项调查都显示,皮马印第安人中的糖尿病非常罕见,与当时美国白人及其他族群的发病率相似。他们虽然贫困,但并未被视为一个特别不健康的群体。
- 二战后的巨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一个转折点。皮马人开始更多地接触现代社会,进入军队或工厂工作,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也随之“西化”。
- 流行病的爆发:到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人员偶然到访皮马人保留地时,他们惊骇地发现,超过30%的成年人血糖水平达到糖尿病标准,50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更是高达50%。这成为当时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高的糖尿病发病率。随之而来的是肥胖症的普遍化,以及糖尿病各种严重并发症(肾衰竭、失明、截肢等)的出现。
探寻原因:三大因素的合力。 NIH的研究人员在皮马人中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深入研究,试图解开这场健康灾难之谜。他们发现,这背后是三个关键因素的共同作用:
- 环境的剧变——饮食西化:皮马人的传统饮食被现代西方饮食所取代,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糖和精制面粉的消费量急剧增加。政府发放的配给品,以及商店里随处可见的软饮料和甜食,使糖成为他们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印证了南非医生乔治·坎贝尔的观察:当一个群体的糖消费量超过某个阈值(约每年70磅)后,糖尿病便开始流行。
- 基因的易感性:研究人员推测,皮马人可能拥有所谓的“节俭基因”(Thrifty Gene),这种基因在食物匮乏的年代有助于储存能量,但在食物(尤其是糖)充足的现代环境中,反而使他们极易患上肥胖和糖尿病。然而,考虑到全球许多不同基因背景的族群在西化后都出现了类似的流行病,这一解释可能并不全面。更可能的解释是,他们适应高糖饮食的时间最短,因此受到的冲击最大。
-
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子宫内环境:这是最令人警醒的发现。NIH的研究表明:
- 患有糖尿病的母亲,其子女在青少年时期肥胖的风险是健康母亲子女的三倍以上。
- 患有糖尿病的母亲,其子女在25岁前患上糖尿病的风险是健康母亲子女的三十倍以上。
这种现象被称为“围产期代谢编程”或“代谢印记”。当怀孕的母亲患有糖尿病或胰岛素抵抗时,其血液中过高的血糖会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这个高糖的子宫环境会“编程”胎儿的新陈代谢系统,使其天生就更容易肥胖和患上糖尿病。
恶性循环的启动。 这就形成了一个代际相传、不断放大的恶性循环:西化饮食导致第一代人出现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 -> 患病的母亲通过子宫环境将易感性传给下一代 -> 下一代在更年轻时就发病,并接着将这种更强的易感性传给第三代……如此往复,使得流行病在短短几代人内就呈爆炸式增长。
皮马人的故事是一个微缩模型,它揭示了全球肥胖与糖尿病大流行的可能机制。它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最初启动这个恶性循环的扳机是什么? 尽管主流观点仍试图将责任归咎于肥胖本身或总热量,但皮马人的经历强烈地暗示,那个最初的、根本性的诱因,很可能就是饮食中急剧增加的糖。
第十一章 “如果/那么”问题:二
本章提出了一个统合性的假说,试图解释为何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慢性病——即“西方疾病”——会聚集性地在采用西方生活方式的人群中出现。作者认为,这些疾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享一个共同的根源。
“西方疾病”的概念。 英国医生丹尼斯·伯基特和休·特罗韦尔在观察了非洲等地的土著居民后,发现在他们接受西化生活方式之前,许多在欧美常见的慢性病,如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多种癌症、胆结石、痛风、阑尾炎等,都极为罕见。这些疾病随着西化进程而出现,因此被称为“西方疾病”。
奥卡姆剃刀原则:寻找单一的根本原因。 伯基特指出,当一系列疾病在同一个群体中同时出现时,最合理的科学假设是它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致病因素。就像吸烟会导致肺癌、支气管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一样,一个单一的环境或饮食因素,也可能根据个体的基因差异和暴露时间长短,引发不同的“西方疾病”。
本书的核心假说:“如果/那么”逻辑。 作者基于此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
- 如果(IF):我们观察到,绝大多数“西方疾病”都与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例如,肥胖、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痛风、癌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普遍存在胰岛素抵抗)。
- 那么(THEN):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的那个因素,很可能就是所有这些“西方疾病”的根本膳食诱因。
结合前几章的论证,作者明确指出,这个根本诱因就是糖(蔗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
糖如何引发一系列西方疾病? 本章随后逐一检视了几种主要的西方疾病,论证它们如何通过胰岛素抵抗这一共同通路与糖联系起来:
- 痛风:传统上认为痛风由过多摄入肉类和酒精引起。但现代研究发现,痛风与代谢综合征紧密相关。生化研究明确证实,糖中的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直接产生大量尿酸——痛风的直接致病物质。同时,高胰岛素水平也会减少肾脏对尿酸的排泄。因此,糖从生产和排泄两个环节增加了体内的尿酸。
- 高血压:传统观点归咎于盐。但大量试验证明,限盐对降压效果甚微。相反,胰岛素有明确的生理作用,即促使肾脏保留钠和水分,从而升高血压。此外,果糖代谢产生的尿酸也会损伤肾脏血管,导致血压升高。因此,由糖引起的胰岛素抵抗和高尿酸血症,是高血压的有力致病机制。
- 癌症:癌症的发病率也呈现出典型的“西方疾病”模式。现代癌症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是,肥胖和糖尿病是多种癌症的强烈风险因素。其生物学联系在于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这两种激素是强效的细胞生长促进剂。胰岛素抵抗导致的高胰岛素和高血糖环境,为癌细胞的生长和繁殖提供了完美的“燃料”和“信号”,如同给癌症火上浇油。一些顶尖癌症研究者因此认为,糖的摄入直接推动了癌症的发展。
- 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这种病常被称为“3型糖尿病”。糖尿病患者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加倍。其联系可能在于:大脑功能依赖于正常的胰岛素信号,而胰岛素抵抗会破坏这种信号;同时,糖尿病和高血压会造成脑部血管损伤(微小中风),这会大大加速痴呆的进程。
结论。 本章总结道,将肥胖、糖尿病、心脏病、痛风、高血压、癌症、老年痴呆等一系列“西方疾病”视为由不同原因(吃太多、吃太咸、吃太油等)导致的孤立病症,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看法。一个更简单、也更可能正确的解释是:它们都是由糖驱动的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这同一棵“病根”上长出的不同“毒果”。因此,糖才是这些现代流行病的共同元凶。
结语:多“少”才算过量?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探讨了一个最实际也最困难的问题:如果我们认定糖是有害的,那么安全的摄入量是多少?多“少”才算过量?
答案是:我们不可能知道。 原因如下:
- “适度”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 建议人们“适度”摄入糖,就像建议吸烟者“适度”吸烟一样,是一个循环论证。我们只有在出现肥胖或疾病时,才知道自己摄入了“过量”,但那时往往为时已晚。对于一个可能具有成瘾性的物质,“适度”可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完全不吃比“只吃一点”要容易得多。
- 伤害的滞后性。 糖的危害是慢性的,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会显现。在症状出现之前,我们无法判断当前的摄入量是否已经“过量”。
- 代际遗传效应。 正如皮马印第安人的例子所展示的,母亲在怀孕期间的代谢状态会“编程”下一代的健康。这意味着,一个在高糖环境中生活了几代人的群体,其对糖的耐受度和反应可能已经与祖先完全不同。安全阈值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低。
一个思想实验。 作者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个从未接触过精制糖的人群,将其分为两组,一组继续无糖生活,另一组开始摄入不断增加的糖。几代人之后,他们的健康状况、疾病谱和寿命会相同吗?作者的答案是,高糖人群的慢性病负担将远超无糖人群。
这个实验揭示了我们当前的困境:我们已经没有一个健康的、无糖的参照系了。 我们所谓的“正常衰老”过程——体重增加、血压升高、血糖控制变差——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由全民高糖饮食造成的病理状态。
现实中的研究困境。 即使我们现在想通过科学实验来找到答案,也极其困难。因为糖在现代加工食品中无处不在,要进行一个严格的“无糖”饮食干预,几乎等同于要求受试者放弃所有加工食品。如果他们因此变得更健康,我们无法确定这究竟是戒糖的功劳,还是因为他们同时戒掉了其他添加剂、精制谷物等。
关于人工甜味剂。 人们用人工甜味剂来替代糖,但这是否是一个好的选择,科学上仍无定论。虽然它们可能没有糖那样的直接代谢危害,但其长期影响仍是未知的。不过,作者认为,与摄入糖相比,使用人工甜味剂作为戒糖的过渡手段,其风险可能要小得多。
最后的建议:亲身去体验。 鉴于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和等待明确答案的漫长过程,作者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将糖视为一种极有可能有害的物质,并据此做出明智的个人选择。他将戒糖比作戒烟:在真正戒掉之前,你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会是怎样。最初可能会有挣扎,但最终,你会达到一个不再渴望它的境界,并开始质疑当初为何如此依赖它。
最终,要回答“多‘少’才算过量?”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或许不是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科学“标准答案”,而是亲自尝试过一种没有糖的生活,去感受它给身体带来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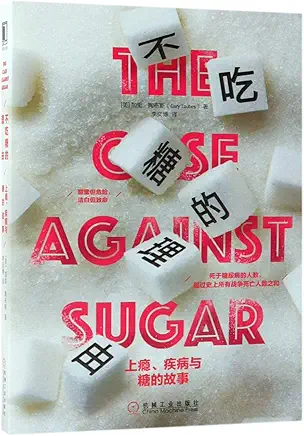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

